关于文本分析的层次
孙绍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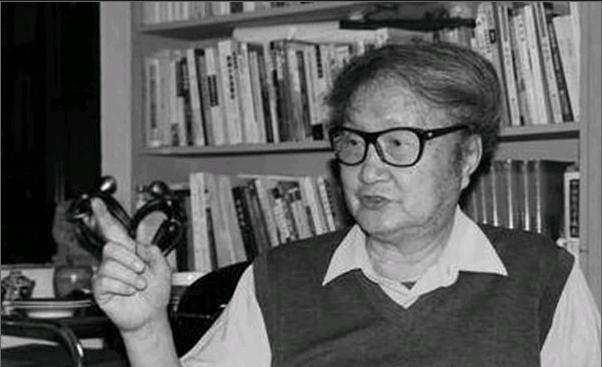


许多文本分析之所以无效,原因在于,空谈分析,实际上根本没有进入分析这一层次。分析的对象是文本的矛盾,而许多无效分析,恰恰停留在文本和外部对象的统一性上。如认为《荷塘月色》反映了大革命失败后知识分子的苦闷,“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惟妙惟肖地反映了美好的“景色”。这从哲学上说,是机械反映论。就是那些注意到文本和外部对象的矛盾的分析文章,也往往把文本当做一个绝对的统一体。如认为《再别康桥》表现了诗人内心的离愁别绪,等等。其实这首经典诗作表现的矛盾很明显:一方面是激动——“满载一船星辉,在星辉斑斓里放歌”,一方面又是不能放歌——“沉默是今晚的康桥”。一方面是和康桥再别,一方面又是和云彩告别。文本分析的无效之所以成为一种顽症,就是因为文本内在的矛盾成为盲点。许多致力于文本分析的学者,满足于为复杂的文本寻找一个原因,单层次的思维模式就这样流毒天下。这不能笼统地怪罪中学和大学教师,而应该怪罪我们这些研究理论的。要进行具体分析,如果没有一定的方法论的自觉,则无从下手。在面对文学经典时,这种困难就更为突出。因为文学形象天衣无缝、水乳交融,一些在方法论上不坚定的老师,在无从下手之时,就妥协了,就不是进行分析,而是沉溺于赞叹了。正是出于这种考虑,本文把可操作性和操作性的系统化作为最高目标,但愿能对把具体分析落实到文本分析的系统工程上,有所助益。
第一,艺术感觉的还原。
唐人贺知章的绝句《咏柳》,从写出来到如今一千多年了,仍然家喻户晓,脍炙人口。原因何在?表面上看这是个小儿科的问题,但是,要真正把它讲清楚,不但对中学教师,而且对大学权威教授,也一点都不轻松。有一位权威教授写了一篇《咏柳赏析》,说“碧玉妆成一树高”是“总体的印象”,“万条垂下绿丝绦”是“具体”写柳丝,柳丝的“茂密”最能表现“柳树的特征”。这就是他的第一个观点:这首诗的艺术感染力,来自表现对象的特征;用理论的语言来说,就是反映柳树的真实。这个论断,表面上看,没有多大问题,但是实质上,是很离谱的。这是一首抒情诗,抒情诗以什么来动人呢?普通中学生都能不假思索地回答“以情动人”,但教授却说以反映事物的特征动人。接下去,这位教授又说,这首诗的最后一句“二月春风似剪刀”很好,好在哪里呢?好在比喻“十分巧妙”。这话当然没有错。但是,这并不需要你讲,读者凭直觉就能感到这个比喻不同凡响。之所以要读你的文章,就是因为感觉到了,说不清原由,想从你的文章中获得答案。而你不以理性分析比喻巧妙的原因,只是用强调的语气宣称感受的结果,这不是有“忽悠”读者之嫌吗?教授说,这首诗还有一个好处,那就是“二月春风似剪刀”一句“歌颂了创造性劳动”。这就更不堪了。前面还只是重复了人家的已知,而这里却是在制造混乱。“创造性劳动”这种意识形态性很强的话语,显然具有20世纪红色革命文学的价值观,怎么可能出现在一千多年前的贵族诗人头脑中?
为什么成天喊着具体分析的教授,到了这里却被形而上学的教条所蒙蔽呢?
这是因为他无法从天衣无缝的形象中找到分析的切入点,他的思想方法不是分析内在的差异,而是外部的统一:贺知章的柳树形象为什么动人呢?因为它反映了柳树的“特征”。客观的特征和形象是一致的,所以是动人的。从美学思想来说,美就是真,美的价值就是对真的认识。从方法论上来说,就是寻求美与真的统一。美是对真的认识,认识世界是为了改造世界,这就是教化。不是政治教化,就是道德教化。既然从《咏柳》无法找到政治教化,就肯定有道德教化。于是“创造性劳动”就脱口而出了。这种贴标签的做法,可以说是对具体分析的践踏。
其实,所谓分析就是要把原本统一的对象加以剖析,根本就不应该从统一性出发,而应该从差异性或者矛盾性出发。艺术之所以成为艺术,就是因为它不是等同于生活,而是诗人的情感特征与对象的特征的猝然遇合,这种遇合不是现实的,而是虚拟的、假定的、想象的。应该从真与假的矛盾入手分析这首诗。例如,明明柳树不是玉的,偏偏要说是碧玉的,明明不是丝织品,偏偏要说是丝织的飘带。为什么要用贵重的玉和丝来假定呢?为了美化,来诗化、表达诗人的感情,而不是为了反映柳树的特征。
但这样的矛盾,并不是直接的呈现,恰恰相反,是隐性的。在诗中,真实与假定是水乳交融,以逼真的形态出现的。要进行分析,是我们共同的愿望,但如果不把假定性揭示出来,分析就成了一句空话。分析之所以是分析,就是要把原本统一的成分,分化出不同的成分。不分化,分析就没有对象,只能沉迷于统一的表面。要把分析的愿望落到实处,就得有一种可操作的方法。我提出使用“还原”的方法。面对形象,在想象中,把那未经作家情感同化、未经假定的原生的形态,想象出来。这是凭着经验就能进行的。比如,柳树明明不是碧玉,却要说它是玉的,不是丝织品,却要说它是丝的。这个矛盾就显示出来了。这就是借助想象,让柳树的特征转化为情感的特征。情感的特征是什么呢?再用“还原”法。柳树很美。在大自然中,是春天来了,温度升高了,湿度变大了,柳树的遗传基因起作用了,才有柳树的美。在科学理性中,柳树的美是大自然的现象,是自然而然的。但诗人的情感很激动,断言柳树的美,比之自然的美还要美,应该是有心设计的,所谓天工加上人美才能理由充分。这就是诗人情感的强化,这就是以情动人。
对于“二月春风似剪刀”,不能大而化之地说“比喻十分巧妙”,而应该分析其中的矛盾。首先,这个比喻中最大的矛盾,就是春风和剪刀。本来,春风是柔和的,怎么会像剪刀一样锋利?冬天的风才是尖利的。但是,我们可以替这位教授解释,因为这是“二月春风”,春寒料峭。但是,我们还可以反问:为什么一定要是剪刀呢?刀锋多得很啊,例如菜刀、军刀。如果说“二月春风似菜刀”“二月春风似军刀”,就是笑话了。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前面有“不知细叶谁裁出”一句话,里边有一个“裁”字,和后面的“剪”字,形成“剪裁”这个词组。这是汉语特有的结构,是固定的自动化的联想。
当然,“还原”方法作为哲学方法并不是我的发明,在西方现象学中早已有了。在现象学看来,一切经过陈述的现象都是主观的,是观念化、价值化了的,因而要进行自由的研究,就得把它“悬搁”起来,在想象中“去蔽”,把它的原生状态“还原”出来。当然,这种原生状态,是不是就那么客观、那么价值中立,也是很有疑问的,但是,多多少少可以摆脱流行和权威观念的先入为主。我的“还原”,在对原生状态的想象上,和现象学是一致的,但我的“还原”只是为了把原生状态和形象之间的差异揭示出来,从而构成矛盾,然后加以分析,并不是为了“去蔽”。当然,这样“还原”的局限是偏重于形而下的操作,但是,很可能,优点也是在这里。当我面对一切违背这种方法的方法的时候,不管它有多么大的权威,我总是坚定地冲击,甚至毫不留情地颠覆。要理解艺术,不能被动地接受,“还原”了,有了矛盾,就可能进入分析,就主动了。朱自清在《荷塘月色》中创造了一种宁静、幽雅、孤寂的境界,但清华园一角并不完全是寂静的世界;相反,喧闹的声音也同样存在,不过给朱先生排除了。一般作家总是偷偷摸摸地、静悄悄地排除与他的感知、情感不相通的东西,并不作任何声明,他们总把自己创造的形象当做客观对象的翻版奉献给读者。但朱先生在《荷塘月色》中却不同,他很坦率地告诉读者:“这时候最热闹的,要数树上的蝉声与水里的蛙声;但热闹是它们的,我什么也没有。”这里,透露了重要的艺术创造原则:作家对于自己感知取向以外的世界是断然排斥的。许多论者对此不甚明白,或不能自觉掌握,因而几乎没有一个分析《荷塘月色》的评论家充分估计到这句话的重要意义。忽略了这句话,也就失去了分析的切入口,也就看不出《荷塘月色》不过是朱先生在以心灵同化清华园一角的宁静景观的同时,又排除了其喧闹的氛围而已。忽略了这个矛盾,分析就无从进行,就不能不蜕化为印象式的赞叹。endprint
第二,多种形式的比较。
要寻求分析的切入口,有许多途径,“还原”并非唯一的法门。最方便的当然是作家创造过程中的修改稿。鲁迅曾经说:“凡是已有定评的大作家,他的作品,全部就说明着‘应该怎样写。只是读者很不容易看出,也就不能领悟。因为在学习者一方面,是必须知道了‘不应该那么写,这才会明白原来‘应该这么写的。这‘不应该那么写,如何知道呢?惠列赛耶夫的《果戈理研究》第六章里,答复着这问题——‘应该这么写,必须从大作家们的完成了的作品去领会。那么,不应该那么写这一面,恐怕最好是从那同一作品的未定稿本去学习了。在这里,简直好像艺术家在对我们用实物教授。恰如他指着每一行,直接对我们这样说——“你看——哪,这是应该删去的。这要缩短,这要改作,因为不自然了。在这里,还得加些渲染,使形象更加显豁些。”(《且介亭杂文二集·不应该那么写》)在我国古典诗话中,类似“春风又绿江南岸”的例子不胜枚举。孟浩然《过故人庄》的最后一句是“还来就菊花”,杨慎阅读的本子恰恰“就”字脱落了,他自己也是诗人,试补了“对菊花”“傍菊花”,都不如“就菊花”。毛泽东的《采桑子·重阳》中最后一句,原来的手稿是“但看黄华不用伤”,后来定稿是“寥廓江天万里霜”。
值得一提的是托尔斯泰曾多次对《复活》进行修改。在写到聂赫留朵夫第一次到监狱中去探望沦为妓女的玛丝洛娃,哭着恳求她宽恕,并且向她求婚时,在原来的稿子上,玛丝洛娃一下子认出他来,立刻非常粗暴地拒绝了他,说:“您滚出去!那时我恳求过您,而现在也求您……如今,我不配做您的,也不配做任何人的妻子。”后来在第五份手稿中,改成玛丝洛娃并没有一下子认出自己往日的情人,但是她仍然很高兴有人来看她,特别是衣着体面的人。在认出了他以后,对于他的求婚,她根本没有听到心里去,很轻率地回答道:“您说的全是蠢话……您找不到比我更好的女人吗?您最好别露出声色,给我一点钱。这儿既没有茶喝,也没有香烟,而我是不能没有烟吸的……这儿的看守长是个骗子,别白花钱。”相比之下,原来的手稿显然很粗糙。玛丝洛娃原本是纯情少女,由于受了聂赫留朵夫的诱惑而被主人驱逐,到城市后沦落为妓女。在原来的手稿中,写她一下子认出了往日的情人,往日的记忆全部唤醒了,并且把所有的痛苦和仇恨都发泄了出来。然而在后来的修改稿中,托尔斯泰把玛丝洛娃的感知、记忆、情感立体化了:首先,她没有一下子认出他来,说明分离日久,也说明往日的记忆深藏在情感深处,痛苦不在表层。其次,最活跃的情绪是眼下的职业习惯,见了陌生男人,只要是有钱的,便高兴起来,连对求婚这样的大事都听不到心里去,这正说明心灵扭曲之深和妓女职业对心灵的毒化之深,即使往日的情人流着泪向她求婚,她也仍然把他当做一个顾客,最本能的反应是先利用他一下,弄点钱买烟抽。说到不要向看守长白花钱时,居然哈哈大笑起来,为自己的聪明而得意非凡。这更显示了玛丝洛娃的表层心理结构完完全全地妓女化了、板结了,因为在这样重大的意外事件的冲击下,它也依然密不透风,可见这些年来她心灵痛苦之深。定稿中的“哈哈大笑”,之所以比初稿中的严词斥责精彩,就是因为更加深刻地显示了她心理结构的化石化,读者记忆中那个年轻美丽、天真纯情的心灵被埋葬得如此之深,其精神似乎完全死亡了。一般读者光是读定稿中的文字,虽然凭着直觉也可以感受到托尔斯泰笔力的不凡,但是却很难说出深刻在何处。一旦和原稿加以对比,平面性的描述和立体性的刻画,其高下、其奥妙就一目了然了。
凭借文学大师的修改稿进入分析,自然是一条捷径,非常可惜的是这样的资料凤毛麟角。但是它们如此有吸引力,以至于人们很难完全放弃。于是许多经典评论家往往采取间接的办法,例如莱辛在他的名著《拉奥孔》中评希腊著名雕塑“拉奥孔”时,创造了一种办法,那就是从相同内容、不同形式的作品中寻求对比。拉奥孔父子被蛇缠死的故事,在维吉尔的史诗中被描写得很惨烈,他们发出了公牛一样的吼声,震响了天宇。可是在雕塑中,拉奥孔并没有张大嘴巴声嘶力竭地吼叫,相反,只是如轻轻叹息一般,在自我抑制中挣扎。莱辛由此得出结论说,由于雕塑是诉诸视觉的,如果嘴巴张得太大,远看起来必然像个黑洞,那是不美的,而用尽全部生命去吼叫,在史诗中却是很美的,因为诗是语言的艺术,并不直接诉诸视觉,而是诉诸读者的想象和经验的回忆。莱辛给了后代评论家以深刻的启示:在雕塑中行不通的,在史诗中却非常成功。只有明白了雕塑中不应该做什么,才会真正懂得雕塑中应该做什么,用评论的术语说,就是只有把握了一种艺术形式的局限性,才能理解它的优越性。对比同题材而不同形式的艺术形象的差异,正是分析的线索。白居易的《长恨歌》和洪升的《长生殿》同样取材于唐明皇和杨贵妃的故事,但是,在诗歌里,李杨的爱情是生死不渝的,而在戏剧里,两个人却发生了严峻的冲突。联系诸多类似的现象,不难看出,在诗歌中,相爱的人,往往是心心相印的,而在戏剧里,相爱的人,则是心心相错的。在戏剧里,没有情感的错位,就没有戏剧性,没有戏可演。同样是在七月七日长生殿,李隆基与杨玉环盟誓:生生死死,永为夫妻。在诗人白居易看来这是非常浪漫的真情,而在小说家鲁迅看来,在这种对话的表层语义下,恰恰掩盖着相反的东西。郁达夫在《奇零集》中回忆鲁迅的话:“他的意思是:以玄宗之明,哪里看不破安禄山和她的关系?所以七月七日长生殿上,玄宗只以来生为约,实在心里有点厌了。……到了马嵬坡下,军士们虽说要杀她,玄宗若对她还有爱情,哪里不能保全她的生命呢?所以这时候,也许是玄宗授意军士们的。”
第三,情感逻辑的还原。
艺术家在艺术形象中表现出来的感觉不同于科学家的感觉。科学家的感觉是冷静的、客观的,追求的是普遍的共同性,而排斥个人的情感;一旦有了个人的情感色彩,就不科学了、没有意义了。可是艺术家恰恰相反,艺术感觉(或心理学的知觉)之所以艺术,就是因为它是经过个人主观情感或智性“歪曲”的。正是因为“歪曲”了,或者用我的术语来说,“变异”了,这种表面上看来比较表层的感觉才能成为深层情感乃至情结的可靠索引。有些作品,尤其是一些直接抒情的作品,往往并不直接诉诸感觉,这时光用感觉“还原”就不够了。例如“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好在什么地方?它并没有明确的感知变异,它的变异在它的情感逻辑之中。这时应该使用的是情感逻辑的“还原”。这几句诗说的是爱情是绝对的,在任何空间、时间,在任何生存状态,都是不变的、永恒的。爱情甚至是超越主体的生死界限的。这是诗的浪漫,其逻辑的特点是绝对化。用逻辑还原的方法,明显不符合理性逻辑。理性逻辑是客观的、冷峻的,是排斥感情色彩的,对任何事物都采取分析的态度。按理性逻辑的高级形态,即辩证逻辑,任何事物都不可能是不变的。在辩证法看来,世界上没有永恒不变的东西,一切都随时间、地点、条件而变化。把恋爱者的情感看成超越时间、地点、条件的东西是无理的,但是,这种不合理性之理,恰恰又符合强烈情感的特点。endprint
情感逻辑的特点不仅是绝对化,而且可以违反矛盾律、排中律、充足理由律。人真动了感情就常常不知是爱还是恨了,明明相爱的人偏偏叫冤家,明明爱得不要命,可见了面又像贾宝玉和林黛玉那样互相折磨。臧克家纪念鲁迅的诗说:“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这按通常的逻辑来说是绝对不通的,要避免这样的自相矛盾,就要把他省略了的成分补充出来:“有的人死了,因为他为人民的幸福而献身,因而他永远活在人民心中。”这很符合理性逻辑了,但却不是诗了。越是到现代派诗歌中,扭曲的程度越大,在小说中,情节是一种因果,一个情感原因导致层层放大的结果,按理性逻辑来说,理由必须充分,这叫充足理由律。可是在情感方面充足了,在理性方面则不可能充足。说贾宝玉因为林黛玉反抗封建秩序,思想一致才爱她,理由这么清楚,却一点感情也没有了。在现代派小说中,恰恰有反逻辑因果的,如余华的《十八岁出门远行》,整个小说的情节的原因和结果都是颠倒的,似乎是无理的。情节的发展好像和逻辑因果开玩笑,反因果性非常明显。例如,主人公以敬烟对司机表示善意,司机接受了善意,却引出粗暴地拒绝搭车的结果;主人公对他凶狠呵斥,他却十分友好起来。半路上,车子发动不起来了,司机本来应该很焦虑的,但他却无所谓。车上的苹果让人家给抢了,本该引发愤怒和保卫的冲动,司机却无动于衷。仔细研读,你会发现,在表面上绝对无理的情节中,包含着一种深邃的道理:这篇小说,有时很写实,有时又自由地、突然地滑向极端荒诞的感觉。用传统现实主义的“细节的真实性”原则去追究,恐怕是要作出否定的评判。然而文学欣赏不能用一个尺度,特别是不能光用读者熟悉的尺度去评判作家的创造。余华之所以不写鼻子被打歪了的痛苦,那是因为他要表现人生有一种特殊状态,是感觉不到痛苦的痛苦——在鸡毛蒜皮的小事上痛苦不已,呼天抢地,而在性命交关的大事上麻木不仁。这是人生的荒谬,但人们对之习以为常,不但没有痛感,反而乐在其中。这是现实的悲剧,然而在艺术上却是喜剧。喜剧的超现实的荒诞,是一种扭曲的逻辑。然而这样的扭曲的逻辑,启发读者想起许多深刻的悖谬的现象,甚至可以说是哲学命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在这最为荒谬的现象背后潜藏着深邃的睿智——没有痛苦的痛苦是最大的痛苦。
第四,价值的还原。
价值还原是个理论问题,但得从具体的个案讲起。《儒林外史》中的“范进中举”,并不完全是吴敬梓的发明,而是他对原始真人真事改编的结果。清朝刘献廷《广阳杂记》卷四中有一段记载:明末高邮有袁体庵者,神医也。有举子举于乡,喜极发狂,笑不止。求体庵诊之。惊曰:“疾不可为矣!不以旬数矣!子宜亟归,迟恐不及也。若道过镇江,必更求何氏诊之。”遂以一书寄何。其人到镇江而疾巳愈,以书致何,何以书示其人,曰:“某公喜极而狂。喜则心窍开张而不可复合,非药石之所能治也。故动以危苦之心,惧之以死,令其忧愁抑郁,则心窍闭。至镇江当已愈矣。”其人见之,北面再拜而去。吁!亦神矣。
“吁!亦神矣。”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啊!医术真是神极了。”可以说这句话是这个小故事的主题:称赞袁医生医术高明。他没有用药物从生理上治这个病人。而是从心理方面成功地治好了他。其全部价值在于科学的实用性,而在《儒林外史》中却变成胡屠户给范进的一记耳光,重点在于出胡屠户的洋相。范进这个丈人本来极端藐视范进。可一旦范进中了举人,为了治病硬着头皮打了他一个耳光,却怕得神经反常,手关节不能自由活动。以为是天上文曲星在惩罚他,连忙讨了一张膏药贴上。这样一改。就把原来故事科学的、实用的理性价值转化为情感的非实用的审美价值了。这里不存在科学的真和艺术的美统一的问题,而是真和美的错位。如果硬要真和美完全统一,则最佳选择是把刘献廷的故事全抄进去,而那样一来,《范进中举》的喜剧美将荡然无存。把科学的实用价值搬到艺术形象中去,不是导致美的升华,而是相反,导致美的消失。
创作就是从科学的真的价值向艺术的美的价值转化。因为理性的科学价值在人类生活中占有优势,审美价值常常处于被压抑的地位。正因为这样。科学家可以在大学课堂中成批成批地培养。而艺术家却不能。
要欣赏艺术,摆脱被动,就要善于从艺术的感觉、逻辑中还原出科学的理性,从二者的矛盾中。分析出情感的审美价值。为什么李白在白帝城向江陵进发时只感到“千里江陵一日还”的速度。而感觉不到三峡礁石的凶险呢?因为他归心似箭。为什么李白觉得并不一定很轻的船很轻呢?因为他流放夜郎,“中道遇赦”,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解除政治压力后。心里感到轻松了。因而即使船再重。航程再险,他也感觉不到。这种感觉的变异和逻辑的变异成为诗人内心激情的一种索引,诗人用这种外在的、可感的、强烈的效果去推动读者想象诗人情感产生的原因。为什么阿Q在被押上刑场之时不大喊冤枉,反而为圆圈画得不圆而遗憾?按常理来还原,正是因为画了这个圆才完成判死刑的手续。通过这个还原。益发见得阿Q的麻木。阿Q越是麻木,在读者心目中越是能激发起焦虑和关注,这就是艺术感染力,这就是审美价值。如果阿Q突然叫起冤枉来。而不是叫喊“过了二十年又是一个(好汉)”,这就和常规的逻辑缩短了距离,喜剧效果就消失了。正因如此,逻辑的还原最后必须走向价值的还原。而从价值的还原中,就不难分析出真正的艺术奥秘了。
第五,历史的还原和比较。
艺术感知还原、逻辑还原和价值还原,都不过是分析艺术形式的静态的逻辑方法,属于一种入门方法。入门以后对作品的内容还得有一个历史的动态的分析,因而需要更高级的方法,这就是“历史还原”。
从理论上说。对一切对象的研究最起码的要求就是把它放到历史环境里去。不管什么样的作品,要作出深刻的分析,只是用今天的眼光去观察是不行的,必须放到产生这些作品的时代(历史)背景中去。还原到产生它的那种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艺术的气候中去。历史的还原,目的是抓住不同历史阶段中艺术倾向和追求的差异。关键是内在的艺术本身的景物、人物内心情感的进展。比如武松打虎,光从一般文学的价值准则来看。当然也可能分析出它对英雄的理解:从力量和勇气来说,武松是超人的:但是从心理上说。他又是平凡的。和一般小人物差不多。分析到这个层次,可以说已经相当有深度了。但是。如果把它放到中国古典小说对英雄人物的想象的过程中去,就可能发现,这对于早于《水浒》的《三国演义》是一个伟大的进步。在《三国演义》中。英雄人物是超人的,面临死亡和磨难是没有痛苦的,如关公刮骨疗毒。虽然医生的刀刮出声音来。但他仍然面不改色,没有武松那种活老虎打死了、死老虎却拖不动的局限。也没有类似下山以后,见了两只假老虎就惧怕的心理。endpri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