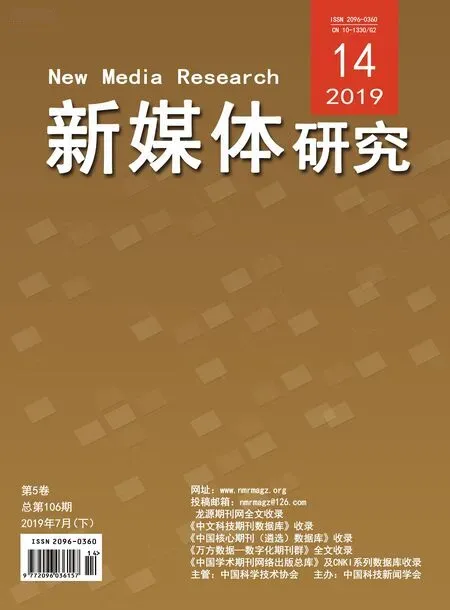错位的“媒介监督”
——浅析新闻报道中的“媒介审判”现象
蔡予乐
厦门大学经济学院,福建厦门 361003
错位的“媒介监督”
——浅析新闻报道中的“媒介审判”现象
蔡予乐
厦门大学经济学院,福建厦门 361003
本文试图更全面、客观、理性地分析论证,重新审视“媒介审判”这一特殊现象与问题。从“媒介审判”的历史沿革及相关研究入手,分析“媒介审判”在我国互联网时代爆发的现象及特点、“媒介审判”与舆论监督之间的关联、理性思考“媒介审判”等。笔者认为媒介审判是一种错位的媒介监督,应当全面理性看待“媒介审判”这一特殊现象,认清其危害,并采取相应策略防范媒介审判的出现,传播独立思考、理性分析的媒介精神。
“媒介审判”;司法;舆论;监督
1 “媒介审判”的产生
“媒介审判”又称为“新闻审判”或者“报刊审判”,作为一个新闻传播界的词汇,“媒介审判”和许多新闻概念一样都源自于欧美,属于西方新闻传播学中的概念。西方学者对其有过诸多的研究和定义。在欧美传播界,普遍认为“媒介审判”是新闻媒介报道正在审理中的案件时超越法律规定,影响审判独立和公正,侵犯人权的现象。[1]“媒介审判”的产生与西方国家的司法土壤和法制文化有着密切关联。在西方国家的法庭审判过程中,施行陪审团制度,陪审团这一角色对于案件的定性常常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于是,通过舆论影响陪审团从而影响最终的判决就成为媒体惯用的手段。随着西方庭审制度的健全和完善,为了避免这种影响的扩大,在一些有着重要社会影响的特殊案件审理过程中,可以申请隔离陪审团。
2 “媒介审判”在互联网时代的爆发
2.1 爆发的土壤
随着大量社交媒体如微博、微信的广泛渗透,自媒体、意见领袖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这给“媒介审判”创造了极为重要的舆论土壤。“媒介审判”现象也呈现由点到面全面开花的态势。1995年的“夹江打假案”、“张金柱案”之后,“媒介审判”越发被公众熟悉。之后我们的舆论环境里出现了“蒋艳萍案”、“深圳梁丽案”、“杭州飙车案”、“湖南罗彩霞案”、“湖北邓玉娇案”,直至这两年的“我爸是李刚”、“许霆案”、“夏俊峰案”等等。在这些案件的审理过程甚至审理之前,媒体已经提前介入,对人物、事件、案情进行了详细的披露,他们甚至比司法机关更早知晓案情的一些细节。由此,司法机关常常在面对媒体质疑时显得滞后而应对不足陷入被动。
2.2 “媒介审判”在互联网时代的新特征
如果说在传统媒介时代,“媒介审判”只是在一定类型的案件和一定社会范围内出现的话,那么在信息技术高度发达、社交媒体普遍应用的网络时代里,“媒介审判”已经呈现爆发之势,愈演愈烈。网络时代的“媒介审判”有着更为显著的特征。
首先,网络媒体传播的双向性甚至多向性,让信息的互动性增强,公众的参与度提高,传播和发散来得更加容易。有学者就认为,互联网的兴起带来了网络舆论的繁荣,网络舆论和传统媒介形成的舆论有着显著的不同。“网络舆论具有交互性、隐匿性、非理性、个性化、发帖随意性、真实性差等特质,使网民个体的舆情表达容易发生变化甚至扭曲。”网络赋予了普通人更多的话语权,言论更加自由和开放,微博、微信、博客、论坛甚至各大图片分享社区都可以发布自己对某一事件的看法和观点。网络言论的一大特点是,匿名、不受约束、激进、缺乏冷静思考和逻辑性,导致言论极富煽动性。
其次,网络时代的“媒介审判”更迎合公众心理诉求。当前我国处于社会急剧转型的时期,由于地区发展不平衡,资源分配存在阶段性的不平等,居民收入差距也存在明显的地区性差距。此外,就业压力大、贫富差距拉大等社会现象和矛盾也导致公众容易对此类事件进行聚集关注,触发共鸣点:同情弱者,宣泄对当事人的不满和愤怒。
3 区分“媒介审判”与“媒介监督”两者内涵
媒介审判与媒介监督从其出发点和表现形式上并无显著区别,它们之间实际上是一种程度上、定位上的区分,甚至在同一个事件中,媒体可以同时扮演“监督者”、“审判者”的角色。我们通过邓玉娇案来看问题就更加清晰一些。2009年5月,一桩爆发于湖北的案件引发全国瞩目。女服务员邓玉娇因与前来消费的官员发生争执,将其刺死,随后邓玉娇被拘留,涉嫌故意杀人罪。媒体在这个阶段只是针对案件进行了报道,如实披露了相关案情,扮演的角色是舆论监督者。不过,随后更多媒体介入,并且在网络上传播后,性质开始发生转变。媒体的站位不再客观与平衡,几乎所有的出发点都聚焦于邓玉娇一面展开。在舆论风暴中,邓玉娇被比作“女英雄”、“中国第一烈女”。一个多月后,法院公开判决,邓玉娇属于防卫过当,“综合考虑各项因素后对其免除刑罚”。有关这一阶段媒体扮演的角色,业界有不同的探讨。有人认为,媒体还是在行使舆论监督的职责,并且监督很到位。另外一些专家认为,媒体的角色在后期的报道过程中出现了明显的偏移。作者更倾向于认同后者的观点。媒体在前后两个阶段的报道中,其立场和出发点、报道目的都出现了变化,不再客观呈现事实,而是聚焦于事件的唯一一方邓玉娇身上。这是有违新闻报道的客观、真实原则的,也忽略了全面性和平衡性。据此可以认为,媒介在该案件的后期报道中,已经有媒介审判的嫌疑,即通过媒体的言论特权,引导舆论朝着一个方向发展,最终影响司法审判。
在正向效应上,媒介监督比媒介审判意义更为长远,也更加符合时代需求。
首先,媒介监督的适用范围更加广泛,它不仅适用于司法类的案件报道,也适用于关系国计民生其他类型的事件。媒介审判所定位的范围仅仅是在有关司法类的案件报道。
其次,媒介监督更强调依据法律法规进行新闻报道监督,在尊重司法的前提下进行相关的报道和采访。
再次,媒介监督在司法类事件报道中,不仅能发挥监督作用,促进司法的进步和法治进程。在当前至少能发挥以下几个重要功能。
1)评判功能。通过正当的舆论监督,把社会上一些假、恶、丑的事物摊开给大众,让公众自己去评判。这是一种积极的力量,有利于阻止不正之风的流行。
2)宣泄功能。在当前的社会环境中,通过媒介的舆论监督报道,有选择的反映普通大众积累的不良情绪,达到宣泄和平衡的作用,有利于负面情绪的消除。
3)激励功能。通过监督报道,让普通大众看到媒介在促进社会公平方面的积极与努力,同时了解相关政府部门正在进行的问题处理进展,有利于激励大众同消极负面现象做斗争的勇气与信心。
由此可见,媒介监督是值得大力提倡的媒介行为,也符合我国当前时代发展的需求。而“媒介审判”则要努力辨识和厘清。同时,在媒介监督过程中,要时刻把握好“度”的原则,只有谨守媒体的正当职责和新闻职业道德,才能避免超过那条红线。[2]
4 正视“媒介审判”
“媒介审判”需要被厘清和认识,从更全面的角度,不是回避也不是全盘否定,而是正视。正视,则是客观、理性的看待“媒介审判”,并且提出相应的可行的应对方案,而不是用行政的方法将其消灭。应当客观认识到,“媒介审判”不仅仅是一个新闻传播问题,还是法律制度和社会认知的问题,因此至少可以从媒介、司法、社会三个维度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应对策。
4.1 媒体当自律、防范“媒体暴力”
媒体应努力加强自身的法制观念并积极带动法律知识的普及。在新闻报道中要防止 “媒介暴力”的出现。作为新闻媒体,在承担新闻传播职责外,更应承担起社会责任,通过报道积极疏导社会情绪、推动社会矛盾的解决,而不是利用刺激的新闻噱头来激化矛盾。
4.2 司法应公正、透明
“媒介审判”爆发的一大重要因素在于司法与媒体沟通渠道的不畅通,不够公开与透明。首先,作为司法部门,应当坚持开放的原则而不是封闭。例如,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和信息公开制度,及时将案件进展情况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对外发布,保持信息的透明度,使自己占据信息发布的制高点。同时,也可以通过各种新媒体传播媒介例,如官方微博、官方微信等平台,及时将案件信息、社会舆论热点、民意趋向以及国家的政策发布与众,传递权威准确信息,让公众享有知情权,提升司法机关的公信力。
4.3 司法制度体系的完善与健全
坚守司法裁判的独立和权威。无罪推定原则,是法律的真实而不是客观事实的真实。这恰好给普通大众带来一种迷惑和恐惧。因此,法院应当在寻求法律真实与客观真实二者相互融合协调上,下更多功夫和努力,构建更容易被普通大众接受的证明标准。在这一点上,将“程序的公正”对外做积极的宣导和阐述,是一个重要的过程。
在司法审判的过程中,完善制度体系是一个防止被舆论左右的重要手段。这一点可以借鉴欧美国家的经验。为了防范媒介审判的干扰,美国就采取了一些积极的手段。
首先,是“空间上易地审判”。这一方法可以让案件当事人避开媒体关注的焦点地域,更加公正客观的审判案件。其次,是采取时间延后审判的方式。这是由于媒体持续热议某一案件,可以将案件审判的时间延后一定的时间,等待媒体报道冷却之后再进行审判,可以最大程度减少媒介审判的干预。最后就是针对案件被媒介审判干预的程度建立审核监察机制。一旦审核发现,案件的审判遭遇了非常严重的媒介干扰,没有得到公正的审判,则可以“推翻原判,重新审理”。[4]
4.4 公众应培养理性思维
“媒介审判”形成的重要因素就是社会公众的关注与推动,因此,要避免新闻审判的负面效应,则需要让社会大众形成更加理性的思维模式。
首先,政府机关和媒体应当携手建立更好的信息沟通平台和机制。通过各种更加公开透明的信息公开机制和平台,例如大众普遍使用的社交媒体平台,与大众进行有效沟通与分享,形成良性的互动机制。政府部门在大众面前应当树立更加权威、科学、透明、亲民的形象,化解公权力与公众之间的鸿沟与不信任。
其次,从公众层面上,应当更加理性客观看待媒体性质,学会分析媒体观点与客观事实之间的关联。公众更应当认识到,在网络信息时代,每一个个体都是一个传播媒介,其言论同样可以起到蝴蝶效应。每一个在互联网信息平台上活动的个人,都应当审慎严肃对待自己的发言与评论,承担自己身为公民的社会责任。
5 结束语
本文通过分析与论证,认为“媒介审判”是当前全球普遍存在并且随着互联网媒介的爆发,越发增多的一种现象。“媒介审判”有其不可忽视的负面效应,它给司法独立及社会意识方面都带来了很大的干扰和影响。通过分析可以看到,作为社会公器的媒体需要积极防范媒介审判的出现,防止滥用媒介职能形成媒介暴力。同时,我们也要积极看到媒介审判在一定程度上的积极作用,理性分析。正视媒介审判这一问题,必须从媒介、法律、社会三个维度对其积极引导和应对,才能让传播媒介更好的推动社会公平与正义、让司法机关更加公正透明、让法律制度更加健全与完善、让公众更加理性。
[1]魏永正.新闻传播法教程[M].3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2]张昊,米彦泽.论”媒介审判”的正效应[J].新闻世界,2010(9).
[3]付松聚,张翅.中国“媒介审判”分析及反思[J].东南传播,2008(1).
[4]林小溪.论媒介效能的持守与溢出——由“媒介审判”所引发的思考[N].发展导报,2013-8-6.
G2
A
2096-0360(2015)14-0002-03
蔡予乐,所在院校为厦门大学经济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