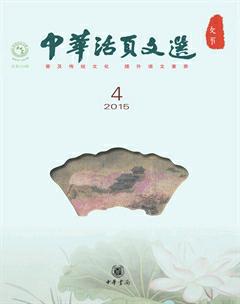怀念师友
季羡林
忆念胡也频先生
我初次见到胡先生是六十年前在山东济南省立高中的讲台上。我当时只有十八岁,是高中三年级的学生。他个子不高,人很清秀,完全是一副南方人的形象。此时日军刚刚退出了占领一年的济南,国民党的军队开了进来,教育有了改革。旧日的山东大学附设高中改为省立高中,校址由绿柳红荷交相辉映的北园搬到车水马龙的杆石桥来,环境大大地改变了,校内颇有一些新气象。专就国文这一门课程而谈,在一年前读的还是《诗经》《书经》和《古文观止》一类的书籍,现在完全改为读白话文学作品。作文也由文言文改为白话文。教员则由前清的翰林、进士改为新文学家。对于我们这一批年轻的大孩子来说,顿有耳目为之一新的感觉,大家都兴高采烈了。
胡先生的居室就在学校的花园门口旁边,常见他走过花园到后面的课堂中去上课。他教书同以前的老师完全不同。他不但不讲《古文观止》,好像连新文学作品也不大讲。每次上课,他都在黑板上大书“什么是现代文艺”几个大字,然后滔滔不绝地讲了起来,直讲得眉飞色舞,浓重的南方口音更加难懂了。下一次上课,黑板上仍然是七个大字“什么是现代文艺”。我们这一群年轻的大孩子听得简直像着了迷。
我们按照他的介绍买了一些当时流行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书籍。那时候,“马克思主义”这个词儿是违禁的,人们只说“普罗文学”或“现代文学”,大家心照不宣,谁都了解。这些书都是译文,我们当然不能全懂,但是仍然怀着朝圣者的心情,硬着头皮读下去。生吞活剥,在所难免。然而“现代文艺”这个名词却时髦起来,传遍了高中的每一个角落,仿佛为这古老的建筑增添了新的光辉。
当时还是国民党的天下,学校大权当然掌握在他们手中。国民党最厌恶、最害怕的就是共产党,似乎有不共戴天之仇,必欲除之而后快。在这样的气氛下,胡先生竟敢明日张胆地宣传“现代文艺”,鼓动学生革命,真如太岁头上动土,国民党对他的仇恨是完全可以想象的。胡先生却是处之泰然。只见他那清瘦的小个子,在校内课堂上,在那座大花园中,迈着轻盈细碎的步子,上身有点向前倾斜,匆匆忙忙,仓仓促促,满面春风,忙得不亦乐乎。他照样在课堂上宣传他的“现代文艺”,侃侃而谈,视敌人如草芥,宛如走入没有敌人的敌阵中。
他不但在课堂上宣传,还在课外进行组织活动。他号召组织了一个现代文艺研究会,由几个学生积极分子带头参加,公然在学生宿舍的走廊上,摆上桌子,贴出布告,昭告全校,踊跃参加,当场报名、填表,一时热闹得像是过节一样。时隔六十年,一直到今天,当时的情景还如在眼前,当时的笑语声还在我耳畔回荡,留给我的印象之深,概可想见了。
有了这样一个组织,胡先生还没有满足,他准备出一个刊物,名称我现在忘记了。第一期的稿子中有我的一篇文章,名叫《现代文艺的使命》。内容现在完全忘记了,无非是革命、革命、革命之类。以我当时的水平之低,恐怕都是从“天书”中生吞活剥地抄来了一些词句,杂凑成篇而已,绝不会是什么像样的文章。
正在这时候,当时蜚声文坛的革命女作家、胡先生的夫人丁玲女士到了济南省立高中,看样子是来探亲的。丁玲的衣着非常讲究,大概代表了上海最新式的服装。相对而言,济南还是相当闭塞淳朴的。丁玲的出现,宛如飞来的一只金凤凰,在我们那些没有见过世面的青年学生眼中,她浑身闪光,辉耀四方。记得丁玲那时候比较胖,又穿了非常高的高跟鞋。济南比不了上海,马路坑坑洼洼,高低不平,高中校内的道路,更是年久失修,穿平底鞋走上去都不太牢靠,何况是高跟鞋。看来丁玲就遇上了“行路难”的问题。胡先生个子比丁玲稍矮。夫人“步履维艰”,有时要扶着胡先生才能迈步。我们这些年轻的学生看了这情景,觉得非常有趣。我们就窃窃私议,说胡先生成了丁玲的手杖。我们其实不但毫无恶意,而且是充满了敬意的。我们心中真觉得胡先生是一个好丈夫,因此对他更增加了崇敬之感,对丁玲我们同样也是尊敬的。
不管胡先生怎样处之泰然,国民党却并没有睡觉。他们的统治机器当时运转得还是比较灵的。国民党对抗大清帝国和反动军阀有过丰富的斗争经验,老谋深算,手法颇多。相比之下,胡先生这个才不过二十多岁的真正的革命家,却没有多少斗争经验,专凭一股革命锐气,革命斗志超过革命经验,宛如初生的犊子不怕虎一样,头顶青天,脚踏大地,把活动都摆在光天化日之下。这确实值得尊敬。但是,勇则勇矣,面对强大的掌握大权的国民党,是注定要失败的。这一点,我始终不知道胡先生是否意识到了。这个谜将永远成为一个谜了。
事情果然急转直下。有一天,国文课堂上见到的不再是胡先生那瘦小的身影,而是一位完全陌生的老师。全班学生都为之愕然。小道消息说,胡先生被国民党通缉,连夜逃到上海去了。到了第二年,1931年,他就同柔石等四人在上海被国民党逮捕,秘密杀害,身中十几枪。当时他只有二十八岁。鲁迅先生当时住在上海,听到这消息以后,他怒发冲冠,拿起如椽巨笔,写了这样一段话:“我们现在以十分的哀悼和铭记,纪念我们的战死者,也就是要牢记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历史的第一页,是同志的鲜血所记录,永远在显示敌人的卑劣的凶暴和启示我们的不断的斗争。”这一段话在当时真能掷地作金石声。
回忆陈寅恪先生
要论我同寅恪先生的关系,应该从六十五年前的清华大学算起。我于1930年考入国立清华大学,入西洋文学系(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改名为外国语文系)。西洋文学系有一套完整的教学计划,必修课规定得有条有理,完完整整。但是给选修课留下的时间却是很富裕的,除了选修课以外,还可以旁听或者偷听,教师不以为忤,学生各得其乐。
就在这个时候,我旁听了寅恪先生的“佛经翻译文学”。参考书用的是《六祖坛经》,我曾到城里一个大庙里去买过此书。寅恪师讲课,同他写文章一样,先把必要的材料写在黑板上,然后再根据材料进行解释、考证,分析、综合,对地名和人名更是特别注意。他的分析细入毫发,如剥蕉叶,愈剥愈细愈剥愈深,然而一本实事求是的精神,不武断,不夸大,不歪曲,不断章取义,他仿佛引导我们走在山阴道上,盘旋曲折,山重水复,柳暗花明,最终豁然开朗,把我们引上阳关大道。读他的文章,听他的课,简直是一种享受,无法比拟的享受。寅恪师这种学风,影响了我的一生。
在清华时,除了上课以外,同陈师的接触并不太多。我没到他家去过一次。有时候,在校内林阴道上,在熙往攘来的学生人流中,有时会见到陈师去上课,身着长袍,朴素无华,肘下夹着一个布包,里面装满了讲课时用的书籍和资料。不认识他的人,恐怕大都把他看成是琉璃厂某一个书店的到清华来送书的老板,绝不会知道,他就是名扬海内外的大学者。他同当时清华留洋归来的大多数西装革履、发光鉴人的教授,迥乎不同,在这一方面,他也给我留下了毕生难忘的印象,令我受益无穷。
离开了水木清华,我同寅恪先生有一个长期的别离。我在济南教了一年国文,就到了德国哥廷根大学。到了这里,我才开始学习梵文、巴利文和吐火罗文。在我一生治学的道路上,这是一个极关重要的转折点。我从此告别了歌德和莎士比亚,同释迦牟尼和弥勒佛打起交道来。不用说,这个转变来自寅恪先生的影响。
经过了轰炸的炼狱,又经过了饥饿,到了1945年,在我来到哥廷根十年之后,我终于盼来了光明,东西法西斯垮台了。此时,我得知寅恪先生在美国医目疾,我连忙写了一封长信,向他汇报我十年来学习的情况,并将自己在哥廷根科学院院刊及其他刊物上发表的一些论文寄呈。出乎我意料的迅速,我得了先生的复信,也是一封长信,告诉我他的近况,并说不久将回国。信中最重要的事情是说,他想向北大校长胡适,代校长傅斯年,文学院长汤用彤几位先生介绍我到北大任教,我真是喜出望外,谁听到能到最高学府去任教而会不引以为荣呢?我于是立即回信,表示同意和感谢。
1946年的深秋,我辗转回到了阔别十二年的北京(当时叫北平),到处是一片“落叶满长安”的悲凉气象。我先在沙滩红楼暂住,随即拜见汤用彤先生。按北大当时的规定,从海外得到了博士学位回国的人,只能任副教授,经过几年的时间,才能转向正教授。我当然不能例外,而且心悦诚服,没有半点非分之想。然而过了大约一周的光景,汤先生告诉我,我已被聘为正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的系主任。这真是石破天惊,大大地出我意料。我这个当一周副教授的纪录,大概也可以进入吉尼斯世界纪录了吧,说自己小高兴,那是谎言,那是矫情。由此也可以看出老一辈学者对后辈的提携和爱护。
不记得是在什么时候,寅恪师也来到北京,仍然住在清华园。在三年之内,我到清华园去过多次。我知道先生年老体弱,最喜欢当年住北京的天主教外国神甫亲手酿造的栅栏红葡萄酒,我曾到今天市委党校所在地当年神甫们的静修院的地下室中去买过几次栅栏红葡萄酒,又长途跋涉送到清华园,送到先生手中,心里颇觉安慰。
还有一件事,也给我留下了毕生难忘的回忆。在解放前夕,政府经济实已完全崩溃。到了冬天,寅恪先生连买煤取暖的钱都没有,我把这情况告诉了已经回国的北大校长胡适之先生。适之先生想赠寅恪先生一笔数目颇大的美元,但是,寅恪先生却拒不接受。最后寅恪先生决定用卖掉藏书的办法来取得适之先生的美元,于是适之先生就派他自己的汽车,让我到寅恪先生家装了一车西文关于佛教和中亚古代语言的极为珍贵的书。陈先生只收2000美元。这个数目在当时虽不算少,然而同书比起来,还是微不足道的。在这一批书中,仅一部《圣彼得堡梵德大词典》市价就远远超过这个数目了。这一批书实际上带有捐赠的性质。而寅恪师对于金钱的一芥不取的狷介性格,由此也可见一斑了。
在我同先生来往的几年中,我们当然会谈到很多话题。谈治学时最多,政治也并非不谈,但极少。寅恪先生绝不是一个“闭门只读圣贤书”的书呆子,他继承了中国“士”的优良传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从他的著作中也可以看出,他非常关心政治。他研究隋唐史,表面上似乎是满篇考证,骨子里谈的都是成败兴衰的政治问题,可惜难得解人。我们谈到当代学术,他当然会对每一个学者都有自己的看法。但是,除了对一位明史专家外,他没有对任何人说贬低的话。对青年学人、只谈优点,一片爱护青年学者的热忱,真令人肃然起敬。
我记忆中的老舍先生
我从高中时代起,就读老舍先生的著作,什么《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二马》,我都读过。到了大学以后,以及离开大学以后,只要他有新作出版,我一定先睹为快,什么《离婚》《骆驼祥子》等等,我都认真读过。最初,由于水平的限制,他的著作我不敢说全都理解。可是我总觉得,他同别的作家不一样。他的语言生动幽默,是地道的北京话,间或也夹上一点山东俗语。他没有许多作家那种忸怩作态让人读了感到浑身难受的非常别扭的文体,一种新鲜活泼的力量跳动在字里行间。他的幽默也同林语堂之流的那种着意为之的幽默不同。总之,老舍先生成了我毕生最喜爱的作家之一,我对他怀有崇高的敬意。
但是,我认识老舍先生却完全出于一个偶然的机会。三十年代初,我离开了高中,到清华大学来念书。当时老舍先生正在济南齐鲁大学教书。济南是我的老家,每年暑假我都回去。李长之是济南人,他是我的唯一的一个小学、中学、大学“三连贯”的同学。有一年暑假,他告诉我,他要在家里请老舍先生吃饭,要我作陪。在旧社会,大学教授架子一般都非常大,他们与大学生之间宛然是两个阶级。要我陪大学教授吃饭,我真有点受宠若惊。及至见到老舍先生,他却全然不是我心目中的那种大学教授。他谈吐自然,蔼然可亲,一点架子也没有,特别是他那一口地道的京腔,铿锵有致,听他说话,简直就像是听音乐,是一种享受。从那以后,我们就算是认识了。
以后是激烈动荡的几十年。我在大学毕业以后,在济南高中教了一年国文,就到欧洲去了,一住就是十一年。中国胜利了,我才回来,在南京住了一个暑假,夜里睡在国立编译馆长之的办公桌上。老舍先生好像同国立编译馆有什么联系。我常从长之口中听到他的名字,但是没有见过面。
我现在已经记不清楚我们重逢时的情景。但是我却清晰地记得五十年代初期召开的一次汉语规范化会议时的情景。当时语言学界的知名人士,以及曲艺界的名人都被邀请参加,这是解放后语言学界的第一次盛会,大家的兴致都很高,会上的气氛也十分亲切融洽。
有一天中午,老舍先生忽然建议,要请大家吃一顿地道的北京饭。大家都知道,老舍先生是地道的北京人,他讲的地道的北京饭一定会是非常地道的,都欣然答应。老舍先生对北京人民生活之熟悉,是众所周知的。有人戏称他为“北京土地爷”。他结交的朋友,三教九流都有。他能一个人坐在大酒缸旁,同洋车夫、旧警察等旧社会的“下等人”,开怀畅饮,亲密无间,宛如亲朋旧友,谁也感觉不到他是大作家、名教授、留洋的学士。能做到这一步的,并世作家中没有第二人。这样一位老北京想请大家吃北京饭,大家的兴致哪能不高涨起来呢?商议的结果是到西四砂锅居去吃白煮肉,当然是老舍先生做东。他同饭馆的经理一直到小伙计都是好朋友,因此饭菜极佳,服务周到。大家尽兴地饱餐了一顿。虽然是一顿简单的饭,然而却令人毕生难忘。
还有一件小事,忘记了是哪一年了,反正我还住在城里翠花胡同没有搬出城外。有一天,我到东安市场北门对门的一家著名的理发馆里去理发,猛然瞥见老舍先生也在那里,正躺在椅子上,下巴上白糊糊的一团肥皂泡沫,正让理发师刮脸。这不是谈话的好时机,只寒暄了几句,就什么也不说了。等我坐在椅子上时,从镜子里看到他跟我打招呼,告别,看到他的身影走出门去。我理完发要付钱时,理发师说:老舍先生已经替你付过了。这样芝麻绿豆的小事殊不足以见老舍先生的精神,但是,难道也不足以见他这种细心体贴人的性情吗?
(选自《北京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