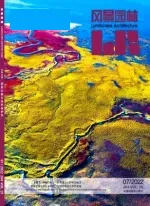文化景观之理论与价值转向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李晓黎 韩锋*
文化景观之理论与价值转向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李晓黎 韩锋*
在文化地理研究视野下,特别是新文化地理研究中对“文化”概念的界定及文化与人关系的探讨背景下,剖析了世界遗产文化景观类型设立的深层次动因——文化景观研究中重要的“文化转向”及其阐发的遗产价值观念重大变革。认为遗产价值观念突破了对精美绝伦的极端关注并注重有形与无形的高度整合;指出这场深刻的理论与价值转向对深度发掘、系统阐释中国风景名胜中精神关联价值、多元社会价值、政治隐喻、历史经历及人类品格意志等方面产生了重大影响。
文化景观;文化地理;文化;遗产价值;风景名胜区;世界遗产;遗产保护
修回日期:2015-07-15
1 引言
文化景观自产生开始便带有鲜明的西方文化地理色彩,从初现端倪到作为一个专门术语进入学界[1],其经历曲折复杂,但始终是对景观意义及价值的不断深入探索。特别是在文化地理研究中重要“文化转向”[2]及20世纪后期不断凸显的后现代思潮[3-4]之下,景观价值阐释从自然地理实证经验走向社会历史背景下的现象逻辑解读,在对景观意义的重新审视与剖析中确立了全新的景观价值秩序,并向世界遗产实践领域迅速渗透。因而,对文化景观研究中重要“理论与价值转向”的剖析为理解文化景观作为世界遗产重要方法论工具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值得指出的是,这种理论与价值转向为我们重新审视人地关系、解读景观事物并深入剖析其内涵提供了独到的见解,并非等同于“从错误走向正确”的道路变化。
近来,全球文化景观遗产实践热潮更表明:文化景观在遗产价值发掘、类型扩展及协调人地关系中的强大生命力,而此则有赖于对文化景观遗产类型设立动因及背景的剖析。因此,立足文化景观研究中对“文化”概念的界定及“文化与人”关系的探讨,明晰“文化转向”之下对景观价值内涵的重新审视,特别是由此而阐发的遗产价值观念变革,显然是学界应关注的焦点。这对深度发掘中国本土文化景观价值,并向国际遗产平台贡献自身力量具有寻根溯源、正本清源的效用。
2 文化景观的缘起及其主旨要义
文化景观的起源与发展涉及对“文化”、“景观”两大根本概念的理解,即:对“文化”本身的界定以及看待“景观”的立场。
从词源上讲,“景观”就表征了自然环境本身以及人类看待生存环境的方式,其概念本身便整合了所有处理人与环境间关系的重要因素[5-6];“景观”更应该被认为是一种“看的方式”,而不仅仅是“看的结果”[7]。这样的视角强烈彰显了“景观”概念对于整合文化与自然、关联人与土地的持续关注。J.B.杰克逊(J.B. Jackson)[7]、W.G.霍斯金斯(W.G. Hoskins)[8]对“景观”的探究更旗帜鲜明地指出了人类应对其进行积极主动地解读;“景观”突破了简单的视觉美感认知或静态文本记录,更是一种典型的文化过程的表征[9]。怀利(Wylie)更把景观作为一种观看世界的方式,其外在形态是一系列文化价值、社会习俗及土地利用方式有机互动的产物[10]。因此,“景观”成了人类所共通的价值体系、信仰及意识形态的产物,更是一种能够被解读的文化建构[5-6]。这样的“景观”概念是本文讨论文化景观理论与价值转向的前提和基础,即:景观突破了外在世界简单直白的自然物象,透过景观表象而揭示的文化意蕴、习俗观念、信仰传统及社会隐喻等内涵成为景观深层次价值所在;“景观”的观念,如何“文化”地去观[3],成为新文化地理视野下理解景观的关键。
文化景观在19世纪中后期德、法历史及地理学者的论著中已现端倪,以奥托·施吕特尔(Otto Schlüter)为代表的德国地理学者对自然地理在景观意义研究中的主导地位提出强烈质疑,极力倡导对文化在景观建构中的决定地位和重要作用进行探究[1,11-12]。同时,随着地理学经典范式遭到德国哲学界的质疑,当时盛行的笛卡尔哲学体系中获取知识的途径同样受到了以胡塞尔(Husserl)为代表的现象哲学家及其同伴的挑战,他们所架构的“现象逻辑”①同样关注习俗及生活模式,聚焦于日常生活及人类经历[13]。因此,文化景观研究中同样认为景观是“有待解读的社会历史的物质表征”[1]。
20世纪早期,文化景观在美国文化地理先驱索尔(Sauer)及其所创立的“伯克利学派”(即传统文化地理学派)引领下作为一个专门术语进入学界[1]。1920年代,索尔将人类学、社会学的视角引入文化地理研究,在对“环境决定论”②的批判中逐渐形成“伯克利学派”[4]。深受上述德国哲学思潮及地理研究视野的影响,索尔提出了经典文化景观定义:“文化景观是由特定的文化族群在自然景观中创建的样式,文化是动因,自然是载体,而文化景观则是呈现的结果”[14]。
在此,文化景观研究中的传统学派(即传统文化地理学派)在“文化”概念界定时将其看作是控制人类行为的决定力量,认为“文化”是特定文化族群中预设的、超稳定的主流文化,文化景观的研究即是寻找景观和预设的静态文化之间的证据,具有鲜明的文化决定论色彩[15-16]。这样的立场在看待“文化”本身及其与人之间关系时是孤立、静止而刻板的,忽略了文化所具有的动态性、多样性以及主体在文化建构中的主动性与创造性,更抹去了复杂社会历史背景对其产生的影响。这样的观念立场成为20世纪后期文化景观研究中新派学者批判的对象。
3 文化景观中重要的“文化转向”
20世纪后期,文化地理研究在对“文化”概念及“文化与人”关系的探讨中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新旧之争”,其间重要的“文化转向”阐发了对景观意义及价值的再思考,不断反思人与自然、文化与自然间的关系。这种认识立场的重要转变阐发了世界遗产领域重大的价值认知变革,为文化景观遗产类别的设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3.1 文化地理研究中的“新旧之争”及重要“文化转向”
1990年代以来,后现代思潮的新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结构主义等哲学背景下“新文化地理学”不断崛起,在对“超有机文化”③的批判中引发了一场激烈的“新旧”之争,其焦点在于:对“文化”概念的界定以及对“文化与人”关系的探讨。“超有机文化”从本体论层面出发,认为文化具有决定力量,是凌驾于个体之上的、神秘的自然法则,文化具备内在“同质性”;个体和文化间是分离的,并且用“条件反射论”来解释人类行为与文化间的关系[16]。
而文化地理研究中的新派学者对“文化”的界定则抿弃了文化与个体相割裂的观念,主张文化的多样性,认为文化总是存在于具体有形的、复杂的社会历史语境及权利关系纠葛中,高度抽象概括的、具备典型“同质性”的文化是不存在的;人类行为则是个体在文化所提供的整体背景下具有选择性、创造性的行为方式[16]。杰克逊(Jackson)更认为文化并非简单的通过眼睛传递给我们的风景,而应该是“看的方式”[7]。邓肯(Duncan)的名言“文化即政治”[16]更深刻揭示了新文化地理学强烈的社会政治倾向。
从而,这种动态具体、相互关联且有机演进的“文化”立场以及对“文化与人”之间的关系的认知显著区别于传统文化地理学派,是为重要的“文化转向”;并且,这样的“文化”立场成为文化地理研究中新派学者的标签,也是本文讨论文化景观所采取的重要立场。这样的“文化”概念界定充分尊重了价值的多元,认同并接纳个体在文化创造中的主动性、选择性,更将其置于宏观历史向度与复杂权力纠葛中进行解读,把文化作为有政治争议的社会建构进行探讨[17]。从而,各类激进思潮以及社会阶层、身份、性别、地位、话语权等都进入“文化”研究视野[17-18]。
在此背景下,梅尔尼克(Melnick)、康斯格罗夫(Cosgrove)、奥黑尔(O'Hare)及阿姆斯特朗(Armstrong)等人均基于各自立场对文化景观概念进行了界定;也有从生活活动及其相互关联的活动系统、附着于主客体之上的可视物质信息以及非物质文化因素层面对文化景观的核心及狭义、广义范畴进行探讨[19]。本文则采取奥黑尔与阿姆斯特朗的观点,即:文化景观是持续演进的、人文化的景观,它由物质景观环境、人类改变环境的印迹和景观对不同人群的意义等要素间的辩证关系构成,并且三者始终持续互动[11];文化景观可以表现为故事情节、神话传说或精神信仰,也能被用于荒野地带、日常景观以及人类有意设计的景观[1];文化景观概念是对历史的动态诠释,是过去、现在和未来间的无缝关联[11]。
3.2 “文化转向”之下对景观意义及其价值的重新审视
文化景观研究进程也就是不断深入探究景观意义并阐释其价值的过程, “文化转向”之下对景观意义的再审视则为文化景观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因而,文化转向不仅是重要的理论转向,更是一场深刻的价值转向。
在重要的文化转向之下,基于“文化”的多样性、具体性、动态性及其与人之间关系的复杂性,文化地理新派学者主张将景观置于宽泛的历史语境及复杂社会系统中进行解读,对景观的研究从人类学到政治学,恢复了文化地理学和政治地理学的联系[17],放弃了景观是传统生活方式表现这类散漫的描述,而直指文化内涵的焦点——价值观念以及相关的符号意义[4],认为景观是“文化的意象”[2],是“看的方式”而不是“看的结果”[7];强调景观意义及其价值的阐释应着力关注文化观念与过程在景观中的作用,注重对构成景观文本的符号及其象征意义的解读[2,20-22]。景观的形态和意义更是受强烈的主观意识的影响,是被带有政治性和社会性的文化所操纵的,景观以“文本”的方式记录了这种意识和文化,通过对此“文本”的解读可以考察社会建构、权力竞争、意识形态和社会空间[15,20]。
因此,景观的象征意义和社会属性成为关注的焦点,强调借用图形图像学、语言学、符号学、文学与历史学、解释学等理论立场和方法论工具[21-22]对景观象征意义与空间隐喻进行探讨,深刻揭示了景观作为物质载体所表征的复杂而广泛的社会经济背景及其与人类意识理念间的相互作用。
3.3 “文化转向”之下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反思
重要“文化转向”之下,人们看待自然与文化的关系便与传统“两元”立场截然不同。1970年代,《保护世界自然和文化遗产公约》鲜明地体现了文化与自然的分离,世界遗产两大类型——自然与文化遗产便是这种思想的产物[23]。而在文化景观概念中,景观作为一种文化建构,自然与文化同时存在于人周围充满人文哲学意义的世界中;这种整合自然与文化的视野与西方主导的自然文化相分离的观念截然相反,人与自然相互依存[24]。自然或景观本身便是而且始终蕴含了深刻的文化意义,即便是毫无人类活动痕迹的荒野也是文化产物,因为它本身所流露出的孤寂荒凉的感受便是纯自然进入人类审美或认知视野的文化建构[5-6]。
总之,文化的重要转向对人与文化、景观与社会文化过程间关联性的思考促使自然与文化对立观念迅速转变,认识到两者间存在的空白,并努力寻求一种重要手段来弥合两者间的裂隙;为文化景观进入世界遗产实践领域并作为一种遗产类型对杰出普遍价值进行鉴别、认知和保护打下了坚实基础。
4 “文化转向”之下遗产价值观念的重大变革
世界遗产文化景观类型的设立有其深厚的哲学背景与理论渊源。特别是对西方“两元分离”哲学立场所主导的遗产观念中人与自然、自然与文化相分离的不断反思,以及在遗产实践中抑制或抹去东方式的非理性的、无形精神价值而带来的一系列境遇,都使得世界遗产亟需一种兼顾物质与精神、架构文化与自然的方法论来解决历史与现时、精英与大众、保护与发展的难题[23]。而文化景观在架构自然与文化、关联人类社会与土地及自然生态系统、强调文化的地方性及多样性[23]等方面的新视野则满足了世界遗产对未来保护发展的需求。
特别的,新文化地理研究中重要的“文化与价值转向”之下强调在宏观历史语境中剖析景观的社会属性与政治意蕴,并且尊重多元文化,关注、认同不同社会阶层的价值及利益诉求。这种透过现象对事物本质的洞悉,使得文化景观成为世界遗产填补空白的有力武器,并向遗产实践领域迅速渗透[23]。
1992年,世界遗产组织修改了《操作指南》,将文化景观作为世界遗产的一个类别纳入世界遗产实践体系,指出:文化景观表征了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是人类与自然环境的共同作品,揭示了人类社会及其所依存的聚居环境的有机演进过程,体现了社会、经济和文化因素在与人类演进中的相互作用和影响;文化景观因其杰出普遍价值、特定地域及文化族群的代表性,以及阐释特定地域文化精髓的能力而成为世界遗产。因而,作为世界遗产的文化景观将景观的象征意义与人类活动所创设的景观形态高度整合[5],其间所揭示的人与自然有机互动正具备了世界遗产所珍视的杰出普遍价值。
在此背景下,世界遗产价值观念也发生了重大变革,突破了以往静态孤立的保护论以及对精英文化、高尚艺术审美的追求;转而强调自然与人类社会在历史有机演进中的相互关联、动态演变,并在整合有形物质遗存与精神信仰等非物质价值之上对遗产价值进行鉴别、认知与保护。
4.1 从对“精英高尚、精美绝伦”的极端关注到“大众日常与精英”的并重
“文化转向”之下对文化主体性、多样性及价值多元化的尊重,使得遗产价值呈多元态势,不同阶层的价值诉求都进入遗产研究视野。景观的研究角度从精英文化、艺术唯美进入到普通大众、复杂演变的社会关系中[23];精英与大众并重使得遗产领域不断关注日常生活中景观的意义,那些普通的,甚至曾被低视的文化和价值、“他者”的价值[4]也因其所揭示的应对特殊生存环境的智慧和韧性而进入遗产研究视野。如:南美地区的咖啡园、烟草园,以及法国北部采矿遗址等便是明证。
特别的,遗产价值认知更突破了对正面价值的关注,负面的或与艰辛的历史相关联的价值也进入到遗产研究视野中,如:毛里求斯莫纳山与奴隶逃亡等重大历史事件或部落的生存发展、社会冲突对抗等相联系的景观也因此而跻身世界遗产。
4.2 从“静态片面”的孤立视野到“动态演变、整体关联”的“有机整体观”
新文化地理学派对抽象、静止而孤立的“文化”概念的批判以及对文化动态演变过程的关注使得遗产价值观念发生了巨大变革:从静态遗址保护到关注动态演进历程、从建筑单体维护到强调遗产所处的整体环境。因而,能够体现人类社会持续演进的国家价值与地方价值的有机融合、文化和地域多样性的彼此渗透、个体和群体间的相互关联和影响、物质景观与非物质观念的有机整合等诸多议题都被纳入遗产价值认知视野中[5-6]。
1980年代,遗产的时间性与地域性不断引发关注,人们认识到:正是在历史与现实的对话中,历史遗址、有形物及其表征的价值才得以阐发;遗产保护的目的并非创造一些属于过去的化石或遗迹,而是要将遗产整合到现实的人类社会生活中,使其对当代人群产生重要意义[25]。1994年的《奈良真实性文件》对真实性的界定也随着人类社会文化背景的差异、本土文化的多元而动态变化,强调将文化的整体环境和本土背景纳入遗产保护视野。
此外,对文化动态性的关注更注重景观的持续演变过程,认为重要的历史遗迹、遗址与地区族群的文化观念及意识形态密切关联;对重要遗址遗迹的考查更关注有形历史物证所揭示的人与自然互动模式,并深入解析其在人类社会发展转型中的关键作用。
4.3 从对“有形物证”的依赖到“物质与精神”的高度合一
“文化转向”之下遗产价值认知和保护突破了有形物质的藩篱,积极吸纳与人类社会演进密切关联并物化在日常生活中的精神信仰、传统习俗、道德体系及意识形态等无形价值;在独特的土地或自然资源利用中将动态的人类社会与具体有形的景观环境、生态系统相关联,将生物多样性与文化多样性维系相统一。
印尼的Soedjito认为:目前文化最重要的表征不在于宏伟高尚的纪念物、遗址、艺术品,而与人类生存物质世界及经历相关联的无形价值与有形遗产同等重要,有形遗产环境及其表征的意象、象征性意义等交织在一起,难以分割[5]。同样,1994年的《奈良真实性文件》也突出强调有形遗产与无形价值间的关联;在遗产领域永恒与变迁、活化与静态、公众参与与孤立保护等话语权争夺中酝酿了遗产价值从有形到无形的重大变革,促使“非物质整体观”[25]进入遗产保护视野。
5 文化景观之重要转向与遗产价值观念变革对中国的启示
中国风景名胜区系统是国家遗产体系层面的杰出代表,目前中国的世界遗产有三分之二源自该系统,对世界遗产文化景观的理论与实践贡献不言而喻。文化景观重要的理论及价值转向为开掘遗产价值提供了强大的认识立场,对深度发掘、系统阐释中国风景名胜体系中所蕴含的文化景观价值,并向世界遗产做出自身贡献产生了重要影响。
第一,在文化景观遗产注重有形与无形价值有机整合、彼此阐发的观念性变革之下,中国风景深度诠释的“物质与精神的高度合一、有形物证与无形价值的完美融糅”成为中国本土文化景观遗产价值开掘之突出重点。
中国风景在文化和自然间相互关系及自然的文化意义上有着上千年的积淀,自然的文化建构所达到的深度与高度在世界上独树一帜。中国人与自然山水相互观照[26]而阐发的人文风骨、雅量高至而境深神远的人文襟怀与艺术精神、创作传统,因自然物象而寄托的品格意志、人伦精神,以及自然山水阐发的对社会变迁、人生际遇的关切,乃至平实恬淡的田园生活中流露出的对人终极关怀的专注等都是中国风景中突出的无形价值所在。在中国风景中,人的心力与智慧灌注于山石草木,自然物象突破了简单直白的外在形态,所寄托的精神追求成为深层次价值所在。这种有形的“物”与“景”和无限的“情”与“境”之间的融合[27]堪称中国风景中潜在文化景观遗产价值之精髓。如:五台山文化景观遗产价值的关键则在于其内在的整体结构,人文与自然、物质与非物质的共同存续关系;是山寺与“活着”的佛教文化的共生体[28]。
第二,文化景观遗产从对精英唯美、艺术经典的极端关注到普通大众、日常体验与精英文化并重的观念性变革使得多元价值跻身世界遗产行列;而中国风景中浪漫与现实、精英与大众、宗教与世俗交相辉映、对照烘托间揭示的现实社会多元价值及其折射出的质朴人文情怀便是对此的完美诠释,是深度发掘中国风景名胜潜在文化景观遗产价值之重点。
中国风景既注重对精英文化的诠释,更专注平实无华的世俗生活、平民文化;在独特的风景建构中并无对精英唯美、高大上的袒护,反而在朴实无华的市井生活中透露着超乎想象的哲理和智慧[29]。酿酒作坊、陶瓷遗迹、茶叶贸易路线,以及盐业开采、精炼及贩运而造就的人类聚落、新疆地区的“坎儿井”灌溉系统、哈尼村寨的稻米梯田等等,一系列与国人日常生活密切关联的景观系统在平实的景致中都透露出“人地互动”间的超凡智慧;所揭示的地方文化族群积累的技术、知识,以及物化在日常中的习俗、传统与信仰都彰显着中国风景中价值的多元。
特别的,中国传统文人在与现实社会的观照间始终流露出深切而朴实的人文襟怀;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间关系的思考细微而无不在,并始终以人伦、人格、人道作为处理复杂世态的准则,关注现世人生[30-32]。这种情感真挚而坚韧的人文关怀便是中国风景所蕴含文化景观遗产价值之独特亮点。
第三,文化景观之重要“文化转向”更倡导用客观、公正的态度正视历史,深入解读景观物证中所揭示的人类经历体验、情感记忆及品格意志,关联历史与现实。诸多与负面价值、历史记忆关联的景观都因此而跻身世界遗产行列。在中国风景名胜区中,诸多与重大历史事件或人类记忆关联的遗址遗迹、纪念地等都因此而具备了潜在的文化景观遗产价值。炎黄帝陵风景区“炎黄遗迹”中所揭示的中华民族坚韧不拔的开拓进取精神、胶东半岛海滨甲午战争纪念地所揭示的中国军民面对外来入侵而奋起抗争、英勇无畏的民族气节等便是典型。
第四,文化景观重要转向之下强调以动态演进、整体关联的视角对遗产价值进行解读,突破了静态、孤立而僵化的困局。中国风景在历史与现实、自然与人类社会、遗产及周围环境的高度整合间渗透的“人地互动”杰出智慧及其折射出的人文精神更是文化景观遗产价值开掘之重点。
中国风景名胜中景观的动态演进完美阐释了传统人文精神灌注之下“可游、可居”的理想境界,高度人文自觉、诗画意境的营造与拟人化的自然审美情趣贯穿始终;并且,物质景观催生的精神信仰与文化传统物化到日常生产生活中,两者有机整合而持续维系了景观的有机演进。稻米种植、梯田劳作、陶瓷泥作、渔业生产等一系列充满智慧与韧性的人地互动模式至今仍在地区人类社会中扮演重要角色,其间所揭示的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哲学思考都是中国风景对世界遗产文化景观的特殊贡献。最典型的如:杭州西湖在上千年的持续演变中融汇和吸附了大量中国儒释道主流文化,承载了深厚的文化与传统,成为西湖作为文化名湖的重要支撑[33]。
第五,“文化转向”之下动态演进、整体关联的遗产价值观更主张在复杂社会变迁及权力纠葛中解读景观的象征意义与政治隐喻。因而,中国风景名胜中山水形胜、历史遗迹及其整体环境的变迁所揭示的时代政治的流变、士人社会地位的摇摆不定,以及传统士人与政权集团间徘徊于“对峙”与“同一”[34]间的权力争斗关系等都是对风景深层次价值的发掘。如:中国皇家园林在大规模的山水整治中所彰显的皇权无上威严,佛道名山逐渐沦为皇权政治操控下维系统治、巩固政权的工具,以及文人写意经典宅园在“壶中天地”中所寄寓的人生出处进退与社会浮沉等都是中国风景中潜在文化景观遗产价值开掘之突出要点。
6 结语
文化景观遗产类型的设立及其在开掘遗产价值中的富有洞见的认识立场与工具手段得益于新文化地理研究中对文化概念及文化与人关系的重大认识变革:抿弃了静态、片面孤立的文化立场,否认抽象、克板文化传统的存在,主张动态、联系而具体的文化观念,尊重多元文化及主体在文化创造中的主动性、创造性。这场重要的“文化转向”更是价值的重要转向,其间所确立的全新遗产价值秩序更成为快速城市化进程中重新审视和剖析文化景观遗产价值并实现人地和谐的强大工具。
这场深刻的遗产价值认知变革对深入发掘中国风景名胜体系中所蕴含的文化景观价值具有深远的影响。在未来研究中,风景名胜在有形物质与精神信仰、自然与景观的完美融合间所阐发的深邃关联意象、人文传统及象征意义;在现实与浪漫、宗教与世俗、精英及大众水乳交融的风景环境中所昭示的人文精神与道德关怀,特别是独特人地互动模式持续维系的景观演进中表露的中国人关乎人与自然、天人关系的哲学立场,及其所揭示的不同社会阶层互动竞争关系等都是能够开掘的突出文化景观遗产价值所在。
注释:
①现象学(Phenomenology)是20世纪西方重要的哲学思潮,为德国犹太哲学家胡塞尔所创立;密切关注现实世界经历体验的本质,在文化研究、社会学、文化地理、艺术与设计领域产生了广泛影响。
②18世纪末,德国政治理论学家拉采尔将达尔文“适者生存”的生物进化论用于人类社会,夸大突出了环境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决定作用,直接启发了1920年代美国以埃伦·森普尔为代表的“环境决定论”。该理论认为人类的身心特征、民族特性、社会组织、文化发展等受自然环境特别是气候条件的支配。
③超有机文化(Super-Organic Culture)由阿尔弗雷德·克罗伯(Alfred Kroeber)和罗伯特·罗维(Robert Lowie)在20世纪早期陈述其梗概,并影响了索尔(Sauer)及其在伯克利的学生。
[1]Armstrong,Helen.Investigating Queensland's Cultural Landscapes: CONTESTED TERRAINS Series,REPORT 1:Setting the Theoretical Scene[R].Australia: Queensland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2001.
[2]Cosgrove D, Jackson P. New Directions in Cultural Geography [J]. Area, 1987, 19 (2):95-101.
[3]向岚麟,吕斌.新文化地理学视角下的文化景观研究进展[J].人文地理,2010, (6):7-13.
[4]唐晓峰.文化转向与地理学[J].读书, 2005, (6): 72-79.
[5]Taylor, Ken.Landscape and Memory:Cultural Landscapes,Intangible Values and Some Thoughts on Asia[C/OL].16th ICOMOS General Assembly and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Finding the spirit of place - between the tangible and the intangible, Canada,Quebec, 2008. [2015-07-23]. http://openarchive.icomos. org/139/1/77-wrVW-272.pdf.
[6]Taylor, Ken. Cultural Landscapes and Asia: Reconciling International and Southeast Asian Regional Values [J]. Landscape Research, 2009, 34(1): 7-31.
[7]Jackson, J. B. Discovering the Vernacular Landscape[M].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1984: 1-8.
[8]Hoskins, W. G.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Landscape[M]. London: Hodder & Stoughton,1955: 14.
[9]Robertson, Iain & Richards, Penny. Studying Cultural Landscapes[M].New Edition. London: Hodder Arnold,2003.
[10]Wylie, J. Landscape[M]. London: Routledge, 2007.
[11]O'Hare, D. Tourism and Small Coastal Settlements: A Cultural Landscape Approach for Urban Design[D]. U.K.:Oxford Brookes University, 1997.
[12]Whitehead, J.W.R. The Urban Landscape: Historical Dimension and Management[M].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Special Publication.No.13. London: Academic Press,1985.
[13]Valle, R. Halling, S. Existential-Phenomenological Perspectives in Psychology[M]. New York: Plenum Press,1989.
[14]Sauer, Carl. The Morphology of Landscape[J].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ublications in Geography. 1925, 2(2): 19-53.
[15]韩锋. 世界遗产文化景观及其国际新动向[J].中国园林. 2007, 23(11):18-21.
[16]Duncan, James S. The Superorganic in American Cultural Geography[J].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1980, 70(2): 181-198.
[17]李蕾蕾. 当代西方“新文化地理学”知识谱系引论[J].人文地理, 2005, (2): 77-83.
[18]唐晓峰,李平.文化转向与后现代主义地理学——约翰斯顿《地理学与地理学家》新版第八章述要[J].人文地理,2000, 15(1): 79-80.
[19]黄昕珮,李琳. 对“文化景观”概念及其范畴的探讨[J].风景园林, 2015, (3): 54-58.
[20]Meinig D. The Interpretation of Ordinary Landscape[M].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11-47, 165-189.
[21]Duncan, James S. The City as Text: The Politics of Landscape Interpretation in The Kandyan Kingdom [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 3-24.
[22]Cosgrove, Denis & Daniels, Stephen. The Iconography of Landscape[M].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8: 1-9, 43-73.
[23]韩锋.文化景观——填补自然和文化之间的空白[J].中国园林, 2010, 26(9): 7-11.
[24]Taylor, Ken & Lennon, Jane L. Managing Cultural Landscapes[M].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Publisher, 2012: 1-44.
[25]Ruggles, D. F.and H. Silverman. Intangible Heritage Embodied[M].New York: Springer, 2009: 1-16.
[26]葛晓音.山水诗与盛唐气象[J].中华遗产, 2007, (9):28-29.
[27]杨锐.论“境”与“境其地”[J].中国园林, 2014, (6): 5-11.
[28]邬东璠,庄优波,杨锐.五台山文化景观遗产突出普遍价值及其保护探讨[J].风景园林,2012, (1): 74-77.
[29]韩锋.解读武当山文化景观[J].中华遗产,2007, (10):26-29.
[30]赵行良.现代化、全球化与中国人文精神的当代建构[J].广东社会科学, 2000, (4): 63-70.
[31]何仁富.儒家与中国“人文中心”的文化精神——唐君毅论中国人文精神(上) [J].北京青年政治学院学报, 2006,15(3): 55-63.
[32]余卫国.论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J].宝鸡社会科学,1999, (3): 33-35.
[33]陈同滨,傅晶,刘剑.世界遗产杭州西湖文化景观突出普遍价值研究[J].风景园林,2012,(2): 68-71.
[34]殷允超.中国画和园林艺术探索中国山水精神[D]曲阜:曲阜师范大学,2007.
The Turning Point in Cultural Landscape and Illuminations on Chinese Landscape Architecture
LI Xiao-li HAN Feng*
Based on crucial definition of “Culture” and “Relationships between culture and people” in the field of New Cultural Geography, this paper analyzes why establish the type of heritage cultural landscape: cultural turning point and reconstructions on heritage values. This article points out that an integral and organically evolving perspective is important for communicating heritage values and also demonstrates the influences of this critical heritage value change on Chinese scenic and historic interest areas, including the spiritual values, multiple social values, history values and political system.
Cultural Landscape; Cultural Geography; Culture; Heritage Values; Scenic and Historic Interest Areas; World Heritage; Heritage Conservation
TU986
A
1673-1530(2015)08-0044-06
10.14085/j.fjyl.2015.08.0044.06
2015-04-11
李晓黎/1982年生/男/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景观学系博士生/研究方向:文化景观(上海 200092)
韩锋/1966年生/女/博士/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景观学系系主任/教授/博导/研究方向:文化景观(上海200092)
邮箱(E-mail): franhanf@g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