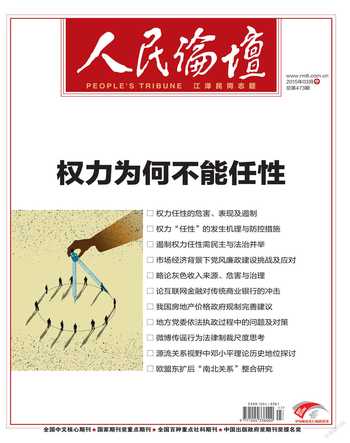国家主义派理论主张述评
徐鸣
【摘要】国家主义派的理论主张大致分为三个主要部分:首先是民族主义的诉求,寻求民族独立与民族崛起;其次是国家主义,国家主义同时体现了民族主义政治上建国的激烈要求,也表达了在国家构建上的主张;最后是全民政治的理想。可以说,国家主义派很好地表达了一个民族在寻求民族崛起和国家建设方面的建设性蓝图。
【关键词】国家主义 全民政治 国性
【中图分类号】G03 【文献标识码】A
近代中国处于新旧交替、东西冲突的风口浪尖,持续这一时代的主题就是如何使中国在这一前所未有的历史大变局中把握住自己的命运。萦绕在这一时期几乎所有中国知识分子脑海的始终只有三个字:“找出路”,为此,或求索于本土古典智慧,或借鉴发挥西方思想,不一而足。又由于当时中国积贫积弱,与西方发达的政治、经济文明相比明显不属于一个发展阶段,因此,后者的理论思潮就成了知识分子解决中国问题时的重要参照系。盛于20世纪20、30年代,以曾琦、李璜、左舜生、陈启天等为骨干的国家主义派便是其中之一,而且是比较有特色的一派。
目前大陆学界对国家主义派的原始资料搜集整理甚为有限,对其的专门研究更是少之又少,而且多从同一思维路径出发,对其评价定性几乎已成定式,多以负面评价为主。本文即试图以较为中立的立场,从国家主义派政治思想对近代中国政治的思考及所能给出的出路的角度出发,分析并评价该学派的思想特征。
民族主义诉求
李璜在《释国家主义》一文中详细解释了国家主义派所主张的“国家主义”一词的具体含义,为此还特意引用了法国辞典Nouveau Larousse与Larousse universel中关于所谓“国家主义”的定义①。在第一次提到“国家主义”一词时,李璜特意注明:Le nationalisme,在英文中即是nationalism一词,该词在中文语境中一般首先被认为是民族主义,其次才被认为可表示“国家主义”之意。此外在李璜文中,“国家”法文为La nation,即nation一词,在目前看来,国家作为一政治单位一般用state来表示,而nation在大多数时候用作民族之意。
国家主义派很清醒地意识到当时中国的险恶处境,外有列强压迫,内无国家统一。国家主义派有很多人曾留学欧洲,如曾琦、李璜等,这些人因此较为了解欧洲国家的历史,并将之与中国相比较。他们的一个发现便是,中国当时的状况很类似于两个国家:一是拿破仑时代法国压迫下的德国;二是普法战争后大败于普鲁士的法国。“战后德国因受凡尔赛条约之压迫及英法兵之久占其领土,感受痛苦甚深,于是以国家主义相号召的政党复盛于其国中。”而法国在1870年败于普鲁士后,“国家主义思想潮便也张大起来,风行全国。”②令国家主义派感到羡慕的是,这两个国家最终都得以“报仇雪耻”,于内完成统一重兴,于外驱逐强权,求得真正独立。而他们之所以取得成功即在于“国家主义”起了主导作用。
一般而言,民族主义在理论家笔下都是一种可怖的形象,通常都与暴力、专制、屠杀联系在一起,因此民族主义一词在很大程度都是一个贬义词,至少与人类的美好生活相距甚远。但厄内斯特·盖尔纳(Ernest Gellner)则从社会学和人类学的角度,分析民族主义的形成和内涵。在盖尔纳看来,工业化是民族主义产生的关键因素,工业化需要一个由国家保护的普遍的、世俗的高层次文化体系,而在工业化的过程中并不是所有的人类群体都能及时做到这一点,那些落后的部分为了自身的生存发展需要,而“创造”出统一的民族的意识和民族主义运动的需要,即为自己这一部分群体建立仅属于自己文化的国家,工业化同样是其唯一目标。这种解释方式可以给民族主义抹去不少贬义色彩,它让我们知道,民族主义即使最终表现很激烈和不宽容,但就其产生的因素来看却是相当中性或合理的,因为工业化、获得与其它人群相对平等的生活水平的要求无论如何都不能被视为罪恶。如此看来,回顾中国近代历史,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思潮不仅是客观存在的,而且也是必然会出现的。甚至可以说,在中国近代出现的诸多思潮中,大多表现出了民族主义的倾向,富强救国的口号作为无可辨驳的共识就是明证。而在这些思潮中,国家主义派却是唯一一个将这种思想倾向和情绪集中而理论化地表达出来的思想派别。
根据盖尔纳的观点,民族并不是一个自然概念,而完全是一个政治概念。在盖尔纳看来,民族主义者的真正目标并不是所谓保护本土文化或种族纯洁性,而是建立起一个能够适应工业化要求的政治体(即国家),这一国家中的文化有其自身的特殊性但必须适应工业化的要求。中国文化中历来以国家为“天下”,虽然也有华夷之分,但由于中华之外的文明大多被认为是不值一提的野蛮人,所以中国的民族意识从来都不强烈。只是到了近代在与列强实力较量之后才不得不承认中国仅仅是诸文明国家中的一个,而且实力远较西方国家为弱。国家主义派对这一亘古未有的变化有着深刻的体会,他们认识到,虽然中国这时正处于诸民族弱肉强食的危急时刻,然而中国作为一个有着自己特殊文化的群体远未能像其它民族那样有着很强的凝聚力。因此,国家主义派感到当时首要的就是号召起国民的民族意识,使整个中国凝聚成一个具有战斗力的民族。这种民族意识被国家主义派称之为“国性”(nationality)。国家主义派的陈启天说:“我们深信振作国民的精神,激励国民的感情,团结国民的意志,以求洗刷国民的耻辱,在当今只有国家主义才能做到。”③也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国家主义派也将自己称作“醒狮派”,“我们的旗帜是‘醒狮运动’。什么叫做‘醒狮运动’?我们中国绰号‘睡狮’,我们中国四万万人就是四万万睡狮。……睡狮要求安睡,须得个个睡狮一齐醒来,合力扫清一切家内家外的小窃大盗。这件事情,我们就叫他‘醒狮运动。’换句话说,醒狮运动就是中国国家主义的运动。”④为完成盖尔纳意义上的“民族再造”,国家主义派理论中有三个方面值得注意。
首先,国家主义派虽与其它各派一样以国家富强为目标,但与当时很多论者,尤其是五四以后的论者不同的是,国家主义派并不因中国的落后而鄙薄传统文化。他们清醒地认识到,虽然中国以西方为师法的对象,但中国不可能抛弃自己的文化而全盘接受西方文化,而且更重要的是,试图这样做只会使中国失去自己的特质而必然沦为西方的附庸。曾琦和李璜在解释国家主义时都曾引用过这样一句话:“国家主义乃是疾视一切不以国家的旧信仰为根本的学说。”国家的旧信仰就是一个国家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所形成的传统和文化,它以各种形式内化到国民的灵魂之中和内心深处,使国民以其特有的行为、思考方式区别于其他人群,从而使整个国家和民族具备独立于其他民族之外的特殊标志。国家主义派非常反对以经济、物质利益的角度分析“国性”。
其次,国家主义派主张大力发展国民教育以培养国民的民族意识。在盖尔纳的分析中,教育即接触和掌握工业化所需的高层次文化的机会,它是导致民族主义的一个关键性自变量。而国家主义派的理论中,教育则承担着两项任务,一是盖尔纳意义上的教育,即注重于国民素质的提升,使其与现代国家的要求相符合;二是对于民族性的培养,使国民能在教育的指引下形成充分的民族意识和为民族献身的精神。
再次,国家主义派反对国际主义,认为一切国际主义的理想和措施都是幼稚的,也是危险的想法。李璜更以反国际主义为国家主义概念一大要义。也正因此国家主义派极力反对孙中山国民党的联俄政策,认为这一做法明显是引狼入室。国家主义派极力主张以国家为出发点,安内攘外,“内除国贼,外抗强权”,国际主义的宣传往往因其无比动听而使人迷惑,辨不清政治斗争的真实局面,于国于民不利。
国家观和全民政治
前文将国家主义派的思想归纳为以民族主义为首要依归,但遗憾的是,我们很难将民族主义本身作为一种建设性的政治理论。这与民族主义自身的特点有关,盖尔纳在解释民族主义的定义时,将民族主义首先确定为一条政治原则,即“认为政治的和民族的单位应该是一致的”,其次是一种情绪,这种情绪是“这一原则被违反时引起的愤怒感,或是实现这一原则带来的满足感”,然后是作为一种运动,即由这种情绪所推动的运动⑤。可见,无论从政治原则、情绪,还是从运动来看,民族主义都表现为首先或主要地与实际政治有关,它只要求我们不惜一切地完成一个民族的政治构建,而不能给我们关于国家构建后政治生活具体该如何安排的有益提示。而且,盖尔纳甚至认为民族主义者自身的学说有很大一部分是“社会学角度的自我欺骗”,因此不值一提。但如果仔细考察国家主义派的言说,我们会发现,国家主义派远不止是盖尔纳意义上的“民族主义骗子”。为全面理解国家主义派的政治理论,我们应当更深入分析其建设性理论。
国家主义特色的国家观。国家主义(etatisme)政治思想最初随着德国浪漫主义的出现而逐渐发展起来,如果溯根求源的话,我们可以在关于国家主义最早的思想家名单上列上黑格尔、费希特、李斯特等人。国家主义在根本上将国家视为本质性的有其自身价值的存在物,而个人在国家中则仅仅作为国家的构成部分而存在,并只有在国家中才获得其本质属性和价值。陈启天对国家的性质作了明确而清楚的表达:“国家民族是一切个人家族的整体,个人家族只是国家民族的细胞,个人家族不能离开国家民族而求得光荣生存。”⑥与黑格尔将国家视为超越于社会之上的组织一样,“国家是全民的共同目的,不是一种功用或工具”。因此,在国家主义派那里,国家作为本源性的概念,明显体现着国家主义的特征。
另一方面,国家主义作为一种政策措施则又可以简单地概括为两个方面的倾向:一是于国内,要求国家在所有政治组成部分中占唯一的主导地位,国家高于个人与社会,个人与社会必须服从于国家;另一方面是就国际而言,国家主义的反对对象是自由主义,认为国家本身始终是国际社会的主体,其唯一目的是维持和促进国家利益,因此,国家主义一般反对自由贸易,如德国18世纪国家主义经济学家李斯特(Friedrich List)就明确反对“世界主义”的经济,主张国家对贸易采取保护主义政策。国家主义派在这一点上作了最清晰阐述的是李璜,李璜明确地将国家政治分为内、外两部分,主张“安内攘外”。于内主张干涉主义;于外则取保护主义。因此,在国家主义派理论中,国家的重要性是放在第一位的,这既与他们接受西方国家主义的思想有关,又与其民族主义的诉求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其实从国家主义本身起源于德国来看,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的诉求本来就非常明显。当英法国家己经完成民主革命或改革,正致力于现代国家建设的时候,德国还处在试图脱离封建时代的痛苦时期。当拿破仑的军队蹂躏欧洲的时候,德国尚未完成统一。这种状况下产生民族主义的思潮是很合理的,而国家主义的思想也同时随着民族主义的要求而出现。近代中国的国情正如17、18世纪的德国一样,内忧外患交替。无独有偶,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在这一时期也被很多中国知识分子所接受。
全民政治理想。国家主义派并不完全局限于对国家核心地位的强调,近代中国刚刚结束封闭的专制帝国时代,新兴知识分子们一方面对西方的民主自由思想趋之若骛,另一方面也不能接受中国的将来仍然是一个人民没有任何权力和自由的专制国家。国家主义派虽然极力宣扬国家主义,他们也不是没有意识到对国家地位的过分强调会抹杀人民的民主权利与自由。
国家主义派的余家菊曾经有一篇名为《国家主义释疑》的演讲,专门对向国家主义派提出的质疑作出回应辨答。余家菊认为国家主义与个人自由并不冲突。国家主义派虽然强调国家的重要性,但同时也强调保护个人自由。为此,国家主义派又不断地强调自由与民主的重要性。几乎所有的国家主义派的成员都提出过民主自由的价值,其中李璜的论述最为全面和到位。李璜直接引用卢梭的《民约论》来论述国家的政治权力必须以国民公利(当然包括自由)为依归。
国家主义派对民主政治的诉求最完全地体现在其“全民政治”的主张上,他们称“全民政治”是其“政治建设理想”,“就是全国民众合治,就是真正的民主主义的政治。”国家主义派主张“全民政治”,认为国家不能只是某个群体的国家,而应该是全民的国家,否则国家仍然只是由一部分所“私有”,仍然不是一个现代的国家。国家主义派的全民政治理想的确反映了其在国家主义理论之下的民主自由要求。
结论
本文将国家主义派的理论主张大致分为三个主要部分:首先是民族主义的诉求,寻求民族独立与民族崛起,这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普遍理想,而国家主义派则集中和理论化地表达了这一要求;其次是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始终是以政治上建国为目标的,国家主义则同时体现了民族主义的激烈要求,也表达了在国家构建上的主张;最后是全民政治的理想,国家的构建并不能承诺一个好政治的出现,在危难时刻确实需要一个强国家权力的存在,但对于长久的政治理想而言,民主与自由则必然是国家长存、人民幸福的保证,再者,民主对于当下国民性和民族凝聚力的养成也是有巨大作用的。如此看来,国家主义派已经很好地表达了一个民族在寻求民族崛起和国家建设方面的建设性蓝图。
国家主义派的理论对于我们今天有其重要的借鉴意义,它至少可以在两个方面给我们以启迪:首先,在我们当前国家的建设方面,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国家的重要性,失去了国家的保护,任何民族或文化都不可能长期存在下去并保持其活力;而另一方面民主又是一个国家必然的归宿,它是一个国家或民族生命力的保证。其次,对于我们认识当前民族问题,国家主义派的理论也告诉我们:所谓民族性和民族群体的内部凝聚力不是自然存在的,是需要人为地去“创造”的,而民族主义者(我们可以将很多分裂势力的领袖称为民族主义者)的最终目的是建立一个属于并保护他们自己心目中“民族”的国家,而无论他们提出什么样动听的、带普遍主义色彩的口号,包括民主、公民投票等等。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在站博士后)
【注释】
①②李璜:《释国家主义》,载《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资料选集》(上册),高军等编,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12页,第312页。
③④陈启天:《醒狮运动发端》,载《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资料选集》(上册),高军等编,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33页,第332页。
⑤[英]厄内斯特·盖尔纳,《民族与民族主义》,韩红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第1页。
⑥《抗战与人生观改造问题》,载《新社会哲学论》,上海商务印书馆,1946年,转引自高军、王桧林、杨树标主编:《中国现代政治思想评要》,北京:华夏出版社,1990年,第275页。
责编/许国荣(实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