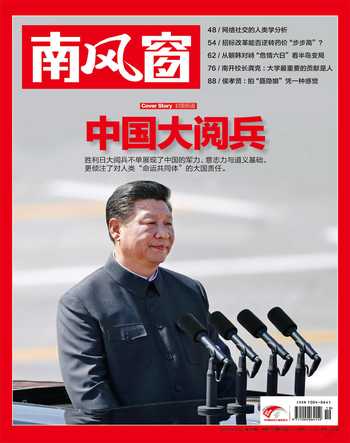黑马迭出的美国两党隐形初选
刁大明
“他们去了华盛顿,然后就软弱了……我绝对不会这样,我保证。”美国地产大亨唐纳德·特朗普在8月29日全美共和党团体联合会年会上,矛头直指华府圈内人。在6月16日正式跳入人满为患的共和党选战池塘之时,特朗普未必预料到将收获梦幻般的崛起:从7月中旬至今始终领跑在全美以及艾奥瓦、新罕布什尔等关键州的初选民调。在与其他16位参选人对比中,特朗普的某些民调支持度竟然高达25%以上,超过了杰布·布什、本·卡森或者斯科特·沃克、泰德·克鲁兹等第二、三名的总和,颇令具政治经验的党内对手唏嘘不已。

特朗普在民调中异军突起,惊呆了一众正统的参选人。
与特朗普意外领先同样令人讶异的还有民主党的吊诡选情。根据最新民调,佛蒙特州国会参议员伯尼·桑德斯正在加紧缩短与希拉里的差距:在全美范围内,桑德斯的支持率已可迫近30%,而希拉里则滑落到50%的红线以下。即便是在关键州艾奥瓦,希、桑两人以37%对30%几近打成平手,而这个数字在3个月前还是极为悬殊的57%对16%。
特朗普和桑德斯两匹“黑马”的跃出,搅乱了以往关于布什家族对决克林顿家族的选情预判,但仔细看却并未跳脱近年来美国政治的运行惯性,只能用“形势比人强”来形容了。
截至7月30日,胜算渺茫的弗吉尼亚州前州长吉姆·吉尔莫搭上末班车,2016年大选的共和党初选已挤入了17位主流参选人,为1970年代共和党采纳初选制度以来参选人数量之最。对照政治光谱,这些参选人可分几类:具州长执政经验的温和务实派,代表人物如杰布·布什、克里斯·克里斯蒂、乔治·帕塔基等;具国会立法经历的意识形态派,代表人物如马可·卢比奥、泰德·克鲁兹、兰德·保罗甚至里克·桑托勒姆等;身为州长、价值观又极保守的跨界参选人,如斯科特·沃克或鲍比·金达尔等。此外,像特朗普、卡森、卡莉·菲奥莉娜等非政治人物的“乱入”曾一度被认为是纯粹的“打酱油”行为,直到特朗普在民调中异军突起,惊呆了一众正统的参选人。
特朗普的蹿红与其具有其他政治人物并不具备的跨界知名度与影响力大有关系。根据针对熟悉度的民调显示,即便是头顶着“总统世家”光环的杰布·布什也被26%的受访者认定为“没有太多听说过”,而像沃克这样的一州之长在威斯康星之外的认知度更为可怜,不熟悉他的民众达到了37%。颇具讽刺的反差是,对特朗普了解不多的受访者在同期内只有8%。特朗普的名字,在耸立于城市中心的特朗普大厦上、在电视真人秀或脱口秀节目中、在一本本讲述实现“美国梦”的成功学传记里耳熟能详,足够锁定特朗普在隐形初选中的先入为主。8月6日共和党总统初选首场辩论因吸引到2400万观众而位列收视率最高的非体育电视节目,也得益于公众对特朗普的狂热关注。
虽然特朗普不具备传统职业政治人物的稳健台风,还多次口无遮拦地发表“政治不正确”言论、甚至把政见演说直接弄成了搞笑脱口秀,但他身上也的确潜藏着某种无可替代的竞选特质。比如,这位40亿身家的成功商人完全能够在联邦法规的允许下“自给自足”地确保竞选经费的持续支撑。虽然富商竞选公职往往失败,比如执掌世界摔角娱乐公司(这里“摔角”有别于“摔跤”)的林达·麦克马洪,两度角逐康涅狄格州国会参议员席位均惜败,但至少如今的特朗普不必像其他对手那样殷勤地跑到加州去拜见因挥金如土而招致骂名的科赫兄弟了。
更重要的是,特朗普巧妙地积聚起共和党阵营各派系的最大公约数:他出身商业,自然能够满足传统商业利益温和派的要求;他言论激进保守,恰好符合意识形态宗教保守派的口味;而他非华府圈内人甚至是“政治素人”的身份标签又迎合了公众反感美国政治极化僵局、迫切渴望彻底改革的内心状态。甚至,特朗普不尊重女性、歧视拉美裔等少数族裔的言论,也被不明是非地认定是“真性情”的表露,颇令共和党草根基本盘心醉。
特朗普的民意崛起,基本上与2012年大选隐形初选期间佩里、赫尔曼·凯恩、纽特·金里奇、桑托勒姆4位参选人从2011年8月到2012年3月之间接连领先米特·罗姆尼、占据民调榜首各一个半月左右的狗血连续剧如出一辙。其时,4人的先后接棒领先凸显了共和党阵营对政坛老将罗姆尼的不认同甚至拒绝,希冀推出反传统、反建制派候选人的狂热倾向。
与前次相比,特朗普目前也只是以两个月的时间领跑民调。他可能像2012年的4位参选人一样,在不久的将来被喜新厌旧的民意替换下来。孟莫斯大学8月31日公布的一项地方民调已显示,卡森在艾奥瓦州以23%追平了特朗普,这极可能是领跑者接棒的预备发令枪。如果特朗普在共和党内出线无望,可能会以独立人士或第三党的身份直接投入总统大选环节。
客观而言,无论特朗普以哪种形式继续竞选,都丝毫无助于共和党夺回总统大位。如果特朗普被民意抛弃、自己也过足瘾而不再恋战,则可能是造成伤害最小的情形。不过,数月来面对一个“怪咖”作祟束手无策的杰布们,又如何能让选民相信他们具有能力与资格来领导国家应对内外挑战呢?如果特朗普奇迹般地获得提名、在总统大选中与希拉里们对决,他目前的初选优势都难以在大选两党对比中延续,甚至会沦为吓跑中间选民的软肋。更为严重的是,与特朗普相比,目前任何一位民主党参选人都享有更多政治经验,这也会让共和党的2016年总统竞选更像是一个庸俗笑话。而如果特朗普最终选择独立参选的话,他势必将明显分散共和党的票仓,进而让民主党人躺着也能进白宫了。
在特朗普领先共和党初选民调1个月后,民主党选情在暗流涌动中突遇拐点。8月11日,富兰克林·皮尔斯大学和《波士顿先驱报》共同进行的民调显示,桑德斯在新罕布什尔州以44%对37%首次超越希拉里。8月16日,桑、希、特3人同天在艾奥瓦造势。桑德斯不但吸引了明显多于希拉里的支持人群,而且在民调中以52%比41%再次击败前第一夫人。就在17日,桑德斯在俄勒冈州波特兰的造势活动竟吸引到了2.8万人,其中有9000人在无法进入会场的情况下决定留在场外,通过同步扬声器聆听了桑德斯的演讲。
这位现年73岁的资深国会议员,从参选之初就被认为是所谓的“议题候选人”,即并不谋求也毫无希望谋求最终提名,只是以自身存在来强化选举议程对某些具有平民主义色彩议题的关注。桑德斯始终以与民主党结盟的“独立身份”示人,实则代表了自由派政治势力中的民主社会主义立场,强调对中低层平民权益的捍卫,从就业到收入不平等,从规制华尔街到阻断金钱对政治的控制,从彻底的移民改革到真正的族裔平等,等等。
桑德斯的亲民立场,同与华尔街维系密切关联的希拉里形成了鲜明反差,一定程度上也收编了原本推举马萨诸塞州国会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参选的左派群体。更令人惊喜的是,由于政治生涯起步于1960年代,桑德斯依然保留着某些那个激荡时代特有的批判精神与运动热情,这种带有“革命范儿”的竞选足以令民主党年轻选民找回那种澎湃的新鲜感。
面对自今年3月持续延烧的“邮件门”,本来已背负着“王朝政治”、“奥巴马烙印”等负面资产的希拉里逐渐陷入了新的且深不可测的泥潭之中,民众信任度也大打折扣。随着希拉里选情变数的扩大,桑德斯这厢也就水涨船高。但冷眼看去,桑德斯显然无法成为第二个奥巴马:他长期抨击金钱对政治的控制,因而竞选经费主要来自小额捐款,缺乏大金主支持,可谓杯水车薪,难以长时间维持全国范围内的竞选活动;他目前的民意斩获大部分得益于同样存在于民主党群体内的反主流、反建制的思潮影响,而他本人的政治立场过于极端与理想化,未必能令民主党主体选民接纳;更为关键的是,年长希拉里6岁的桑德斯根本跟不上民主党新世代的视野与诉求,与奥巴马的“变革魅力”可谓天壤之别。

桑德斯始终以与民主党结盟的“独立身份”示人。
正是由于对希拉里白宫前路的愈发担忧以及对桑德斯可选性的强烈质疑,民主党党内才相继传出关于现任副总统拜登、甚至是卸任15年的前副总统戈尔有意出手的小道消息。由于2016年总统大选的揭幕战即艾奥瓦初选被推迟到2月1日举行,从而在理论上还是为拜登创造了一些闪转腾挪的时间与空间。相比戈尔隐退太久而难以组织有效动员,在过去6年中继续推高副总统权势的拜登还是有实力放手一搏的。
当然,一旦拜登参选,民主党初选天平的砝码将落到曾表达期待“像里根那样有一个老布什接盘”的奥巴马手中。基本可以肯定的是,即便拜登遵从早逝长子遗愿而宣布参选、并得到奥巴马背书,也未必能摇身一变,充当起希拉里白宫路上的拦路猛虎。反而,希拉里甚至可以将奥巴马政治遗产中的负面因素统统切割给副总统拜登。真若如此,TPP伤害的工会利益、伊朗核协议疏远的犹太裔选民、美古复交得罪的古巴裔美国人,至少不会将账全部算到希拉里头上了。
不论是特朗普还是桑德斯,目前两党隐形初选中涌现出的“黑马”现象,不约而同地流露出公众对现行精英政治的不满与反抗。特别是在金融危机前后,美国政治运作显然难以及时而高效地回应国家内政外交的诸多挑战,甚至酿成了茶党、占领华尔街等抗争性社会运动。
即便社会运动暂且偃旗息鼓,其思潮依然萦绕于美国政治舞台,并塑造着最近数次总统和国会选举的基调。其中突出的倾向就是对在位政治圈内人的极度失望与不信任,希望选出非典型的政治人物即圈外人来换取有效的变革。这一趋势不但适用于茶党由社会运动转为政治势力的蜕变及其推动的共和党党内的新陈代谢,也部分解释了2008年奥巴马击败希拉里的初选胜利。而今,这种浪潮并未因“变革者”奥巴马的亲历亲为而退却,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比较而言,奋力重返白宫的共和党党内显露出颇为浓烈的愤怒情绪,直接的表现就是对特朗普、卡森甚至菲奥莉娜等人的无厘头追捧。
时至今日,美国两党政治中反传统、反主流、反在任者以及反建制的趋势,尚未酿成重大的政治失灵,即并未在总统等关键职位的选举中遴选出毫无政治经验、仅仅代表民粹潮流的候选人。不过,面对这种愈来愈近的可能性,美国政治精英在尊重民意的基础上,有必要开启针对初选制度的新一轮改革。
自1972年民主党首次采纳总统初选以来的40多年中,两党各自都曾对各州初选时间的前置问题、党内精英权重与基本盘参与的平衡问题进行了多次改革与调整。作为一种党内民主的体现,如何有效保障民意表达,又将民意控制在理性向度内,始终是初选制度设计的最大难点。
首当其冲的两个争议是:一方面,在各州初选制度的门槛设置上,到底是采取关门方式从而确保所谓的政党意识形态纯洁性,还是采取开门方式进而让参选人更多接受中间选民的考察?另一方面,在初选票数的分配上,到底有多少票分配给党内精英以便纠偏民意,又有多少票要直接交给民意决定?在民粹主义甚嚣尘上、媒体曝光度驱动民意支持度的今天,这些几乎如影随形的问题再次进入了矛盾焦点。如何避免选出一位最差的候选人,已是美国初选政治下一步躲不开的必答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