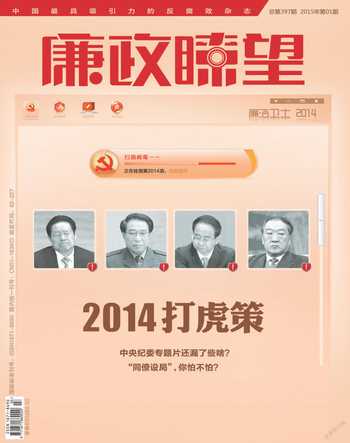梁漱溟之孙:“中国还需要一百个梁漱溟”
刘霄


虽身负“新儒学代表人物”,“国学大师”,“乡建运动领袖”等名号,但因50年代,与毛泽东的争执,让他深陷漩涡。时至“中国乡村建设110周年纪念活动”日前的举行,廉政瞭望记者参与梁漱溟纪念活动,并访问梁漱溟的后人和朋友,追忆这位儒道践行者逝去的某几个侧面。
被边缘的大师
梁漱溟之孙梁钦宁,依然记得多年前和祖父相处的日子。
80年代,西方迪斯科刚刚流入中国,梁钦宁喜欢在家跳迪斯科,他问梁漱溟:“爷爷,你喜欢吗?”90多岁的梁漱溟回了一句:“你喜欢就好。”
梁钦宁吃盐重,和梁漱溟在一张桌子上吃饭,使劲往碗里倒酱油和盐,爷爷也不说他。一次,梁漱溟拿来一本科普书,折角后用红笔勾出题目,递给钦宁,题目是“吃盐多等于慢性自杀”。
在梁钦宁的印象里,祖父虽然博学多识,但却很少说教,儿孙们的人生大事,学业选择都是由着自我。他的后辈发展也较为多元,有从商的,有心理学者,有建筑师,也有报社编辑。
梁漱溟可以说是一个文化守成主义者,但其实并不迂腐,相反尊重多元和包容心态,一以贯之融汇在他的生活里。在接触梁漱溟的后代,以及研究梁漱溟的美国教授艾恺时,他们都会表露一个感受:在中国思想史上这么重要的一个人,和同时期的主要人物相比,却被边缘了。
“文革”结束后,梁漱溟的生活慢慢恢复平静。有人说,梁漱溟在思想界被边缘,或因政治,或因思潮。早在北大任教时,以陈独秀、胡适、吴稚晖为首的反传统文化,提倡新文化的学者就对他“另眼相看”,他是北大教员里少有没有留过洋的人,人们认为他对西方的认识充满了局限,因提倡复兴儒学和传统文化,有人更称他为“封建余孽”。胡适笑话梁漱溟,“一个连电影院都没去过的人,怎么讲东西哲学”。而梁漱溟不以为然,说胡适根本不懂什么叫哲学。
但一个现实却是,梁漱溟从小受的并不是典型的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他甚至没有像胡适那样熟背过四书五经。梁漱溟的小学是在京城第一所洋学堂读的,学的有地理、历史、英文等现代科目,他平时读《启蒙画报》等当时最前卫的报纸,也读翻译过来的西方经典,如密尔和孟德斯鸠。
五四时期学生“火烧赵家楼”事件,引起了民主人士的极力声援,很多人大为赞扬学生的勇气,只有梁漱溟一人在报纸上发表言论,认为应遵循法治,让学生伏法,然后当庭特赦。
“我们是不同的,的确根本不同,我有我的精神,你们有你们的价值。各人抱各自那一点去发挥其对于社会的尽力,在最后的成功上是相成的。”梁漱溟当时这样回应着那些“民主派”们。
他对儒学的钻研始于青年,深触底层人民的苦难并曾两次自杀,他的生命经验告诉他,在西化的浪潮里,中国的问题仍须用中国自身的文化去解决。
一个通体透明的人
72歲的美国汉学家艾恺,至今清楚地记得1980年第一次见梁漱溟的情景,87岁的梁漱溟早早守候在家楼下,两人连续两个礼拜每天交谈四个小时左右,梁漱溟有时连水都不喝一口。
令艾恺惊喜的是,梁漱溟几乎和他的想象没有出入,他说,很大原因是梁漱溟表里如一,读其书如见其人。艾恺可能是非中国血统的汉学家里,能亲眼见到其研究对象的第一人。
梁漱溟是建国后少有的敢言知识分子,被外界所广知的是,1953年与毛泽东发生的摩擦。此后,常常被毛泽东请入中南海对谈的梁漱溟,再未与之单独会面。80年代,梁漱溟曾到过一次毛泽东的故乡韶山,他对自己当年的行为做了一个反思。“当时是我的态度不好,讲话不分场合,使他很为难”。
1966年的某天,红卫兵冲入梁漱溟的家中,一路摔砸,将他住的房子设为“司令部”,赶他与妻子去放柴火的偏屋住。72岁的梁漱溟与老伴睡在地板上,没有被子,就把毛巾系在腰间防止着凉。白天打扫厕所,晚上拿着红卫兵给的稿纸写“罪行交待”,在那些稿纸上,他写出了《儒佛异同论》、《东西方学术概观》。
1974年2月24日,81岁的梁漱溟提着鼓鼓囊囊的皮包走进政协会议室,把讲稿放在茶几上,站起来向大家鞠了个躬,做了题目是《今天我们应当如何评价孔子》的演讲,公开表明自己不批孔,只批林。
学者阎秉华评价,1953年的事没有改变他,他再次触动权威,这在解放后的知识分子中是很少见的,有人因言论惹祸后,噤若寒蝉,再也不敢发声。
从1974年开始,梁漱溟参加专门批斗自己的大会小会将近一百场,他每会必到,以沉默对待,中场休息的时候跑出去打太极拳。
梁钦宁对那段历史仍心有余悸,他现在主要负责祖父生前史料,并推广梁漱溟思想。“文革”过去后,他问祖父:“爷爷,您就不生气吗?”他淡淡地回了句:“他们都还是十五六岁的孩子,和他们生什么气。”
在梁漱溟的后人看来,与老舍等人的命运不同,他能躲过“反右”,文革等劫难,全因那份静气,喜怒并不形于色。他的另一个孙子梁钦东说,“他在家很安静,安静得就像家里没有这个人。”梁钦宁在受访时认为,梁漱溟对权力的零欲望保护了他,他多次谢绝了让其到政府做官的邀请。
一个通体透明的梁漱溟,是后世对他最多的评价。
不常见的中国知识分子
梁漱溟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是在1987年11月中国文化书院的演讲上,他戴着标志性的瓜皮帽,瘦小的身躯坚持站着做完了讲演。
在演讲中,一个令人动容的瞬间是,他情绪有点激动,伸出手来不时敲打着演讲台,94岁的梁漱溟撕扯着嗓子大声道:“我不是书生,也不是学问家,我是一个要拼命干的人,我一生都是拼命干。”
梁漱溟是中国知识分子中不常见的,将自己的理论转化为实践的人,艾恺所称“最后的儒家”,便是形容他知行合一最贴切的概括。
距今已经110年的中国乡村建设史,梁漱溟必被书写于其中。
1927年,梁漱溟离开北大,辗转广东、河南等地筹备乡村建设计划。他不想和只会坐而论道的知识分子呆在一起,他写道:“知识分子徜徉于空气松和的都市或租借,无望其革命,只有下乡而且要到问题最多痛苦最烈的乡间,一定革命。”
他认为中国人不会过团体生活,乡建应是基层群众自己动员起来的运动。梁漱溟乡村建设的主要任务就是为中国创造团体组织的形式,通过这些组织形式,开展经济发展、技术普及、教育和政治改革。
梁漱溟曾有个说法:“中国人民好比豆腐,官府力量强似铁钩,亦许握铁钩的人,好心好意来帮豆腐的忙;但是不帮忙还好点,一帮忙,豆腐必定受伤。”艾恺喜欢重复这个比喻,他在讲演中,用手比划着钩子和豆腐的关系,认为梁漱溟的改革,意在改变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关系。
山东的邹平成为了梁漱溟践行其乡建理论的实验田,也很快成为了乡村建设运动的中心。对比这个时代的乡村建设,如乡村图书馆等项目,梁漱溟乡建的精髓在哪里。梁钦元在回答本刊记者提问时这样评价:“我祖父的乡建理论,更多的是教会农民怎么去用一种民主的生活方式生活。”
随着后世研究新儒学的兴起,政治冰河的解冻,这位中国历史上“最后的儒家”,重回大众的视线。他的后辈深信其思想对后世中国的价值,以期待其改造中国的思想会被记得和传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