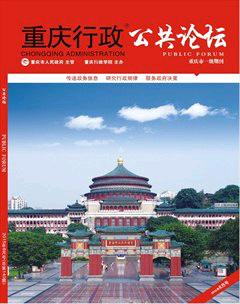论新刑诉法下指定居所的监视居住制度的适用
谢徽+陈亮+张强
监视居住制度是我国上世纪五十年代从前苏联照搬过来的制度。有学者认为该制度存在适用条件模糊、界限难以把握等问题,主张取消该制度。[1]也有学者认为,该制度是否保留,取决于是否有其他强制措施可以取代它,有则可以取消,反之则不可。[2]新刑诉法不仅没有取消该制度,反而增加了该制度的条款,明确了指定居所的监视居住制度,这表明该制度在刑事诉讼中具有其生命力,体现了新刑诉法中保障人权的基本价值要求。针对其适用条件,现予以讨论。
一、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制度沿革
《刑事诉讼法》自1979年7月1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之后,又历经了1996年以及2012年的两次修改。对于“监视居住”制度的规定也前后有三种不同的表述方式。
(一)1979年《刑事诉讼法》的规定
1979年《刑事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一、二款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根据案件情况,对被告人可以拘传、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被监视居住的被告人不得离开指定的区域。监视居住由当地公安派出所执行,或者由受委托的人民公社、被告人的所在单位执行。”由该条文来看,并没有对监视居住的地点进行明确的规定,仅是用“指定的区域”进行了模糊的规定。而对于该条规定也没有相关的司法解释进行进一步的说明。
(二)1996年《刑事诉讼法》的规定
1996年《刑事诉讼法》对于“监视居住”制度的规定,相较修正之前的规定,有了较大的进步,“对监视居住的地点、适用范围、被监视居住人应当遵守的规定、违反规定如何处理均作了明确规定,更便于操作” [3]。其第五十七条第一项规定:“未经执行机关批准不得离开住处,无固定住处的,未经批准不得离开指定的居所”。该条已经明确提出了“指定居所”的概念。因此,“指定居所”的监视居住并不是2012年修正之后的创新发明,并且“指定居所”带来的变相羁押的滥用可能性也并非是修正之后才产生的问题。“指定居所”带来的这种被滥用的可能性至少自1996年就已经存在,甚至自1979年刑诉法颁布以来就在司法实践中存在。2012年新修正的《刑事诉讼法》对于指定居所的监视居住有了新的规定,将在下一部分详述。
二、指定居所的监视居住的适用条件
新《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三条第一、二款规定:“监视居住应当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住处执行;无固定住处的,可以在指定的居所执行。对于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特别重大贿赂犯罪,在住处执行可能有碍侦查的,经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批准,也可以在指定的居所执行。但是,不得在羁押场所、专门的办案场所执行。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除无法通知的以外,应当在执行监视居住后二十四小时以内,通知被监视居住人的家属。”
(一)符合监视居住的条件
关于监视居住的适用条件,新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二条第一、二款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对符合逮捕条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监视居住:1.患有严重疾病、生活不能自理的;2.怀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3.系生活不能自理的人的唯一扶养人;4.因为案件的特殊情况或者办理案件的需要,采取监视居住措施更为适宜的;5.羁押期限届满,案件尚未办结,需要采取监视居住措施的。对符合取保候审条件,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能提出保证人,也不交纳保证金的,可以监视居住。”
对于新修正的监视居住的适用条件,有几点值得注意:其一,明确“非羁押强制措施优先原则”的同时,规定监视居住制度只作为特殊情况下,取保候审制度的替代性措施。其二,基于人道主义等的考量,规定在符合羁押逮捕的情况下,由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身体原因或者孕妇、处于哺乳期的妇女以及家有未成年人无人照料等原因,可以视情况适用监视居住制度,如新法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一)至(三)项之规定。[4]
(二)无固定住处
新《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三条第一款第一句规定:“监视居住应当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住处执行;无固定住处的,可以在指定的居所执行。”由此可见,“无固定住处”是适用“指定居所”的监视居住的重要条件之一。
1. “固定住处”的含义
《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九十八条的规定:“固定住处,是指犯罪嫌疑人在办案机关所在的市、县内生活的合法住处;指定的居所,是指公安机关根据案件情况,在办案机关所在的市、县内为犯罪嫌疑人指定的生活居所。”该条规定对于“固定住处”有两个限定条件:其一,为办案机关所在的市、县内;其二,为“合法”。就笔者看来,对于住处合法性的要求并不存在问题,而对于地域的限制则不无争议。对于地域的要求在司法实践中会方便办案机关的管辖和操作,但是实际上是缩小了“固定住处”的范围,而扩大了“指定居所”的适用,对于嫌疑人的权利的保护是不利的,也与修正之后的新法的立法精神相悖。2012年10月16日通过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中,第一百一十条第二款规定,“固定住处是指犯罪嫌疑人在办案机关所在地的市、县内工作、生活的合法居所。”对比该规则与之前的规定,固定住处的含义增添了“工作”一词,同时将“住处”改为了“居所”。从字面上理解,该修改扩大了固定住处的范围,将工作的合法居所也纳入到了固定住处的含义内。
笔者认为,住处是与一个人的生活相联系的概念,指的是其生活主要内容和休息、饮食相关的地点。对刑事诉讼法中住处的理解不能按民事诉讼法关于住处和居所的含义进行理解,因为,二者所要解决的问题和确定的目的是不同的。[5]对于居住地“经常、连续、固定”的三个要求,也符合新法对于住处“固定”性的规定。
2. “指定居所”的范围
如上文所述,公安部规定中“指定居所”为公安机关为犯罪嫌疑人指定的生活居所。而《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中规定,“指定的居所应当符合下列条件:具备正常的生活、休息条件; 便于监视、管理;能够保证办案安全。”而学术界的观点也大致如此。但是新法规定了不能作为“指定居所”的情形,即不得在羁押场所、专门的办案场所执行监视居住。endprint
然而,新法并没有解决“住处”或“居所”的范围问题。原来的《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中将其表述为“市、县内的生活的”合法住处或居所。但是,这里的“住处”与“指定居所”具体的空间范围又该如何理解,是理解为被监视居住者所居住的房屋以内的空间,还是理解为以被监视居住者所居住的房屋为中心的、用以维持其正常生活而应去的工作和生活、学习的场所呢?而且,对于不同性质、社会危险程度不同的案件,其可以活动的范围是否一样?这些问题在新刑事诉讼法中均未提及。有学者认为,指定的区域应当是指犯罪嫌疑人有一定的活动范围,不能只限于一个房间。[6]笔者认为从保护被监视居住者的权利的角度出发,应当将居所理解为以房屋或指定之房屋为中心的、用以维持其正常生活而应去的生活场所,否则监视居住将变成同羁押强制性相同的强制性措施。并且在我国这样一个国家,其还极有可能被用作侦查的手段和技巧。但是同时又不能将其范围扩得太大,这样又会强制性过小,而与取保候审混同,并且实施监视居住的成本也会相当高。
笔者认为,监视居住中“住处”和“居所”的范围的大小,体现了我国刑事政策的倾向,而在司法实践中,并不是说监视居住就是将人身自由度放到最大,这样的做法不利于强制力的保证,不利于案件事实的调查,也就从根本上否定了监视居住最初的程序设计与价值追求,其关键的核心就在于能够发现事实真相而又能够最大可能的保障嫌疑人的正常生活。笔者认为应当尽快制定关于新刑诉法相关的司法解释,对该问题给予阐述,明确说明我国刑事政策关于这个问题的倾向,笔者认为在实践中应当采取相对宽松的范围,以更好的保护被监视居住人。
(三)对于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特别重大贿赂犯罪,在住处执行可能有碍侦查
在实践中,无固定住所的情况非常少见,以至于前一种情形下的指定居所的监视居住制度甚少使用,[7]因此另外一种情形就值得更加的关注,即根据案件的性质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的划分。新《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三条第一款第二句规定:“对于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特别重大贿赂犯罪,在住处执行可能有碍侦查的,经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批准,也可以在指定的居所执行。”笔者认为在无固定住处时,如需采用监视居住措施的,无论犯何种罪名都应当适用“指定居所”的监视居住,而在有固定住处的时候才去考虑新法中规定的上述三种犯罪的特殊情形。以下对该条款进行界定。
1. 三种罪名的界定
首先,对于“危害国家安全犯罪”的范围应当没有分歧,即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第二编第一章的所有罪名。
其次,对于“恐怖活动犯罪”则存在不同的理解。有人认为“恐怖活动犯罪”是指我国《刑法》中带有恐怖字样的罪名,即“组织、领导、参加恐怖组织罪”(第一百二十条)、“资助恐怖活动罪”(第一百二十条之一)、“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第二百九十一条之一)。有人认为,“恐怖活动犯罪”是指各类恐怖犯罪的行为,包括“劫持航空器罪”(第一百二十一条)、“劫持船只、汽车罪”(第一百二十二条)、“暴力危及飞行安全罪”(第一百二十三条)等一系列罪名,而“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属于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尚未危及不特定多数人的安全,不宜列入“恐怖活动犯罪”。[8]
再次,关于“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有人认为其涉及刑法分则第八章贪污贿赂罪中的七项罪名以及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罪中三项罪名(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和对外国公职人员、公共组织官员行贿罪)。但与前两者的罪名相比,特别重大贿赂犯罪的社会危害程度相对较低,对于此罪名的界定应更加审慎,防止犯罪嫌疑人人权的被侵害。有学者认为,从最高人民检察院提出修法建议的初衷看,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罪中的犯罪并不在其列。“特别重大”应当理解为刑法第八章规定需要判处重刑的贿赂犯罪。[9]那么,在“特别重大”的限制之下,我们就需要对第八章贪污贿赂罪中的七项罪名进行进一步的审查,其中“对单位行贿罪”、“介绍贿赂罪”等,处罚较轻,不属于“特别重大”的范畴。同时,对于“特别重大”本身,应当更加予以明确,不仅应当理解为数额超过一定的限制,而且应当综合考虑案情,[10]应当在把握强制力与人身自由度中寻求解决问题所必须的平衡点,通过对案件本身的了解,以便于发现事实与保障人权为目标,综合考量,最终做出合理的决定。
2. 在住处执行可能有碍侦查
“在住处执行可能有碍侦查”一句的规定是对上述三种罪名适用指定居所的监视居住的另外一个限制。笔者认为,本次刑诉法的修正,在很大程度上是扩大了监视居住的适用,但是对指定居所的监视居住进行了限制,因为,指定居所的监视居住相对一般的监视居住而言,对于人权的限制更大,不能不对其适用加以限制,否则便会侵害嫌疑人的合法权益。因此,不能将上述三个罪名的适用于本句的限制割裂开来,而应当采取“罪名+有碍侦查”的公式来作为适用条件。
秩序与自由是刑事诉讼的基本矛盾,国家的权力和私人权利如何界定,罗科信认为,“国家侦查权对人民权利侵害的许可范围是,使无罪者不会受到不法的调查及过当的被侵害自由,而即使是对有罪者,亦应顾及其所有的辩护权益。” [11]在国家安全和公共利益与嫌疑人的利益之间,新修正之《刑事诉讼法》倾向于保护国家安全和公共利益,同时又尽可能的保护犯罪嫌疑人的权利,因此,对于上述三种犯罪采取更为严格的监视居住。
三、总结
刑事诉讼法的修正对于监视居住的范围进行了扩张,但是对于指定居所的监视居住却采取了谨慎态度,以此来更好的保障嫌疑人或被告人的权利。而对于指定居所的监视居住的适用,首先应当符合新修正的监视居住的规定,其次判断是否有固定住处,若没有固定住处,那么就适用指定居所的监视居住;在有固定住处的情况下,若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特别重大贿赂犯罪,在住处执行可能有碍侦查的,则也可以适用指定居所的监视居住。endprint
必须指出的是,刑诉法中关于监视居住适用条件的具体用语不完善,如在符合监视居住情形时,应该以“应当”这样的确定性词语去替换原文中“可以”这类或然性词语。[12]笔者认为,刑诉法是部“小宪法”,除了法的本质外,还有保障人权的基本要求,法律不能面面俱到的规定好每种情形,这是给予司法机关在具体的案情面前选择更加适合的措施的可能性,并且与拘传、取保候审等强制措施的用语相适应。
固然,指定居所的监视居住制度的适用除了上文所述关于条件方面条款的相关解读外,在司法实践中,更加离不开司法机关对于该制度的具体适用。在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进行执行的过程中,离不开的是对该制度运行的监督,如加强检察机关对适用该措施决定的审查,严格确定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期限,防止期限过长造成的变相羁押的倾向,完善犯罪嫌疑人及其家属、代理人的知情权、申诉的权利等等。
参考文献:
[1]樊崇义等.刑事诉讼法再修改理性思考[M].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2]陈光中.陈光中法学文集[C].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
[3]关于检察机关侦查工作贯彻刑诉法若干问题的意见[R].1996年12月31日最高人民检察院.
[4]郭烁.刑事强制措施的体系及其适用研究一一以非羁押性强制措施为重点.中国政法大学博士学位论文[D].(2011年11月).
[5]杨旺年.关于监视居住几个问题的探讨.法律科学[J].2001年第6期.
[6]陈光中.陈光中法学文集[C].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
[7]党广锁,赵丽萍.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法律监督初探.中国检察官[J].2012年第10期(司法实务).
[8[9]]尹吉.如何理解“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江苏法制报[N].2012年3月27日.
[10]陈光中,于增尊.关于修改后《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若干问题的思考”.法学[J].2012年第11期.
[11]【德】克劳斯·罗科信.刑事诉讼法[M].吴丽琪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12]陈媛.我国监视居住若干问题研究”.法制博览[J]2013年01期.
作者单位:谢徽,陈亮,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检察院
张强,澳门大学
责任编辑:宋英俊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