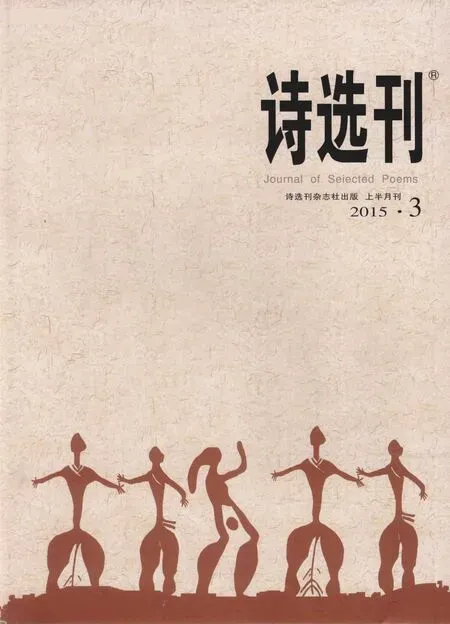整理石头
阎 安
整理石头
阎安
北方的书写者
我要用写下《山海经》的方式
写到一座山 仿佛向着深渊的坠落
山上的一座塔 落过很多鸟的尖尖的塔顶
它的原始的鸽灰色 我写下比冬天
更严峻的静默和消沉 写下塔尖上
孤独的传教士和受他指派的人
每五年都要清理一次的
鸟粪 灰尘和星星的碎屑
我甚至要写下整个北方
在四周的山被削平之后
在高楼和巨大的烟囱比山更加壮观之后
在一条河流 三条河流 九条河流
像下水道一样被安顿在城市深处以后
我要写下整个北方仿佛向着深渊里的坠落
以及用它广阔而略含慵倦的翅膀与爱
紧紧捆绑着坠落而不计较死也不计较生的
仿佛坠落一般奋不顾身的飞翔
我的故乡在秦岭以北
天下人都知道 秦岭以北
(有很多事情一直隐藏得很深)
是我的故乡
山上的月亮透着羞愧的红
像刚刚哭过的样子 它的河流在草丛中
而它石龛里的神佛 被香火熏陶
黝黑中透着红光 就像父亲的红脸膛
被生活和灰尘反复洗涤后
在黑乎乎的胡茬里 闪烁着
某种既压抑又温暖的光泽
天下人都知道 我的故乡
但他们不知道 这些年来拖儿带女在外漂泊
我一直喜欢在暗处沉默
(我也有这从故乡带来的性格)
在暗处 回想父亲在河边杀掉一头老牛后
丧魂失魄 一个人在山上狼一样号哭
红脸膛上老泪纵横
“我只能跑得更远 而无论我跑得多远
我的心里都是摆脱不掉的哭声”
它们继续追逐着那些通灵的牲畜
这些年 一个乡下人
看到真理后的悲惨心境
我和我父亲 我们一直羞于出口
天下人都知道 在我的故乡
牲畜的亡灵比人的灵魂
更长时间地折磨着生活
贫穷是一种古已有之的误会
它的树上不养鸟鸣
只养在秋天向下坠落的树叶
它的河里不养鱼 但养那种蛙鸣
在月夜里 它的叫声
刺穿河流中心蓬勃的草丛
一会儿像父亲的嘀咕
一会儿像婴孩的哭泣
使夜色更寂静更凄美
天下人都知道 我的故乡
父亲和母亲等着归土的村庄
如今显得更加空荡 某个冬季
等我回去以后
那已是父亲归山的日子
雪像白衣服一样紧紧地裹着
奔丧者木棍一样的身子
哭声像结冰的河道一样
蜿蜒而僵硬
天下人都知道 秦岭以北
那是我的故乡 和许多人的故乡
天下人不知道的是 如今那里的人
一天比一天少了
草丛茂盛 蛙鸣寂寥
珍 珠 劫
地球上好多来自天外的事情 比如珍珠
我是打小就决意要获取它的人
我由此也是未及成年就听到了命运的召唤
像逃离劫难一样逃离故乡的人
我爷爷知道我是外出谋取珍珠的人
他归天时我正在西藏 比他灵魂更高的山上
我第一次引颈眺望故乡 第一次
两手空空痛哭流涕
我父亲知道我是寻找珍珠的人
他在梦里能反复看见我
手拿珍珠头破血流的样子
他为此天天为我捏一把冷汗
夜夜为我做一场噩梦
我后来才知道 我们村上
那些从野外拿回珍珠的人
一个个都没有好下场:他们有的莫名其妙地发疯了
像山鬼一样终其一生沿着山脊狂奔
有的旁若无人 对天妄语 昼夜不止
有的在失踪多年后 突然传来消息
那个人已陈尸于异乡的街头
我其实一直在改变自己 比如前不久
我终于回到乡下老家
看望比记忆中的爷爷更为衰老的父亲
却发现只有他依然怀揣一颗至死不渝的心
在临别时一再叮嘱:
“城里珍珠多,喜欢你可以多看看
但千万不要拿它回家
好珍珠烫手也要命啊!”
虽说有些心不在焉 但我仍然像一个乖孩子一样
答应着父亲 一边答应
一边依然是向外走的人
依然是怀揣着灰尘和野性的一个人
一个多年寻找珍珠而不得的人
一个被来自天外的事情所左右的人
但我记住了那一刻 那一刻
傍晚的乡村已暮色苍苍
当父亲和送别的人渐渐隐入黑暗
我也渐渐隐入黑暗之后
我突然变得不能控制自己
在黑暗中徒然地举着空空的两手
禁不住热泪滚滚
异 乡 人
异乡人来到了北方
我的故乡
异乡人 就是那些操着外乡口音
外地面孔的陌生人 他们胖如母鸭
笨如蠢猪 却和我一样喜欢攀登高山
他们带来了满村子的风声
一条路要修到山上 巨石的悬崖将要炸掉
山上的麦浪 将要被驱赶到另外一座山上
只是山顶上的那棵树 有些神奇
正在研究处置方案
我曾经多次尾随他们
看他们冒着危险 喊爹叫娘往高处爬的样子
从后面默数着那些或男或女或肥或瘦的屁股
看它们怎样惊恐不安地扭动
有点幸灾乐祸 但还不至于仇恨
这好像不合常规
很多年中 我像失踪了一样
很多年中 我好像从未存在过一样
很多年中 我好像死了一样
我离开了故乡
我也成了一个异乡人
气球与空虚
地球就像一只令人出其不意的气球
里面是实的 外面是空的
在无边无际的空虚里飘荡着
在无边无际的空虚里飘荡着的气球一样的地球
它的头是重的 它的翅膀是重的 心也是重的
不费吹灰之力就碰落了一架飞机
碰碎了一只老鹰
甚至将不慎撞倒的一座山扔垃圾一样扔进了大海
从而把它们不得要领占领过的空虚
重又还给了无边无际 只有宇宙才配得上的空虚
从而使气球一样在无边无际的空虚中飘荡的地球
有了心脏一般既敏感又敦实的形状
和比心脏还要难以憋破的
但却能被空虚所憋破的气球所验证出的
全部空虚的真理
地 道 战
我一直想修一条地道 一条让对手
和世界全部的对立面 丈二和尚
摸不着头脑的地道 它绝不是
要像鼹鼠那样 一有风吹草动
就非常迅疾地藏起自己的胆小
不是要像蚯蚓那样
嫌这世上的黑暗还不够狠
还要钻入地里去寻找更深的黑暗
然后入住其中 也不是要像在秦岭山中
那些穿破神的肚子的地洞一样
被黑洞洞的羞愧折磨着 空落落地等待报应
我一直想修的那条地道 在我心里
已设计多年 它在所有方位的尽头
它在没有地址的地址上
但它并不抽象 反而十分具体
比如它就在那么一座悬崖上 空闲的时候
有一种闻所未闻的鸟就会飞来
住上一段时间 乘机也可以生儿育女
如果它是在某个峡谷里 那些消失在
传说中的野兽就会回来 出入其中
离去时不留下任何可供追寻的踪印
比如一个人要是有幸住在那里
只能用蜡烛照明 用植物的香气呼吸
手机信号会自动隐没
比如只有我一个人 才谙熟通向那地道的路
那些盯梢的人 关键的时候被我一一甩掉
他们会突然停下来 在十字路口
像盲人一样 左顾右盼
不知所措
我一直在修造着这样一条地道 或许
临到终了它也派不上什么用场
或许有那么一天 其实是无缘无故地
我只是想玩玩自己和自己
捉迷藏的游戏 于是去了那里
把自己藏起来
安 顿
你看到的这个世界 一切都是安顿好的
比如一座小名叫做孤独的山
已经安顿好了两条河流 一条河
在山的这边 另一条河
在山的那边 还安顿好每条河中
河鱼河鳖的胖与瘦
以及不同于鱼鳖的另一种水生物种
它的令人不安的狰狞
天上飞什么鸟 山上跑什么狐狸 鼠辈
河湾里的村庄 老渡口上的古船
这都是安顿好的
你看到的这个世界 安顿好了似的世界
还有厚厚的大平原 有一天让你恍然大悟
住得太低 气候难免有些反常
而你也不是单独在这个世界上
下水道天天堵塞 许多河流 在它的源头
在更远处是另外一回事情 许多的泥泞
和肮脏 只有雷电和暴风雨才能带走
你看到的这个世界 被一再安顿好的世界
今天令你魂不守舍 你必须安顿好
愤怒的大河从上游带下来的死者
河床上过多的堆积物 隔天不过就发臭的
大鱼 老鳖 和比钢铁更坚固的顽石
你看到的这个世界 别人都在安顿自己
你也要安顿自己 但这并非易事
你必须在嫉妒和小心眼的深处 像杀活鱼一样
生吞活剥刮掉自己的鳞片
杀掉自己就像杀掉另外一个朝代的人
杀掉自己就像杀掉
一条鱼
接下来 时光飞逝
可能大祸临头甚至死到临头了
你依然是一个魂不守舍的行者
还在路上 为安顿好自己
还有世界内部那地道一样多疑的黑暗
匆匆赶往别处
好鸟或假想之鸟
一只好鸟 是不会轻易飞越城市的
那是精疲力竭的事情
危险的事情
一只鸟飞过城市头顶
那一定是一只生病的鸟
一只眩晕的鸟
一只半昏迷状态的鸟
一只头脑已在火中死掉
而翅膀还活着的鸟
当然有可能它也是一只
好鸟
目前的形势仍然糟糕 好鸟
应该像传说中的云朵一样
居住在深山里
或者比山更深的什么地方
一只好鸟是不会轻易飞越城市的
协调者的峡谷
我曾是一个赶鸟的人
在北方的群山深处 从一座巅峰
到另一座巅峰 从一座峡谷到另一座峡谷
从一座树林到另一座树林
不断协调鸟与鸟
与树林子 与庙宇里冰冷的神和热气腾腾的香火
与潜伏在荒草中的属羊人和属虎人的关系
我甚至还得协调日月星辰
及其它们之间的关系
协调一场雾到来或离去之后
它们之间的关系
我不仅仅是用棍棒 同时也用语言
那些听着我说话长大的鸟
有时候它们会成群结队
飞向南方
(如果路过秦岭
不慎折翅而死那是另一回事)
在南方 鸟们落下去的地方
它总会叫醒那里的一些山水
另一些山水 继续着一种古已有之的睡眠
喜欢啼叫的鸟们
也会无奈而沉默地在寂静里
走一走 并不惊醒它们
我曾经长久地在北方的高山里
做着赶鸟的工作 与鸟对话
等待各种不同的鸟
自各种不同的季节 不同的方向
飞来又飞去
研究自己阴影的人
这个明显有点神经质的异乡人
戴着一顶宽边安全帽从春天走来
在远郊的一大块空地上作业
喜欢把脸藏到肩膀或帽檐的阴影里
终日背对着阳光的是他 伏地而作的背影
像侍弄一块草坪一样不停地捣鼓着
不断地亮出一些刀子或探测仪之类的东西
终日独自比画着 嘀咕着 甚至沉思着
仿佛即将执行一项不寻常的挖掘计划
这个装模作样的人 在荒地上从春天一直干到夏天
蹲下去又站起来的样子暴露了他的高大和从容
咧嘴一笑时暴露了他那整齐而洁白的牙齿
也暴露了他脸上一阵比一阵多的闪烁不定的阴影
但这个装模作样的人 秋天到来后突然不见了
仿佛消失了一般
那块原封不动留下来的大荒地则证明
从春天一直到夏天 他只是在草丛里作业
从未伤及到地皮和地面以下的东西
我后来才明白:这个夜深了才动身回城
遇到灯光就迅速闪入阴影中行走的人
其实只是一个简单的人 一个被自己的阴影所累
忍无可忍 要在旷野上摆开阵势
寻找如何才能彻底摆脱阴影的方案的人
鱼形的雪
我在旧邮局被玷污的玻璃橱窗中
取回被你的猩红热烧得发烫的雪
我在宇航局秘密基地的保险柜中
取回你在去年寄存的一场雪
我在迟迟不肯死去的草坪的背阴部分
取回背叛者面孔一样的冬青树
及其为它所深藏的阴郁的雪
我在旧书报亭一本旧杂志的黑白雪景的封面上
取回与黑暗同样卑污同样下流的雪
而今夜的雪 夹杂着星光被秘密分解的碎屑
它将落下一切已腐朽殆尽的形式
在孕妇羞愤难当的红晕里
雪将赤裸裸地堆起 梦中的尘土
以及它的全部鱼形的潮湿
中年自画像
在大海边住下来虚掷青春 在大海边
喝了整整十年(一个世代之久)海水
我曾被一种无人认识的怪物鱼咬过几回
跳到海里时被蓝海藻纠缠过几回
(有次还险些被拖下深渊)
我曾拜托水手和信天翁寄往海上的信
一件件石沉大海 喝着海水的等待
让海水拍打着的等待 没等到白了头
却让头发慢慢落光了后脑勺 露出葫芦之美
而一只从北方带去的蓝釉瓷杯
在逃离一场梦里袭来的海啸时
落地而碎 让我喝了一肚子海水的一个梦
以及与大海同样湛蓝的一堆瓷的碎片
同时葬身海底 让海水搓来搓去的黄肚皮
人到中年也未变成海青色的蓝肚皮
在大海边虚掷了全部青春 中年回到了北方
那最容易放弃怨恨也放弃伤怀的高纬度地带
如今我住在抬头就可眺望秦岭的地方
住在很多人天不亮就来打水的水井旁
住在一条隐姓埋名的河(南方叫江)流经的地带
我的不远处有一家戒备森严的飞机制造厂
稍远处据说还有一个秘密的航天器试飞基地
认识一些造飞机的朋友和一些精通
航天飞行秘密的人 如今是我肚子里
除了海水之外仅有的一个小秘密
现在我每天的工作就是有点失魂落魄地
守着我的小秘密
像一个疏于耕种的邋里邋遢的远乡农夫
每天无所事事地傻等着 每天睡很少的觉
一个翻山越岭 连滚带爬从海边归来的人
一个被大海和它虚无的湛蓝淘尽了青春的人
灰溜溜地回到了秦岭以北
如今已不事精耕细种的北方
一肚子瓦蓝瓦蓝的海水没处吐
朝朝暮暮近乎吊儿郎当的悠闲里所深藏的
沉默 和近乎荒唐的小秘密
也没人知道
春天或蓝
白昼折磨着天上的月亮
天空空虚的蓝
折磨着一架直升飞机
我的沉默和一架玩具起重机的颜色
强调着今年的春天 它的荒凉和鲜艳
堕落与美好 呵春天
从浅蓝到深蓝到黑蓝
仿佛一场假设的死亡
一个摘掉面具的男孩的命运就是
他正被无限制地拖下
一个去年就被白天鹅遗弃的
湖泊的深水
一种更深的蓝 一种由直升飞机
和天空频繁发生关系
而不断发出受折磨的嗡嗡声的春天
一种同时包含着同情和堕落的
属于这男孩的命运
而我相信这男孩 他的狂暴的身体
正在深蓝中的平息
我相信在被尘世的睡眠遗忘之后
他曾有的困惑 他对黑蓝的倾向性
就是他要心甘情愿地拖下去
把自己置身于真正黑暗的湖泊中
在那里 像面临最后的结局
他渴望白昼降临
好向天空索取干净的蓝 更多的
比春夏之交的蜉蝣还稠密的
像突然暴发的蓝藻一样性感地勃发的
像倾向于死亡而不可救药地下垂着的
蓝
炼 金 术
我是一个不屈的人 历尽多年周折之后
在一块被冻裂的巨石内部
我提取到了很多哭泣与几乎可以忽略的剧痛
我还是一个颇具神话色彩的人 乘粗心的园丁不注意
在被铁和玻璃控制多年的一棵树
和它委屈地开放着的花蕊中
我搜索出一个失踪的婴儿和一个说谎者
被钝器从后面击破的颅骨残片
其实我真正的身份是一个密探 精通炼金术
一直准备着远赴他乡开山炸石的行程
我将是那个走遍世界 比江湖传说还要神秘的
掌握着全部炼金秘方的人
整理石头
我见到过一个整理石头的人
一个人埋身在石头堆里 背对着众人
一个人像公鸡一样 粗喉咙大嗓门
整天对着石头独自嚷嚷
石头从山中取出来
从采石场一块块地运出来
必须一块块地进行整理
必须让属于石头的整齐而磊落的节奏
高亢而端庄地显现出来
从而抹去它曾被铁杀伤的痕迹
一个因微微有些驼背而显得低沉的人
是全心全意整理石头的人
一遍遍地 他抚摸着
那些杀伤后重又整好的石头
我甚至亲眼目睹过他怎样
借助磊磊巨石之墙端详自己的影子
神情那样专注而满足
仿佛是与一位失散多年的老友猝然相遇
我见到过整理石头的人
一个乍看上去有点冷漠的人 一个囚徒般
把事物弄出不寻常的声响
而自己却安于缄默的人
一个把一块块的石头垒起来
垒出交响曲一样宏大节奏的人
一个像石头一样具有执着气质
和精细纹理的人
我见到过的整理石头的人
我宁愿相信你也见过
甚至相信 某年某月某日
你曾是那个整理石头的人
你就是那个整理石头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