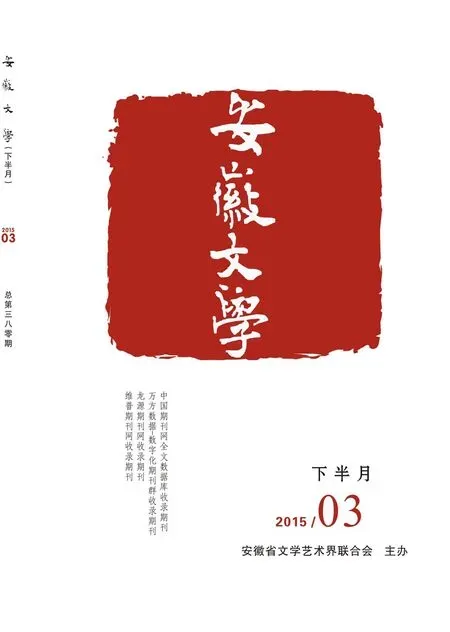论《点石斋画报》中“马车”的图像功能
郝凯利北京大学
论《点石斋画报》中“马车”的图像功能
郝凯利
北京大学
摘要:“马车”作为《点石斋画报》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西洋器物,其图像功能在于:《点石斋画报》以“马车”为媒介,不仅勾勒了一幅处于开放格局中的“看”与“被看”的海上繁华图,而且铺展了一幅带有鲜明现代时间观念和空间意识的都市转型图。两者交织在一起,共同见证了晚清上海现代性的发生。
关键词:《点石斋画报》马车上海现代性
《点石斋画报》于1884年5月8日由上海点石斋书局石印发行,从创刊到终刊,14年间共发表四千六百多幅图画,其题材广博,内容丰富,既是一部鲜活生动的晚清中国社会变迁图史,又是一幅色彩斑斓的晚清上海都市生活画卷。
仔细翻阅《点石斋画报》,我们会发现几百幅表现“海上繁华”的图画中,有近三分之一的篇幅和“马车”有关。相比电灯、电报、火车、轮船、自鸣钟等西洋器物,“马车”这一亦从西方传入的舶来品,是《点石斋画报》中出现频率最高、最受画师青睐的事物。此现象引人关注和思考:“马车”有何魅力以致在《点石斋画报》所绘制的“海上繁华图”中频频亮相?《点石斋画报》通过“马车”这一图像传达了什么样的“海上繁华”景观?本文试图对这些问题做一考察。
一、“马车”上的“看”与“被看”
据熊月之主编的《上海通史·晚清社会》记载:
“上海的马车是在1850年从欧洲输入的。1853年,一个名叫史密斯的外侨,乘坐第一辆马车出现于黄埔滩头。此后,马车便开始在上海街头风行起来。起初,马车的拥有者大多是洋商巨贾,随着马车的不断输入和大量仿制,华商富绅亦开始自备马车,竞相乘坐。之后上海开始出现出租马车,马车遂加入城市客运系统。到20世纪初,出租马车臻于鼎盛,当时的中外官绅富商、王孙公子、闺阁千金、青楼女子出门无不以马车代步,乘坐马车成为一种时髦,一种风气。”[1]
上述文字传达了西洋马车在上海的发展史。马车以方便快捷取代中国传统代步工具轿子的同时,更作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在晚清上海广泛流行。
中国人借助“马车”这一快速流动的空间,把自己的活动范围由室内转向室外,而随着活动空间由内到外,中国人的眼界和心态也通过在“马车”上向外看得以开放、开阔。并且,国人在乘坐马车“看世界”的同时,不自觉或自觉地就会成为别人“看世界”的风景和内容。这样,乘坐马车的人不但是“观者”,同时又是“被观者”,在观赏近代上海崛起的都市景观的同时,又是上海都市景观的构成者。
“马车”上的“看”与“被看”,在《点石斋画报》中一再被强调和显现。比如《虚题实做》:一辆马车置于图像的最前端,其后尾随着三三两两的马车,马车上的人悠然自得地欣赏着沿路美景。而在最前端的马车上坐着一位惊慌失措的女性,她的目光惊异地投向车边的一男性行人,而此人的一只袖子被女子的马车牢牢挂着,男子无法挣脱只得随拖而行。在此男子的不远处,有两个男子探出头来,他们伸长脖子张望着车中的女子以及被车拖行的男子,脸上挂着笑容,俨然一副看热闹的神情。
仔细品读《虚题实做》,就会发现图中每个人都处于“看”与“被看”的双重关系网中。图中的每个人都在“看景”,同时每个人又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充当了别人眼中的风景,成为“被看”的景观。
颇值得玩味的是,“看”与“被看”的关系不只是存在于图像中的每个人身上,这种关系更被延伸到图像之外,在看图的读者和图像之间形成了新的“看”与“被看”的关系。小说家包天笑阅读《点石斋画报》的经历可以佐证这种在读者和图像之间形成的“看”与“被看”的关系:
“我在十二三岁的时候,上海出有一种石印的《点石斋画报》,我最喜欢看了……因为上海那个地方是开风气之先的,外国的什么新发明,新事物,都是先传到上海。譬如像轮船、火车,内地人当时都没有见过的,有它一编在手,可以领略了。风土、习俗,各处有什么不同的,也有了一个印象。”[2]
如果细心揣摩《点石斋画报》中隐藏的多种“看”与“被看”的关系图,我们就会发现《点石斋画报》在图像构成上形成了这样的特点:故事本事的角色只占画面的一小部分,而绝大部分的画面却被故事之外的众多看客们所占据,这样整幅图像由“看”与“被看”构成,不仅复制了现实都市中“看”与“被看”的关系,而且作用于读者,使读者和图像又生产出一种“看∕被看”的阅读关系。
比如《车中斗口》,截取了两名妓女在马车上相互斗骂以及众人围观的场景:图中前首马车上一妓女“回顾后车,立而指骂”,紧随其后的马车上一妓女起立回骂,两者气势汹汹,各不相让。在两辆马车的周围站立着十几个兴致勃勃的旁观者,他们的视线几乎全都聚焦在故事的中心人物身上,指划着、交谈着。有趣的是马车夫干脆也袖手作壁上观,一幅看热闹的样子,后面楼上的窗口里有三两个男女探出脑袋看热闹。这幅图像中,两妓车中斗骂的故事角色往往会被故事之外的众多看客喧宾夺主,图像中的“看”与“被看”不仅是现实都市中“看”与“被看”的复制,而且作用于读者,使读者和图像又生产出一种“看∕被看”的阅读关系。正像罗岗所说:“由于相同的‘观看’逻辑在起作用,使得围观‘妓女斗口’的众人很容易转化为阅读《点石斋画报》的读者。”[3]
再如《马夫凶横》。图像中央停站着一辆马车,马车夫站立车头、扬起马鞭正欲抽打被他撞倒的一位中年女性。这位女性斜躺在车轮旁,痛苦地抬头张望着马车夫。在马车的周围,人们从四面八方涌来并驻足观看。他们挥着手臂,脸露愤怒的神情。更有甚者,在路边高耸林立的茶楼上,人们正站在窗边向下张望,群情激愤。而由《马夫凶横》的文字叙述可以得知,图上的中年女性是因在茶楼前左顾右盼、专心看景以致对飞来横祸猝不及防,遂成为车祸受害者。这样,她就由原来的“看客”转换为被看者。这位女性的看客姿态,正象征着近代中国被纳入资本主义体系后,封建中国乡土文明对照现代西方都市文明时的惊异好奇心态。而图像关注的这桩马车肇事案,从道路交通事故角度显示了都市进程中出现的人口膨胀、车辆拥堵、贫富分化、道德危机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图中人们对马车夫的态度显示了他们对这些社会问题的极大关注,他们路见不平纷纷谴责的态度,表明他们已把自己作为社会的一员,积极融入社会、干预社会现实。这种生活态度与鲁迅笔下看客的那种麻木苟且形成鲜明的对比,它预示着中国人积极参与社会生活的公民意识的觉醒和崛起。
《马夫凶横》一图所配文字的最后这样写道:“然迹其凶横情形,实足令人发指。安得工部局严行查办,有犯必惩,租界中人庶几同歌乐国也夫。”这里,作者不仅与图中看客一样对马夫的行为进行道德层面的强烈谴责,更重要的是,作者还主张从法制这一社会制度层面对马夫的行为进行约束和管理。这种理性思维就于无形中显示了一种有秩序、有规范的现代法制社会正逐步取代以往以人情道德为中心的传统社会的转变。
进一步探究这种代表当时上海民众心声的理性思维,是靠《点石斋画报》这一报刊传媒得以表达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哈贝马斯所提出的“公共领域”这一重要的现代性指标正在近代上海产生与形成。“当他们在非强制的情况下处理普遍问题时,公民们作为一个群体来行动;因此这种行动具有这样的保障,即他们可以自由地集合和组合,可以自由地表达和公开他们的意见。当这个公众达到较大规模时,这种交往需要一定的传播和影响的手段,今天报刊、广播和电视就是这种公共领域的媒介。”[4]从上述哈贝马斯关于“公共领域”的阐释话语来看,《点石斋画报》已成为晚清上海公共领域的有效媒介,它以图文并茂的方式描绘了现代社会雏形在晚清上海形成的轨迹。
通过对上述三幅图像的图文分析,我们可以看到《点石斋画报》以“马车”为媒介,既复制了现实中的“看”与“被看”,又在图像和读者之间生成新的“看”与“被看”。于是,从图像所关注的每个人到图像所关注的整个城市,均处于开放、向外的状态中,在积极“向外看”的姿态中,“都市/乡土”“世界/中国”“现代/传统”这一系列纠结在近代上海发展行程中的诸多问题,均在《点石斋画报》中铺展开来,从而形成了一幅处于开放格局中的“看”与“被看”的海上繁华图。
二、“马车"是时间流逝和空间流动的双重载体
“马车”不同于其他西洋器物的地方在于,它不是静止不动的,它具有时间流逝和空间流动的双重性。在“马车”向前移动的过程中,“马车”既见证了时间的快速流逝,又见证了空间的流动和转换。在“马车”的飞速前行中,中国人不仅培养了现代时间观念和竞争意识,一种追求更快速更有效率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逐步形成;而且拓宽了自身的空间概念,由私人空间转向公共空间,一种参与社会生活、立足现实的公共意识开始出现。“马车”的这种时间、空间双重性被《点石斋画报》很好地利用和结合,从而生成一幅交织了现代时间观念和现代空间意识的“海上繁华图”。
《点石斋画报》中第一幅与“马车”有关的图画是《赛马志盛》:图像的正上方是西人建造的开阔气派的跑马场,在场内的圆形跑道上西人正策马飞奔,快速、紧张、刺激的比赛气氛呼之欲出。而在喧闹的跑马场外是熙熙攘攘、成群结队的观众。他们中有西人也有华人,又以华人观众居多。观众背后是往来的人流和穿梭其中的各式交通工具,马车、人力车、独轮车等,而在人群的最外围是小商贩们摆放的各种零售小摊。整幅图充满了热闹喧哗的气息,而图像中穿梭于人群的马车正在前行,从而和整幅图画的喧闹流动的氛围融为一体。
这里,前行的“马车”形象,绝不是可有可无之笔,它具有很强的象征意义。画家把“马车”置于前行状态,它在前行中和跑马场上的赛马一起见证着时间的飞逝,一种强烈的时间意识在“马车”的移动中凸显出来,而把“马车”置于观看赛马比赛的观众当中,则把“马车”和跑马场这一开放性的公共空间联系在一起,在“马车”的前行中,马车上的人实现着由私人空间转向公共空间,由地理空间转向文化空间的空间拓展。
赛马是最早吸引中国人观看和参与的西人娱乐休闲活动,它和“马车”一样推动了中国人的时间意识
和空间观念的现代建构。赛马是以时间的快慢来衡量比赛输赢的一项活动,中国人在观看赛马的过程中,一种以时间为标准的竞争机制逐渐深入中国人的思想深处,从而形成精确的时间意识。这种追求效率、注重竞争的思想观念在《点石斋画报》中多次出现,如《赛船续述》《西人赛技》《力不同科》《赛脚踏车》等诸图。在空间上,赛马得以进行的场所是露天开阔的跑马场,这种开放性的大型公共活动空间和公园、马路一样,不分区域、行业、阶级、性别,与中国传统的公共活动场所,如戏院、书场、妓院、茶馆、酒楼等室内娱乐场所迥然不同。当华人活动参与其中时,传统文化推崇的尊卑、男女、夷夏之别的等级鸿沟逐渐淡化瓦解,一种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的现代公共空间开始在以跑马场为代表的西方文明载体中形成。因此,《赛马志盛》在“马车”和跑马场的对照性解读中,凸显出一种强烈的时间观念和空间意识。
“现代性就是时间的历史(the history of time):现代性是时间开始具有历史的时间。”[5]《点石斋画报》的图像呈现出对时间的高度关注。我们经常看到《点石斋画报》中的各式西式钟表,从室内到室外,从家庭到政府机关,从传统的娱乐场所到新型的公共空间,无一不见它的身影。最典型的就是描绘江海北关后来居上建成的巨大钟楼的《巨钟新制》:画面中,江海北关前的街道上,七八个华人正站在门前仰望巨钟,指指画画,一副惊奇的模样。画面右下角,一个马车夫从座位上直起身,目光也是聚焦在新制巨钟之上。
《巨钟新制》把前行中的“马车”和代表着精确时间的西式时钟统摄起来,通过“马车”的行进表现一种明确的时间意识。“大自鸣钟轰碧霄,报时报刻自朝朝。行人要对襟头表,驻足墙阴仔细瞧。”[6]以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模糊大概的时间意识被精确的、富有理性的时间意识取代,对时间的敏感和自觉正是由传统向现代转变的一个关键性因素。《点石斋画报》对时间的高度重视鲜明地体现了晚清上海城市现代性发生的痕迹。
《点石斋画报》通过“马车”这个有效载体,不仅表现出对现代时间观念的认同,而且也彰显了现代空间的拓展。翻阅《点石斋画报》中的上海图景,图像关注的焦点在室外空间、公共空间、文化空间,而非室内空间、私人空间、地理空间,即使出现对后者的关注,也往往通过敞开门窗,或掀起门帘的方式来延伸室内空间的社会性,加强对私人空间的社会化关注,绝无对一密闭的孤立的空间投注笔墨。如此一来,“海上繁华”就以开放性、流动性的特征展现在读者面前。而这种特征很大程度上是靠“马车”这个媒介得以实现。
“大抵游沪者有七事:戏园也,酒楼也,茶馆也,烟间也,书场也,马车也,堂子也。”[7]在这里,“马车”作为一移动空间,既跻身于晚清上海林林总总的多种空间之列,又可作为空间之间流动的媒介,游刃有余地实现空间的切换。“马车”在《点石斋画报》中不仅与传统的娱乐空间紧密相连,更重要的是和跑马场、马路、公园这些露天的新型公共空间一起构成了晚清上海都市新景观。
如《游园肇祸》把事件的场景锁定在张园中:“沪北泥城外张氏味莼园,亭台楼阁,位置天然。曩年问津者尚少,自园主人刻意经营,茶寮也、烟塌也、酒筵也、髦儿戏也,一一布置,色色俱全,于是游客纷纭。”在对张园加以重彩浓墨的描述后,故事的主题登场:一少年夫妇乘四轮轿式马车至张园游玩,马忽惊跃,夫妇二人跌入池中,后经众人援救上岸。文字最后针对此次事故做了一番评论:“有识者乃归咎于妇女不宜轻出闺门,是也,然吾独谓该园荷花池畔亦宜围以栏杆,免致偶不经意倾跌堪虞”。
这一番评论透露出两个信息:一则是乘马车、逛公园等活动不再是妓女这一特殊女性群体的专利,官宦女眷、名门闺秀等社会上层女性已经由闺阁庭院走向街头社会,而这对传统社会的男尊女卑的秩序是一巨大冲击,无怪乎那些所谓的“有识者”宣称“妇女不宜轻出闺门”。二则是作者认为“游园肇祸”的根本不在妇女轻出闺门,而在于张园的安全防范措施不够完善。这种对公共场所管理提出意见和建议的做法,表明了作者对公共空间和社会生活的积极关注,而这和《马夫凶横》中,作者呼吁工部局对肇事马夫进行严行查办一样,是一种参与社会管理、干预社会现实的公民意识的显现。因此,《游园肇祸》一图以“马车”为媒介,把张园这一真正意义上的公共空间和晚清女性(已不再是把妓女作为关注重心)联系起来,既预示着女性意识的觉醒,又显示了一种参与社会生活、干预社会现实的公民意识的萌生。这两个方面则是晚清上海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两个重要面向。
综上,《点石斋画报》以“马车”为媒介,通过“马车”这一图像,不仅勾勒了一幅处于开放格局中的“看”与“被看”的海上繁华图,而且铺展了一幅带有鲜明时间意识和空间意识的现代都市转型图。两者交织在一起,共同见证了晚清上海都市现代性的发生。
参考文献
[1]熊月之.上海通史(第5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198.
[2]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M].上海:三联书店,2014:112-113.
[3]罗岗.性别移动与上海流动空间的建构——从《海上花列传》中的“马车”谈开去[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3,35(1):97.
[4](德)哈贝马斯.公共领域[M].上海:三联书店,1998:125.
[5](波兰)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现代性[M].上海:三联书店,2002:174.
[6]袁祖志.沪北竹枝词[N].申报,1872-5-18.
[7](清)葛元煦.沪游杂记[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9: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