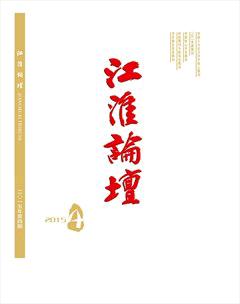梁启超视界中的谭嗣同*
魏义霞
(黑龙江大学哲学学院 哈尔滨 150080)
谭嗣同与梁启超相识时间不长——梁启超说3年,其实不过2年(从谭嗣同1896年的北游访学到1898年的百日维新)。两人结识后相见恨晚,过丛甚密,梁启超更是成为谭嗣同牺牲前生死相托的人。同样是在梁启超的介绍下,谭嗣同第一次对康有为的思想主旨有了较为详细的了解,并且大为折服,用梁启超本人的话说便是“则感动大喜跃,自称私淑弟子”。从此以后,谭嗣同与康有为亦师亦友。由于相识的时间短,更由于谭嗣同的壮烈牺牲,谭嗣同对梁启超并无太多评价,目前看到的第一手材料主要是谭嗣同写给梁启超的7封信。在这7封信中,有4封是写给汪康年和梁启超两人的,只有3封是专门写给梁启超的。与谭嗣同对梁启超的提及和评价相比,梁启超对谭嗣同关注甚多,这也是本文名为《梁启超视界中的谭嗣同》的原因所在。
一、对谭嗣同其人其学的推崇
梁启超是最早对谭嗣同的思想予以宣传、推崇和刊发的思想家。他对谭嗣同的评价是:“谭浏阳志节学行思想,为我中国二十世纪开幕第一人。”[1]这个评价包含对谭嗣同慷慨赴死的英雄气概的敬佩与学术思想的折服。由于对谭嗣同的人品极为敬重,因其人而好其学是梁启超步趋谭嗣同的重要原因。梁启超为谭嗣同的代表作《仁学》作序,并且作《谭嗣同传》,对谭嗣同的生平、为学予以介绍,并且给予了高度评价。与此同时,好史的梁启超作 《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清代学术概论》,率先对中国近代(1840年之后,梁启超统称为“清代”)的思想史予以梳理和研究,使谭嗣同与龚自珍、魏源和康有为等人一样进入了学术研究视野。此外,梁启超在论及中国近代的学术思想或在其他论作中时常提到谭嗣同,在彰显谭嗣同人格魅力的同时,多维度地展示了谭嗣同思想的理论来源、主要内容和基本特征。梁启超对谭嗣同及其思想的介绍和阐发有客观陈述,也有主观评价。透过这些,既可以直观地感受到梁启超对谭嗣同的推崇,又可以领悟谭嗣同与梁启超思想的异同。
梁启超指出,谭嗣同的为人与为学是合一的,其英雄气概就贯注在学术之中;英雄是宗教造就的,正是“应用佛学”成就了谭嗣同的壮举。梁启超写道:“夫人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故为信仰者,苟不扩其量于此数十寒暑以外,则其所信者终有所挠。浏阳《仁学》云:‘好生而恶死,可谓大惑不解者矣,盖于不生不灭瞢焉。瞢而惑,故明知是义,特不胜其死亡之惧,缩朒而不敢为,方更于人祸之所不及,益以纵肆于恶。而顾景汲汲,而四方蹙蹙,惟取自慰快已尔,天下岂复有可治也!……今使灵魂之说明,虽至暗者犹知死后有莫大之事及无穷之苦乐,必不于生前之暂苦暂乐而生贪著厌离之想;知天堂地狱森列于心目,必不敢欺饰放纵,将日迁善以自兢惕;知身为不死之物,虽杀之亦不死,则成仁取义,必无怛怖于其衷,且此生未及竟者,来生固可以补之,复何所惮而不亹亹!’呜呼!此‘应用佛学’之言也。(西人于学术每分纯理与应用两门,如纯理哲学、应用哲学、纯理经济学、应用生计学等是也。浏阳《仁学》,吾谓可名为应用佛学。)浏阳一生得力在此,吾辈所以崇拜浏阳步趋浏阳者,亦当在此。”[2]梁启超对谭嗣同的佛学思想兴趣盎然,与将谭嗣同的代表作《仁学》归结为“应用佛学”相一致,始终从入世“应用”的角度诠释谭嗣同的佛学和《仁学》。这样一来,梁启超便以佛学作为谭嗣同思想的主线,以“应用佛学”为桥梁,将谭嗣同的为人与为学联为一体。
更为重要的是,梁启超是谭嗣同准备杀身成仁时最后的托付。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的《殉难六烈士传·谭嗣同传》中对此有详细记载,读之令人动容:“劝东游,且携所著书及诗文辞稿数本数册家书一箧托焉。曰:‘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今南海之生死未可卜,程婴杵臼,月照西乡,吾与足下分任之。’……君曰:‘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3]谭嗣同的狱中绝笔印证了梁启超的说法,也为两人的情深义重提供了佐证:“八月六日之祸,天地反覆,呜呼痛哉!我圣上之命,悬于太后、贼臣之手,嗣同死矣!嗣同之死毕矣!……嗣同不恨先众人而死,而恨后嗣同而死者之虚生也。啮血书此,告我中国臣民,同兴义愤,翦除国贼,保全我圣上。嗣同生不能报国,死亦为厉鬼,为海内义师之助。卓如未死,以此书付之,卓如其必不负嗣同、皇上也。”[4]事实证明,梁启超没有辜负谭嗣同的重托。谭嗣同牺牲后,梁启超利用各种机会介绍、宣传谭嗣同的思想,并在自己主办的《清议报》上首次刊发谭嗣同的《仁学》。“其《仁学》一书,先择其稍平易者,附印《清议报》中,公诸世焉。 ”[3]在回顾《清议报》一百期所刊内容时,梁启超首推谭嗣同的《仁学》:“其(指《清议报》——引者注)内容之重要者,则有谭浏阳之《仁学》,以宗教之魂,哲学之髓,发挥公理,出乎天天,入乎人人,冲重重之网罗,造劫劫之慧果。其思想为吾人所不能达,其言论为吾人所不敢言,实禹域未有之书,抑众生无价之宝,此编之出现于世界,盖本报为首焉。有饮冰室《自由书》。”[5]在回顾和总结《清议报》所刊的内容时,梁启超最隆重推出的是谭嗣同的《仁学》,之后是自己的《自由书》、《瓜分危言》、《亡羊录》、《灭国新法论》、《少年中国说》、《呵旁观者文》和《过渡时代论》等论著,章炳麟的《儒术新论》及其他内容更列于后。不仅如此,在具体介绍和评价中,梁启超对 《仁学》不惜笔墨——这一点与对待章炳麟的《儒术新论》相比则看得更加清楚:对待后者,梁启超只用了“《儒术新论》诠发教旨,精微独到”一语。由此反观,足见梁启超对谭嗣同的隆重推出,并且极尽溢美之词。至于梁启超所言《仁学》“出现于世界,盖本报为首焉”则属实情,亦表明了梁启超对于推介谭嗣同思想的用力之著和首刊之功。
与此同时,梁启超在自己的论作中时常援引谭嗣同的观点和《仁学》等著作,这样做的初衷固然有借题发挥、利用谭嗣同的人格和观点阐发自己思想的意图,同时也有让更多人了解谭嗣同及其思想的目的。不论动机如何,有一点是不争的事实,那就是:梁启超的做法在客观上对于人们了解谭嗣同及其思想,促进谭嗣同思想的传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推动作用。
二、谭嗣同与梁启超的相互影响
谭嗣同与梁启超的关系既有个人情感,又有共同追求,在朝夕相处、学术切磋中相互影响。按照梁启超的说法,自己与谭嗣同在学问上相互影响,彼此学问都为之一变:一方面,谭嗣同在接触自己后思想为之一变:“自交梁启超后,其学一变。 ”[6]3102另一方面,由于受谭嗣同的影响,自己的思想也为之一变。与“崇拜浏阳步趋浏阳”相一致,梁启超坦言自己的思想受谭嗣同和夏曾佑影响甚深。
在中国近代崇佛史上,梁启超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梁启超对佛教的虔诚和痴迷令人注目,谭嗣同在其中功不可没。据梁启超本人披露,自己早年对佛教兴趣索然,甚至在听闻康有为讲佛教后不为所动。在结识谭嗣同后,梁启超才在谭嗣同的“鞭策”下开始向佛,并由此一发而不可收拾:“文会深通‘法相’、‘华严’两宗,而以‘净土’教学者,学者渐敬信之。谭嗣同从之游一年,本其所得以著《仁学》,尤常鞭策其友梁启超。启超不能深造,顾亦好焉,其所著论,往往推挹佛教。”[6]3105在现存不多的谭嗣同致梁启超的信中,除了商谈变法维新诸事宜之外,还有一封是专门切磋佛教的。[7]
这封信文字较长,内容却十分集中,只讲了一件事,专门为梁启超解释佛法。信中透露了如下信息:第一,谭嗣同与梁启超经常在一起切磋佛学,此信就缘于两人头一天切磋(“昨言……”)的意犹未尽。第二,信中集中呈现了谭嗣同的佛学观,那就是基于华严宗的圆融无碍,宣称佛与众生相即相入,自度度人相即相入。这与谭嗣同在《仁学》中阐发的“一入一切,一切入一”相印证,梁启超在《〈仁学〉序》和《谭嗣同传》中对谭嗣同佛教思想的介绍也是在这个思路下展开的。第三,谭嗣同在信中阐释自己的佛教观,是为了借此点悟梁启超。值得注意的是,信中内容显示,谭嗣同对梁启超的点悟从认识梁启超时就已经开始,“观公两年来……”便是明证。
事实证明,无论谭嗣同的这次点化是否成功,梁启超后来的行为都表明,谭嗣同对梁启超佛学的引领或“督促”效果显著。正是在谭嗣同的“鞭策”和点化下,梁启超从对佛教无动于衷转而顶礼膜拜,如醉如痴。由此,佛教成为梁启超的精神支柱和信仰皈依,梁启超对佛教的痴迷和虔诚甚至达到了癫狂的程度。有这样一件事足以证明这一点:1922年,梁启超在东南大学讲学期间,每天坚持到支那内学院听欧阳竟无讲佛法,风雨无阻,坚持不辍,即使出车祸或身体欠佳也不放弃。对于这段学佛经历以及其中的苦乐,梁启超不止一次在写给孩子们的信中提及,对佛教的热情跃然纸上。[8]梁启超是性情中人,做什么事全凭兴趣所致,对待佛学也不例外。由于兴趣盎然,乐在其中,所以排除万难,乐此不疲。
进而言之,梁启超之所以对佛教如此虔诚和痴狂,是出于真心向往,兴味盎然;同时也因为对佛教的受用,获益匪浅。在写给自己的“宝贝”梁思顺的信中,梁启超概括了自己的宗教观和人生观,也揭开了自己崇尚佛教的秘密所在:“这是宇宙间唯一真理,佛教说的‘业’和‘报’就是这个真理,(我笃信佛教,就在此点,七千卷《大藏经》也只说明这点道理。)凡自己造过的‘业’,无论为善为恶,自己总要受‘报’,一斤报一斤,一两报一两,丝毫不能躲闪,而且善和恶是不准抵消的。……如此,恶业受完了报,才算善业的帐,若使正在享善业的报的时候,又做些恶业,善报受完了,又算恶业的账,并非有个什么上帝做主宰,全是‘自业自得’,又并不是象耶教说的‘到世界末日算总账’,全是‘随作随受’。又不是象耶教说的‘多大罪恶一忏悔便完事’,忏悔后固然得好处,但曾经造过的恶业,并不因忏悔而灭,是要等‘报’受完了才灭。佛教所说的精理,大略如此。他说的六道轮回等等,不过为一般浅人说法,说些有形的天堂地狱,其实我们刻刻在轮回中,一生不知经过多少天堂地狱。……我虽不敢说常住涅槃,但我总算心地清凉的时候多,换句话说,我住天堂时候比住地狱的时候多,也是因为我比较的少造恶业的缘故。我的宗教观、人生观的根本在此,这些话都是我切实受用的所在。”[9]透过这段文字可以想见,佛教对梁启超意味着什么,难怪梁启超将佛教奉为“全世界文化的最高产品”[10]。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最早使梁启超倾心佛教的是谭嗣同。从这个意义上说,谭嗣同对于梁启超虔诚向佛以及对佛教的终身受用功莫大焉。
三、谭嗣同与梁启超的思想异同
诚如梁启超所言,谭嗣同与梁启超的思想相互影响,这使两人的思想之间呈现出诸多相同之处。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曾经对自己与谭嗣同之间的关系有过这样一段记载:“启超屡游京师,渐交当世士大夫,而其讲学最契之友,曰夏曾佑、谭嗣同……此可想见当时彼辈 ‘排荀’运动,实有一种元气淋漓景象。嗣同方治王夫之之学,喜谈名理,谈经济,及交启超,亦盛言大同,运动尤烈。(详次节)而启超之学,受夏、谭影响亦至巨。 ”[6]3099-3100引文作为“排荀”运动中心的“彼辈”指谭嗣同和梁启超,据此可知,两人都言民权,并将荀子视为中国古代君主专制的罪魁祸首加以批判。这表明,谭嗣同、梁启超都反对荀子——这一点与章炳麟天差地别。此外,两人都对老子持否定态度,对老子尚静而贻祸中国的评价如出一辙——这一点与严复相去甚远。谭嗣同在《仁学》中说:“李耳之术之乱中国也,柔静其易知矣。若夫力足以杀尽地球含生之类,胥天地鬼神以沦陷于不仁,而卒无一人能少知其非者,则曰‘俭’。 ”[11]梁启超对谭嗣同的观点深表认同,并且进一步发挥说:“老子有言曰:‘无动为大。’此实千古之罪言也。夫日非动不能发光热,地非动不能育万类,人身之血轮,片刻不动,则全身冻且僵矣。故动者万有之根原也……谭浏阳先生《仁学》云:‘自李耳出,遂使数千年来成乎似忠信似廉洁一无刺无非之乡愿天下。言学术则曰宁静,言治术则曰安静。处事不计是非,而首禁更张,躁妄喜事之名立,百端则是废弛矣;用人不问贤不肖,而多方遏抑,少年意气之论起,柄权则颓暮矣。陈言者则命之曰希望恩泽,程功者则命之曰露才扬己。既为糊名以取之,而复隘其途;既为年资以用之,而复严其等。财则惮辟利源,兵则不贵朝气。统政府六部九卿督抚司道之所朝夕孜孜不已者,不过力制四万万人之动,絷其手足,涂塞其耳目,尽驱以入乎一定不移之乡愿格式。夫群四万万乡愿以为国,教安得不亡,种类安得而可保也?’呜呼!吾每读此言,未尝不废书而叹也。”[12]鉴于两人对诸多问题的认识大致相同,梁启超称谭嗣同为“讲学最契之友”,甚至声称两人对于所学无不契合。梁启超在为谭嗣同的 《仁学》作序时曾经回忆说:“余之识烈士,虽仅三年。然此三年之中,学问言论行事,无所不与共。其于学也,无所不言,无所不契,每共居则促膝对坐一榻中,往复上下,穷天人之奥,或彻数日夜废寝食,论不休,每十日不相见,则论事、论学之书盈一箧。 ”[13]
同样不可否认的是,谭嗣同、梁启超的气质性格、思想来源和学术经历迥然相异,两人的思想也由此呈现出不容忽视的差异。对于这一点,梁启超并不讳言。在肯定自己与谭嗣同思想相同的同时,梁启超揭示了两人思想的差异,并将谭嗣同与自己思想的最大分歧归结为世界主义与国家主义:“《仁学》之政论,归于‘世界主义’……又曰:‘不惟发愿救本国,并彼极盛之西国与夫含生之类,一切皆度之。……不可自言为某国人,当平视万国,皆其国,皆其民。’……其后梁启超居东,渐染欧、日俗论,乃盛倡褊狭的国家主义,惭其死友矣。 ”[6]3103依据这个说法,谭嗣同秉持世界主义,以大同社会为旨归;梁启超恪守民族主义,倡导国家观念和爱国主义。就事实而言,梁启超的说法可谓中肯。饶有趣味的是,梁启超对谭嗣同世界主义、大同理想的评价非同寻常,甚至可以说是“一反常态”。众所周知,恪守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梁启超将救亡图存与民族主义视为不可分割的正反面,故而断言在中国近代,若振兴中华,舍民族主义别无他途。基于这种认识,他对大同主义、世界主义怒不可遏,斥之为宗教家的梦呓。这一点也是梁启超与其老师康有为思想分歧的焦点之一。在论及谭嗣同的大同理想时,梁启超却完全是另一种腔调,不仅没有对大同主义、世界主义流露出一如既往的厌恶、拒斥,反而一再表白自己对大同思想的热衷,有意无意地拉近自己在大同思想方面与谭嗣同的距离:第一,在介绍谭嗣同的思想转变即谭嗣同喜言大同的缘起时,梁启超指出,谭嗣同“及交启超,亦盛言大同,运动尤烈”[6]3099。 这意味着谭嗣同的大同思想与梁启超具有某种关系,甚至是受梁启超的影响所致。“亦盛言大同”之“亦”表明,谭嗣同“盛言大同”,梁启超也“盛言大同”——准确地说,是梁启超“盛言”在先,谭嗣同“盛言”在后,谭嗣同是跟随着梁启超而“盛言大同”的。这与梁启超所言自己“居东,渐染欧、日俗论,乃盛倡褊狭的国家主义”相印证。第二,无论是介绍谭嗣同的大同思想,还是说明自己经过思想转变、秉持国家主义而与谭嗣同的思想渐行渐远,梁启超均没有对谭嗣同的大同思想置一微词,反而以“褊狭的”称自己所倡导的国家主义,以惭愧表达对谭嗣同(“死友”)的心情。梁启超对康有为、谭嗣同大同思想的态度之所以呈现极大反差,除了为死者讳之外,还有更深层的原因,那就是:梁启超一贯认为《仁学》是发扬大乘佛法普度众生之作,谭嗣同本人亦有“不惟发愿救本国”,连同西方国家“皆度之”的“皆其国,皆其民”之语。这样一来,大同思想恰成谭嗣同普度众生的一个注脚,谭嗣同本人又为这一宏愿献出了宝贵的生命。面对谭嗣同知行合一的人格和学问,梁启超敬仰、步趋尚恐不及,又何来质疑!
四、梁启超对谭嗣同的学派归属
尽管与谭嗣同的思想异同互见,梁启超显然引谭嗣同为同调。无论是政治上的志同道合还是与谭嗣同的相互影响,都使梁启超更喜欢突出自己与谭嗣同思想的一致性,这透过他对《仁学》的介绍可见一斑:“嗣同根本的排斥尊古观念,尝曰:‘古而可好,则何必为今之人哉!’(《仁学》卷上)对于中国历史,下一总批评曰:‘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惟大盗利用乡愿,惟乡愿工媚大盗。’(《仁学》卷下)当时谭、梁、夏一派之论调,大约以此为基本。”[6]3102一目了然,梁启超在此与自己归为一派的并无康有为,除了谭嗣同之外,尚有夏曾佑。
值得注意的是,就康有为、谭嗣同与梁启超三人思想的关系而言,梁启超更为突出康有为与谭嗣同思想的一致性:一方面,在将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划分为同一派或归结为同一期的前提下,梁启超总是有意无意地将自己疏离出来。例如,他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写道:“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辈,即生育于此种‘学问饥荒’之环境中,冥思枯索,欲以构成一种‘不中不西即中即西’之新学派,而已为时代所不容。盖固有之旧思想,既深根固蒂,而外来之新思想,又来源浅觳,汲而易竭,其支绌灭裂,固宜然矣。……壬寅、癸卯间……新思想之输入,如火如荼矣。然皆所谓‘梁启超式’的输入,无组织,无选择,本末不具,派别不明,惟以多为贵,而社会亦欢迎之。 ”[6]3104-3105
这段话前半段肯定三人同处 “学问饥荒”之环境中,思想都带有“不中不西即中即西”之特征,理应归为一派——无论是“学问饥荒”之处境还是“不中不西即中即西”之思想都是就康有为、谭嗣同和梁启超思想的共性而言的;后半段所讲的“新思想之输入”主角或者说主体是梁启超,并不包括康有为和谭嗣同两人,并且与严复等人的输入相比带有自身特点,因而冠以“梁启超式的”——这是就梁启超思想的个性而言的,有别于严复,更重要的是与康有为、谭嗣同亦不相同。正是“新思想之输入”使梁启超与康有为、谭嗣同的思想渐行渐远,最终将梁启超从“康、谭一派”中分离出来。另一方面,梁启超多次强调谭嗣同在思想来源上受康有为影响,以此突出、加固谭嗣同与康有为思想的一致性和相同性。有鉴于此,在对中国近代思想进行分期时,梁启超在自己“不在场”的情况下将谭嗣同与康有为归为同一期,给人一种只有康有为、谭嗣同两人思想最相近的印象。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梁启超对从顺治到光绪二百余年间的清代学术进行梳理,并且整合了其递嬗轨迹。他写道:“本朝二百年之学术……实取前此二千年之学术,倒影而缫演之……其在前两期,则霸者之所以监民也至严,学者用聪明才力于他途,或将以自焚,故不得不自锢于无用之用,此惠、戴所以代朱、王也。其在第三期,天下渐多事,监者稍稍驰,而国中方以治经为最高之名誉,学者犹以不附名经师为耻,故别出一途以自重。……其在第四期,则世变日亟,而与域外之交通大开。世变亟,则将穷思其所以致此之由,而对于现今社会根本的组织,起怀疑焉;交通开,则有他社会之思想以为比较,而激刺之、淬厉之。康、谭一派,所由起也。要而论之,此二百余年间,总可命为‘古学复兴时代’。”[14]618在这里,梁启超将清代学术划分为4个不同时期,突出谭嗣同与康有为思想的一致性。在这个视界中,梁启超一面指出清代学术在本质上都是复古之学,一面强调这一复古从整体上呈现出愈复愈古的演变轨迹;由于所复之古的具体内容和核心话题大不相同,从而呈现出泾渭分明的4个时期:第一期顺治、康熙年间,以程朱陆王问题为核心话题;第二期雍正、乾隆、嘉庆年间,以汉学宋学问题为核心话题;第三期道光、咸丰、同治年间,以今古文问题为核心话题;第四期光绪年间,以孟荀、孔老墨为核心话题。各个时期不仅核心话题不同,而且具有自己的代表人物,其中,第四期的代表人物是康有为和谭嗣同。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期的代表人物只有康有为、谭嗣同两人,既没有严复,也没有既是康有为高足,又是谭嗣同“讲学最契之友”的梁启超本人,令人颇感意外。反观前期人物,“惠、戴一派”、“龚、魏一派”,无论是以吴派领袖惠栋、皖派领袖戴震代表乾嘉学派还是将龚自珍、魏源作为近代最早睁开眼睛看世界的开明派相提并论都属“老生常谈”,唯独与之对应的“康、谭一派”别出心裁,因为说到康有为“拉帮结伙”,人们最先想到的往往是“康梁”而绝非“康、谭一派”。
综观梁启超的思想可以发现,凸显康有为、谭嗣同思想的一致性并非偶尔为之。除了此处的“康、谭一派”之外,还有出自《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的这段话:“南海之功安在?则亦解二千年来人心之缚,使之敢于怀疑,而导之以入思想自由之途径而已。自兹以还,浏阳谭壮飞(嗣同)著《仁学》,乃举其冥想所得、实验所得、听受所得者,尽发之而无余,而思想界遂起一大革命。”[14]616这段话与上段相比更为突出康有为对于前清思想的变革之功,同时肯定康有为对谭嗣同思想的引领,甚至将谭嗣同的《仁学》说成是对康有为思想的发挥——“尽发之而无余”。
鉴于康有为、谭嗣同思想的密切关系,梁启超在直接让康有为、谭嗣同两人共同担纲一派(第四期)的同时,还从其他角度凸显两人思想的相同性。他写道:“自龚定庵好言佛,而近今学界代表之数君子,大率与定庵有渊源,故亦皆治佛学,如南海、壮飞及钱塘夏穗卿曾佑其人也。虽由其根器深厚,或其所证过于定庵,要之定庵为其导师,吾能知之。 ”[14]这表明,康有为、谭嗣同均好佛,并且两人的佛学均与龚自珍(龚定庵)具有某种渊源关系。在这个前提下,有两个问题尚须进一步澄清:第一,梁启超认为,第四期与第三期今古文问题具有思想渊源。因此,在作于1920年的《清代学术概论》中,梁启超承认康有为的公羊学与龚自珍一脉相承,并且将康有为称为今文学的集大成者,同时将自己说成是康有为今文学的宣传者和推行者。第二,与《清代学术概论》的主旨和论调大不相同,在作于1902年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梁启超之所以肯定康有为与谭嗣同皆师出龚自珍,是为了突出康有为、谭嗣同思想的一致性;接下来便是以西学“大苏润思想界”的严复,始终不见梁启超的影子。耐人寻味的是,在反复将谭嗣同与康有为相提并论,并且归为同一期时,梁启超并没有让自己出现于其间。这或许是一种谦虚,自认为尚不足以与康有为、谭嗣同一样称为“人物”;或许是一种拒绝,想要委婉表白自己原本就不属于此列——这四期皆属复古之学,而自己是“新思想界之陈涉”。对于这一点,严复没有出现似乎提供了佐证。无论动机和意图如何,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梁启超的做法不仅给人们理解谭嗣同与康有为的关系带来了困惑,而且使梁启超本人与康有为的关系也变得复杂起来。
综上所述,梁启超对谭嗣同思想的历史定位和学派归属既突出了谭嗣同与康有为思想的一致性,又从一个侧面道出了梁启超与康有为思想的微妙关系。这就是说,无论是康有为与梁启超还是谭嗣同与梁启超的思想关系都是多维度的,对于其间的异同关系不可作简单或僵化解。
[1]梁启超.梁启超全集·诗话(第九册)[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2595.
[2]梁启超.梁启超全集·论佛教与群治之关系(第二册)[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908.
[3]梁启超.梁启超全集·谭嗣同传(第一册)[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233.
[4]谭嗣同.谭嗣同全集·致梁启超三[M].北京:中华书局,1998:519.
[5]梁启超.梁启超全集·清议报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报之经历(第一册)[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478-479.
[6]梁启超.梁启超全集·清代学术概论(第五册)[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7]谭嗣同.谭嗣同全集·致梁启超二[M].北京:中华书局,1998:518-519.
[8]梁启超.梁启超全集·致梁思顺(第十册)[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6192.
[9]梁启超.梁启超全集·致孩子们(第十册)[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6212-6213.
[10]梁启超.梁启超全集·治国学的两条大路(第七册)[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4071.
[11]谭嗣同.谭嗣同全集·仁学[M].北京:中华书局,1998:321.
[12]梁启超.梁启超全集·中国积弱溯源论(第一册)[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419.
[13]梁启超.梁启超全集·仁学序(第一册)[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170.
[14]梁启超.梁启超全集·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第二册)[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6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