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
■张秉彤
我的父亲
■张秉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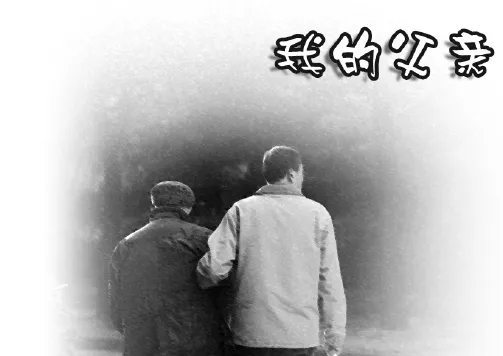
2013年,对我们家人来说,是极为不平凡的一年。这一年的5月28日,父亲的人生道路突然间戛然而止,出人意料,让亲人朋友扼腕叹息,唏嘘不已。
父母原本生活在北京的兄长家,身体健康,豁达开朗。5月间一人独自去了兰州,访亲会友,其乐融融。我是星期六(25日)与父亲最后一次通话,告知他在北京寄给我的东西收到了(之前父亲打电话问过我几次东西收到了没有),同时抱怨因为东西寄到我居住区,耽搁一星期才拿到包裹单,已接近寄存期限,取包裹还要去我上班的附近,父亲听后连连说下次再寄东西,便直接寄到我的单位,再不寄到小区了,并说寄前曾与我母亲商量过。未曾想这次通话竟成诀别。
28日凌晨四时许,接到兄长从委内瑞拉打来电话,说是父亲病重,在医院抢救。同时听到兄长接到电话说医院打算放弃抢救,急得兄长直骂:什么破医院,好好的人进去,便成了这样。我是完全懵了,那天晚上不巧将两个手机都关了,好在还保留了座机,睡得稀里糊涂,接到这样电话,简直是晴天霹雳,一时不知所措。
事情怎么会是这样呢?前两天与父亲通话还好好的。父亲生活一直非常规律,早睡早起,坚持天天锻炼,即使坐火车,途经站时也下车活动,不抽烟不饮酒,喜欢读书写作,并注意收集,将看过的报刊杂志进行剪辑整理,打理得井井有条。还时时提醒我收集我发表过的文章待有机会结集出版。
父亲通过我发表了一些他描写海南、甘肃和美国风土人情的诗词及文章。待他去世后,才了解到他写了许多诗词,并让秉云姐打印了厚厚一本。
当然,生前花费父亲最多心血和耗费最大精力的还是写作他的《西部炊烟》。此书本是父亲1960年到通渭抢救人命时每天记的日记,计有十多万字,整理后已成稿有几年时间了。现有关书稿由我保管,我也是根据自己的意见对书稿作了多次修改,因父亲的突然变故,及后来的医疗官司纠纷,一整年来我便把主要精力放在为父亲讨说法上了,书稿一事被搁置了起来。
官司总算有了结论,经过医学鉴定的确属于医疗责任事故并经庭前调解进行了赔付。说法是讨回了,但父亲永远地走了,我们只能在卧龙山前、大清河畔凭吊父亲的亡灵了。多少个日日夜夜,兄弟姐妹们遥望着逶迤的燕山山脉,凝视着汩汩流淌的黄河、南渡江,还有静谧的明州湖面,向父亲倾诉我们的思念之情。
父亲的一生是艰辛的,父亲的一生又是奋斗不息的。父亲于1949年9月在察哈尔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并在开国大典以文艺兵的身份参加天安门广场演出。在这个时段参军,按理应是非常幸运了,正好赶得上离休序列。但又是何其不幸,所在单位以资料不全等原因不予承认,父亲便拿着当年参军的照片,在全国各地找他同一批的战友(全部为离休干部)及所在部队的领导以证明自己。一次次的找,一次次的开证明,父亲所在单位均以此类凭证不能作为认定依据为由而拒绝。唉,这些过程是多么的不易,父亲内心又是承载了怎样的负重。我曾经陪父亲跑过一次河北,因父亲参军是在察哈尔省,由现在的河北、山西、内蒙三省的部分地区组成,之后察省不存在,要查阅当时的档案何其难,推来扯去,不知所向,只能找人。岁月蹉跎,能找的人越来越少,临了父亲也没能坚持,抱着终生最大的不平和委屈离开了人世间。
父亲在部队上了由中央军委直管的中央高级后勤学校,在油料储运专业学习。复员分配至天津石油学校,后响应国家号召,五十年代来到大西北,在兰州石油学校担任教务长。60年,父亲作为“救命团”小组长深入全国最贫困的地区通渭县抢救大量因饥饿濒于死亡的人。父亲是怀着满腔热忱、怀着对老百姓的无限深情,投入到抢救人命工作中,摸索总结出采用代食品、麦管喂养法等一整套方法,挽救了许许多多人的生命。最贫困的地方、最艰难的岁月,父亲忘我的工作赢得老百姓的广泛赞誉,也与当地群众结下了深厚感情。生于河北阳原大户人家的父亲,后搬迁到张家口市(原察哈尔省会),算是城里人,竟然在通渭县吉川乡许堡村这个地方一呆就是18年。抢救人命工作结束后父亲在当地中学教化学,继续从事教育工作。父亲是多才多艺的,我们小时候都是唱父亲作词作曲的儿歌,记得他还办扫盲班,自己编扫盲课本,教当地人识字唱歌。
父亲是个老军人,部队作风明显,没有不良习惯,坐的时候身板挺得笔直,走起路来像急行军。小时候,父亲紧牵最小的永侠妹在前面快步行进,小妹头上的羊角辫上下翻飞,我和兄长、姐姐后面跑步跟随。父亲教会我们许多苏联老歌曲和革命歌曲,他自己会用俄语、日语唱好多歌曲,并会拉手风琴、吹口琴,晚年又学会了吼秦腔,2013年春节家庭团圆时,父亲还底气十足地给我们演唱《十五贯》《王宝钏》《三滴血》等好几曲秦腔呢。
在我的人生道路上,每到关键节点都是父亲给我指明方向,帮助我渡过难关。我大学毕业后到监狱做管教干部,不愿干。是父亲听广播时,捕捉到兰州大学招收本科试点班,带我找老师了解情况,鼓励我报考,竟如愿以偿。93年独自来到海南,过着居无定所的生活,父亲一直对我放心不下,在我本人不在的情况下,竟成功让我报考西固法院,可惜没有联系到我,错过了考试,等我回去后才知此事。这次因父亲的事与西固法院联系,引起我这段回忆。那些年我一直在南方打工,飘泊不定,97年春节回家,节后父亲与我一起到东方红广场了解省直部门招考公务员,经过比较我们选定了计委和扶贫办两家单位,难以决择,最后几乎是通过抓阄的办法确定了计委。
因我自去西安上学以后,就与家人聚少离多。家人说我继承父亲的优点最多,实际仅指写作方面,我是学文科的,勉为其难而已。就知识面和掌握的技能来讲,父亲要远远强于我。父亲早年在中专是教有机化学的,到村里中学,因父亲有文才,除了教化学外也开始教语文、政治、物理。父亲能写一手漂亮的毛笔字,在通渭时每到春节,家里挤满了人,求父亲写春联,父亲现编现写,忙得不亦乐乎,要知道通渭是全国有名的文化书法之乡呀,能写字、写好字的人很多。很喜欢父亲用粉笔写的大大的空心字,我没有学会;很佩服父亲一个人就能在一面大大的墙上完成图文并茂的黑板报,还记得,父亲在景泰学校办黑板报时画的张海迪,好像;儿子小的时候,父亲来家中,廖廖几笔画了荷花,上面蹲一只小青娃,让我和爱人羡慕不已。
父亲是天下少有好脾气的慈父。多少次我们自以为是地埋怨和数落父亲的一些事时,他老人家默默地坐在小板凳上一声不吭,直到我们说累了,口干舌燥了。记忆中父亲没有打过我一次,只记得有一次不知何事,把父亲惹怒了,在许堡的街道上追我,跑的过程中,我回头看父亲,见父亲脸通红。追没追上,后来的事就不记得了。
父亲对我们管教很严,不允许我们喝酒抽烟。我一直没有抽烟,酒也是单独从不喝,不馋酒,虽然有点量。父亲对我们学习抓得非常严,直到我们上班了,他还督促我们学习。父亲更是以身作则,前些年回兰探亲时,大清早被电视的声音吵醒,起来发现是父亲学习英语,当时我还不理解,颇有微词。那时,父亲已是70左右的人了,为了去他美国小女儿家,苦学英语,笔记本上的英语书写得非常漂亮整齐,年轻时他是学习俄文和日文,英语没有什么底子。小妹小时候学习时,父亲一直是陪着的,坐在一边,将瓜子仁剥好堆放在一起,小妹边学边吃,我们也时不时溜进去,抓些来吃。
父亲一生是曲折的,也许是父亲率直甚至有些天真的性格和直人快语的缘故吧,霉运和不公似乎始终伴着他。“文革”时揪斗、游街,正常年景也不消停,几乎历次运动都难幸免,父亲自嘲他都成老运动员了。这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家庭出身不好,破产地主的成份时时都有可能被置于革命的对立面,即使是我们兄弟姐妹,小时候也是备受家庭成份的煎熬。对此,我们也很是想不通,都破产了,还是什么地主啊?!
看着我们兄弟姐妹一个个长大成人,父亲很满足,也经常以我们为荣。我们兄弟姐妹四个都上了大学,兄长和姐姐都在央企工作,我在政府工作,妹妹留学并定居美国。父亲经常说我们几个子女是他最大的财富。
父亲经过数十年的奋斗,把我们一个个培养出来,日子终于可以好过些,可父亲又意外离去,匆忙得没有留下一句话,没有给他的亲人增添一点点麻烦。每每想起此事,不由让人唏嘘不已,潸然泪下。
总觉得父亲还在我们身边,并没有离我们而去,愿上天保佑,也许父亲已是神仙了。
谨以此文深深怀念我亲爱的父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