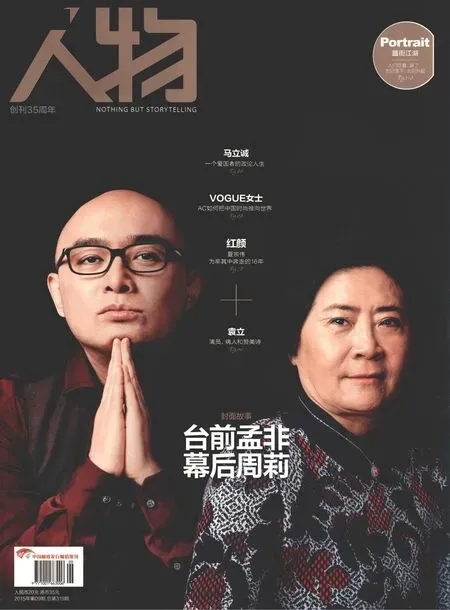柏林爱乐的新首席
柏林爱乐的新首席

基里尔·佩特连科
将在2018年代替
西蒙·拉特爵士的柏林爱乐新首席指挥
从柏林爱乐的换首席风波看德奥音乐在民主时代的遭遇。
2013年1月,西蒙·拉特爵士(Sir Simon Rattle)突然宣布2018年开始不再担任柏林爱乐乐团首席指挥兼音乐总监。拉特在宣布自己的决定时还不过58岁,对于一名指挥来说正当盛年,然而十余年来的高负荷、高曝光率的工作状态简直已经将这位曾经的天才掏空,特别是他在柏林爱乐乐团赖以成名的核心德奥音乐(如贝多芬、勃拉姆斯、瓦格纳与布鲁克纳等)方面几乎毫无作为—这些音乐不仅在德国音乐会听众心目中地位崇高,对于全世界古典音乐爱好者来说都是最受欢迎的核心曲目。自从汉斯·冯·彪罗(Hans von Bülow)等传奇指挥家为乐团注入演奏德奥音乐基因,他们在此后一个多世纪以来还从未在这方面如此广受质疑。人们普遍认为,在拉特爵士任内,柏林爱乐乐团逐渐丧失了自己曾经的核心竞争力与独特的声音,沦为了一支演奏技巧卓越而音乐平庸乏味的乐团。
一个有趣的事实是,1989年,首席指挥赫伯特·冯·卡拉扬(Herbert von Karajan)逝世后,乐团开始以所有团员参与民主选举、一人一票的方式决定下届掌门人,在此之前,首席指挥的选择权一直只掌握在乐团管理层和相关文化主管部门手中。柏林爱乐的“民主化”与这个国家的变化同步,与柏林爱乐大厅仅一墙之隔的柏林墙倒塌也在1989年。
一起变化的还有首席指挥的话语权,此前,首席指挥对乐团的普遍管理方式是独裁式,卡拉扬则更变本加厉,在他35年的绝对统治力下,柏林爱乐乐团被打造成了一支几乎无懈可击的“梦之队”。也正是这种独裁式管理使卡拉扬晚年遭遇乐手们强烈反弹,最终导致了二者关系的破裂。在他死后,乐手们要求以更民主的方式来讨论音乐。
而在科学音乐培训方法下,乐手们演奏水平也在不断进步,这些都让现代乐手们无法再像贝多芬时期,完全隶属于宫廷,听命某一人。在这个乐团越发强势的时代,比起独裁者,改革后的首席指挥更类似于议会中的“议长”:权威依然独一无二,但在实际权力上却等同于普通“议员”。还记得2011年拉特率领柏林爱乐来北京演出,笔者在台下观看了排练,印象最深的就是每一名乐手都可以随时打断指挥,发表自己对音乐处理的见解。
“民主”可以产生伟大音乐吗?从柏林爱乐过去13年来看,似乎这种体制引发的是艺术上的倒退。优秀的音乐需要有明确取向,这个取向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指挥,指挥个人要什么效果,就要抛弃很多东西,如果靠民主方式讨论音乐,间接等于音乐没有统一思想,让它变得这地方像一个人,那个地方又像另一个人,使音乐平均化,也平庸化。尤其是德奥音乐,现代乐团的表现明显不如从前。从贝多芬到勃拉姆斯,再到安东·布鲁克纳,德奥音乐有一种明显的张力,这也是其在演奏时格外强调的东西,它有时不会照顾到每个细节是不是都很完美,而是强调张力中那种一以贯之、不妥协的精神,这需要灌入指挥者清晰强大的意志。因此,乐团在选新总监时,一部分人希望选出一位更具有音乐才能的年轻指挥家,继续维持在音乐上的“民主”;另一部分人则寄希望于在一位更强势的指挥家带领下,重回卡拉扬的“独裁”时代。
2015年5月11日,柏林爱乐乐团全体音乐家集合在柏林市郊的耶稣基督教堂,在这里选出乐团未来掌门人。这个教堂对柏林爱乐来说有特殊意义:柏林爱乐大厅尚未建成时,这里是乐团的排练与录音场地,许多在今天依然广为流传的唱片都在这儿录制。乐团在这里进行投票,明显希望曾经发生在这座教堂里的历史能激励乐手们投下负责任的一票。
教堂外数十名记者焦急等候,忍受着意志力与膀胱的双重考验,据说教堂周围根本找不到卫生间。这也是柏林爱乐乐团在社交网络时代第一次大型人事变动,上一次发生在1999年6月。从Twitter到Facebook,从微博到微信朋友圈,这次换届选举简直成了全世界音乐家、音乐从业者、媒体人及音乐爱好者的狂欢。有好事者PS了一张乐团某圆号演奏员向主要候选人之一安德烈斯·尼尔森斯(Andris Nelsons)表示祝贺的推文截图,这张图令众多人士纷纷中招,接连向尼尔森斯发去“贺电”,包括《BBC音乐杂志》、大提琴家阿尔班·格哈特(Alban Gerhardt)与钢琴家郎朗。
长达11小时的讨论与投票后,闹剧般选举却以“没有产生结果”告终,令各界哗然。在柏林爱乐过去换届中,虽然也发生过卡洛斯·克莱伯(Carlos Kleiber)这样的“隐士”拒绝提名,但还不至于出现全团因为总监问题达不成一致而推迟选举。这已经深刻说明了乐团在未来前景方面产生巨大分歧,矛盾中心点集中在了两位当今最火热的指挥家—安德烈斯·尼尔森斯与克里斯蒂安·蒂勒曼身上。
拉脱维亚指挥家尼尔森斯在不到40岁年龄所取得的艺术成就已经高过前辈,没有人会怀疑在未来的音乐史上他与任何一位指挥大师相比都毫不逊色。不过,尼尔森斯最大的问题也同样在于过分年轻,指挥家本人似乎也不太愿意在这样的年龄草率入主柏林,害怕成为下一个拉特恐怕是他的主要考量。
而现年56岁的蒂勒曼和尼尔森斯不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他们在柏林爱乐如今最缺失的德奥核心曲目上同样优秀,都兼具出众的指挥技巧与丰富乐感,也都是瓦格纳歌剧方面的权威,这些都是乐团看重的特质。
不过二人的差别也同样巨大:相比尼尔森斯广泛的曲目,蒂勒曼几乎与任何乐团都只演出自己擅长但数量有限的曲目,在现代音乐方面也十分谨慎。但蒂勒曼是位血统更纯正的德国指挥家,他在艺术上的强势作风令人联想起老派德国指挥大师们,这恰恰是在卡拉扬逝世20多年后,柏林爱乐乐团的老乐手们发现自己最怀念的东西。代表乐团内部“保守势力”的弦乐声部鼎力支持蒂勒曼,他们很多在卡拉扬时期就一直在柏林爱乐,但年轻人居多的管乐声部更青睐尼尔森斯,两派人马的矛盾最终导致选举流产。
但谁也没想到,柏林爱乐在6月22日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了46岁的俄罗斯指挥家基里尔·佩特连科(Kirill Petrenko)当选。一夜之间,柏林爱乐就圈定了他们的下一任首席指挥兼艺术总监,要知道在一个多月以前的那场闹剧里,佩特连科这个名字只是被当作配角捎带提起。
虽然在中文世界里佩特连科的名字并不响亮,但他在德国音乐界,特别是歌剧领域里的声望已经丝毫不逊色于蒂勒曼等指挥家。基里尔出生于俄国城市鄂木斯克,18岁移居奥地利。25岁时他成了维也纳人民歌剧院的音乐总监。2001年,他在迈宁根剧院上演瓦格纳的《尼伯龙根的指环》被评论界惊为天人。在柏林喜歌剧院任职期间,他除了演出大量歌剧外,还率领这支并不擅长演奏音乐会的乐团奏响了令人印象十分深刻的贝多芬交响曲。
佩特连科2006年2月第一次作为客座指挥与柏林爱乐合作。正如6月22日新闻发布会上一位乐手所提到的,通常当一支乐团迎来一位首次与他们合作的指挥家后,乐手们都会讨论“我们今后还要不要请他再来”,但当乐团第一次与佩特连科合作后,讨论的话题变成了“我们何时才能请他再来?”佩特连科与柏林爱乐合作次数不多,但每次都获得了极高评价,特别是2012年他们携手演绎了《狂喜之诗》,简直成为了这部作品有史以来最令人感到振奋的版本之一。2014年,佩特连科原本计划指挥柏林爱乐演奏马勒的第六交响曲,但指挥家却令人匪夷所思地以“私人原因”取消了音乐会。要知道,在柏林爱乐乐团换届之年作出这样的举动,无异于宣告自己从候选人名单里除名。
但柏林人决定“不计前嫌”,6月21日再度集结投票(这次没有对外披露集结地点)。乐团在尼尔森斯与蒂勒曼身上出现的巨大分歧已尽人皆知,因此,两人都相继宣布在这种情况下退出选举,局面反倒明朗开来。
当接到乐团正式邀约时,佩特连科当即表示同意—这位患有轻微自闭症、惧怕坐飞机的指挥家,决定要勇敢挑战音乐界压力最大的职位,驾驭最难以征服的乐团。
尤为令人感动的是过去一个多月,柏林爱乐所展示出的在艺术上的坚持原则与毫不妥协。
当尼尔森斯与蒂勒曼两位同样优秀的候选人进行角逐时,音乐家们会因为对乐团前景看法不统一各持己见,既没为早日解决争端投出违心的一票,也不会“以大局为重”,甚至不惜在外人前暴露内部分裂;第二轮投票中,乐团又没有为拖延问题选择过渡性质的巴伦勃伊姆,或为票房与赞助邀请杜达梅尔之类在艺术上尚缺打磨的年轻指挥家。
选择佩特连科,可以看出是一个抛弃了除艺术之外所有因素、经过深思熟虑的决定,体现了乐团在面临前途命运这样重大决断时的成熟、理性与骄傲。
虽然很难判断佩特连科上任后究竟会交出什么样的答卷,但一支有着这样风骨的乐团,即便作出错误决定,也一定不会永远沉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