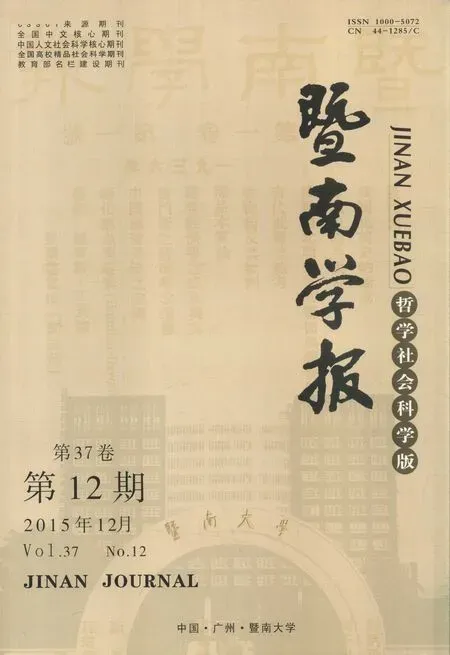敦煌写本《斋琬文》的文体实质及编纂体例
张慕华
(中山大学 学报编辑部,广东 广州 510275)
敦煌写本《斋琬文》的性质与影响,是敦煌斋文研究中的重要内容,因其涉及斋文文体源流及内容变迁,引发学界对其研究的浓厚兴趣。由于敦煌文献资料残缺严重,现已难以再见《斋琬文》全貌,目前留下《序》、目录及少量被确认的篇目内容,这给研究带来较大难度,也引起学界诸多猜测和争论。尤其是对《斋琬文》的称名定义及文体实质,尚未有清晰界定。本文拟在前贤研究基础上,对此问题作进一步辨析,并集中分析《斋琬文》的编纂思想和体例,挖掘其文献学与文体学价值。
一、《斋琬文》的文体实质
(一)《斋琬文》的称名与定义
斋文是佛事活动中常用的一种大型文类,在斋文中夹杂入一个“琬”字,令学界对“斋琬文”的确切定义起了诸多猜测。目前学界对“斋琬文”称名有两种解释:第一种是普遍认同的说法,由那波利贞先生提出,指出琬是琬圭之意,转意为不朽的文章。《说文》解释“琬”字:“琬,圭有琬者,从玉,宛声。”张广达先生认为“琬”当是菁萃之意。第二种由黄征先生提出,认为“琬”通“惋”,似为“哀惋之文”的意思。但《斋琬文》目录中“庆皇猷”等篇目明显是歌颂喜庆而不是哀惋,后黄征先生作了补正,认为“惋”有惊叹之意,“斋琬文”就是“斋叹文”。笔者认同第一种看法。黄征先生不认同第一种解释,觉得“琬”字若按此解释,夹在“斋文”两字中间,比较别扭,正常应作“琬斋文”。实际上,《序》中所提的“叹佛文”才是后人常说的斋文,“斋琬文”的“斋”字并不与“文”字连起搭配。对于这两点,后文还有详释。笔者认为,此处的“斋”字应指斋会,“斋琬文”的字面意思即是斋会中使用的精彩文段。
(二)《斋琬文》的内涵与文本范围
值得探究的是,《斋琬文》所收文样究竟是什么文类?它与叹佛文、斋文之间又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序》称“裁为叹佛文一部”,可知《斋琬文》所收文样应属叹佛文无疑。大多数研究者认为,“叹佛”仅是斋文中的号头片断,而《斋琬文》收录的内容也仅是叹佛或叹德的号头部分。王三庆先生则据P.2547 本《斋琬文》第三“序临官”下有一篇题为“叹佛文”的文段,推测“在各分类小目之前,每每有一叹佛文之冒头,盖为通用冠于各篇之前,知每一斋会时必有赞叹佛陀文字,盖焉请佛受喜降临之常套”。然而,依P.2940 本《斋琬文》载“赞佛德”第一大类目下有一段类似于叹佛号头的文字,却未以“叹佛文”标题;又“庆皇猷”第二大类目直接进入分类小目,并未见王先生所说单列有叹佛文之冒头。经笔者检读,《斋琬文》收录的文样并不仅仅是开端之处的叹佛号头部分,而是包含叹佛、叹各类人事功德以及发愿等内容,而“庆皇猷”下收“鼎祚遐隆”“嘉祥荐祉”两篇均是结构完整的斋文。可见,只要与某类设斋主题相关的精彩斋文或片断内容都会被收入,以制作成供学习、摹写的各类斋文实用模板。这样我们就可理解《斋琬文》为何分成十类八十余条,如果仅是收录叹佛号头部分,岂不千篇一律?若不涉及具体事由,具体细目如何区分?诸如“马死”与“猪死”,它们是如何区分的?
事实上,所谓叹佛文就是斋文。“叹”也即赞叹,是指以口业称美其德也。《文句》二曰:“发言称美名赞叹。”《行事钞》下三曰:“美其功德为赞,赞文不足,又称扬之为叹。”《佛学大辞典》释义“叹佛”即赞叹佛德之偈文也。弥满于经中,禅门之疏及回向之音,以联句或四句偈叹佛德,谓之叹佛。佛经中有不少叹佛偈、叹佛咒,如《无量寿经》里就有法藏比丘叹佛德的偈文。唐代以来,随着佛教世俗斋会的流行,在斋会上赞叹佛法功德、为斋主祈福成为特定的仪式。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卷一“受斋轨则”载,受斋时必叹佛德。圆仁《入唐求法寻礼行记》亦载开成三年(838 年)斋事,有斋叹佛德之仪文。经文中的叹佛偈咒逐渐发展为佛事斋会中诵念的具有结构性段落的叹佛文。《文苑英华》保留有宋之问《太平公主五郎病愈设斋叹佛文》、王维《为崔常侍第十五娘子奉诏落发赞佛文》,均是举行佛事斋会时祈佛祝祷的文辞。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后者全篇结构已与敦煌文献中完整的斋文篇章结构一致,包含叹佛号头、叹斋主德、述事由、叹道场和发愿等几个部分。明人贺复徵编《文章辨体汇选》设有“叹文”一类,将佛教的斋会文书称为“叹佛文”,而道教的斋会文书则被称作“叹道文”。由此可见,“叹佛文”或“赞佛文”,实际上是早期佛教斋会文书的称名,与后来广泛运用的“斋文”实为异名同体。至于P.2547 本《斋琬文》中出现题名为“叹佛文”的号头段落,这在敦煌文献各种抄习本的文样中亦属常见,与此相似的还有用“叹文”“愿文”“庄严文”等来标示的斋文结构性段落文样。如前文所述,在复原的《斋琬文》写本中,此段名为“叹佛文”的号头仅出现过一次,很有可能是后来的书手在传抄过程中添加的。因此,序文所称“叹佛文”应该就是斋文,而非仅是作为结构性段落的叹佛号头。《斋琬文》收录的文样即是各类叹佛文(斋文)中的精粹篇章或文段,各种结构性文段则可以通过剪裁组装的方式被“裁”成一部叹佛文。
此外,关于《斋琬文》是否能涵盖敦煌文献中其他斋文文样或文集这一问题,笔者以为有必要在认清《斋琬文》性质的基础上,对其收录的文本范围加以清晰的界定。“斋琬文”实际上是一部文集的名字,编著者称“裁为叹佛文一部”,可知这部文集所收录文段的文类性质是叹佛文,而“斋琬文”就是作者为这部叹佛文集拟定的名字。事实上,敦煌文献中仅有《斋琬文》一卷,其他斋文集或称《诸杂斋文》《诸文要集》《释门文范》等,并不以“斋琬文”来命名,也没有出现“斋琬文”一词。宋家钰先生在考察斋文源流过程时指出,敦煌文献中有多种诸杂斋文的版本,其中所列文类与《斋琬文》并不完全一致。因此,“斋琬文”不是斋文的通称,只是众多斋文文范中的一个通俗精彩的选本,用“斋琬文”的名义去涵盖各类斋文(或称愿文)是不合适的。
(三)《斋琬文》具有“斋仪”的特征
《序》称“故乃远代高德,先已刊制斋仪”,这表明作者编著《斋琬文》是自有渊源的。此处点出了“斋仪”,可见《斋琬文》与斋仪有密切关系,是世俗版的叹佛文斋仪文本。斋仪源自于书仪,是斋文的范本。所谓“书有书仪,斋有斋仪”,斋仪文集与书仪在很多方面可相较而论。书仪有仪注型、专题型、实例型三种类型,而从《斋琬文》的编纂状况来看,亦可视之为与某种具体斋会对应的专题型斋仪文范。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书仪通常是由程式化的几个部分组合而成的,如完整的《朋友书仪》包含三部分内容,首先是胪列节气时候用语的套话,其次为往复书札,最后是简略的往返书疏。同样,一篇完整的斋文也是由不同功能的文段组合而成的。笔者曾撰文专门分析以斋文为主的佛事文体的这种结构性组合方式,认为“佛事文体的基本文体结构是由具有特定功能的仪文段落按照一定的仪轨程式次第组合成文。这种特殊的文体组合方式充分体现出以功能性为核心导向的结构特点”。这种组合式的文体结构在佛事文体中很常见,如“按特定仪式次序依经编撰的礼忏文在某种程度上已具备指导法会行仪进程的实践作用”。《斋琬文》中大量收录的与题旨相关的叹佛、叹各类人事功德乃至发愿等精彩段落,正是以标准式的功能性文样形式,为“来学者”和“童蒙”提供了学习或模拟的范本。综上所述,《斋琬文》是一部通俗版的斋仪文集,也是精华版的叹佛文(斋文)集锦,其明确的规范性与功能性导向,充分显示了其作为宗教应用仪文范本的典型特征。
二、《斋琬文》的编目体例与编纂思想
虽然,我们现在已很难完全复原《斋琬文》的文本原貌,但对其现存完整的序目进行分析,仍可把握其基本的编排体例和特点,并由此窥探该书的编纂思想,从而了解其产生的深层文化动因。
(一)编目体例
《序》云:“总有八十余条,摄一十等类。所删旧例,献替前规。分上、中、下目,用(永)传末叶(业)。”具体细目分类如下:
1.赞佛德:王宫诞质、逾城出家、转妙法轮、示众寂灭
2.庆皇猷:鼎祚遐隆、嘉祥荐祉、四夷奉命、五谷丰登
3.序临官:刺史、长史、司马、六曹、县令、县丞、主簿、县尉、折冲、果毅、兵曹
4.隅受职:文、武
5.酬庆愿:僧尼、道士、女官
6.报行道:役使(东、西、南、北);征讨(东、西、南、北)
7.悼亡灵:僧尼(法师、律师、禅师);俗人(考妣、男、妇女)
8.述功德:造绣像、织成、镌石、彩画、雕檀、金铜、造幡、造经、造龛、造陈品、造浮屠、造炊轮、开讲、散讲、盂盆、造温室
9.赛祈赞:祈雨、赛雨、赛雪、满月、生日、散学、闪字、藏钩、散讲、三长、平安、邑义、脱难、患差、受戒、赛戒、入宅
10.祐诸畜:放生、赎生、马死、牛死、驼死、驴死、羊死、犬死、猪死
由《序》文可知,《斋琬文》十类八十余条是分上、中、下目来排列的。至于上、中、下目具体对应哪几类,《序》中未明言。笔者分析:上目对应1、2 类,是用于佛俗节庆和帝王庆诞等高级别的佛事法会;中目对应3 至6 类,是针对官场方面(含僧道官方)的一系列贺吉斋会;下目对应7 至10 类,是供民众日常生活类祈禳及民俗活动所用之佛事活动。可以清楚地见到,其所设文类按设斋对象的身份及设斋事由性质进行区分,由佛及俗、从官方到民间,显示出鲜明的等级与阶层序列。
类别下面分条,条的排列也有一定规律可循。如“赞佛德”下设四条,分别按佛祖一生的时间顺序来排列,分别对应四类佛俗纪念节日:王宫诞质(四月八日)是佛祖诞生日,逾城出家(二月八日)是佛祖成道日,转妙法轮(正月十五日)是佛祖传法日,示众寂灭(二月十五)是佛祖涅槃日。“庆皇猷”下设四条则是从国运、朝廷、外交、民治等不同方面,由上及下、由内到外,颂赞帝王政绩功业,为皇帝祝寿祈福。“序临官”专为各级官员贺任祝祷,从“刺史”到“兵曹”是按官职大小排列的。在“报行道”类目中,按东、西、南、北的方位次序来排列。“悼亡灵”类目下,按佛俗之分,僧尼在前,俗人居后,其中法师、律师、禅师又是按职别资格高低来排列,至于俗人,则按辈分和男女性别由高到低排列。“述功德”九篇,从“造绣像”到“造温室”,是按供养三宝(佛、法、僧)功德的类别来排列的。“赛祈赞”所设各条初看较为散乱,都是祈求方面的,但仍有其类别序列:“祈雨”“赛雨”“赛雪”三条是求天,“满月”“生日”是庆生,“闪字”“藏钩”是民俗活动,“三长”“平安”“邑义”是民间社邑活动,“脱难”“患差”“入宅”等是日常居家类祈祷。“祐诸畜”下设几条按先生后死排列,而从“马死”至“猪死”,各种动物死亡设祭的次序应该是按照其在人们生活中的重要程度来安排的。
由上可知,佛事斋会文书是具有明确斋意指向的实用仪文,在不同斋意的斋仪类别下,又可根据具体的设斋事由再次划分仪文的类别。正如章学诚所说:“文章之用多而文体分。”从文体分类法的角度讲,《斋琬文》的这种按斋意事由分编斋文文样的体例,与书仪按礼仪类别划列仪文的编排方法一致,这与斋仪文范作为应用模版的文体性质是相适应的。《斋琬文》这种以类分目、以事类文的编目体例,强调从斋体的内容、功用等方面区分细类,以显示斋会文书的类属层次和系统性,突出了中国传统应用文体分类重实用的根本特点。
(二)编纂思想
斋仪是佛教中国化、世俗化的产物,深受儒家礼仪文化和民俗流变的影响。《斋琬文》是佛教斋仪文范,其编纂思想充分体现了中国佛教世俗化与本土化发展的特点与进程。具体而言,其编纂思想主要体现在:
第一,应机随宜,求全从俗。
隋唐时期,佛教传播的世俗化进程不断加深,以祈福消灾为目的的公、私斋会十分盛行,而《斋琬文》之类的斋文文范即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作者在《序》中追述佛教传法之道时,云:“所以为设善权之术,傍施诱进之端,示其汲引之方,授以随宜之说。”又述及成书缘由,称:“故乃远代高德,先已刊制斋仪,庶陈奖道之规,冀启津梁之轨,虽是词警(惊)掷地,辩架谭天;然载世事之不周,语俗缘而尚缺。”提到远代高德之先贤已刊制斋仪,虽然词句理论非常精彩,但有两点不足:一是“载世事之不周”,指之前的斋仪应用范围不够全面;二是“语俗缘而尚缺”,指之前的斋仪不够通俗。对此,《斋琬文》作者提出“应有所祈者,并此详载”,只要人们有所祈求的事项都尽量纳入,以解决之前斋仪“载世事之不周”之缺陷。从其收录文样所涉斋会类型来看,既有佛俗节庆,又有上自帝王庆诞下至庶民生、老、病、死等诸种日常祈福斋会,体现了此书“求全”的一大编撰特点。又《序》云:“鱼俗鱼真,半文半质。”俗与真相杂,文与质相间,才能更易为俗人理解和应用,也更能满足普通民众的世俗需求,这就解决了之前斋仪“语俗缘而尚缺”的不足,充分表现出“从俗”的特点。《斋琬文》中设斋事由大都与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的俗事相关,其中最能体现“俗缘”的是“赛祈赞”类,祈赛是民间祈禳的重要活动形式,与社会日常生活、习俗结合得相当紧密。该类下所设分目,从“祈雨”至“藏钩”均是民间祈禳和节俗;三长、平安、邑义是民间社邑定期组织的斋讲、斋会活动,此类民间社邑佛事在唐代已成为一种颇为流行的民俗活动;“脱难”“患差”则是为身患疾病的家人设斋祈吉,希望凭借佛法护佑使病体早日痊愈。又如为临官迁职贺吉的“序临官”“隅受职”,为亡者追助往生、为生者祈福灭障的“悼亡灵”文样等斋会发愿,更是应合了斋主趋吉避凶的世俗心理欲求。
第二,叹佛弘道,积累功德。
《斋琬文》作为佛教礼仪文范,是佛教在普通民众中传播的重要工具和载体,故“叹佛弘道”自然成为其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作者自谓“缁林朽铎,寂路轻埃,学阙未闻,才多不敏”,可知其身份是缁门文人。《序》文始赞佛教东传之功德,云:“详夫慧日西沉,纪神功者奥旨。玄飙东扇,隆圣教者哲人。”其后追慕远代高德,为宣扬三宝、匡化众生,“刊制斋仪,庶陈奖道之规,奠启津梁之轨”。作者忧虑于其时之斋仪倡导“抑亦远坠玄□(风),犹沉圣迹之威光”,故其“裁为叹佛文一部,爰自宣扬圣德,终乎庇祐群灵”。而“叹佛文”作为“斋文”之另称,亦可见其核心意图在于宣扬佛法圣德,以为众生求祈福祉。《斋琬文》所录文样第一类即“赞佛德”,分别赞颂佛祖降生、成道、传法和涅槃四个阶段的妙胜功德,之后再按国家、官场、民众之次序定位各类斋文,“酬庆愿”“悼亡灵”两类又均以僧尼佛事序首,其崇敬三宝、叹佛弘道的宗教情怀,是显而易见的。
佛教世俗传播有一个重要的核心理念,即功德思想。佛徒信众从事佛事活动的基本目的,往往是求取功德。从佛事的概念来看,诸佛教化众生乃是佛法功德,佛徒和众生修行礼忏、供养三宝及作一切善行均为功德。可以说,但凡佛事皆为功德而作。在佛教业报因果学说看来,积累功德可通过回向获得善行福报,从而消除恶业灾障、趋吉避凶。受此影响,功德佛事活动在民众中广泛流行,并集中以各类斋会的形式迅速发展。《斋琬文》收录了大量赞叹斋主功德的文段,如“课邑”曰:“于是共敦诚志,各罄珍财,冀弥勒于道初,供释迦于季运。”“藏钩”曰:“故能薄赛少多,回充功德,共珍斋供,以贺新正。”佛教提倡多积功德、广种福田,积功德的重要方式是供养三宝。《斋琬文》又专设“述功德”类目,主要是供养三宝之功德佛事,如佛供养有“造绣像”“织成”“彩画”“金铜”等,法供养有“造幡”“造经”“造龛”等,僧供养有“开讲”“散讲”“造温室”等。就民众供养佛事言,大都属于“利供养”,带有鲜明的施报心理,其功德回向发愿的功利化、庶民化倾向十分明显。如“序临官”之“长史司马”曰:“惟愿寿仙岳而齐固,财江海而同盈,儿郎则穆穆光风,馆阁乃亭亭挂月。”又如“入宅”曰:“夫娘则花萼端肃,志丽邕和;儿郎则门著珪璋,望标冠冕。”
第三,遵礼循道,劝善化俗。
宗教是社会发展的产物,宗教礼仪的内容和形式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社会礼仪制度的影响。《斋琬文》是佛教与中国儒家礼仪文化结合的产物,作为一部面向民众的通俗斋仪文范,其内容涉及皇室、官场和家庭亲族三大群类体系的礼仪伦理关系,带有浓厚的社会生活气息,充分显示出佛教礼仪对社会礼仪的吸收和融汇。“皇权至上”是儒家政治伦理的核心,在传统中国社会,封建帝王往往通过强化其神圣性来凸显自身的合法性,佛教对帝王进行颂赞和美化,在很大程度上强化了国家政权的神圣性。《斋琬文》“庆皇猷”下设“鼎祚遐隆、嘉祥荐祉、四夷奉命、五谷丰登”四类文样,是专为颂圣贺诞所作,其颂赞的重心由“颂佛”向“颂君”转移,将君王佛化,以佛喻君,拜君如拜佛。随着唐代社会官僚化程度的加深,官场礼仪也迅速发展起来。吴丽娱先生指出:“唐后期礼的重心被转移于地方官场。藩镇格局直拟朝廷,官礼仪节之复杂和森严隆重不下于庙堂;朝廷和藩镇、藩镇和藩镇的礼仪关系成为晚唐五代最大的礼仪特色。”“序临官”“隅受职”所收各级、各类官员任职贺吉斋文文样,显示了佛教对官僚活动的渗透。如“刺史”一文赞颂曰:“惟公股肱王室,匡赞邦家,任重济川,委临方岳。于是剖符千里,建节百城,露冕宣威,褰帷演化,朱轮始憩,下车扬恩慧之风;翠盖将临,拂座置檀那之供。”这些颂赞地方统治者及其僚属的品行和政绩的文句,体现出鲜明的儒家“忠臣”“贤臣”伦理意识。《斋琬文》记录和反映了佛教积极参与封建官方礼仪的历史事实,显示出遵礼循道的编纂思想,而其中的“礼”和“道”,即是以维护和巩固封建皇权统治为根本意旨的儒家纲常之礼和伦常之道。
中国化的佛教更多地包容了世俗伦理的内容,其社会功能更多地趋向于一种劝善化俗之道。作为深入民众社会生活的佛教斋会,其教化伦常与匡化世风之功不可小窥。《斋琬文》自第7 至10类所设篇目,大都与普通庶民社会日常生活相关,展示出浓厚的伦理教化色彩。如“赛祈赞”中的“三长”“平安”“邑义”,属于民间社邑佛事斋会,具有调节邑众群体之关系、淳化民风的社会作用。其中多有颂赞邑民贤良品行以及邑户间团结互助之纯朴乡风的文句,“课邑”曰:“惟某等并是别宗昆季,追用十室之闲;异族弟兄,托交四海之内。可谓帮家令望,乡党楷模……所以家家发菩提之意,世世起擅戒之心,共结胜恩,佥崇妙善。”又如“悼亡灵”中有许多赞叹亡人德行的文句,若男子则以儒家“仁义”“忠孝”之德赞颂,“亡考”曰:“仁信克著,礼则弥深,唱琉范于八纮,播英声于九服。事亲以孝,事君以忠,竭力于家,尽命于国。”女子则颂赞其温婉贤淑之妇德,“亡妣”则曰:“四德光备,六行昭宣,内范冠乎良箴,中馈苞乎美斋诫。”
三、《斋琬文》的文献性质与文体学意义
(一)《斋琬文》的文献性质及其价值
从文献学角度来看,《斋琬文》的内容来源应属于编述类型。“综合我国古代文献,从其内容的来源方面进行分析,不外三大类:第一是‘著作’,将一切从感性认识所取得的经验教训,提高到理性认识以后,抽出最基本、最精要的结论,而成为一种富于创造性的理论,这才是‘著作’。第二是‘编述’,将过去已有的书籍,重新用新的体例,加以改造、组织的功夫,编为适应于客观需要的本子,这叫做‘编述’。第三是‘抄纂’,将过去繁多复杂的材料,加以排比撮录,分门别类地用一种新的体式出现,这成为‘抄纂’。”《序》云:“辄以课玅螺累,偶木成□(林),狂简斐然,裁为叹佛文一部。”编著者在修习佛法课业的过程中,经过自己的加工改造,裁成一部叹佛文,而且“□耳目之所历,窃形遗迹之所经”,表明《斋琬文》所录文样并非自己原创,而是源自对别人文章的汲取。“所删旧例,献替前规”,也表明作者为适应当时的客观需要在体例方面作了改造。由此可知,《斋琬文》是一部编述型的文献。
从编辑学的角度来看,《斋琬文》作为一部编述型的文献,以类目条例来进行区分,有类书的特点,同时又收录了斋文篇章或文段,具有文章总集的特征。总的来看,其性质介于类书与文章总集之间。学界关于类书的概念界定虽不统一,但大同小异,“所谓‘类书’,是指将原文加以分类另行编排的书籍”。《斋琬文》按照内容将叹佛文区分为十类八十余条,分类编排的特征是非常明显的。胡道静先生认为类书“区分胪列,靡所不载”。而《斋琬文》“应有所祈者,并此详载”,虽然是针对斋文专题来分类收集,但也是非常全面的了。《汉语大辞典》解释类书是“辑录各门类或某一门类的资料,并依内容或字、韵分门别类编排,供寻检、征引的工具书”。《斋琬文》作为斋仪文书模板,也为学习写作者提供了模仿和套用的方便。就这一点来看,《斋琬文》与《文苑英华》有类似之处。“《文苑英华》把古人的作品分类编纂,主要的意图在于为读书人和官僚提供考试作文和办公应酬的方便,使应用者有所依傍,得以模仿拼凑。否则,我们就很难理解《英华》选录了那么多律赋、试帖诗、策论、公牍这一现象。”《文苑英华》一般被看作类书,但由于其文类收集较多,又是按照《文选》的模式来分类摘引文章,就有了总集的特点,与传统类书有较大区别。当然,《斋琬文》侧重于按内容分类,与《文苑英华》以文体分类相比,较为单一,但斋文文体风格的展现却是非常突出的。
(二)《斋琬文》的文体学意义
吴承学先生指出:“称名取类、以类相从的体例,则表现了对这个体系的范围、结构、秩序及各组成部分的认识方法与理解程度。”作为斋仪文范的文集,《斋琬文》对于佛教斋会文书的文体类型和文体风格,都起到了很好的揭示作用。
佛教斋文的流行是佛教传播中国化、世俗化的产物,与僧伽使用的佛教律仪文书不同,佛教斋文由于面向普通民众,其内容广泛涉及社会各阶层的日常生活,适用对象与运用场合都不尽相同,故其文体类型庞杂、琐细,加之“古代文体命名的随意性极大,故文体分类的标准也就相当模糊”,这使我们很难清晰界定把握佛教斋文的文类体系。在传世文献中,仅保留了零散的几篇唐代佛教斋会文书,且称名和体式均不统一,尚不能为文类研究提供足够的文献材料。有幸的是,敦煌文献集中保留了大量唐五代佛教斋会文书的篇章或文样,甚至有不少斋文文范集,这为研究佛教斋文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值得一提的是,只有敦煌写本《斋琬文》这部斋文文范才附有详细完整的序目,其“总有八十余条,撮一十等类”的编目,清晰详尽地展示了佛教斋文的文体类型与属性。据《斋琬文》序目可知,唐末五代敦煌流行的佛教斋文是广泛适用于佛俗节庆、官方庆典(包括帝王及各级僚臣)、民间祈禳等功德法会、斋会的礼仪文书。佛教斋文的文体类别是依据斋会的性质、斋主身份以及斋意事由来区分的,其称名除常用“斋文”外,还可以斋会的名称命名,如“二月八日文”“四月八日文”等,或以具体的事由命名,如“患差文”“入宅文”等。这种“称名取类,以类相从”的体例,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应用文体按行为方式和功用划分实用文体类型的基本分类标准。
斋文是佛教礼仪文书,本身就有高雅庄严的要求,而作为斋文精粹文样典范的《斋琬文》,更是注重文辞的雅丽。从语体形式来看,《斋琬文》所收文样和文句均是四六骈偶的美文,表现出中国传统礼仪文书“典重温雅”的文体风格。所谓“骈文必征典”,用典是《斋琬文》的重要特点。《序》文开篇就连用两事典,追赞“纪神功者”“隆圣教者”宣扬佛法之功。文曰“于是慷慨摩腾,御龙车而游帝里;抑扬僧会,启金相而耀皇畿”,分别寓指东汉时印度高僧摩腾驾白马入洛阳献释迦图像并诸经以及三国时康僧会在建邺为吴主演示佛骨舍利之灵迹二事。又如用人物典,曰“龙树抽英,冠千龄而擢秀;马鸣驰誉,振万古而流光”,“庐山则杞梓成林,清河则波澜藻镜”,龙树、马鸣、庐山、清河均是佛教史上的名僧大德。再如“嘉祥荐祉”中多引用各类祥瑞物相贺吉,像“白狼”“赤雀”“素麟”“嘉禾”“芝草”等都是喻示太平治世的古代祥瑞之物。此外,《斋琬文》又称“叹佛文”,“叹”在佛教是音声呗赞的偈颂。在中国古代文体的基本语体形式之中,骈体由于其用词典雅且注重音韵方面的优势相当明显,其与佛经文体中的偈颂与呗赞具有相似的语体功能。因此,《斋琬文》利用骈文“协其音,偶其辞”的押韵、对偶形式,既适应了中国本土的语言表述方式又不失赞佛之根本,极大地便利了斋文的讽诵与传播。《斋琬文》采用骈文语体,究其根本是受魏晋以来社会礼仪文体骈俪风气的习染和讲唱、诵读类文学惯用骈偶铺排方式来叙事的影响。它打破了汉译佛经文体不用骈语古文、弃文质实的语体规则,形成典重温雅、华丽藻饰的礼仪制词文体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