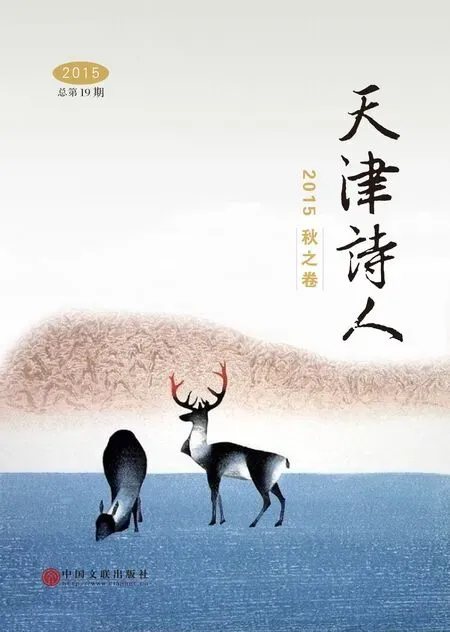当下诗坛:对诗歌空间“数”值的再认识
卢辉
一 诗歌写作:“空间地域”与“心理时长”的交融
1 诗歌“双重空间”和“单向空间”
“地域的转换”与“经历过的地方”对创作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地域或地方与创作的关系有它几个层面的东西,一是出生、成长、生活的地域或地方,由于它的长久性,它是“宿命式”、“渐变式”、“持久式”、“积淀式”的生存空间与精神岩层,它是双重空间;二是旅行、经历过的地域或地方,由于它的短暂性,它是“新奇式”、“瞬息式”、“突变式”、“直击式”、“显露式”的即席空间,它是单向空间。按这样的二个层面来说,地域或地方空间有它的“器质性”和“物理性”的一面,也有它“生理性”和“神启性”的一面。就拿我早期的诗歌创作来说,我先后写了许多象《关于战争以及它的后遗症》、《穿过战争到达谁的伤口》、《再过泸定桥》、《中国从那个山坡下来》等一批战争类的长诗。迄今为止,这些战争长诗在中国诗坛究竟有多大的影响力我不敢妄言,但它们肯定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这批战争长诗的问世正是“地域的转换”与“经历过的地方”对我的影响。也许有人会提出质疑,我不是一个“战士”哪来的战争呈递,然而,从“都市”到“山坳”反差性极强的空间变换,在我幼小的心灵里何尝不是一场历炼式的“战争”,在我成长过程中,一种寻求“突破”的渴望是那样的“壮怀激烈”。我的确不是一个“战士”,但我肯定是一个“斗士”,在我经过某个象“泸定桥”这样的战争“遗迹”之后,持久性的“积淀”与“宿命”终于找到突变性的“直击”与“显露”,这样的影响力既是空间的,更是神启的。
2 诗歌的“空间体式”与“精神透视”
其实“空间体式”在绘画上有较严格的“技术参数”,比如坐标、三维、透视、 焦点、分割线等等,也就是“不成规矩何成方圆”之说,这里强调的是绘画的“基点和骨感”,从现代诗创作而言,“空间体式”没有象绘画有硬性的“数值”, 而且, 谈的更多是“时空观”,因为,只有时空观的存在,才有现代诗的“精神透视”, 即心象, 正所谓:心之所至,四面八方。因此,现代诗的时空跨越给人更多的是“超验”、 “魔幻”、“突兀”和“新奇”,它不象格律诗有许多内在的规定性, 有较为严格的韵律把控。不过,有一点,如果把古典诗歌中“东篱”、“栅栏”、“南山” 等被象征的“空间”当成是一种“体式”的话,我们就要警惕其“古典的指向”, 千万不可用之后将“现代的指向”掏空,使之深陷古意而出不来,所以,用古典被象征过的“空间物象”,只有改变其言说方式,才能达到“穿越”的效果:比如我早期的一首小诗《夜》的一节:“情人向西我不相信/很多柵栏都是古典的伤痕/我出发到最流水的地方”。它不一定是好诗,但它能说明被古典诗用过的“柵栏”,究竟诗歌创作者是回到“柵栏”的情景中沉缅一番,还是“跳”出来,拿“柵栏”为现代所用,回避那个柵栏的“特定空间”所导致的意义阻隔,巧用栅栏的“弥漫性”进行意义重组,所以才有“出发到最流水的地方”的洒脱诗意。
二 诗歌写作:形式空间的特定“数”值
1 “特殊诗体”的存在是“被”动的,而不是“主”动
在我看来,“特殊诗体”大多都不是现代诗人刻意所为的,尽管我不否认现代诗坛有让人拍案叫绝的、只以二行、三行作节或单首诗的个案存在。其实,诗歌写作是一种很智性,很知性的“精神劳作”,诗歌很讲究“第一推动力”,即诗写的缘起是经验的“唤醒”,还是某个很有磁性的“词语”的撩拨,是一次突如其来的莫名昭示,还是对某个感兴趣物象的“精神掘进”……林林总总的“第一推动力”告诉我们,任何的诗节存在都是“被动”的,而不是“主动”的,就象是一场径赛,你的气力、耐力、勇力决定你“跑”出的数值,在你的所能之处,一定也是你最精彩之处, 反之亦然,写诗也是这样,当你的经验、感悟、发现、精进等所到之处、所能之处一定是你“最好的精神表征”,至于,你需要多少行(特定空间)来承载,这只有以你的“精神舒坦”和“精神饱和”为尺度。就拿汤养宗的著名的二行诗《父亲与草》来说, “我父亲说草是除不完的。他在地里锄了一辈子草/他死后,草又在他坟头长了出来。”在我看来,这绝对不是他刻意而为之的结果。其实,汤养宗写这首的“第一推动力”,就是许许多多关于父亲影像“芒点”的突现。正是:草为本, 草为父; 草为命,草为心,这样的二律回环就是人的一生,在此,诗人再不需要大篇幅、 大铺排、大叙事、大时空来完成对父亲的“再造”与“再现”,而是用这,看似“常态”的除草与长草,来“回顾”父亲的一生,乃至生死的“造化”。的确,诗歌写作就是这样奇妙,它总有一种莫名的“第一推动力”让你在精神旅途或迂回,或顿悟,或灵机,或得道……而诗歌的可能空间也随之展开。
2 诗歌“可能空间”的“象形容量”和“意指容量”
诗歌有别于其他文体的最大特性就在于诗歌所具有的“可能空间”,这个“可能空间”既有汉字自身的“象形容量”,也有诗人借力汉字的“意指容量”,我一向认为,诗歌比起任何文体更需要“空间”(灵府),而这个空间的存在与否取决于“可感”的宽度和长度,从文论而言,可感的空间,其实就是“思考”的“外延”,所谓思则远、远则空便是这理。诗歌语言之所以要有“可感”的底线,说的就是诗歌所能“唤起”的可能空间,这个可能空间是连绵的、持续的、弥漫的、牵引的“玄想地”: 比如,我早期的作品《黄昏》里的一节:“割开橙黄色的余晖/底下有昨天的风/两匹飞马拖着岁月/时间分明在流”。在这一节里,时空交错,大化合一;天上人间, 似水流年。一幅“天地皆我心,心随天地行”的画卷。从这个诗例不难看出,诗歌的空间意象,讲的就是画境,就是要让欣赏者在“品读”诗句的第一味中有着“唤起”(吊味口)的可能,进而,入乎其中,任我遨游;所思所得,尽在其中。这才是诗歌由空间意象所带来的无穷魅力。
三 诗歌写作:寻找“生态空间”的“期许值”
1 物质文化生态是不可再生的
首先,我所理解的文化生态应该是一种自觉的、持续的、原生的、参差的、多样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所显露的美好的姿态或生动的意态,它远离强制的、短暂的、人为的、化一的、整齐的“大一统”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在这个基点上,我所需要的当下文化生态肯定是千百年流传下来的、融入到百姓生活中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从物质文化生态来说,它具有不可再生性,许多历史文化遗产一旦毁损, 传统风格一旦变异,人居环境一旦破坏,将是人类文明的损失,物质文化生态, 能为诗人融入历史,穿越古今提供更为开阔的“可能空间”;从精神文化生态来说,比如,上世纪50年代起的舆论一律,只许信仰不准思考,封闭锁国,杜绝世界信息,精神生活的清教徒化等等,导致了10年灾难的文化沙化。对诗人而言,精神文化生态的沙化,其恶果无疑是一种扼杀。最让人揪心的是对精神文化生态的污染和破坏往往是隐性的,它对社会精神的腐蚀、国民素质的凌夷,乃至对人性的残害,往往不会在短时期内显示其危害,那只有用理性鉴别才能察知。所以,我所期待的文化生态是一种自觉的、持续的、原生的、参差的、多样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正如诗人于坚曾经说过的“像上帝一样的思考,象市民一样生活”应该最能体现当下诗人对文化生态的“期许值”。
2 诗歌的“批评空间”是双向并进的思维过程
我一向把“评”的本身也当成一种“艺品”,更重要的是“人学”,读诗,就象读一个人,你必然要去做种种揣摩的“侵入”,所以,我不喜欢所谓“学院式”的评述, 我的点评爱“兴致所来”,不爱“套路”,故容易让人在另一个“实用”的维度觉得“玄”,这可能也是我的缺点,反之也是我的优点。我在多种场合说过,评诗就象是对人的一次“窥探”或者就算是“算一卦”也行,如果评对了,进到作品里去了, 能说出写作者的用意,或从另一个侧面为写作者点亮了另一盏灯,你就会喜出望外, 有一种成就感,难道不是吗?其实千万不要把评诗过程中的“评”与“读”割开,因为它是双向并进的“思维过程”,“读”是用心去“理顺”,“评”是“顺理”成文,它是一个过程的两极,不存在谁重谁轻的问题,王国维《人间词话》说得好:“入乎其内, 出乎其外”。我以为,入(读)不了其“内”,焉能出(评)乎其外,所以,只要你懂得“读”已是在暗中评判了。所以,我一向认为,评者首先要把自己也当成是“写者”才有可能在角色置换过程中获取零距离的“测评”,否则,居高临下,引经据典, 永远只能干“敲边鼓”的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