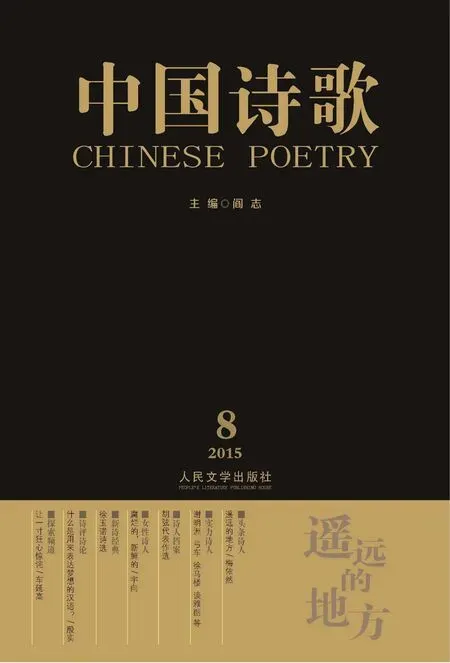诗学观点
□李羚瑞/辑
诗学观点
□李羚瑞/辑
●孙德喜认为,面对当下诗歌的不景气,有人提出建立新诗的形式规范的设想,试图通过具体的诗歌形式规范来约束诗歌,从而让诗歌在形式上像诗歌的样子,叶橹并不赞同这样的主张。他认为诗歌的本质不在具体的形式,而在其中蕴涵的诗质,而规范不仅不能解决诗歌的不景气的问题,而且还可能因其“限制”而形成对诗歌创作的“约束”,进而“会成为对创造性和可能性的遏制”,但这并不是说叶橹否定诗歌的形式。他提出了诗歌的形式感问题,认为诗歌不应该有统一的形式规范,而应该根据各自抒情感和表达思想的需要,进而建立起相应的诗歌形式,因而诗歌的形式感所体现的就是形式上的自由。
(《论叶橹的诗歌批评》,《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期)
●方长安认为,从前有人将译诗视为自己的白话新诗作品,主要原因一是以诗歌是不能翻译的观念为认识前提,将翻译看成创作,也就是高度肯定译者的创造性劳动;二是以外国诗歌尤其是西洋诗歌支持中国的白话新诗运动,赋予中国的诗歌革命和白话新诗创作以世界潮流性、进步性,也就是赋予中国白话新诗存在的合法性。但实际上这暗含着中国白话新诗的不自信,其隐患就是肯定那时中国诗歌一味地去民族化倾向,忘记自己还有几千年悠久的诗歌传统,肯定那时诗坛盲目地向国外诗歌学习的倾向,其结果是使白话新诗逐渐失去民族诗歌个性,失去民族文化神韵。
(
《对新诗建构与发展问题的思考——〈新诗年选(一九一九年)〉的现代诗学立场与诗歌史价值》,《文学评论》,2015年第2期)
●杨林认为,诗歌要有诗性,才能成其为诗歌,而诗性的实现,最为重要的就是意象经营的独一无二。诗性意味的深邃性、哲理性与本质性,是通过独特的意象来构建意境,通过这意境来引领读者进入思考,使得个体生命的个性体验上升到共性共鸣的艺术审美境界。没有独一无二的意象构建,就缺乏共性共鸣的真实性,就缺乏个性感受的感染力。从蚂蚁这一独一无二的意象经营中,感受到蚂蚁与诗人独特个体的卑贱与坚忍,感悟到人的卑微的生命意义,体验到诗歌诗性意味的完美的艺术享受。
(《杨林读诗之特朗斯特罗姆与南鸥》,《湖南文艺》,2015年4月号)
●张宇刚认为,马永平的诗朴素,平实,沉稳,举重若轻,字里行间总有一种明朗的忧伤和柔韧的坚强;其追怀往昔,摹写事象,往往不拘形迹,而自能抵达内心,彰显精神,于时代层云之上,勾勒出一颗不屈灵魂的高蹈。他的诗歌观察细致,手法地道,摒弃了隐喻和象征,每以白描行事,下笔如同在说话,如同在生活;在一派不疾不徐中,必备的修辞、技巧亦巧焉隐于其间,情怀沛然——他的诗分明超越了修辞、技巧,超越了俗世的物象,不尚奢华,直抵本体。他的诗苦涩而轻松,无招胜有招,表象的简单与内里的繁复,达成奇异的张力,彰显对人生、对命运、对宇宙的本真性体悟。
(《不像诗人的诗人,及其诗》,《文学自由谈》,2015年第2期)
●王攸欣认为,中国诗歌具有强大的抒情诗传统,形成了丰富多样的风格和技巧。情感表达的微妙、蕴藉,意境营构的超旷、悠远,意象选择的自然、恰切,语言运用的准确、凝练,音律琢磨的细密、谨严,章法构思的完整、流转,是历代名作的主流特征,其典雅含蓄、空灵深切的审美风格非西方诗所能媲美。卞之琳在自己的诗中承接并创新了这一传统,吸纳了西方最新的诗学经验,在诗中融入、化入中国传统,显露了中国精神、中国风度。卞之琳的诗真正稳固建立了中国新诗的审美基质。
(《卞之琳诗作的文化-诗学阐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5年第3期)
●杨匡汉认为,现代诗似乎不必过多考虑“新诗”与“旧诗”。双水分流,双峰对看,朝着“现代”的同一方向,在高处汇聚,有何不可、不好?我们曾经以“启蒙”与“救亡”之变奏为背景讨论现代新诗的“合法性”,并予以历史化。但同时对另一个“活性因子”——抒情传统及其在新变中的渗透,不应忽略不计。在古典传统文化落幕的“诗界革命”时代,有没有古典诗词的现代生产?有没有以旧体诗词为骨干的抒情传统对新诗“历史化”的顽强抗拒?有没有古典所展示的抒情主体性在现代情境下书写的脉络和意义?答案是肯定的。所以我们要重视中西诗歌观点的交集和差异,新旧诗歌理念的越界潜能,歧异与故常的流动性和相对性,守成与新变在同一位诗人身上多重暧昧的呈现。我们也正是从“新”“旧”互渗互动中,把握现代诗暗涌的脉搏。
(《堂郡絮语》,《诗选刊》,2015年4月号)
●罗振亚认为,新世纪文坛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走出边缘化低谷的诗歌境遇逐渐好转。大多数诗歌自觉回归诗歌本体,致力于各种艺术可能性的挖掘和打造,提升着诗歌的品位,尤其是“及物”策略的明智选择,将诗歌和现实之间的关系调整到了相对理想的状态。诗人们不完全拒斥超验、永恒的情思元素,可是已注意讲究“及物”对象选取的稳妥、恰切,在典型、多维的日常处境和经验的有效敞开中,更接地气地建构诗歌的形象美学,与当代生活的联系更为广泛。一些诗人没将现实因子直接搬入诗中,进行黏滞泥实的恢复与呈现,而是依靠能动的主体精神和象征思维等艺术手段的支撑,在呈象过程中充满灵性,获得一定的精神提升,甚至有时还能提供出某种新的精神向度。
(《“及物”与当下诗歌的境遇》,《光明日报》,2015年4月13日)
●蒋登科认为,诗学是以理解为基础的学科。在诗学研究中,最根本的是对诗人的精神世界以及为了表达这种世界而采取的艺术方式的研究。在中国传统诗学中,大多数诗论都是优秀诗人通过自己的创作经验总结出来的,具有明显的感悟性、经验性特征,甚至是以诗的方式写出的诗话。在现代诗歌研究越来越走向学术化、技术化的时候,梁平以一个诗人的身份,从经验、感悟的角度谈诗,而且是张扬一种符合诗歌历史与现状的“正”的观念,对于诗歌创作、研究都提出了很多具有价值的观点,这对于矫正诗学研究中出现的越来越离开诗歌本身的那些现象,对于人们全面、准确地理解诗之本质、作用等,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价值。
(《诗人的诗之思》,《人民日报》,2015年5月5日)
●于坚认为,真正好的诗就像塔一样,塔基广大,语言直接、简单,让很多人有感觉,被打动,可以进入,但诗真正的核心,它要表达的最隐秘的部分,是一层层往上升的,读者经验的深度不同,对诗的领悟也就不同。不是说只有作者才有精神性的东西,读者只是像学生那样一一接受。诗是对无的召唤,如果读者心中对“无”毫无感悟,满脑袋都是如何占有,他就无法进入诗。现在一个不太好的现象是,一个安静的诗人一旦被网络注意,被媒体发现,马上就会变成新秀,喧嚣起来,浮躁起来。在微博微信带来诗歌传播的“百花齐放”的时候,如何树立和建立写诗的“金字塔”,恐怕是我们应该关注的问题。诗并不像想象的那么平易近人,这不是对诗的要求,是对世故的要求。
(《真正好的诗就像塔一样》,《人民日报》,2015年5月5日)
●王志清认为,当下散文诗创作的同质化问题突出,经典缺席,重要原因出在语言上。换言之,当下散文诗突出的弊端是:语言僵化,缺乏体温,思想稀释,缺乏鲜活生动的个性和锐气。散文诗的语言应该是诗性的。何谓诗性?即尽可能弱化其写实性,不以再现为主,而强化其表现性,激增其情感含量与美感因素。或言之,散文诗的语言难就难在要不断地解决再现和表现之间的矛盾。对于散文诗作家来说,作品中的“语言”绝非一般性意义的“词汇”。散文诗的语言,应该已是一种意义,一种形象,一种诗人的灵感,一种诗性的活性载体,而具有诗性所特有的饱满弹性,发生形态的变异与喻指的暗示,因此也具有真正的诗才有的丰富性和不确定性。
(《散文诗:语言决定命运》,《文学报》,2015年4月30日)
●任白认为,祭司也好牧师也罢,诗人都被看成是沟通被日常生活所蒙蔽的深邃世界的某种灵媒。他有异于常人的感知能力,能够先于我们的哭泣看到泪水之海,能够透过墙上巨大的阴影察觉到身后无名灾难的咻咻鼻息。他是此岸的他者,甚至也是彼岸的他者,因为生活在别处,灵魂永远不可能在现实的怀中安睡。诗人不可或缺,或者说诗歌不可或缺,再或者说我们对心爱之物的爱不可或缺。特别是在今天这个“贫困到以至于无法感知其自身的贫困”的年代,我们被自己和他人的恐惧与狂热一起驱赶着,不知所终。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有人失声痛哭,有人大声呼喊,或者,干脆转过身去,用他落寞的背影来发布一个艰难的选择和狂妄的判决。
(《为什么——〈耳语〉后记》,《作家》,2015年第4期)
●叶橹认为,诗歌的抒情性日渐式微而智性因素却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渗透其间,或许正是社会发展过程中人们的思维和感情方式受到潜移默化的表现。在当下的社会,人们似乎很难找回曾经有过的那种纯情和稚性,因为弥漫在我们生活周围的气氛已然被杂色的物质侵入和浸染,所以我们不能指望诗人像生活在真空中那样作纯情的歌唱。但是,身处当下物欲横流人情淡薄之现实而许多诗人已然孜孜以求地力图表现人性中的真情,正是诗人作为社会良知的载体的一种现身。所以诗歌创作中不管是主情还是主智的作品,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
(《主情乎?主智乎?》,《扬子江》,2015年第2期)
●谭五昌认为,吉狄马加成功地超越了其特定的“彝族诗人身份”和“彝人意识”的命名与表达,诗人已从本土化、民族化立场的诗歌书写与姿态固守中突入到更为开阔的世界性精神文化视野,表达着更为深刻而普遍性的忧患意识和人类情怀。在当下的全球化语境中,吉狄马加并未盲目地以“世界性”诗人的身份自居,很多时候他反而持守自身的民族诗人文化身份,这使得他的写作富有根性,而不飘在虚无、时尚的文化浮尘中,因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世界性写作”其实是可疑的。作为一个彝族人,吉狄马加在现代文明和传统民族文化冲突中,在人类的精神困境和灵魂阵痛中几乎别无选择地渴望突围。这是一种精神的宿命。
(《雪豹的诗性呼告,或关于自然环境的生存忧思录——对吉狄马加近作〈我,雪豹……〉的一种解读》,《文艺争鸣》,2015年4月号)
●耿林莽认为,想象力是从生活中来,是诗人在现实人生的体验中,长期积累而得,是他创作仓库中的“库存”。生活经验越丰富,想象力驰骋的空间就越广阔。就我的创作实践而言,局限于一时一事的具体之实构思的作品很少,而且往往效果欠佳,从宏观视野、广阔空间汲取素材,调动细节,展开思考,浮想联翩的构思方式,常能取得更大的自由,获得丰富的构思资源。所以,散文诗不是再现,也不是表现,而是创造,是艺术的创造、诗美意境的创造:“美而幻”,便是她的“完成式”。
(《散文诗,美而幻》,《散文诗》,2015年4月上半月刊)
●陈仲义认为,好诗是用生命、泪水、疼痛去结晶的。生命体验的本真、自然质朴,经过语感的催化,外化为纸上的分行建筑。余秀华的一些诗作具备好诗的基本质素,具备迅速进入“召唤结构”的响应条件(只差导火线)。她的特殊遭际缩小文本生成与接受的落差,她的传达方式容易让“性情美学”或“情灵美学”(自撰),迅速抵达接受心理中的“动容”部位。悄然心动或怦然心动,所带来的温暖、澄明、抚慰、照亮,是好诗接受的一般“体征”。正是余秀华诗歌里的基本盘面,呈现出诗歌基本品质与质素,酿成的总体“感动”效应,符合接受的审美尺度与需求,她最终才得以自己的先天“短板”,反倒收获了一场诗歌的“嘉年华”。
(《好诗的接受品质及其“附加值”——“余热”触探》,《诗歌月刊》,2015年第4期)
●杨庆祥认为,诗歌,尤其是现代主义诗歌,必须有“我”,这已经成了一种陈规式的设定。但正如阿兰·巴丢所尖锐质疑的,如果割裂了“我”和“我们”的有机关系,这个“我”还有创造性吗?他真的能代表“我们”吗?这也许是现代主义诗歌面临的最大的合法化危机。而要破除这个危机,就必须重新理解“我”和“我们”之间的关系,不能因为“我们”不够理想或者“我们”曾经以各种主义之名对“我”实施了压迫,就不承认这个“我们”的存在或者彻底割裂这两者的联系,从而让现代主义诗歌写作变成一个内循环的,拥有虚假的个人主体和语言能指的游戏。这是一种写作和思考上的惰性,这种惰性的蔓延,让我们当下的诗歌写作没有力量。
(《重启一种“对话式”的诗歌写作》,《诗刊》,2015年4月上半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