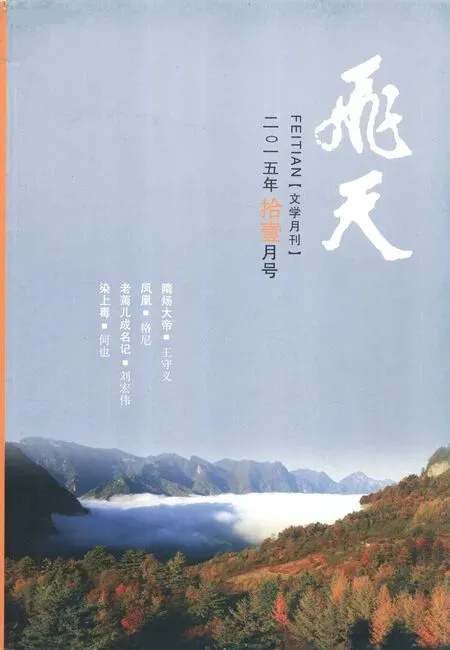丝路文学的民族审美
贺 颖
丝绸之路作为世界语境内具有深刻意义的历史故道,其间更为人所关注的,是它同时更是一条具有深厚美学意义的人类文明走廊。古老的丝路文明可以称为中国多民族文化的整体故园与乡愁,其间蕴涵着各个民族的生活视域与精神核心。自然环境是我们生命的栖息地,同时对人类的精神禀赋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艺术的呈现源自于人的精神品格的律动,自然对人的沐浴便在此鲜明地展现出来。环境的卓绝、征途的漫漫寂寥,对丝路之上的每个人都是极致的精神拷问,更是对意志与体魄的考量,也可以说恰恰因为如此,才形成了丝路文化的多元共生、自强自信、热烈殊异的宏阔格局,众多的少数民族,如古之北狄、匈奴、塞人、月氏、乌孙、鲜卑、柔然、突厥、吐蕃、回纥、契丹、蒙古等等,今天仍有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蒙古族、回族、塔吉克族、塔塔尔族、乌孜别克族、俄罗斯族、达斡尔族、满族、锡伯族等等,穿梭往来于东西方文明交汇激荡的神秘地带,丰富而差异的文化在这里交流、碰撞、融合,结构出了丝路之上繁复深远文明的况味,以及绚艳华彩的文学宝藏。
这些宝藏有别于生活中的物质珍品,极力深藏于世界的隐秘角落,这些文学艺术的宝藏,往往有着丰富多重的美学价值,却又从来素朴如丝路之上达达的马蹄,如跫跫足音,如依依驼铃声,或如抬头可见的星群,萦绕于丝路上的生活与生命之间。
像许多民族都有自己的英雄史诗一样,诞生于公元8世纪左右的《乌古斯传》是维吾尔族史诗中最著名的一部。《乌古斯传》又被维族人民习惯地称为《乌古斯汗传说》,最初在民间口头流传,公元13世纪写成回鹘文本,可以说是丝路文学的早期典范。长诗反映了古代维吾尔人的生活与斗争,他们古老的宗教信仰、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神奇的乌古斯汗。降生后即会说话,不久便能行走,他以生肉和酒为食,牧马、打猎为业,曾杀死独角兽为民除害,即汗位后征战四方。史诗的内容是从氏族时代到封建汗国的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交代了一个民族的英雄神为那片土地带来的神秘与神奇,同时也淋漓尽致地反映出当时维吾尔人的生产方式、生活习俗和思想观念。更为可贵的是,长诗中引用了很多民间传说,引出一些部落的渊源,这本身就是丝路文学最宝贵的特质之一。据说后来的史诗有了更加珍贵的手抄本,并部分改用了散文文体,留下了部分韵文,在阅读上愈加有了新的艺术魅力。史诗以叙事为主,却不乏意蕴表达上的含蓄深刻,同时诗态奇绝骄纵,诗境雄浑壮阔,文体缜密,形象集中生动,且艺术表现手法多种多样,现实的描述与富于神秘色彩的神话传说相互交织浑然一体,语言精准而极具力量,韵律与节奏鲜明和谐,呈现出绝佳的艺术特质,不愧为史诗之作。事实上这部英雄史诗不但在维吾尔族中流传广泛,而且在汉族中也难能可贵地留有痕迹。如在张闻笙的武侠小说《风雪载英雄》中就有这样的描述:“戏台上正演《乌古斯传》的优伶戏。戏子都戴面具饰扮人物。此戏是说回鹘人祖先乌古斯可汗领着几个王子率兵西征,由一只苍狼带路……”
由此可见,丝路文化精神对各民族文化的影响,是一种长期的碰撞与冲突的结果,各民族中最本质、最独特的文化特质在碰撞中可能会被不断强化,而另一方面也有一些记忆与印痕,在反复不断的冲撞中被消磨殆尽,渐渐弥散于历史的风烟之中。或者可以说,丝路文化的诞生,是一次文化上的洗礼与考量。事实也已经证明,唯有真实准确地反映民族精神中最独有、最震撼的艺术作品,才能历经这样的拷问,而一再获得生命与灵魂的双重新生,获得普世的经典传承。令人倍感欣慰的是,一大批富有鲜明的民族特色、民族气息、民俗风情的多民族文学作品历经了拷问,并最终成为丝路文学史上重要的华彩篇章。
地理位置的独特,沿途自然与人文环境的繁复,形成了无尽广博与深邃的文化背景,同时,这些文化背景也成为了丝路上特有的文化精神,并与各民族之间形成一种神秘的互融,相互影响也相互激荡,并一路自遥远的历史逶迤而来。著名作家张贤亮因《绿化树》、《灵与肉》等作品,为中外文坛所熟知,但他的另一篇较少为大家所提及的作品《肖尔布拉克》同样是一篇深具意蕴的作品,后来被搬上银幕,才为更多人所熟知。小说以新疆苍茫的天山公路为背景语境,讲述了一个只身闯荡到西域的内地青年,在新疆的情感、前程、家庭生活等一系列命运轨迹。这部作品虽然大部分在讲述着关于爱情的丝丝缕缕,但却不同于一般的情话或个体的情感罗曼史,小说向人们呈现的是一个为了生活,常年奔行于路上的普通人的欢喜悲愁,这样的奔行,这样的喜忧,今天看来,完全就是一种现代的丝路人生。当马蹄与驼铃换成了汽笛声声,当和平的岁月替代了远年的战乱,而永远不变的是丝路之上为生活而奔行的人们对爱的向往,对灵魂中善和美的光亮,以及对今天的珍惜,对明天的一切终会变得美好的朴素而感人的信念与探寻。
这条古老神秘的路途之上,因其关于民俗、农林、节庆、军事、屯垦、宗教等方面的特殊文化语境,从而骄傲地诞生出了炫彩的散文、诗歌、曲艺、戏剧、小说、行旅文学、民间文艺等丰富的艺术形式,而生活在丝路沿途的各个民族,在丝路特有的精神品格的浸润下,其作品必然形成同样特有的开放包容、自强不息、激越苍古的文化质地与民族艺术审美,从这些作品中,我们更多体会到的,就是热烈殊异、炽真奔放的民族气息,真切鲜活、深沉激荡而震撼人心。
回族作家张承志的《心灵史》便是这样一部每每读过,总会在心中涌动巨浪的作品。这是一次建构在信仰之上的心灵远征,是一个笃信神明者与世界的对抗或交汇。作者的心魂背后,是一条葳蕤复悲壮的生命线,一种与神明紧紧相融的精神引人敬意丛生,其间浑厚深酽的哲思洞见,引人叹美。诚然,一切哲思必定是信仰的必然,而一切信仰的指向也必定是哲思,这该是哲学与宗教最为隐秘的思辩,也更像一个问题的提出,却几乎没人能给出确切答案。唯一可以确定的,是二者皆关乎心灵。
而心灵的意义指向,从来就是生命的终极价值。也许这便是作者心中关于《心灵史》的一丝视角吧。我们可以从作品中毫不费力地感受到那种深沉炽烈的信仰,纯粹而无畏。无论我们是否有自己的信仰,都不妨碍我们在作品中感受来自生命、灵魂与信仰及命运深处的巨大张力,仿佛警醒,仿佛历险,仿佛启蒙。
有如盲目无知的笃信必会导致轻信,深刻清醒的认知必会指向信仰,此刻的信仰,显然是一条通向安谧宁静的必经之路。而这条路,想来也该是丝路文明的一种隐喻,或者说是丝路文明从来就存在的一种历史模式,这种模式的形成是潜意识的,甚至连作者自己、连历史自己亦未曾意识到,但神奇的是,这样的模式一经被阐释而出,就如同被洗去尘埃的圣物,在天地间渐渐舒朗,明洁、神性而完美。
“长久以来,我匹马单枪闯过一阵又一阵。我渐渐感到一种奇特的感情,一种渴望诡异、渴望巨大的收容的感情。”这是一个生命个体在苍茫的天地间无法规避的悲壮,而这又何尝不是天下众生的茫然?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曾将人类孤单的宿命揭示得刻骨而无望,孤单星球的孤单生命们,无论老守田园或于路上不倦奔行,究竟有什么可以予我们以困顿中的些许慰藉,除了心灵的信仰。在《心灵史》前言中,作者这样说:“它们深深地吸引着我,强拉着我,诱惑着我。那最初的时刻降临时我毫无悟性——我并没有察觉:万能的造物之主为我人生转折安排的瞬间,已经实现了。我沉入了这片海。我变成了他们之中的一个。”我想这句话不只表明了作者自身对信仰的感性呈现与智性表达,同时几乎是每个读者所能感受到的史诗般的苍古与悠长。这样有别于丝路文明中民歌民谣的瑰美、故事传说的神秘的百转千回、边塞诗文的粗犷激越,唯独以宗教文学而呈现的渡人渡己的灵魂审美作品,该是丝路文学语境考量下的多民族文学更为厚重的文化上的斑斓多彩,文明上的奇幻与多元。
土地养育肉身,文化养育精神。命运的浑厚壮美,生命的深远神秘,信仰的神性与慈悲,给了作者足够浓烈的心灵体验,更为作者提供了足够纯熟的艺术审美力量,作者的生命与灵魂因此生长出有别于自己既有精神质地的纷繁认知,书写出了丝路文学的传世之作。
一部心灵史,此刻就是一条命运的长路,路的一端是永不模糊的过往,而另一端则是无限伸长的未知。我们仿佛再次听到丝路古道上奔行的足音,才深度了解了为什么说时间的回返有时就是美学的回归,正是这些以精神真理为终极目的的文学作品,让我们一次次聆听着丝路之上达达的马蹄,琴瑟猎猎,以及风中吟咏,月下悲欢。
张承志的另一篇佳作《黑骏马》,其间浓郁的草原风情,与厚重的历史意蕴所交互而散发出来的现实主义美学内涵,是对作者集文学、历史考古、绘画于一身的学者精神质地的深度彰显。文中有这样一段话:“我渐渐感到,那些过于激昂和辽远的尾音,那此世难逢的感伤,那古朴的悲剧故事;还有,那深沉而挚切的爱情,都不过是一些倚托或框架。或者说,都只是那灵性赖以音乐化的色彩和调子,而那古歌内在的真正灵魂却要隐蔽得多,复杂得多。就是它,世世代代地给我们的祖先和我们以铭心的感受,却又永远不让我们有彻底体味它的可能。”也许正是对这样真正灵魂的渴念与追索,作者找到了书写现实与理想的最具人文属性的契合点。
小说以辽阔壮美的草原为背景,以一首古老民歌《黑骏马》为主线,描写了蒙古族青年白音宝力格的成长历程,以及他和索米娅的爱情悲剧。小说以风拂草地的舒缓节奏、长调般忧伤的笔触,再现了草原民族的风情,呈现了草原人民质朴善良的精神伦理观。
巧合的是,这依然是一个在路上的故事,主人公不断的出走与返回,仿佛是对丝路文学的再一次神秘的暗合。作者以情感的脉络为主线,为读者奉上的是乌珠穆沁草原上的自然万物、民族风情、文化民俗等璀璨如星辰的文化内涵;通过炽烈如焰火的情感与生活,展示的是草原人民的浑厚情愫。作者以深沉的敬意,于自己鲜活的个人经验中获取了文学审美的可能,使作品因而成个书写个体命运的有效途径,而作品的涵蕴亦因此有了更具深意的文化潜意识。主人公的生命历程,仿佛是一种与命运的执拗抗争、有关灵魂的遗忘与记忆、有关天地的热烈与悲凉,使作品由此抵达一种陌生的美学秘境,经由对一种宏阔文明之旅展开刻骨地观想,从而对世界、对生命与心灵、对爱与善,建立了一种真切诚挚的美学诉求。
“当我的长调和全部音乐终于悄然逝去的一霎间,我滚鞍下马,猛的把身体扑进青青的茂密草丛之中。我悄悄亲吻着这苦涩的草地,亲吻着这片留下了我和索米娅的斑斑足迹和炽热爱情,这出现过我永志不忘的美丽朝霞和伸展着我的亲人们生路的大草原。我悄悄地哭了,就像古歌中那个骑着黑骏马的牧人一样。”主人公将身体扑进草原的刹那,他的身体与灵魂再次双双回到了故乡,倾听着草原的心跳与苍茫的长调,主人公找到了自己永恒的乡愁。
正如丝路文明也是丝路文学的灵魂故乡一样,各民族人民对丝路之上的天地风物、悲喜欢爱、满怀敬意与感恩,呈现出挚烈的审视与颂唱,以及如《黑骏马》的主人公将身魂扑进草原般的恒远乡愁。如此结构而出的作品或深沉绚艳、炽真苍茫,或神秘炽烈,既是自我心神的交锋,也仿佛是这片神秘地带之上,人与天地间某种异样的和解。此刻的个体的生命,亦完成了精神的在场,以及对一种文明的敬畏与抵达、走近、聆听、审视与探索。相信这些勇于周旋新的精神结构的勇气,必定会创作出满足新的美学标准的艺术作品,而这样的作品必将以一种返魅的高贵,唤醒一个时代的祛魅与荒寒。
沿着神秘的丝绸之路,各民族人民以丰富多彩的语言,借由异彩纷呈的民族特质,完成着不同时期的文学进化与演变。于是有了今天“丝路文学”新的文学地理研究。历史总在以惊人的相似,暗合着某种令人惊心的神秘,正如当初人们对丝绸之路的命名很快得到世界的公认一般,今天“丝路文学”一经提出,同样获得了高度的认可与整齐的认知,如此地耐人寻味而意蕴深长。这应该是对一种文学内在意义指向的深度理解,对一种特定文化语境内涵及界定的自然贯通,既仿佛某种意义的启蒙,又分明对历史文明之光的回望,历史与现代的交汇延伸,形成一幅别具意味的文学景致。丝路文学的诞生与发展,源于神秘古老的丝绸之路,各民族文学在历史向今天的不息激荡之中,顽强地葆有着丝路文明的刻骨印记,执著无畏地诠释着这片遥远地带的乡愁,因此,以丝路文化的发展历程探问丝路文学的历史、此在与未来,于丝路文学语境下考量多民族文学创作的艺术审美,不单单是对少数民族文学史的追索与阐发,同时更是对多民族文学批评与精神指向的伦理吁求及价值观照。这不是今人对丝路文化的一厢情愿,而恰恰是古老人类文明赋予我们的关于美学回返的人文使命,是灵魂对人类整体精神结构的恒久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