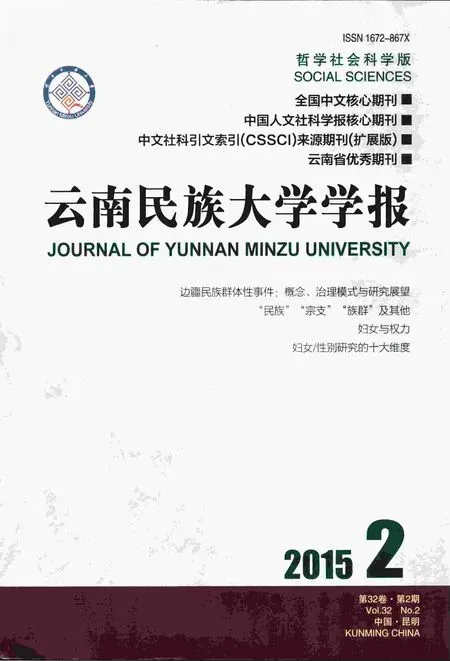语言传播的本质规律探究
潘巍巍
(北京联合大学师范学院,北京100011;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教育研究中心,北京100089)
语言传播是人类语言发展史中的普遍现象,是语言经过长期扩散的结果。语言在一个地区产生以后,随着使用该语言人群的迁移而扩散,于是该语言分布区逐步扩大。语言传播所带来的后果,或是新来的语言代替旧的语言;或是旧的语言退到边远地区;或是产生语言的新分化,出现新的方言或新的语言等。因此,语言传播反映了语言的发展与变化,其现状分布体现了各种自然要素与社会要素之间的关系。那么各个历史时期和不同地区的语言传播在本质上有什么共同之处?语言传播具有哪些特性?相互交叉的心理现象,社会现象和语言现象在语言传播中的作用如何?语言传播的途径是否有什么规律?本文将对以上问题逐一探讨。
一、语言传播的动态本质
语言传播离不开传播学,传播的本质是传播活动的根本性质,是指传播活动组成要素之间的内在的、稳定的联系,它是由传播活动的本身所具有的特殊矛盾所决定的。①邵培仁:《传播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年版。那么何为语言的传播活动?Robert Cooper 在研究语言政策时,认为语言传播是“一个交际网络为了实现特定的交际功能而采用某种语言或语言变体,随着时间的推移,该网络的规模得以扩大。”②Cooper,Robert L.A. ,Framework for the Study of Language Spread. In R.L.Cooper eds. Language Spread:Studies in diffusion and social change. Bloomington,I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82.可见语言传播本质上是一个交际网络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扩大的行为活动。从Robert Cooper (1982)的定义看,笔者认为语言传播的本质可以从形式、功能以及渗透三个方面来深入探究。
首先,形式即某种语言或语言的变体,这主要由所传播语言本身的多样性,以及传播语言和当地语言之间的结构相似度引起的。语言在各自的传播过程中相互接触,随着语言之间的接触关系越密切,相互的影响就越深刻,最终导致语言各变体的内部结构发生变化,出现语言的借用、双语现象、融合以及混合等现象。而语言形式的差异本身就是语言传播中的因变量,从中可以归纳出语言传播活动的本质特征。
(1)复合性。它指语言在扩散接触中,一种语言吸收其它语言成分,形成复合语言。语言的借用现象充分体现了这一点,因为不同的语言一经接触会互相影响,导致语言之间互相吸收外来成分出现变体,一般从语言的基本单位—词语开始,而且借用过来的词必须受到它从属的语音系统和语法系统的制约。例如早在十六和十七世纪时,大量的拉丁语、法语和其他语言被借入英语使用;中国汉代以后从印度借来大量的佛教用语,如罗汉、佛、和尚、僧等。
(2)渐变性。语言传播过程中,不会有现存语言的突然死亡和新语言的突然产生,而是经过新质的要素的逐渐积累,也要经过旧质要素的逐渐衰亡来实现的。①简·爱切生:《语言的变化:进步还是退化?》,北京:语文出版社,1997 年版,第253 页。从双语现象到语言融合的过程就充分体现了语言传播的渐变性。语言融合的过程大体上是先出现双重语言现象,最后导致一种语言排挤、替代另一种语言而完成语言的统一。例如,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在拉丁美洲,它们一方面通过过渡型双语政策,另一方面殖民、屠杀、驱赶等办法减少印第安人,缩小其居住范围,扩大殖民者人数和活动范围以扩大其语言分布区,最后致使大量印第安民族语言的濒临死亡。
(3)不稳定性。语言在扩散时,与其他语言接触往往出现一种“混合”语言,即两种语言“拼凑”在一起。有的混合语言往往交际功能有限,生命力不长,体现了语言传播的不稳定性。例如洋泾浜语(皮钦语pidgin),通常由一个上层语言和多个下层语言拼凑,为适应当地人与外族人的日常交际而临时产生的一种辅助性的交际工具,没有文法。一旦最初交际的理由减弱或消失,或一个社会集团成员学到另一个社会集团的语言时,它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稳定性差。大部分洋泾浜语是以欧洲语言为基础的,如英语、法语、西班牙语、荷兰语和葡萄牙语等,这反映了殖民主义的历史,19 世纪末上海的洋泾浜英语如今已退出历史舞台。
(4)演化性。语言传播时通常是由简单形式演化为复杂体系。混合语之一克里奥尔语(Creole)的形成就体现了语言传播的演化性。一旦有人把洋泾浜作为母语来学习和使用,就形成了克里奥尔语。多发生在由殖民劳工构成的社会或国家、地区中。由于语言不通,只能说一种洋泾浜化了的殖民者的语言,长期生活在一个社会,互相通婚,有了后代,便把这种洋泾浜作为母语来学习,并逐渐扩大词汇量,语法也逐渐规范化,从而形成克里奥尔语。例如海地以法语为基础的克里奥尔语,牙麦加以英语为基础的克里奥尔语。
其次,功能即交际功能,指语言传播的目的。在多语地区,说话者为了达到不同的目的而选择不同的语言,反映了说话者在信息交流中强调自己的社会价值和社会地位。从功能角度,语言传播的本质特征还可以表现为:
(5)竞争性。从平行关系的维度看,语言跨越地理和人种界限进行扩散,即产生语言传播的竞争性。在传播过程中,二种以上语言同时存在就会产生竞争和排它现象,主要体现在语言的集团间传播(between-group)和集团内部(within -group)传播。以英语的传播为例,最初在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英语作为集团间传播的媒介语言,主要用于移民群体与主流社会之间,移民集团内部的传播只使用母语,但如今英语跨越了集团间的传播,跻身进入移民集团内部,取代了移民者原有母语的功能,这使英语对民族语言的地位造成了威胁,很明显产生了语言的竞争和排它现象。
(6)等级性。从垂直关系的维度看,语言在社会中不同阶层之间的信息交流,特别是社会上层同普通民众之间的交流过程,关系到语言传播的等级性,具体包括社会阶层,年龄结构等因素。例如美国的一些俚语,stoned (醉鬼)、far out (先锋派人物)、heavy (小偷)。这类俚语先在下层社会使用,而后向上层社会传播。也有一些俚语有先在上层社会流行,到不再使用以后,才从下层社会中消失,都从阶层这个角度体现了语言传播的等级性。从年龄结构看, “盖了帽”的俚语30 岁以下的人中占54.8%,而在31—50 岁人中只占13.7%。可见,在青年人中占多数。这种俚语现正在向年龄较大的人中间传播。②王恩涌:《文化地理学导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 年版。
第三,渗透指既指语言扩散的方式,也可以指语言被接受的程度。从扩散方式看,语言一旦形成,总要由其起源地向外传播,达到一定的使用范围,包括人群和地区的范围,才不至于消亡,才能在使用的人群和地区中随着其生产的进步和文化的发展而不断地得到发展,这一观点主要是受Johannes Schmidt (1872)的波浪理论的影响。他认为语言特征在传播过程中相互渗透,由一个特定的语言区域向周围扩散,就像水波波浪一样向周围传播,以同心圆为同心如水波向周围扩散传播。③Johannes Schmidt,The Relationship of the Indo-European Languages. Weimar 1872.这种语言特征对临近区域的语言影响最大,而随着距离的远离影响逐渐减小。所以语言传播的本质还表现为:
(7)外延性。即语言是呈波状向外放射,语言或语言要素作为波源,它的扩散如同波一样向四周散开,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波源的波相遇后,便形成了一个新的语言现象的生长点,这些新的语言生长点发展成熟后又可能成为新的波源,逐渐扩大语言圈域,通常语言圈域都是由小到大向外延伸。
(8)层序性。由于语言是呈波状扩散,对某些地区来说就有多次重复的层序性。早期传入的古老语言和后来传入的新语言有着不同的层序性,往往新语言是在古语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差别很大。例如在我国现代七大汉语方言中,北方方言可以看成是古汉语经过数千年在广大北方地区发展起来的。其余六大方言却是北方居民在历史上不断南迁逐步形成的。显然,他们早期使用的语言与现在的六大方言相差很远。
从语言被接受程度的角度看,语言态度界定语言选择,或者说,语言选择是语言态度的反映。人们在传播一种语言时,除了要求这种语言具备应有的交际功能外,更重要的是人们对这种语言是否认可,在感情上对这种语言是否接受。所以语言传播的本质还具有选择性。
(9)选择性。积极的语言传播态度和扎实的落实措施可以加快传播速度,提高传播质量;反之则会延缓传播速度,影响传播质量。从语言传播的主、客体角度出发,有四个接受新语言的标准变项:(1)意识(awareness):传播者是否意识到某种语言的重要地位;(2)评价(evaluation):传播者是否对某一语言采取赞同或反对的态度; (3)熟练程度(proficiency):传播者是否熟练掌握一种新的语言; (4)使用(usage):传播者是否大量使用该语言①邵培仁:《传播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年版。。以新加坡为例。新加坡是一个由华人、马来人、印度人和英国人等组成的多民族、多语种的国家,官方语言的选择除了政治上的原因外(新加坡是英联邦国家,殖民时期英语是官方语言,新加坡的英语普及率高),还要权衡汉语、马来语和泰米尔与之间的语言冲突等会引发的民族问题,从语言和谐和实用主义出发,选择英语和三大民族语言同为官方语言。
二、语言传播的二维路径
语言传播与文化传播相似,它的路径大体上分为空间传播和时间传播两类。所谓空间传播,主要指语言通过操某种语言的人或集团从一地迁移到另一地,从而把这种语言带到迁居地。时间传播是一种语言传播的延续,主要通过其他媒介来进行传播。
(一)语言的空间传播
从目前世界上语言的传播格局看,语言的空间传播可分为占据式传播、蔓延式传播和变异式传播。(1)语言的占据式传播指被移民从原居地带到新居地的语言至今仍与原居地语言基本相似,仍属于同一语言系统。例如17 世纪初英国人向北美大规模的迁移就属于语言的占据式传播,它使得英语在历史上第一次远离欧洲本土,从英格兰岛到达新大陆并且在后来永久性地居住。虽然欧洲各国移民也都纷纷涌入北美洲,但由于最早以英国人为最多,他们的语言文化、生活方式和法律制度等构筑了后来美国社会的基础。可见英语这种原居住地语言的地位已经在新居住地成为一种不可剥夺的主导意识,是典型的语言占据式传播的结果。 (2)语言的蔓延式传播即移民并不以扩张为目的,占领成片的广大地区,而只是有选择地在某地定居下来,处于当地语言的包围之中。一般说来,如果两种语言互不相通,在经常相遇的情况下,说这两种话的人就必须设法建立用来交际的共同语言。因此,语言的蔓延式传播中形成的语言往往属于混合型语言,新居地的语言并不完全同于原居地的语言。例如英国商人在西非奴隶贩卖使用的洋泾浜英语和克里奥尔英语就是这种语言传播的结果。 (3)语言的变异式传播指移民迁移到新居地之后与土著杂居,移民语言中往往会掺杂进土著语言,加之土著语言地位较高,移民又处于土著的包围之中,移民语言不可能长期保留原有的面貌或特征,随着时间的推移,移民语言被土著语言所同化,从而导致移民所具有的语言与原居地语言完全不同。例如从1770 年到1852 年,一批在英国和爱尔兰宣判有罪的人被转移到澳大利亚,随后又有大批从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的自由移民来到澳大利亚,他们的语言就受到澳大利亚土著人方言的影响,形成特有的澳大利亚英语变体。
语言的空间传播一般受制于三方面的因素。首先,不同语言之间的差异是语言空间传播的外在动力。任何语言都有不同于其他语言的地方,无论强于其他语言,还是弱于其他语言,都会引起其他语言的注意。随着人类迁徙到不同的地方,语言的差异性逐渐显现,分别体现在语法、语音和词汇三个方面,只要有条件,这种扩散关系就能确立。语言之间的差异可能导致A 语言被B 语言同化,或是代替B 语言,或是使B 语言退到边远地区;有时随着A 语言区的扩大而产生语言的分化,出现新的方言或新的语言。
其次,语言的自身发展是语言空间扩散的内在动力。语言在封闭状况下发展非常缓慢,它需要借助社会这个载体不断的演变和发展。如果一种语言面临强势语言的入侵时,必然存在语言生存问题,因此语言自身必须不断地与时俱进,呈现出开放的趋势,这主要植根于语言深层的发展和生存的动因。如果一种语言自身面临扩散与否的选择时,其根本动因在于价值。这取决于那种语言领有者的社会及历史地位。一个弱小民族,其语言除去学术上的认知意义,及或许存在的微弱的外交作用,几乎没有传播价值;反之,有价值的语言才会被其他语言选择和传播。
第三,政治边界和地理障碍常常限制语言空间的扩散,语言的空间传播也需要一些助力。鉴于各种社会政治因素和两地距离的远近及交际网络的疏密和语言演变扩散的速度及相互影响的大小有密切的关系,所以一定的交通条件和有利的社会政治环境可以大大促进语言在空间上的传播速度。例如,中世纪东亚世界汉语和伊斯兰世界的阿拉伯语以及欧洲的拉丁语流行最为广泛,但由于受制于生产力低下等客观因素,这些语言的传播并没有突破大洋的阻隔,仅限于陆路的传播,但15 世纪末到17 世纪中期地理大发现的到来,促成了语言海陆的传播,使整个世界连在一起。另外,欧洲殖民的海外扩张,正好也为欧洲语言在殖民地的广泛传播提供了适合的政治环境,形成了通用语真正意义上在全球的推广:葡萄牙语、西班牙语和英语几乎覆盖了西半球;英语成为澳洲大陆、南亚和东南亚大部分地区的优势语言;法语与阿拉伯语在非洲北部并驾齐驱;俄语则控制了整个亚洲北部,形成了西方语言在世界传播的版图。
(二)语言的时间传播
语言的时间传播是一种语言传播的延续,它不是面对面的传播行为,而是传播主体隐蔽了历史背景,通过借助媒体进行传播,以克服时间的局限。例如在国内或国外有目的地推行某种语言,不仅需要借助国民语言教育和对外语言教学,而且还要借助广播电影电视、网络、书籍等媒体促进语言的扩散。
语言的时间传播可分为显性传播和隐性传播。显性传播是指通过政府法令以及条例规则等明文规定的政策来传播语言;隐性传播是指通过语言意识形态、语言实践活动等体现出来的语言倾向,以及可能影响到语言生活的其他法律条文或政府文件。隐性传播虽不是关于语言生活的明文规定,但是能够起到语言显性传播的作用。而显性传播如果过于强硬也有负面影响,因为当一种语言的传播成为一套强有力的思维模式、价值系统、生活习惯等思维定势时,可能给后人带来沉重的因袭负担,构成语言发展的巨大障碍,甚至堵塞了代际语言传播渠道。所以语言的显性传播和隐性传播是辩证的关系,二者相辅相成。语言的显性传播是隐性传播的“法规化”外在体现,在执行中仍然需要隐性传播的支撑,需要时甚至转化为各种隐性的语言传播,从而进一步引导隐性语言传播向着显性语言传播的方向凝聚和发展。一个国家可以没有显性语言传播,但如果同时没有一致的、足够有力的隐性语言传播,那么,这个国家的语言生活将是“碎片化的”。①李宇明:《重视隐性语言政策研究——李英姿〈美国语言政策研究〉序》,《语言文字报》2013 -03 -26。例如美国的语言政策之所以发挥威力在于其中微妙的隐性部分即语言文化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隐性政策的标准和效果,可能对政府机构实践产生更大的影响,并可以形成和控制语言行为,这往往比官方的语言政策更有力量,反而更能取得预期目标”②Schiffman,Harold F. Linguistics Culture and Language Policy. Landon and New York:Rutledge:Routledge,1996.
三、语言传播的普遍模式
当今世界语言分布的格局是由于历史上的斗争和融合形成的,它记录了一些重大的事件,见证了一个国家(或王朝)的荣辱兴衰。通过语言这个窗口,我们或许可以窥见历史演进的一般规律,从而解答语言在历史长河中能够兴旺繁荣,繁衍发展主要遵循几种传播模式。
(一)军事扩张模式
军事殖民扩张是语言输出的一种最直接也是最有效的方式。殖民统治扩张到哪里,殖民国家的语言也就扩张到哪里,语言从来都是强国施行其政治、经济、宗教影响的主要工具。因为只要殖民国家占领一个地区后,该国语言会迅速成为政府用语,而掌握该语言的人会在成为政府雇员、公司雇员以及在经商等方面享有优先权,会支配更多的资源,拥有更高的社会地位,获得更多的实际利益。从历史角度看,中世纪希腊语之所以能够风行地中海靠的是古希腊军队的剑与矛,拉丁语称雄欧洲一千年主要取决于罗马军团的威力,阿拉伯语在中东和北非的广泛使用就是凭借8 世纪以来摩尔人的征伐。近代西班牙语、葡萄牙语和法语盛行于南美、非洲或远东,也是由于文艺复兴时期西班牙、葡萄牙和法国通过其陆军和海军强力推行海外扩张的结果。这些通用语言的发展和衰落充分显示了通用语和帝国扩张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
(二)人口迁移模式
人口迁移是语言扩散的直接动因。人是语言传播的直接载体,语言的传播扩散是通过人的交谈移动直接完成的,没有人口移动,在通讯条件比较落后的时代,语言的传播扩散几乎无法实现。移民作为人口迁移的一种方式,促进了语言的传播发展。从英国建立第一块殖民地起,就不断的有英国人远离故土,通过人口迁移的方式移居到海外殖民地,他们有的是获刑的罪犯、有的是为了摆脱政治和宗教迫害、有的是为了在海外大发横财、有的是为了纯粹的拓居戍边。英国成了近代以来最大的人口输出国,大批的移民不但将英国的文化和宗教带到了世界各地,更是将英语撒遍了世界各个角落,得到广泛的传播。
(三)经济文化模式
贸易历来是语言交流的重要途径之一。如果人们意识到使用某种语言会与经济利益挂钩,该语言就会得到广泛传播。一战前,英国就是依托着殖民地之间的商业活动与遍布世界各大洲的殖民地进行着频繁而大规模的贸易,奠定霸主地位,对英语的传播起到了强劲的推动作用。二战后美国取代了英国,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加大英语的扩张力度。以美国为首的英语国家经济文化的的迅速崛起,使美国成为世界重要的文化产品输出国,通过不同的媒介,例如饮食文化、音乐、影视、互联网等等,已轻松的文化方式把英语传遍世界各个角落。可见,强大的经济后盾是英语后期如此迅速和广泛地传播的最根本原因。
(四)科技革新模式
一旦一门语言充当接触接新技术的先决条件,也会得到传播。语言传播与人类历史的科技革命是息息相关的。语言传播的第一革命是从语言变成符号(公元前3500 年)开始的。随着符号的产生,语言第一次与科技联系起来,人类通过语言描述的社会经验,被符号记录下来,成为科技符号。这代表语言传播从时间的久远和空间的广阔上实现了真正意义的超越。印刷术的发明又解决了语言传播由于竹简、帛书等媒介笨重、符号复杂、复制困难带来的问题,突破了上流社会对语言的垄断和在传播上的特权,为语言传播开辟了一条便捷、高效、省钱、省力的空中通道。电报传播时代的到来突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使语言传播瞬息万里;在没有识字需要的情况下,为人类提供了超越识字障碍、跳入大众语言传播的一个方法。目前互联网的形成更使语言传播不仅具有其他传播模式的特点,还具有自己的主动性、参与性、交谈性和操作性的特点。
(五)宗教推广模式
宗教是语言传播主要依赖的手段,很多语言如希腊语、拉丁语、阿拉伯语、英语、汉语等传播均发端于宗教推广模式。这些语言古时候都有经文或经书,而且都出现在最早的经文记载中,因为当时的语言研究是传教士们为了传播宗教而设立的一门实用学科,可以说语言传播和演变所带来的影响,几乎不在传教者的关心范围内,然而宗教的发展却成为语言文化要素的传播媒介,奠定了语言传播的坚实基础。随着海外大殖民时期的到来,宗教成为国家殖民扩张的政治工具,它对于语言传播表现出明显的攻击性、强制性和国家目的性。比如罗马帝国的拉丁语、中美王国的玛雅语及西班牙语和法语在非洲的传播、阿拉伯语通过伊斯兰教扩大影响力等等,虽然打着传播基督福音的幌子,但实质上是将语言和宗教同时移植到新领地,强加给所谓的欠发达的民族,以稳固殖民统治。二战以后,旧的殖民体系被打破,发达国家的宗教传播多以“文化交流”、“资助”等间接和隐蔽的方式推广自己的语言。鉴于此,无论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语言推广,形式和内容更加隐蔽,宗教在实现同化的过程中都在其中发挥巨大的作用。
四、结论
一种语言的传播既是一个漫长渐进的过程,又是一个多种复杂因素交叉互动的过程。它既需要深厚的历史、文化、科学技术等底蕴,又需借助强大的政治实力和军事威慑力作为后盾,再后来正式教育成为语言最常用的传播渠道,当然语言传播和影响仍然有赖于该语言民族政治、宗教、经济、文化、军事等领域的地位,后者的此消彼涨是前者兴衰更迭的晴雨表。
语言传播的方式不是简单意义的平面扩散,语言的传播除了在空间领域(包括共时的地理或是社会阶层)呈渐进扩散,在历时上语言的传播也以渐进扩散的方式来完成,充分体现了传播的共时性与历时性。语言传播常常打破本地语言的原有格局,新旧语言之间产生激烈的冲突。在打破旧的平衡达到新平衡的过程中,旧语言中许多僵化的东西在新语言的冲击下会悄然逝去,新语言中某些适宜本区域的内容则会扎下根来,出现语言的整合现象。语言传播也可以导致语言的区域分化。这主要因为在语言扩散过程中,外来语言往往会在一个区域中造成不同的影响。一方面语言传播的交通条件不同,会导致语言扩散过程中出现时间差,进而出现语言的区域分化;另一方面外来语言对语言中心和边缘区影响不同,导致中心区原有语言势力强,对外来语言具有强大的抵抗力,接受外来语言慢,而边缘语言区原有语言势力弱,容易接受外来语言,甚至被外来语言所同化。
纵观语言传播,语言扩散又是一个涵化的过程,螺旋式的传播形式也是语言在时空中传播的常态。由于特定的历史原因与复杂的政治因素,语言在传播过程中也必然经历迫于压力被孤立、再逐渐接受最后再广泛使用等阶段。有的语言即使有一种正式的书面的显性传播政策,也不一定被贯彻实施,其实施的效果更不一定得到保证和始终如一。有的语言虽然国家和机构并没有以显性的方式传播语言,但是公众对于适宜的语言或者行为却往往有明确的取向,可见一些来自于社会的语言实践或者语言信仰,常常以更为潜移默化的方式在支配人们对于语言的选择。
鉴于此,在梳理语言传播规律的同时,要结合中国国情形成具备自身特色的推广模式,从宏观上把握汉语国际推广的战略思想,不能盲目扩张,也不能在合作中丧失主动权。既要结合汉语“走出去”的实际需要,在世界语言系统中为汉语的国际化传播找准定位,又要兼顾汉语推广的显性和隐性政策,权衡两种政策的微妙关系。总之,一种语言想真正获得长久的国际化地位离不开所属国家的政治、经济地位的稳固与强大,同时需要全面考虑语言自身的价值、历史环境和民众的语言态度等因素之间的博弈。这是一个举步维艰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