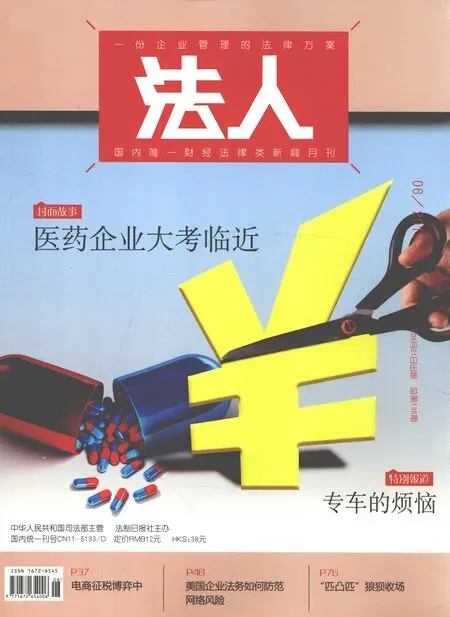一位瑞士律师的中国江湖
◎ 文 《法人》见习记者 辛颖
一位瑞士律师的中国江湖
◎ 文 《法人》见习记者 辛颖
“我希望瑞士更了解中国,也希望中国更了解欧洲。”
“北京也是我的家,我很怀念20年前的蓝天。”一年22次时差调整,30年往返于中国与瑞士之间,陶培恩博士亲历了中国日新月异的变化,见证了中国经济对外开放和法治建设的点滴进程。他在青葱岁月时推开一扇文化之门,自此将自己的事业系在这片土地上,他创建了瑞士律师事务所在中国的第一家实体法律服务机构——瑞士文斐律师事务所中国代表处。
陶培恩是位中国通,他带你回忆“穿着制服”的80年代,和你侃侃孔孟之道,与你讨论中国制度的历史渊源,为你比较中国与欧洲的法律不同。采访陶培恩的机会并不多,他每个月只在北京待一周左右,日程总是排得很满。除了苏黎世,北京、上海、香港以及台湾也需要他定期去处理业务。
虽然采访时间约在了下午两点,可陶培恩还是没来得及吃午饭,从另一个会议中抽身之后,他直接开始了与《法人》记者的交流,回忆起他与中国的缘分,其中故事颇多。
孤身闯中国
1985年,在中国人还不理解“文化交流”为何物的时候,19岁的陶培恩就背着行囊只身来到北京,试图敲开一扇中国的门。
“我就是对中国非常感兴趣,我想了解中国人的生活和文化。”在美国就读高中的时候,陶培恩第一次接触到中国学生,他讶异于这些有着完全不同文化、家庭背景的聪明学生们,他了解到这是一个重视教育与知识的国度,强烈的求知欲促使他在服兵役一结束就决定启程。
然而,那时的中国改革开放不久,计划经济背景下的百姓生活仍旧相对闭塞,事情与他所设想的相差甚远。三个月的时间,他没有在北京找到一个愿意容纳他的家庭,每敲开一扇门,所收获的只是异样的审视目光。最终,政府发现了这个“有毛病”的外国小伙,陶培恩被迫结束了他与北京的短暂结缘。
轻言放弃显然不是有志青年的行事风格,陶培恩从香港转至台湾,并成功找到了一个乐于接受“文化交流”的家庭,除了学习中文,他还通过在快餐店打零工、照顾小孩子来赚取自己的生活费用。
其实在服兵役期间陶培恩就准备开始学习中文,中文的魅力远远超过了游戏、酒吧对他的吸引,他的休闲生活与同伴们完全不同。可惜命运和他开了一个小玩笑,一本他钻研了6个月时间的苏黎世“中文”教材,被台湾同胞无情地证实“这不是中文”。
“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语言。”陶培恩的调侃中还残存着些许对那本教材的埋怨。在台湾生活不到一年的时间,陶培恩对中国文化的兴趣愈加浓厚,于是他向高雄中山大学的中文系递交了申请材料,准备进一步深造。
生活不会一直一帆风顺下去,家庭变故的原因迫使他不能再随性而为,必须认真的考虑他地生活以及未来。
“我需要选择一个真正有用的专业,而不仅仅是我喜欢的。”法律,就这样走进了陶培恩的生活。而陶培恩并没有就此放弃自己的兴趣所在,反而更好地将二者结合在一起。接下来的几年,他往返于瑞士和台湾之间,在瑞士苏黎世大学读法律以及在台湾学习中文。直到大学毕业,陶培恩才真正地告诉大家,他的专业是法律,而此前他一直伪装成中文系的学生。
当然,陶培恩在台湾收获的不仅仅是中文知识,还结识了他的太太,一个温柔可人的台湾女孩。
“她在我学习中文的学校教书,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听到了她甜美的声音,讲话也非常有趣,我就很顽皮地跑过去问她‘你是谁?’。”缘份的画卷慢慢展开,后来她跟随他来到了瑞士。
大学毕业之后,陶培恩找到了北京大学知识产权法的一位教授指导他的毕业论文,借着撰写毕业论文的机会,他终于又回到了北京。
把根种在中国
“我一直在观察中国的法律市场,自从1992年中国出现私有化合伙制律师事务以来,我就开始向他们投递简历,虽然那
时我还没有毕业,不过让他们接受我似乎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陶培恩从未停止他的尝试,尽管两年间所有的简历都石沉大海。
执着总会伴随着机遇,一位到瑞士留学的中国律师在听到陶培恩的抱怨后,为他提供了一封推荐信。海问律师事务所接纳了这位年轻的瑞士律师。
“由于同时在撰写毕业论文,在海问我还只是一个实习生,但这个机会对我十分重要。”此时的陶培恩已经在瑞士Bulach地方法院以及律所都有了一定的实习经验。根据瑞士的规定,取得律师职业资格需要具备一定的实务经验,而毕业论文也是在毕业之后才开始撰写。
那时海问的核心业务是公司上市,而根据陶培恩的经验,他被分配到了国际业务部门,主要负责合资企业的合同履行、诉讼、仲裁等。回忆起当时的工作环境,陶培恩仍记得,“那时的中国除了上市公司,没有什么人真正地重视律师,那还是一个靠关系的时代,而不是法律”。
刚刚进入海问,陶培恩的工作内容和普通的实习生没有什么区别,熟悉各种业务,各种帮忙,陶培恩也确实积累了一些关于合资企业的业务经验。但陶培恩对自己的期待,并不是一个平凡的实习生那么简单。他开始主动接触客户并参加一些活动,向那些已经进入中国的瑞士企业推荐自己。连他自己也没想到,真的有客户产生了合作意向,他就这样为海问找到了项目,并拿到了在中国的第一笔律师收入。
1998年,由于陶培恩在瑞士工作的律所需要,他又一次返回了瑞士。已经在中国积累了丰富人脉的陶培恩认为,他回到瑞士依然可以从事与中国有关的业务,也可以通过与中国律师的合作完成中、欧企业的相关业务。
不久,客户中的两家大型瑞士企业直接找到陶培恩,“如果你希望继续代理我们在中国的业务,你们律所必须要有在中国的代表处”。原来,与中国律师的业务合作并没有陶培恩设想的那般轻松,瑞士企业在与中国律师接触后有很多不顺利的方面,文化的代沟使得合作并不那么愉快。
一位年轻的瑞士律师能够有如此级别的客户在瑞士并不多见,陶培恩意识到了问题的重要性,并及时和律所的其他合伙人进行了沟通,他们决定在中国设立代表处。然而彼时的中国法律服务市场开放程度仍然有限,想要设立外国律所的代表处需要很多的审批手续,有的外国律所甚至为此等了六年。
2000年,恰逢中国与瑞士建交50周年,从递交材料到获得审批,陶培恩只用了3个月,并理所当然地成为了中国代表处的负责人,尽管那时的代表处只有两个人。
随着中国代表处业务的逐步发展,业务领域逐渐扩大,而陶培恩原本所在律所的其他合伙人与中国业务完全脱节,加之其自身利益和风险的一些考量。陶培恩认为,是时候做出一个新的决定了。
2006年,陶培恩带着他在中国的业务从原本的律所正式独立出来,成立了如今的瑞士文斐律师事务所,在苏黎世、北京、上海等地均设有办公室。

陶培恩
成为中瑞企业间的桥梁
回忆在中国的30年,陶培恩感慨道自己真的很幸运,“30年前的中国,马路上都是自行车,做饭要靠烧煤,冬天只有白菜,夏天唯一的乐趣就是吃西瓜。我认为现在中国的年轻人并不真的理解中国,他们认为中国就是现在这么富有,而我每一天都在感受中国的变化”。
除了律所的业务,陶培恩还以国际商会仲裁庭首席仲裁员的法律秘书的身份在国际仲裁领域获得初期执业经验,并代理过国内外多个仲裁机构的案件。谈及自己作为律师、仲裁员、上市公司董事的身份,陶培恩认为其相辅相成地提升了自己的执业水平。只有作为律师经过撰写合同的磨炼,以及在董事会上深入企业真正的困境,才能更好地从另一个角度去完成仲裁的业务。
据陶培恩介绍,在文斐律师事务所提供的法律服务中,比较成熟的就是境外企业到中国的投资业务,伴随着中国政策的改变,从早期局限的中外合资企业到对外商独资企业的开放,业务涉及金融、保险、工程、建筑、电信、水泥、纺织、传媒等诸多行业。
“我最期待的业务其实是中国公司对欧洲的投资。”然而这类业务直到四年前才姗姗来迟。陶培恩向《法人》记者介绍道,“以前如果一个公司决定在欧洲设立工厂,他可能不会选择瑞士,因为瑞士是一个服务性的中心而且投资成本较高。较为常见的选择是,在瑞士设立欧洲区总部。并且中国公司收购瑞士企业往往出于对商标、客户等考虑,而非工厂本身。然而,自2014年7月1日《中瑞自由贸易协定》生效后,在瑞士建立销售渠道、研发中心或区域性总部以打开欧洲市场是一个理想的选择。此外,中国生产型企业并购瑞士企业更注重于并购本身的规模经济效应以及瑞士企业在机械、化工和医疗等行业中的技术优势。”
介绍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化以及习惯,是陶培恩工作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与中国相比,瑞士是一个程序制度非常严格的国家。当中国投资者感觉到这其中的流程过于烦琐,或者比自己预期的要耗费时间时,他们会习惯性地催促律师并建议律师去相关部门了解情况,而陶培恩需要让他们明白这是不可改变的制度流程,按照程序逐步进行不会有任何不妥之处。而在打过一两次交道之后,中国投资者就能够平心静气了。
瑞士企业也会面临类似的问题,尤其是早期进入中国的外商企业。那时中国的公司制度还不健全,虽然设立公司的审批非常严格,但公司设立后的相关监管却可能处于空白状态。而在欧洲,设立公司几乎没有门槛,但后续的公司管理却有很多的要求。所以欧洲企业初到中国,往往感觉对于企业的监管非常松懈,但是随着中国的监管逐渐完善,外商企业面临的问题会逐渐显露出来。陶培恩就要尽量帮企业避免这种情况出现,而类似的文化隔阂还有很多。
“我希望瑞士更了解中国,也希望中国更了解欧洲。中国现在有那么多的人了解美国,从美国回到中国。但是中国和欧洲的互相了解实在太少,虽然这种情况在近十年有所改善,但是还远远不够,所以很多人不能理解中国的特色制度是有历史原因的。互联网、媒体、社交网络为我们的互相了解提供了更多的机会,但毕竟有限。我希望看到的交流并不是局限于虚拟世界的,而是真真切切的。”陶培恩说道。
对话陶培恩
《法人》:能介绍一下你最骄傲的事情吗?
陶培恩:我想我最骄傲的事情还是我的家庭和孩子,我们是一个很成功的中外合资企业。我想如果是一个瑞士太太也许早就离开我了,我今天的成绩确实非常需要家庭的支持。虽然我在工作上投入了很多,但是工作是不能和家庭相比较的。我希望以后不要后悔花了那么多的时间在工作上,我会陪着我的儿子踢足球,陪着我的女儿到世界各地去旅行,去非洲帮助农民,工作是为了生活。
《法人》:你年轻时的理想是做一名律师吗?
陶培恩:我追求公平正义,但是我的理想并不是做律师。我年轻时是一个环保主义者,所以那时拒绝开车。为了向我的足球队队友证明我的坚持,我每次比赛都不乘球队的车,自己去坐火车、公交,当然这需要很多时间。不过有一次我实在来不及,迟到了,比赛也输了,所以队友说不该怀疑我的理想,但是希望我还是能够和他们一起坐车。不过后来出于工作的需要我还是开始开车了。
《法人》:你曾考虑过考取中国的律师执业资格证书吗?
陶培恩:在我还年轻的时候,确实考虑过,不过当时中国对于大陆以外的人是否有资格考试没有明确的规定。当然我在考中国驾驶执照时的痛苦经历对此的影响也很大。2000年左右的时候,工作需要我去参加了驾照的考试,虽然我的日常中文没有问题,但是“离合器”“手刹车”等对我来说都是很专业的词汇,而且那个时候的理论部分还是笔试,不像现在有电脑,有英文试卷。所以对我来说通过那个考试真的很难。而且,考虑到我从事的主要是国际业务,中国律师资格影响不是非常大,后来就放弃了。
《法人》:你对律所下一步的规划是什么?
陶培恩:我希望能够多做一些有意思的案子,和人打交道的案子,而不是盲目地扩大。比如我在五年间为一家上市公司争取权益保护,并取得一些阶段性胜利的时候,成就感是很令人愉快的。律所目前20人的规模就是我的极限了,这样我才能了解、掌控律所的业务,律所和律师是应当为自己的业务负责任的,我见过很多因为扩张而失去管理的例子,这不是我所希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