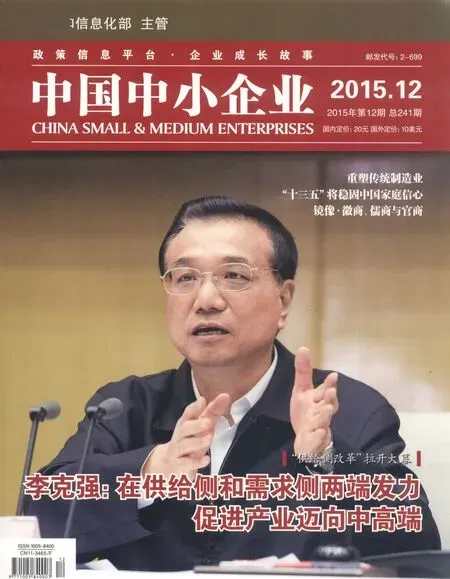徽商、儒商与官商
文/宋怡青
徽商、儒商与官商
文/宋怡青

徽商是中国十大商帮之一,在明清商界叱咤近300余年,其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于“崇儒”。来自“程朱阙里”的徽商,将儒学“仁义礼智信”的要义作为待人处事的行为准则,以儒家道德标准来规范商业经营活动。所以,徽商与同时代的其他商帮相比,有重信义、尚礼仪、好读书等特点,这些特点为徽商赢得声誉,也为其商业竞争中战胜对手、赢得市场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但是过度“崇儒”,不少徽商致富后,或弃贾从儒,或让子弟专习儒业。这也导致徽商整个群体实力削弱,最终没落。

贾儒结合
徽商是指古徽六邑(即歙县、休宁、祁门、黟县、绩溪、婺源)之人,在本土及远离本土经营商业,是典型的封建商帮。
徽商自南宋发端。明嘉靖以后,徽州从事商贾的人数大量增加,逐渐发展成为中国商界的一支劲旅,活跃于大江南北、黄河两岸,乃至日本、暹罗、东南亚各国。所谓“两淮八总商,邑人恒占其四”,说的便是徽商在盐业领域开创了独执牛耳的局面。
尤其到了康熙中叶,徽商一跃成为十大商帮之首,在全国范围内造成了极大影响,有着“无徽不成镇”的美誉。
与其他商帮类似,徽商的兴起也与地理位置有着密切关联。徽州境内山多、地少、土瘠、人稠,生存问题千百年来困扰着当地人,除了传统的业儒、务农之外,经商也是谋生的一个途径。徽州有句民谚:“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这便是徽商从小背井离乡、自力更生的生动写照。
但是,与其他商帮不同,徽商与儒家文化有着历史的亲和性。几次人口迁徙,更为徽州奠定了文化基础。
《程朱阙里志》记载,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封建士大夫和仕宦因躲避战乱,迁移到黄山脚下。他们给当时的皖南山区,带来了中原文化的精髓,即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读典诵经、崇尚礼仪的儒风在徽州这块土地上开始生根发芽。
这些学说在皖南进而发展成了影响宋明清三代封建统治者指导思想的程朱理学,为儒家文化传承的典型。至南宋,徽州作为朱熹的桑梓地,读朱子之书,取朱子之教,秉朱子之礼,蔚然成风。
由于古徽州是一个“十户之村,不废诵读”。徽商基本上也都来自于儒生。有的弃儒服贾,是因为家遭变故,无以为生,只好从贾。譬如,清代婺源县的董邦直本来都读书,后因家庭生计所迫奉父命去经商;有的是屡进科场、仕途无望之后,被迫从事商业活动。休宁人程祖德“连举未第,退事于商”。
这种文化情节反映在现实中,大多数徽商是“亦商亦儒”。甚至一部分徽商认为经商仅是解决生存危机的一种手段,内心深处依然将“业儒入仕”作为终极理想目标,在经商致富后,弃贾从儒。
黟县人汪廷榜少年时学习经商,28岁那年,在汉口观景时,他内心萌动了弃商从文的想法,于是就开始读书,学文词。
而大多数徽商也认为“非诗书不能显亲”,要求下一代尽可能专攻科举,实现光宗耀祖的人生理想。徽商这种致富后或弃贾从儒,或让子弟专习儒业,也导致徽商整个群体实力削弱,最终没落。
诚意敬业
“诚信”一直是儒家道德学说的核心,被视为“进德修业之本”。所谓“诚”是指诚信不欺、诚实无妄。
儒家的诚信观念对贾而好儒的徽商产生了深刻影响。在浓厚的儒家文化氛围下成长起来的徽州人,自幼饱读儒家经典,耳濡目染儒家诚信观念。他们巧妙地运用和改造儒家学说中的“诚信”思想,形成了独特的商业原则和经营理念,并且在经商过程中身体力行。
徽商“生财有道”的经营理念便是儒家的义利观,即“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歙县《汪氏统宗谱》记载,徽商的信条是“职虽为利,非义不可取也”,恪守“以义取利”、“利缘义取”的贾道原则,强调货真价实,结果往往是“不言利而利自饶”。
现实中,徽商不但鄙夷豪夺强取,更鄙弃欺诈行骗。主张“诚信经营”,讲
究商业道德。
明朝徽州黟县有个叫江遂志的商人,幼时家境贫寒,在别人劝说下背井离乡外出经商,却遭人诬陷,资本全部被没收。后来祸不单行,货物遭遇风暴尽数损失。但是年过五十的他没有改变对商业的诚意追求,毅然往来于金陵、淮扬的盐场,最终富甲一方。
诚意敬业,从徽商重信誉、货真价实、货不二价、童叟无欺、秤准、斗满、尺足这些营商戒律信条随处可见。
徽商梅文义,“诚笃不欺人,亦不疑人欺。”他所获得利润反而比正常情况下多三倍,“往往信人之诳,而利反三倍”。
清末绩溪红顶商人胡雪岩在杭州城开设的胡庆余堂大门口有他亲笔所书的“戒欺”匾额,旁有小字“凡有贸易均不得欺字,药业关系性命,尤为不可欺”。
徽商以诚信为核心的价值观念,正是徽商经营思想的精髓。徽商也赢得了“一代儒商”的美誉,改变人们“无商不奸”的旧看法。
不仅对待顾客诚实无欺,对待商业合作伙伴徽商也同样诚信待人。很多徽商创业初期资金不足,往往采取合伙经营的形式。在此过程中,徽商始终如一地以诚信为本,与合作伙伴互相扶持,诚实不欺,守信不渝。
徽商追求“以德治商”的境界,将“诚信”贯穿于商业行为始终。正是这种态度,使得徽商在内部能够团结齐心,凝聚力量;在外部能树立良好的商业信誉,获得顾客充分信任,建立起良性的商业循环,最终在激烈的商战中独占鳌头。
刘伯山在《中国一代儒商》中具体论述了徽商的儒商本质,认为徽商重儒而不轻贾,贾儒结合,一张一弛,迭相为用,这是一种新的价值观。
恪守崇德
儒家主张道德优先的价值取向,推崇尽义尽孝的礼义规范,强调以德为先的教化,标榜舍利取义的君子人格。徽商的价值观也深深浸透了儒家“崇德”的价值取向,并且从自身的经济需要出发,对其进行了改造、变通和融合,形成了“贾而好儒”的特色。
清代学者戴震称徽商“虽为贾者,咸近士风。”
在徽商看来,经商目的是谋生,而维持生计不仅仅是满足个人的生存需要,更应满足整个家庭和家族的生存需要。徽商常常将赡养父母、抚养兄弟子侄、遗爱族人当作自己经商的具体目的,从而践行了理学家所宣扬的孝道。
这种尽孝的思想还进一步扩大到宗族内部。徽州人中有一些人在经商成功后,往往资助、提携贫苦族人。不少徽州宗族特别重视祖产的增值。《安徽省土地改革资料》记载,截至1950年代初土改时,徽州宗族祠堂拥有耕地占徽州总耕地的15%以上。
自古以来很多商人在致富之后,将所获利润挥霍浪费,为世人所诟病。而徽商则崇尚儒家的以义制利,用儒家的道德伦理来规范和指导自己的消费行为。勤俭节约在徽商之间蔚然成风。黟县一代“大富之间,日食不过一脔。”
徽商所获得的利润以各种形式流向了社会、乡里和宗族。譬如赈灾济贫、兴修水利、修筑道路、捐资助饷、兴建书院祠堂等。这些做法或利于国家,或造福于地方,无一不合乎儒家的道德要求。
如明初黟县屏山人舒志道,经营有成而广为乐善好施。《黟县志》记载,志道公为人志量宽洪,乐善好施,凡桥梁、道路、庙宇、衙舍,无不助财修理。舒志道本人也由于多行善事义举,所以威望很高,“通邑称为善士,屡受知府、知县、族奖。”
再譬如,民国初年,黟县横冈吴子敬在上海做丝商生意,每当春蚕吐丝时节必到无锡收丝。因交通不便,1915年,吴子敬出资银元32324元,在黄埠墩渡口建造了无锡第一座铁桥。自此以后,无锡、宜兴、上海等公路交通全面贯通。该桥因为是吴子敬一人独资兴建,就题名为“吴桥”。吴子敬平生慷慨义气,先后在上海创办了救熄会(消防机构)、孤儿院、敬老院、贫民小学等,为当地百姓送去了福音。
其实,在徽州一府六县,吴子敬这种从事公益事业的徽商,不胜枚举。徽商的这种行为使徽商加速了与主流群体、寄寓地的文化交流,更为自身树立了良好的形象,获得了荣誉与声名,成为了经营过程中无形的财富。但是后世也有学者认为,徽商的义行义举有矫枉过正之嫌,导致了徽商获得的大部分利润没有再进入流通领域扩大生产经营,这也导致了日后徽商资本的萎缩。
官商合流
官商合流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商人自身贾儒结合的延续,贾而好儒的徽商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徽商无论行商或坐贾,无论在本地抑或外籍,无论大贾、
中贾抑或小贾,他们大多攀援官僚士大夫,这是崇儒的表现。

在中国官僚社会里,权力主宰一切,徽商要想在商界站稳脚跟,并求得发展,就必须与权势结缘;而要与权势结缘,除了金钱之外,最重要的就是儒术了,因为儒与官通,官僚为了附庸风雅,自然对儒术存有浓厚的兴趣。
与其他商帮相比,徽商有较高的文化修养,这也有利于他们攀援官僚势力。徽商喜欢结交文人、攀援官宦。他们也重视教育,经商获利之后,喜欢设置塾学、捐修官学、建设书院,延请名师、扶持士子,为府学、县学、书院提供束脩,这也为官商更深结合打下基础。
在重农抑商的传统社会,徽商获得封建政府的青睐,无疑如虎添翼。特别是徽州的盐商,他们赢得了统治阶层的支持,得以把持两淮两浙的盐利,对于徽州商帮的发展,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徽商也乐意资助一些士子,因为士子或许就是将来官员。乾隆、嘉靖年间的《绩溪县志》记载:有一天清晨,万年米行的东家曹显应打开店门,看见一个衣衫单薄的年轻人,卷缩在屋檐下,冻得浑身瑟缩,他忙将年轻人引入店堂内的火盆旁。这个年轻人就是许国,他是县里读书的秀才,昨天回家探母回来迟了,关了城门,他只好露宿在曹家米行的屋檐下。曹显应见他身体瘦弱,谈吐文雅,便视为知己,长期供养他食宿,后又资助他赴京参加科考。许国金榜题名,身居高官显爵,与曹显应交情也愈加弥笃。
此后,万年米行的昌盛,除了曹氏父子善于经营外,自然少不了许国这样的高官作后台给他们带来的好处。
徽商的代表之一胡雪岩的发迹也折射出官商结合。当年左宗棠迎战太平天国,在兵粮短缺的情况下,胡雪岩雪中送炭,三天之内筹集了10万石粮食,解决了左宗棠的燃眉之急。后来胡雪岩逐渐得到左宗棠的重用。1866年胡协助左宗棠创办福州船政局,后又主持上海采运局局务。胡雪岩依仗湘军权势,在各省设立阜康银号20余处,并经营中药、丝茶业务,操纵江浙商业,资金最高达2000万两以上,是当时的中国首富。
这种官商联盟深度结合,使得徽商们的命运与时代的政治经济制度息息相关。但是官商关系具有不稳定性和不可靠性,而且官的力量过于强大,这种不确定性更是体现得越明显。商人往往会被当官者或多或少地利用,最终落个悲惨的结局。当依附的后台土崩瓦解之际,徽商也最终走向了没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