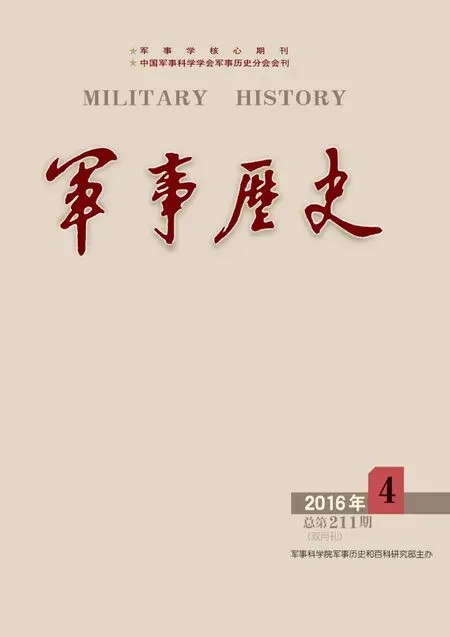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军事战略转变历程探析
★
发生于土地革命时期的“国内游击战争和国内正规战争之间的转变”*《毛泽东选集》,第2卷,55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是人民军队经历的第一次军事战略转变。第一次军事战略转变持续近5年时间,由于两次“左”倾错误的干扰和影响,整个历程充满艰险曲折,大体可以分为初步实现、曲折反复和最终实现三个阶段。
一、转变的初步实现
自1930年5月全国红军会议至第三次反“围剿”胜利,转变得以初步实现。这一阶段,红军克服了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带来的危害,提出了以“诱敌深入”为核心的积极防御战略方针,初步实现了由游击兵团向正规兵团、由游击战向运动战的转变。
(一)转变的起点。关于第一次军事战略转变的起点问题,学术界有不同的认识。多数研究成果粗略地将其界定在1930年夏,部分涉及这一问题的著述将起始时间定在中央根据地第一次反“围剿”。虽有学者提出转变始于全国红军代表会议,但未做进一步论证。第一次军事战略转变的起点,应当确定为1930年5月中旬中共中央在上海秘密召开的全国红军代表会议。其理由和依据如下:
首先,会议所讨论的问题事关红军建设和发展大局。会上,代表们除了报告各自所在地区的红军创建与斗争情况,相互交流建军经验外,重点就红军的任务,红军的纲领,红军的策略路线,各军发展的路线,红军扩大问题,红军的编制,政治委员制度、政治部政治工作,士兵委员会,红军中党的组织与地方党部关系问题,红军中党的公开问题和公开的指挥问题等11个方面的问题进行了讨论,并形成了相应的决定。此前中央军委制定的若干计划大纲中确定的诸多原则、措施和要求等大都体现在此次会议的相关决定中。此次会议是对李立三“左”倾冒险的政治战略在军事领域较为全面的贯彻落实。会议的许多决定都带有明显的激进色彩,如“红军战略战术的第一个要求便是集中进攻。红军革命的战争只有进攻,无所谓退守”*《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8,55~63页,中央档案馆、广东省档案馆编印,1982。,要求在3个月以内扩大至50万红军,等等,不符合当时敌强我弱的实际情况和中国革命战争发展规律,超越了红军发展的实际。但此次会议提出的同一地区两军成立统一前委,两军以上成立军团,统一部队编制,制定条例法规等措施,基本符合红军的发展的方向,对加强红军中党的领导和集中指挥,打破狭隘地域观念,消除游击习气,进行正规建设等,都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其次,参加全国红军代表会议的人员具有广泛的代表性。这次会议,是红军创建以来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性的会议,由于它与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接续进行,与会人员基本都要出席这两次会议,因而参加全国红军会议的代表既有各地红军的代表,还包括了赣西南、闽西、湘鄂赣边、鄂西、鄂豫皖边、右江等根据地的代表。这就使此次会议对红军的建设和发展具有了空前的影响力。
第三,会议决定得到了强力推行。在中共中央的强力推行下,会议所作出的决定,在各根据地的红军中得到了贯彻落实。会议结束后,中共中央即派涂振农作为中央特派员,赶赴红4军传达中央指示,贯彻新的路线。6月20日,中共中央又批准了中共长江局根据全国红军代表会议精神制定的《中央军委长江办事处工作计划》,赋予红4军新的战略任务,要求红4军“将中央军委新的路线迅速传达下去,从根本上转变旧的路线”*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战史研究部编:《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史料选编》,第2辑第1册,140页。。红5军由滕代远、何长工,鄂西特委由段德昌等参会人员负责传达全国红军代表会议精神,并督促执行。
总体看,全国红军代表会议是中共中央军事战略转变在红军中的动员和部署会议,它直接推动了红军建立正规兵团等一系列正规建设的迅速展开,促成了军事战略转变的发生,对红军的建设和作战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二)转变的初步完成。转变伊始,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为推行集中进攻战略,强调“军事的战术,配备,编制,组织都应随着整个政治路线而改变”*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97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着力将红军锻造成为一支正规的“铁军”*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433页。。全国红军代表会议后,按照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要求和部署,红军以组建正规兵团为开端,迅速展开正规建设。组建了军团和方面军等正规兵团,按照“三三制”原则对部队进行了多次整编,初步形成相对集中统一的指挥体系,创建红军的参谋部、政治部及后勤保障等相关机构;在院校教育和部队教育训练上也取得了大的发展,并建立了炮兵、无线电、重机枪、工兵等专业技术部(分)队;开启了以条令条例治军的进程,对红军的建设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总体看,红军的游击习气大为减弱,正规性得到很大加强,初步实现了由游击兵团向正规兵团的转变。
与此同时,红军克服了李立三“左”倾错误的干扰,初步实现了向运动战的转变。红军尝试了阵地战和运动战两种正规战作战形式,这是军事战略转变开始后,两种军事战略指导思想在红军作战实践中经受的初次检验。总体看,攻势作战中的阵地战乏善可陈,但运动战却在游击战的基础上有了新的发展。一是红军开始将相继组建的军团、方面军作为高级战术兵团和基本战役兵团在作战中使用,作战兵力大为增强,作战规模迅速扩大。二是红军的作战开始在长的战线和大的战区内进行,许多作战行动要进行数百里甚至上千里转战,以达成对目标之敌的包围态势。三是红军作战多以外线进攻战展开,能够集中优势兵力,以速决的方式结束战斗,并迅即转移,待机而动。当然,受主客观多重因素的制约,这一时期红军的运动战形式尚属于较为初级的阶段,带有较强的游击性,没有形成较为明确的运动战作战思想和原则。但是很显然,红军的作战形式已超越了先前以分散流动为基本形式、以袭击为主要战法的游击战,开始具有了运动战所必备的“正规兵团、战役战斗的优势兵力、进攻性和流动性”*中国军事百科全书编审委员会编:《中国军事百科全书·战略》(第2版),447页,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4。的基本属性。两种作战形式在作战实践中的鲜明对比,对红军产生了重要影响,为红军在随后的反“围剿”作战中更广泛地实行运动战做好了铺垫和准备。
1930年10月的罗坊会议是这一时期的重要转折点。会议纠正了李立三“左”倾错误,红军的战略方针从集中进攻转变为积极防御,作战形式全面转向运动战。“等到战胜敌人的第三次‘围剿’,于是全部红军作战的原则就形成了”*《毛泽东选集》,第1卷,204页。。红军以“诱敌深入”为核心的积极防御战略方针和运动战作战原则的形成,标志着红军初步实现了由游击战向运动战的转变。
二、转变的曲折
(一)转变走向曲折。三次反“围剿”的胜利,使红军得到很大的发展,根据地逐步巩固和扩大,特别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建立,为红军的正规建设提供了更为有力的支撑和保证。这一时期,红军的各项正规建设持续推进,获得了全面发展。但与此同时,随着王明“左”倾错误占据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红军再次由积极防御转为积极进攻,运动战的作战原则被动摇。在积极进攻战略指导下,红军再一次展开以夺取中心城市为目标的攻势作战。1932年,红一方面军连续发起六次进攻战役,经历了赣州战役等阵地战的失败和漳州战役等运动战的胜利。由于战略指导上的错误,尽管红军取得了一些战役战斗的胜利,但预期的战略目的,即夺取中心城市实现一省数省首先胜利和以进攻打破敌军的“围剿”,均没有实现。同年7月展开的第四次反“围剿”受到了“左”倾错误的严重干扰和影响,尤以鄂豫皖红四方面军、湘鄂西红3军为甚。两支主力红军的领导人张国焘、夏曦等奉行“左”倾错误,放弃积极防御战略方针和运动战,先是推行进攻战略盲目冒进,继而转为保守主义的消极防御,最终变成了逃跑主义。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展开后,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一再否决周恩来、朱德、王稼祥等提出的大踏步进退、在运动中歼灭敌人的设想,数度命令红一方面军攻打南丰等坚城。在攻打南丰不利,敌情日益严峻的关头,周恩来、朱德等毅然放弃阵地攻坚,实施诱敌深入,以运动战的战法,集中兵力,打歼灭战、速决战,赢得了红军战争史上规模空前的大兵团伏击战的胜利,一举打破了国民党军的第四次“围剿”。红一方面军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在危难中稳定了中国革命的大局,是向三次反“围剿”中形成的积极防御战略方针和运动战的回归,也是对“左”倾错误的一次成功抵制。
(二)转变遭受重创。政略决定战略,政治路线的错误,终究会戕害军事战略。1934年1月,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将“左”倾错误推向顶峰,冒险主义的进攻战略和阵地战完全取代了积极防御战略和运动战。第五次反“围剿”展开后,面对国民党军新的堡垒主义战术,“左”倾领导人企图“御敌于国门之外”,红军被迫在敌人堡垒群间辗转寻敌,向敌堡垒和坚固阵地发动正面进攻。在遭遇很大损失后,“左”倾领导人又从进攻战略转而奉行保守主义的消极防御战略,分兵把口、层层设防、节节抵抗,同时寄希望于“短促突击”这样的所谓“现代的军事战术”*石志夫、周文琪编:《李德与中国革命(有关资料)》,93页,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寻求以战斗的胜利累积而致战役的胜利,由战役的胜利最终导致战略上的胜利。在这一战术指导下,红军丧失了主动权和机动性,不断与强大的敌人在阵地战中拼消耗,最终完全失去了在根据地内打破“围剿”的可能,被迫进行战略转移。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与鄂豫皖、湘鄂西苏区第四次反“围剿”所走过的轨迹如出一辙,几乎是一次历史的重演。其内在的共性原因就在于“左”倾错误对中国革命及中国革命战争实际的背离和对马克思主义本质精神的背弃。
三、转变的完成
(一)拨正转变方向。长征初期,“左”倾领导人延续了错误的军事战略,由消极防御转为逃跑主义。红军长征是为了转变被动局面而进行的战略转移行动,长征中的红军时刻处在运动之中,处理好“走”与“打”的关系就显得尤为重要。此时,“走”是目的,“打”是手段,“打”是为了能更好地“走”,因而,既要避免硬碰硬地与强敌决战,也要反对消极避战的逃跑主义。但由于“左”倾领导人急于夺路西进,运动中的红军不仅没能发挥出大踏步进退机动灵活的运动战特长,反而常常被迫与强敌进行阵地战对垒,打而难走;而在有利战机出现时,却又放弃以打促变,只走不打。特别是没有利用敌军兵力较为分散、协同困难、内部分歧严重的有利时机,集中兵力,寻机对敌进行歼灭性打击,以缓解困境,创造新局面,而是采取了消极避战的方针,“就是对孤立的、拖得疲劳不堪的敌军,也未主动反击,只是招架,实质上是惊慌失措的退却逃跑”*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央档案馆编:《遵义会议文献》,9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尤其当红军进入湘南地区后,群众基础好且已脱离了国民党军精心布置的堡垒地域,利于红军展开运动作战,毛泽东、彭德怀等都曾建议乘敌各部尚未靠拢之际,组织力量进行反击,寻歼敌一路或一部,以“迫使蒋军改变部署”*《彭德怀自述》,19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变被动为主动,但均未被采纳。这就必然造成长征初期红军迭遇险境,屡遭失利的被动局面。
自湘江战役遭受极为惨重的损失始,正确与错误的博弈和斗争逐渐公开化,“焦点是红军战略行动方针问题”*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272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洛甫)等就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军事领导上战略战术的错误,对“左”倾领导人提出了公开批评,极力主张红军重拾运动战法宝,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在运动中各个击破敌人,而不能只是被动地逃跑;在红军行动方向上,主张放弃去湘西同红2、红6军团会合的计划,转向贵州前进,寻求在敌人力量薄弱的川滇黔边建立新根据地。但这些批评和建议均未被接受。直至黎平会议,经过激烈的斗争,才纠正了红军前进方向,避免了投入国民党军十几万大军在红军西去湘西路上张开的大网。猴场会议后,红军拉开了重新回归运动战的序幕。
(二)完成战略转变。遵义会议纠正了“左”倾军事错误,重新确立了正确的军事路线,毛泽东重新回到了红军的领导岗位,红军完成了向积极防御(决战防御)战略方针和运动战的再次转变。通过对第一次军事战略转变进行整体的梳理,笔者认为,转变的终点应当确定为遵义会议。其原因在于:
第一,红军在第三次反“围剿”后完成的向运动战的转变与中共中央的军事战略并不一致。中共中央所推动的第一次军事战略转变是由游击战争向正规战争的转变,是战争样式的转变。在中共中央的视野中,正规战争是“国家和国家作战,大军和大军作战”*《毛泽东选集》,第1卷,205页。,红军的任务是占领中心城市,实现一省与数省乃至全国的胜利,因而,红军的战略只能是进攻,作战形式也应当是阵地战而非带有游击性的运动战。尽管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早在1930年9月就被纠正,但对“左”倾错误的认识并不彻底,因而王明得以借批判“立三路线”之机,在共产国际帮助下,很快在中共中央占据统治地位并实行较之“立三路线”更“左”的路线。总体看,中共中央的军事战略自转变开始直至遵义会议前始终未发生根本变化。这也就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毛泽东领导红一方面军通过运动战取得了多次重大的胜利,但依然被排挤出了红军的领导岗位;周恩来、朱德等在取得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会被逐渐架空。
第二,遵义会议纠正了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确立了正确的军事路线,从而使党的军事战略同红军所遵循的积极防御战略方针和运动战的作战形式第一次高度统一起来。这其中,《遵义会议决议》第一次以中共中央决议的形式肯定积极防御(决战防御),并要求全党全军必须实现“从阵地战战术(短促突击)到运动战战术的坚决的迅速的转变”*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央档案馆编:《遵义会议文献》,24页。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毛泽东重新回到红军领导岗位更使这种转变拥有了坚强有力的领导。
第三,《遵义会议决议》的传达,对于统一全党全军的思想,彻底纠正在军事领导和指挥上所犯的错误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决议得到了坚决的贯彻落实,各主力红军由此彻底摆脱了“左”倾错误的束缚。遵义会议是红军战略战术的一个重要分水岭,以四渡赤水为开端,红军重新回到了积极防御和运动战的正确道路。
通观整个转变历程,“左”倾错误的干扰和影响始终挥之不去,正确与错误相互交织,斗争艰巨、复杂、激烈,从而使转变变得异常艰难曲折,跌宕起伏,在“付出了极大的牺牲,然后才从血的教训中纠正过来”*《毛泽东选集》,第2卷,550页。。从一定意义上讲,第一次军事战略转变的历程就是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走向成熟,进而走向独立自主领导中国革命和中国革命战争的历史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