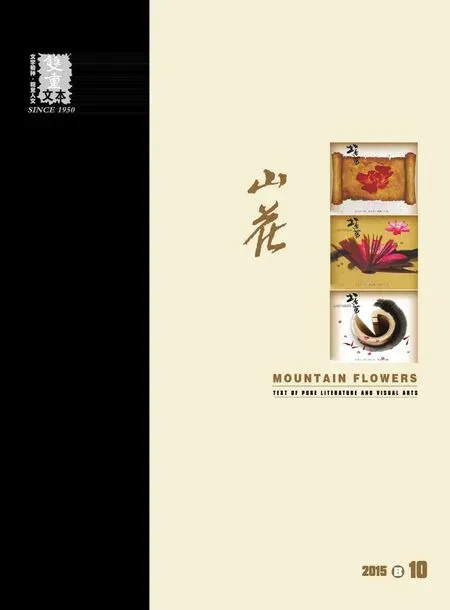阉割的主体:论田中禾长篇小说《父亲和她们》人物形象的文学史意义
郭浩波
阉割的主体:论田中禾长篇小说《父亲和她们》人物形象的文学史意义
郭浩波
《父亲和她们》讲述了一个20世纪40年代一男二女间产生的激情、爱情和亲情等相互纠葛错综的家庭离合故事。
本文认为,《父亲和她们》的审美价值或在于,它以个人的成长经验穿透历史思考①,保持并还原了对他(她)们的历史生存态的直觉认知;并且,基于此种特质,作品以其内涵有趣的症候揭示了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主体建构与意识形态之间存有紧张关系的历史根源和知识基础差异。
独特叙述结构的功能
根据父亲马文昌的表述,民团的拘捕使得他得以与母亲林春如有缘结识,并发展为后来的爱情恩怨故事。从叙述来看,父亲对此事也给予了颇有些宿命意味的自我认定。然而,对故事的理解要从马文昌拒婚、黎明出走这一情节开始。如果说在难童学校的请愿、揭露贪污的举动是马文昌遭民团拘捕的直接原因,那么其深层次原因则是他为民族命运、国家前途等这样的崇高理想所鼓动的满腔热忱使然。母亲林春如的自我叙述也同样表明,马文昌引起她的注意并非相貌出众或家庭出身,而是出自对他充满活力和激情的生活方式的认同。林春如受二哥嘱托接马文昌出狱,并且在随后的逃难中,二人内心一直在暗中相互打量。林春如外表锐利威严的冷冰冰态度,反倒让马文昌内心在捉摸无定中燃起了亲近她的欲望冲动;而马文昌这种为男女情感所促动的情态也为林春如敏锐地感知到了。两个年轻人由局促紧张到逐渐产生亲近的冲动,由疏离冷淡到产生好感的过程,也恰是他们在令人窒息的逃亡过程中所发生的全部故事,晦暗不明的凶险外部环境从两个方向拉近了这对漂泊年轻人的心灵距离。如果仅在故事层面理解这对青年男女之间的爱恨情仇,这不过是一个平淡无奇的爱情故事形象。而在叙述结构上看,这一家族秘史深层涌荡的时代激情,深切地暗示出一代知识分子自我主体建构的内在迷惘和分裂痛苦。
为着身后晦暗中的林春如,马文昌迎着日本人的刺刀走出去这一细节,促使林春如对父亲的爱情情感变得明朗、炽烈,这一英雄救美式的悲壮表演征服了林春如的爱情堡垒。但是,我们又不能将他们这种爱情情感仅只理解为纯粹风花雪月式的私性情感。这一点不难理解,联系到马文昌在西安从大哥林春长那里“截留”林春如,以及两人在《震旦报》上同时声明与旧式婚姻解除关系,再到两人不得不凄凄切切痛楚分开等系列情节,如若上升到结构层面,就明显察觉着文本叙述已经将事件或场景深植在以大哥林春长旧式家长势力的新旧对立语境之中,故事情节不过仅是对父亲这种由激情缔结爱情之能量的戏剧性考量:
男人的眼泪是征服女人、免除自己责任的最有力的武器。他的头脑重新又变得机灵、智慧,激情再次从他心底涌出来,变成无法遏制的冲动。“在封建势力面前我们绝不退缩!绝不回头!你说得对,这不是咱们两个人的事儿,这是一场革命!”
落下左肋隐痛毛病的林春如曾经无数次地默吟“forget”, 这样一个细节重复颇富意味地暗示了她对马文昌的爱既真切又忧惧。此中表明,林春如意识到了他们之间的爱情中隐藏有另一种情绪,即,非爱情的时代激情。这在林春如和马文昌两人一生恩怨情仇的发展中清晰地阐明了这一点。
实质上,故事情节所表现出来的推动力量,决定于更深层次的文本结构,即,林春如与马文昌的分手情节具有着文学史意义层面的结构效能,使得这两个形象在现代历史中呈现出来隐晦微妙的本质差异。从叙述发展来看,将一对革命婚恋青年分开,并以各自不同的个体经验表述同一历史时间,这就已经与中国现代文学中常见的革命青年婚恋形象,由个体到集体的成长叙述存有明显不同。之所以特别指出这一情节具有重要意义,是因为在林春如和马文昌等二人的个体经验表述与革命之间,明显呈现为两种截然不同的关系。如果说林春如试图将其追求理想自由的一腔激情融入革命集体而不成,无奈中与革命激情日渐疏离,并重返生命常态;那么马文昌就是另一种截然不同的尴尬境况,即,力图保持那个时代独特的革命激情却总是“漏洞百出”,尽管他能在日常性中获得一时庇护,但是他内心涌荡的革命激情最终还是令其“訇然倒下”。
综观现代文学,就激情与爱情的叙述,主流历史叙述中的“革命成长”叙述模式通常勾勒出一条“出走”、“爱情”、“革命”等这样一种人生历程,这大体是一条激情与爱情的融合、渗透,以至于前者压制后者,并最终融入革命集体的路径趋向。有关在爱情主题中掺杂“激情”并改变故事情节发展走向的“革命成长”经典作品,莫过于杨沫的《青春之歌》。我们在林道静先后结识三个优秀男子,并萌生感情的成长历程中不难发现,林道静接受卢嘉川那种“志同道合”式爱情的同时,却也在内心里比较了余永泽给她的“小资情调”的感情。林道静之所以最终下决心离开余永泽不是因为爱情已经湮灭,而是林道静体味到了在她与余永泽之间已经丧失了激情,而这种激情恰恰在江华或卢嘉川这种革命者那里可以重新得到。由着这种重新发现并体味到的激情,林道静一次又一次地想象着她与革命者江华的爱情;只不过因为江华的牺牲,林道静的爱情最后落在了同是革命者的卢嘉川身上。这种叙述或许能够给我们这样的一种启示,“革命成长”小说中的青年男女爱情始终是“小资情调”+“革命激情”、并且是后者逐渐居于支配地位的混合掺杂态的暧昧情感。
由是而言,林春如和马文昌“分手”这一情节,在结构上决定性地规范着两种不同的激情特质,即,追求理想自由的启蒙激情和作为世俗政治意识形态的革命激情。
阉割主体
从方德胜、肖芝兰,到江静、邹凡等,林春如在其生命历程的一次次“危机”中,直觉式地培养起基于个体经验的历史意识。然而作品并不着力于对事件的本质化叙述,而是更重视将诸多事件转化为个人经验,并以异于时代主流激进意识形态的弱观念,即,以存于多个个体经验中的诸如善良、正义、人性等内涵构筑起另一种时间长度②。
回溯中国近现代文学历史可以发现一种症候,无论新文学早期“问题小说”的观念性创作,还是创造社作家表现内在自我和时代使命之间存有的矛盾,及至左翼文学、解放区文艺创作中对人性与阶级或革命间关系日渐局促的意识形态化处置,诸多此类迹象表明,近现代时期以来,情感—理性—自由意志互相交织,形成了一个独特的逻辑框架,而启蒙价值与启蒙思想就是在这一中心框架中展开的③。然而,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民族抗战以及第二次国内战争等接续不断的政治动荡中,新文化运动最初的那种启蒙精神或情感价值也随着时代变化发生了变异,在胡风的政治抒情长诗《时间开始了》中我们不难体味到一种漫弥历史的澎湃激情,然而这种激情的主体形象已然面目全非,失去了启蒙精神所追求的主体创造性。
名字一改,再看从前,就像看另一个人,心里敞亮多了,像甩掉一个大包袱。穿上军装的一刹那,有种做梦的感觉,觉得自己已经脱胎换骨,变成另一个人。我打定了主意,以后除了林春生,林家人我谁也不认。
从变成革命军人曾超的那一刻起,说起家庭,我就会情不自禁地情绪激动,好像心底里有一堆干柴,见火就会轰一下燃烧起来,只能用最苛刻的词句才能表达我的憎恶。
在林春如内心里,把对群众讲话的方德胜形象与马文昌的对照比较这一细节中,能更有趣地表现她更名“曾超”后的切身体验,从正面直接表明了他们爱情中政治革命激情的支配地位。对林春如而言,她有意无意地将政委方德胜视为革命队伍里自我成长的监护者,特别是方德胜一席极富时代隐喻色彩的话语指引,令林春如切实地体验到自身在不断“被践踏”、“摧折”中的“茁壮成长”。更名“曾超”这一举动,准确生动地呈现了她力图通过“阶级分析”来划清与旧家庭关系的历史真实图景,在这种不断的自我叙述中完成其革命身份的加工塑造。
然而,方德胜与林春如之间的关系的实质是“看”与“被看”,即,审视关系。方德胜的一句话,即,革命队伍里“处处和别人不一样,这不好”的诚恳告诫,表明方德胜作为革命意识形态“大他者”的监护人是十分敏锐的。自林春如在“二壮参军”中对方德胜隐隐直觉到 “不满”以及就女人与革命的直觉认知,再到县图书馆长江静对林春如“带襻”方口布鞋等日常装束的注视,等等。这些经验表述表明,林春如的 “特别”在“大他者”严密注视下恰如她那把随身携带的“提琴”一样惹人注目。
林春如在作为“革命成长”监护者的方德胜注视中,总在内心里感觉着某种隐隐的“不安”和“自责”。 这不只是林春如于“大他者”的监查审视中自我直觉到的一种“畏怯”,准确地讲,这是一种依靠女性直觉经验到的一种“尴尬”。在林春如喟叹“这就是女人,这就是革命”时,她清楚意识到了女性与革命之间存有一种尴尬关系,但是此时的林春如肯定没有意识到意识形态“大他者”的另一副卑劣面孔。毫无例外,在马文昌本人也经验到了这样一个无可奈何的“尴尬”境况。当刘英用食指历点着马文昌的脑门儿历数他无法涤除的家族血缘历史“污点”的时候,伴随马文昌那种“脱胎换骨,重新做人”的政治诚恳态度,不也曾经令其直觉到一个在他人生某处“游荡的幽灵”④?
在林春如经验到的激情与革命之间复杂关系的每一次“危机”中,几乎无处不充斥着作为本体在场的“性”的隐约踪迹。作为监护者,无论是方德胜还是江静,都表现出对林春如主体性中存有的某些“特别”给予了劝告甚或警告;再有林春如在组织面前高举私性“铁红色纸卷”的愤怒抗击,等等。我们在其中总能发现女性(性)和革命(意识形态)之间存有的紧张关系。同样,在我们梳理马文昌这样一个具有坚定革命信仰的形象内涵时,同样能够发现,他居然在林春如、肖芝兰甚至刘英这三个女人之间总是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似乎他与女性之间的关系缔结只能依靠激情这样一种隐秘方式,比如与林春如的初识,以及与其学生姜卫东母亲的暧昧关系,有趣的是姜卫东这个形象,不正是作为马文昌流落异乡、在研究鱼塘养殖期间的激情式症候的“实存”之证明么。
女性与革命之间的这种尴尬关系,并非是一种偶然症候,是伴随现代性的出现而诞生的⑤。斯洛文尼亚学者齐泽克在论及笛卡尔主体存有自然属性与超验性的内在割裂时表示,主体所拥有的自然属性被贬低为同动物和环境一样,被视为开发的对象,前现代时期作为自然象征的女性在现代性发展中逐步丧失了其被保护或合法地位⑤。作为一项浩大的体制性工程,现代性执迷于追求普遍性本质,力求“消除差异”,现代性的法律秩序要求摆脱诸如此类的物质性快感。与此相关,齐泽克在论及拉康理论中“他者欲望”之谜时,提出的“小对体”概念认为,主体欲望恰是他者欲望,并且主体基于他者欲望进行了主体建构,这意味着主体在他者欲望的注视中同时也被剥夺了自我主体性;然而,出乎意料的是,他者欲望的隐秘对象并非是主体所幻想的欲望主体,其真相却是对欲望主体之原质,即对主体之自然事物基质的隐秘凝视,他者切实地从这一隐秘凝视中获得了卑劣的快感,这种隐秘快感所凭附的真实主体之自然事物基质就是“小对体”⑤。
由此而言,无论是政委方德胜,还是图书馆长江静,他们作为意识形态所驱遣的“大他者”监护着林春如的主体建构,要求林春如的主体性能够合乎要求地“消弭差异”,达至现代性法律所要求的中性基质。然而,吊诡的是,方德胜明显意识到了林春如主体性中存有的“特别”——比如“小资情调”,却还是顽执地对她表现出特有的热忱和诚恳;明知林春如“与别人不一样”,江静却仍然异乎热忱地为上级领导老梁和林春如牵线做媒,以致在组织对其私人生活肆意窥觑甚或戏弄中,林春如不得不以私性自然进行决绝式抗争,等等。这些无不表明,处于主体间性位置的林春如,在他者欲望的凝视或审查中,隐秘切实地察知着他者对其浸透具体“生活方式”等传统感性基质之自我真实主体的阉割,此种境况里的林春如无疑是在为其主体性进行着自觉或不自觉的自我保护或防御。
齐泽克就拉康理论中“小对体”概念的这一矛盾得出了一个悖论结论:“小对体”正是在丧失中显现的⑤。细读《父亲和她们》这部作品可以清晰勾勒出,林春如作为自我主体形象与 “大他者”之间存有的矛盾冲突过程:先是在林春如直觉地以“性”抗击他者、维护自我主体性的那一时刻,已经潜意识地触及了真实主体性之原质的存在,比如林春如与马文昌之间私自缔结的情爱关系,可视为对封建主体性窒息的反抗,再如林春如对政委方德胜内心产生的莫名其妙的“自责”与“回避”,其中已隐约可见她这种自我主体性觉知历程中充满的窘境与纠葛。有趣的是,“性”作为“小对体”的显现,恰是在这一内在冲突历程中得以昭示,恰是在“大他者”对自我主体之原质的剥夺、否定的时刻同时出现的,林春如手里高擎的那条女性私性“铁红色纸卷”不是切切实实地令双方真相都暴露无遗么。
恰在此一丧失与显现的同一时刻,他者的隐秘快感的卑劣脸孔才真正显现。
激情回归日常
当林春如对自我主体性遭受“阉割”有着知觉之时,也正是她将启蒙激情依照启蒙理性逻辑转向日常的开始。
在她深陷日常性生活窘境之时,“他们正在惩罚我”④。深夜里间隔着墙壁对邹凡的一番自我生命的忏悔式表白,充分展露了在其日常回归路途中,她的灵魂不断遭遇着那些在自我生命中曾经出现或经过的人们。我们虽然看到,迫于对儿子马长安前途的忧虑,她最终与老政委方德胜缔结婚姻。然而,林春如这种日常回归并非自陷“庸常”,只需要注意林春如对儿子马长安近乎严苛的教导方式,比如林春如送琴授谱给儿子马长安,完全可以视为对其深埋心底的启蒙激情接续的期望,再如她与青年诗人邹凡之间的诗性爱情萌生,特别是在林春如与肖芝兰两个女人围绕马长安这个孩子的反复“较量”中,颇能曲折显示出林春如内心蕴藏的启蒙激情依然存在。
有学者这样认为,“五四”的发生地点极具广场想象的象征意味,并在以后的革命成长小说中,通过反复叙述重构为一个想象的文化空间。这个空间为公共话语和公共意志所充斥,它不具有生活日常性和私人性,它不允许有任何疑虑、困顿和个人隐秘⑥。法国学者朱利安·本达就这种政治激情表示,它是近现代社会发展的历史产物,表现为人与他人的对立情感,民族热情、阶级热情和国家热情是其主要形式。个中秘密在于,现代社会的组织方式中有两种新添加的要素,即进化观念和历史法则,这样两个要素支配了人们的政治激情,即使他们的金钱欲、享乐欲望、家族之间的爱、虚荣心,等等,也不得不转移到自己从属的整体之中,因为他们认为,个人在自己所扎根的整体之中;这一整体的命令是强有力的,甚至连感觉都要维护命令的权威⑦。
如康德所言,激情或热忱不过是内在对外部刺激的反应,“激情或热忱不能思考”⑧。激情或受难一样,在日常中并非一定有意义,但是它们属主体性自我的自然事物真实。然而,在近现代历史叙述中,二者都被主流意识观念从不同角度、以不同方式赋予了沉重意义。卡西勒在其《启蒙哲学》中指出,在笛卡尔、高乃依等人认为,合乎理性的意志统治着一切感官欲求、欲望和激情,正是这种统治宣告了人的自由,表明了人的自由。但是,卡西勒认为这是斯多葛式的观念;到了18世纪则前进了一大步,不再认为情感纯粹是一种障碍,而是试图表明,它们是一切理智活动的原始的、不可或缺的动力和刺激③。
当然,就一部具体的文学作品而言,构成情节的具体事件或场景都是以偶然事件为材料的,并且这种偶然事件本身并不具有经验性质,它能够对人的经验意识发生作用,是因为时间进程中人类生活预定的和在文化方面起作用的一些导向使然。本质上,偶然仅只是一个时间的质,它之所以被历史本质化拒斥是因为偶然颠倒了期待的视角。反观林春如这个形象,她以属于个人体验的偶然时间,直觉地施加了对于追求历史本质化的主流意识形态观念的反作用力,其人生成长轨迹与本质化的宏大历史渐行渐远,随着文本叙述发展,呈现为一条努力保持或重建一个对于个人生活来说是必要的内部或外部环境秩序的人生轨迹。
《父亲和她们》这部作品,无论结构情节还是人物形象内涵,以及几个人物形象之间的作用关系,等等,其中无处不流贯着一种独特的直觉表述特质。这样一些非认知成分或因素在作品中通过第一人称的多重经验表述,于消解现代性的历史本质化压力的同时,又不动声色地避开了后现代主义针对意识形态化历史一贯的极端个人性诗意书写的暗礁。正是这些综合性特质铸就了《父亲和她们》这部作品的宁静质朴品格;更具文学史意义的是,作品以其异于传统革命成长叙事的叙述结构,功能性地展露出针对一代知识分子自我叙述中有关启蒙、激情、爱情和革命等相互间复杂关系的准确质疑和揭露力量,使得文本就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的反思以及自我反思具有着可资征信的史料价值。
注释:
①德国学者约恩·吕森指出:“历史思考绝不仅仅是思考,······那些非认知成分和因素同样需要得到足够的重视。”([德]约恩·吕森:《历史思考的新途径》,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版,第6页)
②“弱观念”是基于美国社会学者约翰·罗尔斯《正义论》中提出的“善的弱理论”,本文为着表述准确将其概念进行了转换。(参见[美]约翰·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11、312页。)
③张光芒:《论启蒙》,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77、101注释3页。
④田中禾:《父亲和她们》,作家出版社2010年版,第218、224、193页。
⑤[斯洛文尼亚]斯拉沃热·齐泽克:《幻想的瘟疫》,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3、14、9-13、15页。
⑥戴锦华:《思有涯》,山东友谊出版社2006年1月第1版,第39页。
⑦[法]朱利安·本达:《知识分子的背叛》,孙传钊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正文第1-17页。
⑧康德:《三大批判合集》,邓晓芒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14页。
2014年度河南省社科联、河南省经团联调研课题《文学艺术课堂教学与大学生人格塑造》,项目编号为SKL-2014-1939。
郭浩波(1972— ),男,河南洛阳人,郑州师范学院文学院讲师,主要从事现代文学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