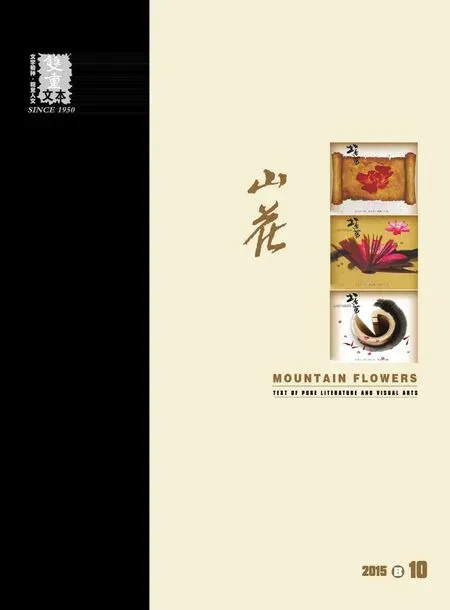面对诗歌的勇气与疑虑
周明全+霍俊明
周明全:霍兄现在大名鼎鼎,但对你的求学经历,似乎还有很多人不知,能否简单介绍一下?
霍俊明:一切都是虚名和浮尘。
现在,翻开我的求学档案!
小学一到四年级在村里的小学,五年级到六年级在隔壁村张庄子中心小学。那时上学都是徒步。1988年考上县城的重点中学,第一次出门住宿,那时患上了严重的思乡病。高中就不说了,那时整个校园都是随处可见的暴力斗殴场面,临毕业前喜欢上了一个同班女生。1996年大学中文系毕业后,我以优秀生(那时中文系168个人,一届只有四名优秀生)的身份到老家一个镇上高中当语文老师,期间诸多挫折辛苦就不提了。那时是实行分配,自己没有任何选择权,我又没有资本去走后门蝇营狗苟。
一个无比平常的黄昏,我对着办公室门外的巨大绒花树发呆——后来,这棵树被推土机给铲除了。那天,我做了一个决定,不能在这里混一辈子。1999年秋天顶着种种压力和学校领导的反对,我毅然停薪留职去河北师范大学准备考研。2000年我以初试和复试均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河北师范大学读中国现当代文学硕士研究生。那时还有一个黑色插曲。我的入学通知书迟迟没有收到,那时没有手机,连最时兴的BP机也买不起,家里也没有固定电话。一天学校快放学时,教导处接到一个电话说找我,我当时又不在学校,刚好我爱人从教导处经过接到了这个对我人生来说至关重要的电话。原来河北师大早就下了调档案的函给我所在的县教育局,可是河北师大一直没收到档案。第二天一早,我坐上一辆三轮车直奔县城教育局,一路上简直是惊险之极。到了教育局档案处,我强压怒火对工作人员直截了当说明来意。我半带威胁地说,如果我入不了学这个责任你们全部承担。最后拿到档案,厚厚的一摞。按照当时规定本人是不能见档案的。当时河北师大研究生处破例让我带着档案去石家庄,因为我是最后一个了。连夜坐上唐山开往石家庄的火车,车速慢,人又多,我挤到火车过道上。我有时不得不到火车的车厢接缝处,窗外是黑夜中依稀闪现的灯火。
上研究生时导师就是我心仪已久的著名先锋诗论家陈超先生,他是河北师大的一个传奇,甚至是一个神话。可以说,陈超是我真正意义上的诗歌启蒙老师。2002年夏天我研究生二年级的时候到秦皇岛的河北科技师范学院开始给中文系本科生上中国当代文学史和诗歌课。2003年研究生毕业前夕,一直犹豫是去工作还是考博,因为那时家里急需要我挣钱养家糊口,孩子已经五岁。最终我咬咬牙,考博。在2003年愚人节,从北京考完试回河北的火车上,我听到了张国荣跳楼自杀的消息,我也看到火车上有很多人已经戴上了口罩——那时还不知道一场突如其来甚于猛虎的SARS即将到来。最终我被南开大学和首都师范大学同时录取,我在如何选择上有些不知所措。最终,能够投到吴思敬老师门下,得力于陈超老师的指引。一个夜晚,陈超老师对我说:“俊明,既然走上了诗歌的道路就接着走下去吧!”我想当初的选择是正确的。当我在2003年夏天来到北京,穿过嘈杂的校园和吴思敬老师见面的时候,在泡桐树的巨大的浓荫下我看到他慈祥宽蔼的神情,我也找到了自己的诗歌和批评之路。而今位于北京西三环北路首都师范大学北一区西北角位置的四层白色楼房——“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已经成了一个诗歌“圣地”。如今,“吴门弟子”已经成为中国诗歌批评界的重要力量,我为自己成为其中一员而自豪。我曾经趁着酒兴对吴思敬先生袒露心声,说能够成为他的学生绝对是最正确的一次选择。如今吴思敬老师已经不再带新的研究生了,这让很多心仪诗歌批评的人心存遗憾。有很多人惊讶于我选择了两位中国诗歌界最具重要性的诗歌批评大家,硕导陈超,博导吴思敬,这确实是我莫大的荣幸。2006年博士毕业到北京教育学院中文系工作,与王家新有过短暂的同事之缘,他一年后调入中国人民大学。2010年6月我到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跟随李怡老师读博士后。2013年初春调入中国作协工作至今。
周明全:你更愿意别人称呼你诗人还是评论家?和你第一次接触的时候,我有两个彼此关联的印象:第一,你是一个性情中人,感情充沛,敏感也脆弱。第二,你真诚得可爱,一边说着不喝酒,一边随着情绪的潮涨一杯接一杯地下肚。让自己“痛并快乐着”。我一直支持古人“文如其人”的观点,认为一个人的性情和他的文章趣味是连体的。我读你的批评也是觉得非常有个性特征,尤其喜欢看你论著的前言后语。呵呵!说到这里,我心里立刻响起一个颇为严厉的声音:“研究要客观!”但到底有多少人喜欢那些格式规范却又冷冰冰的话语方式!批评或是研究能不能有个人趣味,是否还讲究文章之道,我想请你谈谈你的想法。
霍俊明:我几乎在很多场合滴酒不沾,但我也会连续几天喝倒在酒桌上。我每年为数不多的喝酒都是因为最好的朋友,包括我的导师陈超、吴思敬以及我的一些诗友。我不善饮,但有时候属于酒胆惊人和临场发挥那一拨儿。我一喝酒就上脸,满脸通红,但我想那时的我是最真实的。
我曾在一份简历中排序如下:诗人、诗评家、博士。这一排序显然是我自己一厢情愿的决定,与公众意志没有任何关系。博士排在三者的最后是因为在我看来博士更像是一种身份和知识的尺度,同时更是稻粱谋的手段,它在今天显得过于普通和功利化了,所以我把它排在最后一位。而之所以将诗人放在第一位显然表达了我对“诗人”的绝对尊重,还有我对自己诗歌写作和批评的认识。显然我的诗歌写作是业余的,和那些具有多重才华和重要性的写诗者相比较有着巨大的差异,但是我知道诗歌写作对于我的诗歌批评意味着什么——很多的批评家的文字自身非常苦涩乏味,成了学究和掉书袋,而我更想做到批评文字的准确、生动和个人化,这可能也得到了一部分诗人和批评家的认可。而这种行文的激情、生动、尖锐和个人化正是来自于诗歌写作时对语言能力的控制与提高。批评和写作一样都有自身的命运,而“诗人批评家”这是我一生都必定要追寻的。
乔治·斯坦纳曾不无悲观地指认“文学批评”往往是短命的,“文学批评和文学阐释的著述生命有限,难以长久流传……大多数研究著述属于过眼云烟,学术著作和学术期刊文章尤其如此。在鉴赏情趣、评价标准和使用术语进行辩论的历史上,这样的文学研究著述或多或少代表某个具体的时段。用不了多久,它们有的在繁冗的脚注中找到了葬身之所,有的待在图书馆书架上悄无声息地搜集尘埃。”艾略特将批评家分为四类,而他最为倾心的就是“诗人批评家”——“我们不妨说,他是写过一些文学评论的诗人。要归入这一类的批评家,有一个条件。那就是,他的名气主要来自他的诗歌,但他的评论之所以有价值,不是因为有助于理解他本人的诗歌,而是有其自身的价值”。对于我来说,近年来我越来越反感于“掉书袋”和“理论癖”的批评方式。如果说把批评也作为一种创造性的文体,那么“诗人批评家”就是最理想的了。因为这种特殊性的“价值”来自于诗性直觉、会心而精准地对诗歌这一特殊文体语言特质的感受力以及诗性的持续发现能力。“诗人批评家”使得直觉和学养获得平衡,感性和理性达成一致,在诗歌写作和诗歌批评之间不断交互、往返和互相求证。这必然是一个“双手”写作的人。这种带有互补性质的写作无疑带有“问题”的重要性和“说话”的有效性。严谨、精密、深入、尖锐的理论思辨能力与会心、精妙的感受力和细读能力的完美结合使得陈超的诗论既有理论深度又能带来阅读的欢欣。我希望有一天,我能成为“诗人批评家”中的一员。在2006年写作《尴尬的一代》时,我就有意尝试这种“诗人批评”的写作方式。这本书让人印象深刻的是其中酣畅的散文化的、“激情”化的言说方式。据说有一个70后女性诗人是用一个晚上读完整本书的,当时她正发着高烧,可她后来说拿起这本书之后就不想再放下了,她觉得书中燃烧的情绪让她体会到久违的文学批评的热度和体温,同时也因为一代人的共同情感、体验甚至是写作生活让她重新在往日和现实中获得了感动。
周明全:在诗歌界,我常常听到诗人抱怨评论家不读诗,不懂诗,评论家抱怨诗人不懂思想和理论,诗人和诗歌评论家齐声抱怨文学大势已去,诗歌成了圈内游戏,但又有人引用古今中外证据,证明精英化的诗歌都是曲高和寡,书都卖得很少的。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霍俊明:可以肯定,有一部分评论家是不读诗的,有一部分诗歌评论家是不懂诗歌的。这些评论家一个个更像是站在舞台上的魔术师,手里拿着那顶黑色礼帽。他们用各种眼花缭乱又看似高深莫测的专业伎俩不断掏出花样翻新的东西。但最终,那顶帽子里却空无一物。而不变的仍是大众对诗歌的不解和疑问——有好诗吗?有好诗人吗?为什么诗歌读不懂?大众喜欢的诗你们专业诗人为什么总是不屑一顾满眼鄙夷?
当大众和业内人士如此热议诗歌这种“边缘文体”,需要审慎分析,不要急于肯定或否定。面对缺乏“共识”的激辩,面对公信力和评判标准缺失的新诗,亟须建立诗歌和诗人的尊严,这既是美学的问题又是历史的问题。在一个精神涣散和阅读碎片化的时代,已很难有文学作为整体性的全民文化事件被狂欢化地热议与评骘,但诗歌却是例外。引爆人们眼球,饱受各种争议,不断被推到风口浪尖的恰恰是诗歌和诗人。无论诗歌被业内指认为多么繁荣和具有重要性,总会有为数众多的人对诗歌予以批评、取笑和无端指责、攻讦。这就是“新诗”的“原罪”,因为从没有类似情况发生在古典诗词那里。中国新诗一直没有权威的“立法者”出现。即使从美学上谈论同一首诗,也往往是歧义纷生,这又进一步加深了普通读者对诗歌和评论标准的疑问。甚至在特殊的社会文化语境之下大众对诗歌的解读又形成了集体性的道德判断。多年来人们已经习惯了“诗歌”与“大众”之间的平行或天然的疏离关系,诗人不在“理想国”之内。但是一旦诗歌和“大众”发生关联往往就是作为诗歌噱头、娱乐事件、新闻爆点。这又进一步都使得诗歌在公众那里缺乏公信力。对于中国文学场域来说,很多时候诗歌是被置放于社会公德和民众伦理评判的天平上。而公共生活、个人生活以及写作的精神生活给我们提供的就是一个常说常新的话题——诗人如何站在生活的面前?
这就是“诗歌”与“公众”的话题。诗人似乎更喜欢自说自话,一直是朋友间的趣味。所以会有很多人站出来理直气壮地说“诗歌就是献给无限的少数人”。诗歌就是精英的事业。这也没错。诗歌有文体自身的特殊性,这是事实。诗歌不被一部分人理解和接受也纯属正常。如果搞当年“大跃进”和“文革”全民写诗的运动,才更可笑。但是,如果把诗歌的晦涩、怪癖、非介入性和一些缺点都拿“精英”来作为盾牌也显得非常恶心。
周明全:今天,什么样的诗才是你心目中的好诗呢?
霍俊明:好诗的标准是什么?有没有一个既被专业人士认同又能够在最大面积的受众那里产生共识的诗歌评价标准?换言之,被指认为文学性要求最高又最为私密的诗歌如何能够有效地被社会公众认可?甚至,被指认为“天才事业”的“小众”、“精英”诗歌有没有必要“取悦”于更多的读者?这也一直是我的疑虑。
中国现代汉语诗坛一直没有权威的“立法者”出现,其建立的法度能够被更多人接受与认可。既然连专业人士内部都没有共识又何谈诗歌写作和诗歌评价标准的公信力?这既在于完善现代汉语诗歌传统的自身建构尚需时日(比如对好诗的积累和经典化工作,对专业和一般诗人审美标准的培养和提高),又在于一些诗歌批评家和研究者们的话语幻觉。
关于好诗的标准,不同流派、风格的诗人那里自然会有不同的说法,标准必然涉及新诗自身的“传统”建设。显然,这仍然是一个继续的过程。好诗在不同阅读者那里也会有不同的标准,即使是同一首诗,在普通读者那里和专业读者那里阅读感受也不同,即使在专业内部也是聚讼纷纭。说到底,好诗又是具有超越时空的精神膂力的。无论是“轻小”的诗,还是“精神体量庞大”的诗,都应该是“真实”之诗。这是语言的真实,修辞的真实,历史的真实,而非虚伪、矫情、夸张、代言和工具。
周明全:当下批评失语、批评失效一直是媒体的热门话题,你认为是这样吗?好的文学批评应该具备什么样的品质?好的批评家,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质?
霍俊明:批评的失语和失效肯定是存在的,这是一个客观事实。可另外一个吊诡的现象却是,在各种平台有那么多的人在叽叽喳喳热闹非凡地发议论。
批评家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改变大众对某位诗人、对过去某个时期文学的兴趣?批评家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他的时代读者的趣味?艾略特的答案显得很是悲观:几乎没有。而当下诗歌写作和诗歌批评出现了“两张皮”的现象。一方面是乡村写作和城市写作的等量齐观,关注现实题材的诗歌大量涌现,并引起社会广泛的认知度,但也因为缺乏对现实的深入理解和诗歌的转化能力而导致类型、平面和空泛。另一方面是诗歌批评和理论研究的自说自话,缺乏对当下诗歌写作现象的深入和透彻的梳理、反思和总结,空泛地谈论诗歌美学,套用西方文论,对诗歌历史的掉书袋式的研究。
我认为一个好的评论家应该在一个时代具有重要性,甚至这种重要性能够超越时代而成为有效的共时体。
而说到素质,我认为一个最重要的标准是应该具有“求真意志”。这既是关于诗学修辞学的,又是关乎诗歌与世界、时代和生存关系的,也即同时具有“美学的重要性”和“历史的有效性”。而能够同时做到这两点,显然是太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