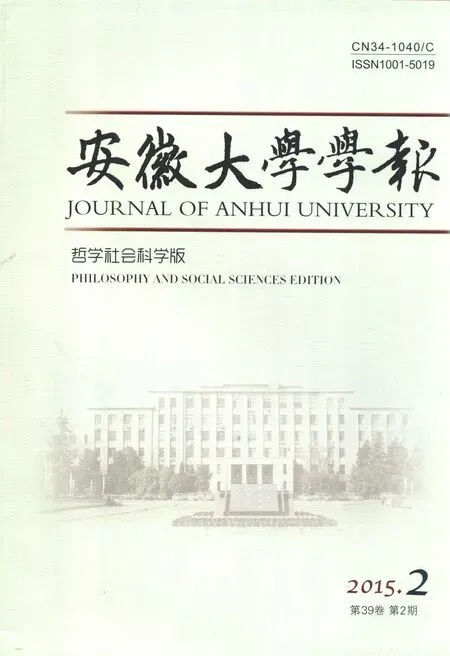从“重生”到“为我”
——杨朱学说的异化历程
石 超
从“重生”到“为我”
——杨朱学说的异化历程
石超
摘要:“不拔一毛”“不利天下”的口号由杨朱首次提出。其虽以“重生”为鹄的,却亦隐含“为我”之倾向。后者在杨朱后学的强调与阐发下,异化出以“纵欲为我”说为特征的享乐主义。该过程以一段魏牟与詹何之间的对话为开端,经由《庄子·盗跖》篇的系统阐发,最终完成于《列子·杨朱》篇。因此,对杨朱后学“纵欲为我”说之发展历程的批判性考察,将有助于澄清学界对杨朱思想的长期误读,进而为全面、深入展开先秦、魏晋道家哲学史的研究工作奠定良好的基础。
关键词:杨朱;魏牟;重生;为我;纵欲;道家
杨朱是先秦道家的重要代表,但他在思想史上的作用长期遭到忽视乃至曲解。这集中表现在,对杨朱思想的把握一概以“为我”而论。这种认识滥觞于孟子,沿袭于中古,盖棺于近代,相因成习,几成定局*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论断出自朱熹与胡适。朱熹曰:“取为我者,仅足于为我而已,不及为人也。”(《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357页)胡适说:“杨朱的‘为我主义’是有旁证的(如孟子所说)”,“杨朱的人生哲学只是一种极端的‘为我主义’”,“凡是极端为我的人,没有一个不抱悲观的”(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耿志云导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26页、128页、129页)。两人皆以“为我”二字概括杨朱之思想,并将其引至“自私自利”“悲观厌世”之结论。对此,现代学者在论及杨朱思想时,虽能注意到其“轻物重生”“贵己”等积极面相,但在行文中,却仍然不自觉地使用具有明显价值取向的“为我”二字作为概括。如吴泽的《杨朱思想的演化与学派问题》(《学术月刊》1957年第8期)、焦国成的《杨朱学派“为我主义”辨析》(《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89第6期)、李纯一的《杨朱学派“为我”学说和音乐思想》(《中国音乐学》1992年第2期)、连劭名的《杨朱学说新考》(《理论学刊》2010年第1期)等。这说明时至今日学界对于如何界定杨朱思想这一问题,仍不能达成共识。原因在于对杨朱本人之思想与杨朱后学之思想的划分未能给予应有的关注。。然而,我们不禁要问,这一饱受诟病的学说,何以能在墨子之后、孟子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成为“盈天下”之“显学”?为厘清以上疑问,并为杨朱思想正名,笔者试图重新梳理杨朱学说从“重生”到“为我”的流变历程。
一、杨朱“重生”不“为我”
文献不足,是研究杨朱思想的最大困难。因此,通过他人之口和别派之书,以及靠零星记载来拼合、梳理杨朱思想,就是我们不得不采用的方法。魏晋以前,明确记载杨朱其人,并论及杨朱思想的可靠文献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孟子》和《韩非子》:孟子称杨朱“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清)焦循:《孟子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915页。;韩非称其“重生”,“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胫一毛”*(清)王先慎:《韩非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459页。。对此,冯友兰曾做过精彩的分析:“大概杨朱一派有‘不拔一毛’、‘不利天下’的口号。这个口号可能有两个解释。一个是,只要杨朱肯拔他身上一根毛,他就可以享受世界上最大的利益,这样,他还是不干。另一个是,只要杨朱肯拔他身上一根毛,全世界就可以都受到利益,这样,杨朱还是不干。前者是韩非所说的解释,是‘轻物重生’的一个极端的例;后者是孟轲所说的解释,是‘为我’的一个极端的例。两个解释可能都是正确的,各说明杨朱的思想的一个方面。”*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72页。显然,冯友兰已经敏锐地察觉到二人的对立。但他试图把两种对立的概括揉成一体,使之成为杨朱思想的两个方面。窃以为,这种解释失之草率。与其说“重生”和“为我”各是杨朱思想的一个方面,毋宁说二者更像是在杨朱之后出现的两种对其思想的不同解读方式。而杨朱本人的思想中并无此分歧。况且,《吕氏春秋》称“阳(杨)生贵己”*许维遹:《吕氏春秋集释》,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467页。,《淮南子》称杨朱“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何宁:《淮南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940页。,都与韩非“轻物重生”的概括保持一致,而与孟子称其“为我”相抵牾。除此以外,《庄子·骈拇》篇更将杨朱及其后学的形象描绘为辩者,且斥其所论多为“无用之言”*(清)郭庆藩:《庄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314页。。以上种种,均显示杨朱学派之思想主旨及其流变过程是非常复杂的问题,简单化的处理,会使我们错过很多有益的发现。
不难看出,当时学界对杨朱思想的概括不外乎“重生”与“为我”,二者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又集中体现于“生”与“我”二字。《说文》曰:“生,进也。象草木生出土上。”*(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276页。“生”含有生命、存活之意象,是一种与“死”相对的生命力发生作用、展开活动之过程。同时,“生”又常常与“性”相通,指人的先天本性。与“性”相对的则是“情”与“欲”。荀子曰:“性者,天之就也;情者,性之质也;欲者,情之应也。”*(清)王先谦:《荀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428页。一方面,“情”“欲”皆根源于“性”,而“性”则是“天”所赋予,正所谓“性自命出,命自天降”,而“情生于性”*李零:《郭店楚简校读记》,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05页。。另一方面,由“性”到“情”,再到“欲”,则是从一般到具体,再到特殊的个性化展开。就“性”而言,人人相同。“性”接于物,表现为情,具体体现为“喜、怒、哀、惧、爱、恶、欲”。在这些感于物而自然触发的诸情之中,“欲”又特别含有“以私心占有”之意象。当“性”经过“情”而表现为“欲”,一种极端个人化的情绪体验便出现,而后者常常唯“我”独晓,难与外人道。可见,“生”与“我”相差甚远,虽有一定的内在联系,但在实际运用时,却主要表现为两种相反的意象。换言之,“我”与“生(性)”相比,蕴含更多的“占有之意味”,而这种不同恰恰是被常识所忽视的。

基于以上对“我”字的分析,我们就可以重新审视孟子用“为我”说概括杨朱思想的用意。结合开篇提到的另外三种对杨朱思想的概括*分别是“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轻物重生”以及“贵己”。,不难看出:如果“为我”说包含“我”字“身、垂、施、戈、杀”的全部意象,那么其他三种则至多包含有“身、垂”之两种意象。如“贵己”“重生”“全性保真”,都只是就身体之完全、维持和已有空间的不受侵犯而言。而“轻物”“不以物累形”则是对“施、戈、杀”所表达的占有、扩张,以及毁灭“非我”之意味的直接否定。而且,阳(杨)子还说过这样的话:“行贤而去自贤之心,安往而不爱哉!”陈鼓应译作:“行为良善而能去除自我炫耀的信念,到哪里会不受喜爱呢!”*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564页。显然,杨朱本人是明确主张以反求自身且谦虚自隐的方式来实现“贵己重生”的。这种思想与“扩张本我,武力外求”的“为我”说,相去甚远。所以,“为我”说是对杨朱思想的曲解,是对其思想薄弱环节的刻意放大,甚至还可能是将对他人的批评,错误地归于杨朱名下。
因此,以“为我”概括杨朱及其后学之思想,是孟子有意为之,并不是对杨朱本人思想的客观反映。当然,孟子自己也承认他的“好辩”是“不得已”*(清)焦循:《孟子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461页。。能够取得辩论之胜利,将论敌论点中容易导致极端错误的基点进行放大,亦为辩论中常常使用的技巧。这更能说明,杨朱“重生”不“为我”。
二、魏牟“重伤”不“自胜”
孟子对杨朱的曲解既已澄清,另一问题接踵而至:既然是一种曲解,为什么会在历史上留下如此巨大的影响,以至于后人径自将“为我”说的帽子扣给杨朱?不可否认,在杨朱“不拔一毛”“不利天下”的口号中,确可导出“为我”之说。在战国,大致与孟子相当或略早的时代,也确有一大批人根据这一点而大肆宣扬各种“为我”论,这些言论的逻辑终点,就是“纵欲为我”的极端主张。而且,他们往往还将自己的论证归于杨朱,这也是致使孟子误以为杨朱本人即执此观点的原因之一。其实,最早主张“纵欲为我”的代表人物当为它嚣和魏牟。荀子曰:“纵情性,安恣睢,禽兽行,不足以合文通治。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众。是它嚣、魏牟也。”*(清)王先谦:《荀子集解》,第91页。因此,孟子的批判矛头,应当指向它嚣与魏牟,或其追随者才对*按,关于它嚣、魏牟两人,杨倞注曰:“它嚣,未详何代人。”又,“牟,魏公子,封于中山,《汉书·艺文志》道家有《公子牟》四篇。班固曰:‘先庄子,庄子称之。’”(王先谦:《荀子集解》,第91页)又张湛注《列子·仲尼》篇谓魏牟为(魏)“文侯子”(杨伯峻:《列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137页)。《吕氏春秋·审为》高注也说:“子牟,魏公子也,作书四篇。魏伐得中山,公以邑子牟,因曰中山公子牟也。”(许维遹:《吕氏春秋集释》,第592页)张舜徽先生的解释对我们很有启发:“其人在周末,放任自适,与蒙庄为近;而又通于名理,能以善辩胜人者也。”(张舜徽:《汉书艺文志通释》,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第141页)据此可知,魏牟的主要活动时间要略早于孟子和庄子,荀子谓其“纵情性,安恣睢”“放任自适”的理论主张和行为,与孟子所批评的“为我”说相似;其“通于名理”“善辩”的论学方式,与庄子所讥刺的“累瓦结绳窜句棰辞”(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第254页)的形象吻合。。可惜,《汉志》所录《公子牟》四篇早佚,虽还有马国翰辑《公子牟子》一篇*(清)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扬州:广陵书社,2004年,第2688页。,但此篇大部分与《汉志》所录不符,这不仅体现在二者时代不合,就它们的言论、思想而言,也存在明显对立。
但据笔者考察,马氏所辑材料中,仍有一条值得信赖*按,《辑佚书》首先收录《庄子·秋水》篇中魏牟与公孙龙的一场辩论。在这则故事中,魏牟作为庄子学说的捍卫者出现。这大概是庄子学派借“魏牟”之口表达自己思想的作品,其中,虽然鲜明地刻画出魏牟的辩者形象,但其所论内容与杨朱学派无关,且时代不早于庄子,所以不应被视为《汉志·公子牟》的轶文。与此条类似,但未收入《辑佚书》的还有《列子·仲尼》篇的一段材料。在这则故事里,与公子牟辩论的是乐正子舆。与《秋水》篇的记载相反,公子牟在此又以公孙龙的坚定追随者之形象出现(见杨伯峻《列子集释》,第137页)。面对这种互相矛盾的记载,以及时代上的明显不符,我们只能同时将两条材料舍弃。其次是《战国策·赵策三》“平原君谓平阳君曰”章。这里的公子牟与范雎同时,且教导范雎要贵而不骄,以防“死亡”。这与“纵情性,安恣睢”的主张截然相反。此公子牟大概不会是荀子所批判的魏牟,主要原因同样是其时代太晚。又《赵策三》“建信君贵于赵”章,说魏牟与赵悼襄王同时,且两人相见于秦始皇三年,谈论的是治国之道,主张用人唯才(见何建章《战国策注释》,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732~724页;第750~751页)。这些言论与道家思想距离较远,亦与《汉志》所载《公子牟》四篇属道家的情况不洽,且时代亦远远晚于庄子。故此二条同样不能被当作《公子牟》之佚文。,此条同时见于《庄子·让王》《吕氏春秋·审为》《淮南子·道应训》,以及《文子·下德》。本文所引,以《让王》为主,其文曰:“中山公子牟谓瞻(詹)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阙之下,奈何?’瞻子曰:‘重生。重生则利轻。’中山公子牟曰:‘虽知之,未能自胜也。’瞻子曰:‘不能自胜则从(纵),神无恶乎?不能自胜而强不从(纵)者,此之谓重伤。重伤之人,无寿类矣!’魏牟,万乘之公子也,其隐岩穴也,难为于布衣之士,虽未至乎道,可谓有其意矣!”*(清)郭庆藩:《庄子集释》,第979~981页。其中,涉及“重生轻利”“不能自胜则从(纵)”等概念,与杨朱思想主旨密切相关。而此“中山公子牟”应当就是荀子所谓魏牟。
值得注意的是《让王》篇对魏牟的评价:“魏牟,万乘之公子也,其隐岩穴也,难为于布衣之士,虽未至乎道,可谓有其意矣!”成疏曰:“夫大国王孙,生而荣贵,遂能岩栖谷隐,身履艰辛,虽未阶乎玄道,而有清高之志,足以激贪励俗也。”*(清)郭庆藩:《庄子集释》,第981页。可见,与孟子、荀子径自斥之为“禽兽”不同,庄子学派对于魏牟多有称许之意。以此为前提,便可深入体会魏牟“重伤”之苦。其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阙之下,奈何?”詹子答:“重生。重生则利轻。”何谓重生?许慎注曰“重己之性也”*按,原文本为:“重生,己之性也。”何宁撰《集释》引吴承仕曰:“此文应作‘重生,重己之性也。’”(何宁:《淮南子集释》,第849页)所说诚是,今从之。。詹子亦即要魏牟“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能如此,自然视“利”为“轻”。显然,詹何正是以杨朱之基本主张开导魏牟。但对于同样熟知杨朱学说的魏牟来说,这根本无益于解决其困惑。因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他知不知道“轻物重生”之益处;相反,其所以困惑,正在于他“知之”而“未能自胜”。换言之,魏牟的情况与常人累于外物而导致身体、心性之伤害的情形不同,他明知“重生则利轻”,但由于特殊的身份和过多的牵绊,导致他不能将其所知贯彻于行动。因此,他不仅身伤于物,而且神伤于虑,即詹何所谓“重伤”。对此,高诱解曰:“‘重’读‘复重’之‘重’。”*许维遹:《吕氏春秋集释》,第592页。陈奇猷引俞樾曰:“‘重伤’犹再伤也。不能自胜则已伤矣,又强制之而不使纵,是再伤也,故曰‘此之谓重伤’。”*陈奇猷:《吕氏春秋新校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472页。面对魏牟所遭受的身心双重伤害,詹何心虽怜之,但爱莫能助,于是说出“不能自胜则从(纵),神无恶乎”的话。此话意即,既然不可抛弃外在之物,阻止身伤于物,便无须因此而勉强。不勉强,就不会在遭受物伤的同时,还要忍受“神”伤。于是,“纵欲”说竟是在一种极为特殊的情境下,首次并被迫由詹子提出。
可见,詹何所言,自有前提。他绝非主张一切人在一切情况下都应“纵欲”,而是要人们在“物伤”不可去除的情况下,毋再强禁其欲而导致神伤。就詹子本人而言,其思想无疑倾向于“贵己重生”。但魏牟如何,则由于文献不足之故,无法论定。若荀子对魏牟的评价属实,那他必然是在这次谈话之后,即放弃“贵己重生”之信仰,而堕落成“纵情性”“安恣睢”之“享乐主义者”或“纵欲主义者”。果真如此,那么魏牟绝对可以被视为道家“纵欲为我”派之开创者。即便荀子言过其实,魏牟并未堕落,“纵欲为我”说的“种子”也必将因为此次谈话而播出。总之,无论如何推断,魏牟都是使得杨朱思想从“贵己重生”向“纵欲为我”演变、异化的关键人物。
三、纵欲者,惧死且厌生
魏牟之后,“纵欲为我”说得到极大的宣扬与发展,其体系化的理论建构工作落实于文本,即是《庄子·盗跖》篇中关于孔子与盗跖的一则寓言。这篇文献的来源问题,历来是学者争议的焦点。细读其文,归其旨趣,可以发现,“纵欲为我”说竟是贯穿该篇文献的核心思想,恰可看做是该派学者借盗跖之口来宣扬自己主张的寓言作品。此作品经后代学者的整理,遂加入《庄子》一书,并借此得以传世*对于该篇文献的作者、成书时代,以及流传过程,廖名春先生在其《出土简帛丛考》一书中,有过详备的论述(参见廖名春《出土简帛丛考》,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廖先生认为该篇文献乃为庄子后学所作,对此,或许仍有可以讨论的余地。重要的是,无论该篇文献是否是庄子学派的作品,都不能否定其受“纵欲为我”说之深刻影响。换言之,即便《盗跖》篇确为庄子后学之作品,也一定是庄子后学中颇受“纵欲为我”说影响的弟子之作品。无论哪种情况,都不会影响后文的分析与结论。,又因为其思想风格和主旨与庄子学派主体思想略有差异,而被归于“杂篇”。
具体而言,《盗跖》篇在“纵欲为我”这条思想主线的贯穿下,分别提出离家、弃国、不以天下为利的人生观,圣贤可羞、忠臣不足贵的价值观,以及人生苦短、及时纵欲的享乐观。就文笔而论,该篇文献脉络清晰,层次分明。首先,文章开篇交代“孔子与柳下季为友”,而“柳下季之弟,名曰盗跖”。接着文章描写盗跖横行天下、“万民苦之”的恶行。然后是孔子与柳下季的一段对话,孔子责之曰:“若父不能诏其子,兄不能教其弟,则无贵父子兄弟之亲矣”,并表示自己“请为先生往说之”;柳下季则劝阻孔子“必无往”,一则因为盗跖“不听父之诏”“不受兄之教”,二则因其“为人也,心如涌泉,意如飘风,强足以距敌,辩足以饰非,顺其心则喜,逆其心则怒,易辱人以言”,即便以孔子之“辩”,亦将无可“奈之何”*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第825页。。这段描写,为后文盗跖雄辩、强横的形象做出铺垫,也点出纵欲为我派无视父子、兄弟等人伦而离家、弃国的人生观。第二段,描写孔子在颜回、子贡的陪同下见到盗跖。孔子以盗跖有“三德”而奉承之,并以立之为诸侯之利而诱导之。可是,盗跖却对孔子一通奚落,并狂言道:“城之大者,莫大乎天下矣。尧舜有天下,子孙无置锥之地;汤武立为天子,而后世绝灭;非以其利大故邪?”*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第827页。显然,这样的思想、言论,是对杨朱“不拔一毛”“不利天下”之口号的继承。但同样明显的,是《盗跖》篇所谓“不以天下为利”,乃是建立在背弃人伦、自私自利的基础之上的。换言之,他们口中的“不以天下为利”,实际是不愿以“利天下”之苦而损害己身之利的“自私自利”主义。这种解读,明显是对杨朱学说的扭曲与异化。第三段,借盗跖之口,重点论述圣贤可羞、忠臣不足贵的价值观。其文曰:“黄帝……与蚩尤战……流血百里。尧舜作,立群臣,汤放其主,武王杀纣。自是以后,以强陵弱,以众暴寡。汤武以来,皆乱人之徒也。”又说“此六子者……其行乃甚可羞也”。这是以圣王为天下始乱之所由。接着,又历举伯夷、叔齐、鲍焦、申徒狄、介子推、尾生、王子比干,以及伍子胥,认为古之贤士、忠臣“无异于磔犬流豕操瓢而乞者”,“卒为天下笑”。对于忠、信等美德,已近乎诋毁和谩骂*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第827~828页。。最后,《盗跖》篇的作者终于将其“人生当以纵欲为务”的根本观点抛出。其文曰:“今吾告子以人之情,目欲视色,耳欲听声,口欲察味,志气欲盈。人上寿百岁,中寿八十,下寿六十,除病瘐死丧忧患,其中开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过四五日而已矣。天与地无穷,人死者有时,操有时之具而托于无穷之间,忽然无异骐骥之驰过隙也。不能说其志意,养其寿命者,皆非通道者也。”*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第828~829页。如果说,当年魏牟借詹何之口抛出“不能自胜则纵之”的言论时,还有些支支吾吾、难于启齿的话,在《盗跖》篇中,这种思想倾向则已完全异化为对纵欲主义、享乐主义的赤裸裸的宣扬,其对杨朱思想的歪曲与误读,可谓非常清楚了。总之,“纵欲为我”派的理论在《庄子·盗跖》篇中初次得到系统的阐述。
在此之后,随着历史车轮的推进与时代思潮的转向,“纵欲为我”的理论曾一度失去市场,于秦汉时代几乎销声匿迹。然而,汉帝国的衰落与解体,又一次导致类似于战国时代群雄割据的政治格局。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下,“纵欲为我”派的思想再次死灰复燃。这一次,他们径自举起杨朱的招牌,以更新、更雄辩的姿态再次登上历史舞台。而成书于魏晋时代的《列子·杨朱》篇,则是其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文本化。此篇议论无论篇幅和理论的精致,都远远超过前人,真正做到“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进而“足以欺惑愚众”。
该派学者在论证“纵欲”有理时,首先提出“万物所异者生也,所同者死也”的人生观。具体讲,人生而“有贤愚、贵贱”,此为“所异”者;但无论贤愚、贵贱,一朝赴死,则同归于“臭腐、消灭”,此为“所同”者。而且,无论生死、贤愚、贵贱、臭腐、消灭,都“非所能也”*按,严北溟、严捷撰《译注》曰:“非所能:不是自己所能作主的。能,指主观能力的作用。”(严北溟、严捷:《列子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81页),“生非所(能)生,死非所(能)死,贤非所(能)贤,愚非所(能)愚,贵非所(能)贵,贱非所(能)贱”*按,此句诸“能”字据杨伯峻《集释》补,所说甚是,今从之(杨伯峻撰:《列子集释》,第221页)。。面对命中注定的“同归于死”,以及人们改变此命运的力不从心,悲观的情绪弥漫在他们的思想中。人生变为一场注定走向死亡的无期徒刑,这场徒刑或长或短、或荣或辱,“十年亦死,百年亦死。仁圣亦死,凶愚亦死。生则尧舜,死则腐骨;生则桀纣,死则腐骨”。同是苦刑,长短何异?荣辱何异?“腐骨一矣”!*杨伯峻:《列子集释》,第221页。
因此,人生之“所异”便毫无意义。“贤愚、好丑、成败、是非,无不消灭,但迟速之间耳。矜一时之毁誉,以焦苦其神形,要死后数百年中余名,岂足润枯骨?何生之乐哉?”*杨伯峻:《列子集释》,第234页。凡享天下之美誉盛名者,莫过于“舜、禹、周、孔”。然而,虞舜“穷毒”,大禹“忧苦”,周公“危惧”,仲尼“遑遽”。“四圣者,生无一日之欢,死有万世之名。名者,固非实之所取也。虽称之弗知,虽赏之不知,与株块无以异矣。”*杨伯峻:《列子集释》,第231~232页。凡负天下之贬毁恶名者,莫过于夏桀、殷纣。然而,夏桀“逸荡”,殷纣“放纵”,“二凶也,生有从(纵)欲之欢,死被愚暴之名。实者,固非名之所与也,虽毁之不知,虽罚*按,此处“罚”字本为“称”字,今据杨伯峻《集解》引俞樾说改(参见杨伯峻《列子集释》,第232页)。之弗知,此与株块奚以异矣”*杨伯峻:《列子集释》,第232页。。
可见,“虽美之所归,苦以至终,同归于死”;“虽恶之所归,乐以至终,亦同归于死”*杨伯峻:《列子集释》,第233页。。与其誙誙然执着于“一时之毁誉”“死后之余名”,不若熙熙然享此生之乐、纵当身之欲。这在“纵欲为我”派看来,就是人生之最大意义。可惜,人生既苦又短,想要及时行乐,几乎无望。“百年,寿之大齐。得百年者千无一焉。设有一者,孩抱以逮昏老,几居其半矣。夜眠之所弭,昼觉之所遣,又几居其半矣。痛疾哀苦,亡失忧惧,又几居其半矣。量十数年之中,逌然而自得亡介焉之虑者,亦亡一时之中尔。则人之生也奚为哉?奚乐哉?”*杨伯峻:《列子集释》,第219页。人活一世,长寿者,不过百岁。除去孩抱、昏老、夜眠、昼觉,其所剩之可以为“我”支配的时间少之又少。而在这些少得可怜的时间里,人们还要“为刑赏之所禁劝,名法之所进退;遑遑尔竞一时之虚誉,规死后之余荣;偊偊尔顺耳目之观听,惜身意之是非;徒失当年之至乐,不能自肆于一时。重囚累梏”*杨伯峻:《列子集释》,第219~220页。。对人生之苦、短的悲观倾诉,在“纵欲为我”派那里,已臻于无以复加的程度。
那么,出于长久享乐、痛快纵欲之目的,人们是否应该“贵生爱身,以蕲*按,同“祈”。不死”“以蕲久生”?出乎预料,“纵欲为我”派竟给出这样的答案:“理无不死”“理无久生”。如前所论,人生虽苦,但总有一死。死是苦的终极解脱,享乐、纵欲不过是缓解痛苦的临时麻药。若不能享乐、纵欲,“百年犹厌其多,况久生之苦也乎?”*杨伯峻:《列子集释》,第229页。既然“久生”不若有死,那么“速亡”益于迟死乎?人生无聊、愁苦若此,何不“践锋刃,入汤火,得所志”?与常理相反,他们给出的回答竟是:“既生,则废而任之,究其所欲,以俟于死。将死,则废而任之,究其所之,以放于尽。无不废,无不任,何遽迟速于其间乎?”*杨伯峻:《列子集释》,第230页。质言之,无论生死,都要“废*按,废者,《说文》段注曰“弃之”(《说文解字注》,第450页),意即“放任之,弃置之”。而任之”。
于是,生则“究其所欲,以俟于死”,要“勤能使逸,饥能使饱,寒能使温,穷能使达”。换言之,在“纵欲为我”派的观念中,养“生”之关键,即在于“肆之而已,勿壅勿阏”。其具体纲目曰:“恣耳之所欲听,恣目之所欲视,恣鼻之所欲向,恣口之所欲言,恣体之所欲安,恣意之所欲行。”*杨伯峻:《列子集释》,第222页。更进一步讲:“耳之所欲闻者音声,而不得听,谓之阏聪;目之所欲见者美色,而不得视,谓之阏明;鼻之所欲向者椒兰,而不得嗅,谓之阏颤;口之所欲道者是非,而不得言,谓之阏智;体之所欲安者美厚,而不得从,谓之阏适;意之所欲为者放逸,而不得行,谓之阏性。”*杨伯峻:《列子集释》,第223页。可见,“凡此诸阏,废虐之主”*按,严北溟、严捷《列子译注》(第183页)曰:“废虐:大残害。废,《诗·小雅》毛传:‘废,大也。’主:主要原因。”。若“去废虐之主,熙熙然以俟死,一日、一月,一年、十年”,此“所谓养”;若“拘此废虐之主,录而不舍,戚戚然以至久生,百年、千年、万年”,此非“所谓养”*杨伯峻:《列子集释》,第223页。;若弃其“所谓养”,而从其非“所谓养”,则“弗若死”!死又奈何?“究其所之,以放于尽”。要“不含珠玉,不服文锦,不陈牺牲,不设明器”。“既死”,身“岂在我哉”?“焚之亦可,沈之亦可,瘗之亦可,露之亦可,衣薪而弃诸沟壑亦可,衮衣绣裳而纳诸石椁亦可,唯所遇焉。”*杨伯峻:《列子集释》,第226页、221页、232页、223~224页。
此即“纵欲为我”派的“生死之道”。他们还说,以此道“治内者”,可以使“物未必乱,而性交逸”。不仅如此,若能将此“道”“推之于天下”,竟可使“君臣之道息”*杨伯峻:《列子集释》,第224页、226页、226页。。基于这样一套近乎狂言的理论,他们进而以巨富子贡之后人为主角,杜撰出一则寓言*见《列子·杨朱》篇“卫端木叔者,子贡之世也”章(杨伯峻:《列子集释》,第227~229页)。,并借此向世人展示他们的理想世界、理想人生与理想人格。
四、小结
至此,“纵欲为我”派之理论形态及其发展历程已呈于读者。显而易见,该理论绝不是广大劳苦大众所能提出的。它代表的,正是一切处于没落阶段的贵族之心声。这些曾经享受着最高待遇、不可一世的“君子”们,面对历史剧变加在自己身上的毁灭性打击,过着惶惶不可终日的生活。他们既害怕“速死”,又厌倦“久生”,于是得过且过,将全部精力用于挥霍、纵欲;还恬不知耻地找来一帮学者、门客,打着杨朱的旗号,为自己的荒淫生活作论证;进而,杜撰出一套充满悲观厌世色彩的纵欲主义学说。
这种学说一经问世,便激起各家各派的激烈反对。先秦儒家将其称为“禽兽”,就是最好的例证。但从学术源流的角度看,“纵欲为我”说亦是整个道家学派在历史演进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一环。正是这种极端化、片面化的变异,才能激起道家学者的进一步反思。在先秦时代,对“纵欲为我”说进行的最彻底的批判,来自道家内部的庄子。他所提出的“吾(贵己重生)丧我(纵欲为我)”之命题,在某种程度上说,正是以矫正、肃清“纵欲为我”之徒对道家思想的歪曲、异化为鹄的。不仅如此,庄子哲学更在批判的基础上,提出“齐物论”“逍遥游”等光辉思想,对前期杨朱学派的有益遗产给予全面的继承和提升,并最终使先秦道家身体观臻于完善。而在魏晋时代,也正是因为“纵欲为我”说的再次复活,才激起嵇康、阮籍等玄学家深入思考纵欲与养生、生命与死亡、名教与自然等哲学命题,进而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等进步思想,使得中国古代哲学之思维水平大为提升。
责任编校:余沉
DOI:10.13796/j.cnki.1001-5019.2015.02.002
中图分类号:B22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019(2015)02-0011-08
作者简介:石超,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1008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