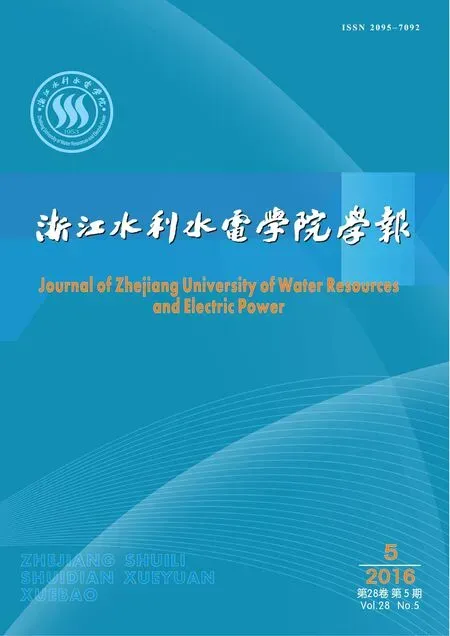近世以来余杭北湖的治理及变迁研究
胡勇军,陆文龙
(1.浙江水利水电学院 基础社科部,浙江 杭州 310018;2.上海师范大学 人文与传播学院,上海 200234)
近世以来余杭北湖的治理及变迁研究
胡勇军1,陆文龙2
(1.浙江水利水电学院 基础社科部,浙江 杭州 310018;2.上海师范大学 人文与传播学院,上海 200234)
余杭北湖开挖于唐代,是东苕溪上游修筑较早、规模较大的人工湖泊之一,具有蓄水泄洪的重要功能.由于北湖地处偏僻、湖区广阔,自开挖之后历朝政府都没有进行有效的浚治,淤积非常严重.清末曾对北湖进行过一次疏浚,但因客民垦殖,效果并不明显.民国时期,浙江水利局的水利专家和地方人士提出浚湖的规划方案,但因资金缺乏、技术落后以及战争等因素的影响,最后不了了之.
余杭;北湖;疏浚;治理
余杭南湖和北湖是东苕溪上游最早的分洪、滞洪工程,也是太湖流域兴筑最早、规模较大的人工湖泊,具有蓄水、灌溉和防洪的功能.汉代以降,南湖和北湖在东苕溪流域防洪抗旱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南湖开挖于东汉熹平年间(172—177年),当时的余杭县令陈浑“相形度势,于溪南浚南上、下湖,幅员数十里,筑高塘汇水”.唐宝历中(825—826年),县令归珧“因汉令陈浑故迹,置县南、县西二湖,又于县北二里开北湖,溉田千余顷.[1]”
目前中外学者对南湖有不少研究,例如:日本学者本田治对宋代南湖水利功能的复原[2];郑肇经在研究太湖水利技术史的时候,也论及了南湖的历史与功能[3];斯波义信阐明了东汉至清初南湖水利的变迁、生态环境的变化以及社会反应[4];森田明论述了清末地方政府对南湖的疏浚及客民与水利治理之间的关系问题[5].然而关于北湖的研究还是一片空白,本文将重点论述北湖的疏浚以及变迁历史.
1 北湖的开挖以及淤积情况
北湖位于余姚瓶窑镇西南,中苕溪左岸,介于中、北苕溪之间,原为一片草荡,古称天荒荡,今称北湖草荡,土名仇山草荡.历史文献中关于北湖最早的记载为《新唐书·地理志》:“北三里有北湖,亦珧所开,溉田千余顷.珧又筑甬道,通西北大路,行旅无山水之患.[6]”由此可见,北湖的开辟跟当时浙西的水系及其地理环境有莫大的关联.
浙西境内最大的水系为苕溪,其发源于东西天目山.据民国《重修浙江通志稿》记载:“一出天目山之阴.出天目山之阳者,……一曰南苕溪,一曰中苕溪,一曰北苕溪,总称东苕溪.[7]”苕溪流域发源地天目山是个暴雨中心,洪水多发地,常常造成下游三角洲严重内涝[8].因此,地方政府非常重视当地的水利治理,正所谓“其民为政,莫要于水利”.
余杭位于东苕溪上游地区,上承天目山系诸水,下贯杭、嘉、湖三府.溪水流至余杭扇形地,襟带山川,地势平彻,易成洪涝,所以余杭“堤防之设,比他邑尤为重要.余杭之人视水如寇盗,堤防如城廓”[9].东汉熹平年间(172—177年),余杭县令陈浑于县城西南筑塘围湖,凿涵导洪,分杀苕溪水势.唐宝历元年(825年),归珧出任余杭县令.当时南湖年久失修,湮废严重,归珧遂“因其旧,增修南上、下两湖,溉田千余顷,民以富实”[10].此外,他还在瓶窑镇附近开辟北湖,蓄水泄洪,调节中、北苕溪之水,灌溉农田千余顷.据《惠泽祠碑记》载:“昔洪水冲决堤岸,功用弗成.公与神誓,‘民遭此水溺,不能拯救,是某不职也.神矜于民,亦何忍视其灾!’堤由是筑就.至今,人名之曰‘归长官塘’.[1]”
关于北湖原来的位置以及面积大小,由于记载较少,加上图籍经久失传,故而无可考证.清嘉庆《余杭县志》称:余杭北湖“在县北五里,周六十里,引苕溪诸水以灌民田”.民国时期,德清地方士绅许炳堃在《浙西水利刍议》一文中说:“考余杭北门外新岭南北之地势,均极低漥.宣统三年水满,至石凉亭之屋顶可乘船至新岭之半腰.以今之情形,证古之传志,新岭南北周五六十里之地,或即为北湖遗址.然以何处为界趾,则无.指名询诸就地父老,只知仇山十八埧,皆侵占北湖而成田者”.根据实地考察,他认为“北湖之界应北至北苕溪之险塘,东至南苕溪之险塘,西北至陶村港、漕桥港合流处,东南至何家陡门,西至中苕溪,在沙塘村出口处”[11].浙江水利局第二测量队队长赵震有参考晚近图志,并结合实地察勘,对北湖的界线有更加详细的说明.他认为北湖之界“东至南苕溪之险塘,东南至西涵陡门,西北至曹桥,西至小横山,北至北苕溪之险塘,南至西山,周围六十里有奇,面积五万三千二百六十余亩(内仇山占积八百四十亩,土壩占积五百五十亩).幅员辽阔,三倍南湖”[12].
关于北湖堤塘的高度,历代的地方志中多有记载.咸淳《临安志》载:“其源出诸山,塘高一丈,广二丈五尺,以其在县北,故名北湖”[13].嘉庆《余杭县志》记述云:“塘高一丈二尺,上广一丈七尺,下广二丈二尺”.康熙《余杭县志》云:“查湖县北三十五里,源出诸山,即后汉所封摇泰之湖,溉田甚广.塘高一丈,上广一丈七尺,下广二丈二尺”.
汉代,陈浑在余杭县南开挖南湖,筑塘汇水,主要是调节南苕溪上游的水量,防止县城直接遭受洪水冲激.康熙《余杭县志》载:“余水自天目,万山涨暴,而悍籍南湖,以为潴泄.修筑得宜,不独全邑倚命,三吴实嘉赖之”[10].民国时期,余杭地方人士傅仁祺也曾说:“谈苕溪水利者,莫不颂及南湖”[14].唐代,余杭县令归珧又继而开辟北湖,蓄水泄洪,调节中、北苕溪之水,灌溉农田.但相比南湖,北湖地处偏僻、湖区广阔,自从开挖之后,一直未加疏浚,导致湖底淤垫,乡民围垦,湖面日促,淤积情况比南湖更加严重.
1928年,汪胡桢等人根据浙江陆军测量局在1914年所测地形图对北湖面积进行计量,未垦区域“四周不及三十里,面积不过二十三方里,合一万二千四百二十亩”[15].1931年江浙地区发生重大水灾,时人曾评述:“北湖面积五万余亩,今则庐舍桑麻,均成村落,容受之量,因此锐减”[16].1936年太湖水利委员会第二设计测量队长章锡绶对北湖进行实地勘察,他在报告中说:“至于北湖之情形,则更非南湖可比,非特历年无人修治,且已大部分成田,无复湖形.蓄洩之能力,仅在未垦殖小部分,约1.72 km2的面积,于最大洪水位时,如民国十一年者,尚能容蓄二公尺之水量而已.至于低于民国十一年之洪水位,而足以为地方之灾者,仍不能灌入暂储,以为救急之用”[17].
南北湖的淤塞,导致蓄水能力严重下降,在夏季往往发生洪灾.对此,浙江水利局以及当时的水利专家都有评述.浙江水利局在分析苕溪流域受灾的原因时说:“上游有甚大致水源面积,而溪道多在峡谷中,地势下倾特甚,不易蓄洪,山水一发,即一泄而下.上游无蓄水之湖荡,或其他蓄水设备,即东苕溪之南北湖亦淤塞失用”[18].扬子江水利委员会总工程师孙辅世在东苕溪防洪初步计划视察报告中也曾说到:“惟瓶窑以下,地势平坦,两岸均赖堤防.东堤关系余杭、杭县、德清、吴兴一带之农田者甚巨,而近年南北湖之效用渐弱,更易漫溢.民国十一年及二十年,均蒙其害,实为整理东苕溪之主要问题所在”[19].章锡绶在东苕溪防灾计划中指出:“两湖(南湖和北湖)之效用,日趋荒废,无怪东苕溪之灾患日趋严重.换言之,即东苕溪潦旱之灾患,实系蓄洩之能运用否也”[17].
2 清末及民国北湖的浚治与争议
从现有的历史文献记载来看,南湖自东汉陈浑开挖以来,较大规模的疏浚次数达十余次;而北湖自唐代以后,历朝政府几乎都未加以浚治,直到清光绪十一年(1885年),粮储道廖寿丰修浚相公庙一带,拨营兵五百人挑濬北湖,三年完成,“其时尚有湖基万余亩及西溪、南山等草荡共数千亩.[12]”光绪十三年(1887年),城绅前户部左侍郎王文韶等呈称:“余杭县南北两湖全行淤塞,有关杭嘉湖三郡水利,呈乞筹款浚治.又以两湖并举无此巨款,请先浚北湖”.对此,浙江巡抚刘秉璋给予批准,并“札布政使孙嘉谷、粮道廖寿丰,会同绅士丁丙、仲学辂筹议章程,核办所需经费,在粮道廖寿丰捐存浚湖经费五千两项下支给,如有不敷,再动善后经费.[20]”邑绅仲学辂1)为瓶窑镇长命仲家村人,是开浚北湖的有力支持者.他认为“苕溪隶杭州者为上游,水势猛厉,经嘉兴湖州者为下游,水势宽缓,故重上游,上游尤重钱塘一节,十塘五闸,独扼险要,以卫杭嘉湖三郡田庐,其持以分水势稍缓冲激者,首在余杭之北湖,次在南湖”[21].
1)仲学辂,字昴庭,清钱塘瓶窑镇长命仲家村人.同治年间举人,曾任淳安县教谕、宁波府学教授.仲学辂生平博览群书,论说范围甚大,含医学,水利,农桑等项目,著有《钱邑苕溪险塘杂记》、《南北湖开浚记》、《广蚕桑说辑补》等书.
接到浙江巡抚刘秉璋的批示之后,孙嘉谷、廖寿丰和邑绅丁丙等人立即准备浚湖事宜.这时余杭士绅董震向知县路保和提议优先开浚南湖,其理由为“北湖之利不及南湖,与其先浚北湖,工钜而利仅一隅,不若先浚南湖,工省而惠及三郡”.在双方意见不一的情况下,刘秉璋饬令杭州府吴世荣会同地方士绅前往现场查勘.结果,又提出了第三种意见,即“南北两湖均宜开浚,惟工程浩大经费难筹.请于余杭先挑竹木河,再浚南湖.汤湾以下先挖河中积砂,兼培南北塘堤,再浚北湖”.最后,因浚湖的经费没有得到解决,开浚一事只好作罢.实际上,明清以来地方政府以及乡绅关于浚湖问题经常时常发生争议,比如萧山湘湖就因为垦湖种殖和产权问题而不断引发纠纷[22].
同为东苕溪上游的分洪、滞洪工程,为何两湖的浚治情况有这么大的反差.究其原因,主要跟两者的地理位置和疏浚工程费用有极大的关系.许炳堃在《浙西水利刍议》一文中论述了北湖面积较南湖大数倍,因而疏浚较难.他说:“北湖当南、北、中三苕溪会合之冲,与南湖之仅受南苕一溪之水者,较水量多寡相去倍蓰.故其面积亦较南湖为大,徙以僻,在北乡无人注意.故南湖之浚,诸家记载代有篇章,开濬之事,亦每阅数十年而一举”.光绪十六年(1890年),浙江巡抚崧骏奉上谕对南湖进行疏浚,他对南北湖浚治的难易有这样的评述:“南北两湖同为三苕暴涨分潴之地,均已淤高.然南湖界址犹存,多浚一尺,即有一尺之利.北湖涨退之后,一望平原,旁无崖岸,工程尤巨,无从措办”[20].由此可见,北湖位置较偏北,且面积比南湖大数倍,加上一直没有得到浚治,淤积情况比较严重.故而要对其进行疏浚,无论是人力和财力都比疏浚南湖花费要多,并且效果不一定理想.
尽管清光绪年间廖寿丰对北湖进行挑浚,恢复湖基一万余亩,但是到了民国时候,客民不断垦殖,当时就有“挑草荡一担泥,年多余杭一石米”的俗语[23].1915年春,许炳堃亲自前往北湖进行实地调查,结果不容乐观,昔日恢复的湖基,“今又桑田交错、草舍相连,只未筑隄拒水,佔作坝田耳.然久而不治,必渐有筑隄者,隄成则北湖痕迹更荡然无存矣.北湖久不挑濬,而光绪初年尚有万数千亩,今不出三十年而侵占如此之甚者”[11].
1916年,浙江省水利局第二测量队队长赵震有对三苕的地理环境进行实地勘察后分析说:“南、北二苕环束东北,中苕横贯湖中,天目万山之水由此过脉如沟浍.然中、南二苕直趋余杭之汤湾渡,两水会合,北行五里至瓶窑之相公庙,北苕来注之,此为三苕会合之处”.故而,他认为北湖的形状为三角形,“巨浸适当其冲,承受三苕之流,停顿湍急之势,与南湖仅受南苕一溪之水者,其水量多寡相去倍蓗,故北湖之形势较南湖尤为险要也”.对此,赵震有提出解决浙西水利的正本清源之道,即“三苕亦宜择要与北湖并加疏浚”,且修浚之举“不能视为缓图”.同时,他还对疏浚三苕和北湖的工程费用进行了概算.
除了赵震有之外,余杭北一区自治委员施广福也认为,“治本之要,厥惟开浚北湖,上有容纳之量,下无冲突之虞”.他认为,疏浚北湖主要有三利:“其利一,潦则藉以储蓄,旱则资以灌溉;其利二,瘠土化为腴壤,险塘永庆安澜;其利三,但言之匪艰,行之惟艰.”对于时人所说的“工程之钜需数十万,际此财政竭绌之时,安能办此不急之务?”他却大不为然,认为如果北湖一年不遭水患,“丰收何可臆算,一邑计之固不足,三郡计之则有余”[22].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浙江省政府鉴于北湖“年久失修,淤成平陆,强豪侵占,填地垦植桑竹”,而“湖泽有关农田灌溉,年久淤塞者急应修理,以利耕泄”[24],遂组织清理委员会对北湖进行实地测量和勘界.由于历代乡民垦殖,湖界已经模糊不清,以致在清丈过程中时有纠纷发生.1933年,余杭县商会、农会、教育会电呈浙江省政府,称清理界址委员会组织的清丈队将本在北湖在身之外的姚坝、黄坝、蔡家塘、李坝、仇山塘等处划入界湖以内,遍竖红椿,以致数千农民非常惶骇.随后,浙江省政府饬令浙江水利局进行审核,清理余杭北湖界址委员会遂召开第五次常会,并议决“根据杭州府志、余杭县志、北湖地形图及本会调查报告,说明各坝塘在北湖范围以内”[25].对此,余杭和德清县农会等机构表示不满,再次呈请浙江省政府复议.最后,经界址委员会第七次委员会议议决:一是苕溪测量尚存进行,将来测竣后,计划之时,必须择适当地点建筑蓄水库,如在北湖范围之内,应尽先使用北湖草荡及仇山草荡等处,至姚坝、黄坝,应视所需蓄水量之多寡,酌量情形,分别先后办理.二是此次清理之后,应请重申禁令,姚坝、黄坝不准再行升科,北湖草荡及仇山草荡等处应禁止升科及开垦,嗣后如有围垦情形,即可证明侵占[26].然而由于资金缺乏、技术落后以及战争等因素的影响,清理委员会并没有对北湖进行有效的浚治.
从北湖的浚治可以看出,民国时期中国水利发展史处于一个承前启后的重要阶段,地方水利事业也从传统向现代转变.西方先进的科技理论和工程技术逐渐替代了中国古代的治河思想和水利技术,但是由于受到人力、资金、技术、战争等多种因素的制约,民国时期水利建设举步维艰.
[1] 张吉安,朱文藻.嘉庆余杭县志[C]//中国地方志集成·浙江府县志辑.上海:上海书店,1993.
[2] [日]本田治.宋代杭州及び后背地の水利と水利组织[C]//梅原郁.中国近世の城市と文化.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84.
[3] 郑肇经.太湖水利技术史[M].北京:北京农业出版社,1987.
[4] [日]斯波义信.浙江省余杭县南湖水利始末[C]//布目潮风博士古稀纪念论文集东亚的法与社会.东京:汲古书院,1990.
[5] [日]森田明.清代水利与区域社会[M].雷国山,叶 琳,译.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8.
[6] 欧阳修,宋 祁.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7] 浙江省方志办.重修浙江通志稿[M].北京:方志出版社,2010.
[8] 陆建伟.秦汉时期浙江苕溪流域的开发[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4(2):17-23.
[9] 李 卫,嵇曾筠.雍正浙江通志[C]//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
[10] 张思齐.康熙余杭县志[C]//中国地方志集成·浙江府县志辑.上海:上海书店,1993.
[11] 许炳堃.浙西水利刍议[J].河务季刊报,1923(9):17-18.
[12] 余杭县志编纂委员会.余杭县志[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
[13] 潜说友.咸淳临安志[C]//[清]永 瑢,纪 昀.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4.
[14] 傅仁祺.疏浚余杭南湖计划之商榷[J].浙江建设月刊,1934(5):61.
[15] 林保元,汪胡桢.调查浙西水道报告书[J].太湖流域水利季刊,1928(4):36.
[16] 周可宝,卢永龙.二十年浙江省之水灾[J].浙江省建设月刊,1933(6):70.
[17] 章锡绶.浙西东苕溪防灾计划之商榷[J].扬子江水利委员会季刊,1936(2):12-13.
[18] 浙江省水利局.浙江省水利局年刊[R].杭州:浙江省水利局,1929.
[19] 孙辅世.东苕溪防洪初步计划视察报告[J].扬子江水利委员会季刊,1937(1):55.
[20] 褚成博,褚成亮.光绪余杭县志稿[C]//中国地方志集成·浙江府县志辑.上海:上海书店,1993.
[21] 仲学辂.南北湖开浚说[J].浙江省通志馆馆刊,1945(2):105-106.
[22] 陈志根.湘湖历史上官绅民间的合作与冲突[J].浙江水利水电学院学报,2015,27(2):1-5.
[23] 施广福.余杭绅士广福节略[M].石印本.浙江图书馆藏,1916.
[24] 整理湖泽[N].申报,1933-10-09(08).
[25] 浙江省水利局.划分余杭北湖界址[J].浙江省建设月刊,1933(6):11-12.
[26] 浙江省水利局.清理余杭北湖界址[J].浙江省建设月刊,1934(10):21.
OnGovernanceandChangesofNorthLakeinYuhanginModernTimes
HU Yong-jun1,LU Wen-long2
(1.Department of Social Science,Zhejiang University of Water Resources and Electric Power,Hangzhou 310018,China;2.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Communications,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Shanghai 200234,China)
The North Lake of in Yuhang was dug in the Tang Dynasty as one of the larger artificial lakes on the upstream of Dongtiaoxi with the important functions as water storage and flood discharge. Due to its remoteness and broadness,the government in the past dynasties didn’t carry out effective desilting works after excavation,resulting in serious siltation.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there was a dredging conducted by the government,but the effect was not obvious because of reclamation. During the period of Republic of China,hydraulic experts and local people in Zhejiang Water Conservancy Bureau proposed planning scheme of lake dredging,but for various reasons such as money shortage,backward technology and wars,there was no final result.
Yuhang; North Lake; dredging; governance
2016-04-12
2016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资助项目(16YJC770010);2016年度杭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科研基金资助项目(M16JC013)
胡勇军(1986-),男,江苏泰兴人,博士,讲师,研究方向为浙江水利史.
G07,TV882.9
A
1008-536X(2016)10-000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