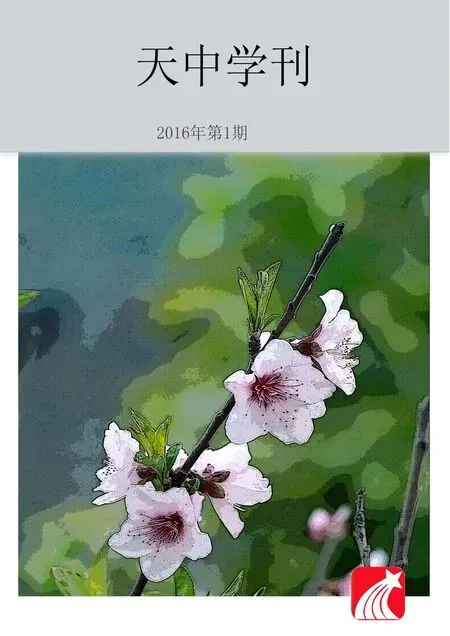论民事诉讼当事人恒定原则——兼评《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249条之适用
胡轶(西南政法大学 法学院,重庆 401120)
论民事诉讼当事人恒定原则——兼评《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249条之适用
胡轶
(西南政法大学 法学院,重庆 401120)
摘 要:《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249条确立了当事人恒定原则,但该解释规定过于简略,可能存在适用上的困难,需要从解释论上予以回应,具体做法是:在坚持自由处分原则与于原诉讼无影响原则前提下,对争议民事权利义务的继受方式和范围进行限制;保障继受人诉讼参与权利,继受人可以申请以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的身份参加诉讼或者承担诉讼,并且不可以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生效裁判对继受人具有既判力,当继受人的权利是基于善意取得或系争物时,既判力不及于自无权利而善意取得权利的第三人。
关键词:《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249条;当事人恒定原则;继受;既判力;主观范围
一、问题的提出
对于诉讼系属中因正当当事人死亡或者消灭而导致诉讼发生的承继问题,我国法律有所规定,司法实务对此也不存在认知偏差,理论上称之为“当然承担”。然而,诉讼系属中争议的民事权利义务转移问题在诉讼法上并未明确规定,司法实务对这种问题的认知也不尽相同。在最高人民法院34号指导案例①中,在债权受让人即权利承受人是否可以作为申请执行人直接申请执行的问题上,福建省高院和最高人民法院的观点并不一致。福建省高院认为,诉讼系属中债权受让人不可以作为申请人直接申请执行,如申请执行,需要先申请变更执行主体。而最高人民法院认为,诉讼系属中债权受让人可以作为申请人直接申请执行。两者争议的焦点表面上是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18条理解的差异,实际上是对诉讼系属中争议民事权利转移时受让人是否受终局判决既判力约束的不同理解。在给付之诉中,终局判决会产生既判力、执行力,既判力的主客观范围直接决定执行力的主客观范围。由此推论,争议民事权利受让人能否也可作为既判力所及对象直接影响执行申请人主体资格的确定?对于这种涉及理论根源的问题,上述指导案例并未进行回应,仅在其裁判要点中表明,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权利人在进入执行程序前合法转让债权的,债权受让人即权利承受人可以作为申请执行人直接申请执行,无须执行法院做出变更申请执行人的裁定。上述指导案例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明确了受让人执行主体资格确定的程序路径,但缺乏系统地解决问题的体系,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受让人程序路径规则不清的问题,难以广泛适用。不难发现,法律对诉讼系属中的争议民事权利义务转移问题不是没有规制,而是缺乏统一的适用规则。因此,从保障司法稳定及当事人利益出发看问题,统一规则的制定势在必行。
2015年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新民诉司法解释》)第249条规定,既有“当事人恒定主义”的特色,也有“诉讼承继主义”的特色。作为一项新的程序制度,当事人恒定原则一定程度上回应了司法的需要,对于司法实践统一适用程序规则有很大的帮助。然而,《新民诉司法解释》第249条关于“当事人恒定原则”的规定过于简单粗糙,其具体的原则、适用范围、程序参与、既判力扩张等规定尚不明确,其与实体法之间的衔接问题也未说明,法条的构造同样缺乏系统化,在司法实践中将可能给当事人、法院造成具体应用上的困难。因此,本文试图对《新民诉司法解释》第249条的具体适用问题展开探讨,以期对司法实践有所裨益。
二、自由处分原则和于原诉讼无影响原则
《新民诉司法解释》第249条规定,在诉讼中,争议的民事权利义务转移,不影响当事人的诉讼主体资格和诉讼地位。这一规定适用的是自由处分原则和于原诉讼无影响原则。自由处分原则和于原诉讼无影响原则,是当事人恒定原则的子原则,也是当事人恒定原则得以确定、施行的基础。自由处分原则是指,诉讼系属中,当事人有权转让处于争议中的民事权利义务,不因民事权利义务具有诉讼负担而被限制实体法上的权利。自由处分原则体现的是对诉讼系属中当事人实体法上权利的尊重,是当事人恒定原则得以施行的实体法基础。于原诉讼无影响原则是指,原诉讼当事人在转移或让与事实发生改变后,法院判决无需顾虑转移或让与事实,不能要求原告在转移或让与之后变更其诉讼请求,原告的诉求仍具有合法性。当然,这不排除在特定情形下的诉讼承担。如果一方当事人在诉讼对其不利的情形下,将争议权利义务出让资力不佳的第三人,以脱离诉讼,规避不利诉讼后果,从而导致对方当事人即使最后获得胜诉判决,亦难免会遭受损害[1]96,那么为了保障对方当事人利益,原先的诉讼不受转移或让与的影响,出让人仍为当事人并具有诉讼实施权,他仍以法定诉讼担当的角色,就受让人的权利以自己的名义进行诉讼,受让人则丧失诉讼实施权。受让人因不具有诉讼实施权而受禁止重复诉讼的约束。于原诉讼无影响原则,体现了保障对方当事人利益及追求诉讼经济的目的,是当事人恒定原则的程序法基础。
三、争议民事权利义务的继受
争议民事权利义务继受,系指在诉讼系属中争议民事权利义务转让给案外继受人。《新民诉司法解释》第249条对争议民事权利义务继受的方式与范畴并未明确界定。这样,争议民事权利义务继受就可能因法条不清晰而出现适用过宽或过窄的问题。
(一) 争议民事权利义务继受的方式
争议的民事权利义务,系指争议诉讼标的所承载的权利义务。争议的民事权利义务除具有民事法律效力以外,还具有诉讼负担的效力。诉讼负担,简而言之,就是指正在形成的既判力的有利或者不利后果[2]34。争议民事权利义务既然具有诉讼负担,其转移方式适用实体法上的规定毋庸置疑。争议民事权利义务转移方式,可包括基于法律行为的转移、依照法律规定的转移、因国家行为所为的转移(如公用征收)。争议民事权利义务本质上具有实体法属性,不能因为具有诉讼负担就否定实体权利自由转移的规则,但考虑到具有诉讼负担这一程序要素,争议民事权利义务的转移仍应当与实体权利自由转移规则有所区别。例如,依据《民事诉讼法》第111条规定,被采取保全措施的系争物或者权利不得进行转让。此外,民法上的继承,因信托任务终了而所生受托人更换,诉讼程序上当然中止及承受诉讼等情况,不适用当事人恒定原则。此类事项属于“当然承担”范围,不为《新民诉司法解释》第249条所涵盖。
(二) 争议民事权利义务继受的范围
《新民诉司法解释》第249条第1项规定,在诉讼中,争议的民事权利义务转移的,不影响当事人的诉讼主体资格和诉讼地位。此规定仅规范争议民事权利义务的继受,并未规定诉讼系争物继受的情形。这样在理解上就会产生争议民事权利义务继受的范围是否应包含诉讼系争物的困惑。
我国台湾地区的民事诉讼法第254条第1项规定,诉讼系属中为诉讼标的的法律关系,虽移转于第三人,于诉讼无影响。台湾部分学者认为,应将诉讼标的的法律关系作广义理解,应包含诉讼系争物。这种学说被称之为“实体法属性说”。该学说立足于实体法观点,将台湾地区的民事诉讼法第401条第1项所定的诉讼系属系争物特定继受人解读为:倘以人之关系(债权、债务关系)为诉讼标的者,必继受该法律关系之权利或义务人始足当之;倘以对物关系(物权关系)为诉讼标的时,则所谓继受人系包括受让标的物之人[3]22。确定判决所认定者,为对人之债权时,因债权效力仅及于特定当事人,单纯受让系争物之人,既然不是当然受让该债权的权利义务,自然不是确定判决效力当然所及之人,因而诉讼系争物不包含基于债权请求权而转移的情形。这是典型的德国民事诉讼法的传统观点。此外,也有学说认为,系争物包含基于债权请求权而被转移的系争物,这种观点被称之为“新程序保障说”。该学说认为,新法以程序权保障的有无,作为界定判决效力主观范围大小及判定其发挥作用是否具有正当性的基础。依此诉讼法上观点所为判决,原则上并不考虑该判决系以物权关系或债权关系为诉讼标的,不考虑继受人所继受之标的物为物权、债权或其他标的物,且不以本诉讼程序已赋予该继受人实际上获有事前的程序保障为前提,但为保障受该判决效力扩张的继受人的程序权及固有利益,本诉法院应尽可能为职权通知以赋予事前的程序保障,使继受人有适时提出足以保护其权益的攻防方法的机会,而避免事后发生其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4]11−12。
从法条内容看,我国对争议民事权利义务的认识更接近台湾地区对法律关系的理解,因此,我们在界定争议民事权利义务的范围时,应借鉴台湾地区的“实体法属性说”为宜。受台湾“新程序保障说”影响,我国虽增加了第三人撤销之诉制度,但这与台湾地区所提供的程序保障制度还相去甚远。不过,现阶段而言,我国并不适宜援用该学说。另外,争议的民事权利义务继受并不包含义务继受和权利义务概括继受,因继受人通常需要对方当事人的同意才能受让争议民事权利义务,债权人因此再无保护的必要。因此,义务继受和权利义务概括继受不属于民事权利义务继受范围。
综上,争议民事权利义务继受范围包含权利继受和基于物权请求之诉讼系争物继受。
四、继受人的诉讼参与
为保障对方当事人的利益及追求诉讼经济,《新民诉司法解释》第249条第1项采取于原诉讼无影响原则。转移人已经不具有实体法上的利益,对诉讼并无利益上的驱动,继受人有理由担心转移人不佳致使诉讼实施对其不利。因而,法律有必要赋予继受人参与诉讼程序的机会。就诉讼程序而言,《新民诉司法解释》第249条并未对继受人的程序参与问题给予系统规定,仅规定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参与及承担诉讼两种程序参与方式,而对第三人撤销之诉适用的可能性并无明示。该法条虽然允许受让人以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参加诉讼或者直接替代转移人承担诉讼,但对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参加诉讼的程序以及实体权利与程序权利相分离导致的诉讼形态上的冲突未有定论。在继受人承担诉讼问题上,该法条对继受人具体承担的条件的界定也是模糊的,不具有指导司法实务的意义。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该法条对继受人程序保障并不充分。一般情况下,这种规定难以对出让人行为进行约束,继受人有受虚假诉讼之虞。继受人在诉讼参与上是否有其他路径的可能,亟待研究。于此分述如下:
(一) 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参加诉讼
《新民诉司法解释》第249条第2项明确规定,继受人可以作为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参加诉讼。这与域外的规定有所差异。无论是德国还是我国台湾地区民事诉讼法,都规定继受人均可以提起主参加诉讼和辅助参加诉讼。相较之下,我国的规定比较简单,以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身份参加诉讼从内涵上更接近于辅助参加诉讼。就辅助参加诉讼而言,有一般辅助参加诉讼和准用共同诉讼规定的辅助参加诉讼之别。在德国,当继受人欠缺承担诉讼或提起主参加诉讼的可能,依《德国民事诉讼法》第265条第2项第3句的规定,继受人不得为准用共同诉讼规定的辅助参加,仅得为辅助参加。依我国台湾地区“民事诉讼法”第58条、第62条的规定,该第三人为辅助转移人而参加诉讼时,不论在事实审还是第三审,因其为诉讼标的之权利、义务之归属主体,该诉讼标的于第三人(参加人)和转移人(被参加人)间必须合一确定,故为独立性参加而非从属性参加[4]128−129。对比而言,第三人准用共同诉讼规定辅助参加诉讼充分考虑了第三人(参加人)具有实体法上的处分权利。允许第三人独立性参加,才能更好地保护其利益。
在我国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参与诉讼的模式下,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具有实体权利与诉讼权利不对等的情形,对此应分别从程序法和实体法的角度加以界定。从程序法视角出发,在当事人恒定原则的模式下,继受人因承继具有诉讼负担的争议民事权利义务,当然接受程序法上的约束,即继受人只能以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的身份参与诉讼。从实体法的视角出发,继受人能够在程序以外对实体法律关系进行处理,进而影响诉讼程序中当事人双方的攻击防御乃至诉讼结果。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该种模式下,继受人与出让人之间具有民事法律关系,出让人的不当行为导致继受人权利难以实现的,继受人可以基于双方的民事法律关系请求损害赔偿。可见,此处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除具有程序法上第三人特性以外,还兼具实体法第三人的特性,有别于一般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
依《新民诉司法解释》第81条规定,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可以申请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参加诉讼。然而,当事人恒定原则并未涉及人民法院通知参加诉讼的规定。那么,是否就能因此认为只有继受人申请参加这一途径?就域外经验而言,通知当事人参加诉讼的制度有诉讼告知制度和职权通知制度之说,其原理在于追求纠纷的一次性解决。因此,法官通知继受人参加诉讼也有其道理。其道理特别在于,在没有充足的程序保障情况下,既判力及于继受人,难以让人信服;而且通过法院通知参加诉讼这一方式,继受人使用第三人撤销之诉也无可能,避免了不要的诉讼耗费。但是,规定法院有义务、职权通知继受人参加诉讼,就增加了法院不必要的负担,与当事人恒定原则追求诉讼经济、稳定的目标相冲突。更为重要的是,争议民事权利义务在诉讼系属中是否转移?对此,法院依职权将其调查清楚的难度并不小,一旦法院不能依职权通知继受人参加诉讼,继受人就可以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这样,当事人恒定原则也就会成为空谈。因此,为贯彻当事人恒定原则,继受人参加诉讼宜采用主动申请模式,而不必采用法院依职权通知的模式。
(二) 承担诉讼
《新民诉司法解释》第249条第2项规定,受让人申请替代当事人承担诉讼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决定是否准许。此种情况可称为承担诉讼。在德国,继受人承担诉讼,因不同情况而作不同处理。如为动产权利或诉讼系争物的继受,依《德国民事诉讼法》第265条第2项第2句的规定,对方当事人同意,继受人始得承担诉讼,只有在转移人滥用其同意权的情形下,继受人承担诉讼始无须对方当事人同意。如为不动产诉讼系争物或权利继受,依《德国民事诉讼法》第266条第1项的规定,就土地主张权利存在(或不在)或基于土地而生的义务在占有人与第三人之间发生争讼的,而且在诉讼系属中该土地被转移的,权利继受人有权依当时诉讼进行的状况承担该诉讼[3]17。在我国台湾地区,继受人承担诉讼的条件较德国更为宽松,其民事诉讼法第254条规定,受转移之第三人如经双方当事人同意,得申请代当事人承担诉讼。该条同时又规定,仅对方当事人不同意者,转移之当事人或该第三人得申请法院以裁定该第三人承担诉讼。盖因诉讼标的之法律关系既已转移,转移人与该诉讼利害关系已渐淡薄,未必能够期待其致力于攻防,故为保障受让人的固有权益及程序权,使其能承担诉讼,也使诉讼结果更能直接解决三人间的纠纷[3]8。
我国在规制承担诉讼条件时须慎重考虑诉讼秩序与程序保障之间的平衡。在这方面,台湾地区的模式,要求法官对程序利益的把握要有较高的业务能力,恐难以在我国普遍施行。结合实际,我国的承担诉讼宜采用德国模式,要限制法院自由裁判权的适用。但考虑有虚假诉讼、恶意诉讼的可能,法院可不经双方当事人同意直接追加第三人参与诉讼,使得诉讼更加周全。
(三) 其他诉讼参与路径
就《新民诉司法解释》的规定而言,继受人参与诉讼的机会并不够充分,由此可能给司法实践带来一些问题,比如,出让人与对方当事人进行虚假诉讼,造成继受人利益受损。因此,有必要探讨赋予继受人其他诉讼参与的可能性。事实上,在我国台湾地区,允许继受人提起主参加诉讼,就争议法律关系对原诉讼当事人提起诉讼。除此之外,台湾地区的法律还允许继受人在无诉讼通知参加的前提下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以保障其程序利益。主参加之诉与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参加之诉非常类似,得以直接赋予受让人以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参加诉讼,但是却与其可以以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参加诉讼的法条规定有冲突。另外,第三人撤销之诉,与法院依职权通知密切相关。在我国台湾地区,只有在无诉讼告知或者职权告知的情况下,才有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可能。在当事人恒定原则下,如果法院不能依职权通知继受人参加诉讼,继受人不能参与诉讼,就不具有不可归责于自身的理由,自然不能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如果法院能依职权通知继受人参加诉讼,继受人不能参加诉讼就可能具有不可归责于自身的理由,自然就可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新民诉司法解释》第249条中并无法院职权通知的规定,继受人也就没有适用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可能。由此可见,此两条路径皆无实现之可能。不过,继受人作为终局判决既判力承受者,当然可以提起再审之诉,以遏制虚假诉讼的滥用。
五、既判力及于继受人
《新民诉司法解释》第249条第1项中规定,人民法院做出的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对受让人具有拘束力。这里的判决、裁定对受让人具有约束力,主要系指终局判决的既判力及于继受人,而既判力为判决最主要的效力。在诉讼系属中,当事人转让其争议的民事权利义务,基于当事人恒定原则的适用,于诉讼并无影响,既判力自动及于继受人。但是,有关既判力及于继受人的合理性和范围,法条都未说明。继受人未参与诉讼,却要受到终局判决既判力的约束,难免有所不公。因此,论述既判力及于继受人的合理性确有必要。而关于既判力及于继受人范围的问题,也因为确定既判力主观范围扩大的界限关系到继受人利益的保护与诉讼秩序的稳定,有必要加以说明。
(一) 既判力及于继受人的合理性
在当事人恒定原则下,人民法院做出的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对受让人具有拘束力。这主要指终局判决的既判力及于继受人。根据我国《新民诉司法解释》第249条的规定,在当事人恒定原则下,有两种情形既判力及于继受人:一种是继受人参加诉讼或者承担诉讼;另一种是继受人没有参与到诉讼中。
就继受人参加诉讼或者承担诉讼的情况而言,判决的既判力当然约束继受人,不存在既判力主观范围的扩张。这其实比较好理解,大陆法系的理论和立法对既判力主观范围的传统界定是:既判力原则上作用于原审诉讼中对立的双方当事人。在我国,对此处的“当事人”概念应作广义理解,除原告、被告以外,还包括共同诉讼人、诉讼代表人、第三人等所有对诉讼标的进行争执并处于类似原告、被告诉讼地位的诉讼主体[5]141。特殊情况下,出让人部分转让争议诉讼标的所承载的权利义务,继受人不论是以当事人恒定原则还是以与本案争议诉讼标的有利害关系为理由参加诉讼,都是本案的正当当事人,并不会导致判决既判力的主观范围扩大。
就继受人未能参加诉讼的情况,既判力如何及于他?对于这一问题,有必要梳理既判力的本质属性问题。有学者认为,既判力的本质属性应兼顾生效判决既判力的实体法(私法)属性与诉讼法(公法)属性[5]138。既判力本质上属于实体法(私法)的效力,同时在形式上兼顾诉讼法(公法)的效力。既判力源于判决所确定的实体法律关系,从而对当事人产生约束性效果,要求其按照确定判决处理其民事权利义务关系。在此种情况下,继受人承继具有诉讼负担的权利义务,实为判决既判力所涵盖的客观范围。既判力本质属性为实体法(私法)属性,当既判力所涵盖的实体法律关系发生变动时,必然会反射到既判力涵盖的主观范围,如此,判决的既判力主观范围就会扩大到继受人。其中,继受人没有参与诉讼,包括转移人部分转让争议民事权利义务以及转移人全部转让争议民事权利义务两种情况。在转移之人部分或者全部转让争议民事权利义务情况下,继受人没有参与诉讼,人民法院做出的生效判决、裁定对继受人依然具有拘束力,存在判决既判力主观范围的扩大。在部分转让的情况下,继受人与转移人之间关系更类似于共同诉讼的结构。依此种理解,继受人是否参加诉讼事实上对诉讼进程会产生影响。从对法条解读上看,这与所确立的当事人恒定原则是相矛盾的,确立当事人恒定原则的目的、机能在于使本诉讼当事人适格,避免因当事人的转移行为而使诉讼受影响,从而使该诉讼真正能发挥解决纷争的实际效用,谋求诉讼经济,保护程序利益,并达到实现权利之目的。允许部分转让情况下受让人以共同诉讼人的身份参加诉讼,还会陷入循环转让的逻辑困境,会给对方当事人带来无尽的诉讼困扰。
(二) 既判力及于继受人的范围
《新民诉司法解释》第249条中涉及的争议民事权利义务为既判力及于继受人的依据。对争议民事权利义务的解读直接影响对既判力主观范围的扩张界限。前述中对于争议民事权利义务继受范围进行界定,包含权利继受和基于物权请求之诉讼系争物继受。在此范围内,争议民事权利义务转移,既判力始及于继受人。既判力是否及于自无权利而善意取得权利的人?对此,《新民诉司法解释》并未规定。
当继受人的权利是基于善意取得或系争物时,传统观点认为既判力主观范围不会扩大。这是因为,善意取得在法律性质上为原始取得而非继受取得。出现这种情况,继受人承继没有诉讼负担的权利义务,能例外地不承受判决的效力。关于善意取得之例外不承受,《德国民事诉讼法》第325条第2项有明文规定,关于民法上保护从无权利之人取得权利之人的规定,准用之。这里的善意取得在德国存在诸多争论。其中,“实体法善意取得说”[3]33最符合法条原意。《德国民事诉讼法》第325条第2项规范旨意,主要是使实体法上善意取得的第三人免受既判力主观效力范围扩张,实体法上允许自无权利人善意取得的保护规定仍被贯彻,其善意取得的权利应获得确保,不受诉讼法既判力的影响。该项规定完全依实体法上善意取得的要件,决定既判力是否扩张及于该继受人[3]40。也有学说并不认同“实体法善意取得说”,认为其仅立足实体法观点,并未兼顾诉讼法上的观点,以至于不当缩小了判决效力的主观范围。在有充分事前程序保障及事后程序保障情况下,判决的效力当然及于善意取得权利第三人。鉴于程序保障不足现状及适用第三人撤销之诉的疑虑,就既判力及于继受人的范围问题,我国立法宜借鉴“实体法善意取得说”,即当继受人的权利是基于善意取得或系争物时,既判力不及于自无权利而善意取得权利的第三人。
《新民诉司法解释》第249条确立的当事人恒定原则,弥补了长期以来存在的法律空缺,实为民事诉讼法上一次重大进步,对于维护诉讼的稳定、提升诉讼经济与保障程序利益有诸多益处。不过,该解释仍然存在一定问题:第一,该规定还过于抽象化,相较于域外成熟的当事人恒定原则体系,缺乏可操作性程序路径,难以真正地应用于司法实践。第二,该规定在相关制度运行上存在适用冲突。我国民事诉讼法是在兼糅各国经验基础上制定的,兼具各国制度特色,直接适用域外成型经验难免造成适用上的冲突。例如,在当事人恒定原则下,继受人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就与已有制度存在内在冲突性。因此,我国当事人恒定原则宜借鉴德国民事诉讼法精细化、逻辑化规则方法,同时也应吸纳我国台湾地区加强程序利益保障的方式,但也不宜过于松动当事人恒定原则的适用。第三,该规定与相关实体法的衔接还需亟待完善,并在完善过程中,考虑我国特有制度与域外经验不同制度的具体适用。例如,相较于德国、台湾地区,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为我国特有制度,其程序参与性迥然异于辅助参加。从实体权利与程序权利难以分离的视角出发,我们更应重视实体法与诉讼法之间的配合,纯粹的实体法思路或者纯粹的诉讼法思路都是不合时宜的。
注释:
① 李晓玲、李鹏裕申请执行厦门海洋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厦门海洋实业总公司执行复议案。
参考文献:
[1] 刘学在.略论民事诉讼中的诉讼系属[J].法学评论,2002(6).
[2] 杜睿哲.诉讼系属中债权转让时的抗辩与反诉[J].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04(6).
[3] 刘明生.诉讼系争物或诉讼标的权利之继受与既判力主观范围之扩张[J].政大法学评论,2013(138).
[4] 许宦士.诉讼参与与判决效力[M].台北:新学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0.
[5] 丁宝同.论民事判决债权受让人之再审申请主体资格——以“民事判决效力之主体范围扩张理论”和“诉讼承继主义”为中心的立体论证[J].法学家,2013(4).
〔责任编辑 叶厚隽〕
An Analysis of the Principle of Client Eternally-fixed Doctrine in Civil Procedure——Comment on Section 249 on Judicial Explanation of the Civil Procedural Act
HU Yi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Chongqing 401120, China)
Abstract:Section 249 on Judici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Civil Procedural Act establishes the principle of constant party. However, this provision is so simple that it may be difficult on judicial application, thus we should analyze it from the interpretation theory. On the principle of free disposition and principle of no influence in the original proceedings, restrict successor’s way and range of disputed civil rights and obligations. Besides, we should protect heirs’ rights of litigation participation. On one hand, Heirs could apply for the qualifications to participate as accessory intervener or inherit proceedings. On the other hand, heirs shall not revoke the action as third party. Finally, valid decision produce adjudged force to heirs. When applied principle of bona fide acquisition, judicial decision haven’t effect on heirs.
Key words:Section 249 on Judicial Explanation of the Civil Procedural Act; client eternally-fixed doctrine; inherit of dispute civil rights and obligations; adjudged force; subjective scope
作者简介:胡轶(1976-),男,江西南昌人,博士研究生。
收稿日期:2015-08-01
中图分类号:D925.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5261(2016)01−005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