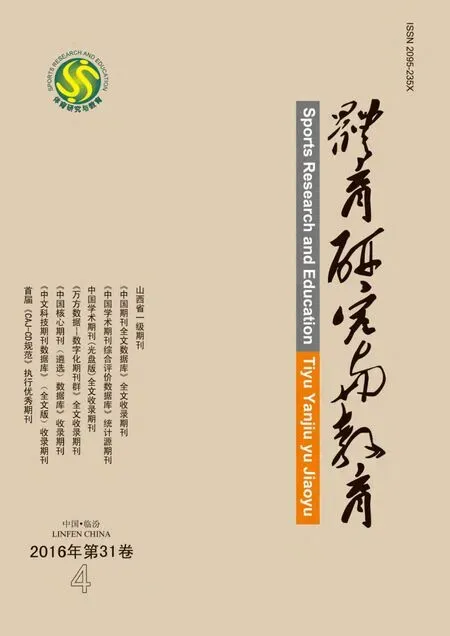“负面体育报道”对大学生体育态度的影响
——以天津市大学生群体为例
李军松,弓 成
“负面体育报道”通常是指经过人为加工而成的负面体育新闻报道,一般称之为“消极体育报道”或是“负面体育新闻”[1]。它一方面有利于反映和揭露体育事业发展过程中的敏感、灰暗面,唤起公众的关注和警醒;另一方面,肆意地煽情、夸大甚至歪曲乃至捏造事实的“负面体育报道”也会削弱人们对体育本身的关注,甚至损害体育的形象,影响体育事业健康、顺利的发展。在校大学生作为体育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和大众传媒的主要受众者,他们在接触到这些与体育精神相悖的“负面体育报道”之后的态度是怎样的,对体育的认知,乃至社会现实的认知又会产生怎样的影响?笔者以天津市部分大学生为样本,针对“负面体育报道”对当前我国大学生体育态度的影响进行调查和分析,探讨大学生的社会认知图式,以期为教育部门进行思想教育提供参考依据,也促使新闻从业人员正视“负面体育报道”,从思想层面和可操作层面调整报道方式和形式,净化中国体育的舆论环境,弘扬正面效应,规避负面效果。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本研究是以天津市大学生群体为调查对象的一项探索性研究。样本选自南开大学、天津科技大学、天津财经大学、天津师范大学和和天津滨海职业学院等五所高校。共发放问卷1 000份,收回982份。剔除无效问卷18份,共回收有效问卷964份,回收率96.40%。调查样本中,男生占46.4%、女生占53.6%;重点本科院校生占21.6%、普通本科院校生占56.4%、高职高专院校生占22.0%;文史类专业学生占 42.7%、理工类专业学生占57.3%;大一学生占25.6%、大二学生占35.7%、大三学生占20.3% 、大四学生占18.4% 。
1.2 研究方法
在对人类行为做解释时,人们总是把态度放在非常显著的位置。社会心理学中的态度改变,是指在一定的社会影响下,已经形成的态度以及在接受某一信息或意见的影响后,所引起的相应变化。[2]根据研究目的和费斯廷格的认知不协调理论关于态度及态度改变的研究,笔者编制了《“负面体育报道”对大学生体育态度影响调查问卷》,对“负面体育报道”与大学生的体育态度和行为的关联性进行了定量定性分析与研究。问卷共有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对人口学统计变量的测量,包括性别、学校、年级和专业类型以及对体育的状况;第二部分主要考察大学生对体育和体育报道的认知与态度;第三部分主要测量大学生接触“负面体育报道”之后的态度和行为变化。
2 调查结果与分析
2.1 大学生对“负面体育报道”的接触
调查显示:除了27.6%的大学生在积极参与和“亲身体验”体育运动中获取对体育的认知外,更多的大学生主要通过“社交方式”“学校教育”和“媒体报道”等方式获取,分别占样本总量的7.3%、21.8%和49.4%。其中,从“媒体报道”中获取量最大,样本中95.4%的大学生会借助媒体报道了解和认识体育,仅有4.6%的大学生从来不关注媒体体育报道。可见,在当今媒介化社会里,对于直接经验越来越缺乏的大学生来说,大众传媒是他们窥探世界、获取体育认知的主要窗口,甚至已经超过了大学生的亲身体验和学校教育。
与以往“报喜不报忧”的新闻报道模式不同,现如今“负面体育报道”频繁地出现在大学生的信息流当中。通过对“负面体育报道”的接触频率进行分析,将接触频率分为“经常”“比较经常”“偶尔”“从未接触”四种情形。结果显示:接触频率为“偶尔”的最多,占样本总量的65.4%;“经常”“比较经常”和“从未接触”分别占样本的8.1%、21.4%、5.2%。如果剔除4.6%的“从不”关注体育报道的被调查者,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发现920个样本中有878个样本不同程度接触过“负面体育报道”,占有效样本的95.4%。不仅如此,67.4%的大学生会持续关注某些“负面体育报道”,追踪相关的后续报道。
总而言之,基于对体育的偏爱,大多数大学生会通过多种方式不同程度地参与体育运动,获取相关的体验和认知。大众传媒以自身独特的优势和特点成为当前我国大学生获得体育认知的主渠道。“负面体育报道”更以其内容的光怪陆离,形式的触目色变,有意无意地吸引了大多数大学生为之侧目。
2.2 大学生对“负面体育报道”的认知
费斯廷格认为:当人们“发现他们所做的事情与他们所知道的不符,或者是听到的观点与他们已有的观点不一致时”[3],就会产生认知不协调。不协调所造成的不适感会促使人们采取行动,减少不协调。为了深入地了解大学生接触“负面体育报道”之后在态度和行为上的反应,笔者对大学生的体育的已有认知、对“负面体育报道”可信度的认知和新旧认知的一致性三个变量进行了统计学分析。
2.2.1大学生对体育的已有认知对被调查大学生关于体育的已有认知分析,样本中74.3%的大学生认为体育应该是“公平公正”的。在体育运动中,不应讲门第、尊卑;不存在除个人身体、心理以外的任何不平等;最讲法制,不徇私情;最讲现实,不论资历;最讲务实,不图虚妄。体育运动要求每一个参加者都应当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去竞争,尤其是一些对抗性的运动项目,如足球、篮球、拳击等。也有25.7%的大学生认为体育可以是“美与丑并存”,因为任何事物都有正反两面性。但是错误的价值观可能导致人性的畸变,甚至不惜违反体育道德、社会公德、法律、法规。
2.2.2大学生对“负面体育报道”可信度的认知“负面体育报道”主要集中于暴露和批判那些与现行社会秩序和道德标准相冲突的观念和行为上,如假球黑哨、官员腐败、艳遇绯闻等。这些有害的、非积极的、违背社会主流价值观的体育报道在大学生心目中的可信度直接关乎大学生的认知水平以及对体育的态度。若将可信度分为五个程度,分别为“完全可信”“大多数可信”“不好辨别”“大多数不可信”和“完全不可信”。其中,可信度为“不好辨别”的最多,达到58.5%;“完全可信”“大多数可信”“大多数不可信”和“完全不可信”四个程度分别占样本总量的1.7%、25.7%、14.1%、0%。相比较而言,大学生对“负面体育报道”的可信度更趋于信任。
2.2.3大学生对新旧认知的不一致性的认知新旧认知之间的不一致是产生不协调和不适感的决定性因素。不协调的程度越高,解除不协调的压力就越大,就越可能做出相应的态度改变。样本中绝大多数大学生认为“负面体育报道”与自己已有认知存在差异,仅有2.7%的大学生感知不到差异。认知不协调必然导致心理上的不适感,心理上的不适感对于个人构造自己内心世界有着重要的影响和效力,常常推动人们去重新建构自己的认知,去根除一切搅扰。
如果将对体育持有不同看法的大学生与感知“负面体育报道”认知差异相比较,我们还进一步发现持有体育应该是“公平公正”观点的大学生更能感受到认知的不一致性,“负面体育报道”给他们带来的不适感也会更加强烈。
2.3 “负面体育报道”对大学生态度与行为的影响
在所调查的大学生中,关注“偏爱的体育项目、团队、运动员”类型体育报道的最多,占45.0%。这也正暗合了当前青年大学生对体育文化的需求与追求。“没有特别的”关注占19.3%;关注“赛场风云”的占26.8%;“幕后新闻”的占8.9%。根据研究设计,本研究着力考察在接触到自己所偏爱的体育项目、团队和运动员的负面报道时,大学生在态度与行为上所做的改变。
2.3.1大学生的态度与行为反应状况在关注体育报道时,大多数大学生通常会倾向选择关注自己偏爱的运动员的情况。63.3%的大学生所喜欢的运动员出现过“负面体育报道”,其中,报道频率为“偶尔”的最多,高达63.3%;“经常”“从不”和“没注意到”三组分别占样本的6.6%、16.4%、20.3%。
当所偏爱的运动员出现“负面体育报道”时,大学生必然会在心理上产生一定程度的不适感,并采取相应的态度与行为。将大学生的态度和行为分为四种情况,分别为“非常失望,好感全无”“一时失足,值得原谅”“寻找理由,为他辩护”和“根本不信,媒体造谣”,占样本总量比分别为10.0%、67.0%、14.1%、8.9%。
类似的情形也在大学生偏爱的体育项目、团队出现负面报道时得到验证。样本中4.8%的大学生“无法接受,改变喜好对象”;49.2%的大学生改变态度,认为“白璧微瑕,属于正常现象”;还有46.1%的大学生无法接受“负面体育报道”,选择了“尽量排斥负面信息”和“寻找理由,为之辩护”。
2.3.2大学生的态度与行为选择理由基于上述调查,当对所偏爱的体育项目、团队、运动员因“负面体育报道”的出现而产生新旧认知不一致时,大学生必然会产生心理上的不适感,并在态度和行为上做出选择来去除一切搅扰而使心理恢复平静。那么,为什么大学生的态度与行为在同一事件上表现出不一致呢?费斯廷格的认知不协调理论从“知”“行”角度入手对此做出了解释。
(1)改变行为。“因他美好而偏爱”,是部分大学生对体育项目、团队、运动员偏爱行为的动因。然而,如果“负面体育报道”的出现让部分大学生感知已有认知是错误的,那么,对大学生来说,解除认知不协调的最好方法就是改变偏爱行为。因为一旦偏爱行为得以改变,对偏爱行为的认知就会改变。因此,样本中10.0%的大学生选择“非常失望,转向其他”运动员;4.8%的大学生“无法接受,改变喜欢对象”,选择喜欢其他体育项目、团队,以此来达到解除认知不协调的目的。
(2)改变态度。费斯廷格认为,当不协调出现而又不能改变行为时,可以通过改变态度来减弱或解除不协调。对偏爱的运动员,选择“调低期望,合理评价”的大学生占样本量的8.9%;对偏爱的体育项目、团队,给出“白玉微瑕,属于正常现象”的评价占样本量的49.2%。之所以如此,在于这部分大学生理性地接受了偏爱运动员、体育项目、团队的负面报道,原来“他并不如想象中的那般美好”。这样,他们就通过改变自己对其的态度评价而使认知达到协调。
(3)增加新的认知元素。当不协调出现而又无法改变行为时,人们还可以通过增加与某一特定元素相协调的认知元素,从而提高认知系统中协调元素的比例,这也可以使不协调的程度得以减弱。因而,当接触到“负面体育报道”而又无法改变偏爱行为时,81.1%的大学生为所偏爱的运动员,5.4%的大学生为所偏爱的体育项目、团队“寻找理由,为他辩护”。
当不协调出现时,除设法减少它以外,大学生还可以能动地避开那些很可能使这种不协调增加的情境因素和信息因素,或者不去求证负面信息,回避后续报道;或是否认、贬损和声讨媒体造谣,贬损他人等。调查中发现,40.7%的大学生会为自己所偏爱的体育项目、团队做出这样的态度和行为选择。
2.4 “负面体育报道”对大学生体育态度影响的持久性
“负面体育报道”给大学生所带来的变化不仅在于促使大学生在态度和行为上做出调整,而且还将不断地丰富大学生对社会现实的主观感知。调查结果表明,38.8%的大学生认为“负面体育报道”会影响到自己对社会现实的看法。当然,也有61.2%的大学生认为“负面体育报道”不会从根本上改变自己对社会现实的认知。然而,费斯廷格认为,“当认知元素所反映的是确定无疑的现实时,改变的可能性几乎为零。”[4]“负面体育报道”一旦泛滥成灾将深刻影响大学生对社会现实的主观认知,尽管这种认知改变可以减弱认知不协调,但对大学生体育态度的影响将是长期而不易改变的。
笔者对大学生是否会因时间推移及具体情况的改变而改变对曾经出现过负面报道的体育项目、团队、运动员的态度进行了调查和分析。将态度改变的程度分为五种,分别为“绝对不会”“会有一点改变”“很大程度地改变”“完全改变”,分别占样本总量的13.3%、72.8%、12.2%、1.7%。可见,一旦基于已有认知而形成的态度将是非常牢固的。除非出现新的认知矛盾积累至足够的认知不协调量才有可能促使大学生的态度和行为发生新的改变。
3 结论
在本次调查中,97.3%的被调查者感受了对体育的已有认知与“负面体育报道”之间的不一致,尤其是认同体育应当是“公平公正”的大学生。这种认知不协调所造成的心理上不适感会更加强烈。解除不协调的压力也越大,改变态度和行为的动力或动机就越强。
“负面体育报道”所造成的认知不协调推动着大学生重建自己的认知,却除一切搅扰,达到协调一致的目的。但是,在不协调减弱过程中,认知的改变同时就伴随着抵制改变的阻力。因此,同样是接触“负面体育报道”,不同的被调查者在态度和行为上所做出的选择却存在着很大差异。或是选择改变行为,或是选择改变态度,或是选择增加新的认知元素,或是能动地避开那些很可能使这种不协调增加的情境因素和信息因素,来达到解除或减弱不协调的目的。
态度改变的最大的阻力来自环境,环境本身也是抵抗改变的因素。“负面体育报道”多大程度地寻求社会的支持,就有多大可能促成旧态度的转变,新态度的形成。调查结果表明,目前有61.2%的大学生认为“负面体育报道”不会从根本上改变自己对社会现实的认知,意味着我国大学生所处的环境因素对体育运动依然保有良好的期待和支持;调查中数据也显示了当前大多数大学生并没有因为“负面体育报道”的频繁出现而从根本上改变自己已有的对体育的态度。
“负面体育报道”是大学生解读世界的重要钥匙和认知元素。如果运用不得当,大学生一旦依此做出态度和行为上的调整,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将是长期深远而持久的。因此,“负面体育报道”虽然有预警监督等功能,但也需要整治媒介环境,释放其正能量,规避负能量。受众,尤其是大学生,则需要努力提高自身媒介素养,理性对待传媒报道,避免深陷其中,为之左右。
[1] 蔡明明,曲业煌,李江.对“负面体育信息”与“负面体育报道”关系的再论证[J].南京体育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11(5):26~28.
[2] 申荷永.社会心理学原理和应用[M].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1999.
[3] 理查德·韦斯特,林恩·H·特纳.传播理论导引:分析与应用[M].刘海龙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4] 朱芸,张锋.认知不协调理论述评[J].外国教育资料,1998(6):27~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