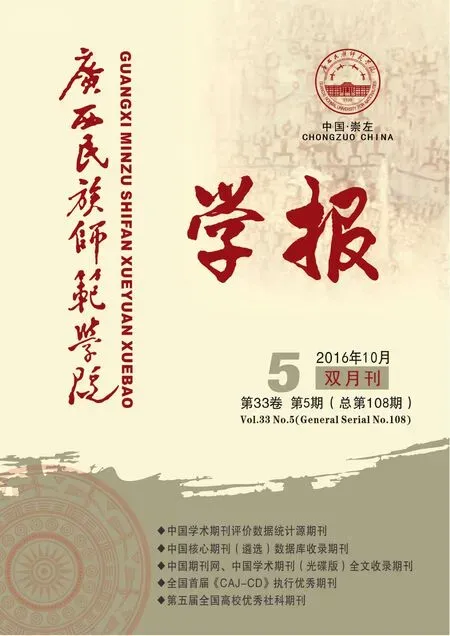龙舟习俗与地域社会建构
——以小洲村为例
黄素娟
(广东财经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华南商业史研究中心,广东广州510320)
龙舟习俗与地域社会建构
——以小洲村为例
黄素娟
(广东财经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华南商业史研究中心,广东广州510320)
龙舟习俗被视为是传统岭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构建乡村社会关系网络的一种重要手段。小洲村的龙舟活动在村内通过宗族血缘关系与地缘关系进行组织,而在村外则起着缔结联盟的作用。与本村关系最为紧密的盟友互称为“兄弟村”,关系较疏远的称为“老表村”。而关系不好的乡村,即便是近邻,双方也不会有龙舟来往。
小洲村;龙舟;地域社会
在今天,龙舟习俗被视为是传统岭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小洲村地处广州市海珠区东南隅,为珠江、河涌所环绕,与诸多的岭南水乡一样拥有悠久的龙舟文化传统。2014年5月28日,端午节前夕,广州本地生活网站——“广州本地宝”围绕着端午节习俗,推出了《小洲村2014年看龙舟赛全攻略》专题报道。编辑在旅游攻略中强烈推荐广州市民在端午节当日到海珠区小洲等村落观赏极具岭南水乡特色的龙舟活动,其在网页上如此推介:
仑头、小洲及土华三村靠近珠江口,江面非常宽阔,超过百米,六七十艘龙舟集会有气势。仑头、小洲是保存不错的岭南水乡,风景秀丽,很适宜一家大小看龙舟。[1]可见,小洲及其附近的村落的龙舟活动被视为品味传统岭南文化的重要方式。随后许多媒体更是不吝篇幅对其进行深入追踪报道。各大媒体不断“帮助”读者与观众找寻与解读小洲龙舟活动的各种细节。端午节当晚,广东电视台更是在黄金节目《今日关注》中详细报道了小洲龙舟活动的盛况。翌日,这一报道又被中央电视台的新闻栏目选中。中央电视台将小洲龙舟活动作为典型的广东民俗介绍给全国的电视观众。在经过各级媒体的层层渲染之后,小洲的龙舟活动已成为了广州市重要的文化景观。
而回到小洲村的乡村发展脉络中,龙舟活动不只是一种乡村民俗,更是构建地域社会关系网络一种重要手段。至今,村中仍流传着不少关于龙舟的故事,一种说法是新中国成立前,小洲每年爬龙舟都是架着机关枪去的;另一种说法是小洲的九条龙舟出去,十条龙舟回来——即抢夺了一艘龙舟带回来之意。每当村民们讲起这些“架势”(粤语,意为“厉害的”)的故事,脸上掩不住地都是笑意。这是令他们倍感骄傲的辉煌过去,代表着小洲村的兴盛。细细品味却会发现,当中隐含着乡村之间社会关系的玄机。
一、水路与龙舟仪式
水路网络,既是水乡经济活动的中心,也是龙舟活动的基础。小洲村地处河南岛东南部水道交错,密如蛛网,一部分为天然的河流,而一部分则是人工开凿的水道。大体上说,在珠江前航道的黄埔涌由河南岛北部入口,分为两支:一支向东行,由黄埔村附近出口;另一支则向东南流经花岗与松岗之间,名为赤沙滘,至石榴岗东南会合南部诸水道而入珠江南支。岛的南部是珠江后航道,又有“沥滘涌”。岛内还有各种大小不一、人工开凿的沟渠,纵横交错。[2]185围绕着小洲的两条河涌,称为“西江涌”和“细涌”,均流经瀛洲古码头,汇入官洲河面。小洲村内的简氏宗祠都濒临河道,面涌而建。河涌网络的一边是往省城广州,运输米粮、蔬菜、水果至米栏、菜栏和果栏;另一边是联络外乡,通过新洲、黄埔水道可以直下香港。河涌环绕的地理环境使得舟楫在水乡人们的生活中有着独一无二的重要性,既是衣食住行必备的交通工具,也是交际往来、情感交流的方式。最常见的是靠人力划的小艇,每户村民都有一艘。还有用以载客的客艇,多搭竹篷以遮蔽雨水和日光,大艇可容十或十余人。用于载水果、蔬菜、稻谷、河泥的,称“果艇”“菜艇”“米艇”“泥艇”或“马鞍艇”等。而龙舟并非人们日常生活的交通工具,它是人们用以表达情感的仪式性工具。
“爬龙舟”是小洲全村共同的盛典,村民们以宗族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参与其中。相传小洲开村于元末明初,村中现在仍流传着“邱、黄、梁、饶、林、钟六姓开村”的故事。明初,简姓迁入,使得小洲成为简氏族人的聚居地。目前村内有常住人口6500人,90%以上为简姓。保存至今的简氏宗祠有十余座之多,分东源公与西溪公两大派系,均为克成祖之后。村内按地段划分为东、西、南、北、中五约,约下为社。“社”指的是由生产队演变而来经济合作社,全村共有十六个社。其中第一、第十六社为北约,第二、第三社为东约,第四、第五、第六、第七、第八、第九社为南约,第十、第十一为中约,第十二、第十三、第十四社为西约。此外,第十五社为公社化时期从各社抽人组成。中约与西约地段相连,联系紧密,统称“中西约”。龙舟是以约为活动单位,每个约是一个独立的经济核算单位,有各自临时组织筹备的“龙船会”。会员是经济合作社的社长,负责龙舟活动的经费筹措和物资采购。而各约龙舟活动的地点则是约内最大的祠堂。龙船会办公、张贴龙舟募捐名单和活动安排事宜、举行龙舟仪式、约内村民“吃龙船饭”均在祠堂进行。参与的村民各有分工。划船的是成年男子,上船后或敲锣打鼓或充当桡手,或为揸胎(即掌舵人),或扶神、摇长幡、放鞭炮。这是所有男丁的责任和义务。一个男丁如果不去爬龙舟,会被同龄人耻笑,也会被家长责骂。①年长者一般不再上船,在岸上充当仪式指导,或在接景时充当“接锣”招引龙舟。妇女不能上龙舟,一般负责拜神及充当后勤,烧龙舟茶、派龙舟饼、安排“龙船饭”等事宜。为了人身安全,小孩一般不上龙舟。但在五月初六会安排所有男孩上船体验。这种安排显然是有意识地培养孩子对于龙舟活动的认同感。
龙舟是一种隆重而庄严神圣的活动,有既定的仪式程序。除了“请龙归乡”,每年小洲的龙舟活动大致包括:四月初“起龙”,五月初一“采青”,五月初二“接景”,五月初三至初五外出探亲,五月初六男孩划龙舟,五月初七日“藏龙”。主要的仪式活动如下:
(一)请龙归乡
小洲村目前有两种龙舟,一种称为“传统龙”,长12丈(约40米),可以乘坐70~80男丁;一种称为“细龙”,即国际标准龙舟,乘坐22~23人。“传统龙”是以约为单位,每约拥有1艘,全村共4艘。“细龙”则是青年爱好者自发组成的龙船协会组织,现有7艘。珠江三角洲地区所见的这两种龙舟都是在番禺区大石镇的上滘村制作。上滘村有十几间龙舟作坊,造龙舟已有140多年的历史,素以“样式好、密度高、扒得快、够坚牢”而驰名于珠三角地区。[3]164在过去,购置一条新龙舟是一件非常神圣的事。据老人回忆,新龙舟造好下水的时候,必定要桃20~30名青年带备新挠桨到船坞去“请龙归村”。下水前,“要拜一轮神仙,又要烧一轮炮仗,又要请喃呒先生来为新龙点睛,又要洒过圣水,这样才能够落船。”②下水后,将本村村庙中的“神”请到船上,指派专人“扶神”。这样才能划回自己家乡。但近年,这种仪式已日渐消失。新造的龙舟是一般是由汽车运载回村。
(二)起龙
每年四月初,龙船会就要召集人手“起龙”,即将龙舟从深涌淤泥里挖起、洗净。故民谚有云“四月八,龙舟透底挖”。②清末民国时期,起龙后即要到姚大总管庙中去“请龙”。该庙供奉的是明代洪武乙丑(1385年)进士姚观文。据姚氏族谱记载,姚观文官直隶监察御史、经略大总管。他生平“孝友渊睦,矜穷恤困,解衣推食,当时咸称”。因此在他死后,人们便在瀛洲之阳(即小洲村北面)立庙供奉,“绘塑真容立庙祀,致敬为感应威灵姚大总管之神焉。”[4]新中国成立后姚大总管庙被拆毁,请龙的仪式也就随之而逝。③起龙后龙舟要晾干、上油、修饰,放置在祠堂门口,等待五月初一的正式活动。
(三)采青
五月初一是小洲村龙舟装龙头、采青的日子。装龙头前先得“点龙头灯”,即用小刀割下公鸡鸡冠的一角,然后用事先沾过生姜的毛笔(寓意“生生猛猛”)沾上鸡冠的鲜血点在龙眼上。接下来是拜龙头仪式:先烧几串小炮仗,然后在龙头前摆上一个装满供品和两张神符的竹筐,然后焚香祷祝、再烧炮仗,最后将龙头安装到龙舟上,并将神符分别贴在龙头和龙尾。随后要对龙舟进行装饰。每条龙舟的配置一个大鼓、四个锣架和各挂铜锣一面,每面铜锣配刺绣罗伞一顶。船头与罗伞等距的船舱中还设一个木制小神龛,称为“门官庵”。神龛亦配刺绣罗伞一顶。在大鼓旁则是一面长幡,而头锣架和二锣架之间的是一面黑底白字的姓氏旗,上书“瀛洲简氏”。有时还会放置一面黑底白色的七星旗,象征本村的主神北帝。在龙头龙尾位各有4面红色小长条标旗,上书“瀛洲飞龙”。装饰好后的龙舟大张旗鼓,神采奕奕。到探亲时,龙头、龙尾、锣架、打鼓的位置都是要通过“投墨”的方式来竞投。装饰好的龙舟就可以去采青了。将龙舟划出码头,直达村外河边,就地采拔岸边上的野草挂于龙头、龙尾上,表示龙“吃青”。之后,一路敲锣打鼓,边放鞭炮边爬回码头,便大功告成。据说以前采青是要到稻田里采几株禾苗,寓意五谷丰登;但如今已无稻田,只好采些青草代替。④完成采青仪式后,龙舟便开始探亲,通常首先是在村内互访祠堂。龙舟在村内的河涌来回划行,互拜祠堂,而这恰好成为展示村内各约人口与经济实力的场合。例如中西约龙舟的路线是从西溪简公祠出发,沿沿河涌方向到达瀛洲古码头,经过简佛祖庙,抵达简氏大宗祠,再经东池简公祠,然后回龙,再至瀛洲古码头,最后回到西溪简公祠。每到一个祠堂前,龙舟便要烧炮以示来访,而岸上村民也要烧炮表示欢迎,场面极为热闹。此时村内各约隐约间会相互比较桡手和炮仗的多寡,这正是村中各约人口与经济实力的体现。一条传统龙舟可以乘坐70~80男丁,从一艘龙舟上桡手的多寡可以看出一个约人丁的兴旺程度。但由于近年来越来越青年加入了龙船协会,去爬“细龙”,所以几个约的龙舟都有“人丁不足”之虞。龙舟活动除了持续供应的茶水、龙舟饼、龙舟饭外,还要燃放大量鞭炮、制作彩旗标语,以及要租赁指挥船只等等,需要耗费大量金钱。因此,一个约的经济状态往往决定了龙舟活动的盛大与否。2015年中西约龙舟获得的捐赠和赞助高达近9万元,明显高于其他各约,所以他们燃放的鞭炮最大亦最多。当然,龙舟活动更重要的是体现小洲村与其他乡村的关系。
二、龙舟与乡村联盟
小洲村的龙舟活动水域涵盖了珠江前、后两航道周围的五十多个乡村。包括河南岛上的小洲、土华、仑头、赤沙、石榴岗、龙潭、新村、大塘、上涌、沥滘等10个乡村;珠江后航道南岸的大石、新基、员岗、陈边、板桥、市头、曾边和新造等8个乡村;官洲水面的官洲、北亭、南步、贝岗、赤坎、南亭、长洲等7个乡村;黄埔水面的新洲、新村、石基、华坑、下沙、塘口、鱼珠、石溪、珠村等9个乡村;珠江前航道沿岸的琶洲、沙溪、宦溪、东圃、黄村、车陂、棠下、程界、员村、谭村、渔村、猎德、冼村、石牌、寺右、杨箕等16个乡村。端午期间,这些乡村的龙舟你来我往,相互探亲趁景。
“龙舟景”指的是各地有龙舟的乡村按当地自然地域、潮汐而约定俗成在某月某日进行龙舟竞赛或相互探访。龙舟聚集的地方,谓之为“景”,又有大景小景之别。清末民国期间,茭塘司著名的龙舟景有五月初一新洲景、五月初二官山景、五月初三市头景、五月初四新造景等。其中官山景和新造景最为热闹。官山是邻近小洲村一个墟市,隔河与官洲对望,河面宽阔而水流缓慢,有利于龙舟聚集,且河两岸可容纳上万观众。因此鹿步司、慕德里以及东莞等各地的龙舟都会来趁景。新造1932年成为番禺县府所在地,江面宽阔,江岸线长,成为禺南最有号召力的龙舟竞渡场地。据说民国年间严博球任县长时,在新造景招赛,有百多艘龙舟参加竞渡,观看者有数万人之众。[5]176-177时至今日,各乡村仍保留了趁景的习俗。农历五月初一深涌景,接景的是东圃、珠村、黄村等乡村;五月初二仑头景(又称“官山景”),接景的是小洲、仑头、土华、官洲等乡村;五月初三龙溪景(又称“车陂景”),接景的是车陂等乡村;五月初四下沙景,接景的是文冲、庙头等乡村;五月初五广州景,接景的是猎德、石牌、冼村、杨箕村等乡村。⑤
龙舟探亲趁景实际上是乡村间缔结联盟,互相来往、联络感情的一种方式。为了获得更好的生存资源,水乡的乡村之间通过宗族血缘、婚姻关系、相互救助等方式缔结联盟。这种关系体现在称呼上,与本村关系最紧密的盟友互称“兄弟村”,与本村关系较疏离的称“老表村”。龙舟探亲时,这两种村落互动的礼仪明显有所差异。兄弟村之间会互拜祠堂,开席宴请“龙船饭”;老表村之间则互送拜帖,上岸休息、吃茶点。而关系不好的乡村,即便是近邻,也不会有龙舟来往。
小洲有两个“兄弟村”,一个是车陂简氏,一个是下沙村。车陂简氏与小洲联盟的基础是宗族血缘关系。新中国成立前,车陂按有祠堂的姓氏划分为8个约,简氏与王姓、黎姓同住在车陂涌东岸,建有同章简公祠。[6]39同村建有祠堂的还有郝、苏、王、梁、黄、黎、马、麦等姓氏。由于车陂简氏在人口和经济实力上均不占优势,所以不得不结交盟友,以便不受同村其他姓氏的欺辱。除了小洲村,车陂简氏与黄村也互称“兄弟村”。据小洲村老人们的回忆,车陂简氏过去人丁少,也比较贫困。每逢小洲龙舟去探亲,车陂简氏要全族出来接待,连七八岁的小孩也要帮忙端茶递水。偶尔还会发生无法供应龙舟饼、龙舟茶的窘况。⑥如今车陂简氏的经济已大大改善,而小洲村近年的经济发展却相对迟滞,这令不少小洲老人不胜唏嘘。小洲的另一个兄弟村是下沙村,但下沙并无简姓。关于两村如何成为“兄弟”,小洲村至今仍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抗日时期,下沙村民逃难到小洲,在小洲躲过一劫,避免了亡村。于是下沙的先祖告诫后人“没有小洲,就没有下沙”,须世代交好。①可见,小洲与下沙联盟的基础是互相救助。直至今日,小洲村与车陂简氏、下沙两村关系仍很紧密。每逢五月初二日,车陂简氏和下沙村的龙舟都会到小洲趁景。龙舟沿河涌划到简氏宗祠上岸,拜祭过祠堂后,小洲村民会热情招待他们到酒楼吃龙船饭。而五月初三、初四日,小洲龙舟则分别到车陂和下沙探亲。除了四个约的传统龙舟外,由年轻的龙舟爱好者组成的7条细龙也会随行。每约配一艘指挥船,随行补给茶水和龙舟饭。这样,参与小洲龙舟探亲的成员多达近500人,浩浩荡荡,气势恢宏。在村民看来,这种宏大场面是极有“面子”的。
除兄弟村外,其他到小洲趁景的乡村都被笼统称为“老表村”。每逢五月初二日,小洲龙舟会早早在瀛洲古码头准备好龙舟饼和龙舟茶,负责招引龙舟的“接锣”老人在岸边严阵以待。早点九点前后,龙舟陆续入闸前来趁景。龙舟上鼓声阵阵伴随炮仗声声,而岸上“接锣”则敲打铜锣表示欢迎。龙舟靠岸前要来洄游弋三两趟,以示意礼貌。接待的工作人员则会热情地招呼老表入村喝茶、吃饼。趁景的乡村要递上拜帖,上书“敬领谢贝岗南约村民拜”等字样;而接景的乡村也要回以龙舟帖,上书“敬领谢瀛洲飞龙仝仁鞠躬”等字样。这些拜帖会被张贴到醒目的公告栏上。每张拜帖代表一艘船,越多龙舟来探访就表明本村越有“面子”。据统计,2014来小洲趁景的龙舟约有110艘;而2015年增加至145艘。这些龙舟来自附近的46个乡村(见表1)。同样地,小洲龙舟亦会在趁景之际拜访其他乡村。2015年端午期间,小洲龙舟共拜访了北亭、官洲、车陂、黄埔、新洲、仑头、下沙、棠下、珠村、渔民新村、石基、琶洲、猎德、寺佑和贝岗等15个乡村。

表1 2015年小洲村龙舟拜帖村落及其龙舟数
而与本村关系不好的乡村,即便是近邻,双方也不会来往探亲。小洲村与土华村就是例证。两村地段相邻,相隔一条河涌。清代光绪年间,小洲与土华因为争挖河涌淤泥而发生冲突。小洲人坚持认为自己在官涌取泥,土华人认为其取土华的田里取泥,遂引发激烈械斗。双方冲突持续多年,一度相互炮轰,两村均有多人伤亡。最终不得不由番禺县官府和附近的乡绅出面调解。[7]两村自此互视为仇敌,互不通婚。一到龙舟时节,青年们聚集,极易发生打架斗殴,两村遂无龙舟往来。新中国成立后,两村同属于新滘公社,关系有所缓解,开始通婚,也曾有过短暂的交往。2000年前后,两村因在车陂水面附近发生龙舟的相互碰蹭,再次爆发激烈的斗殴。此后,双方再无龙舟往来。⑥至今,土华龙舟经过小洲水面仍是不动声色,匆匆划过。
结语
通过梳理小洲村龙舟活动的情况,可以看到龙舟习俗体现着水乡村落间的各种社会关系。在村内,龙舟活动通过宗族血缘和地缘关系相互连接,并展示出不同约与宗族房支的人口与经济实力;在村际间,龙舟是建立盟约、构建乡村社会秩序的文化手段,体现着各乡村间社会地位的差异。在龙舟习俗中人多势众的热闹场面,既是对乡村经济实力的最好展示,也是村民们共同构建的自我认同与集体认同。
时至今日,随着城市化进展的加快与现代化生活方式的出现,城市郊区的乡村文化日渐有消失之虞。附着在小洲村龙舟文化的内在意涵也正在发生着重大的改变。在龙舟仪式中,请龙拜神等环节逐渐弱化。青年一代龙舟爱好者逐渐加入龙船协会组织的“细龙”,而导致“传统龙”人丁日少。随着周围乡村经济的发展,小洲村原本作为帮助弱小乡村的角色也日渐衰微。但正如前述各大媒体的关注,对于热爱岭南传统文化的知识精英、媒体人及普通市民而言,小洲龙舟已然是岭南传统文化的代名词,是他们守护岭南传统文化的重要阵地。这种城市与乡村文化相互构建的过程则是另一个有待探讨的课题。⑦
注释:
①据2015年6月17日采访。
②据2014年11月29日采访。
③据2014年10月18日和2015年6月20日采访。
④据2015年6月16日采访。
⑤见小洲村龙舟宣传单。
⑥据2015年6月18日采访。
⑦论文调查过程中得到广州市海珠区华州街道办、小洲村委会、小洲村父老的大力支持,以及陈艳瑜、黄祎、周易、林绮纯等同学的帮忙,特此致谢!
[1]本地宝整理.小洲村2014端午节看龙舟赛全攻略[O L]. http://gz.bendibao.com/tour/2014528/ly160705.shtml,2015-5-28.
[2]梁溥.广州河南岛的聚落地理[J].勷勤大学.1935.
[3]屈九,可张.番禺龙舟杂谈.番禺文史资料第十七期[M].广州市番禺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2004.
[4]姚斌.番禺姚氏先贤立目和列传[O L].http://blog.sina. com.cn/s/blog_6c1c123a0100t6ut.html,2011-8-7.
[5]梁谋.番禺龙舟习俗.番禺文史资料第十七期[M].广州市番禺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2004.
[6]天河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车陂村志[M].北京:中华书局,2003.
[7]粤东简氏大同谱[M].卷十.
责任编辑:谢雪莲
The Custom of Dragon Boat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Regional Society——A Case Study of Xiaozhou Village
HUANG Su-juan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inance&Economics,Guangzhou,510320)
The custom of dragon boat is regarded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traditional Lingnan culture,and is also an import way to construct the network of rural social relations.Dragon boat activity in Xiaozhou village is organized through the clan kinship and geographical relation.While,outside the village,dragon boat activity plays the role of forming alliances.The most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the village is called Brother Village,and the alienated called Cousin Village.The two sides with bad relationship, even close neighbors,also won't have the dragon boat relationship.
Xiaozhou Village,dragon boat,regional society
B93
A
1674-8891(2016)05-0048-04
2016-06-19
本文系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二五”规划2014年度青年项目“近代广州城市土地产权研究”(项目号:GD14YLS01),以及参与的广东财经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华南商业史研究中心与广州市海珠区华洲街道办合作的项目“小洲村历史文化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黄素娟(1982—),广东河源人,历史学博士,广东财经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应用社会学系讲师,主要研究方向:近代广州城市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