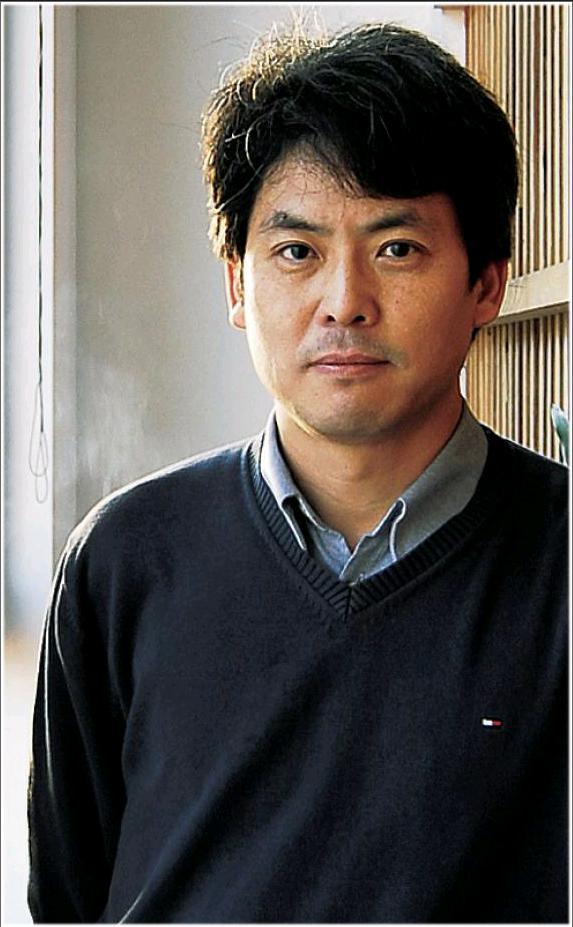周恺:穿越建筑的唯美
周恺这位公认的建筑界的大帅哥,其建筑设计作品也颇具美学修养,唯美而有韵律。此次,他的同门师兄崔恺作为提问者既追溯了其审美养成的多元背景,也探讨了他的设计思维逻辑,同时也提出了在当下中国必须面对的问题:建筑设计的中国性应该如何表达?
崔恺:从学习建筑这方面来讲,你是很有天分的学生,非常突出。你在学建筑之前有没有对空间的感受或者对美的培养?你以前的基础是什么?
周恺:我学建筑学纯属偶然,但也有必然。小的时候,据我父母说从两岁多就开始画画,也没有人教我,反正就是喜欢画。高考后回家商量专业,我父亲就说学建筑学吧,反正也爱画,找个轻省的活干,没想到找了个这一生最累的活。那时候不懂空间感受,有的只是美术方面的一些熏陶。
美·形式·静态·动态
崔恺:就美术这么一个称谓来讲,往往会把东西做得很漂亮,或者说是形式美。形式的东西很重,我的问题也是在这儿。我看你的建筑,首先一点是很漂亮,这件事跟你原来画画喜欢美术的背景有关。有很多人认为建筑不是平面的,也不是一个平面加上另外一个平面,而是一个连贯的空间体验。就你这样的背景,是不是你美术的基础影响了你思维的习惯,使你更重视平面,或者说某一个静止空间的影像在脑子里特别强。是不是这样?
周恺:首先我同意说建筑是一个连贯的空间体验,空间的营造也始终是我在设计中的重点。但的确在设计中有唯美成分,很可能在天大的学习经历有影响。其实您的设计在某些时候我也能感到有些类似,是否我们都读过彭一刚先生的研究生,受先生的影响更大一些呢?
崔恺:这一点我也很有认同,彭先生对我们俩的影响都是很大的,比如学生时代的训练。
周恺:我补充—下,在做设计中我从没刻意强化过形式美,尤其在近几年,那完全不是我的重点,可有时还是有人这样看。
崔恺:变成一种职业习惯了。
周恺:三下两下就那样儿了。
崔恺:很多人要达到唯美的感觉,非常不容易,因为没有这个基础,或者说他的想像力不够,他的训练不够。坦率说,我们都作为彭先生的学生,彭先生对你的评价是很高的。如果用审美、用形式美来判断一个学生的才华,或者学生的潜质,我觉得彭先生显然是偏向你的。不光彭先生这么认为,我自己也是这么认为的,你的基础更好一些。
我想到彭先生做设计的时候,对画面质量的要求是极高的。换句话说,他的建筑一定要有一个特别好的,跟他透视图完全一样的画面呈现,但是,彭先生没画另外一个透视的时候,那个透视就不在他的有效控制之内。你有没有这样感觉?
周恺:有过,我可能很多地方都跟彭先生有点像,您刚才说的这个情况彭先生多多少少也聊过。后来我感觉这个东西就是你的习惯,或者你的方式。后期我试图做过很多不同的改变,但是有一个惯性,我也在做这方面的尝试,但是怎么变底子还是有影子,我想这个东西不是随便就能改变的,可能需要一些大的刺激。
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
崔恺: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在天大校园内,我们非常熟悉的环境当中,一个湖边上,旁边有一些既定的老房子,一边是原先设计院的办公楼,一边是体育馆。上学时早上曾经坐在那儿背外语、打乒乓球什么的。这个房子我很喜欢,我喜欢它,更多来自于我初看到你那个房子的设计时,那种视觉上的愉悦,空间上的整合。建成以后我也去过几次,尤其前不久跟很多建筑师去参观。一个放在校园里边的建筑,你用一个完型的空间系统把它自我完成,跟校园的界面,有开放的地方,有些时候又是一个隔离。这使我有几个问题:
第一,你认为这样一个校园的建筑是独善其身好呢,还是向学校开放的好?
第二,对周围不同历史时期的建筑,你觉得应该是对比的好,还是协调的好?
第三,对建筑自身在里面表达的建筑情结,或者一种文化情结,跟校园总体环境是什么样的关系?或者是试图施加一种什么样的影响?
周恺:其实我希望这个建筑有一定的封闭性,因为建筑的对面是体育场,南面是实验室,北面是小体育馆,只有朝向西边是一个湖,还被另一个房子遮挡了一半。另外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也有一些的特性,在工科院校引入一个人文色彩很浓的学院,这是学校的用意。当时我跟冯先生聊了很多次,希望在这里给学生们创造一个跟校园其他的空间不太一样,有些意境的东西。这也是冯先生当时跟我聊得最多的,当时他还有一些要求,希望这个建筑是给中国人用的,倒不强调一定是中国的传统形式,希望这个房子是现代的,但是是有东方色彩的,跟中国人居住理念、场所理念相融的。
这个房子有一定的围合感,是一个院子,当你进入的时候,希望有一种不一样的空间感受,你的心境能够被这个空间感染。虽然围合着,但这个院子是可以自由穿过的,它更像是一个容器放在地上。当穿过这个院子时,你能感受到空间围合对你的制约。你看不到周边的建筑,能看到的是保留的树木、水和一片属于你自己的天空。
第二个问题设计中也有回答。这个房子跟周边的老建筑,它的秩序和高度是呼应的,在外墙的材料、色调,以及明暗关系上是相融的。我刻意保留了基地上原有的树木。你要是不太经意,从路边走过去,不会注意到这个房子。我希望房子在学校原来的秩序上,不是突兀的,是融在校园里面的,但我又不希望它向周边的语言靠。这个房子在某种意义上是协调的,但在它的院子内部是强调自己个性的。
我是先做了院子,再把房子放到院子里,当然房子和院子是合二为一的。再把建筑底部架空,把院子还回来,水池和保留下来的树木,也是希望强调一种环境和建筑的相融性,强调建筑对原来环境的尊重,甚至对某种记忆的尊重。比如说原球场边的那排树,它现在还在,盖了新建筑,球场不见了,但树还在。我希望大家走进去的时候,能感受到跟其他教学楼不太一样,但还有某种联想。使用中,院子的主人又不断往里面加了不少东西,这个院子原来是空的,只有树,后来冯先生搬来一个老的门楼放进去,又找来老船和两块石头。
崔恺:变成一个收藏的地方。
周恺:原先这个房子能够直接穿过,但后来因为穿越的人太多,据冯先生说管理上不方便,他便把院子前后加上了门,在使用上和原来的设计,是有些不一样的。
崔恺:我非常同意你刚才解释的设计思路,因为我也有类似的一些经历。你刚才说到这个设计冯先生希望是一个中国性的东西,带有中国、文化,传递这么一个价值观。你采用的策略是蛮中国的,因为中国文太的东西实际上原本就发生院子里边,实际上中国整个城市都发生在院子里边。这原本是一个很有逻辑性的事,但是从天津大学、从你的建筑的周围环境,以及从整个中国城市的变迁来看,这个中国性已经慢慢消失了。大家现在看到院子反而不认识了,或者说并不敏感这个院子本身带来中国性的问题。我们设想如果把曾经的这些楼,前面都加上院子,如果我们把现在正在新建的这些建筑,都要求以院落、书院形式来做,我相信完全是另一个格局,可能会很东方的。但实际上又不是这样,反而这个院子设计在这里变得很特殊了,别的建筑都是开敞的,这儿有一个院子,围起来了,不仅仅是围起来,因为在使用上的一些顾虑又把它封闭起来了。这是我的困惑,并不是提给你的问题。
我上次在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走的时候,有很多人一起参观,其中有一个情景:很多人都在走中间那个大楼梯,上去的时候所有人都奇怪,这楼梯上去干什么呢?因为走上去发现是一个小门,就觉得这楼梯是不是有问题?这楼梯上哪去?当时很多人在嘀咕。我原先在想这可能不是一个楼梯,这根本就是一个阶梯教室。我又想,一个建筑空间在表达的时候,跟使用方式实际是有关系的,这种使用方式如何能够让人辨认?能够让人正确的使用?在很多具体项目当中,我们追求某种空间的趣味,如何能够恰当地跟使用要求有关?对这个问题,我是可以了解和理解的,但对很多人来讲不太理解,这种情况在你的其他项目当中有没有?
周恺:好像不多。当然这种解释其实没意思,我也不想这么来解释。这房子本来中间是一个中厅,其实也有内院的感觉,上面有天光,是两排房子夹着一个厅。至于上面做的楼梯,它既在下面形成了展厅的储藏空间,又在上面形成了一个开敞的阶梯教室。我们可以看到楼梯跟这个房子是一样宽,在上面有一个偏置的栏杆,把它分成台阶和坐凳,坐凳上原设有木板,这个木板施工时没钱做,所以我不想为它多解释。后来冯先生做了很多垫子,开会时才会拿出来给大家用。
崔恺:那天垫子没在那儿。
周恺:开会的时候才给大家拿过来。另外空间也是可以有不同的使用方式和理解。如果每个东西都是一一对应的,我倒觉得不会有趣。我甚至鼓励使用者,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利用空间。后来冯先生也在这里面搞过各种不一样的东西,把它变成展厅、把它变成一个发布会的台子等等。
崔恺:这件事让我觉得,建筑实际上是一种中间状态,如果把人的活动作为它的终极状态的话,实际上建筑就是一种中间状态。换句话说你完成的是一个具有可能性的空间装置,它会继续被发展、完善,或者改用。我们也相信有品位的使用者,他们会使这个建筑更有意思。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应该是这么一个例子,它没完,它有很多可能性,它每一天可能都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