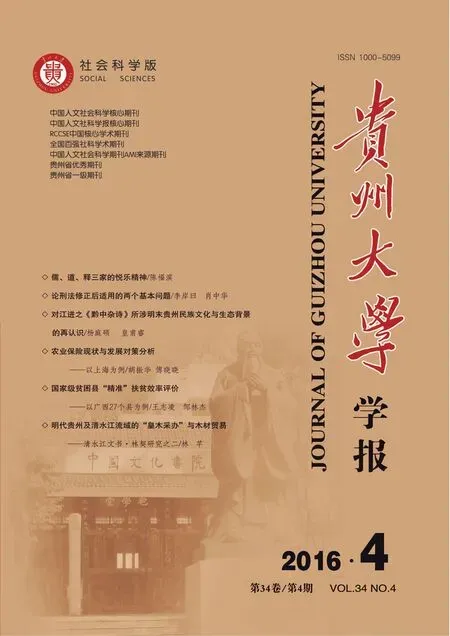打造梵净山“佛光之城”的文化枢纽地位及其实践路径
栾成斌,杨春华
(1.贵州大学 中国文化书院,贵州 贵阳 550025;2.贵州大学 历史与民族文化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
打造梵净山“佛光之城”的文化枢纽地位及其实践路径
栾成斌1,杨春华2
(1.贵州大学 中国文化书院,贵州贵阳550025;2.贵州大学 历史与民族文化学院,贵州贵阳550025)
梵净山地区由于自身的区位优势,明清以来的统治者意在将其作为区域文化枢纽而打造,在万历、康熙两朝尤为突出。梵净山佛学的这两次关键重兴,都与当时军政形势密不可分,成为中央王朝边疆治理战略的重要一环。梵净山佛学义理的根本在于弥勒净土,净土观念的深度研究有必要成为该区域旅游文化事业发展之基础,而近代以降以太虚一脉为代表的“人间佛教”净土思想可以作为理论借鉴。弥勒净土的当下实践需要从心灵层面与社会公益层面统筹打造,并具备强有力的文化抓手和更宽广的交流视野,吸取已经成熟的运作经验,为区域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提供契理契机的坚实支撑。
梵净山;文化枢纽;净土;人间佛教
国际DOI编码:10.15958/j.cnki.gdxbshb.2016.04.021
梵净山处于贵州、湖南、四川(今重庆)三省交界地区,是古代武陵五溪各少数民族交流融汇的重要区域。梵净山开发最早可以追溯到西汉时期,而佛教的传入则肇始于北宋初年;至明清之际,梵净山开发达到一个高峰阶段,特别以万历、康熙两朝皇权力量介入,促进梵净山重建开发与佛教文化的两次高潮,从而崛起成为与四川峨眉、云南鸡足鼎立而三的西南佛教名山。概而言之,梵净山在西南地区重要历史地位的形成,一方面除了佛教内在理路的继承和发展因素之外,另一方面更是因为其特殊的地理环境、民族关系,以及与周边政治军事形势的重要性,而对中原王朝管辖区域的重建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梵净山明清之际出现的两次佛教文化与旅游开发的高潮,都与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成为中央王朝借以教化民众、加强治理边疆的重要一环。当前,梵净山开发与旅游发展进入到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国务院《国发2号文件》明确提出,贵州要“建设梵净山等精品景区,培育‘梵天净土’等一批旅游休闲度假胜地”。梵净山当地的江口县也提出,要把梵净山打造成为“佛光之城”。本文从历史地理角度观察梵净山文化枢纽地位的形成,并研究其路径与方法,以为当前梵净山开放和旅游发展提供一些现实启发和借鉴作用。
一、从历史地理角度观察梵净山的文化枢纽地位
梵净山既是西南地区一座历史悠久、文化深厚的佛教名山,又是中国著名的“弥勒菩萨道场”。梵净山核心地区位于贵州省东北部江口、印江、松桃三县边境,方圆达六七百里,最高峰凤凰山海拔2572米,老金顶(玉皇顶)2494米,新金顶(红云顶)2336米,三峰高耸,不仅是云贵高原上相对高度最高的山峰,而且还是武陵山脉的主峰,于汉代正式得名“三山谷”*《汉书·地理志》“辰阳”条载:“三山谷,辰水所出;南入沅,七百五十里。”三山谷,即今梵净山;辰水,即源于梵净山的贵州锦江,经铜仁入湖南,汇沅江后流入洞庭湖。。梵净山处于古代“武陵五溪”腹地,自战国秦汉以来就一直是当地“武陵蛮夷”朝拜的神山、圣山。北宋时期,佛教正式传入该山。[1]318因此,梵净山不仅具有两千多年的武陵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底蕴,而且还有一千多年的佛教传承历史,[2]成为外来文化与本土区域文化交流融汇的重要节点。明清时期,万历皇帝、康熙皇帝对这一节点善加运用,前后两次加冕敕封,使得梵净山成为“贵州第一佛教名山”和著名的“中国弥勒菩萨道场”。
以民族政策作为政治号召的明王朝建立后,对贵州地区少数民族采取安抚政策,这种安抚政策一直持续到永乐十一年(1413),梵净山附近思南、思州土司因争夺矿场发生混战,明朝政府废除土司,建立贵州行省,并在梵净山环山周围地区设置四府:思南府、铜仁府、松桃府、石阡府。作为控扼四府的梵净山地区,其战略价值巨大,即《敕赐碑》中所谓的“山连四府,当与国运俱隆”。这一战略价值在平播战争之后显得尤为突出。
万历二十七年(1599),“播州之乱”祸及梵净, 平播之战中各族人民的生命财产损失极为惨重,“播土旧民,仅存十之一二”[3]。伴随播州之乱的发生,梵净山地区也出现了持续的动荡。“自杨应龙平后,销兵太多,苗仲所在为寇。”[4]“其在水硍山,介入铜仁、思、石者,曰山苗,红苗之羽翼也,窥自平播后财力弹竭,有轻汉心,经年剽掠无虚日。”[5]为了医治战争创伤并消弭南部边患,明王朝采取了两手策略,具体如下:
其一,在此进行了较彻底的改土归流[5]。将播州分设遵义、平越二府,并置二州、八县。改遵义长官司为遵义县,改真州长官司为真安州,设桐梓、绥阳、仁怀三县,以上四县一州均属遵义府,隶属四川;改黄平安抚司为黄平州,改余庆长官司为余庆县,改瓮水安抚司为瓮安县,并置湄潭县,以上一州、三县属平越府,隶贵州。又割龙泉县属石阡府。同时,设威远卫于遵义,下辖前、后、中、左、右五所,每所驻军一千。因杨应龙闭关停用的驿道也得以恢复,为重建统治秩序,明王朝一方面安抚原有土官、土目,政治上予以适当安排,填补地方权力真空。如真州长官司正、副长官平杨有功,正长官安排为州土同知,副长官安排为土判官;对于投降的“夷目”也给予适当安排:上赤水里头目袁年,父遭酷祸,投降最早,授以所镇抚职衔。仁怀里头目王继元、安罗二村头目罗国民、罗国显等,念其“改邪归正”,量授冠带。同时,明王朝还在播州设立遵义、平越两府学,增设真安州学,恢复杨应龙时期有所倒退的文教事业。这些措施,对于稳定大乱后的原播州地区起到了重要作用。
其二,加强佛教教化作用。考虑到当时严峻的军政形势,“又有红苗,环铜仁、石阡、思州、思南四郡,数几十万;而镇远、清平间,大江、小江、九股诸种,皆(杨)应龙遗孽,众万余。臣部率止万三千,何以御贼”。[5]单纯的军事手段已经不能适应播州之乱后的边疆形势,能够驯化人心的有效工具亟需出现,诚如贵州总兵陈汝忠在《重修木桶观音阁碑记》中说:“苗喜劫杀,好杀戮。彼大士者,西方上人也,恶争禁杀,一以无争为教。吾从而事之,焉知彼苗僚者不闻大士之风而变于汉乎?未必于岩邑无补也。”[7]正是基于这一背景与基本判断,明王朝皇权介入,以梵净山为战略支撑点进行佛寺重建。在明朝统治者看来,佛教能够有效起到“敷训导民”的作用,可以使人“乐为善事”而不谋反,值得大力提倡。明朝中央政府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僧官制度,与学官、道官制度相辅而行。佛教影响所及,深入到少数民族地区,如水西安氏崇尚佛事,成化年间,安贵荣即在水西建立佛寺,今尚存残钟一口。成化二十一年(1485年),宣慰使安贵荣与夫人奢豚于水西本境建永兴寺,并仿贵阳大兴寺铸铜钟一口悬于寺内,其上铸有彝、汉两种文字,并有“朝暮德鸣,以镇一方,尚祈佛佑,俾我子孙代”[8]376等字样,这是统治者所希望看到的。
梵净山第一次因皇权而兴也正是在“播州之乱”后。作为安抚边地民众成本较少而功效较高的选择,万历四十六年(1618),明神宗降旨重建梵净山金顶,令妙玄为钦命僧,建立“天”“恩”字号五大皇寺,各级官员亲往督查重建。因这次重建惠沾皇恩,故而梵净山之名播于天下,所谓“古殿灯燃长白昼,危楼钟动欲黄昏”[7]。逐渐形成了五大皇庵、六大脚庵,环山四大古寺的格局。各寺厘定寺产,招纳僧户,修藏经塔,香火盛极一时。“尽自开辟迄今,海内信奉而奔趋,不啻若云而若水,王公大人之钦谒,恒见月异而日新。”[9]其辐射区域的影响力表现为上扬与下行两个方向,“上扬的方向,参禅悟道,修学佛学,以理性的精神开拓梵净山佛教的生命空间:由此梵净山吸引了大量的文人学者来寻求生命关怀;下行的方向,朝山拜佛,念佛放生,以信仰的要求来表达梵净山佛教的象征力量,由此梵净山吸引了大批的普通民众来寻求心灵的慰藉。”[10]
总之,梵净山佛学因初次皇权介入而振兴,适应了当时的军政局势,有利于边疆形势的稳定,成为中央王朝边疆治理政策的一部分。
康熙帝平定三藩之乱后,对包括贵州在内的西南地区改土归流政策作了重大调整,恢复了清初对西南土司的安抚政策。
康熙二十五年二月十六日(1686年3月9日),谕大学士等:
近云贵督、抚及四川、广西巡抚俱疏请征剿土司。朕思从来控制苗蛮,惟在绥以恩德,不宜生事骚扰。今览蔡毓荣奏疏已稔悉其情由,盖因土司地方所产金帛异物颇多,不肖之人苛求剥削,苟不遂所欲,辄以为抗拒反叛,请兵征剿。在地方官则杀少报多,希冒军功;在土官则动生疑惧,携志寒心,此适足启衅耳。朕惟以逆贼剿除,四方底定,期于无事。如蔡毓荣、王继文、哈占等身为督、抚,不思安静抚绥,惟求诛无已,是何理也?前出征云南,赵良栋将彼等过端几至发露,穆占之家举首,朕寝其议,若此等尚多,朕无不洞悉,但事系已结,朕不复究,置之宽宥。至云贵督、抚居官殊无善状,或地处辽远,朕不悉知,亦未可定。尔等将此谕旨,传示九卿、詹事、科、道令其详议具奏。[11]卷16-17
康熙皇帝之所以对西南土司采取安抚政策,原因有三:
第一,平定三藩之乱、收复台湾后,康熙皇帝将主要精力放在北方。为平定准噶尔部破坏国家统一的活动,康熙帝多次亲征,之后历经雍正、乾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努力才结束北部边疆问题。加之康熙时,沙俄已经扩张到了东北地区,对清朝的边疆稳定构成了现实的威胁。因此,云贵地区的改土归流不是头等大事,没有提上议事议程。
第二,康熙皇帝后期,为诸子储位之争,耗费了大量精力,折腾得“几欲先死”,加之身体状况也欠佳,无暇顾及西南边疆的土司问题。即使后期发生了“驱准保藏”战役,康熙皇帝对于西南地区也是以安抚为主。
第三,康熙皇帝对待归顺臣民比较宽厚,土司问题也是如此。康熙二十一年十二月初九日(1683年1月6日),兵部议复云南贵州总督蔡毓荣疏言:
请禁民人及土司携藏兵器,并不许汉人将铅、硝、硫黄货于彝人。应如所请。”得旨:“众土司人等全赖弩弓、长枪捕猎以为生计,今概行禁止,则土司俱失其生业。治民惟在所司官抚绥安戟,若不爱惜兵民,肆其残虐,民操白梃亦可为非。九卿详议以闻。[11]卷106:18
康熙的政治性格可见一斑。尤其是康熙后期,在“天下事,兴一利不如除一弊”的思想指导下,更是安于现状,对社会现实采取谅解和宽容态度。如其所言:
为大吏者,亦需安静,安静即为地方之福。[12]56
“三藩之乱”被平定后,梵净山作为区域文化与外部文化融汇交流的重要枢纽,重新得到中央王朝敕封,梵净山佛教再次鼎盛,并与西南佛教名山峨嵋、鸡足成三足鼎立之势,《镇国寺碑记》云:“数百年进香男妇,时来时往,若城市然。”山麓诸寺也应接不暇。除了将明代“五大皇庵”扩建外,另将“六大脚庵”增建至“四十八大脚庵”。其中,太平寺、坝梅寺、回香寺、钟灵寺闻名遐迩。[9]
这一局面的出现无疑有力配合了中央王朝贵州改土归流的总体战略。明清以降,中央王朝通过改流使国家的军事、行政力量直接进入各少数民族社会内部,在制度上打破了各民族间封闭的文化空间,为汉文化的强势进入及其与贵州各少数民族文化间的相互交融创造了条件,形成了独具区域特色的地方文化。改土归流后,少数民族文化不断发展,但文化结构的主导力量变成以儒、道、释三教合一为代表的汉文化。在国家行政力量的强力推动下,汉文化对少数民族地区形成了强大的吸引力和示范性,自觉模仿学习汉族生产、生活方式和文化习俗成为各少数民族走出边缘融入主流社会的主导选择。[13]
这种变迁对土司的影响是巨大的。贵州永丰州原土司“恐土民向学有知,不便于彼之苛政,不许读书”,“虽有学校,人才不得科贡。”[14]清政府改流之后,广设学校和义学,特别是开科取士,使一部分人有了读书或入仕参政的机会,笼络、吸引了一大批知识分子。在国家行政力量和民间社会力量的合力推动下,原土司区内逐渐完成了汉文化对少数民族文化主导地位的替换,梵净山佛学的繁荣发展正可以视作这一发展的具体表现。概而言之,梵净山佛学除却内在理路的承继发展,因其特殊的地理环境与周边形势而对皇朝区域重建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梵净山佛学的两次关键重兴,都与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成为中央王朝边疆治理政策的重要一环。
二、“弥勒净土”思想的深入挖掘与当下应用
梵净山佛教义理的根本在于弥勒净土:“梵净山由于一山具足弥勒之佛像、菩萨像和比丘像,因而梵净山又具足弥勒全部之净土,即兜率净土、人间净土以及道场净土,形成提升道德、净化人心、走向解脱的一大庄严神圣的净土世界。”[15]这一点不研究深入,则所有的外部活动缺少相应的理论支撑。
净土观念由来已久,近代其所意指逐渐由未来转向现世。民国著名佛学家太虚大师在《佛法救世主义》一文中,设计了一个全面人间净土建设方案,即从“心的净化”到“器的净化”再到“众的净化”。在“心的净化”中,首先要确立“上求佛果,下化众生”的志向,然后按佛教戒律,精进修行,沿着菩萨的道路渐趋最后的觉悟和解脱。在“器的净化”中,太虚主张广泛吸收自然科学的成果,改进交通工具,发展游艺场所,改善人民生活。而在“众的净化”中,太虚又主张利用古今各种人生哲学和社会学、政治学的精华,以及佛教的七众律仪来规范社会生活,以至推广到广大的有情类乃至整个宇宙,共同达到净化的究竟地位。[16]98-99弥勒净土的文化内涵相对于太虚等佛学思想当然有其特殊性,但就人间净土这一终极目的来讲,是基本一致的。
弥勒净土思想的深入开发有几个要点:
其一, 人生改善。即充分提倡五乘共济为主的人修行,以改善人间、改进人生的目的为激励,适当引导转化,可以将礼佛民众的价值方向统纳入“中国梦”的伟大追求中去。
其二, 后世增胜。希望后世比现在生活得好,即基于后世增胜为目的的修行观,这种增胜不限于人间,还由人上升到欲界、色界、无色界。就目前而言,我们可以将后世增胜的净土观充分挖掘,将礼佛民众引导到生态环保、可持续发展的价值路径上,为子孙后代留住青山绿水,也是弥勒净土的内在要求。
其三,解脱生死。只有生死彻底解脱,方可跳出三界轮回。对于以梵净山作为心灵休憩的礼佛民众而言,需要将出世入世的辩证关系明了,即以出世之心态,做入世之事业,尤其是对于人间财势之态度,应秉持淡然之态度,培养民众健康豁达的财富观念与人生态度,建立不断完善的慈善事业。
其四,法界无障。“法界即真如别名,即无分别智相应之真如。”脱去所知障,而对诸法实相彻底明了,“二无我者,即人无我法无我,诸识三分诸法,皆无我故,曰诸法二无我。”[17]86此大乘特有之气象。这一净土观与破除我执,号召民众与时俱进、终身学习的观念相契合。
就梵净山地区而言,净土理想的规划与落实可以从两个层面深入挖掘:一是个体心灵层面的道德建设,正如台湾慈济功德会的创始人证严法师所言:“佛法要人间化,必须先净化人间;要净化人间,必须先身体力行净化自己。如何净化呢?就是培养清净的法爱。所谓的法爱,就是对普天下众生,都能心生敬爱、觉情,而且爱得无所求、爱得很普遍。”[18]47二是社会层面的净土规划,即以环境保护、慈善公益、社会公德等为内容的净土建设,将其统摄于“中国梦”的伟大追求中去,诚所谓“诸法中无论任何一法,皆诸法之总相,以皆能摄一切法故。”[17]87
三、佛教文化枢纽的内部建设与外部视野
梵净山作为区域文化枢纽的历史功用直至清末仍存。清光绪年间,在梵净山围剿太平军余部刘胜的贵州巡抚岑毓英即注意到文化教育对安定少数民族社会秩序和发展当地经济的重要性,有鉴于此,他不仅奏请将铜仁县移到军事位置重要的梵净山南麓的大江口,而且还建立了当地第一所书院——“卓山书院”。为保证书院的经费收入,他又同意将梵净山罗江寺、大佛寺的部分田地和寺产划归“卓山书院”所有,“卓山书院”后来改建为“双江书院”(1891),以书院为抓手,培养了一大批有益国家社会的人才。[19]
当前,梵净山开发与旅游发展进入到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国务院2012《国发2号文件》明确提出,贵州要“建设梵净山等精品景区,培育‘梵天净土’等一批旅游休闲度假胜地”。梵净山当地的江口县也提出要把梵净山打造成为“佛光之城”。以史为鉴,梵净山作为未来可能的一大文化枢纽和旅游精品景区,需要于内部建设与外部视野两方面入手重点建设。
所谓内部建设,即需要一个有力的抓手,这一抓手有两方面的内涵:其一是打造市民学校等官方性质的机构,可于此下设佛学大讲堂、旅游知识培训学校等项目。从长远来看,梵净山佛学旅游文化建设需要本土人才的生生不息,而本土不同层次佛学旅游人才的培养,需要以市民学校等抓手统筹城乡两地的文化建设,在配合区域城镇化的具体过程中,通过旅游知识下乡村的静态统筹与乡村农民入户城镇后市民化的动态统筹两个方面实现佛学旅游知识的全民普及,为打造区域文化枢纽提供坚实的群众文化基础;其二是借鉴台湾“慈济功德会”的慈济模式,以及星云法师佛光山的“星云模式”等人间佛教的活动,将慈善事业与寺庙发展实现打通,可以考虑成立专项基金会,建立专门网站与平面媒体,实现佛寺慈善经济自身的永续发展。
所谓外部视野,即需要以净土观念为统摄,与区域外人间净土的理论倡导者及实践者实现互动。近代佛学泰斗太虚大师的人生佛教是适应时代发展趋势的产物,此后,印顺法师又在太虚人生佛教的基础上,提出了人间佛教的思想。承继这一思想,证严法师开创了慈济功德会,经几十年之发展,形成了影响广泛的慈善、医疗、教育、人文四大志业。“慈济文化终极目标是在于净化人心,建设祥和的人间净土。而为厚实台湾民众的‘爱心存底’,以达成慈济精神国家化的目标,慈济文化致力于‘向下扎根’的落实工作,不论是文化下乡、幸福人生讲座,或是各项活动的举办,皆朝着此一目标迈进。”[20]167
台湾主流佛教界的净土观念与梵净山弥勒净土相通之处甚多,若梵净山在内部建设做强做大做细基础上,主动为之,很有可能实现两地有效的交流与互动,借助于“生态贵阳”“佛教名山联席会议”等平台,必大有可为。诚如是,梵净山佛学不仅是西南佛教文化一大枢纽,更可提升至海峡两岸文化交流层面加以运作。
四、结语
梵净山地区由于自身的区位优势,明清以来的统治者意在将其作为区域文化枢纽而打造,万历、康熙两朝尤为突出。梵净山佛学的这两次关键重兴,都与当时的军政形势密不可分,成为中央王朝边疆治理战略的重要一环。梵净山佛学义理的根本在于弥勒净土,净土观念的深度研究有必要成为该区域旅游文化事业发展之基础,而近代以降以太虚一脉为代表的人间佛教净土思想可以作为理论借鉴。所谓“凭个人一片清净之心,去修集许多净善的因缘,逐步进行,久而久之,此恶浊之人间,便可一变而为庄严之净土,不必于人间之外,另求净土。”[21]45这一思想由台湾慈济功德会的证严法师落实于社会实践,并形成了一整套运转有效的工作体系,通过对佛法观念进行自觉调适,适应了时代潮流和社会现状。弥勒净土的当下实践需要从心灵层面与社会公益层面统筹打造,并具备强有力的文化抓手,培养各个层次佛学旅游本土人才,吸取已经成熟的运作经验,具备更宽广的交流视野,为区域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提供契理契机的坚实支撑。
[1]张明.2010中国梵净山弥勒道场金玉弥勒开光仪式暨佛教文化研讨会综述[J].世界宗教研究,2011(1):183-185.
[2]张明.梵净山历代高僧考略[J].人文世界(第四辑),成都.巴蜀书社,2011:318-345.
[3]明实录.明神宗实录:卷357[M].北京:中华书局,1985:8.
[4]张廷玉,等.明史:卷257(张鹤鸣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4.
[5]张廷玉,等.晚史:贵州土司(新添条)[M].北京:中华书局,1974.
[6]栾成斌.贵州改土归流源流考[D].贵阳:贵州大学,2010.
[7]张明.梵净山弥勒道场〈敕赐碑〉研究[J].世界宗教研究,2012(4).
[8]贵州通史编委会.贵州通史·明代的贵州[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3.
[9]张明.梵净山佛教源流考[J].佛学研究,2005(14):284-292.
[10]王路平.贵州第一佛教名山梵净山佛教考论(下)[J].世界宗教研究,2015(2):1-9.
[11]清实录·圣祖实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5.
[12]王戎笙.清代全史:第四卷[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
[13]刘伦文.国家行政力量与民间社会力量的互动——论改土归流后鄂西南土家族社会文化变迁的动力[J].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4):13-16.
[14]钟添.思南府志·拾遗[M].上海:上海古籍书店,1962年影印本.
[15]王路平,释行愿.论贵州梵净山弥勒菩萨道场[J].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5):34-40.
[16]李明友.太虚及其人间佛教[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
[17]印顺法师.太虚大师选集(上)[M].台北:正闻出版社,1982.
[18]释证严.精思语[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19]张明.贵州巡抚岑毓英与梵净山佛教重建[J].成都:巴蜀书社,人文世界.2016(7):77-90.
[20]释证严.慈济年鉴(1994)[M].台北:慈济文化出版社,1995.
[21]麻天祥.反观人生的玄览之路[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
(责任编辑钟昭会)
2015-12-17
贵州省哲学社科规划课题“梵净山弥勒道场的形成研究”(11GZYB02)。
栾成斌(1982—),男,山东青岛人,博士,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阳明文化研究院)校聘副教授,贵州省高校人文社科研究基地“中华传统文化与贵州地域文化研究中心”专职研究人员。研究方向:历史金融地理、西南区域文化。杨春华(1984—),女,四川资阳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区城文化史。
G127
A
1000-5099(2016)04-0128-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