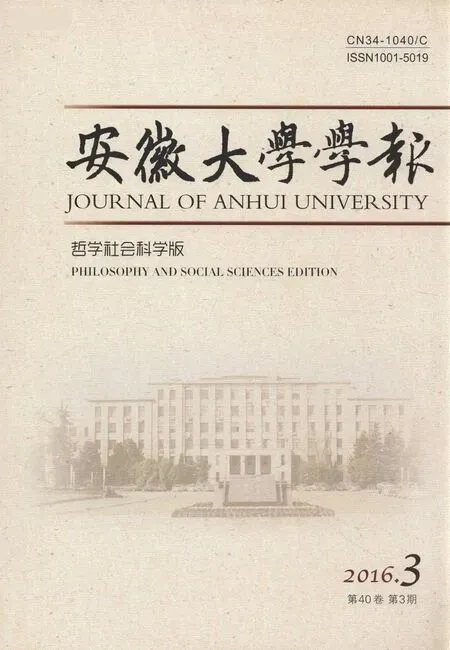论德性伦理学的规范性诉求
——从科尔斯戈德规范性概念出发
韩燕丽
论德性伦理学的规范性诉求
——从科尔斯戈德规范性概念出发
韩燕丽
摘要:基于科尔斯戈德对道德概念规范性的分析,可以发现,当代德性伦理学面临的质疑和挑战实质上大多源于批判者对德性规范性的诉求。而这种规范性诉求的产生以及引发的相关争论,实则忽略了两种实践性概念的区别,即古代伦理学与现代伦理学的“人应该如何生活”与 “人应该如何行动”之间的差异和裂隙。为了弥合这种裂隙,必须规范伦理生活目标,将古代伦理学的“人应该如何生活”融入现代伦理学语境中,这种融合将使得德性伦理学的应用呈现为一种弱规范性解读。
关键词:德性伦理学;规范性;实践性
一、问题的提出
当我们在谈论道德伦理学时,往往寄希望于它可以对道德行为做出解释,为现实生活中的道德问题指明出路。换言之,我们对道德一词的提及和运用总是伴随着强或弱的道德要求。这种要求无时无刻不渗透在我们的意识之中,简单来讲,我们对伦理学的这种道德要求,就是对它的规范性*本文倾向于用道德的规范性( normativity)来证成道德的实践性(practicality),“规范性”意在表明一种标准,而“实践性”意在考察这种标准是否可以指导道德实践生活。德性伦理学实践性的证成必然考察行动的规范性。实际上,规范性问题本身就涉及一种“道德观念的实践和心理效应”,与“实践性”一词有着多层重叠。同时,本文试图用规范性问题证成实践性问题,即规范性更多地作为一种标准来衡量德性伦理学是否可以应用于现实道德生活。期望的表现。
毋庸置疑,我们希望人们顺从“道德”二字所暗含的道德要求。但是如何从伦理学角度对道德概念蕴含的道德要求给出分析,是解决道德规范性问题的关键所在。道德哲学家科尔斯戈德(Christine M. Korsgaard)清晰地意识到这一点,她在《规范性的来源》一书中论证了这一问题。她宣称道德概念之所以蕴含道德要求,是因为“伦理标准是规范性的。伦理标准不只是在描述我们实际调节行为的方式,还向我们提出了要求。我们在使用这些标准的时候,实际上在互相提出要求”*Christine M. Korsgaard, The Sources of Normativit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p. 8. 书中涉及的专业术语翻译参考了中文译本,[美]克里斯蒂娜·科尔斯戈德:《规范性的来源》,杨顺利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她把道德的这种特质称为“道德观念的实践和心理效应”:道德概念自身之所以涉及道德要求,是因为道德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一直起着指导实践的作用。
“道德观念的实践和心理效应”可以在两种意义和标准上进行解读。其一是,为什么这些道德观念对我们影响那么深刻,以及它们是如何影响我们的,这可以被称为解释完备性标准(explanatory adequacy)。其二是,如果道德具有这种特质,那么这种重要性如何可以得到确证,我们应该做些什么才可以证成它,这可以被称为规范或证成完备性标准(normative or justificatory adequacy)*Christine M. Korsgaard, The Sources of Normativity, p. 13.。
本文认同科尔斯戈德对道德观念规范性的分析。而德性伦理学作为现代道德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解读规范性问题必然要在这一框架下进行。按照上述两种完备性标准,德性伦理学必须回应的是,第一,德性为什么以及在何种意义上对道德主体的实践生活产生影响;第二,德性伦理学具有规范性,那么如何确证这种规范性,以及我们怎样行动才可以确证它具有规范性。由于篇幅有限,本文的讨论只限于后者,即按照德性伦理学的宗旨,德性伦理学应该如何指导道德主体的道德实践活动,如何对行动问题给出说明。实际上,当我们基于科尔斯戈德的理论,重新审视当代德性伦理学的规范性问题及其面临的挑战,可以发现,学界对当代德性伦理学的质疑,大多出于其对德性规范性的诉求。然而这种规范性诉求的产生以及引发的相关争论,实则又都忽略了两种实践性概念的区别。因此本文也将着重探析这两种这实践性概念,以求探索当代德性伦理学的应用图景。
二、 规范性诉求与学界已有的讨论
如前所述,我们对当代德性伦理学规范性诉求的分析主要集中在“证成完备性”方面。关于此点,学界目前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德性伦理学地位的必要性、德性的自足性以及德性与规则的关系等方面。
沃森(Gray Watson)在“论德性品质的首要性”一文*Gray Watson, On the Primacy of Character, Identity, Character, and Morality, eds. by Flanagan and Rorty, 1997, pp. 483-493.中指出,德性伦理学要想捍卫自己的独立性,就需要解决两种困境:第一种,如何确保德性在德性伦理学应用中的首要性。任何伦理学的应用都是在某种伦理学图景中将某种原则当做最大化标准来施用,比如功利主义将效力最大化当作主要原则,但这一过程并不完全否认其他原则的合法性。而德性伦理学的应用是将德性作为最大化标准,同时也认可规则的应用。因为德性伦理学并不排斥规则,于是问题变为,如何在德性伦理学框架内解读规则、运用规则。第二种困境是如何确保德性伦理学的基础即人性论足够坚固,人性论是一种客观性的描述,这种客观性的描述如何能够呈现规范性。
沃森的评论代表了很多学者关于德性伦理学的态度,他们认为德性伦理学关于德性的各种证成是不成功的,而当我们从其他理论的视角来处理德性时,德性未必不值得我们拥有。换言之,当德性伦理学中的德性不保持其首要性地位,德性伦理学不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而仅仅作为一门德性理论,德性一样可以起作用。这也就是认为德性伦理学对德性的处理不具有独特性,德性伦理学完全可以被德性理论替代。比如,吉沃(Julia Driver)试图从后果主义角度,对德性进行处理。她的论证逻辑是,规避后果主义的缺点,放弃效用原则,在对价值采取一系列理解的基础上,建立德性的后果论。在她这里,评价个体行动的标准来源于德性品质产生的后果。或者说,在吉沃看来,德性就是一种可以产生善或好的道德品质。对于这种品质,我们没有必要努力获得,也没有必要试图维持。因为,德性本身如果自然而然可以给我们带来好处,我们自然会去追寻德性。易言之,她的观点是,“最好的德性,本质上就是后果主义的”*Julia Driver, Uneasy Virtu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2007, p. 140.。
后果主义视角下对德性的处理方式符合人类的内心直觉。但吉沃的这番论证,有点像是《理想国》中苏格拉底对正义讨论的延伸。她误解了德性伦理学的本意,德性伦理学显然并不是仅仅从后果意义上处理德性。德性伦理学意在通过对德性图景的描绘,表明现代道德生活不应该忽略“人应该如何生活”这一问题。如果德性仅仅因为可以给人们带来善及益处而值得拥有,那它与功利主义又有何区别。
毋庸置疑,德性伦理学对推崇德性首要性是不遗余力的。但问题是,这种对首要性的推崇在什么意义上是合理的,以及这一德性又是否具有充分的自足性以引发行动者做出德性行为。人们对德性的这种合理性期望,被称为德性品质的自我激发效能(self-motivational efficiency)。从另一个层面来讲,德性之所以成为一种优良的被普遍认可的道德品质,正是因为德性品质源于自我激发。
对于德性品质自行激发的效能,学者们各执一词。莫瑞特(Maria Merrit)指出,按照上述逻辑,在德性品质自行激发效能下考察德性,就会发现 “德性成为一种完全独立于行为者的外在因素,尤其是完全独立于特殊的社会关系和设置(settings)的一种品质”*Maria Merritt, Virtue Ethics and Situationist Personality Psychology, Ethical Theory and Moral Practice, vol. 3, no. 4, 2000, pp. 365-383.。基于这一点,很多社会心理学家质疑德性伦理学。因为这种论证面对的问题是,现实生活中,被人推崇的德性状态几乎没有行为者可以达到。这就意味着行为者都拥有德性状态会成为一种苛求。而遵循这种逻辑,我们培养德性的模式会与亚里士多德的本意背道而驰。因此,如果德性具有很高的自我激发效能,我们呈现德性行为又受到情境的影响,那么我们在培养德性时,就必须把社会因素以及其他因素考虑进来。
与此同时,苛求德性行为者诱发的另一种后果是,若现实道德生活中,很少人可以达到这种德性要求,那么我们就完全不可能论证德性伦理学具有规范性。因为落实到现实道德生活,这种可以获得圆满德性状态的行为者被称为道德榜样,这种道德榜样在生活中不可能真正存在。换言之,道德榜样只能被无限接近。同时,设想道德榜样在某个情景中会如何行动,会给出具有德性的行动,这一假设本身面临这样一种困境,即,道德榜样的动机以及行动理由,并不一定与行为者自身的行动理由相符。于是,德性伦理学就要面对斯多克(Michael Stocker)“现代道德分裂症”*Michael Stoke, The Schizophreina of Modern Ethical Theories, Virtue Ethics, eds. by Roger Crisp and Michael Slot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66-78.的指责,也就是说,促使行为者给出道德行动的动机,并不是行为者自己的动机,而是道德榜样的动机,这对道德行为者来说是一种自我分裂。如此一来,我们可能要对行为者的行为认知过程产生质疑,对行为者的理性(rationality)能力进行怀疑。
本文并不认同上述对德性品质自行激发效能的分析。事实上,我们在当代德性伦理学语境下谈论德性品质的自行激发效能时,并未把德性当作完全独立于社会环境之外的因素。相反,德性的构成以及作用机制离不开诸多社会因素的共同作用。与此同时,德性伦理学对道德榜样的推崇是一种倡导,是试图用道德榜样的宣传,营造一种良好的社会氛围,契合社会传统习俗。同时,在上述分析中,莫瑞特认为如果在现实道德生活中不存在完全意义上的道德圣徒,那么追寻圆满德性的可能性就会受到质疑。现实道德生活中,与莫瑞特持相似想法的学者并不在少数,但用现实道德生活中不存在的完满道德圣徒来质疑道德榜样,这本身就是对德性伦理学宗旨的误解。对于德性伦理学家来说,德性生活更多地是一种值得生活的生活状态,这种生活状态是一种心向往之的理想存在。也许完满的道德圣徒与完满的德性生活并不存在,但这并不影响德性伦理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而存在。就好比宇宙黑洞是否真的存在尚值得怀疑,但我们对宇宙黑洞的各种理论论证并不能说没有意义,正是因为这些理论论证的存在,我们才有可能无限接近事实真相。
除了对德性品质自足性的质疑,现代道德哲学对德性伦理学规范性质疑的另一个方面是,德性伦理学既然宣称自身是一门独立学科,比德性理论更具有完备性,那么德性伦理学在应用方面如何保持德性的首要性呢?
具体来说,对这一问题的回应分为两类:一类是德性伦理学的应用必须拒斥规则,只有这样才可以保持德性伦理学的独立性。另一类是,德性伦理学在应用中不排斥规则,关键是如何理解德性伦理学中的规则,在何种程度上德性与规则可以相容。
前一类的支持者,即宣称德性伦理学应该拒斥规则的学者,认为德性伦理学的应有之义是关注德性行为者而不是分离的行为本身。那么,为了显示德性伦理学的独特性,就应该与以往规范伦理学关注行为的应用方式明显分开。这种逻辑是指望在纯粹德性的基础上建立道德王国。但显然这一基础并不坚固。与此相反,一些学者指出德性伦理学不能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与义务论和功利主义三足鼎立*很多学者持这种观点。Cf. Harold Alderman, By Virtue of a Virtue, The Review of Metaphysis, vol. 36, no. 1,1982, pp. 127-153. Robert B. Louden, On Some Vices of Virtue Ethics, American Philosophical Quarterly, vol. 21, no. 3, 1984, p. 237.,则走向了另一种极端。
后一类的支持者认为,在应用德性伦理学的过程中没有必要拒斥规则,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应用规则,同时又保持德性的首要性。一些德性伦理学家指出,德性伦理学确实存在一些德性规则,如“做一个诚实的人”*Rosalind Hursthouse, On Virtue Ethic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 8.。但这一规则对我们的生活起到何种指导作用,却值得进一步审视。另有一些学者则试图对德性与规则的关系给出各种解读,比如有学者指出规则自身就是“德性的语法”*Robert C. Roberts, Virtues and Rules, Philosophy and Phenomenological Research, vol. 51, no. 2, 1991, pp. 325-343.。
上述讨论并没有完全彻底地解决德性伦理学应用过程中如何保持德性首要性这一问题。本文更加支持的是新亚里士多德主义德性伦理学的反编码化(anti-codifiability)的立场。这种观点宣称,德性伦理学的伦理规则是不可编码化的。当我们重新审视道德主体应该如何行动时,必须回归到“有德性的人”这个概念中来,也即麦克道威尔(John MacDowell)指出的:“一个人在一个场合知道应该去做什么,不是通过应用一般性的原则,而是通过成为一种特定类型的人”*John McDowell, Virtue and Reason, Monist, vol. 62, 1979, pp. 331-350.。因为成为某种特定类型的人,获得对具体情景的敏感性,结合实践智慧,然后道德主体根据现实情况给出行动,这更加契合道德生活的复杂性。他还指出,“亚里士多德对伦理学中普遍真理的怀疑,意味着这个普遍概念(即,怎么做才是德性)的内容无法被明确地、具体地书写下来。无疑它是可以被表达出来,通过可以分享这一普遍概念的行为者,或者如亚里士多德在第三卷到第五卷中所做的那样,通过列举德性以及给予拥有德性的人的品格以表述”*John McDowell, Comments on “Some Rational Aspects of Incontinence”, Southern Journal of Philosophy, vol. 27, 1988, pp. 89-102.。纳斯鲍姆(Martha Nussbaum)对于规则在亚里士多德伦理学中的作用也给出了相似的评价*如其所言:“道德原则就好比一本幽默手册里的规则一般,不是说得太多,就是说得太少。说得太多,是因为规则缺乏弹性,而忽略了道德与幽默一样,必须针对不同的情境做出适当的反应。说得太少,是因为情境的复杂性不是简单的道德原则可以掌握的。” Cf. Martha Nussbaum, Love’s Knowledg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 71-72.。
对德性伦理学进行反编码化的应用受到很多学者的青睐,它试图回归到“有德性的人”这个概念,来分析如何应用德性伦理学的问题。对道德规则反编码化(anti-codifiability)的应用,契合德性伦理学复兴的初衷,符合德性伦理学及其如何应用的主旨。换言之,德性伦理学对“我们应该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的关注并不意味着它会忽略“我们应该如何行动”,或者弱化行动问题。德性伦理学意在提供一种反编码化的应用,这种反编码化的应用不是简单僵化或标新立异的应用规则,而是在德性品质的基础上,以有德性的人为中心,在实践智慧下,结合具体的情境感知做出德性行为。厘清上述观点,是我们应用德性伦理学的前提。
为了更好地理解德性规范性的种种诉求,也为了回应德性伦理学面临的种种挑战,本文试图提出两种实践性概念,并在此两种实践性概念的框架下,探讨当代德性伦理学的应用前景。
三、两种实践性概念与伦理学目标
德性伦理学认为伦理生活的核心是“我应该如何生活”,或者是“我们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而现代道德哲学认为伦理生活的核心是“我应该如何行动(做什么)”。正是这种伦理生活核心意识的改变,导致了现代道德哲学的一些困境。在这一背景下,德性伦理学试图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扭转人们对伦理生活核心的关注,弱化德性伦理学与规范伦理学的差异,指出德性伦理学自身也具有规范性,可以指导道德实践生活。
实际上,德性伦理学一直都以指导道德实践生活为宗旨,只是古代伦理学与现代伦理学的生活目标不再一致。正如余纪元指出的,德性伦理学不论在古希腊还是在中国古代哲学中都被称为实践科学(practical science), 但是古代哲学对伦理学实践目标的设定与现代道德哲学有很大不同。古代伦理学的目标是我们应该成为一个更好地人,应该向善地生活,除此之外,“在古代伦理学中,存在一个实践概念,与现代道德哲学的实践概念有着很大的不同”*Yu Jiyuan, The Practicality of Ancient Virtue Ethics: Greece and China, Dao, vol. 9, no. 3, 2010, pp. 289-302.。
古代伦理学与现代道德哲学对实践性的界定有一些根本上的区别。以现代道德哲学与亚里士多德传统为例,概括来讲,亚里士多德传统中的实践性,重视目的论与功能论证,同时强调实践者的整全性和实践境域的特殊性。现代道德哲学则重视行动的规则主义和工具主义,将人自身的完善以及人与人的交往简化为人对物的操作。这种简化过程就是遗失目的论与功能论证的过程。“亚里士多德实践哲学作为一种传统一直延续到前现代,其传统地位的丧失昭示着现代性问题的出现。新亚里士多德主义宣称,现代性及其实践哲学的问题恰恰就在于,它们遗失了亚里士多德传统中那些最为重要的东西”*刘宇:《当代新亚里士多德主义实践哲学的理论建构及其困境》,《哲学研究》2013年第1期。。这是因为,首先,近代科学的发展,以及启蒙运动的产生,促使人们抛弃了亚里士多德传统中的目的论,更确切地说,抛弃了客观的善以及目的论的形而上学基础,同时,又忽略或者丧失了对人作为实践整全性的关注。其次,因为否定客观的善,又否定了形而上的目的论,行为者不得不关注于主观目的。但是不同的行为者具有不同的主观目的诉求,导致出现主观目的多样化的现象。当不同的道德主体试图协调多样化目的时,必然会出现不同目的之间的不可通约性。最后,古代道德哲学与现代道德哲学的不同旨趣,决定了人们关注点的不同。这种不同不仅反映了道德哲学在人们生活中扮演的角色不同,也体现了不同时代人们生活追求的不同。在古代道德哲学中,人们视生活为一个整体,注重理性的以及有目标的计划性生活,宣称“未反思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Plato, Apology, The Trial and Death of Socrates (Third Edition), trans. by G. M. A Grube, New York: 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 2000, p. 39.。如余纪元指出的,在这一过程中,哲学俨然已经成为一种生活方式。而现代社会更多的将哲学作为一种专业性的学术之道,即“现代伦理学更多地成了一种学科训练和理论追问(theoretical inquiry), 这样做伦理学是一个事情,生活是另外一个事情”*Yu Jiyuan, The Practicality of Ancient Virtue Ethics: Greece and China, Dao, vol. 9, no. 3, 2010, pp. 289-302.。
如前所述,古代哲学与现代道德哲学存在两种实践性概念,且古代哲学与现代道德哲学在伦理目标上存在差异。现代伦理学确实已经成为一种专业化的学习与训练,不再是古代伦理学般与生活密切相关的修行。现代伦理学受启蒙运动以来现代化的影响颇深,我们不可能完全复归古代,也不可能完全复制古代伦理学的伦理目标。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伦理学已经完全与现代道德生活脱离,也不意味着,现代伦理学拒绝作为一种生活方式而存在,更不意味着,行为者不需要从伦理学视角寻求道德问题的答案。
换言之,古代哲学的实践性概念,指道德主体关注道德生活的整全性,以“人应该如何生活”为关注点,但并不忽略生活中的行动,其行动以更加有效地指导伦理学生活为目标,与道德生活有紧密联系。现代道德哲学的实践性概念是指,道德主体的关注点是“人应该如何行动”,且实践的目标设置偏向专业化哲学学科训练,哲学与生活的关系松懈。可以看到,两种实践性概念之间存在裂隙,它们的关注点以及实践目标皆不相同。
很多学者的研究都涉及实践性概念的相关分析,只是并未明确提出两种实践性概念的划分并给予明确界定。如麦金太尔在《追寻美德》中指出,任何时代的道德以及道德要求,都与特定的道德实践或文化传统紧密相连*[美]A. 麦金太尔:《追寻美德》,宋继杰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年,第8页。。在此基础上,道德主体形成不同的道德自我以及不同的道德实践合理性。麦金太尔批评了启蒙运动的理性概念和道德概念,意在指出现代道德哲学与古希腊伦理学的实践性概念是不同的。其虽未明确用“两种实践性”一词涵盖不同伦理学的实践关注点,但实际上一直对不同传统或文化的实践性及其差异保持着敏感性。
对于两种实践性概念的区分是较为明确的,问题在于如何弥合它们的裂隙。余纪元提出,解决两种实践性概念的裂隙,关键在于加强现代道德哲学研究与生活的密切联系,规范道德生活目标。本文认同这一观点,也就是说,在何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践履古代伦理学的伦理目标,也即如何在关注“我们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这一问题的同时,不忽略现代道德哲学中的行动问题。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事实上就是如何应用当代德性伦理学的问题。同时,澄清以上这些问题也将十分有助于德性伦理学的复归。因为“如果我们仅仅是在伦理学的方法论上去复兴德性伦理学,而忘了指明德性伦理学目标的重要性,那么德性伦理学的复兴就是片面的”*Yu Jiyuan, The Practicality of Ancient Virtue Ethics: Greece and China, Dao, vol. 9, no. 3, 2010, pp. 289-302.。
遗憾的是,余纪元并没有指出,我们到底应该如何规范伦理学的生活目标,以及德性伦理学生活目标的规范是一种什么意义上的规范。换言之,这种规范与规范伦理学的规范有何区别,又在何种意义上对行为者是有效的。只有对这些问题给予充分的澄清之后, 才有可能真正解决德性伦理学的规范性问题。
四、对两种实践性裂隙的弥合与弱规范性
古代德性伦理学的立意是,哲学选择关乎生活方式,关乎人的现实道德生活,同时,道德生活作为一个整体,与哲学活动的探寻有着密切关系。在这里,哲学选择是根植于道德行为者生存的真实选择。而到了现代,行为者不可避免依旧面临选择,只是这种选择与行为者的生活方式不再具有那么紧密的联系。但是,古代德性伦理学与当代德性伦理学状态下的德性行为者的共通性在于,德性主体都渴望一种好的生活状态,都欲求一种善的生活。也就是说,行为者对完善个人自我状态的欲求从未改变。这种欲求是促使道德主体探寻德性、追求幸福生活的主要动力。在此基础上,道德主体培养德性,因为“德性的发展是人类原始善性展开的修养过程”*[美]余纪元:《德性之镜:孔子与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林航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96页。。简言之,无论在古代德性伦理学还是现代德性伦理学中,道德主体选择德性行为的过程都是一种自我完善、自我完成、自我实现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他们从未放弃对“伦理生活更有效”的诉求以及对好的生活的渴望。
对好的生活的渴望是道德行为者的一种自身诉求,也就是说,对好生活的欲求是道德主体自身的一种“弱规范性”*很多学者对规范性概念进行了追溯与定义。“规范”一词不管是在西方学界还是中国哲学语境中都具有尺规和模具的意思,这决定了规范本身就具有限定、约束以及指引意味。不同的学者按照不同标准将规范性进行了不同的分类。按其来源,规范性可以分为外在规范性和内在规范性。按其起作用的方式,规范性可以分为显规范性与隐规范性,这种区分多存在于语言实践哲学中。而本文对规范性的讨论,倾向于从道德主体的约束力量来将规范性分为强规范性与弱规范性。详参郭贵春、赵晓聃《规范性问题的语义转向与语用进路》,《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8期。诉求。这种“弱规范性”不是规范伦理学意义上的道德命令或者道德义务等强规范,而是道德行为者对“如何做人”“我们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或“我们应该如何生活”的一种反思以及道德实践。这种道德反思及实践并不满足于规范伦理学图景中显现的僵化道德律令式的生活,而是试图在规范伦理学之外,寻求一种有意义的生活。
弱规范性不同于强制性的外在制约,不对道德主体有强制性的道德要求,而是一种引导性的规范。这种规范更多地像医生的处方,如果道德主体认可医生的医者素养,认可处方背后的理念,或者认为自身需要处方,那自然会照方吃药,祛病延年;如不认可也不会是不道德的。但这也并不等于弱规范性是一种无力的规范性。德性伦理学的弱规范性,是用弱名称表达强意愿。在这种意义上,德性伦理学对规范性的解释,都是在一种弱规范性的意义上给予呈现。因为德性伦理学本身并不以行动规范性为关注点,而是关注一种好的生活状态。获得这种好的生活状态是道德主体的一种理想化追求,而应用德性伦理学就是讨论这种追求在现实道德生活中如何可能。值得庆幸的是,在现代道德哲学语境下,道德主体自我完成、自我完善的弱规范性诉求依旧大量存在。
综上,我们对如何应用当代德性伦理学提供了一种新的解题思路,即,“我们应该如何生活”这一追问,可以融入现代伦理学语境中,呈现为一种弱规范解读。简言之,“我们应该如何生活”是一种个人修为,是道德主体致力于自我完善、自我完成的选择,它更关乎道德行为者自身,是行为者对自己要成为一种什么样的人、选择何种生活方式的考量。就像纳斯鲍姆所说,一个理性的社会人,肯定会根据自己的本性要求,认同某种生活方式而排斥其他生活方式*M. Nussbaum, Human Functioning and Social Justice: In Defense of Aristotelian Essentialism, Political Theory, 1992, vol. 20, no. 2, pp. 202-246.。
对于上述这种德性伦理学弱规范式的应用,一个可能的问题在于,道德主体的德性行为是否成为一种主观性的个人选择,即是否会陷入“主观主义”的困境,又或者说,这种论证如何应对道德相对主义的指控?本文认为上述指控并不成立。首先,德性伦理学并不要求行为者用一个唯一标准来衡量道德选择。一方面,道德选择本身就具有多样化的生活事实。这种生活事实决定了用单一的标准来衡量道德选择的对错这一行为本身就是错误的。另一方面,一个真正具有德性的道德行为者所给出的道德选择,必定是经过慎思后的选择,这种选择虽然带有主观主义色彩,但在具体行为中具有一定的话语确定性*李义天对这一问题给出了分析,如他指出,“德性伦理学在一与多的问题上持有一种地方性立场——德性伦理学承认世界上存在多个‘好’,承认它们相对各自的道德传统是最好的,但它不会像道德相对主义那样承认它们一样好;德性伦理学承认多个‘好’,无法通过一把共同的尺子来加以衡量,但不会像道德相对主义那样承认它们之间无法进行任何衡量。”见李义天《美德伦理学与道德多样性》,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第262页。。
其次,“人应该如何生活”是一种在处理自我与他人关系时,道德行为者必然面临的抉择。道德主体给出这种选择的基础,是自我的构成性理解。一种成功的自我构成性理解不会轻易陷入相对主义误区。因为,自我理解的构成性过程是一种道德主体真实生存状态的过程。只有行为者对自我理解地更加透彻之后,才可能更好地自我实现。
五、结论
本文通过审视当代德性伦理学所面临的诸多挑战,表明这些挑战实质上都是源于对德性伦理学规范性的诉求。借助“两种实践性概念”,本文意在指出,在德性伦理学视阈下,道德主体对行动规范性只能呈现一种弱规范性解读,这种解读方式旨在为应用德性伦理学提供一种新的理解,而并非说明其所呈现的规范性是唯一的真理。如陈嘉映所说,当对一种事物给出证明时,我们的目的并不需要仅仅把目标放在共识之上,达成所谓真正共识的困难远远大于提出一种理论或者证成一种理论的困难。哲学世界是一个充满各种意见的世界,哲学理论工作者最重要的成功,就是在诸多意见中为自己的想法寻求更多地理解与支持。而理解与支持中,必然包含彼此双方的退让与承认。这种退让与承认既是基于对现实理论世界不同出发点以及不同论证目的的尊重,也是对他者理解世界方法的宽容*陈嘉映:《伦理学有什么用?》,《世界哲学》2014年第5期。。也正是在此意义上,本文希望通过对德性伦理学实践性问题的论证,为德性伦理学的规范性立场争取一定的理解与认同。
责任编校:余沉
DOI:10.13796/j.cnki.1001-5019.2016.03.003
中图分类号:B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019(2016)03-0019-07
作者简介:韩燕丽,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博士研究生(山东 济南250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