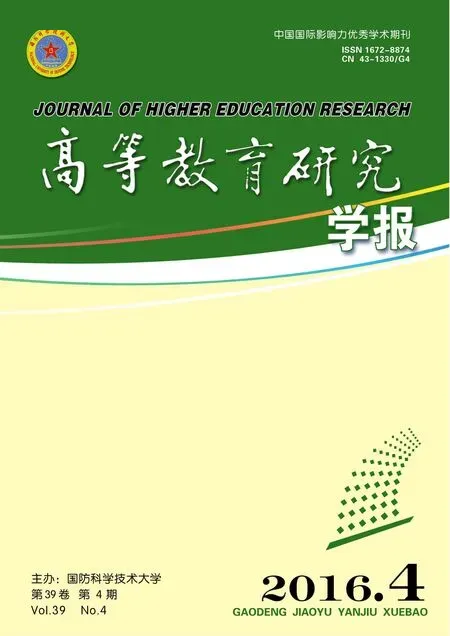课程与大学
张楚廷
(湖南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
课程与大学
张楚廷
(湖南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
大学开设课程的数量、质量与学校水平是息息相关的。大学是个思想库,大学包罗万象,大学是一部百科全书,都通过课程来体现。专业、学科、科研与教学,也都能够通过课程自然而有效地联结起来。课程对一流的学科建设至关重要,建立起一流学科之后,靠自身力量办成世界一流大学,是中国学者有智慧与能力做到的事情。
课程;大学;一流
十余年前,湖南省各高校的教务处长聚会,对教学进行研讨。我应邀作了学术报告,报告过程中,面对坐第一排的湘潭大学教务处长,我问道:“你学校里开多少门课程?”他很快就回答:“600门。”我为他点赞,他对自己大学的课程心中有数。
不过,我也必须说,复旦大学已开出两三千门课,北京大学已开出6000门课,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则开出了10000门课程。那时,我所在的大学开出了1500门课程。
自然,这不只是一个数量问题。开设课程的多少,显然与学校水平有关。故而,这个数量与质量是紧密联系的。在中国为什么北京大学开出的课程最多?这是想多就多得起来的吗?伯克利在10000门课程之外,如果学生另有需要,他们就可以开出第10001、第10002门课程。我将此现象比喻为课程“超市”,作为“顾客”的学生想要什么,就有什么,真是可以各取所需了啊。
有的人,不求有什么学历文凭,就只修读一两门自己喜爱的课程,唯有为着提升自己的修养。当然,这需要有十分自由、灵活的制度,不只是交点钱的问题。
若要取得学历文凭之类,可能就需要在某个专业上就读。然而,所谓专业也就是经过某种组合所构成的课程群。课程数量很大,组成专业的能力必然更强。这种组合亦非易事,多少要有一些心理学、教育学知识才可能寻求一种较好的组合。
学分制对于与以课程为基础、为核心的教育是特别相匹配的。学分制起源于美国,我想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学生的权利得到更充分的保障,应是这种制度产生的根本原因。学分制显然更有利于学生多方面的自由选择,与学年制相比即可明白这一点。
以本科为例,若实行学年制,一般就需要在四年、五年内毕业了吧。学分制则不然,如果本科以拿满160个学分即可获得学士学位的话,学生在三年里修满额了,就可毕业,拿到文凭。如果想把修读时间拉得更长,中间还去在社会上寻求某种工作,这样七八年,甚至在更长时间里累积拿满学分也可以,很自由。
这样,可能会出现一个凑学分的现象,捡容易拿学分的课程去修读,只要凑满学分就够了。于是,有一个改进:需要在满学分的前提下,让课程群有一定的板块结构。
在与某种改善了学分制结合在一起的时候,课程在数量上的决定性作用,就可得到保障了。课程可视为给学生提供的基本营养品,抑或是商品。记得在若干年以前,本科阶段的一个学分值80美元;以160个学分计,拿满学分,总共就是12800美元。现今的价格如何,我已不知,可能在研究生阶段的单价更高了。
至于我们这里,现行的是学分制还是学年制,还是别的什么混合制,我并不十分清楚。这些年,我都是为博士生、硕士生开课,也不知道管理部门实行怎样的制度,我只管教书了。
我想说,不仅一所大学的水平与其开设课程的数量有密切关系,而且,一位教师的水平也与其开设课程的门数有密切关系。记得芝加哥大学的施特劳斯教授开设了80门课程,我本人已开设了25门课程。美国大学大都实行小课程制,即一两个学分构成一门课。而我所开设的课,有过多达相当于五六个学分的课,例如微积分课程。由此可说,我已开设了四五十门课应当不为过。即令如此,我也还不及施特劳斯。不过,上天若让我多活几年,还能继续站在讲坛上,我再新开几门课程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为什么我想多开设一些课程呢?这有多方面的原因。第一,每开一门课,就多了一扇通向世界文化的窗口;第二,没学过,没研究过的,我也想挑战,迫使自己研究得更多;第三,即使学过的,这跟教过还是很不一样;第四,我在迎接挑战时,也是挑战了自己,看自己能走多远,这种挑战的结果往往能推动我研究新的课题,因为我总是把读书、教书与出书联系起来的,由此而更深入地与书打交道。
当然,我不会盲目地追求开课的数量,对质量与水平的关注,这一根本点我天然地不可能忽略。粗制滥造与我无关。一辈子形成的理论兴趣、哲学兴趣不可能再丢失。在能确保质量的必然前提下,多开一些课程,这本身即可是一种追求。甚至,我感觉到自己对课程已颇有感情,还写了一篇题为《课程颂》的小文章呢。由小见大,欲在大的方面有所作为,必在课程上下功夫,且由此出发才可能走得更远。应当说,由于我已有相当数量的著述,这就为自己编制课程、开发课程提供了良好的基础。最近,我对此似乎已生出了更明确的想法。
大学是一个思想库,它还不只是用来“蓄”水的,它还有自己的活水源头。这个源头在哪里?在大学教授的头脑里。由此,大学不只是用来做库存的,它还生产 “水”,生产思想。大学是一块十分特别的地方,它特别能出思想,还出格外的、特别的思想。大学就是这样活着的,这样与众不同地生活着,奔跑着,一往无前。
大学是一部百科全书。这个“百”字只是一种关于 “多”的表达,它不封顶的,有多少装多少;它是包罗万象的,只看是否想到,凡想到的必追问之。越是神秘的,它越感兴趣。大学也是最愿意迎接挑战的机构,由此,它也首先是挑战自己。如果挑战失败,它必定会屡败屡战,并力求最终的获胜;因而,从相对较长的过程看,大学是屡战屡胜的,它有智慧的头脑,并且还可让先天的智慧再增长。
大学不只是传授高深学问的,大学还发展人的智慧;大学不仅发展人的知性智慧,还发展人的哲性智慧、德性智慧。大学把整个宇宙展现在学生面前,让他们看个够,看个究竟。由此,让他们知道:宇宙从哪里来?我们人类从哪里来?我们个人自己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一往直前,还是常常有回归之时?
不言而喻,并非所有的大学都能做到这一点。那我们就只对能做到这一点的大学来说吧。然而,正是这样的大学才具有代表性。说穿了,大学也就是通过五光十色的课程来实现这一点的。大学把宇宙的大门撬开了。恐怕还有一点,大学不敢讲大话:我也能把人完全说清楚。尽管最能说清楚人的仍然是大学,但它也无法把人的全部神秘揭开。还是如我多次说过的那样:上天把所有的秘密放在了人身上。由此,上天就这样作了安排,无人能把人的全部秘密打开。
哲学上有可知论与不可知论之争。可知论认为,作为一个过程,人总是可以知晓任何事物的。近几千年的历史,显示人所已知晓的东西业已构成了一个海洋。不可知论则认为,无论怎样,人也不可能知晓一切,人类也不可能。不可知论面临一个悖论:你是怎么知道人类不可能知晓一切的呢?你能举出一例来说明:存在着永远无法知晓的问题吗?你怎么知道一个不可知晓的事物都不存在吗?怎么证明它不存在?
大学独特的智慧正在于,它懂得有些东西是人永远也弄不懂的,比如说,人本身。尽管大学从许多方面在研究着人,也只是尽可能多地去认识人。苏格拉底的“认识你自己”,可换为“认识人自己”。苏格拉底最了不起的地方,可能是预言了对人的认识的极端困难性。事实上,有史以来,直面人的哲学家并不多。
无论怎样去说大学是个思想库,大学包罗万象,大学是一部百科全书,都离不开那个“基础粒子”——课程,都通过课程来体现,那个“库”里保存的和不断增加的东西都以课程的形式存在为最好。大学问家们在向那个思想库投放时,也最愿意以课程的方式实现。甚至,这就是那些大科学家、哲学家的夙愿,他们特别希望自己的学问能变成或进入课程,当然,他们也深知做到这一点不容易。
大学问家为何关注课程?
叶圣陶的文章可以进入课本,有些古文和唐诗宗词能进入课程,这或许是他们没有料到的。当初他们在创作时也绝无可能想到未来会有这种结果。这一结果是在历史中形成的,是他们创作的价值为后人所明白,尤其是哪些知晓教育意义的人,由他们从前人的创作中进行精选,使之成为培育后人的范本。
对于研究生的教学,教师中有不少人是讲自己写的东西。教什么,写什么;写什么,教什么,不去啃别人嚼过的馒头。也就是,开什么课,自己写;自己写出来的东西使之成为课程。教师为何乐于这样做呢?显然,当自己所研究的东西能进入课程时,其留存的可能性增大,其学术价值也增大,或许还能引发出新的感悟,获得新的发展。在教学过程中,让自己的思绪随着自己的讲述放飞时,是有可能生出新的灵感来,至少有利于自己的理论更加系统化。
数学界的大人物,如吴文俊、华罗庚、关肇直等都是十分热衷于教学,把自己的成果变成课程的。
据我所知,一些世界一流大学,如哈佛大学、加州理工大学,都重视本科生教育。哈佛在校生约两万人,其中八千名本科生,即每年招两千名本科生。加州理工大学(即CIT),每年招两百名左右的本科生,连同研究生,在校学生2200名,本科生所占比例与哈佛相近,均为百分之四十左右。为什么这些名牌大学也热衷于本科生教育呢?
首先是那些学问大师很盼望自己的研究成果能凝结到本科生的课本上去。当然,高质量的本科生对于研究生教育也是至关重要的,但主要原因还在于本科生教学有利于整个大学这盘棋走活;除了有利于各种教育资源的有效利用外,大师们投入本科生课程的开发,也大大利于整体办学水平的提高。并且,那些大师愿意为本科生开课。这很重要,让本科生们能领略到大师的风采,甚至能影响到他的一生。换言之,这些大师对学校隐性文化的生成起特别大的作用。
我们这里曾有过关于教授或研究生的指导教师们必须给本科生上课的要求。然而,在美国,这无须规定。规定了的,可能是不一定做到了的。还有一些管理上的问题造成了某种利益驱动,使得教授们之中的一些人不太情愿给本科生上课。
我还记得,本科一二年级的课,在许多年以前,是由最有水平、最有经验的教师上的。不知今日状况如何了。例如,我常提到一些大数学家们为本科一二年级开课。反之,高年级的专业就由比较年轻的教师们上课。基础打好了,再往上走,就容易多了。
我1955年上大学,当时为我们讲一二年级课程的,正是水平最高的李盛华教授、肖伊莘教授和杨少岩、李传和等优秀教师。虽然1955年至1959年,经过了不少动荡,四年本科只安心念了一年半,可正是这一年半的基础打得好,毕业以后的自学,困难就少多了。大学本科阶段的高年级课程,直至硕士、博士的学位课程,我都通过自学完成了。拨乱反正之后,李盛华教授又为我们年轻教师讲授了一系列那时候尚处于前沿的数学知识,如测度论、半群理论等。
另外,我们还可看到,在美国大学里不存在教学与科研的所谓矛盾问题。在科研与教学之间,乃至与本科生的教学之间,都通过课程自然而有效地联结起来了。
我们中国这种教学与科研矛盾的问题,多少受到当年苏联的影响。实际上,在二十世纪的三四十年代并不是那样分离的。现在,我们这里还有一个产学研结合的说法。我们知道,美国在二战期间,连武器的研发都是放在大学的,且多是私立大学,那是自然的产学研结合,用不着喊口号。良好的机制最有力量。
大学里有专业,而专业实则是一个适当构建起来的课程群。高水平的大学讲究学科,本科生在专业上念,研究生在学科上念。学科的高水平是课程建设的后盾,从而,高水平学科也是高水平专业的后盾,高水平学科孕育出高水平课程。
从学科到课程,尤其是本科生课程,这中间尚需一些心理学、教育学知识。有此,则能使课程的编制与建设更有效。越是高年级,这种编制的困难反倒越小;越是低年级,尤其是本科,特别需要课程编制者匠心独具。但大师们能有此匠心。
我记得,在CIT有80位院士,其中人文科学院士28位,占35%。这里,我们看到了在世界一流大学里人文科学决定性作用的一例;然而此处我们的重点是说,这35%的院士都很愿意为本科生讲课。
这里,也还有个机制的问题。那就是科学研究与教学汇合于大学,而不是分离。前苏联和曾经的中国,科学研究是由专门的机构进行的。这种分割式的做法明显不符合辩证法,而苏联恰好是宣称自己信奉辩证唯物主义的。倒是不如此宣称的美国没有这种分割,他们的科研与教学高度结合,都融入大学。
自19世纪初,洪堡将科学研究引入大学以来,这种结合的传统一直存在于大学。唯一例外的正是前苏联和曾经的中国。从更具体的方面看,那些生活在被隔离开来的专门研究院所里的科学家、学问家们,即使想把自己的研究成果转化为课程,亦将十分困难了。强烈的愿望也无法实现。
现在流传着“双一流的说法”,即一流学科与一流大学。这是一种“一流”情结影响着国人,都盼望着自己国家有世界一流大学出现。但这种主观愿望却让许多客观因素制约着,并且,在对“一流”的理解上存在着不少问题。
有人说,只要有十一二个一流学科,就是一流大学了。如果只有十一二个一流工科,这样的大学绝不可能一流,充其量是二流、三流的大学。麻省理工大学(MIT)在20世纪30年代70%是土木建筑,一所典型的工科大学,当时就只是美国的二流、三流大学。在该大学董事会改变了办学方向,决心大力发展文理,并经过了十多年努力之后才成为美国一流从而也是世界一流大学了。如今,许多大学的董事会,更多的校长、教育家明白这个道理了:如有强大的文理即可成为世界一流,没有一流文理无论如何成不了世界一流大学。这就是学科结构问题。
另一个问题是:一流学科,包括一流的文理从哪里来?没有一流的师资行吗?
第三个问题是:一流的师资能否开发出一流的课程来?他们有兴趣吗?他们有必要的心理学、教育学知识来支撑他们的开发吗?开发的其他条件具备吗?
第四个问题是:有相应的机制保障吗?有较好的客观环境吗?
故而,总归而言,需有一流的环境或机制,有一流的师资,有一流的课程,有具备良好结构的一流学科,才可能有一流的大学。故而是五个“一流”,两个远远不够啊。
在上述五个一流中,一流的环境与机制的形成,不是大学或教师的直接责任。比如说,没有谁比生活在大学里的更了解大学,更懂大学;因而,大学是无须外在力量介入的。如果外在介入了,大学能办好吗?还能一流吗?无须有的东西有了,还能指望一流大学吗?这个问题恐怕不是大学自身可以解决的。
看看那些拥有世界一流大学的地方,他们要么是政府完全不管它(如美国);要么给你钱后也完全不管大学内部事务(如欧洲),他们的一流就生长出来了。
因而,在上述五个“一流”中,第一个“一流”是必须具备的,然而,它不属于大学自身。在第一个“一流”具备后,随之的四个“一流”就都是大学自己的事了。可是,只要第一个“一流”出现了,靠自身力量办成世界一流大学,中国人是能做到的,中国学者有智慧、有能力。由此也可以说中国人的一流情结,并非一厢情愿。
(责任编辑:赵惠君)
On Courses and Universities
ZHANG Chu-ting
(CollegeofEducationScience,HunanNormalUniversity,Changsha410081,China)
The number and the quality of courses offered by a university are closely linked with its teaching level. A university is a think-bank and an all-embracing encyclopedia,which is demonstrated through courses. Specialties,curricula,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teaching are naturally and effectively connected through courses. Courses are vital for disciplinary construction of top-ranking. After having established top-ranking curricula,it is possible for Chinese scholars to build world first-class universities by taking their own efforts and using their wisdom and capability.
courses;universities;first-class
2016-11-11
张楚廷(1937-),男,湖北天门人。湖南师范大学前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南涉外经济学院名誉校长,主要从事教育哲学、高等教育学研究。
G640
A
1672-8874 (2016) 04-0048-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