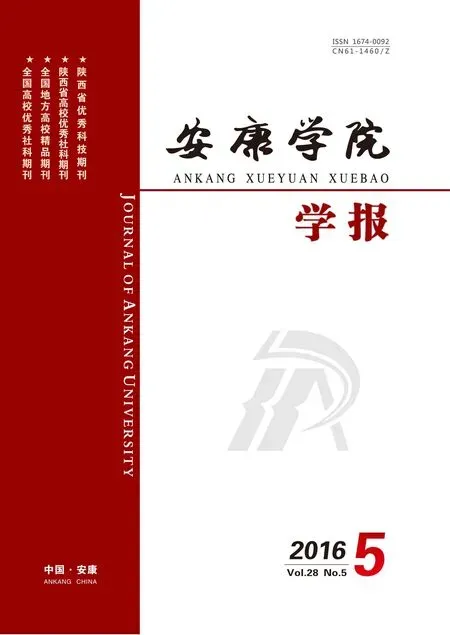辩诉协商制度微探
游雅南
(西安政治学院 军事法学系,陕西 西安 710068)
辩诉协商制度微探
游雅南
(西安政治学院 军事法学系,陕西 西安 710068)
辩诉协商作为一种司法制度,是从美国建立并发展起来的。因其具有高效、灵活、便捷的特点,故自建立之初便一直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并逐步向世界其他国家发展。随着我国法治进程的推进,引入辩诉协商制度已成为必然。当然,这种引入不是对国外制度的简单移植,而是从我国国情、军情出发,建立辩诉协商制度中国化的改良模式,并对其风险加以有效的控制和防范。
辩诉协商;刑事诉讼;军事刑事诉讼
一、辩诉协商制度概述
辩诉协商作为一种司法制度,最初是从美国建立并发展起来的。据考察,最早在1840年就已经出现了这种协商的实践[1]。所谓辩诉协商(Plea Negotiation),又称辩诉交易(Plea Bargaining) 或者辩诉协议(Plea Agreement)。布莱克法律词典把辩诉协商解释为:“刑事被告人作出有罪答辩以换取检察官较轻的罪名或者数项指控中的一项或者几项的某种让步,通常是在获得较轻的判决或者撤销其他指控的情况下,检察官和被告人之间经过协商达成的协议。”[2]19世纪30、40年代,美国经济高速发展,城市化速度加快,人们也从一个地方不断的迁移到另一个地方,这导致了社会财富的分配不均,社会矛盾激化,犯罪率飙升的问题。为了能够利用有限的司法资源解决日益增多的案件,检察官开始使用协商交易的方式换取被告人的认罪,形成了辩诉协商这一诉讼形式。然而,尽管辩诉协商在实践中一直被广泛运用,但因多数法院对此存在着抵触情绪,所以协议几乎都是私下进行的。直到1970年,联邦最高法院通过布拉迪诉美国案(Brady V.U.S.)①被告人布拉迪于1959年被控以绑架罪,由于被绑架人获救时已经受伤,按照《美国法典》第18卷1201(a)规定最高刑是死刑。布拉迪诉讼开始时选择了无罪答辩,在得知同案其他被告人将会作认罪答辩并就布拉迪的犯罪事实作证时,布拉迪也做了认罪答辩。1967年他提出其认罪答辩时受到减轻量刑的引诱而并非自愿,但法院一致认为布拉迪并未接受到任何减轻量刑的引诱表示,并做出了“答辩系自愿,明知做出”的结论。才正式赋予了辩诉协商的合法性地位,使得这一长期应用于司法实践中的做法从幕后走向台前。1974年7月1日美国《联邦刑事诉讼规则》出台,其中第四章第11条对辩诉协商的一般原则及公布、接受、驳回等一系列程序都予以法典化和制度化,辩诉协商作为一项实际运作多年的刑事简化程序被固定下来。辩诉协商制度是在实践中产生的,它力求在当事人意思自治和平等的基础上达成“共赢”,而且辩诉协商还具有结案快、效率高,有利于解决案件严重积压的问题以及能够减轻对刑事司法系统的巨大压力等优点,所以其一经问世即获得了蓬勃的生命力。现在的美国,刑事案件中通过辩诉交易来结案的比率已经达到了90%[3]。尽管美国有反对者对此制度提出了种种非议,但辩诉协商在没有增加法官、检察官的数量下,迅速解决了大量的刑事案件,节约了有限的司法资源,故此为司法部门乐于采用[4]。随着辩诉协商制度的合法化和广泛应用,它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地位也越来越重要。这一制度在世界上很多国家生根、发芽并迅速发展,各国结合本国国情对辩诉协商制度不断予以改进,成为当今最重要的刑事诉讼制度之一。
二、辩诉协商制度的适用意义
辩诉协商制度已经在许多国家盛行,而且它在很大程度上也突破了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的界限。在当前我国推进依法治国的进程中,我们可适当的引入此项制度,将其纳入法律规范轨道,从而促进司法改革。
(一)满足司法高效,节约诉讼资源
随着经济的蓬勃发展,我国的犯罪率也逐年增加。从1990年、2000年、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以及《2014年中国人权事业的进展》白皮书可以看到,1990年全国审结一审刑事案件54.7552万件;2000年,全国共审结一审刑事案件55.8万余件;2010年全国审结一审刑事案件77.9641万件;2014年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审结一审刑事案件102.3万件。案件处理的增长率迅猛上升,司法机关的人力、物力、财力资源却十分有限,案件往往得不到及时处理,积压的工作量可想而知,这种矛盾的状态严重制约了各项工作的正常开展。对司法机关而言,结案时间的延长造成了司法资源的极大浪费,可能导致与案件有关的证据大量流失,造成未决案件的堆积;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而言,案件长时间得不到处理或审判导致被无限期的羁押,自由的丧失,财产甚至生命等实体性权利处于不明确状态,对未知结果的恐惧使得他们惶惶不安;对被害人而言,长时间的诉讼过程,也会使其身心俱疲而饱受煎熬。“处罚犯罪的刑罚越是及时和迅速,就越是公正有益。”[5]虽然我国刑事诉讼中的简易程序制度能够提高一部分案件的诉讼效率,但其适用范围十分有限,而且也不能避免庭审活动的进行,在缓解我国刑事审判压力方面仍是杯水车薪。因此,建立一条快速便捷的诉讼程序就成为一种可供考虑的选择。辩诉协商制度恰好是实现用有限的司法资源尽快解决司法问题的有效途径,它简化了诉讼的繁冗程序,参与辩诉协商活动的控辩双方都乐于接受这种处理案件的方式并能从中受益。通过辩诉协商程序,可为不堪重荷的司法部门减负,从而集中精力检控、审判社会影响更广情况更复杂的案件。
(二)符合我国刑事政策的精神
我国刑事诉讼法律中并没有规定辩诉协商制度,但却不乏辩诉协商的因素。例如我国一贯实行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刑事政策无疑蕴含着辩诉协商的精髓,而且在司法实践中也存在着检察官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行辩诉交易的司法操作。尽管我国的刑事政策逐渐从“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转变为“宽严相济”,这一“宽严相济”的政策中同样有“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身影。2010年2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它对于最大限度地预防和减少犯罪、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引入辩诉协商制度,能够最大限度的发挥刑事政策的优势,避免实践中出现的“坦白从宽,牢底坐穿;抗拒从严,回家过年”的司法悖论,给坦白者以司法救济,对他们弃恶从善服膺法律的意愿以相对较轻处罚来实现特殊预防与惩罚的目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接受检察官的提议认罪,得到了司法机关允诺的“宽恕”,使人们重拾对司法机关的信任,维护了司法威严,刑事司法工作也从而进入良性循环。
(三)保障当事人的权利
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将“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了我国刑事诉讼法的基本任务,体现了惩治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是从《宪法》第三十三条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后,又一部法律规定了尊重和保障人权,标志着我国人权保障的显著进步。因此,在我国的职权主义诉讼模式中,代表国家行使追诉权的控方要与长期处在弱势地位的辩方力求平等,在法律实施的空间里,给予每个人应得的权益。从程序上看,辩诉协商制度不仅给予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看得见”的机会,还赋予其亲自有效参与司法程序的机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再仅仅是被处置的对象,而是在自愿、自由、明知的基础上通过参与刑事诉讼活动,运用合理、合法的诉讼行为影响甚至决定自己的命运。被害人在美国的辩诉协商程序中并不能直接参与,但笔者认为,为了更好地保障被害人的合法权利和合理诉求,尊重被害人意见,我国在引入该制度时应进行必要的改良,赋予被害人参与协商的机会。一旦达成协议,被害人可尽早从诉累中解脱出来,尽快获得赔偿,以恢复被犯罪行为所打破的正常生活状态,身体和精神得到抚慰[6]。
三、辩诉协商制度在普通刑事诉讼中的改良运用
2002年4月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发生了被媒体称作是“中国辩诉交易第一案”的“孟广虎故意伤害案”。当时,牡丹江市铁路运输检察院及法院共同协商并报高级法院,首次采用该方式审结此案。这一做法证明了我国引入辩诉协商制度并非遥不可及的事情。建立有中国特色的辩诉协商制度,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考量:
(一)适用辩诉协商制度应具备的条件
辩诉协商在进行具体操作时,应具备以下条件:必须是具备一定证据而证据又不充分的案件;虽然我国检察官在刑事诉讼中居于主导地位,但在适用辩诉协商制度中还应当妥善安排处理好“检察官——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害人”三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笔者并不赞同美国将被害人排除在辩诉协商之外的规定,我国应该将被害人吸纳为参与的主体,以便表达其合理诉求。三方主体在公平、自愿、明智的前提下协商并达成一致意见后才能运用该制度。
(二)不适用辩诉协商的案件类型
为了不影响辩诉协商制度的效果发挥,笔者认为不宜将适用案件范围划定过窄。反观之,划定辩诉协商不适用交易的案件类型更具实务操作性。主要涵括以下三类:一是犯罪性质严重的案件。如危害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国家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危害国家安全罪;故意杀人、强奸、抢劫等严重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暴力性犯罪;其他的如毒品犯罪、涉黑犯罪等。二是犯罪情节特别严重的案件。三是惯犯、累犯、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
(三)规定辩诉协商内容
对于量刑减免幅度,检察官向法院提出建议时一般不能少于法定刑的1/3,特殊情况不能少于1/2。如果量刑幅度过小,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缺乏吸引力而大大降低辩诉协商的成交率;倘若量刑幅度过大,则摒弃了制度设计的最初基调,也损害了司法公正,有“暗箱操作”的嫌疑,不利于刑罚目的实现。对于罪名及犯罪性质,要禁止进行交易。其原因在于罪名与定性涉及法律理解的统一性,故辩诉双方无权谈判、协商、交易。对罪名和犯罪性质的协商作出禁止性规定,一方面延续了法律的严肃性和一贯性原则,另一方面也增加透明度,可以防止检察官滥用权力。
(四)协商结果处理方式
辩诉协商过程应基于平等、自愿、公开、理智、真实的前提下进行,倘若检察官故意诱导、欺骗而使犯罪嫌疑人意思表示不真实或者私下与辩方律师秘密协议而侵害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抑或检察官损害、违背、无视被害人在协商中的诉求,犯罪嫌疑人、被害人有权终止协商。此为处理方式一;处理方式二,检察机关与犯罪嫌疑人无法达成合意,或达成合意后犯罪嫌疑人反悔,协商视为无效,案件则自动转为普通诉讼程序继续进行;处理方式三,三方共识达成后形成书面协议,并提请法院审查,在法院尚未采信之前,被告人有权撤销协议。依法终止协商或者撤销协议的,视同协商、协议自始没有发生,辩诉双方在庭审中均不得将协商的情况或协议的内容作为证据使用;处理方式四,通过辩诉协商达成一致共识的案件,自检察院提起公诉之日起至判决前,被告人不得反悔。
(五)加强对检察官的监督
为了避免检察官在进行辩诉协商时滥用权力、徇私枉法,有必要从法律层面上建立起严格的约束机制。如建立辩诉协商审查程序,即达成协议后,有义务接受法院的一系列审查,内容主要是法官对被告人及被害人是否出于明智、理智、自愿地接受协议后果进行审查,以及对检察官的定罪建议是否准确,量刑建议是否合理进行审查;加强上级检察机关的监管力度;接受民众的监督、举报等。此外,还要从完善检察官的遴选制度及奖惩机制上来提高检察官专业素养和道德素质。
四、辩诉协商制度在军队中的引入
我国军事刑事诉讼领域实行局部的“军民同制”原则,即军事刑事诉讼与普通刑事诉讼部分同制、部分分制,军队平时适用我国《刑事诉讼法》基本上是没有问题的,因此军队开展辩诉协商程序可参照笔者之前在普通刑事诉讼所设计的内容来操作,这里不再赘述。但从战时军事刑事诉讼的特点来看,战时军事司法资源相对紧缺,有时候取证较为困难,通过辩诉协商制度来解决部分案件,不仅有利于提高军事司法效率,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军事法院的负担,而且可达到以最低限度的国家、军队、个人痛苦换取大限度避免非战斗性减员的效果。虽然辩诉协商制度本身具有天生的缺陷,但并非不可行,只要我们合理运用,扬长避短,兴利除弊,发挥其可借鉴的优势,就能将消极因素转化为积极因素。笔者对于战时辩诉协商制度的构建有以下几点拙见:
(一)战时辩诉协商适用范围
战时以维护军事利益,保障军事行动顺利进行为中心。因此,为了维护优质高效战时军事秩序,实现“双赢”的局面,有必要将辩诉协商适用范围作出规定。一是适用于性质不严重、危害性较小,证据确实但不充分的案件。这类案件的处理能够减轻犯罪军人的心理压力,促其改过自新,重新服务军队。二是适用于事实清楚但证据不充分,因受战时条件所限取证困难的案件。由于战时条件的复杂性加大了取证的难度,而欲达到起诉标准的要求,可能要耗费大量的时间、人力和财力,而且也会过度牵扯军事司法机关的精力,形成案件积压。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发生,有必要将此类案件通过辩诉协商来解决。表面上看,辩诉协商虽然从轻处罚了犯罪,但实际是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可能流失的正义,不失为一个好结果[7]。对于情节复杂、性质恶劣、影响力大、波及面广、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案件,不适用辩诉协商。
(二)战时辩诉协商内容
辩诉协商的目的是要在公平与效率的博弈中取得最佳平衡点,如何把握好这种动态的平衡,则需要对作为控诉一方的军事检察官的交易权限范围作出明确规定。根据国外司法实践并结合我军实际情况,可将军事检察官协商的权限定为减轻指控和刑罚让步两项内容。对于减轻指控,军事检察机关只能放弃指控数个犯罪构成事实中的次要犯罪事实,或者数罪中的次要犯罪。对于刑罚让步,战时犯罪嫌疑人可能获得的量刑减免幅度最多不得超过其应当判处刑罚的1/3。
(三)战时辩诉协商的程序
首先,战时辩诉协商的发起申请权在检察官手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被害人没有此项权利。军事检察院依据辩诉协商适用范围决定能否以辩诉协商的形式解决。经初步审查后,军事检察官认为案件可以适用的,则与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律师沟通。涉及被害人时,军事检察官应当组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被害人就赔偿问题进行商讨,达成共识后可将赔偿协议纳入军事检察院的量刑建议中。辩诉协商的过程要确保三方是在平等、自愿的前提下达成一致意见。其次,军事检察官应提出辩诉协商意见并报请检察长批准。最后,军事检察官应制作决定书,并写明协商具体内容、参与人、时间、地点等要素。辩方以及被害人核对无误后应在协议书上签名或盖章,之后协议书移交法院进行审查。
(四)军事法院审查程序
军事法院对战时辩诉协商的审查,是为了防止军事检察官在辩诉协商过程中因滥用职权导致牺牲公正的不正当交易发生,也是为了保证军事法院定罪权的完整性和国家刑罚权的统一行使。在审理方式上,军事法院接到军事检察院移送的辩诉协议书、案卷和证据材料后,应及时指定军事法官对案件进行审查并作出裁决。军事法官审查案件一般以书面形式进行,但须听取被告人、被害人对辩诉协商过程及协议书的意见,必要时也可通知军事检察院派员到场。在协商案件裁判的法律后果上,应视不同情况,分别作出以下裁定或判决:第一,协议并非出于被告人自愿,或者军事检察院指控的罪名错误或量刑畸轻的,裁定将案件退回军事检察院重新处理;第二,军事检察院指控的罪名正确、量刑建议合理的,按照协议的内容进行判决;第三,军事检察院指控的罪名正确但量刑建议畸重的,按照指控的罪名判处较轻的刑罚。
[1]王兆鹏.美国刑事诉讼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52.
[2]BRYAN A GARNER.Black’s Law Dictionary[M].8th Edition.Thomson business,2004:1190.
[3]李向楠.论辩诉交易在我国的构建[D].北京:中国政法大学,2012:4.
[4]陈卫东,刘计划.从建立被告人有罪答辩制度到引入辩诉交易——论美国辩诉交易制度的借鉴意义[M]//陈光中.辩诉交易在中国.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3.
[5]贝卡利亚.论犯罪与刑罚[M].黄风,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56.
[6]丁浩勇.辩诉交易:必要性、可行性与适用条件[D].吉林:吉林大学,2007:17.
[7]董策文.辩诉交易制度中国化研究[D].大连:大连海事大学,2012:30.
【责任编校龙霞】
Probe on Plea Negotiation System
YOU Yanan
(Military Law Department,Xi’an Politics InstituteofPLA,Xi’an 710068,Shaanxi,China)
As a kind of judicial system,the plea negotiation is established and developed from the United States.The plea negotiation system has the advantages of high efficiency,flexible and convenient.It is form the beginning of its establishment,the plea negotiation system has maintained fresh vitality,and gradually to expand other coutries around the world.With the promotion of the rule of law,the introduction of plea negotiation system has become inevitable.However,such application is not the simple transplantation of the system. On the contrary,we should establish improvedmodel of pleanegotiation system in China,proceeding from the realistic conditions of our nation and army,and exerting effective control on the risks.
pleanegotiation system;criminal procedure;military criminal procedure
D925.2
A
1674-0092(2016)05-0104-04
10.16858/j.issn.1674-0092.2016.05.023
2016-03-20
游雅南,女,四川成都人,西安政治学院军事法学系讲师,军事法学硕士,主要从事军事司法研究。
——以“被告人会见权”为切入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