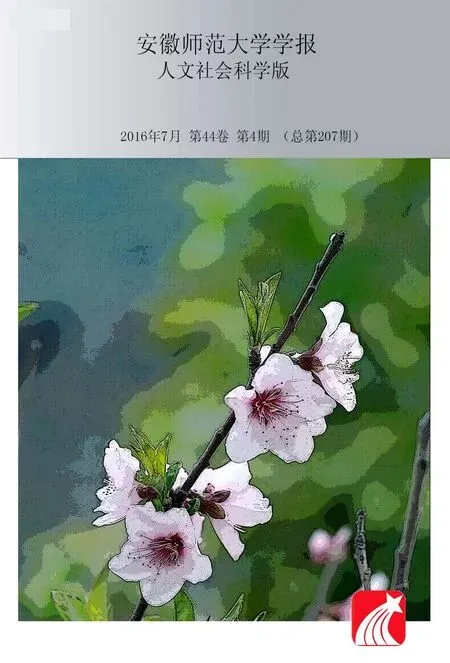我国社会政策碎片化与民生困境*
包先康
(安徽工程大学 人文学院/MPA教育中心,安徽 芜湖 241000)
【社会学研究】
我国社会政策碎片化与民生困境*
包先康
(安徽工程大学 人文学院/MPA教育中心,安徽 芜湖 241000)
关键词:社会政策;碎片化;民生困境;人本取向
摘要: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社会政策一直呈现出碎片化的特征,具体表现为非系统化、非一体化和非常态化。社会政策的碎片化曾经引发了诸多民生困境。要走出民生困境,需要建构人本取向的社会政策体系。人本取向的社会政策是一种“基本保障+资产积累+增能”的新范式。要建构这样一种新范式,社会政策的制定要由供给导向转向需求导向,并建构满足民众多层次、多样化需求的社会政策体系。
社会政策是政府对社会问题与人的需要的回应。系统的、科学的社会政策可以较好地对出现的社会问题和不断变化的人的需要作出即时有效的回应。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浅层的、深层的社会问题不断出现,而不能得到有效的解决;同时,人的多层次、多样化的需要不能得到有效的满足而心存抱怨。于是,我国从事社会政策研究的学者开始反思我国的社会政策。李迎生[1]和王思斌[2]指出,相对于经济政策,我国的社会政策处于弱势地位,并且是残缺不全的,使得公民的社会权得不到很好地保护,加剧社会风险。程玲的研究指出,改革开放前我国政府建构的社会政策体系“呈现出非现代性、非规范性、非一体化和非持续性的特征”[3]。还有学者对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碎片化”[4]和“社会保险的碎片化”[5]的原因和危害进行了揭示,分别提出了建构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和社会保险体系的基本路径。既有的研究基本上把握了我国社会政策的基本现状,并揭示出特定社会政策的碎片化特征。本文试图进一步阐明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社会政策体系“碎片化”的具体表现,论证社会政策碎片化必然会引发民生困境,进而试图建构出走出民生困境的社会政策新范式。
一、我国社会政策碎片化的表现
新中国成立之初,基于尽快恢复社会秩序的考量,国家先后制定了以社会保障为基础的一系列社会政策。及至1978年,大陆逐步形成了体现朴素平等主义思想的初级形态的社会政策体系,其特征总体正如许多学者指出的那样,表现为碎片化。后来市场化导向的改革,不仅没有改变这种状况,在特定时期社会政策反而变得更加支离破碎。我国社会政策碎片化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非系统化
现代社会政策皆由一系列相互关联、相互配合与协调的规则和行动体系构成的。从社会政策实践发展史看,其主要功能在于规避工业文明所带来的更大的不确定性和风险,即社会政策是 “一种风险管理系统”,履行着“重新分配风险”[6]21的职能,并通过有效的“风险管理”和“风险分配”,降低个体、组织和社会风险,从而使得社会民生得以保障,而不至于让民众陷入生活困难、社会陷入失序或无序。但这种功能的履行,任何一个单一的社会政策皆难以担当,只有系统化的社会政策才能充分而有效地发挥其功能。可是,长期以来,我国社会政策呈现着不完整、非均衡的非系统化的特征。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政府开始了以社会保障为核心的社会政策体系建构。20世纪50年代一开始,政务院就先后颁布了《救济失业工人暂行办法》(1950)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1951)。这两个文件对城市职工的基本医疗、生育、失业、养老、病假、伤残、死亡等待遇作了最低标准的规定。从而在特定时期、特定群体中建构了低水平的“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保障体系。但后来,由于过于强调意识形态的斗争,出现了“社会问题政治化”[7]的倾向,建立于计划经济体制之上的、具有浓厚政治意识形态色彩的社会保障制度的根本目标是要“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和共产党领导的先进性”[8]37。其逻辑是:资本主义社会曾经出现的社会问题,社会主义国家不应该发生。它使得很多社会问题——就业问题、教育问题、住房问题等——隐性地存在着,导致了社会政策的遮蔽,影响了社会政策体系的进一步完善。而这种社会政策体系本身有着试图以社会保障取代社会政策的倾向,进而忽视了其他社会政策的制定和完善,使其体系既不完整,发展也不均衡。
自改革开放至21世纪初,伴随着社会深度转型,我国的社会政策也发生了较明显的变革。这次变革是基于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以社会保险制度建设为核心的社会政策体系建构过程。
20世纪80年代,基于平衡新老企业养老负担不均衡的问题和提高全民所有制企业市场竞争力的考虑,中央政府于1984年在全民所有制企业尝试退休费用社会统筹试点;第二年人事部发出了《劳动人事部保险福利局关于做好统筹退休金与退休职工服务管理工作意见》,确立了全民所有制企业职工养老社会统筹的基本政策框架;第三年中央政府决定在国有企业新招的工人中一律实行合同制,并规定了合同工与固定工差异化的养老金筹资模式和收益规则,这既是我国探索新型社会保险制度开始的标志,也因此开启了基于不同福利待遇而将国有企事业单位的员工区别为体制内和体制外的先河,社会政策也因此变得更加支离破碎。
20世纪90年代,我国政府继续深化这种社会政策体系的建设。在养老保险方面,1991-1999年国务院先后颁布了《关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1991)、《关于深化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通知》(1995)、《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1997)、《关于实行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省级统筹和行业统筹移交地方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1998)、《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1999),至此,基本确立了现行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在医疗保险方面,1988 -1999年相关部门先后出台了《职工医疗保险制度改革设想》(1988)、《关于试行职工大病医疗费用社会统筹的建议》(1992)、《关于职工医疗制度改革的试点》(1994)、《国务院关于建立职工基本医疗制度的决定》(1999)等文件,逐步确立了医疗成本由国家、企业、个人三方合理负担、实行统账结合的社会保险制度。至此,自改革开放至新世纪之初,以社会保险为核心的社会政策体系框架基本形成。但社会保险并不能等同于社会政策,以社会保险代替社会政策,也必然会造成社会政策体系的不完整。
21世纪,随着民生问题和社会公平问题日益突出,迫切需要我国政府做出积极而有效的回应,以满足未来可持续的、健康发展需要。在此背景下,我国政府立足于解决当前面临的社会问题并为将来的发展确立方向和原则,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目标和“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原则,逐步确立了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与加强社会管理”为重点的社会建设,这为“社会政策时代的来临”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思路。以关注弱势群体为出发点、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基础、以加强公众权利保护和切实保障社会公平为核心的社会政策体系正在逐步形成。但到目前为止,以满足社会成员多样化、多层次需要的完整的社会政策体系并未真正形成,也就难以充分发挥其正功能。
(二)非一体化
我国的社会政策非一体化是指各种社会政策以相互分离的状态存在,具体的表现为:社会政策的城乡分割、部门分割、地区分割、体制内与体制外的分割等。
就城乡而言,城乡分割的总体性制度安排是导致社会政策城乡分割的根源之一。从社会政策体系建构来看,我国社会政策建构“重城市轻农村”“先城市后农村”“城乡有别”。以社会保险为例,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国家社会保险制度关注的对象主要指向城市职工,农村除了“五保制度”和“集体合作医疗”之外,农民基本上被排斥在社会保险范围之外;改革开放至21世纪初社会保险制度改革及体系的建构,仍以满足城市职工和居民的需要为主。社会保险是如此,其他的社会政策亦基本如是。直至21世纪,随着社会主义新农村战略的确立,农村社会政策才逐步纳入到新农村建设体系之中,逐步普及了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和农村低保制度,逐步建立了农村医疗救助制度等。但城乡的社会政策体系是两套封闭的体系,各自封闭运行。
就部门而言,在社会政策领域,长期形成的部门福利根深蒂固,不同部门享有的社会福利水平、福利的供给方式往往差别悬殊。除了新中国之初在全国范围的城市职工中实施短暂的统一的社会福利供给之外,改革开放前基本上实施的是单位福利。改革开放后,随着福利双轨制的实施,单位福利并未得到根本改变,单位间的福利鸿沟、国有企事业单位和政府部门同其他经济组织、社会组织间的福利鸿沟不仅没有缩小,反而进一步扩大。以养老为例,很长时间内公务员系统和大部分的国有事业单位,并未融入社会养老统筹之中,而且享有较高水平的养老服务,而企业职工基本上全部纳入社会养老统筹中,他们享受的养老服务的水平较低。
就地区而言,由于我国地域辽阔,区域间发展不平衡,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社会保障“社会化”改革,中央政府在社会政策领域中角色的弱化甚至退出,以及地方社会政策创新的强化与跟进,“各地社会保障制度安排和福利水平的差距进一步加大,福利的地方化趋势更加明显”[9]。随着社会保障和福利的地方化,经济发达地区的城乡居民,能够享受比欠发达地区高得多的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的地区差别日趋突出。
就同一部门或单位而言,体制内和体制外工作人员的社会保障具体制度和实际福利水平也存在着特别明显的差异。这在政府部门、国有企事业单位表现得十分突出。改革开放以来,在政府部门、国有企事业单位实行定编定岗,在编的成员属于体制内的人,他们能够享有体制内较好的福利,而在体制外的合同工、临聘人员往往被排斥在体制福利之外。
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的“区隔”,使得社会政策的碎片化变得更加直接、具体,进而使得城乡差别、地区差别、部门差别和个体之间的差别变成社会成员之间的直接体验,社会排斥和社会不平等由抽象变得具体,这严重影响了社会成员生存、生活和发展困境的归因。社会风险加剧,增加了社会和谐环境形成的阻力。
(三)非常态化
在相当长时期内,我国的社会政策存在着一种“事本主义”的取向,社会政策的制定本着一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宗旨,很少考虑人的正当、合法、真实和根本性发展的需要,也较少考虑政策的长期后果,社会政策具有应急性或非常态化的特征,这是我国社会政策碎片化的又一体现。
计划经济年代,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我国政府在某些方面采取了“非社会问题化”[3]的策略,也就不能出台相关社会政策。以就业政策为例,20世纪50年代,中国政府就向国际社会宣布,中国解决了失业问题。但后来,由于经济发展出现了问题,就业成了严重的问题。面对这一问题,政府出台了“待业”政策,后来干脆用政治动员的方式,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以缓解城市就业压力。改革开放之初至20世纪90年代,由于意识形态的惯性,“失业”仍是一个难以启齿的概念,面对城市企业开始出现职工待工和停工现象,国务院先后颁布了《关于妥善处理部分全民所有制企业停工待工有关问题的通知》(1990)和《国有企业富余职工安置规定》(1993)政策,这两个政策具有明显的应急性特征,再加上政策规定的模糊性,其实施并未达到理想效果。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大量国有企业员工在“减员增效”的改革中失业,又“创造性”地提出了“下岗”的概念,并出台了《关于切实做好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工作的通知》(1998)。这个文件只是针对大中型国有企业下岗员工提供基本生活保障、就业服务,而不针对其他企业或行业的待工和停工人员,具有明显的甩包袱的事本主义倾向。从后来政策的实施效果来看,国家再就业工程较多地带有“就事论事”的色彩,缺乏对整体改革的配合。这种“重事不重人”、下岗和失业区别对待的政策,也就很难解决当时所面临的失业和下岗问题。总体上来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就业政策具有明显的丢包袱的市场化的倾向,而政府在促进就业、就业服务和劳动者权利保护等应该有所作为的就业政策领域,难有很好地作为,就业政策的非常态化也就在所难免。应急性政策不仅不利于社会保障制度衔接与监管,还在客观上进一步拉大了城乡差距。[10]
二、我国社会政策碎片化引发的民生困境
前述碎片化特征,使得我国社会政策面对复杂的社会问题和人的多层次、多样化的需要,必然顾犹不及。在特定的时期、特定的情况下必然会造成部分甚至相当一部分社会成员不能为社会政策所覆盖,而陷入民生困境。
在中国古代,“民生”问题是个人或家庭问题。古人云:“民生在勤,勤则不匮。”(《左传(宣公十二年》)现代社会,民生一词的内涵进一步扩大,更多地体现为公共问题。孙中山指出,“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存,国民的生计,群众的生命。”[11]802他又指出,“民生就是政治的中心,就是经济的中心和种种历史活动的中心。”[11]825“民生是社会一切活动的原动力。”[11]835可见,在“三民主义”理论中,“民生”已经涉及到了社会生活的诸领域,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内容,而取其广义。既然民生问题已是公共问题,就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来解决,也就成为执政党必须关注的问题。因此,中共十七大报告提出了要“加快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12],十八大报告提出“加强社会建设,必须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要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在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上持续取得新进展,努力让人民过上更好生活。”[13]因此,从社会建设的视角来看,民生特指社会民生,是指社会成员基本生存生活状态和切身利益,具有生存保底性、基础保障性和发展性的特征。保障和改善民生需要建立基础性的社会保障体系、公共卫生体系、义务教育、住房保障制度,以更好地保障民众基本生活、促进人的发展与社会和谐。这些体系和制度的建构,正是社会政策的使命,而社会政策的本质是对社会福利领域的干预,社会福利与社会民生存在着高度的一致,因此,社会政策与社会民生是高度契合的。从历史经验和国际实践来看,制定和实施合理的、系统性的社会政策是解决民生问题的有效途径之一。
(一)生存型民生困境
生存型民生保障旨在保障民众底线的基本生计,具体地包括社会救济、最低生活保障、基础性的社会保障、义务教育、基础性的公共卫生、基础性的住房保障等,意在解决民众的“基本生存和生活”问题。其本质就是要“让人有尊严的活着”,即维护“人性的尊严”。社会科学意义上的“人性尊严”是指“人基于所处的社会关系和人自身的需求,通过一定的形式而具有或表现出的不可冒犯、不可亵渎、不可侵犯或不可剥夺的一种社会存在状态。”[14]9“人性尊严”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只要他是一个生命体,就具备了‘人性尊严’的权利主体资格,不因其身份、性别、种族、阶级、国籍、地位、能力之不同而有所不同,亦不因其对于社会之贡献的多少而异其评价。”[15]因此,生存型民生保护应该具有“去商品化”的性质。与之相应,基础型的社会政策应具有“去商品化”、普惠性的特征。
计划经济年代,我国在城市建立了体制内“准福利国家模式”的社会政策体系,体制内的社会成员可以获得“无限”保障,而体制外的人由于缺少单位的支持,基本生存和正常生活难以为继。在农村,除了“五保”、集体合作医疗和特殊困难的救助外,农民生存主要依靠集体经济支持,谈不上来自国家的福利支持。反之,在国家经济处于困难时期,农村经济却成了国家经济的主要支撑,实际上,城市体制内的福利的获取主要来自于农民的奉献,这就导致了在很多年景中,很多农村家庭都要度过痛苦的“青黄不接”期,过着“吃了上顿没下顿”的生活,基本生存难以保证,正常生活难以为续。这一时期,社会政策体系是不完整的,社会政策具有明显的“城市本位”——实际上的“官本位”——的倾向,普通农民难以获得来自国家层面的社会政策的“阳光雨露”,生存和生活十分艰难。
市场经济进程中,邓小平的“发展是硬道理”被部分决策者误解为“发展经济是硬道理”。在这种思想指导之下的发展实践,一切工作都要为经济发展服务。为了将国有经济培育成为有活力的市场经济主体,在政府的推动下,20世纪90年代,国有企业开展了减员增效“运动”,让数千万国有企业员工纷纷下岗,变为实际的失业者,成为体制外的人。但由于社会政策体系建构的滞后,使得相当一部分下岗工人生活陷入了困境。在农村,随着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在欠发达地区,集体经济出现了“虚化”和“空洞化”,致使曾经依赖于集体经济支撑的“五保制度”落空。同样,曾经依赖于集体经济支撑的合作医疗所能提供的公共医疗服务,也向“商品化”方向转变,其结果是:五保老人老无所依,农村出现了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现象,这些人的生存和基本生活难以保障。同时,大量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农村家庭的养老功能弱化,但农村社会保障体系迟迟未能建立,很多农村留守老人面临生存威胁,生活十分艰难。以上种种皆由社会政策支离破碎使其保底功能难以充分发挥造成的。
(二)发展型民生困境
发展型民生保障是指有利于提高民众发展机会和发展能力的生计状态或福利状态,它包括充分就业问题、较高质量的公共教育和基本的职业培训问题、消除社会歧视问题、提供公平合理的社会流动渠道以及与之相关的基本权益保护问题等,旨在解决民众基本的发展机会和发展能力问题,从而“让人有希望的活着”; 即在现有的制度安排下和相关政策的支持下,每个社会成员都能够获得相对均等的发展机会和发展能力的提高,并能够在公平竞争的环境下实现自我价值。合理的社会政策可以为社会成员提供像相对公平的发展机会和发展能力,而碎片化化、不合理的社会政策将会剥夺部分人的发展机会,阻碍个人能力的发展,从而让这些人看不到希望。
计划经济年代,就就业政策而言,国家为体制内的城市社会成员提供了“充分就业”的机会,而体制外的社会成员的就业机会被剥夺,造成了这部分社会成员就业困境,从而陷入生存困境,更谈不上获得公平的发展机会。在农村,将农民固定在土地上,实现了农民的“充分就业”,但这种充分就业是以牺牲进城机会为代价,从而使农民由一种职业固化为一种身份,再加上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为基础的一系列制度安排,农民谋求职业身份转变的渠道被堵死,真正形成“龙生龙凤生凤,老鼠养儿去打洞”的职业分途和身份固化的局面。这样的就业政策堵死了人们自由的职业流动之路,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职业身份变得“没有希望”。同样,公共教育和公平教育机会也难以得到保障,基本的职业培训难以保证,制度性的社会歧视堵死了公平合理的社会流动渠道。
市场经济背景下,政府加快了社会政策的调整和创新,但至今仍未根本改变社会政策碎片化的现状,致使相当一部分人被排除在社会政策的关怀之外,正如有人所指出的,中国的渐进改革过程,对许多社会群体而言,是一个走向更多的“无保障”(insecurity)的过程。[16]以公共教育为例,文革以后,我国政府加快了教育改革的步伐,教育政策发生了积极的变化,特别是近年来,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建立、职业教育受到重视、教育资助体系逐步完善、教育不平等状况也有所改善,但公共教育政策的碎片化状况并未得到根本改变。公共教育投入的城市化倾向使得公共优质教育资源向城市集中,加剧了城乡教育发展的不平衡,农民子女能够进入著名学府的机会变得越来越少;国家层面的公共教育均衡机制缺乏,导致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各类教育之间的差距明显;在我国高等教育领域,长期形成了“重普通高等教育、轻职业技术教育”的理念和行为倾向,高职教育被视为二流教育。致使许多高职院校生均经费不足,高水平的技能型和“双师型”教师严重不足,职业教育异化为“普通教育”。而高职院校恰恰集中了来自教育欠发达地区农村的孩子,他们在这样的高职院校中难以学到他们需要的职业技能,严重影响了他们日后的职业发展和职业前途。
社会政策应是一个完整的体系,任何单一的、相互分割的、支离破碎的社会政策在解决民生问题时会出现“按下葫芦,冒出瓢”的现象。只有各种社会政策间实现了有机的科学组合,才能真正发挥社会政策在克服民生困境中的作用。
三、人本取向的社会政策新范式的建构
实践中的社会政策价值取向大致可归纳为:“官本主义、民本主义、事本主义和人本主义”[17]。依此价值分类,社会政策取向可归纳为四种类型:官本取向、事本取向、民本取向和人本取向。由于社会政策是解决人的问题,因此我们需要建构人本取向的社会政策。
(一)理据
在中国传统中,官本主义和民本主义价值观长期并存,影响至深。从社会政策的视角看,所谓官本主义即始终置官僚或官僚行政机构于首位,一切以确保所有官僚在国家诸分配体系中的实际利益和优先位置的一种社会价值观念;所谓民本主义即在官本位的前提下,以确保全体民众享受基本权利的一种社会价值观。官本主义的社会政策“视官僚为答案”,官僚或官僚机构垄断了所有的话语权,缺少社会和民众的参与;在福利分配过程中,优先满足官僚集团的需要,虽然有时也会给予民众少量的福利,但体现了明显的“施舍——报恩”的逻辑。社会政策的官本位必将民众的实际利益置之度外,是碎片化的、保护少数人利益的、异化的政策。而民本主义的社会政策强调以民为本,理念上将民众的实际利益放在优先考虑的位置;但在实践中,其制定和执行是以官本位为前提的。数千来中国文化所提倡的民本实质上是“官以民为本”,离开了官本,也就无所谓民本。因此,绝大多数情况下,“以民为本”往往是不可持续的,甚至不能实现,民本只不过是一些思想家的“乌托邦”式的设想。因而,在民本主义价值观指导下制定社会政策很容易导致社会政策的多轨制。这样,无论是官本主义、还是民本主义的社会政策都是碎片化的。
事本主义价值观和人本主义价值观可视作现代社会的产物,它们的诞生皆与世俗主义的盛行密不可分。世俗主义具有丰富的内涵,它包括关注现实的人本主义、关注效率的理性主义、关注自致地位的个人主义和关注社会参与的平等主义。在理性主义那里,做事情即解决问题,做好了“事情”也就解决了问题,而所谓“做好事情”的标准就是效率,即以较少的投入获取较大的产出。因此,理性主义价值观是事本主义的价值基础。从社会政策的视角来看,事本主义就是处处以事为中心,以考核为目标,以达标为动力,如此等等。[17]事本主义的社会政策“以机械性效率为标准”“视问题的解决为答案”“视达标为目的”。这种“以机械性效率为标准进行成本收益分析,以此评估公共服务绩效,这样的行政活动自然也就谈不上有效地改善人们的生存状况。”[18]338这样的社会政策很容易造成“政策异化”。它使“以解决人的问题为宗旨的公共政策却给人们造成危害,即人的异化,致使人们对政策不满,反过来危及政府自身。”[19]事本主义社会政策常常具有应急性、事后性,缺乏前瞻性和连续性,也就缺乏预防和及时救治的基础功能,它可能会导致“社会的坍塌”[20]15-16,而难以建构一个“免于恐惧和贫困”[21]41的社会。
人本主义是与事本主义相对立的价值观。从社会政策的角度来看,所谓人本主义“就是一切以人为中心,一切为了人的利益,强调人是社会政策思考的逻辑起点的一种社会价值体系,它关注的是社会政策的制订和实施的根本出发点是为了人的权利、尊严、需要、成长、发展以及最终实现人的价值。”[17]实际上,任何公共政策行动的本质和核心就是政策主体通过政策行动彰显人的主体性存在。人的主体性存在为社会发展提供了动力源,而社会的全面发展也以满足主体的需要为终极目标。然而,在现实的公共政策实践中,我们通常将公共政策单纯理解为协调人们的利益关系,满足政治需要,服膺于权力的工具,出现了公共政策“政治化”和“经济化”[7]37倾向,忽视人与自然、人与自身的关系等与人的生存、发展密切相关的基本问题。其结果导致了政策与人割裂甚至对立起来,这正是自有国家以来许多政权虽历经更迭与变迁,但很多基本的社会问题始终得不到很好解决的根源之所在。
人的问题,是包括社会政策在内的公共政策的核心问题。哈罗德·拉斯韦尔创立政策科学的初衷是要帮助人们解决“社会中人的基本问题”[22]。后来,他在《政策科学的未来》中就呼吁“建立一门以社会中人的生活的更大问题为方向的解决问题的学科”[23]6。R.M.克朗指出,政策科学是“探求对人类系统的了解与改进”[24]28。他们的共同点是:政策科学将解决“人的问题”为己任的,视与“人的问题”相关的社会问题为公共政策的客体。这就决定了包括社会政策在内的公共政策必须是人本取向的,人本取向的社会政策才能根本上让国民走出民生困境。
(二)范式
综上,必须建构人本取向的社会政策新范式。人本取向的社会政策,并非福利国家式的社会政策,“因为福利国家式的社会政策只会供养弱者,却不能使他们变得更坚强;虽可临时缓解他们的贫困,却很难减轻贫困的程度,更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他们的贫困问题;虽然保障了他们的基本收入,却很难同时促进社会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25]它在实践中会出现一种叫做“福利悖论”的东西:福利国家式的社会政策在保护弱者的同时,会使得弱者更弱。我们要建构的人本取向的社会政策的目标应该是:在保护弱者的同时,要使他们变得越来越强。因而,人本取向的社会政策应该具备:“基本保障+资产积累+增能”的功能。社会政策的基本保障职能可通过“福利国家式”的社会政策来履行。而“资产积累”的功能只能通过“资产型社会政策”来实现。因为,“资产型社会政策不仅能够增加个人财富,提高个人抗风险的能力,而且能更大程度地增加国家的经济生产力,从而使社会政策与经济发展更好地协调起来。”[26]因此,“现代新型社会政策不能将重点放在穷人的基本保障上面,而应该强调授权于个人,促进个人资产的长期积累,以推动个人、家庭和社区的发展,并以这种发展来促进社会整体的长期发展。”[27]由于社会政策要解决的是人的问题,所以它还必须解决人的发展问题。故人本取向的社会政策必须注重人力资本的投资,即加强在公共教育和公共卫生领域的投资,这种投资不仅能提高个人的人力资本储备,还能提高全社会人力资本,提高国家的竞争力,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也实现了社会政策与经济政策的良性互动,提高全社会的福祉。至此,人本取向的社会政策的基本假设是:“收入+资产+能力”才能使得人们过得更好些,特别对困难群体而言。
(三)策略
首先,社会政策的制定要由供给导向转向需求导向。长期以来,我国社会政策的制定是供给导向的。供给导向的社会政策很容易陷入长官意志的陷阱,官僚可以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而制定出有利于官僚的社会政策,从而使得社会政策具有明显的官本取向;或者出于政绩的考量,或者出于堵漏洞的需要而制定出应急性的事本取向的社会政策;或者出于合法性的考量,为了获得民众的支持和认同,而制定出民本取向的社会政策。无论官本取向的社会政策,还是事本取向的社会政策,都必然是碎片化的;即使民本取向的社会政策,也会因为长官意志,不能充分了解民众的需求,而遵循“施舍——报恩”的逻辑,也会使得社会政策出现碎片化。社会政策制定的需求导向,要求社会政策制定过程中,充分倾听民众的意见,让他们充分表达其利益需求,这就需要开展充分的调查研究,掌握尽可能多的需求信息;同时,在社会政策制定过程中,鼓励和积极引导民众参与其中,参与意味着平等、意味着共享,从而保护其合法的权益。依据需求导向制定的社会政策,由于有了充分的倾听、调研和民众参与,而更容易制定出人本取向的社会政策,它更能解决人的问题、反映人的需要。
其次,建构满足社会成员多层次、多样化需求的社会政策。人本取向的社会政策一定是多层次、多样化的,因为人的需要是多层次、多样化的。其一,建立全国统一的普惠型的社会政策。普惠型的社会政策旨在满足全体国民的基本需求,以保证所有的社会成员在正常的情况下能够有尊严地活着,具有托底的功能。其二,建构促进民众财富增长的资产型社会政策。资产型社会政策旨在通过赋权等措施促进“资本积累”,让社会成员(特别是弱势群体)获得自我发展,减少其对福利的依赖,从而推动社会的整体进步。其三,建构有利于提高人的能力的增能型社会政策。增能型社会政策旨在通过对个人或家庭的人力资本的投入,提升社会成员捕捉发展机会的能力,提高其职业竞争力,这不仅能改变个人和家庭的境遇,也能促进整个国家的人力资本的提升,提高国家的国际竞争力,进而更好地保障和改善民生。总之,人本取向的社会政策体系由于能充分体现社会共享原则、特殊关照原则和全面发展原则,因而能够更好地解决民生问题,促进社会和谐与进步。
参考文献:
[1]李迎生.社会政策与社会和谐[J].教学与研究,2005(12):13-18.
[2]王思斌.我国社会政策的弱势性及其转变[J].学海,2006(6):25-30.
[3]程玲.中国社会政策的演变与发展[J].河北学刊,2010(4):123-125.
[4]郑秉文.中国社保“碎片化制度”危害与“碎片化冲动”探源[J]. 甘肃社会科学,2009(3):51-58.
[5]盛和泰.养老保险“碎片化”的成因分析与应对策略[J]. 保险研究,2011(5):32-35.
[6]安东尼·吉登斯.失控的世界——全球化如何重塑我们的生活[M].周红云,译.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
[7]包先康,朱士群.非社会问题化与社会政策遮蔽[J].晋阳学刊,2011(4):28-32.
[8]关信平.社会政策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
[9]彭浩然、岳经纶.东莞医改与神木医改:地方社会政策创新的经验与挑战[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1):165-171.
[10]张秀兰,等.改革开放30年:在应急中建立的中国社会保障制度[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9(2):120-128.
[11]孙中山.孙中山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12]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07-10-25(01).
[13]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12-11-09(02).
[14]韩德强.论人的尊严:法学视角下人的尊严理论的诠释[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
[15]陈进华.民生伦理:关于民生问题的伦理学诠释[J].哲学研究,2010(3):99-102.
[16]Cook S..From Rice Bowl to Safety Net:Insecurity and Social Protection during China's Transition[J].Development Policy Review, 2002,20(5):615-635.
[17]范明林.从社会政策的过程观谈社会政策的价值取向[J].社会,2002(2):24-27.
[18]丁煌.西方行政学说史[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
[19]张晓峰.政治理性主义与中国转型时期公共政策中人的问题[J].理论探讨,2005(3):86-88.
[20]Polanyi,K.The Great Transformation.Boston:Beacon Press,1957.
[21]考夫曼.社会福利国家面临的挑战[M].王学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22]陈振明.政策科学的“研究论纲”[J].中国社会科学,1997(4):48-61.
[23]Harold D.Lasswell.The Future of Political Science.New York:Atherton,1963.
[24]R.M.克朗.系统分析与政策科学[M].陈东威,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
[25]冯希莹.社会福利政策范式新走向:实施以资产为本的社会福利政策——对谢若登的《资产与穷人:一项新的美国福利政策》的解读[J].社会学研究,2009(2):216-227.
[26]Sherraden, Michel.Assets and the Poor:A New American Welfare Policy[M].New York:M.E.Sharpe,1991.
[27]杨团,孙炳耀.资产社会政策与中国社会保障体系重构[J].江苏社会科学,2005(2):206-211.
责任编辑:汪效驷
Social Policy Fragmentation and Plight of People's Livelihood in China
BAO Xian-kang
(CollegeofHumanities/CentreofMPAEducation,AnhuiPolytechnicUniversity,WuhuAnhui241000,China)
Key words:social policy; fragmentation; the plight of people's livelihood; people orientation
Abstract:Since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social policies have been show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fragmentation in China, which specially embody non-systematization, non-integration and non-normalization. The fragmentation of social policies has led to a series of plights of people's livelihood. To get out of the people's livelihood difficulties, it is necessary to construct the people oriented social policies. The people oriented social policies are a new paradigm about “basic security + asset accumulation + growth”. To construct such a new paradigm, the formulation of social policies should shift from the supply oriented to demand oriented, and construct the social policy system to meet the public the multi-level and diversified needs.
DOI:10.14182/j.cnki.j.anu.2016.04.018
* 收稿日期:2015-11-11;修回日期: 2015-12-03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15BSH022);安徽省高校人文社科重大研究项目(SK2015ZD05);安徽省省级质量工程项目(2014jyxm184)
作者简介:包先康(1964-),男,安徽舒城人,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农村社会学、政治社会学、社会政策和公共管理。
中图分类号:D03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2435(2016)04-0515-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