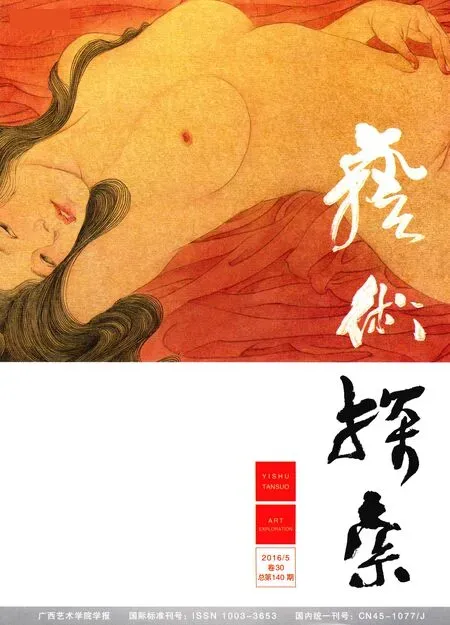情:明中叶后中国古典戏曲批评中的一个关键词
梁晓萍
(山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山西 临汾041004)
情:明中叶后中国古典戏曲批评中的一个关键词
梁晓萍
(山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山西 临汾041004)
“情”是中国古典戏曲批评及戏曲美学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词。情为欲嗜之别称,乃人人皆有的一种心理体验,与生俱来的情质朴、单纯,不假修饰,这种对情之本源的认识直接影响到中国古代的审美趣味和审美判断,以及后世关于情本、性情、情景、情理、意境等诸种哲学、文学的理性思索。从情之内蕴的角度看,魏晋时的“诗缘情”理论摆脱了汉代以来儒家政教和功利思想的束缚,使“情”渐次成为遴选和批评文学的重要杠杆。中国古典戏曲批评非常重视“情”,尤至明中叶后,以汤显祖为代表的诸多创作者、批评者纷纷在序、跋、书信、曲品等文章中,以“情”为出发点,表达自己对于戏曲及人生的看法,呈现出一种众士以情品曲的整体态势。真实性、唯一性、可感性是曲论之“情”的基本特征,情的传达建立在对情与景、情与事以及情与理等关系的理解与处理上。
情;中国古典戏曲;批评;汤显祖;孟称舜
情,古义“人之阴气有欲者”[1]531,即古人认为情乃由欲而生之阴气,内传欲流,通于五脏,是人类社会特有的最为复杂、最为壮观、最扣人心弦、最动人心魄的一种心理体验,元好问“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的诗句,道出了无数痴男怨女的滚滚世情。“情”又是中国古代文论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词,在中国古典戏曲批评及戏曲美学中表现得非常突出。
早在先秦,哲人们便开始论情,孟子论性善,言必称尧、舜,已关涉情感。此时关于“情”的思考已非常深刻,如《礼记·礼运》曰:“故圣人作则,必以天地为本,以阴阳为端,以四时为柄,以日星为纪……人情以为田,四灵以为畜。”“以天地为本,故物可举也。以阴阳为端,故情可睹也。以四时为柄,故事可劝也。”“人情以为田,故人以为奥也。四灵以为畜,故饮食有由也。”“何谓四灵?麟、凤、龟、龙,谓之四灵。故龙以为畜,故鱼鲔不淰;凤以为畜,故鸟不獝;麟以为畜,故兽不狘;龟以为畜,故人情不失。”[2]1424-1425这几段文字固然不仅仅阐释“情”,却在天人关系的探究中点出了“情”之重要性。那么,“情”是源何而生的?为什么“情”之失会让人紧张?作为一种审美范畴,它与人的生存之间有何关系?以“情”为文的文论思想经历了怎样的变化?
一、“情”之本源
情,本义为欲念,指人皆有的喜、怒、哀、乐、惧等七情六欲,具有可感、动人的外向性特征。战国的楚墓竹简中有大量关于“情”的言论,如“诗亡离志,乐亡离情,文亡离言”“喜斯慆,慆斯奋,奋斯咏”等,昭示出古人对于人之欲望的认可与肯定。《礼记·礼运》较早对“情”作出心理学意义上的界定:“何谓人情?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弗学而能。”[2]1422人情就是喜、怒、哀、惧、爱、恶、欲等七种心情,是人与生俱来的本能,不需要专门学习便可获得。这里特别强调“情”的生理本能性,意味着只要是具有正常人格因素和价值判断的人都具有情,因为它与生命同源同生,自然而然。《吕氏春秋·情欲》曰:“欲有情,情有节。圣人修节以止欲,故不过行其情也。故耳之欲五
声,目之欲五色,口之欲五味,情也。此三者,贵贱愚智贤不肖欲之若一,虽神农、黄帝其与桀、纣同。”[3]84人们对五声、五色、五味的欲求本身就是情,这里实际上强调的就是情的天生特性,认为情与人的生命活动密不可分,即只要有人的生命活动,就会有“情”,这就从生理层面肯定了情的必然性。而且还指出,此“情”的存在,与人后天发展的品性以及身份无关,并非智者与高贵之人才有情,这又从社会的层面肯定了情的普遍性。《说文解字》释情曰:“情,人之阴气有欲者。”[1]531以气说情,将人的情推到了生命的本源处。情既然是天生的,那么就不需要后天学习,倘若凭借后天学习而得情,那便是从染缸里得到的情,是虚情假情,是矫揉造作的情,便是老庄所竭力鞭挞的情。
不过,古人对情的认识还不仅如此,恰如柏拉图认识到文艺可以煸动人情而使社会不紊,因而担忧,并将文艺驱逐出“理想国”一样,中国古人也认识到“情”之欲有恶的一面,需要以“礼”加以规约。《礼记·礼运》曰:“故圣王修义之柄、礼之序,以治人情。故人情者,圣王之田也。修礼以耕之,陈义以种之,讲学以耨之,本仁以聚之,播乐以安之。”[2]1426为什么要对“情”“耕之”“耨之”“聚之”“安之”呢?因为“情”如田地,不以“礼”加以管理与规约就会滋蔓、张扬,就会膨胀、诱惑,这个比喻实际上暗示出情之欲念“恶”的一面——情有贪婪的属性,情欲过分,冲动的内心就难以自持,就会酿成情之苦果。《管子·权修》也强调民情需要加以辨别、审察并谨慎引导,否则民便不可得。董仲舒《春秋繁露》如此论述:“天令之谓命,命非圣人不行;质朴之谓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谓情,情非度制不节。是故王者上谨于承天意,以顺命也;下务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别上下之序,以防欲也;修此三者,而大本举矣。”[4]600董仲舒的观点标识出汉代人对于“情”乃人欲以及对情需要制约的普遍认识。
情由欲生,情本为欲的观点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意义:首先,它昭示出“情”乃人人皆有的一种心理体验,是人类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种属性与元素,与生俱来,弗学而能;其次,与生俱来的情质朴、单纯,不假修饰,天然自然,启示人们在进行情感表达时亦要力争做到保持真情,收起伪饰;第三,这种对情之本源的认识直接影响到中国古代的审美趣味和审美认识,并直接影响到后世关于情本、性情、情景、情理、意境等诸种哲学、文学的理性思考。
中国诗学理论对于诗歌抒情性本质的认识有一个自觉化的过程,最初的提法为“诗言志”。《尚书·舜典》记舜的话说:“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5]130“诗言志”被朱自清称为中国诗论的“开山纲领”[6]137,并且,他从赋诗言志、献诗陈志、教诗明志、作诗言志四个方面对“诗言志”作了详尽的考察。“诗言志”中“志”侧重指志向、抱负、思想,兼有个人情感的意味。战国中期以后,由于对诗歌抒情特点的重视以及学术上百家争鸣现象的出现,“志”的含义逐渐扩大,情的成分不断增加,甚至以政教为特点的儒家著作中也出现了“诗言志”的思想。《论语》中就有两次“言志”的记载:
颜渊、季路侍。子曰:“盍各言尔志?”子路曰:“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公冶长》)[7]52
(曾晳)鼓瑟希,铿尔,舍瑟而作。对曰:“异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伤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先进》)[7]119
子路的志向是与朋友分享车马、轻裘这些物质财富,这是对纯洁友情的珍重;曾晳的志向是暮春时分,携三五知己,“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追求的是一种自由的人生境界。这两种志向都舍弃了身外之物,舍弃了功利目的性,具有着浓郁的抒情特色。
汉代,受《楚辞》创作实绩和文学、音乐理论的影响,以《诗经》为主要观照对象而形成的“诗言志”理论发展成为对象更加宽泛的“情志合一”的诗歌本体论。《毛诗序》曰:“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2]1529“志”侧重指被“独尊”的儒术的文化诉求,而“情”则体现了在这种专制统治下艰难生存的个体的精神寄托。这里强调了“情”之于“志”与“诗”的重要性,凸显了“情”在诗歌中的地位与作用。受“情志合一”理论的影响,汉代的诗歌批评也突出“情”的价值。《汉书·艺文志》曰:(汉乐府)“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评论《诗经》曰:“故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8]1708汉代诗学理论对于诗歌抒情性的关注尽管常常受到儒家政教观念的节制,要求“发乎情,止乎礼义”,但发自遭遇到沉重专制压力的士人内心的“言情”思想不
断地对之进行反拨,诗学理论正沿着“情”的轨道自觉而悄然地前行。
魏晋时期,人的自觉带动了文学的自觉以及诗学观念的自觉,“情志合一”理论中“志”的束缚渐被剥离,终于,西晋文论家陆机在《文赋》中提出了“诗缘情”理论:“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9]147。这一观点不同于“诗言志”,也有别于“情志合一”,此“情”不是因人伦之废、刑政之苛而伤而哀,不是因礼义而止而藏,不是用“诗”去言的“在心之志”,而是“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因四季的变化生发出不同的情感,流溢出不同的感叹。心中之情因感于自然之物而自然流露,这种崭新的诗学观念从审美的高度来认识诗歌的本质,是对传统文学观念的一种挑战,它标志着人们对诗歌的认识摆脱了群体意志的束缚和挤压,而走向个性情感的抒发和个体生命意识的独特表达。
强调诗歌审美特性的“诗缘情”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魏晋以后中国诗学的整体格局,改变了人们对文学特征的认识。首先表现在它影响了文学批评的标准,如萧统选文的标准为“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综缉辞采”“错比文华”[10]2;刘勰《文心雕龙·情采》云:“文采所以饰言,而辩丽本于情性”[11]346。其次,“诗缘情”思想还改变了人们对传统理论术语,譬如“兴”的看法。汉人认为“兴”的根源在于人们心中的政治教化、道德伦理等观念,诗人据此而寻求外在的事物以暗示比喻,批评时则需依“喻”而推观念,这样不明晓诗人何以如此作文,便主观辄事探求的做法,其结果难免有穿凿之弊。“诗缘情”理论却告知人们,“兴”由感而生发,“情”才是“兴”的真正根源,批评当然也应从“情”出发,分析“兴”之意味。
陆机之后,“诗缘情”理论为不少批评者所重视,并进行了继承与阐释。如钟嵘《诗品序》开篇云:“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照烛三才,辉丽万有,灵祗待之以致飨,幽微藉之以昭告。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12]233钟嵘认为,物由气动,人由物感,情便因物而生,情动便为诗,情是诗歌的本源。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云:“文章者,盖情性之风标,神明之律吕也。蕴思含毫,游心内运;放言落纸,气韵天成。莫不禀以生灵,迁乎爱嗜,机见殊门,赏悟纷杂。”[13]340萧氏把文章看作人的情性的风标,力主性情是文章之本,认为其“迁乎爱嗜”,关乎趣味,因此反对雍容典雅,却缺少真情的诗歌。唐代诗学对“诗缘情”理论表现出欣赏与接受的态度,王维、李白、杜甫、白居易等大家都曾发表过自己的见解,如杜甫曰:“缘情慰飘荡”[14]273,白居易曰:“寓兴、放言、缘情、绮语者,亦往往有之”[15]6909,并以创作实绩践行了“诗缘情”理论。宋代诗学批评受理学的影响,整体出现了“主理”的倾向,这一倾向使宋代诗学批评在整体上偏离了“情”的轨道,幸而还有一些微弱的声音存在。
总之,“诗缘情”理论摆脱了汉代以来儒家政治教化和功利思想的束缚,抖落了经学礼义的沉重包袱,看到了“情”在文学中的动力作用,使“情”这一审美特质成为遴选和批评诗歌的重要杠杆,也为古典时期曲学批评中“情”的标尺的确立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二、汤氏论曲:曲总为情
中国古典戏曲批评非常重视“情”,尤至明中叶及以后,以汤显祖为代表的许多创作者、批评者,纷纷在序、跋、书信、曲品等文章中,以“情”为武器,表达自己对于文艺及人生的看法。明中叶以前,尽管剧作家早已接续中国古代的言情传统,创作出如《张协状元》《错立身》《西厢记》等作品深刻反映当时的婚姻爱情观,并传递出“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的爱情理想,然而,由于当时还少有人从理论高度对创作实绩进行及时的总结与引导,因此,戏曲批评中的“情”这一审美理想尚处于隐性阶段。到明中叶及其后,一大批文人站在“以理格情”的审美价值的对立面,自觉地推行以情为美的戏曲观念,并将“情”视为戏曲之根本。在这一方面,汤显祖无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代表人物。
汤显祖(1550~1616年),字义仍,号海若,又号若士,别署清远道人,临川(今属江西)人。汤氏一生,用吕天成语概括乃“绝代奇才,冠工博学。周旋狂社,坎坷宦途”[16]213。汤显祖以戏曲创作名重一时,以“临川四梦”闻名于世,是天才的戏剧家;他又是杰出的思想家和批评家,他的戏曲批评观散见于一些题词、序文、信笺及评点著作中。
汤显祖的戏曲批评观,一言以蔽之:尚情。首先需要阐明的是,对于汤显祖笔下的“情”有不同的理解:有人认为指“伟大的思想”;有人认为指“一般人情”;也有人认为指“现实生活”;还有人认为其论著中反复强调的“情”,是一个复杂的概念,有才情、人
情、情志、情趣、情思、激情,也有道情、文情、交情等。①代表人物与作品分别为侯外庐《论汤显祖剧用四种》;游国恩等主编《中国文学史》;周贻白《中国戏曲发展史纲要》;叶长海《中国戏剧学史稿》。见叶长海《中国戏剧学史稿》,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5年,第141页。对于其中关涉日常生活的“情”,不是本文探讨的范畴,本文重在关注理论意义上的“情”。
宏观地讲,“情”泛指人的主观思想,结合中国传统诗学理论、汤显祖所处时代的哲学思潮以及汤氏本人的人格气质,汤氏所讲的“情”当指与无意识相关的冲动、欲望和有意识的志向、愿望等的融合,而这种“情”无论有意识还是无意识,都排除世俗的功利观,而与天然的审美联系在一起。
人生而有情。思欢怒愁,感于幽微,流乎啸歌,形诸动摇。或一往而尽,或积日不能自休。盖自凤凰鸟兽以至巴夷渝鬼,无不能舞能歌,以灵机自相转活,而况吾人。[17]608
人生而有“思欢怒愁”等情,情是人自然而然的一种本真存在,人的情由外物所感而生发出来,一旦生发,便有时“一往而尽”,有时“积日不能自休”,于是或歌或舞,即人的“啸歌”“动摇”等,都因“情”而生。凤凰鸟兽、巴夷渝鬼亦然,感于情而歌而舞,以“灵机”互相传递情愫。这种“情”不知所起,自人生堕地便有之,所谓“自然发于情性”,这是一种超验的情感,它缘自先天,发乎自我,无缘无故,自缘自在,是一股至深至诚、可以冲破一切人为阻碍的力量。杜丽娘和柳梦梅之间的情爱便是这种至情,他们的情超越了肉体之形骸,是一种深刻的自然本性之吸引,这种情,从某种意义上讲,已经超越了简单的男情女爱之边界,跃升为一种更为普遍的人类之爱。
人生而有“情”,有“情”之人构成了一个有“情”之世。汤显祖言:“世总为情,情生诗歌,而行于神。天下之声音笑貌大小生死,不出乎是。”[18]1050。汤显祖以“情”作为批评戏曲的核心标尺,如他在《三先生合评元本西厢记·叙》中说:
兹崔张一传,微之造业于前,实甫、汉卿续业于后,人靡不信其事为实事。余读之,随评之,人信亦信,茫不解其事之有无。好事者,辄以旦暮不能自必之语,直欲公行海内,冤哉!毒哉!陷余以无间罪狱也。嗟乎!事之所无,安知非情之所有?情之所有,又安知非事之所有?[19]655
人们读《西厢》,皆信其事为实事,然“信亦信,茫不解其事之有无”。这种求证的态度令人可敬,然在汤显祖看来,实无必要,因为“事”因“情”生,“事”即“情”之演义,“情”才是艺术的生命,有此“情”何必疑此“事”?
“情”是汤氏品戏的出发点与终结点,他甚至将“志”亦巧妙地转义为“情”,然后从“情”出发批评戏曲:
余于声律之道,瞠乎未入其室也。《书》曰:“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志也者,情也。先民所谓“发乎情,止乎礼义者”是也。嗟乎,万物之情各有其志。董以董之情而索崔、张之情于花月徘徊之间,余亦以余之情而索董之情于笔墨烟波之际。董之发乎情也,铿金戛石,可以如抗而如坠;余之发乎情,宴酣啸傲,可以以翱而以翔。然则余于定律和声处,虽于古人未之逮焉,而至如《书》之所称为言为永者,殆庶几其近之矣。[20]573
汤显祖在这里表达了四层意思:一,自谦对于声律不如对曲辞研究得更为深入,故在声律方面,“于古人未之逮”,而在“《书》之所称为言为永”方面,则“庶几其近之矣”。二,从源头上梳理“情”的存在价值,并将“志”引入“情”的轨道:“志”发乎“情”,“志”即为“情”。并推而至于“万物各有其情”。三,肯定了董氏《西厢》是有情之作品。四,表明自己以“情”为批评标准。董以董之情于花月徘徊之间索崔、张之情,而汤以汤之情于笔墨烟波之际索董之情,这样,“情”成了作者与读者之间的桥梁,无情之人则无法批评有情之作品。
以“情”为批评标准,汤显祖肯定《红梅记》中为裴生风采所吸引,竟不避权相贾似道的慧娘之胆识与义无反顾。汤氏认为该女子很有“胆量”,而其“胆量”乃因“情”而生发,故汤氏之喝彩也是为慧娘之“情”而脱口。以“情”为批评标准,汤显祖赞叹《西楼记》中主人公于叔夜弃功名等身外之物如敝履的执著之情。以“情”为批评标准,汤显祖讴歌人间之异梦。《异梦记》第七出《窥看》出批曰:“谁曰梦无根,此折是也,惟此处种下奇情,才有异梦。”[21]80由此可见,汤显祖不仅以人所共知的创作解释了戏曲之“情”,还从理论的角度将“情”界定为戏曲批评的首要标准。
汤显祖还对情与理的关系作出独特的诠释:
天下女子有情宁有如杜丽娘者乎。梦其人即病,病即弥连,至手画形容传于世而后死。死三年矣,复能溟漠中求得其所梦者而生。如丽娘
者,乃可谓之有情人耳。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梦中之情,何必非真。天下岂少梦中之人耶。必因荐枕而成亲,待挂冠而为密者,皆形骸之论也。……嗟夫,人世之事,非人世所可尽。自非通人,恒以理相格耳。第云理之所必无,安知情之所必有耶。[22]1093
这是创作宗旨宣言,许多学者都已从这个角度进行了有益的探索①如叶长海指出:“理”者,指客观事理;“情”者,指主观情思。也就是说,在创作中是允许按作者的意愿及情感的逻辑来结构戏剧的,而不能光以事物“常理”来相“格”;因为“人世之事,非人世所可尽”,在需要的时候,是可以上天下地、出生入死的。因而可以说,汤显祖关于“情”与“理”的这一段话,实际上是他对艺术创作规律的一种认识,我们还可以理解为这是他关于浪漫主义创作原则的宣言。叶长海《中国戏剧学史稿》,第143页。,同时也是批评标准宣言。按照接受美学的理解,每一位作家都有预设的能够把他(她)的作品加以具体化的隐含读者,这种隐含读者与作家的创作动机、文本内涵、所选材料等紧密相连,他们最能与文本形成交流,最能贴近作家的灵魂。所以作家对他们的期望也就是作家批评观的体现,而《牡丹亭记·题词》中就有汤显祖心目中隐含读者的存在。汤氏指出:杜丽娘乃有情之人,且为至情之人,一往情深,故而她可以死而复生,这件事显然不合常“理”,以“理”求之,便会顿足失望;但它合“情”,以“情”解之,则豁然开朗。当“理”与“情”相撞时,“情”是“理”的最高指挥,“理”应当服从于“情”的调配,而不是与之相悖,文学批评中的这种“屈就人情”并非“理”的失败,而是“理”最好的选择。可见,隐含读者一定是位有情之人,解情之人,以情而品文本之人。
汤显祖尚情的批评观念在别处也有显现。《沈氏弋说·序》说:
今昔异时,行于其时者三:理尔,势尔,情尔。以此乘天下之吉凶,决万物之成毁。作者以效其为,而言者以立其辨,皆是物也。事固有理至而势违,势合而情反,情在而理亡,故虽自古名世建立,常有精微要眇不可告语人者。史氏虽材,常随其通博奇诡之趣,言所欲言,是故记而不伦,论而少衷。何也?当其时,三者不获并露而周施,况后时而言,溢此遗彼,固然矣。嗟夫!是非者理也,重轻者势也,爱恶者情也。三者无穷,言亦无穷。[23]1841
在汤显祖看来,世界由理、势、情三者构成,缺一不可,然而在他所处的时代,缺乏的不是理、势,而是情。礼法与权势使得整个社会乌烟瘴气,人心惶惶,面对动辄得咎、自由难觅的现实境遇,他义无反顾地为“情”呐喊,期冀一个洋溢着情的世界的出现。这里,汤显祖的情已脱开了一般意义上的男女之情,也不仅仅拥有个性解放的内涵,他已经将“情”的范围扩展至宇宙人生,使其具有了生生不息的宇宙人生精神的内蕴。具体到与“言”相关的意识形态,汤氏认为,“言”关涉是非、重轻、爱恶,分别为哲学家、政治家和文艺家之言。其中,“情”是文艺家发言之核心,那么,要想使这个理、势强劲的社会变得整饬有序,文学则务必要举起“情”的大旗,以“情”为重要的衡量标尺,这便将汤氏批评的“尚情”主张标举而出。
陈继儒于其《牡丹亭题词》一文中,记录了有关汤显祖的一则趣事,其中,在与张新建相国的对话中,汤显祖明确表达了自己的尚情的审美主张和人生志向:“师讲性,某讲情”[24]1545。何谓“性”?“性”即理学家所言之“理”,它强调一种先验的支配规律,认为自然界与人世间存在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体精神。这种观点从尊重自然这一层面来讲是有积极意义的,尤其在今天看来,“胆大妄为”的人需要有一种“崇敬”自然规律的“敬畏”意识对其进行有效规约。然而关键在于,明代的理学家将之当作人世间的普遍规律,并将之运用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构建中,使世间的尊卑等级以及社会秩序成为一种不可颠覆的客观存在,认为人要认识并自觉遵从这种万古不移的等级与秩序,具体到当时,即要人们严格并自觉遵守三纲五常等封建教条,这就严重束缚了人之为人的本真性,泯灭了人的自由天性。正是在此基础上,汤显祖等尚“情”的主张才具有不可忽视的时代意义。
与尚“理”思想比较,汤显祖选择了尚“情”,在“情”与“法”二者中,汤氏又选择什么呢?
王骥德认为“临川汤奉常之曲,当置‘法’字无论,尽是案头异书”[25]165,吕天成借王骥德语指出临川近狂,“妙词情而越词检”[16]212。“异书”“妙词情”是越“法”的结果,倘若斤斤守法,不敢越“法”一步,让“情”倦缩于“法”规定的圆圈内前思后想,则“法”必定吞噬掉“情”,“情”则淹没于“法”。当然,这里越法是在懂法和遵守一般法基础之上的灵机之变,绝非
不懂法却蛮干的外行行为。汤显祖在“情”与“法”关系方面极为辩证的批评原则可以从别处觅得踪影:
文字,起伏离合断续而已。极其变,自熟而自知之。父不能得其子也。虽然,尽于法与机耳。法若止而机若行。……故法圣而机神。此予之所迁延流离而不能得者也。而以教吾子,此岂不谓之大愚也哉。[26]1100
总之各效其品之所异,无失于法之所同耳已。况吾江西固名理地也。故真有才者,原理以定常,适法以尽变。常不定不可以定品,变不尽不可以尽才。才不可强而致也。品不可功力而求。子言之,吾思中行而不可得,则必狂狷者矣。语之于文,狷者精约严厉,好正务洁。持斤捉引,不失绳墨。士则雅焉。然予所喜,乃多进取者。……因以裁其狂斐之致,无诡于型,无羡于幅,峨峨然,沨沨然。[27]1077
联系汤氏教季子开远之文与《揽秀楼序文》,汤氏的主张自见。文字应当尽于法,尽于机,法是文之绳墨,机为文之人情,法常止,而机常行,最好的结果是止于当止,行于当行。真正有才者,能做到“原理以定常,适法以尽变”,这样既可定其品,又可尽其才,两全其美。可见,汤氏既重于“法”,也重于“情”。然而“情”与“法”常常难以两全,汤氏便遭遇到这样的挑剔。当晚辈向其倾诉此苦时,汤氏立场鲜明地指出:狷者尽管能做到持斤捉引,不失绳墨,但他仍然喜欢“进取”者,喜欢敢于不为“法”所拘而因“情”打破常规的文章。《萧伯玉制义题词》中,汤氏对那些误认为委弃绳墨者是窃取名声的说法进行了批判。曰:
予少病此语。必若所云,张旭之颠,李白之狂,亦谓不如此名不可猝成耶。第曰怪怪奇奇,不可时施,是则然耳。[28]1100
唐代以颠狂为美,认为不颠不狂,其名不彰,后世之人皆奉其言,并以此来衡量士人文辞的好坏。但有人曲解其意,认为倘有委弃绳墨,纵横心意,力成一家之言者,便不过为“沸名”而来,似乎打破“法”之人全都为了名声。汤显祖不同意这种偷换概念的看法,他赞赏“极尽剧法之变”的《红梅记》,贬抑《焚香记》中及登程、招婿、传报王魁凶信时“颇类常套”的做法,①“境界纡迴宛转,绝处逢生,极尽剧场之变。”(《红梅记总评》)“独金垒换书,及登程,及招婿,及传报王魁凶信,颇类常套。”(《焚香记总评》)徐朔方笺校《汤显祖诗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1085页。并进一步提出“怪怪奇奇,不可时施”②翠娱阁本评云:“奇怪不可常,而寻常寓奇怪。此乃真奇奇怪怪。文开合处,殊有古意。”又评“怪怪奇奇,不可时施”句云:“时施,亦不奇怪矣。”徐朔方笺校《汤显祖诗文集》,第1101页。的主张。其并非置“法”于不顾,相反,他认为“法”是前人总结得出的关于词、句、曲、律、场等多方面的经验,它可以使戏曲更能贴近人情,更易打动观众,因此,守法是越法之前提;鉴于人情喜变之需要,固守常套会让人生闷;不顾及法而强行越法,则会适得其反,因为越法的前提是为“情”,而非为求变之“名”。
总之,汤显祖的戏曲批评标准侧重对于情感的观照,这种情是一种普遍的“人情”,不是仅指爱情。汤显祖“尚情”的批评观是他在与“崇理”“尚法”等思想的比较中生成的。需要指出的是,汤显祖尚情,但他并不排斥理与法,反而要求戏曲要力争原理、合法,只是强调当情与理、情与法难以兼融时,一定要以“情”为第一要务。因为他深知:传“情”是戏曲的责任,“情”是戏曲之灵魂,失却灵魂即失却一切。
三、以情论曲岂独若士一人
在戏曲批评方面坚持以“情”为标准的不止若士一人,若士前后,徐渭、潘之恒、冯梦龙、孟称舜、袁于令等都以情论曲。
徐渭在戏曲批评方面主张“宜真”,要求真挚感人。这里,“真”并非超越“情”之术语,恰恰是“情”的别种称呼。在批评《琵琶记》时,徐渭慧眼独到:
或言:“《琵琶记》高处在《庆寿》、《成婚》、《弹琴》、《赏月》诸大套。”此犹有规模可寻。惟《食糠》、《尝药》、《筑坟》、《写真》诸作,从人心流出,严沧浪言“水中之月,空中之影”,最不可到。[29]243
对《庆寿》《成婚》《弹琴》《赏月》等被许多文人赞为高雅的曲子不屑一顾,却对《食糠》《尝药》《筑坟》《写真》等很少被人提及的曲子大加赞赏,其原因就是《食糠》等诸作“从人心流出”。“从人心流出”即真情流露,不虚情,不矫情,一任情感自然倾泻。这里,徐渭取舍的标准是“真情”,而汤显祖即继承了这一主张。
潘之恒有几十年的戏曲鉴赏经验,他从《牡丹亭》等剧本的艺术成就中得到启示,总结出戏曲的根本在于传“情”,并以此为标准进行戏曲批评的实践。承继汤显祖的戏曲观,潘之恒对《牡丹亭》进行了恰切的发挥性评价:
夫情所之,不知其所始,不知其所终,不知
其所离,不知其所合。在若有若无、若远若近、若存若亡之间,其斯为情之所必至,而不知其所以然;不知其所以然,而后情有所不可尽,而死生生死之无足怪也。[30]185
《牡丹亭》中“生而死”“死而复生”的情节并不奇怪,因为它缘于始终、离合、存亡皆迷离恍惚的“情”。“情”是这种安排的导演,以“情”出发欣赏此曲,一切都可迎刃而解,那些不解此曲者,正是因为不能站在“情”的立场。
潘之恒指出,《琵琶》《拜月》《荆钗》《西厢》等成功的秘诀都在于它们是有“情”之作:“推本所自,《琵琶》之为思也,《拜月》之为错也,《荆钗》之为亡也,《西厢》之为梦也,皆生于情。”[31]13而《牡丹亭》同样因为把“情”发挥至极致而令人赞叹。
潘之恒不仅自己以情品曲,还要求演员——这一独特的鉴赏与创作群体也以情品曲,他强调唯“有情人”才能贴近作品,理解戏曲:“能痴者而后能情,能情者而后能写情。”而且还指导演员品味杜、柳之“情”的同中之异:“杜之情痴而幻,柳之情痴而荡;一以梦为真,一以生为真。”[30]185
冯梦龙曾改编汤显祖、张凤翼、李玉等人的传奇多种,定名为《墨憨斋定本传奇》,尚情是其编选的重要理论依据。在《太霞新奏·序》中,冯梦龙说:
文之善达性情者,无如诗,三百篇之可以兴人者,唯其发于中情,自然而然故也。自唐人用以取士,而诗入于套;六朝用以见才,而诗入于艰;宋人用以讲学,而诗入于腐;而从来性情之郁,不得不变而之词曲。……今日之曲,又将为昔日之诗。词肤调乱,而不足以达人之性情,势必再变而之《粉红莲》、《打枣竿》矣。[32]7
冯氏认为,诗三百篇因为发于情,善达情,自然而然,故而成为后世之范。然自唐人以诗取士,诗便渗入了真情以外的功名,于是“入于套”;又六朝以诗见才,故“诗入于艰”;又宋人以诗讲学,故“诗入于腐”。人之情因套语、艰语、腐语而受到阻滞,诗不得已而变为词曲。相反,民间文学《粉红莲》《打枣竿》等,正是因为传达“真情”才具备了替代文人雅曲的实力。由此可见,在冯氏看来,戏曲是人情表达之选择的结果,那么,“达情”便成为戏曲之为戏曲的根本,“情”也便成为戏曲的核心。既而,“主情”便成为冯梦龙戏曲批评的标准之一。
冯梦龙评《洒雪堂》曰:
是记穷极男女生死离合之情,词复婉丽可歌,较《牡丹亭》、《楚江情》未必远逊,而哀惨动人,更似过之。若当场更得真正情人写出生面,定令四座泣数行下。[20]1349
西陵梅孝己《洒雪堂》剧写贾娉娉借尸还魂,与魏鹏结为夫妇的故事,内容极似《牡丹亭》。有人曾戏讽其“活剥汤义仍,生吞《牡丹亭》”。冯梦龙则以“情”为据,认为此剧将男女离合之情写得哀惨动人,与《牡丹亭》比未必远逊。冯梦龙评《风流梦》(即改编了的《牡丹亭》)时,借用王季重之语充分肯定了《牡丹亭》剧对于“真情”的揭示:
若士先生千古逸才,所著“四梦”,《牡丹亭》最胜。王季重叙云:“笑者真笑,笑即有声;啼者真啼,啼即有泪;叹者真叹,叹即有气。丽娘之妖,梦梅之痴,老夫人之软,杜安抚之古执,陈最良之腐,春香之贼牢,无不从肋节窍髓,以探其七情生动之微。”此数语直为本传点睛。[20]1235
冯氏认为,《牡丹亭》中,每一个形象都因其真情流露而生动非凡。
凌濛初同样主张以情品曲,他反对华靡的无“情”之语,认为靡词尽管外表好看,如绣阁罗纬、铜壶银箭、黄莺紫燕、浪蝶狂蜂之类,但千篇一律;使事、隐语,意如商谜,但令人困惑;它们最大的不足就是埋没不露己,真情尽失,因此被凌濛初责为难解之“锢疾”“道之大劫”[33]253。
晚明戏曲作家和戏曲理论家孟称舜,不仅因其创作实践被称为“传情家第一手”①孟称舜《二胥记》第一出《标目》,巽倩龙友氏眉批:“昔称马东黎之词如风鸣朝阳,乔梦符之词如神鳌鼓浪,此曲可为兼之曩见,其夗央土冢词酸梦幽艳,风流蕴藉,为传情家第一手。此又何苍凉雄壮也,乃知情至之人可以为义夫节婿,即可为忠臣孝子。”《古本戏曲丛刊三集》,北京:文学古籍刊行社,1957年,第1-2页。,还在戏曲理论与批评方面多次提到“情”的价值与意义,并以“情”作为衡量戏曲的重要砝码。与汤显祖一样,孟称舜亦认为万物有情:“世间不特有知识的,俱有性情,即花草之物,亦非无情。可不道天若有情天亦老,月如无恨月长圆。”他认为这种情具有永恒性:“投至得山枯与海竭,看将来恨绵绵只有情难绝。”并且,他看到了戏曲传情的本质及其渊源:“诗变而为词,词变而为曲,词者诗之余而曲之祖也。……盖词与诗、曲,体格虽异,而同本于作者之情。……(张柳之词与苏辛之词)两家各有其美,亦各有其病。然达其情而不以词掩,
则皆填词者之所宗,不可以优劣言也。”[34]555词为曲宗,谈词即是谈曲。这里,孟称舜暗示:戏曲文学与古典诗学一脉相承,形虽变化,然传情之主旨未变,且只要曲能达情,即为好曲,这就把历史与现在、作者与读者关联在一起,很好地解释了“曲贵传情”的历史沿革与主体需求,为主情的批评观找寻到了有力的依据。
孟称舜批评郑光祖的《倩女离魂》楔子【赏花时】一曲曰:“酸楚哀怨,令人断肠。昔时《西厢记》,近日《牡丹亭》,皆为传情绝调。”[35]573孟氏称赞《倩女离魂》能以(酸楚哀怨之)情动人,与《西厢》《牡丹》一样,堪为传情绝调。这里,孟称舜的批评标准非常明晰,即以“情”为审美标准。从“情”的角度看,《西厢》《牡丹》均传达了人间真情,是真情使其具有了穿越时空的魅力;以此论之,《倩女离魂》也因其传达了真情而进入极品的行列。
孟称舜主情的批评观从其编选的《古今名剧合选》中处处可以见到。实际上,编选的“选”必定有据可依,取舍一定有标准可凭。在《古今名剧合选·序》中,孟称舜分别评价了沈璟“专尚谐律”和汤显祖“专尚工词”的弊病,指出二者皆有偏见;并在肯定汤显祖“工词而不失才人之胜”的才情及其“世总关情”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选择标准:“予此选去取颇严,然以词足达情者为最,而协律者次之。”[36]558孟称舜认为文词重于音律,而文词又以是否达情为标准,即情是词的核心,无情则无真正之词,不传情则非真正之曲。这种以是否传情、能否达情为据的戏曲评选标准,是孟称舜戏曲批评的基本准则。
孟称舜评吴昌龄《二郎收猪八戒》第三折裴女的一段唱词《滚绣球》曰:“凄清痛绝”[37]14,认为这一段曲将裴女的思念与忧愁都表现出来了,为真情之曲。评宫天挺《范张鸡黍》第二折【隔尾】曰:“似俱有感而言”[38]18;“通篇如听薤露歌,使人悲涕不禁”[38]26。评《谇范叔》第一折【油葫芦】曰:“是作者自道其胸臆。”[39]6评马致远《青衫泪》第二折【尾煞】曰:“种情无限”[40]16;评其第四折【随煞】“再不去万里天涯你这般愁,鬓萧萧将白发少年心撇罢。再不去趁春风攀折凤城花”曰:“想作者亦自有情”[40]32。评白朴《墙头马上》第二折【煞尾】曰:“相如傲世,文君知人,此是作者回护处,亦是聪慧女子本情”[41]13,认为私奔的李千金具有人之本情。评纪均祥《赵氏孤儿》曰:“此是千古最痛最快之事,应有一篇极痛快文发之。读此觉太史公传犹为寂寥,非大作手不易办也。”[42]1-2从“情”的角度看,即使太史公传都未必能比得上《赵氏孤儿》,这种激赏之语尽管有些夸饰,但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孟称舜对于“情”的崇尚。
孟称舜在《贞文记》题词中说:“男女相感,俱出于情。情似非正也,而予谓天下之贞女,必天下之情女者何?不以贫富移,不以妍丑夺,从一而终,之死不二,非天下之至种情者而能之乎?然则有见才而悦,慕色而亡者,其安足以言情哉?”[43]562摒弃掉其中出于男权思想而对女子人为设置的枷锁不论,孟称舜对于真情的呼唤与肯定以宣言的方式再一次显示了其主情的批评观。
明末袁于令继承了以情品曲的传统,大胆地提出“世界只一‘情’”的说法,对明代“言情”说进行了总结。《焚香记·序》中,袁于令指出:
剧场即一世界,世界只一“情”。人以剧场假而情真,不知当场者有情人也,顾曲者尤属有情人也;即从旁之堵墙而观听者,若童子,若瞽叟,若村媪,无非有情人也。倘演者不真,则观者精神不动;然作者不真,则演者之精神亦不灵。[44]82
袁于令认为,作者应当“真”,要写真情,因为“世界只一‘情’”,剧场之情即从世界之情而来;更重要的是,当场者均为有情人,顾曲者都属有情人,他们会用情观戏曲,用情品曲。这样,袁于令以演员、作家和观众为三位一体,以剧场为凝结之所,着重从审美接受者的角度强调了戏曲批评的标准——主情。
明中叶以来的曲家多尚“情”,以“情”论曲,那么,此“情”特质如何?又如何对其进行有效传达?
四、情之特质与有效传达
真实是曲“情”之最为根本的特质。中国古人历来崇尚质朴、本色的自然之情,认为这种情感是最为基本、最为原始、最为粗糙却也是最为优秀、最为感人的一种品质。《礼记·表记》指出:“子曰:‘君子不以色亲人。情疏而貌亲,在小人则穿窬之盗也与?’子曰:‘情欲信,辞欲巧。’”[45]822强调人的情感应当是以信实为特征,愈真诚,愈实在,愈是一种真实的表达,而那种貌亲而情疏的虚伪之情,显然是小人之行为,与凿壁偷窃毫无二致。老庄更是反对矫饰之情,《庄子·应帝王》曰:“泰氏,其卧徐徐,其觉于于。一以己为马,一以己为牛;其知情信,其德甚真,而未始入于非人。”[46]211伏羲氏睡卧的时候宽缓安闲,觉醒的时
候悠游自得;他听任有的人把自己看作马与牛;他的才思真实无伪,他的德行纯真可信,而且从不曾涉入物我两分的困境,将自己变作“非人”,此即为真情。
明中叶以来的诸多戏曲批评理论家,都十分重视情感的真实性。《倩女离魂》第一折【混江龙】如下:
(正旦)断人肠正是这莫秋天道,尽收拾心事上眉梢。镜台儿何曾揽照,绣针儿不待拈着,常恨夜坐窗前烛影昏。一任晚妆楼上月儿高。这鸳帏幼女共蜗舍书生,本是夫妻义分,却做兄妹排行,煞尊堂间阻,俺情义难绝,他偷传锦字,我暗寄香囊,都则是家前院后,又不隔地北天南,空误了数番密约,虚过了几度黄昏。无缘配合,有分熬煎,情默默难解自无聊,冷清清谁问他孤吊,病恹恹赢得伤怀抱,瘦岩岩则怕娘知道。观之远天宽地窄,染之重梦断魂劳。[47]4
倩女的这段唱词极富真情,渲染了她深爱着王文举,却被天地阻隔的伤感,因思念而心神不定的满腹怒恨。孟称舜极为欣赏这段曲词,评曰:“絮絮叨叨,说尽儿女情肠”,并指出:“吴兴本于此支删去将半,殊觉寂寂矣”。[46]4臧晋叔将此支曲删去将半的做法,固然有其独特的考虑与道理,但孟氏对此深为不满,因为他认为恰恰是絮絮叨叨,反复诉说,才是真情流露,才能淋漓尽致地抒发了张倩女的思念、凄凉、哀怨之情绪,及其孤寂、冷落、落寞的处境。这正是此曲的佳妙之处,岂能删之,岂容删之,故又将全支曲悉数录下,由此可见真情在孟氏心中的分量与地位。
李渔也十分重视戏曲情感的真实性,在谈“科诨”时,他说:“真为笑也不真,其为乐也,亦甚苦矣。”[48]64谈到传奇的结尾时,他提出“但其会合之故,须要自然而然,水到渠成,非由车戽。最忌无因而至,突如其来,与勉强生情,拉成一处”[48]69。勉强生情,就会使真实的情感遭遇表达的挫折,使戏曲的质量大打折扣。在谈到声容、结构、化妆等戏曲环节时,李渔同样多次提到对于真情的呵护。
孟称舜、李渔等对于戏曲情感表达真实性的要求,与中国古典美学传统有着非常紧密的关联,从先秦老子的赤子之论到庄子的心斋、坐忘之观点,从汉代王充的“疾虚妄”,反“增产”、反“溢真”,到左思的“匪本匪实,览者奚信”,从刘勰的“不失其真”“不坠其实”的理论,到白居易的“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的思考,都为古典戏曲批评中的“真情”观打下了厚实的观念基础。
戏曲批评之“情”还具有唯一性,即突出情感的独特性,强调情感的个体性,这种个体性之情感既要求与语境相符,又要求与个体的身份相吻合,从而使其不可复制,具有无可替代性。关汉卿《窦娥冤》第一折【油葫芦】如下;
(正旦)莫不是八字儿该载着一世忧,谁似我无尽头,须知道人心不似水长流。我从二岁母亲身亡后,到七岁与父分离久,嫁的个同住人,他可又拔着短筹,撇得俺婆妇每都把空房守,端的个有谁问,有谁偢?[49]7
这段唱词,窦娥毫不遮掩,哔哔剥剥,原生态地喷泄而出,语言虽朴实无华,平淡无奇,却把她幼年即丧母离父,年纪轻轻又丧夫守寡的悲惨处境、内心的悲哀和苦痛抒发得淋漓尽致,没有比喻,没有拟人,没有修饰,没有月亮,没有落叶,只有直通通的话语,明明白白的言词,然情感却非常丰富,并且与她未受过多少教育的童养媳身份非常相符。孟称舜批曰:“何等真切”[49]7真是一语中的。倘若换一段《西厢记》里张生或崔莺莺的唱词,则真情全无,境界也全无。
情感的唯一性还表现在情感表达的差异性上,毛泽东眼中的梅花乐观放达,迥异于陆游眼中高洁、孤寂的梅花,是因为二人各自有着独特的情感体验。《西厢记》中,红娘的体贴之情,张生热烈的爱慕之情,莺莺矜持的相思之情,各个不同;《琵琶记》中,五娘的孝顺之情,蔡伯喈的忠心之感,张公的仗义之情,都被金圣叹、毛声山等批评家一一析出。
戏曲批评所尚之“情”不仅具有真实性、独特性,还有可感性。感情不同于理性,不是抽象的存在,它往往与身边的人、事、物紧密相连,使其具有可听、可触、可摸、可见的特点。金圣叹在《西厢记》批评中多次关注这一特点。《惊艳》一折,张生有说词曰:“行路之间,早到黄河这边,你看好形势也可”,金圣叹评曰:“张生之志,张生得自言之:张生之品,张生不得自言之也。张生不得自言,则将谁代不言,而法又决不得不言,于是须便反借黄河,快然一吐其胸中隐隐岳岳之无寄事。呜呼!真奇文大文也。”[50]6黄河是张生的眼前之物,滚滚黄河奔流到海的气势恰如胸怀大志却湖海飘零的张生,这样就不仅把张生塑造成一位满怀抱负、有志未就的士子,把他与《霍小玉传》开篇便欲“得一佳偶”的李益区别开来,而且还蕴含了张生是一位有情之人,面对黄河便生大志未就之情,
救《西厢》于淫书滥情之中。张生的情感是可感的,我们可以通过黄河、天空、太阳等景物轻轻地走到张生的面前,去触摸他那颗怦怦而动的心。
中国古典戏曲批评不仅言情,而且思考如何传情,即在具体方法的层面思考“曲贵传情”,使戏曲传情拥有可以践行的依凭。这种思考主要表现在对于情与景、情与事以及情与理等其他范畴关系的理解上。
王国维《人间词话》中说:“昔人论诗词有景语、情语之别,不知一切景语,皆情语也。”[51]34情,欲也;景,境也。情语是人们主观的情思,景语则是用以展示情的客观存在,二者的关系是借景抒情,情景交融,景非独景,情非孤情,情为本体,景为依凭。王国维是情景说的集大成者,在他之前,中国古人有过深刻的探寻印迹,从《礼记·乐记》“感于物而动”的萌芽,到刘勰首开“情以物兴”“物以情观”的情景交融理论,从王昌龄的三境说到姜夔《白石道人诗说》中“意中有景,景中有意”的观点,从元代杨载《诗法家数》中“写景,景中含意,事中瞰景,要细密清淡;写意,要意中带景,议论发明”的看法,到明人谢榛《四溟诗话》中的“情景孤不自成”之论,再到王夫之《姜斋诗话》中的情景交融之妙解,处处可见古人对于情感传达方法的思考。
脱胎于抒情传统母体中的中国古典戏曲,同样擅长于将情与景交融得恰到好处,一曲《西厢》,将张生与莺莺别离时的情与景写得令人叫绝:“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一曲《梧桐雨》,巧妙地将“梧桐雨”这一含情的意象不时托出,衬托出李杨爱情的复杂意蕴;窦娥蒙冤时有六月飞雪,丽娘游园时则有莺歌燕语,如是等等,不一而足。中国古典戏曲理论家十分关注借景这种传情方式,或者拈出片断,即时点评,如金圣叹评张生出场时的抒怀唱词,点出了借眼中之景别致写出张生之情的传情特点。或者就戏曲文本的整体效果作一评价,如祁彪佳评《朱履》曰:“备诸苦境,刻肖人情”[52]24;评《奇节》曰:“情与景合,无境不肖”[52]44。
景与情的关系,互相依存,互相促进。有时属正衬,如陈继儒评《红拂记》第三十四出红拂女的唱词曰:“曲有情景,极妙。”[53]334曲中红拂女唱道:“东风吹柳日初长,雨余芳草斜阳,杏花零落燕泥香,睡损红妆。香篆暗消鸾凤,画屏萦绕潇湘,峭寒轻透薄罗裳,无限思量。”首二句写春雨初霁,白昼渐长,东风吹拂着柳条,斜阳映照着芳草,烘托出一种极好的春睡氛围。红拂女本该好好享受如此春色,静谧地做个美梦,然而正当盛开的杏花打落在地,零落的杏花堕地沾泥,篆香已经销尽,红拂女依然清醒;画屏上的云雾绕梁,如红拂女的思绪一般纷乱,料峭的寒风中,满心都是对远方李靖的思念。由此可见,东风吹柳、春日渐长、斜阳芳草、零落杏花、香篆暗消、画屏萦绕、峭寒春风等,都为红拂女而设,这些景象的设置,极好地传递了红拂女盼心上人归来的焦急心情。景与情的关系有时又为反衬,以乐景写哀愁,或以悲境衬喜情。如吴舒凫评《长生殿》第九出【绣带儿】和【宜春令】二曲曰:“风定日迟,鸟声花影,纯写寂寥光景,与贵妃在宫繁艳之状不同,而又以愁境引起欢情,转到追悔之意,无限婉折。”[54]26此二曲乃唐明皇在将心生妒恨的杨贵妃撵出宫廷后所唱。【绣带儿】曰:“春风静,宫帘半启,难消日影迟迟。听好鸟犹作欢声,睹新花似斗容辉。追悔。”【宜春令】曰:“悔杀咱一刬儿粗疏,不解他十分的娇殢。枉负了怜香惜玉,那些情致。”[54]26-27春日载阳,春风和定,本当令人快意,而唐明皇却深恼日影迟迟,时光太慢;欢快的鸟声令他想起了爱妃的声音,鲜嫩的花儿令他想起了爱妃的丰采,于是,好景便成了他内心懊悔与惆怅的催化剂。
戏曲是叙事艺术,戏曲情感的传达同样离不开故事的展开。故事如何开端,如何发展,如何走向高潮,如何收煞,故事如何言说,由谁来讲,怎样讲,都会影响到情感的表达。现代叙事学比较全面地讲到了叙事艺术的各个方面,关涉叙述话语、叙述动作、叙述时间、叙述频率、叙述声音等多方面的内容,中国古典戏曲批评尽管没有如此完善的理论系统,但早已注意到情感与叙事之间不可忽略的关系。
吕天成论曲,提出“情从境传”来论述写景与传情的关系;孟称舜没有机械地照搬诗文中情景交融之说,他根据戏曲的代言体特点,把叙事、写景、传情三者联系起来考虑,强调在叙事中描绘景物、传达感情。这是前人所未论及的见解。在《柳枝集》中,孟称舜尤为注意在叙事、写景中传情的段子。如杨显之《秋夜潇湘雨》第三折【黄钟醉花阴】:
(正旦)忽听得摧林怪风鼓,更那堪瓮瀽盆倾骤雨,耽疼痛,捱程途,风雨相催,雨点儿何时住。眼见的折挫杀女娇妹,我在这空野荒郊可着谁做主?[55]18
这里叙写的是狂风大作、倾盆大雨的背景,描写了翠
鸾被丈夫休弃后又被诬入狱,被押解而行走在荒郊野外时的落魄之惨状,其间传递出女主人公凄凉、悲怨之情和孤苦无助之情。孟氏评曰:“通折就情写景语,不修饰而楚楚堪痛。”[55]18寥寥数语,道出了这段唱词的抒情特色及其传情方法,也将其通过在叙事中写景,通过景物而把情感的抒发与情节的演变和推进天衣无缝地交织在一起而不空泛的特点揭示了出来。
金圣叹以人物形象的塑造为核心修改和评点《西厢》,叙事安排均为人物的情感服务,譬如他在情节上对王《西厢》作了很多增删,目的就是使叙事能更好地符合莺莺、张生等各自的身份,很好地传达人物的情感。王《西厢》安排莺莺和红娘到佛殿玩耍,被张生撞见,金本改为让张生误闯入莺莺的“活动范围”;王《西厢》中,莺莺与张生打了个照面,“(红云)那壁有人,咱家去来。(旦回顾觑末下)”,这里,莺莺一方是主动者;金圣叹则将之改为莺莺和红娘是被观察者,她们没有看到张生,使莺莺成为一个中规中矩的大家闺秀。再如王本《西厢》第二本第一折,孙飞虎放言要攻破寺庙,强掳莺莺为妻,老夫人和众和尚万分焦虑,最后莺莺出主意,说谁能退兵就嫁给谁,张生迎难鼓掌而上,声称有退敌之策,“(旦背云)只愿这生退了贼者”,得到老夫人的允诺后,“(末云)既是恁的,体唬了我浑家,请入卧房里去,俺自有退兵之策。(夫人云)小姐和红娘回去者!(旦对红云)难得此生这一片好心!”莺莺的语言显得非常主动,直白急切,恨不马上嫁给张生;而张生也显得非常轻浮,直呼莺莺为“浑家”;“难得此生一片好心”一句语意不甚明了,易产生歧义:不知是感谢张生让她回房休息,还是感谢他能退兵。金圣叹删去了莺莺与张生的一些直切、轻浮之语,代之以具体的计策,让在场者和读者都相信这种安排可以解除危难,然后,老夫人让莺莺、红娘回房休息,此时,莺莺才由衷地说了句“红娘,真难得他也”。短短的一句话,温柔体贴,发自肺腑,既有敬佩又存感激,颇具真情。
从以上的叙事安排可以见出金圣叹以事衬情的批评观。金圣叹认为,整部《西厢》,止写双文一个人,写双文当然要写出其内心的真情实感,所以,写红娘、张生、夫人、法本、孙飞虎、杜确等,都是为写双文,不写红娘,写不出双文的矜持徘徊,不写张生,写不出双文的缠绵悱恻,不写老夫人,写不出莺莺对爱情的渴望,如此等等。
情与理是一对相依相存又相斥相悖的范畴,二者的关系大体可以表述为情依于理。早在先秦时代,孔子的“诗可以怨”论、温柔敦厚的诗教观便露出了情理关系思考的端倪,他强调以理节情;战国时,荀子强调以理养情;汉代《毛诗序》肯定情感抒发的现实需求,但强调“止乎礼义”,并限制怨刺手法的使用;宋代理学盛行,使情与理的关系变得紧张起来,艺术批评领域尚理抑情,至此,“以理节情,以理统情,以理驭情,理制约情,情被理所制约的传统情理观逐步形成”[56]132。明代早期,情理关系承继宋代理学的风尚,依然强调“以文明理”,然至明代中晚期,情理关系开始变化,新的情理观主张尚情,以情统理,情中有理,理寓情内。古典戏曲批评观念中,情感关系也大致可以分为两种:情依于理与以情统理,两相比较,各有其存在的时空。明代前期,尊理的成分稍多一些,而至明中晚期,则尚情的成分更为浓烈。
汤显祖认为:“情有者,理必无;理有者,情必无,真是一刀两断语。”[57]129情与理似乎水火难容。针对程朱理学宣扬的那种超验化、理念化的封建伦理道德的“理”,汤显祖《牡丹亭记·题词》明确主“情”,他对那种禁锢人的自然情感欲望的做法大加鞭挞,让“情”在与“理”的对峙与撞击中扬眉吐气,高傲胜出,将“以理格情”的大旗易为“以情格理”,还“情”以一片自由的天地,尽管这种情还有“梦”的成分,还因压抑与摧残而找不到出路,还只能在戏中释放,但毕竟这一抹遥远的绿意已让人感受到了春的脚步和春的气息。
当然,在理与情的关系方面,汤显祖并非纯粹舍理,只不过“情”在他的批评观念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成分。敢于冲破封建阻碍、为爱情出生入死的杜丽娘在复活后为柳梦梅所追求时,她不忘告诫曰:“秀才可记的古书云:必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主张依循“鬼可虚情,入须实礼”的古训,并以此拒绝柳生,使其二人的婚姻回到“奉旨完婚”的古老轨道上去。恰如王思任所言,丽娘之情是“正”之情,“得《易》之咸,从一而终”,“可与殉夫以死”的贞节之妇相比。《牡丹亭》这种“变奏”式①郭英德认为《牡丹亭》之情“并没有超逸出传统文学观念的矩范,仍然是传统文学观念的变奏,只是更多地涂染了时代所赋予的主体精神和感性色彩而已”。郭英德《明清传奇戏曲文体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180页。而非颠覆性的处理与安排
充分体现了汤显祖复杂的情理主张。
孟称舜等其他主情派戏曲批评家也非常巧妙地解释着“情”,非常有度地把握着情与理的关系。首先,在对“情”的理解上,孟称舜同样将其解释为“正”情:“男女相感,俱出于情。情似非正也,而予谓天下之贞女,必天下之情女者何?不以贫富移,不以妍丑夺,从一以终,之死不二,非天下之至情者而能之乎?然则世有见才而悦,慕色而亡者,其安足言情者哉?必如玉娘者而后可以言情,此此记所以为言情之书也。”[58]562可见,孟称舜所谓的“情”乃“从一以终,之死不二”的“正”情,而非“见才而悦,慕色而亡”之情,甚而后者是不足以言情的。其次,在对情理关系的把握上,孟称舜可谓用了一番心思。他在《娇红记·题词》中指出:“天下义夫节妇,所为至死而不悔者,岂以为理所当然而为之邪?笃于其性,发于其情。”[59]559为通情与理,孟氏以“性”作为连接,他认为“至死而不悔”的“义夫节妇”,并不是封建伦理说教的成功,而是“笃于其性,发于其情”的结果,娇娘、申生“两人皆从一而终,至于没身而不悔者”,并不是“父母之命,媒约之言”“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封建道德,而恰恰是被封建礼教视为“有类狂童、淫女所为”的自由相恋,同心相结。所以,把“节义”归因于“性情”,这就把“人欲”与“天理”联系起来,完成了“私欲之中,天理所寓”“理者,存于欲者也”“人心本无天理,天理从人欲中见”等思想的艺术阐释。
李渔同样是将情与理折衷兼顾的一位戏曲理论家,他认为“情”“文”“有裨风教”是戏曲作品三个核心的审美价值。李渔格外强调“至情”之于“至文”的重要作用,强调真情实感是戏曲文学最根本的性质,是戏曲的出发点,离开了情,即如再求“工”而“工”依然难至。但是李渔同样主张“情”与“理”要兼顾,譬如他曾借其剧中人物之口,指出“从肝膈上起见的叫做情,从袵席上起见的叫做欲”,同属相思之人,前者叫情痴,后者只能叫欲鬼。不仅如此,李渔还通过强调戏曲的劝惩功能而突出其“理”性之特征,也正是基于此,他将《琵琶记》中的部分情节作了修改。
明中叶后,以汤显祖为代表的中国古典戏曲批评者以“情”品曲,主张戏曲应当写真情,达真情。其中,尽管不同的批评者对“情”的理解各异,甚至有人将“理”“义”“节”等封建思想渗入“情”中,但都未影响到主情派对戏曲的鉴赏观念。这种尚情的戏曲批评观承继了中国古代的诗学传统,是明代社会经济、政治、哲学思潮、市民文化等合力的结果,也是明代戏曲理论与批评家们互相影响的结果。它的存在对不利于戏曲发展的“尚理”思想进行了及时纠偏和有力反拨,为戏曲的进一步繁荣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1]说文解字段注[M].影印.成都:成都古籍书店,1981.
[2]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下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0.
[3]陈奇猷.吕氏春秋校释(一)[M].北京:学林出版社,1984.
[4]班固.汉书·董仲舒传[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5]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上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0.
[6]朱自清.诗言志辨·序[M]//朱自清全集.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
[7]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
[8]班固.汉书·艺文志[M].北京:中华书局,1962.
[9]陆机.文赋[M]//魏晋南北朝文论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
[10]萧统.文选序[M]//萧统,编.文选(上).李善,注.北京:中华书局,1977.
[11]刘勰,著.周振甫,注.文心雕龙注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12]钟嵘.诗品序[M]//孟蓝天,赵国存,张祖彬,编著.中国文论精华.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3.
[13]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M]//魏晋南北朝文论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
[14]杜甫.偶题[M]//陈贻焮,主编.增订注释全唐诗(二).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
[15]白居易.苏州南禅院·自氏文集记[M]//全唐文(七).北京:中华书局,1983.
[16]吕天成.曲品[M]//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六).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
[17]汤显祖.宜黄县戏神清源师庙记[M]//俞为民,孙蓉蓉,主编.历代曲话汇编(明代编第一集).合肥:黄山书社,2006.
[18]汤显祖.耳伯麻姑游诗序[M]//徐朔方,笺校.汤显祖诗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2.
[19]汤显祖.三先生合评元本西厢记·叙[M]//蔡毅,编著.中国古典戏曲序跋汇编(二).济南:齐鲁书社,1989.
[20]汤显祖.《董解元西厢》题辞[M]//蔡毅,编著.中国古典戏曲序跋汇编(二).济南:齐鲁书社,1989.
[21]徐国,涂育珍.临川戏曲评点研究[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7.
[22]汤显祖.牡丹亭记·题词[M]//徐朔方,笺校.汤显祖诗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2.
[23]汤显祖.沈氏弋说·序[M]//徐朔方,笺校.汤显祖诗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2.
[24]陈继儒.牡丹亭题词[M]//徐朔方,笺校.汤显祖诗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2.
[25]王骥德.曲律[M]//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四).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
[26]汤显祖.汤许二会元制义点阅题词[M]//徐朔方,笺校.汤显祖诗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2.
[27]汤显祖.揽秀楼文选序[M]//徐朔方,笺校.汤显祖诗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2.
[28]汤显祖.萧伯玉制义题词[M]//徐朔方,笺校.汤显祖诗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2.
[29]徐渭.南词叙录[M]//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三).北京:中国戏
剧出版社,1959.
[30]潘之恒.亘史[M]//俞为民,孙蓉蓉,主编.历代曲话汇编(明代编第二集).合肥:黄山书社,2006.
[31]汪效倚.潘之恒曲话[M].北京:中国出版社,1988.
[32]冯梦龙.太霞新奏·序[M]//俞为民,孙蓉蓉,主编.历代曲话汇编(明代编第三集).合肥:黄山书社,2006.
[33]凌蒙初.谭曲杂剳[M]//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四).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
[34]孟称舜.古今词统序[M]//孟称舜集.北京:中华书局,2005.
[35]孟称舜.倩女离魂总评[M]//孟称舜集.北京:中华书局,2005.
[36]孟称舜.古今名剧合选·序[M]//孟称舜集.北京:中华书局,2005.
[37]孟称舜评《二郎收猪八戒》[M]//古本戏曲丛刊(四集之八).古今名剧合选(五).北京:商务印书馆,1958.
[38]孟称舜评《范张鸡黍》[M]//古本戏曲丛刊(四集之八).古今名剧合选(十).北京:商务印书馆,1958.
[39]孟称舜评《谇范叔》[M]//古本戏曲丛刊(四集之八).古今名剧合选(十三).北京:商务印书馆,1958.
[40]孟称舜评《青衫泪》[M]//古本戏曲丛刊(四集之八).古今名剧合选(二).北京:商务印书馆,1958.
[41]孟称舜评《墙头马上》[M]//古本戏曲丛刊(四集之八).古今名剧合选(四).北京:商务印书馆,1958.
[42]孟称舜评《赵氏孤儿》[M]//古本戏曲丛刊(四集之八).古今名剧合选(十四).北京:商务印书馆,1958.
[43]孟称舜.《张玉娘闺房三清鹦鹉墓贞文记》题词[M]//孟称舜集.北京:中华书局,2005.
[44]袁于令.焚香记·序[M]//俞为民,孙蓉蓉,主编.历代曲话汇编(明代编第一集).合肥:黄山书社,2006.
[45]王文锦,译解.礼记译解[M].北京:中华书局,2001.
[46]陈鼓应,注解.庄子今注今译[M].北京:中华书局,1983.
[47]孟称舜评《倩女离魂》[M]//古本戏曲丛刊(四集之八).古今名剧合选(一).北京:商务印书馆,1958.
[48]李渔.闲情偶寄[M]//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七).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
[49]孟称舜评《窦娥冤》[M]//古本戏曲丛刊(四集之八).古今名剧合选(十一).北京:商务印书馆,1958.
[50]王实甫.西厢记[M].金圣叹,评点.上海: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51]王国维.人间词话[M]//人间词话删稿(4).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52]祁彪佳.远山堂曲品[M]//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六).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
[53]陈继儒.陈眉公批评红拂记[M]//北京大学图书馆,编辑.不登大雅文库珍本戏曲丛刊(十二).北京:学苑出版社,2003.
[54]吴舒凫.长生殿·眉批[M]//古本戏曲丛刊(五集).影印.北京:商务印书馆,1958.
[55]孟称舜.秋夜潇湘雨·眉批[M]//古本戏曲丛刊(四集之八).古今名剧合选(四).北京:商务印书馆,1958.
[56]李建中.中国古代文论范畴发生史[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
[57]汤显祖.寄达观[M]//玉茗堂尺犊.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
[58]孟称舜.贞文记·题词[M]//孟称舜集.北京:中华书局,2005.
[59]孟称舜.娇红记·题词[M]//孟称舜集.北京:中华书局,2005.
(责任编辑、校对:刘绽霞)
Feelings:A Key Word in the Criticism of Chinese Classical Drama After the Middle Period of Ming Dynasty
Liang Xiaoping
"Feelings"is a key word in the criticism of Chinese classical drama and the aesthetic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opera. Interpreted as favor,passion and emotions,feelings is only innate with human beings which is simple and genuine in origin,which exerts influence on aesthetic points of value in ancient China and the philosophical reflections on literature.The literary advocacy popular in Wei and Jin dynasties that poetry evolved from feelings which sets up feelings as the yardstick in literary criticism,which was poles apart from the Confucianism and utilitarianism.In ancient China,great importance had been attached to"feelings"in drama criticism.After middle Ming dynasty,in preface,postscript,letters,and drama,leading dramatists and critics including Tang Xianzu aired their ideas about drama and life at large.Authenticity,uniqueness and sensibility are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emotion"in drama critical theories,and the communication of emotion is based on understanding and dealing wi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motion and scene.
Feelings,Chinese Classical Drama,Criticism,Tang Xianzu,Meng Chengshun
J820.9
A
1003-3653(2016)05-0088-13
10.13574/j.cnki.artsexp.2016.05.010
2016-06-26
梁晓萍(1972~),女,山西平遥人,博士,山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研究方向:文艺理论与美学。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中国古典戏曲品评观念研究”(12YJC760043);山西师范大学文理学院教改项目“读图时代文学理论的教学改革”(WL2015JCXM-X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