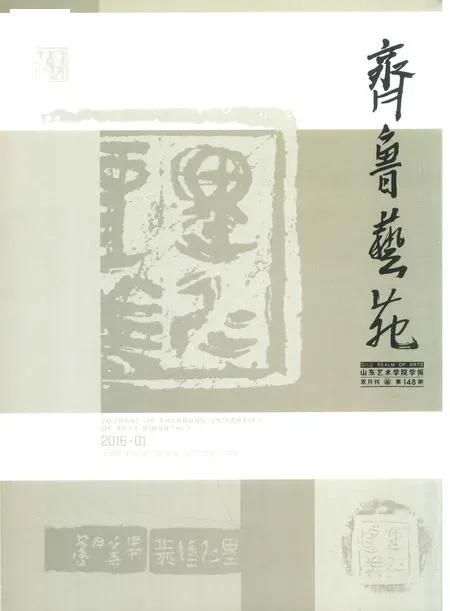是否有“他者”再“失语”?
——论徐棻作品中女性角色的言说
常慧娟(上海戏剧学院研究生部,上海 201102)
是否有“他者”再“失语”?
——论徐棻作品中女性角色的言说
常慧娟
(上海戏剧学院研究生部,上海201102)
摘要:60年笔耕不辍的女性剧作家徐棻带着独有的强烈的“徐棻意识”创作了单保留下来就400多万字的戏剧作品,塑造了独特的女性形象,因此从性别文化批评的视角去赏析其中的女性形象变得尤为重要。参照《第二性》理论观照,其对女性角色的塑造折射出女性作家主体在特定语境中的独特表达。
关键词:《第二性》;女性作家;女性角色;独特表达
曾参军赴朝、读过北大、当过官、演过戏、经历过“四清”运动、“文化大革命”和“拨乱反正”的女性剧作家徐棻,在其丰富多彩的生活中坚持60多年笔耕不辍,创作出了大量的戏剧作品。戏剧评论家张羽军将其创作分为三个阶段:其一,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突破传统,为“突破古人”;其二是“突破自己”;其三是开始对自己的作品进行“形态建构”[1](P26)。在不断求新的创作风格的流变中,唯一不变的是这位“巴蜀才女”[2](P22)所独有的、被众多评论家所一致认可的“徐棻意识”;张羽军对此做出了详细而准确的解读:“所谓‘徐棻意识’——就是她的‘人文意识’——‘人性被文明化后的人道’和‘文化被人道化后的文明’所熔铸整合而注入她的作品中的审美意识”[3](P25)。正是由于这位女性剧作家强烈的创作风格及其塑造的独特女性形象,使得从性别文化批评的视角解读作品变得具有必要性。本文将围绕着徐棻作品中是否存在“他者”以及“他者”是否“失语”两个问题展开简要的分析,换句话说“他者”是如何在女性作家作品中实现的“言说”。
一、“他者”的界定以及徐棻作品中的“他者”因素
《圣经》中,从“夏娃是用亚当的一根多余的肋骨做成”起,女人便被放置在了附属的地位。正如米什莱[4]曾说:“女人,是个相对的人……”西方女性主义批评对“历史”的解剖也同样具有相同的性质:“‘历史’(history)之构词无非就是‘他的’(his)而不是她的(her)故事(story)。”[5](P55)不难发现,无论是从女性的个人地位还是女性被书写的历史中,“女人”一词始终是附属并且相对于男人而言的。如西蒙娜· 德·波伏娃所说:“定义和区分女人的参照物是男人,而定义和区分男人的参照物却不是女人。她是附属的人,是同主要者(theessential)相对立的次要者(theinessential)。他是主体(theSubject),是绝对(theAbsolute),而她则是他者(theOth—er)。”[6](P11)因此,在男女的性别关系中,女性被指为“他者”一定是有男性这一“此者”(theOne)为参照物,但同时,“他者”的形成又不是以树立“他者”而得以命名,而是在“此者”树立自己时形成了“他者”。如波伏娃所说:“并不是他者在将本身界定为他者的过程中确立了此者,而是此者在把本身界定为此者的过程中树立了他者”,“他者是按照此者为树立他自己而选择的独特方式而被独特地界定的”[7](P13,286)。因此,“他者”在被书写的过程是一个二元性的表达,是附属于主体的相对者。
带着这种观念去阅读作家作品,那么一定会从中找寻出作品中的“他者”或者带有“他者”因素的相对者。而戏剧家徐棻的作品中则带有某种特殊性,因其是女性作家,并带有强烈的人文意识,作品自然流露着作家对于女性命运的深刻思考和对于女性的希望,也因此在某种程度上体现着作家的主观性表达,即“女性文学叙事在本质上是被某种价值观念渗透着的话语叙事”[8]。戏剧家徐棻的川剧作品《燕燕》,将关汉卿元杂剧的残本《诈妮子调风月》中的喜剧改为现在的悲剧。其中,就燕燕所处的婚姻的封建家长制时期而言,作为丫鬟的燕燕是绝对没有发言权的,总镇夫人则是话语权力的表达者。而在戏中,男主角李维德替父辩冤、锦衣绣袍归来,势利的老夫人随即转变态度,积极迎合奉承侄子李维德,这里,真正的话语权力发生了转移。因此在后面的“情变”、“说媒”、“抗婚”的戏剧段落中,李维德和燕燕便是直接的关系主体。在这一对关系中,李维德为达到自己“一男兼得二美”的目的,使用计谋让老夫人命令燕燕替自己去说媒娶回莺莺,再娶燕燕为二房,那么主客体便出现了。男性角色李维德为树立起自己的权威,强迫燕燕“利他”。对于李维德而言,燕燕是仆人,是他利用的工具和战胜的对象,因此在李维德达到自己目的的同时,燕燕被自主地定义为“他者”,并且构成燕燕自身无法超越困境这一事实。这是一个层面,而作为一个女性作家的戏剧作品,到此绝非结束。女性戏剧家徐棻改变了原有的燕燕做二房的喜剧结局,也不像其他论者提出的“结局的改变还可以有多种选择:可以是燕燕被弃后嫁给忠厚老实的贫苦男仆;也可以是燕燕被卖他乡,沦落为妓;还可以是李、贾为杀人灭口,谋害了燕燕”[9](P53)……而是让燕燕奋起反抗:“五更鼓惊裂肝胆,声声问怎度今天?怎容得虎狼称心愿,怎看得魔鬼披红衫。怎能够任他作践,怎雪我耻辱般般”[10](P138),面对“自由自在做个人”[11](P123)的欲罢不能,枉费自己对贵公子李维德的痴心一片,最终燕燕以死抗争。如果“燕燕”这一女性形象用作者在塑造心中的新时代女性理想这一表达来形容尚不够格的话,那么至少徐棻是将自己的女性视角融入其中,并对“燕燕”这一女性角色充满着期待。在新时代的语境下,燕燕追求真挚爱情再正常不过,然而在无力改变的封建家长制的环境中,用毅然决然的刚烈的死来诅咒李维德的婚礼却是对所处环境的最大反叛。因此,在作者笔下,燕燕由被树立的“他者”转变为树立自己的“此者”,“我”无法超越,宁愿“我”用死来诅咒你李维德“白凶当头噩运缠”[12](P138)。这也体现着燕燕克服阻力以争取自由的努力,是燕燕努力想要保持的不受践踏的自我尊严,具有着浪漫主义精神。同时,在李维德与燕燕这一对直接的关系中,与燕燕相对立的李维德便成为了“他者”。可以说,因为女性作家将女性视角融入其中,并带有某种程度上的角色期待,因而作品叙事的表达视角发生了转变,“他者”的范畴也由《第二性》中普遍所指的依附于男性的女性转而成为与话语表达者相对立的一面。
二、“他”与“他者”的关系
“他”与“他者”的关系是每一个生存者都经历的戏剧性的事件。西蒙娜·德·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提到婴儿也经历了他与他者的关系。她认为,婴儿在6个月左右,通过对于动作的模仿,开始显示出想吸引别人的欲望,然而这种态度不是有意采取的,也无须为它的存在设想出一种处境[13](P310)。而与婴儿不同的是,戏剧家徐棻作品中的“他”与“他者”呈现着两种明显的现象:(一)“他”与“他者”之间的转化;(二)“他者”经历着明白自己具有他性、相异性的体验,并经历着自主生存与客观自我——“做他者”的冲突,而在转换为“此者”的过程中“被限定的存在”。
(一)“他”与“他者”之间的转化
正如前文所述,川剧《燕燕》中,相对于所处环境,燕燕是“他者”,而在其后的行动转换中,我们又可以将燕燕看成是“此者”而成为“主要者”。当然,也有可能使其不成为主要者,那便如波伏娃所说,“如果承认这个次要的有意识的人,也有明显的主观性,也能够进行Cogito[我思],那么也就等于承认这个人实际上是主权的,能够重新变为主要者。为了使所有的相互性都完全成为不可能,必须使他者对自己也是一个他者,必须让他的主观性受他的他性影响”[14](P298)。而《燕燕》中,燕燕并没有使自己的主观意志屈从于李维德,没有放弃自己对于真挚爱情和做一个自由人的追求,因而她不被她的“他性”所影响,也就顺利地完成了由“他者”向“主要者”的转化。无场次川剧《死水微澜》中也有同样的表现。在封建婚姻的时期,女性角色邓幺姑原本是被书写的“他者”,被封建婚姻制度束缚着命运而不得翻身,然而在戏中,这一原本不得改变的现实被改变了,邓幺姑并没有遵循原有的应该遵循的从一而终的婚姻,而是先后三次嫁人,其中有对民族外来侵略的本能反抗,而更重要的是邓幺姑这个原本被树立的“他者”在封建的环境中对封建婚姻的大胆反抗,而使得她从“他者”转变为不被自己“他性”所束缚的“主要者”。
(二)“他者”经历着明白自己具有他性、相异性的体验,并经历着自主生存与客观自我——“做他者”的冲突,而在转换为“此者”的过程中“被限定的存在”。
所谓“他性、相异性的体验”和“做他者的冲突”,波伏娃分别举了这两个例子来做解释:“当小女孩开始学习在世界上如何生活,领悟到在世界上做一个女人意味着什么时,产生的正是这种体验”[15](P343)和“人们教导她说,为了讨人喜欢,她必须尽力去讨好,必须把自己变成客体;所以,她应当放弃自主的权利”[16](P324)。那么这里便强调了一种转变,两个阶段的过程:一种转变是从一个有自我主观意识的主体的人向一个客体、即他者的转变;两个阶段一是放弃自主权利,即主观的自由意识,二是做他者。在戏剧家徐棻的作品中,女性角色同样经历着这样的体验和冲突,如川剧现代戏《都督夫人董竹君》中,女主角董竹君“再不见宽厚的丈夫做家长,只见着粗暴的男人施独裁”[17](P84)便是“他性”的体现,她想创实业,她的这些怒斥是对丈夫怀有期待的失望,本以为可以得到丈夫的赞同和帮助,而换来的却是丈夫的斥责和醉酒后的打骂;还有后面的“那是我多年的愿望心底埋”和“如果失败了,从此以后,你说啥,我听啥;你叫我做啥,我就做啥。乖乖做一个你想要的女人”[18](P84—85),这是如果创实业失败对丈夫的依赖的一种假设,是她的“他性”。而为实现创实业这一愿望请求丈夫的认同本身就是在吸引丈夫的关注,希望得到他的赞同和帮助,也是“他者”的“他性”所在。而女性角色董竹君在这一过程中所面临的一切困境,包括丈夫对董竹君和李高的误会,都可以看作是相异性的体验。剧中,董竹君从不遵从老家婆婆旧规矩到读书学习,再到外出办实业工厂,从办实业到卖掉工厂回归家庭,到最后的离婚开餐馆,从董竹君的这一系列的经历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有她的主观意识支配下的行动,有对丈夫的讨好和妥协,有再次离开丈夫的毅然决然,这便是她所经历的自主生存与客观自我——“做他者”的冲突。同时身为女性的她既要顾全丈夫,又要关心照顾自己的孩子,并且不甘放弃自己的信念,还坚守着妇道的尊严,一种角色,多重的限制下存在,即是剧中董竹君这一女性角色的“被限定的存在”。
川剧《田姐与庄周》是戏剧家徐棻取材于冯梦龙的小说《庄子休鼓盆成大道》经过改造被誉为“化腐朽为神奇”的一部戏。在这部戏中,戏剧家徐棻聚焦于两个主人公,无论是庄周还是田氏,在对方面前互为“他”和“他者”。田氏年轻貌美,面对楚王孙的来访,不由自主地心中泛起涟漪:“花一朵,情两般,谁是谁非谁能言?只觉春风吹池水,荡起了甜也荡起了酸。”[19](P41)当女性角色田氏意识的主观性产生作用时,那么此时相对于庄周,她就成为相对于庄周的“主要者”,庄周即为“他者”。而后面田氏谨遵妇道“田氏知妇道,奉君当至诚。先生若不信,盟誓对神灵”时,她的“他性”意识占据上风,而又将她转化为庄周的“他者”。最终因为得知是丈夫在试自己,而自己却已动心有违妇道,羞辱难耐,垂绫而死,因此对田氏而言,她没有超越自己的强烈主观性,在这一方面,她没有《燕燕》中燕燕的果敢,她仍旧回归到了“他者”的角色,被限制的存在中。而庄周在戏中被削弱了神化意味的身份,被塑造为一个正常的活生生的人,也同一般男人一样有着人性的弱点。在和田氏的直接关系中,他原本处于“他”的地位,然而当不能挣脱自己为自己戴上的枷锁而去试妻时,他的行动和内心无法战胜自己,此时他又成为田氏的“他者”。这便是作者的高超之处,把观赏性和哲理性相结合,在古老戏曲的传统表现手法中融入现代的含蓄而又多义的思想,诉说着具有复杂心理的“人”,活生生的“人”。
三、“特权的他者”通过自己实现主体
对于“特权的他者”,波伏娃总结了不同作家笔下的女性神话。她认为,对于蒙特朗来说,他是超越者,而女人匍匐在地上,他的脚下,那么可以推论的是,任由他度量他与女性之间距离的女性可以被认为是“特权的他者”;克洛代尔认为只有上帝是超越者,男人只是扩展了生活的领域,而女人则是维持原有的生活,那么负责维持原有生活的女人也可以看作是“特权的他者”;还有司汤达,“对于这位人文主义者来说,两性的自由存在在其相互的关系中实现了他们自身”,那么此刻“特权的他者”可以看作是互为彼此的“他”和“她”。[20](P286—287)由此,笔者认为,在女性戏剧家徐棻的作品中,“特权的他者”或者体现为抗争的女性角色,或者体现为自我毁灭的女性角色,而被实现的主体或者是她们自己,或者是她们屈从的男性主体和环境,通过实现主体而体现出女性角色的“存在感”,实现“他者”的言说。
正如晋剧《烂柯山下》,戏剧家徐棻以一组衙役为贯穿线,塑造了朱买臣和崔巧凤的悲剧。剧中的崔巧凤可视为彻头彻尾的“他者”,不嫌弃穷酸学生朱买臣而嫁与他,洗衣做饭,上山砍柴,只为夫君考取进士;而在两次的三年进士不得后,她不想再忍受穷苦生活,求休书迫使朱买臣离家;当朱买臣锦衣归来时她却遭丈夫马前泼水,正是这一关键性的戏剧动作,让崔巧凤备受羞辱:“只落得,马前泼水遭耻笑,只落得,覆水难收枉断魂……”[21](P240)而“特权的他者”便是后面“执盆去打长江水”[22](P240)的崔巧凤,是经历过前面一切为丈夫的努力在此刻化为乌有且被羞辱的一种困境下做出的特殊行动,也正是崔巧凤的含羞而死让朱买臣意识到了曾经“又像老爷又像仙”[23](P244)的妻子巧凤的好生伺候,曾经“凤冠霞帔与她穿”的盟誓,朱买臣回心转意却为时已晚。女性角色崔巧凤从头至尾都在用行动做着男人身边的女性,是附属于男性的地位,即便在被丈夫羞辱、不被认可的时候仍没有反抗而是以死亡来完成女人的使命,这样的“他者”也实现了死亡的诉说,在朱买臣实现为男人这一主体的同时也以他自己的悔恨体现出巧凤的存在感,然而这种诉说是被动的,是没有超越性的“他者”的言说。
同样的方式,在融戏曲写意性、虚拟性、程式性、符号性以及综合歌、舞、杂技等多种审美特点于一身的跨文化的川剧《欲海狂潮》中,蒲兰这一女性角色也以自我毁灭的方式使男性主体得以实现。《田姐与庄周》中的田氏也是如此。而同样是自我毁灭但以反抗的女性形象出现的是《燕燕》中的燕燕,所不同的是,燕燕作为“特权的他者”实现的主体是她自己,她实现了宁死也要有尊严的自身价值。
四、主体实现自己是否是绝对精神
讨论是否是绝对精神意旨是根据剧中角色在主观和客观之间所做出的选择,在剧中主体实现自我的基础上找寻作者主体在作品中的人文性的表达。笔者认为,这里的绝对精神是狭义的绝对精神,是主体主观意识和客观环境两者的合力结果的呈现。就像川剧《王熙凤》,整部剧中,作者让王熙凤始终处于“主要者”的地位,而她所在的一切环境都是“他者”,剧中王熙凤机关算尽、百般讨好老太太、两面三刀、心狠手毒,然而她的要求都达到了,她一呼百应,得到老太太喜欢,将尤二姐打垮,保住自己的地位,一个非常丰满的、立体的形象跃然纸上,是她战胜了环境,也是环境铸就了她,是主观的意识和客观的环境融合的结果,因而她树立了她自己,成为主体,同时也实现了她的绝对精神。而在这部戏中,作者也通过塑造这样的一个王熙凤而将庞大的《红楼梦》的经典形象立在了舞台上,同时能让观众接受,因而这也是改编再创作的超越。
《燕燕》中,身处底层的丫鬟燕燕被贵公子李维德始乱终弃,坚决不屈身做二房,毅然决然以死亡来做出反抗,虽然作者将燕燕塑造成了悲剧的命运,但我们依然看到作者赋予燕燕追求自我尊严的强烈的主观意识,以及她对所处封建婚姻环境的强烈反抗。如前文所述的,多位论者都提出燕燕的命运可以有多种,而戏剧家徐棻都没有写,而是塑造了现在的燕燕,我们不能不说,这种具有绝对精神的“燕燕”实质上是作者主体赋予她的精神,这也正是作家作品中“人的尊严不容践踏”这一主题的体现,同时也可以说,在这部剧中,乃至《都督夫人董竹君》《目连之母》《死水微澜》等更多的作品中,戏剧家徐棻投入了女权主义的情怀,通过古老戏曲中的这位具有现代精神的丫鬟燕燕,作者思考着女性的处境,阐述着女性应有的精神,表达着她的女性理想。
结语
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上看戏剧家徐棻的作品,她都可以说是“站在时代高度去审视、反思、领悟我们的历史和文明”[24](P31),也无论是“燕燕”、“田氏”、“董竹君”,还是“王熙凤”、“邓幺姑”、“崔巧凤”、“蒲兰”等,作者笔下的女性角色以不同方式反抗着所处的环境,坚守着自己的信念,追求着自身的价值,虽然摆脱不了所处环境的困境,但都在某种程度上突破超越着自我,作为父权话语下的“他者”要么奋力反抗,要么做着从“他者”到“此者”的转化,而她们所做出的努力也正是实现的“他者”言说,这寄予着女性作家本身对于女性角色的期待和希望,也是戏剧家徐棻完成的一次又一次带有“徐棻意识”的人文表达。
参考文献:
[1][3][24]张羽军.文心涵大千世界剧作写性灵情思——论徐棻剧作的艺术成就[A].羽军.徐棻剧作研究论文集萃[C].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10.
[2]严福昌.巴蜀才女的“玫瑰园”[A].羽军.徐棻剧作研究论文集萃[C].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10.
[4]米什莱(1798~1874):法国历史学家。
[5][9]李祥林.从徐棻剧作看“第二性”世界的多面呈现[A].羽军.徐棻剧作研究论文集萃[C].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10.
[6][7][14][20]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I[M].陶铁柱译.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
[8]刘巍.被遮蔽的女性叙事——重读沈祖棻历史小说[J].社会科学辑刊,2011,(2).
[10][11][12]徐棻.燕燕[A].徐棻剧作精选(上)[M].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09.
[13][15][16]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II[M].陶铁柱.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
[17][18]徐棻.都督夫人董竹君[A].徐棻剧作精选(上)[M].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09.
[19]徐棻.田姐与庄周[A].徐棻剧作精选(上)[M].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09.
[21][22][23]徐棻.烂柯山下[A].徐棻剧作精选(下)[M].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09.
(责任编辑:景虹梅)
中图分类号:J8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236(2016)01—0108—04
doi:10.3969/j.issn.1002—2236.2016.01.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