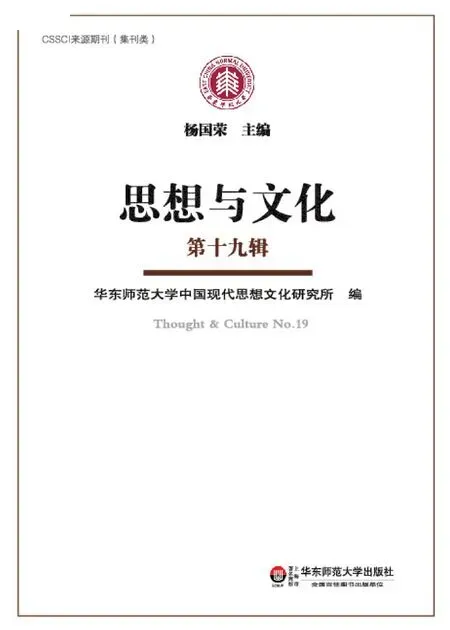〗张载是气一元论者还是理气二元论者
●耀明
有关张载的宇宙本体论,大陆学者多理解为“气本体论”或“气一元论”,而海外新儒家则多理解为“理本体论”或“理气二元论”。二说似皆各有所据,而实未得张载学说之全。以下分别对二说略加分析、评论,并尝试提出另一较为合理的解释,以期掌握张载宇宙本体论之实。
一、“气一元论”的论据
将张载的宇宙本体论定性为“气本体论”,我认为并不恰当。因为可聚可散的气乃现象界的东西或成份,而非宇宙本体或形上实体。张载虽也使用“本体”一词,但这主要是用来表示“本然状态”或“本来体段”,而非“形上实体”。相对地说,称张载的学说为“气一元论”似乎较佳。有关“气一元论”的论据,大概可归纳为四点,即“一气二态”说,“清浊转化”说,“水冰凝释”之喻,及对治佛、老二家之说。
有关“一气二态”之说,主要有以下几条值得注意的论点:
(1)太虚无形,气之本体,其聚其散,变化之客形尔。①张载:《张载集》,章锡琛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第7页。
(2)气之为物,散入无形,适得吾体;聚为有象,不失吾常。太虚不能无气,气不能不聚而为万物,万物不能不散而为太虚。循是出入,是皆不得已而然也。②张载:《张载集》,章锡琛点校,第7页。
(3)知虚空即气,则有无、隐显、神化、性命通一无二。③张载:《张载集》,章锡琛点校,第8页。
(4)气本之虚则湛一无形,感而生则聚而有象。④张载:《张载集》,章锡琛点校,第10页。
(5)太虚者,气之体。气有阴阳,屈伸相感之无穷,故神之应也无穷;其散无数,故神之应也无数。虽无穷,其实湛然;虽无数,其实一而已。阴阳之气,散则万殊,人莫知其一也;合则混然,人不见其殊也。形聚为物,形溃反原。反原者,其游魂为变与!⑤张载:《张载集》,章锡琛点校,第66、184页。
(6)气聚则离明得施而有形,气不聚则离明不得施而无形。方其聚也,安得不谓之有[客]?方其散也,安得遽谓之无?①张载:《张载集》,章锡琛点校,第10、182页。综合以上六条之所说,张载似以气之聚散可有二态之循环交变。所谓“太虚无形”似表示气于未聚散时之本然状态,即“气之本体”。聚为有象之物,及散而物化,只是“变化之客形”,已非气之原初状态。气之由聚而散,以至散入无形,乃是“形聚为物,形溃反原”的过程,亦即“散而为太虚”之“不得已而然”的过程。此一由无形而有形,又由有形而无形之出入变化,并不是无中生有及有归于无。因为不管如何变化,气之常体恒在不失,此乃“有无混一之常”。由于“气能一有无”,故此“无”非“一无所有”,而是“气本之虚”的原初状态者。太虚无形与物有形象相对而言,二者的关系可以表示为“幽明”或“隐显”。为“幽”为“隐”,乃指气之散而为太虚或虚空之本然状态;为“明”为“显”,乃指气之聚为万物之客形。依此,宇宙生化的过程不过是此“一气二态”的“幽明”之变化,“气一元论”之说当可成立。
至于“清浊转化”之说,以下五项值得注意:
(7)散殊而可象为气,清通而不可象为神。②张载:《张载集》,章锡琛点校,第7页。
(8)气坱然太虚,升降飞扬,未尝止息。……浮而上者阳之清,降而下者阴之浊。③张载:《张载集》,章锡琛点校,第10、244页。
(9)太虚为清,清则无碍,无碍故神;反清为浊,浊则碍,碍则形。④张载:《张载集》,章锡琛点校,第9页。
(10)凡气清则通,昏则壅,清极则神。⑤张载:《张载集》,章锡琛点校,第9、201页。
(11)两体者,虚实也,动静也,聚散也,清浊也,其究一而已。⑥张载:《张载集》,章锡琛点校,第9、233页。
张载认为气之一物可有两种体现方式,即所谓“虚实”、“动静”、“聚散”及“清浊”等“两体”或“二端”。以“清浊”而言,由清虚之神转化为浊碍之形,张载并不认为这是二物之生成关系,而是一物之二态的转化。既然阴阳属气,清浊亦当就气言,而清浊之转化或反清为浊的过程便只能理解为一气二态之转,而不可能表示二物之变,因此,张载有关清浊二端的关系之说法亦有助于“气一元论”的诠释。
张载的“水冰凝释”之喻更是“一气二态”的具体说明。他说:
(12)气之聚散于太虚,犹冰凝释于水。知太虚即气,则无无。①张载:《张载集》,章锡琛点校,第10、200页。
(13)海水凝则冰,浮则沤,然冰之才,沤之性,其存其亡,海不得而与焉。推是足以究死生之说。②张载:《张载集》,章锡琛点校,第19页。
如果源自太虚之气的聚散过程犹如水与冰的凝释关系,或如海水之凝为冰,浮则沤的关系,则“一气二态”或“一物二性”之说当可成立,而对张载的宇宙本体论作“气一元论”的诠释亦属恰切。
至于张载对佛老二家“有无”之说的批评,可进一步印证上述“气一元论”的诠释。他说:
(14)彼语寂灭者往而不反,徇生执有者物而不化,二者虽有间矣,以言乎失道则均焉。③张载:《张载集》,章锡琛点校,第7页。
(15)若谓虚能生气,则虚无穷,气有限,体用殊绝,入老氏“有生于无”自然之论,不识有无混一之常。若谓万象为太虚中所见之物,则物与虚不相资,形自形,性自性,形性、天人不相待而有,陷于浮屠以山河大地为见病之说。此道不明,正由懵者略知体虚空为性,不知本天道为用,反以人见之小因缘天地。明有不尽,则诬世界乾坤为幻化。幽明不能举其要,遂躐等妄意而然。不悟一阴一阳范围天地、通乎昼夜、三极大中之矩,遂使儒、佛、老、庄混然一涂。语天道性命者,不罔于恍惚梦幻,则定以“有生于无”,为穷高极微之论。入德之途,不知择术而求,多见其蔽于诐而陷于淫矣。①张载:《张载集》,章锡琛点校,第10页。
张载批评“徇生执有者物而不化”,乃是针对道家及道教的“长生”之说;他批评“虚能生气”或“有生于无”,则是针对老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之说。前说之谬乃在肯定有物可恒存而不受气化所影响;而后说之误则在以虚无之道体可有生化之作用。由于“天行何尝有息?”亦即由太虚至万物之气化的往反过程是不会停息的,且是“不得已而然”的,故张载不可能接受“物而不化”的观点。又由于“太虚不能无气”,“天惟运动一气”,“物虽是实,本自虚来”,及“天地从虚中来”,可见他反对“虚能生气”,主要因为他的“虚”是“即气”的,而道家的“虚”乃是“不识有无混一之常”之虚空性的道体。至于佛家言“寂灭”,以一切法皆空,故万物不过剎那生灭之幻像,可谓“往而不反”。佛家所言之空性并不能作为存在物所以生成的根据,故可谓“物与虚不相资”,“形与性不相待”。要与佛、道二家之“虚”区别开来,张载强调他的“虚”乃是“至虚之实”,是“本天道为用”的,亦即是不离气化者。此即所谓“神,天德;化,天道。德,其体;道,其用。一于气而已。”②张载:《张载集》,章锡琛点校,第15页。由此可见,张载的“太虚”或“虚空”不可能被理解为道家的虚无性的道体,或佛家的虚空性的法性。而唯一有助于析别的合理解释,便是以“太虚”或“虚空”为“气之本然状态”,而非“气之外的另一实体”。
二、“理气二元论”的论据
以“理气二元论”或“理本体论”来解释张载的宇宙本体论,也是言之有据的。其论据可分四方面言之,分别是“虚与神之性为气所固有”之说,“神待形然后着”之说,“神一天下之动”之说,及“长在不死”或“无动摇”之说。兹分别论析如次。
张载认为与物不同的道可有不同的称谓:“语其推行故曰‘道’,语其不测故曰‘神’,语其生生故曰‘易’,其实一物,指事[而]异名尔。”③张载:《张载集》,章锡琛点校,第65—66、184页。此外,他又说“理义即是天道也”①张载:《张载集》,章锡琛点校,第234页。 张载:《张载集》,章锡琛点校,第16、205页。,“天道即性也”②张载:《张载集》,章锡琛点校,第234页。 张载:《张载集》,章锡琛点校,第18、197页。,并以“神”、“虚”及“理”为“天德”③张载: 《张载集》,章锡琛点校,第15、131、269页。,可知他使用的“道”、“理”、“性”、“易”、“虚”及“神”等词乃是就不同面相来指涉同一事物。这一系列的名词都似有“超越体性”而非“物质属性”的含义,而似不太可能只作“气之本然状态”来理解。最明显的证据是张载以“虚与神之性为气所固有”之说。他说:“气之性本虚而神,则神与性乃气所固有,此鬼神所以体物而不可遗也。”④张载:《张载集》,章锡琛点校,第63、323页。既然“虚与神之性为气所固有”,“虚与神之性”便不可能是“气”之本身。所谓“至之谓神,以其伸也;反之为鬼,以其归也”⑤张载:《张载集》,章锡琛点校,第7、19页。。此虚与神之性以或伸或归、或往或反之方式体现于万物之中,似乎是一种超越体性。
要进一步证明此“气所固有”之“性”不是一般“物质属性”,而是“超越体性”或“形上实体”,可从张载对形与神之关系的说法入手。他说:“凡天地法象,皆神化之糟粕尔。”⑥张载:《张载集》,章锡琛点校,第19页。“万物形色,神之糟粕。”⑦张载:《张载集》,章锡琛点校,第9页。相对于“糟粕”之“物”而言,“神”的存有地位当更重要,神之存在当更为真实。不过,虚与神是湛一无形、合一不测及莫知其乡的,所谓“神无方”而“易无体”,故必须体现于物中,才能得其征验。因此张载说:“太虚无体,则无以验其迁动于外也。”⑧张载:《张载集》,章锡琛点校,第11页。“凡言神,亦必待形然后着。不得形,神何以见?”⑨张载:《张载集》,章锡琛点校,第208—209页。依此,他明显以无方所、形体限制之神、虚或易等必须借有方所、形体之物(如星体)以征验之、显现之。如是,“虚与神之性”不可能没有“超越体性”的含义。
此外,张载心目中的虚与神之性不仅是事物背后的德性,更且是一大动力。他说:“天下之动,神鼓之也。”①“惟神为能变化,以其一天下之动也。人能知变化之道,其必知神之为也。”②张载:《张载集》,章锡琛点校,第234页。 张载:《张载集》,章锡琛点校,第18、197页。就是人身之成,也是由于天神之功,故曰:“成吾身者,天之神也。不知以性成身,而自谓由身发智,贪天功为己力,吾不知其知也。”①张载:《张载集》,章锡琛点校,第25页。此处“因身发智”正表示物质躯体内在的属性,而“以性成身”与之对比,明显表示物质躯体之外(其上或其后)的动力。张载说;“太虚者,天之实也。万物取足于太虚,人亦出于太虚。太虚者,心之实也。”②张载:《张载集》,章锡琛点校,第324页。可见天地万物及人要“出于太虚”,必先“取足于太虚”。取之若有不足,即动力不够,便无法生化出来。张载一方面说“天地以虚为德”,另一方面又说:“虚者,天地之祖,天地从虚中来。”③张载:《张载集》,章锡琛点校,第326页。明显以虚与神既为天地万物之性,亦为天地万物之祖。此一“祖”字正正表示一种先在的动力,而不可能是气之一态。
对张载来说,有形之物可因气之聚散而有成有毁,有生有灭,但虚与神之性则是“长在不死”、“无动摇”者。他说:“道德性命是长在不死之物也。己身则死,此则常在。”④张载:《张载集》,章锡琛点校,第273页。又说:“天地之道无非以至虚为实。……凡有形之物即易坏,惟太虚无动摇,故为至实。”⑤张载:《张载集》,章锡琛点校,第325页。既然有形之物皆易坏,而虚与神之性或道德性命之物不因有形之物的毁坏而消亡或动摇,将这种虚德或神性理解为具有超越或形上意义的实体,无疑是顺理成章的。总结来说,张载以气、物为有聚散、生灭相者,而虚、神为常在、至实者,则以“理气二元论”或“理本体论”来解释他的宇宙本体论,亦是相当合理的。
三、程朱的评论
程朱对张载学说之批评乃是众所周知的,但鲜有人注意其中若干批评的要点,对理解张载学说实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二程虽盛赞《西铭》,对《正蒙》其余各篇却甚有意见。例如:“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若如或者以清、虚、一、大为天道,则乃以器言,而非道也。”⑥程颢、程颐:《二程集》,王孝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18页。“子厚以清、虚、一、大名天道,是以器言,非形而上者。”⑦程颢、程颐:《二程集》,王孝鱼点校,第1174页。“(横渠)立清、虚、一、大为万物之原,恐未安。须兼清浊虚实乃可言神。道体物不遗,不应有方所。”①程颢、程颐:《二程集》,王孝鱼点校,第21页。按张载以清通而不可象之“神”与湛一无形之“虚”形容天道,乃明显不过者;至其言“一”与“大”,也许是根据张载所谓“神无方,易无体,大且一而已尔”②张载:《张载集》,章锡琛点校,第15页。之说。牟宗三先生对二程的批评不以为然,他说:“横渠诚有滞辞,然其实意却并不是以太虚神体为器(气),为形而下者。直谓其‘以器言’,非是。又据横渠‘兼体不累以存神’之义说,横渠正是‘兼清浊虚实’以言神者,神并非是单独属于清也,亦非是以神为清气之质性,以气说神也。明道于此,未能尽其实。此种误会亦由于横渠简别不精而然。”③牟宗三:《心体与性体》第一册,台北:正中书局,1989年,第419页。从“道则兼体而无累”言,道或(虚与神之)性当不限于阳之清,而亦兼阴之浊,牟先生对二程的反驳似不无道理。但张载既以“太虚为清,清则无碍,无碍故神;反清为浊,浊则碍,碍则形。”④张载:《张载集》,章锡琛点校,第9页。又认为“凡气清则通,昏则壅,清极则神。”⑤张载:《张载集》,章锡琛点校,第9、201页。似乎又不太可能不把虚与神之性归属于清而绝于浊。依此,清、浊既就气言,清虚之神亦当就气言,因而是形而下者。个人认为牟先生对二程的反驳并非没有道理,不过二程对张载学说之批评也不是无的放矢的。因此,说横渠“简别不精”是对的,说明道之说纯属“误会”则颇欠公允。
牟先生认为朱熹对张载学说的理解更差,直是“全不相应”⑥牟宗三:《心体与性体》第一册,第432页。。然而,个人认为朱熹的批评比二程的更为鞭辟入里,实有助于揭示张载宇宙本体论中的真实困境,而非全不相应。朱熹的评语可列示如下:
(16)横渠辟释氏轮回之说,然其说聚散屈伸处。其弊却是大轮回。盖释氏是个个各自轮回,横渠是一发和了,依旧一大轮回。⑦黎靖德编:《朱子语类》,王星贤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537页。
(17)横渠说道,止于形器中拣个好底说耳。谓清为道,则浊之中果非道乎?“客感客形”与“无感无形”未免有两截之病,圣人不如此说,如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又曰:“一阴一阳之谓道”。①黎靖德编:《朱子语类》,王星贤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533页。
(18)横渠“清、虚、一、大”却是偏。他后来又要兼清浊虚实言,然皆是形而下,盖此理则清浊虚实皆在其中。②黎靖德编:《朱子语类》,王星贤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539页。
(19)问:“横渠‘清、虚、一、大’恐入空去否?”曰:“也不是入空,他都向一边了。这道德本平正,清也有是理,浊也有是理,虚也有是理,实也有是理,皆此之所为也。他说成这一边有,那一边无,要将这一边去管那一边。”③黎靖德编:《朱子语类》,王星贤点校,第2539页。
(20)问:“横渠有‘清、虚、一、大’之说,又要兼清浊虚实。”曰:“渠初云‘清、虚、一、大’,为伊川诘难,乃云‘清兼浊,虚兼实,一兼二,大兼小’。渠本要说形而上,反成形而下,最是于此处不分明。如《参两》云:以参为阳,两为阴,阳有太极,阴无太极。他要强索精思,必得于己,而其差如此。”又问:“横渠云:‘太虚即气’,乃是指理为虚,似非形而下。”曰:“纵指理为虚,亦如何夹气作一处?”④黎靖德编:《朱子语类》,王星贤点校,第2538页。
朱熹所谓“一大轮回”,正是针对张载的“形聚为物,形溃反原”,由太虚至万物之间的气化之出入过程。此一由太虚至万物,复由万物反至太虚之过程,乃是一种变化的循环,朱熹概括之为“一大轮回”,实不为过。至于朱熹反对以“清、虚、一、大言“道”言“理”,主要因为他认为“清浊虚实”等皆是就气之二端言,皆属形而下者。凡落在气化现象层面上说的,朱熹都否定有关概念具有“超越实体”或“形上本体”的含义。张载一方面以“清浊”、“虚实”、“动静”、“聚散”等言气之二端,即气之二种状态或活动,另一方面又以清通之神或湛一之虚为道、理或性,而两种“清”、“虚”又似无分别,故朱熹评“横渠说道,止于形器中拣个好底说耳”,即于形器层面上的“清浊”、“虚实”等之中拣个好的“清”、“虚”来说道,实亦公允。况且张载以清、虚的太虚之神一边为理,浊碍成形一边则不是理,既然虚、神之理是“充塞无间”的,也体现在浊碍成形之物中,这岂非是“要将这一边去管那一边”?朱熹反对以清的一边去管浊的一边,正因为他认为“清浊虚实”等皆就气言,而天理乃是遍在的,体物而不遗的,可体现于气的任何状态或活动中,因此作为气之一态的清与虚是不可能被视为天理的。依照朱熹的看法,即使张载后来主张“清、虚、一、大”是“兼清浊虚实”言的,但由于前后之“清”、“虚”实无差异,尽管他本意可能以前者为形而上者,却不免说成形而下者。朱熹以上的批评不只显示张载之说“简别不精”,似乎更可说是“思想混淆”。然而,此一混淆之产生也许不是偶然的,而朱熹的批评正可以引导我们去寻找一个合理的解释。
四、宇宙生化论与形上本体论之混漫
顺着程朱的思路,我们可以找到更多的证据来证明张载的宇宙本体论有“混淆”或“混漫”之处。由上述的分析可知,太虚之神若作为气之本然状态及反原之所在,是不可能同时又作为万物之体性或德性的,更不可能具有形上本体或超越实体的含义。除非“清”、“虚”等词可有二义,否则此一混漫将使张载的学说陷入无法自拔的理论困境之中。
事实上,张载的“清”、“虚”等词之用法并无二义,只是他在迁就气化与体性二种不同的角色时不自觉地引出互相刺谬的种种说法来。例如他对“湛一”或“湛然”之表述便有不协之处。他一方面说:“气本之虚,则湛一无形,感而生则聚而有象。”①张载:《张载集》,章锡琛点校,第10页。明显以湛一之虚本身是无形无象的;可是在另一方面又说:“苟健、顺、动、止、浩然、湛然之得言,皆可名之象尔。然则象若非气,指何为象?时若非象,指何为时?”②张载:《张载集》,章锡琛点校,第16、219页。及“若以耳目所及求理,则安得尽!如言寂然、湛然亦须有此象。有气方有象,虽未形,不害象在其中。”③张载:《张载集》,章锡琛点校,第231页。则又以寂然、湛然之虚为有象有气者。视湛一之虚为无形无象,自可与“超越体性”之说相配合;但视之为有象有气,便明显与超越或形上的解释背道而驰。
其次,张载对于“寂然之静”与“湛然之虚”的说法也有混淆不清之处。例如他一方面说:太虚之“至静无感,性之渊源”④张载:《张载集》,章锡琛点校,第7页。;另一方面又说“无所不感者,虚也”①张载:《张载集》,章锡琛点校,第63页。。再者,依他的“一物两体”说,他主张以虚实、清浊、动静及聚散等为气之二端或两体;可是在另一方面,他却认为“至虚之实,实而不固;至静之动,动而不穷。实而不固,则一而散;动而不穷,故往且来”②张载:《张载集》,章锡琛点校,第64页。,“静者善之本,虚者静之本。静犹对动,虚则至一”③张载:《张载集》,章锡琛点校,第32页。,及“天行何尝有息?正以静,有何期程?此动是静中之动,静中之动,动而不穷,又有甚首尾起灭?自有天地以来以迄于今,盖为静而动”④张载:《张载集》,章锡琛点校,第113页。。似乎又在二端或两体之外或之上,另立一“至虚”、“至静”或“至一”之体或本,以为天行、物化之所依的体性。依气之二端或两体之说,虚与实对,静与动反,二端不可能兼容,只能一阴一阳地起伏往反,必须在一“首尾起灭”的“期程”中发生。亦即必须肯定有生灭相、时空相,才能说明二端在气化或物化过程中之辩证的相续关系和作用。然而,若依其“至虚”、“至静”或“至一”之说,上述的对待关系便消失了。此时的虚不与实对,故可说“至虚之实”;静亦不与动反,故可说“静中之动”。这种“至虚”、“至静”或“至一”的东西是贯彻在一切活动之中的,其本身当然不可能“首尾起灭”的“期程”,亦即不可能有生灭相、时空相的。如是,此“至虚”、“至静”或“至一”者似有超越实体或形上本体的涵义,明显与二端或两体之中的“虚”、“静”不同。但是,张载既以此至虚、至静之太虚为气化或物化之出入、往反过程中的起点与终点,并据此以评定佛家“往而不反”与道家“物而不化”二说之不当,则此至虚、至静之太虚又似乎不太可能不是二端或两体之一,似乎不太可能是另有超越体性的含义。
最后,张载的“一物两体”与“形而上”的说法也是大有问题的。他一方面说:“一物两体,气也”⑤张载:《张载集》,章锡琛点校,第10页。,及“气能一有无”;⑥张载:《张载集》,章锡琛点校,第207页。另一方面又说:“一物而两体,其太极之谓与”⑦张载:《张载集》,章锡琛点校,第48、231页。,及“有无虚实通为一物者,性也”。⑧张载:《张载集》,章锡琛点校,第63页。这似乎混淆了形而下的气与形而上的太极之分际。无怪乎他有时会说:“阴阳,气也,而谓之天。”⑨张载:《张载集》,章锡琛点校,第48页。及在“阴阳者,天之气也”下自注云:“亦可谓道”等,这不是把形而下的气与形而上的天或道搅混了吗?事实上,张载所谓“形而上”者也没有程朱“超越体性”的涵义,而只就“无形迹”者言。例如他说:“运于无形之谓道,形而下者不足以言之。”①张载:《张载集》,章锡琛点校,第207页。“形而上者是无形体者,故形而上者谓之道也;形而下者是有形体者,故形而下者谓之器。无形迹者即道也,如大德敦化也;有形迹者即器也,见于事实即礼义是也。”②张载:《张载集》,章锡琛点校,第207页。及“凡不形以上者,皆谓之道,惟是有无相接与形不形处知之为难。”③张载:《张载集》,章锡琛点校,第207页。可见他是以“无形迹”来界定“形而上”的。但是,由于“气聚则离明得施而有形,气不聚则离明不得施而无形。方其聚也,安得不谓之有?方其散也,安得遽谓之无?”④张载:《张载集》,章锡琛点校,第8、182页。可知“无形”只是“气不聚”以至“离明不得施”的后果,并非预设“超越的体性”。张载又认为“形而上者,得意斯得名,得名斯得象;不得名,非得象者也。故语道至于不能象,则名言亡矣。”⑤张载:《张载集》,章锡琛点校,第15页。“凡可状,皆有也;凡有,皆象也;凡象,皆气也。”⑥张载:《张载集》,章锡琛点校,第63、323页。及“形而上者,得辞斯得象,但于不形中得以措辞者,已是得象可状也。”⑦张载:《张载集》,章锡琛点校,第231页。凡此皆明显以“形而上者”为“于不形中得象可状”也。既然可状之象皆属气,此岂非以形而上者属气?即使属气之“形而上者”是至为清通、虚灵的,对程朱理学来说,仍不免是形而下者。
张载的思想混漫其实可以从他的一段语录中充份反映出来。他说:“天地以虚为德,至善者虚也。虚者天地之祖,天地从虚中来。”⑧张载:《张载集》,章锡琛点校,第326页。这段话看似无大问题,其实正可透示出张载思想混漫的原因,更可以引领我们认识到绝大多数宋明理学家或多或少都触犯的一个共同毛病,此即宇宙论(宇宙生化论或宇宙本根论)与本体论(存有论或形上学)混而为一的病痛。我们知道,哲学上的宇宙论乃是探究宇宙万物生成变化之要素、根源或第一因等问题的学问,这必然涉及事物生成变化的过程,必须落在一个时空系列上来理解。但本体论则是探讨存在物之所以存在所必须预设的非经验性的条件,或现象背后的本质或本体的学问,这样的本质或本体并不涉及具体事物的发生过程,不会受到时空条件的限制。倘若这种本质或本体是独立于经验世界而自存者,具有超越的性格,那便不可能具有生灭相和时空性的。因此,对于一种具有超越性格的形上本体论来说,有关的本体或实体概念是逻辑地不可能用作宇宙生化论中有关生化项目的概念。换言之,超越时空而不生不灭的本体或实体不可能同时又是在时空中有生灭变化的本根元素。以张载来说,他把有时空性的宇宙气化论与超越时空的形上本体论混而为一,可谓格格不入。所谓“宇宙本体论”,就此一意义区分而言,乃是一种不通的说法。因为凡在生化过程中的,便不是本体;凡是本体的,便不在生化过程中。张载一方面以虚为天地之德(性)或体(性),另一方面又以之为天地之祖,以天地万物从虚中来,二说可谓南辕北辙,不相协合。因为同一“虚”概念不可能既表示形上本体论的德性或体性,又表示宇宙生化论的生化起点。前者是没有“首尾起灭”的“期程”的,但后者却不可能不落在生化的过程上来理解。
个人认为,张载为针对佛道二家蹈空游虚之论,乃强调实然的气化层面以对治之,遂不免有气化自然主义的倾向。但是,二程当时提出的批评不可能对他没有影响。伊川虽否认吕大临所谓“尽弃其学而学焉”之说,实质上受二程的影响而使张载有所徘徊于形上与形下之间乃不可避免者。其实,这种宇宙论与本体论的混漫,其来有自,并非张载独有的问题。至少从《老子》和《易传》开始,便已开启此一混漫之风。《老子》一方面言“道生之”,另一方面言“德畜之”;《易传》一方面“太极生两仪”,另一方面言“体物而不遗”,都有以同一概念用作宇宙生化起点和遍在的体性或德性二义。然而,此二义于此是不能兼容的。张载的“太虚”虽被程朱斥为形而下者,但他们自家所谓形而上的“天理”又何尝不被他们理解为生两仪四象的太极,为生化过程的起点?程朱与张载,实五十步与百步之间矣!张载的“太虚之气”便于说宇宙生化论,却难以融入形上本体论。相反的,程朱的“太极之理”便于说形上本体论,却难以配合宇宙生化论。无论张载与程朱,都希望建立一套综合宇宙生化论与形上本体论而成为“宇宙本体论”的学说,可惜他们都并不成功,而且是不可能成功,理由是二者逻辑地不可协合之故。张载明显的思想混漫与其他宋明理学家隐晦的思想混漫其实是建基在同一错误的思考模式之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