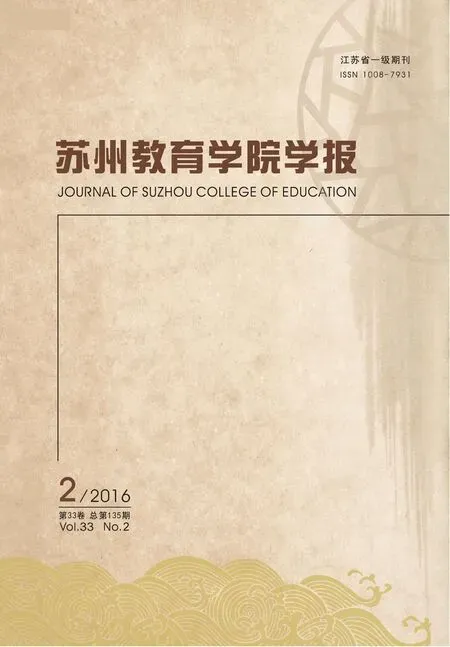有关司马中原的评论综述
郑明(东吴大学 人文社会学院,台湾 台北 10084)
有关司马中原的评论综述
摘 要:自1949年迄今,评论司马中原的文章有二百多篇,重要的评论集中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大部分评论又集中于他的小说,尤其是他的代表作《荒原》与《狂风沙》。评论者可以分为“作家型”与“学者型”两种:作家时常用很感性的笔触来抒发阅读后的感想,笔下带着感情,时常闪现精辟见解,有时又结合司马中原本人一起讨论,对于认识作家与作品,是非常重要的参考资料;至于学者的论述,一般比较理性严肃,论述比较严谨,就文论文,上乘之作往往鞭辟入里。司马中原的小说,还有许多评论空间未被发掘,而他独具风格的感性散文,更被评论界忽视,所以,“司马中原”是当代台湾文学研究有待继续开发的领域。
关键词:司马中原;《荒原》;《狂风沙》;感性散文
司马中原,正如他的名字,将像一匹千里名驹驰骋在现代文学大中原的历史里。
是命运和天性共同塑造了司马中原,他自己说:如果生活在承平时代,就会在家乡小镇终老,过一生悠闲平静的日子,恋爱生子、饮茶喝酒,任意挥洒他与生俱来的浪漫与柔情。①参见司马中原:《我的少年时代》,见《月光河》,九歌出版社1982年版;司马中原:《我的写作生活》,见《老爬虫的告白》,九歌出版社2002年版;司马中原:《拾级而登—我投向创作的动机和过程》,见《我的第一步》,时报出版公司1981年版。
偏偏还是个孩子,就遇着战乱,不得不在流离的烽火中加速成长,逼迫他的灵魂面对民族的苦难,焠炼出强烈的忧患意识、深厚的人道精神和铁血英豪的雄壮心志。
天生性情与后天境遇的反差,使得司马中原的创作具有两种相反有时又相成的特色:论阳刚雄浑,他的长篇小说经常气势磅礴如椽笔泼墨;论阴柔唯美,他的抒情散文总是细致妍丽如蜡染拓印。这两种风格时而分离、时而交迭地流荡在他的作品中。②齐邦媛说:“司马中原在《荒原》《狂风沙》和他‘乡野传说’系列的短篇小说中每逢写到乡土,文字立刻变得温柔缠绵,哪怕前一段还在写浴血交锋的场面。”(齐邦媛:《二度漂流的文学》,《联合报》1993年6月26—27日)齐邦媛又说:“三百页的《荒原》里只有三页写歪胡癞儿曾有过的情爱,与妻子在月夜坐在河岸一块石上,‘她从他手里接过孩子,解怀喂奶……’那样温存的夜里,野蛛丝黏黏地把他们牵连在一起。……同书中,贵隆与银花的婚姻,历经现实的种种磨难,不弃不离。贵隆死后,她带着三岁的孤儿火生去上坟,教他认识大火劫后又茁生的树和草,‘初茁的草尖直立着,像一把把嫩绿的小剑,高举在地上朝天宣誓,宣誓它们永不死亡。’在这结尾的一章中,作者一口气写了四页花草树木的名字和生长姿态,我每读都仍感惊讶,一个作家在怎样精力旺盛的年月,看过了,记得了,这些坟墓外充满生机的希望远景,用这样丰富优美,抒情叙事交纠的文字写出苦难这一种结局?”(《百年苍茫中—〈荒原〉〈狂风沙〉再起》,《联合报》2006年5月23日)
现实即便异常残酷,伟大的生命必然会在经年累月的一刀一剜的创痛中,火浴出更强劲的生命力。司马中原之可贵在于:长期面对民族种性不堪的原始面貌,仍然深深宝爱着这个可悯可嫌的民族;即使在最绝望的时候,也不放弃对自己家国的希望,充分印证他生命里拥有高蹈的人文精神、丰沛的能量与爱力。
一
自1949年迄今,评论司马中原的文章颇为零碎,以小说文类评论最多,时间则集中于20世纪70年代以前。
20世纪90年代,两岸开放交流后,恰逢当代文学热兴起,照理司马中原研究应该可以成为显学,可惜,他最具代表性的小说在时代需要下被贴上“反共文学”标签,当然不适合大陆。至于台湾,1970年代以后,本土文学势头极甚,他又很难得到研究者的青睐。
当代台湾特别强调“乡土”,自1970年代迄今,学界讨论司马中原小说,几乎全从怀乡/乡土角度切入,王德威的《乡愁的超越与困境—司马中原与朱西宁的乡土小说》[1]、范铭如的《合纵连横—1960年代台湾小说》[2]都只针对“乡土”一点进行论述,至于齐邦媛的《司马中原笔下震撼山野的哀痛》[3]也用“具象化的乡愁”定调。在特别强调台湾本土文学的时代,似乎不得不把司马中原这一代的小说归类于怀乡的乡土文学才能在台湾文学中占有名分。
把司马中原小说框限在“乡土”文学,已经缩小了检视小说的范围,王德威在《乡愁的超越与困境—司马中原与朱西宁的乡土小说》中就针对《荒原》[4]及《狂风沙》[5]的乡土情结发言。幸好他有延展性的申论:“司马的小说,有强烈的道德使命感。司马将此一道德命题与政治相连锁,终在他的乡土上营造了一复国(或建国)神话;乡土小说绝不止于怀念故土而已;它们间接透露了小说家(及读者)诠释、超拔历史环境的不同叙事手段。”[1]280这一评论使得司马中原的“乡土小说”不只是狭义的怀念故土,而是成为结合了政治/种族/人性的大河小说。
《荒原》结束时,所有的英雄几乎牺牲殆尽,理想其实已经破灭。王德威认为“根植乡土的国家与英雄神话,仍待继续。于此耐人寻味的是,司马中原的故事不再往下发展,反而倒退到更早的‘过去’。他的皇皇巨作《狂风沙》正是北伐前后,淮北盐贩除奸报国的传说为背景。莫非在那更缈远的时代,司马方能召唤出更刻骨铭心的乡愁想象,更动人心魄的英雄事迹?”[1]284-285可说是王德威从乡土角度注释《狂风沙》的创见。
至于王德威说:
《狂风沙》一书最动人的时刻,往往不在于演述人与历史逆境间种种不可测的搏斗,而在于伸张邪不胜正的天理,及英雄人由“衰亡到升扬”的道德境界。尽管关东山的遭遇,已兼具悲剧人物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宿命气息,以及唐吉诃德式的荒谬素质,他最终作为道德典范的意义,要大于一切。[1]286
这种诠释早已超越乡土文学的层次。
老实说,如果放在另外一个时空,司马中原的小说可以和《三国演义》《水浒传》相抗衡,也因当代商业社会多元化、信息社会多变化、台湾社会本土化种种因素,可谓处在天不时、地不利、人不和的环境里,不能不令人唏嘘。①齐邦媛在《二度漂流的文学》中说:“司马中原早期的短篇小说和《荒原》《狂风沙》等,情意深挚引起广大共鸣,也曾给青年作家相当影响。但是他们在这个不幸的政治挂帅的世界,既被贴上‘反共’标签又被责为‘压根儿不认识这块土地(台湾)的历史和人民’,在大陆和台湾的文学史中都找不到有尊严的地位,将只有作1949年辞乡后的第二度漂流了。”(齐邦媛:《二度漂流的文学》,《联合报》1993年6月26—27日)
在评论司马中原的文章中,可以分为作家型与学者型两种评论者②作家型如姜穆、魏子云、张默、吴友诗、宋瑞等,学者型如齐邦媛、王德威、范铭如等。。两者特质不同,作家型评论者大抵用非常感性的笔触来抒发他们阅读的感想,除了笔下时常带着感情,更经常出现创作者才有的敏慧眼光与独到见解。这些作家有些同时也是司马中原的朋友,这便经常可以看到作者边评论司马中原的文章,边印证司马中原的行事为人,当把“文”和“人”结合在一起讨论时,对于认识作家与作品,又是非常珍贵的参考资料。由于感性主导,作家书写评介,结构有时比较宽松,引用原文也偏长,偶尔还会“跑野马”。
至于学者的论述,比较严肃,照理结构应该比较严谨,不过近年许多学院里的师生执迷于某些西方理论,但又不能像王溢嘉之于精神分析学理,既入乎其内,又再出乎其外,从学理中得到一把庖丁解牛的利刃,诠释作品便有独到的新解。故此,有些学院中的学者,虽长篇大论发表论文,内容其实空洞。
二
司马中原在早期长篇小说中就常有难以辨别是邪非邪的乡野传说,到后来出版社主动要求他专攻乡野传奇、灵异故事,故产量颇丰。
作为读者,我们关心的是司马中原用怎样的心态来书写这些乡野传奇?陈义芝在《春风一样悠悠地吹着—司马中原先生专访》中,请教他写作这些乡野传奇是否考虑到文学技巧。司马答说:
我考虑到,而且非常烦恼。比方说,如果我们采用短篇小说那种精炼的结构、形式,多用了一些西洋技巧,那么,传说的韵味就没有了。如果用传说的方式,则又难免冗杂、松懈。可是我最后还是用了后者—像一个老头娓娓说故事的方式那是典型的中国式,题材的本身就必须要用那种方式,不用那种方式就不是传说。[6]
没错,读者如果需要神话传说,那么基本形式是无法改变的。不过,只是书写神话传说,作家也不肯仅仅止于重述故事而已,对于这一部分,王溢嘉在《论司马中原的灵异小说》[7]一文中,有比司马中原的解说更精辟的分类与分析。
王溢嘉从心理分析学、文化学、神话学等角度系列分析多本中国古典小说,又曾分析笔记小说中的灵异作品,把原来被视为通俗读物的志怪小说放在民族/人类的集体意识与集体潜意识中观察,既有历史的纵深,又有人性的广度,附带也谈及艺术手法。
王溢嘉不仅凝视司马中原的小说本身,同时从他的灵异小说看出当代社会的“集体意识”与“集体潜意识”,是格外发人深省的上等论文。
三
高全之曾写有三篇评论司马中原的论文,在1975年他把它们改写成《司马中原英雄的衰亡与升扬》[8]95-123,论点与旧作已大不相同,故后者才是高全之的定论。
文本第一节就宣布:“我们还会列举作者本人对作品的解释,与事实不符的实例。”[8]97高全之从《狂风沙》里的英雄关东山切入,探索书写者与隐藏作者之间或呼应或反差的内涵,非常有意味。
高全之认为,《狂风沙》“在人性刻画上有所选择,划地自限。我们以为,这是作者表现创意的地方。这本书最大的兴趣与成就,在于讨论领导人物的能力限度与道德操守……《狂风沙》的悲剧也许是:人不自知地具有无限伸张的权力意志,而这种权力意志侵害到他人的生存权利”[8]117-118。可谓真知灼见。
高全之认为《狂风沙》里人物大多是扁平人物①司马中原经常有意让他的英雄人物单一化,他在《我的写作生活》(《老爬虫的告白》)中夫子自道:“在众多的题材里面,我特别喜爱勇壮的悲剧……我要高高举起我心目里的英雄们,使‘英雄有颂,勇者留名’。”,以致于人物形象显得单调,同时“《狂风沙》里男人对婚姻的态度有两个不兼容的极端。一方面司马中原对男人维持家庭生计这份传统责任非常执着……另一方面,作者对婚姻避之犹恐不及。关东山正是例子……他没能在婚姻以外寻求异性(心理与生理双方面的)慰藉。这就提供了性压抑的可能”[8]109。
王德威在《乡愁的超越与困境—司马中原与朱西宁的乡土小说》中说:
高全之在他专论司马中原英雄人物的文章中,已为关东山画下谱系。关的形象与地位,正与《三国演义》中的关云长、《水浒传》中的关胜,一脉相承。司马中原受传统说部演义的影响,因此不言自明。作为一“有德”的英雄,关东山令人无可疵议。但正如高文指出,这样完美的形象之后,似乎总欠缺了什么。比如关东山对性及个人欲望的压抑,虽然成全了大我,就有不近“人”情之处。由于司马中原坚持“一种独特的简单的人性体察,一种决不肯深入的自限”。[1]286
高全之认同关东山形象来自《三国演义》关羽与《水浒传》关胜,笔者认为更确切地说,来自传统中国小说/民间的英雄形象,不论《三国演义》中的孔明或关羽,都经过美化成为扁平人物,而王德威同意高全之“关东山对性及个人欲望的压抑”恰恰是《水浒传》中众英雄好汉的共同特质。
高全之特别强调《狂风沙》“拒绝了《三国演义》和《水浒传》认可的异性慰藉”。这里,笔者比较同意孙述宇与之完全相反的看法①孙述宇还说:“好汉不但不可寻花问柳,最好根本不与女性沾上任何关系。对于亡命行动而言,色欲固然有害,家庭也有妨碍。因此,水浒宣传家大力宣扬独身的好处。梁山英雄中最多姿彩的都是独身汉子,像鲁智深、武松、李逵、石秀、杨志、燕青等等,他们闯荡江湖之时无牵无挂……”(孙述宇:《水浒传的来历、心态与艺术》,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0年版,第305页):
(《水浒传》中)做英雄的必要条件之一,就是“不好色”。不能作战取胜,或者不讲义气,固然不是英雄;若是“贪女色”,也“不是好汉的勾当”(宋江评王英之语,在卅二回,页504)。忠义堂上的好汉十九都够得上这个条件。为首的天王晁盖,除了“平生仗义疏财,专爱结识天下好汉”之外,又“最爱刺枪使棒,亦自身壮力健,不娶妻室,终日只是打熬筋骨”。[9]
孙述宇使用相当多的文字不但解释水浒英雄极力排斥女性慰藉,甚至视女性为祸水。同时,表现得最出色的英雄好汉不但是单身不亲女色,而且看不出有任何的性压抑呢。
四
对《荒原》的评论是有关司马中原论述中篇数最多、成绩也最丰富者。其中魏子云发表于1964 年2月《皇冠》的《款步于〈荒原〉内外—兼论司马中原之“新感觉”表现》、吴友诗发表于1964 年4月《新文艺》的《评〈荒原〉》、张默发表于1968年10月《新文艺》的《从荒野出发—试论司马中原的〈荒原〉》等文章,皆是有力之作,同时也说明1960年代是司马中原的《荒原》开始受到文坛充分肯定的时代。
由于台湾当时的政治氛围,《荒原》被归类为“反共小说”,事实上,整本小说只说到八路军与“老中央”,作者对八路军与“老中央”都有批有评。司马中原在1963年致李英豪的信中说明了他的立场:
多少年来,中国的动乱,民族的流离,我是身受者;但中国的农民们的痛苦比我们更深,我写《荒原》一书,实际上,是在为全中国的农民说话,我本身就是那样的农民,我认为(并不全部肯定的),这世界任何个体,都有权保有它内在的心灵世界,谁要摧毁这个世界,它将被判定为暴力。所以,与其说我反共,不如说,我反对一切暴力。[10]
这就是张默说“《荒原》的确是一座熠熠生辉的多面结晶体,它有一个中心思想为其紧紧束系着。这个中心思想,就是一切暴力都是必须摧毁的”[10]。张默认为全书结局象征作者对中国农民的感情与寄望:“作者在结局时,拉出贵隆放了一把空前的大火,烧了三天三夜,把所有的匪徒所有的劫难都烧死了,偌大的荒原只剩下银花和火生(贵隆的遗腹子),看来的确是够悲壮苍凉的。那个火生就是作者特别塑造的人物,他是红草荒原唯一新生的火种,整个民族生存延续的象征,只要有一个人在,他们一定要不屈不挠地生活下去,不断地抗争下去。”[10]确然饶富意义。
大荒发表于1974年10月《中华文艺》的《三度空间—谈司马中原》,最能代表作家以感性之笔夹叙夹议的文章,内有两人可贵的私交,也有许多智性的评点,例如他说司马中原“处处都洋溢着诗的情调和气氛”,举例之后说:“我想这是司马中原心的底层的声音,哀而不伤,凄而不厉,以空空灵灵的文字托出委委婉婉的情感,真是感人至深。若无诗人情怀,何能臻此?”[11]
大荒此文主要在介绍司马中原各种作品,文末似乎急着收尾,因而有点仓促。
五
齐邦媛共有四篇文章②发表时间依序是:《司马中原笔下震撼山野的哀痛》1973年8月发表于《中外文学》,此文后收入作者《千年之泪》书中,易名为:《震撼山野的哀痛—司马中原〈荒原〉》;《抬轿走出〈狂风沙〉》1990年3月5日发表于《联合报》;《二度漂流的文学》1993年6月26—27日发表于《联合报》;《百年苍茫中〈荒原〉〈狂风沙〉再起》2006年5月23日发表于《联合报》。谈论司马中原,是司马的重要知音。
《司马中原笔下震撼山野的哀痛》[3]—该文后收入作者《千年之泪》书中,题目改为《震撼山野的哀痛—司马中原〈荒原〉》,副标题虽明言评《荒原》,但论文内容几乎是全面性地综论司马中原全部作品—还延伸到其他作家。文中,齐邦媛把司马中原重要作品按主题和表现形式分为三类:史诗性的、纯抒情的、乡野传闻的。《荒原》自然属于第一类,《狂风沙》则被她归在“乡野传闻”中①有些论者把《狂风沙》跟《荒原》放在一类。。
齐邦媛特别提出《荒原》和《狼烟》并列为史诗性作品的代表,她说:
史诗性的小说是司马中原以山河恋为经,以30年前抗日剿匪的战争为纬,衬托出人性正邪之争的作品。这些经验由他的笔尖给予读者“一种悲愤的敲击,揭露出东方古老大地上人们艰困的生存状貌”,而“深深体会到他们如何在现实悲剧之上,建立起肯定的生存的价值观”。(见《荒原》《再版前记》)这一类作品以《荒原》和今年4月中旬才在《中国时报》“人间”版连载完稿的《狼烟》为代表。若把他这两本书的书名联缀起来成为“荒原狼烟”,可见贯穿他20年写作生涯的是一首激情汹涌的民族苦难而不屈服的史诗。[3]
这些创见可谓掷地有声。齐邦媛同时把司马中原和外国作家、中国现当代作家评比,且下论断,例如:
无可置疑的这本《荒原》和姜贵的《旋风》,乃至纪刚的《滚滚辽河》都将会在中国文学史上代表我们这奇特而可贵的时代,它们都以雄浑的笔触写我们国土上刚刚发生的苦难,和一些可敬的灵魂在国家和个人的苦难中不屈的奋斗。[3]
诸如此类文字,俨然是以文学史家的立场发言,厚重而深刻。
发表于1990年的《抬轿走出〈狂风沙〉》[12],用感性之笔、散文化方式,从台湾当时的选举文化到中国传统轿子的象征意义切入《狂风沙》的主题,结尾再回到台湾当时的政治/文化现象。此一解读角度可谓别开生面,极具创见,文中说:
司马中原用二十页篇幅写轿饰与抬轿,可说是一种文字的炫耀,创造了狂风沙中仅有的欢乐景象。自此之后,就全是血腥杀伐,隔离、出卖、陷害,荒草枯树了。而在这二十页中,竟从无一字说到轿上供奉的神明?它们会是空轿么?……[12]
可谓齐邦媛极佳的发现,由此而引申出:
《狂风沙》一书百万字可以说是建筑在神轿的意象之上的。轿中供奉的是忠义双全的关公现代版—关八爷。……在军阀暴政的狂风沙中,这些厄运的基层人奉有德的英雄如神明,将他供奉在万人仰望的轿中,希望能抬着这样的轿子走出狂风沙,走进太平岁月。这位英雄不仅智勇过人,而且仁厚无私,他恨残暴,反淫邪,为了忠义,舍身忘己……[12]
司马中原在小说中塑造的救世英雄含有很多传说成分,这完全来自中国的传统文化,历史上只要昏君执政必然出现知识分子的“诸葛亮情结”,此所以《三国演义》过度美化孔明与刘备如鱼得水的情分。乱世中的平民百姓就只有寄托不世出的英雄豪杰,此所以《水浒传》有一百零八位好汉因官逼而民反。齐邦媛说《狂风沙》“生动地重现了20世纪初期中国人的困境、期待与失望”。
确然,不论是《狂风沙》还是《荒原》都是充满无力感的大悲剧,救世英雄只存在于传说甚至幻象中,从古至今的现实世界里并不曾出现,可是,卑微的人民从来没有放弃这种向往。
齐邦媛在《百年苍茫中〈荒原〉〈狂风沙〉再起》中说得好:“(司马中原)笔下创造这些略带夸张性的侠义汉子,一则在希望与想象中抵挡绝望,再则作为集体忧伤的补偿。”[13]
齐邦媛对司马作品的分析、字里行间的精彩论断,经常让人击节赞叹,可惜她的论述面时常过于广泛,讨论的文本不够多也不够仔细,实在遗憾。但仅仅阅读齐邦媛这些文章,就知她是研究司马的上等人选。
六
李英豪是通盘评论司马中原不可或缺的人物。虽然只写过一篇评论司马中原的论文:1964年撰写的《试论司马中原》[14]58-92,但他是最早全面讨论司马中原小说的人。
《试论司马中原》综论司马中原1964年之前发表的小说,被认为是香港/台湾现代主义引进者的李英豪,把司马中原跟中、西,尤其是西方作家评比,否定司马中原是一位现代主义者,并断言“司马中原在表现论上,是一个稳实求进的‘新写实主义者’”[14]72,真是饶富意味!
李英豪在论文一开始,就断言司马中原的小说“显示了浓烈的民族悲剧感”![14]58“从长篇《荒原》到短篇《加拉猛之墓》,从《加拉猛之墓》到《灵语》,从古老社会承平的理想到人们倔强默忍地接受不断的悲剧,都无不包含着中国这个民族的无数苦难与隐秘欲望。……司马中原的成功不在其说故事的本领,而在于其对无数生存情境的显露,在于个人对这个民族最原始真诚的情感;这种种显露与情感仍未足构成一个小说家的伟大,他的伟大更有赖于文体和语言上个人的表现力;或者说,更有赖于表现力与意想所融浑成的整体。”[14]59论文一开篇就句句铿锵,让人击节称叹!而后文对司马中原如何统纳、理解、同情、表现整个民族的脉搏有更深入的诠释。
李英豪指出司马中原悲剧作品的积极意义:“小说的价值也就不在迷乱处失落,而在‘穿过悲剧再无悲剧’的生命的肯定。写草原上的野蛮,写抗暴时的勇敢,写童騃中的希冀……都无非是在增强这种生之肯定价值。”[14]85
李英豪的大胆模拟,更是超出新批评的眼界,他指出司马中原小说的文体和语言“都是诗的,以呈现内心的原貌”[14]73。把司马的小说和穆木天的诗和陆蠡如诗般的散文《囚绿记》模拟,给予司马中原“诗小说”[14]73之名,可谓视域独特!
另外,他认为司马中原的长篇、中篇和部分短篇,又接近“史”。总结来说:司马中原“在历史客体现实的系列上,架构他主观人道的诗的秩序。因而一方面是史的写实,一方面是诗的象征与暗喻”[14]73-74。《荒原》正是一部典型的“史诗”小说。李英豪诠释司马中原众小说如何同时结合“诗”和“史”时,可谓举证历历。
至于司马中原的文体、语言、经验三者的连锁关系以及写作技巧等,都要言不烦,分析得丝丝入扣。
七
司马中原有十多本散文创作,在当代亦有戛戛独造之处,值得研究。可惜,台湾讨论司马中原散文的篇章极少。
1996年1月大陆学者刘正伟在《野味—司马中原的散文》中认为“司马中原的散文,迎面扑来的是一股浓郁的野味……他的散文里通俗的意蕴、朴素的乡野价值观,渊博而鲜活的乡土民俗知识,独特的民间文学视角,构成一种特殊的审美风味:野味”[15]。
这种观点,笔者并不同意。不过,作品本来就是一个开放的文本,让读者“百家齐放”地阅读。笔者并不完全否定他诠释司马中原散文的野味主要来自三个方面:“取材俗,人情真,结构随意。”[15]而且,刘氏的说法,增加了更多讨论空间。
刘氏说:“拈出一个俗字,说他的散文,当然是想与所谓雅的散文相区别的。”[15]实际上,笔者认为司马中原虽选择乡野题材,但文笔典雅、情感丰厚,而技巧也有很多可圈可点之处。
刘氏此文把司马中原的散文归为三类:一类是叙事写景,歌颂亲情、友情,怀人感事的;一类是象征散文;一类是杂感。
宋瑞的《从〈月光河〉看司马中原》[16]最能代表早期作家书写评论的风格,也就是,以随笔的方式书写读后感式的批评。
宋瑞此文虽然不长,可是出现相当多精彩的评语,例如说司马中原的散文之笔“亮丽奇拔”,“佩服他的却是思想的层次”,“以其如椽之笔去勾画他生命中的梦痕,描摹其记忆中的涟漪时,便历历如绘,好像长江大河……”,“(他)把生命当作一本大剪贴簿的数据,将美好的事物给剪存下来,于是,在夜深人静之际,他一个人独坐于孤灯之下翻阅这本记忆的剪贴簿,把心灵沉浸在梦痕中,去品味由过往的日子酿成的佳酿,那丝丝的流散的记忆的脉络,便从心田的纺织机上条理明晰地编织成匹匹的锦绣文章”[16],诸如此类,纯粹是由作家的感性之笔写出的真情实感,让人动容。
也因为是作家随笔的路数,接着宋瑞突然笔锋一转,大谈他读小说《荒原》的历程感想等,实在有点突兀。等到谈过瘾了,再转回来:“在他小说之外读到的他的散文,韵味隽永,节奏有如诗篇,我又觉得他亦是一个诗人的材料。”[16]回来谈散文,但居然又跳回《荒原》,既而就结束,让人觉得文章还没有写完,尤其好像还没开始好好谈题目中的《月光河》呢!即使这样,仍然不能掩盖宋瑞文章的可贵之处,尤其他的论点和刘正伟成为对比,是饶富意味的事情。
司马中原最可玩赏的是感性散文,这是他最贴心的文类,苍凉凄美与深情浪漫几乎是司马中原抒情散文的底纹。铺陈其上的则是婉转如珠、浏亮如玉的语言(正如宋瑞说的“亮丽奇拔”)。阅读司马中原典型的抒情散文,不论是视觉、触觉与整个心灵上都有抚触墨绿绸缎般极为细致温润的感觉,让人很难想象他同是书写《狂风沙》里关八爷的作者。
司马中原的抒情散文时常出现两种人物;一种是绝美而柔弱、通晓诗书事理的薄命红颜,可说是他小说《绿杨村》[17]中三姊妹造型的延伸,也是他心目中挥之不去的女性原型;另一种是司马中原亲身经历的苦难时代常有的流浪汉,苍苍凉凉走过乱世,永远没有根,怀抱着对于逝去事物的无限惆怅,这种人物,在司马的小说中,往往扩展成侠客、路客,在仗义拔刀之外共同具备的感性身世。
像《绿杨村》这样的小说,几乎都用他抒情散文的优美文字来铺陈,光是那篇序文,读了就让人回肠荡气呢。
刘正伟说司马中原散文中有一类是“象征散文”,可惜刘氏没有展开来论述。
笔者认为被许多人当作小说的《黎明列车》[18]应该是诗/散文/小说的中间文类。它缺乏小说的故事、情节、冲突与纠葛,也没有小说的对话,全篇只是主角的内心独白。所以,把它当作散文并无不妥,同时也是象征散文,运用大量的象征与意象,使它又像诗。
《黎明列车》的主题是:在战乱中,男女两人相遇四次,男主角渴望跟她结交/恋爱/结婚,竟然两人从未交谈一语,造成有缘无份的遗憾。极简单的一种感情,却写得摇曳生姿,动人无比。
《黎明列车》的题目就是两个象征符号:黎明原来象征希望与光明转眼将至,在此同时也暗示刚刚才摆脱黑暗,想要追求新希望。至于列车,是全篇最重要的象征。火车前进,如人生不得不往前行。而火车是人造的,按照时间开停,一站一站地走,有起站,有终点,永远规律地走着。正常的人生也像列车一样,有约定俗成的轨道,走着它应有的规律:儿童时快乐、青春期风华、中年时奋斗、壮年已有成、晚年可安享。然而,命运的列车打乱应有的步调,战争列车把人生带到生死一瞬间的惨境,主角无法掌控自己生命的列车……更甚者,搭到不幸时代的列车,则无法按照常规行驶。本文用风象征时代:时代的狂风把人搭上战乱的列车,人只能接受命运的摆布。
此外,花,象征爱情,文章中单字“花”字出现19次(未包括花的名字,如“剑兰”等,及花圃、花朵等复字,否则更多)。
花园,象征有夫有妻的家,全篇出现12次。花开代表爱情成熟,故花都绽放了就成为花园,花园象征家庭。
其余如黑夜、雾、风景、鹰、燕、蛾、新婚夫妇、梦蝶、鸽、露水等等都是饱含意义的象征符号。
司马中原寓言体的散文也是可圈可点,值得再三玩味。他个人的身世,时常不知不觉流露其中,例如《黑陶》[19]300-301这种看似咏物的小品就是代表之一。
《黑陶》用第一人称描写一具中国乡下民间家常使用的物品“黑陶”:“我总是那几种乡野习见的形式,经乡野心灵捏塑,使我具有质朴、愚拙、鲁钝的外表。”[19]300完全应了刘正伟说的“取材俗”。
黑陶是“几乎觅不着任何文明的装饰,我恒赤裸,我的颜色原出自火烧的泥土。笨拙的方形连锁回纹,是我的束带,一茎芽,数片叶,就是我生命的基形”[19]300。用乡野的泥土为原料,由乡野的天然艺术家塑造而成,长得简单质朴甚至笨拙鲁钝,读者明显可以看出黑陶最大特色是“土气”,土气是远离文明的。
被比拟成人的黑陶,有他的个性,有鲜明的好恶:他喜欢乡野、喜欢自然、喜欢单纯,只想当原始粗陋的黑陶,到井底汲水。他厌弃知识文明,他不喜欢被编派,不喜欢离开乡野。可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有一天,黑陶被当成文明世界所谓的艺术品,被转手、被移位、被改名换姓。离开乡野的黑陶觉得被“囚”在壁架上,其痛苦可想而知。
当然更痛苦的是它的名字老是被胡乱编派。号称艺术家的老头称黑陶“多么古典!”(黑陶把这称赞当成名字是多么具有讽刺效果!),而他的儿子却称黑陶“多么现代!”,这可不是赞美黑陶兼具古典与现代,而是更加深刻地讽刺所谓的艺术家、收藏家们。
读者稍加留意,就会发现这篇文章是继承了中国传统咏物风格的小品。文章里黑陶的特色跟书写者自己的特色被绾合起来,表面写黑陶,其实写自己。也因此,全篇描写黑陶的外在形象并不多,反而侧重它的精神特质。咏物小品时常捏塑物品本身并不存在的特色,最明显的是它的个性、它的脾气,但因为完全地拟人化了,读者更容易接收到作者所要投射的主题。
文章一开头:“黑陶,我是。”[19]300已经隐隐暗示没有出现的隐藏作者“我”也是一具黑陶。不过这个句型最可贵的地方在于倒装句式,黑陶放在前面,强化黑陶的地位,强化黑陶精神的重要。
至于这篇文章的结构,像司马中原其他寓言体作品一样,很有机杼。文章一开头用的是“黑陶,我是”,这个倒装句型出现两次,它和“我是黑陶”参差出现在整篇文章中,成为整篇文章的支柱。读者如果注意,这篇散文具有音乐的旋律,这四个字正是它的主旋律。论者时常说司马中原的散文像诗,《黑陶》就是,并不输给陆蠡。
以上简单谈论,只想表示司马中原散文并非“结构随意”。
司马中原的散文中,除了议论性的专栏外,抒情怀旧和乡野趣谭是他创作中两个主要的方向。“乡野趣谭”本来是用散文表现乡野传奇的另一种方式,后来又成为他用短篇小说发展出的系列“乡野传奇”。
整体来说,司马中原是当代台湾文坛的重要作家,但相对的,研究司马中原的论文实在偏少,更遗憾的是:还没有一位作家或学者能长时间,或全面性地研究他的作品。
参考文献:
[1] 王德威.乡愁的超越与困境—司马中原与朱西宁的乡土小说[M]//王德威.小说中国:晚清到当代的中文小说.台北:麦田出版有限公司,1993.
[2] 范铭如.合纵连横—1960年代台湾小说[J].淡江大学中文学报,2003(8):37-48.
[3] 齐邦媛.司马中原笔下震撼山野的哀痛[J].中外文学,1973,2(3):4-12.
[4] 司马中原.荒原[M].高雄:大业书店,1962.
[5] 司马中原.狂风沙[M].台北:皇冠杂志社,1967.
[6] 陈义芝.春风一样悠悠地吹着—司马中原先生专访[J].中华文艺,1977(79):4-20.
[7] 王溢嘉.论司马中原的灵异小说[M].林耀德,孟樊.流行天下—当代台湾通俗文学论.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2:241-270.
[8] 高全之.司马中原英雄的衰亡与升扬[M]//高全之.当代中国小说评论.台北:幼狮文化公司,1978.
[9] 孙述宇.水浒传的来历、心态与艺术[M].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0:301.
[10] 张默.从荒野出发—试论司马中原的《荒原》[J].新文艺,1968(151):21-36.
[11] 大荒.三度空间—谈司马中原[J].中华文艺,1974(44):115-123.
[12] 齐邦媛.抬轿走出《狂风沙》[N].联合报,1990-03-05(29).
[13] 齐邦媛.百年苍茫中《荒原》《狂风沙》再起[N].联合报,2006-05-23(E7).
[14] 李英豪.试论司马中原[M]//李英豪.从流动出发.台中:普天出版社,1972.
[15] 刘正伟.野味—司马中原的散文[J].淮阴师专学报,1996,18(1):11-13.
[16] 宋瑞.从《月光河》看司马中原[N].新生报,1978-11-26(12).
[17] 司马中原.绿杨村[M].台北:皇冠杂志社,1970.
[18] 司马中原.黎明列车[M]//司马中原.司马中原自选集.台北:黎明文化公司,1975:119-129.
[19] 司马中原.黑陶[M]//郑明娳.台湾散文选.广州:花城出版社,1993.
(责任编辑:时 新)
A Summary of the Reviews on Sima Zhongyuan
ZHENG Mingli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Department of Humanities and Sociology School, Soochow University, Taipei 10084, China)
Abstract:There have been over two hundred reviews on Sima Zhongyuan since 1949, among which the weighty ones appeared before the 1970s, and most of which focus on his novels, particularly his master pieces of Huang Yuan and Kuang Feng Sha.The reviews fall into the two categories of the writer style and the scholar type.Writers tend to express their thoughts with a sensuous touch, and their words contain feelings and frequently present penetrating ideas.Writers will make occasional discussions with the lifetime of Sima Zhongyuan, which provides critical references for understanding the author and his works.In comparison, scholars’ reviews are generally sensible and serious, and their discussions are precise and based on the works proper, with the highquality ones always penetrating.There is still plenty of scope for reviewing Sima Zhongyuan’s novels, while his unique sensuous essays are even ignored by the literary critics.Therefore, “Sima Zhongyuan” is an area yet to be developed continually for the contemporary literary research in Taiwan.
Key words:Sima Zhongyuan; Huang Yuan; Kuang Feng Sha; sensuous essays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7931(2016)02-0038-09
DOI:10.16217/j.cnki.szxbsk.2016.02.008
收稿日期:2015-11-15
作者简介:郑明(1949—),女,台湾新竹人,教授,博士,研究方向:古典小说、现当代文学、现代散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