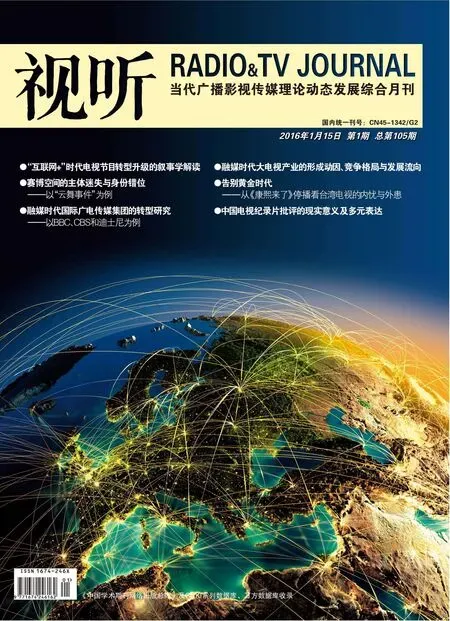浅析谍战剧中的“英雄叙事”——以《借枪》为例
□程文
浅析谍战剧中的“英雄叙事”——以《借枪》为例
□程文
摘要:进入新世纪后,在个体民主意识觉醒的同时,国家集体荣誉感在逐步流失,观众不再天真地认同传统“高大全”式的脸谱化人物,时代需要新的英雄。新世纪的谍战剧巧妙地契合了和平年代观众的猎奇心理和英雄情结,选择了战争那个“意识形态多元化”的年代——暗合当下“文化多元化”的背景,巧妙地映衬当下职场政治的竞争、人际关系的复杂,为观众创造了一个新的平民英雄神话。文章试图从历时性的角度来一窥新世纪前后谍战题材影视剧在“英雄叙事”方面的异同,并从《借枪》一剧的人物、冲突和结局三个方面来浅析剧中英雄人物的塑造。
关键词:英雄叙事;谍战剧;借枪;人物;冲突;结局
一、“敌暗我明”的平民英雄神话
目前我国学界对于谍战剧的定义还有待商榷,参照郝建《中国电视剧文化研究与类型》以及魏南江《中国类型电视剧研究》中的相关部分,笔者认为只要同时包括“间谍”和“战争”两个基本类型元素的电视剧都可称为“谍战剧”。按照谍战剧中主要间谍身份立场的不同,可以分为敌暗我明的“反特模式”与敌明我暗的“地工模式”两种子类型。建国初期一度流行的“反特片”即是“反特模式”的最佳例证,而自《暗算》以后盛行中国内地的谍战剧大多属于“地工模式”。
谍战剧的这两种模式一直同时并存,只是由于年代的不同而各领风骚。福柯曾言:“重要的不是神话讲述的年代,重要的是讲述神话的年代。”作为“英雄叙事”绝佳载体的谍战题材影视剧,因其所处的时代背景不同而讲述了一段段风格迥异的英雄神话。
新世纪之前,由于受到冷战思维和“文革”思维的影响,此时的谍战类型影视剧以“反特模式”为主,讲述了公安或侦查英雄与“美蒋特务”或“苏联特务”斗智斗勇,最终维护了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神话。此时作品的叙事线索比较单一,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强烈的政治性,人物设置二元对立、善恶分明,特别强调“文以载道”的创作观。
在大众文化和消费文化流行的今天,以2002年《誓言无声》的播出为起点,2006年《暗算》的热播为强力助推,在2009年“国庆献礼剧”《潜伏》的加温下,谍战题材影视剧再一次领跑了中国的电视荧屏和电影银幕。与上个时期完全不同,此时的作品以“地工模式”为主,倾向于讲述一个平民英雄突破现实困境的合围,忠诚于自己的信仰,最终实现个人最高理想的神话。此时国共两党不再是截然对立的双方,政治意识形态落为背景,情感消费凸显在前台。在人物塑造上,虽然对党和国家的绝对忠诚、与对敌斗争的坚强意志依然是轴心,但视点更多地转向了为信仰做出奉献和牺牲的个体身上,改变了往日的“高、大、全”的完美英雄脸谱,将英雄还原成了小人物,以更感性、更细致的人物内化性格让观众耳目一新。
任何一个时代都需要英雄,因为英雄成功的神话“为人们提供一套消除危机、解决问题的逻辑模式”。①对于上个世纪处于阶级斗争和冷战思维影响下的人们来说,谍战题材影视剧无外乎起到了告诫群众要站稳立场,坚决与反动势力进行斗争,排除异己,增强社会凝聚力的作用。通过形象生动的叙事,间接地把消除潜在危险的方式演示出来,使当时的观众一方面将如何“反特”明了于胸,另一方面更加坚定了自己的政治立场。
进入新世纪后,在个体民主意识觉醒的同时,国家集体荣誉感在逐步流失,观众不再天真地认同传统“高大全”式的脸谱化人物,时代需要新的英雄。新世纪的谍战剧巧妙地契合了和平年代观众的猎奇心理和英雄情结,选择了战争那个“意识形态多元化”的年代——暗合当下“文化多元化”的背景,巧妙地映衬当下职场政治的竞争、人际关系的复杂,为观众创造了一个新的平民英雄神话。这个新神话不仅仅只是观众暂时逃离平乏现实的途径,也是解决职场和人际关系问题的模本。那么这个新的“英雄”到底是如何塑造出来的呢?下面就以电视剧《借枪》为例试图来探讨“英雄”是怎样的炼成的。
二、“潜伏”在表象之下的人物真相
人物设计包含人物塑造和人物真相两个方面。“人物塑造是所有观察到的素质的综合,人物真相潜伏于这一面具之下。”②谍战剧这一类型决定了其“英雄”必定与众不同、“表里不一”。《借枪》一开场通过熊阔海与妻子周书真的对话,塑造了一个庸碌平凡的小市民。
周书真:“能人熊阔海,这可是最后的煎饼果子了,打明儿起,咱们就得打开后窗喝西北风了,咸菜还有。”
熊阔海:“我看今儿这煎饼果子个儿大,孩子肯定吃不了,一会你吃了,我有这碗粥撑着。您猜怎么着,真撑着了。”
周书真:“今天下了班先买一袋杂合面,然后再要半车煤……万成当的两张当票到期了,得赶紧赎当。嫣嫣上学得要一块钱学费……”
熊阔海:“嫣嫣,等支了薪回来,明儿个爸爸带你上聚合楼八大碗,黄焖鸡块、南煎丸子、元宝肉、素什锦……”
单从这段对话中我们就可以看出熊阔海应该是天津人,可能学过相声,所以他风趣幽默,经常插科打诨,没个正经。他和妻子和睦恩爱,以前过得应该不穷,但现在却落魄到要典当家产。本剧开场仅五分钟就把剧中最大的矛盾——“缺钱”点明,然后围绕这个矛盾,一次又一次考验熊阔海。为了买情报,熊阔海把随便在报纸上抄录的名单交给杨小菊,谎称是共产党地下组织;还是为了买日军扫荡行动的情报,熊阔海把自家的房子抵押给了杨小菊。
“人物真相只能通过两难选择来表现,然而善恶或是非之间的选择根本不是什么选择,真正的选择是两难之择。它发生于两种情境。一是两善取其一的选择,二是两恶取其轻的选择。”③《借枪》中的熊阔海就是被两难抉择一直压得喘不过气来的“悲剧英雄”。面对生活的困境,他是选择购买高价的情报,还是选择能养活一家人的生活?面对加藤敬二的威胁,他是选择妻女生命的安全,还是北平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安全?熊阔海在愈大的压力之下选择的行动,愈能深刻而真实地揭示其心思缜密、热血抗日的性格真相。这里的压力不仅来自社会外在层面,也来自个人内心层面,只有在所有层面上都对主要人物的人性进行深入探索,才能最终完成英雄人物的“形象工程”。
社会外在层面上最大的压力来自“砍头行动”的目标——加藤敬二,他也是本剧的主要对立面。拉乔斯·埃格里说:“没有对立体,就没有戏。”④这个在权力、武力和意志力上明显比熊阔海强大得多的人物,多次粉碎暗杀行动,是主角行动的根本原因和动力。另外,由老于所代表的同志之间的冲突,杨小菊所代表的国共之间的冲突,以及安德森所代表的朋友之间的冲突,都是熊阔海必须周旋和交涉的,他们不失时机地插入到主要的民族矛盾中,围绕着“忠诚”这一核心性格,又添入了睿智、果断、幽默、义气等熊阔海独有的性格真相。
熊阔海对妻女的牵挂是他个人内心层面上的压力,也是他真正的冲突和矛盾,同时也成了他最致命的软肋。当加藤敬二用周书真的生命来逼迫熊阔海投降时,熊阔海曾一时冲动想要放下一切带着妻女远走高飞。他的这种犹豫不仅是人物性格决定的,也是观众的“集体无意识”决定的。在成为英雄之前,他首先是一个人,有与观众相同的弱点和软肋。但如果这个情节发生在新世纪之前的谍战题材作品中,“高大全”必然会毫不犹豫地“告别”妻女亲人。应该说,对人物内心层面上矛盾的刻画是新世纪谍战剧,乃至其他类型剧,在人物塑造上最大的突破和进步。正因为这一点,才使“英雄”不再“高大全、假大空”,他的一切行为有了心理依据和支撑,同时也有了观众的认同。
三、亘古不变的“中式英雄”原型
法国剧作家皮埃尔·让说:“任何好的命题都由三个要素组成,第一个是人物,第二个是冲突,第三个是结局。”⑤结局必须首先能够满足观众的期待,但又不能以他们所期望的方式给予。在“英雄叙事”中,结局往往是确立“英雄”身份、提升主题的关键。熊阔海在行动当天得知太田将替代加藤出席欢送会后,急中生智立刻导演了新一轮的“砍头行动”。他先假装在“射杀太田”事件中受伤住院,然后让裴艳玲冒充是嫣嫣的生母,为了接回嫣嫣而将熊阔海的藏身之处出卖给加藤敬二。他选择了同归于尽,在记者的簇拥中一击枪毙了加藤。从此高潮“射击事件”开始,该剧就挫败了读者的猜测,并且成功地引入新的意义——“处决”。或许,每个中国人心中都有亲手“处决”那些侵略我们国家、残杀我们同胞的日本鬼子的潜在欲望。熊阔海的一枪是悲壮的,也是大快人心的。他替观众做了观众自己做不到的事,完成了一个“英雄”的使命。
然而这种“悲剧英雄”式的结尾仿佛并不陌生。法国的乔治·普罗第提出“三十六种戏剧模式”,其中第二十种就是为了主义而牺牲自己,包括恋爱和生命。⑥这种“悲剧英雄”的形象在中外神话中都有涉及,例如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中被阿波罗的暗箭射中脚踵而死的特洛伊英雄阿喀琉斯,以及惨死于徒弟逢蒙之手的射日英雄羿。
神话“深刻地体现着一个民族的早期文化,并在以后的历史进程中,积淀在民族精神的底层,转变为一种自律性的集体无意识,深刻地影响和左右着文化整体的全部发展”。⑦西方神话中的英雄往往以自我为中心,突出自己,一见有人危害自己或者不遂己愿,就不择手段残酷地进行惩戒和报复。与之不同,我国传统神话中的英雄都有着崇高而美好的道德情操,以大义为重,弱化自我。因此,当我们从历时性的角度来考察谍战题材影视剧中的“英雄叙事”流变时,我们就会发现,时代在改变,但是传统文化的影响力量并不会改变。即使中国谍战剧中的“英雄”由宏大叙事转变为微小叙事,由“高大全”式转变为平民式,但其中的“忠臣原型”和“良将原型”不会动摇、不会改变。无论是新世纪以前还是以后的谍战题材作品,其中的英雄必然足智多谋、智勇双全,必然能为信仰、组织或国家牺牲一切,永不背叛。
结语
总之,尽管时代背景的不同,新世纪前后谍战剧中的“英雄叙事”在人物塑造方面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尤其细腻地表现了英雄内心层面的矛盾之纠结,丰富地发展了英雄外在层面的矛盾之复杂。但由于中华民族“集体无意识”的影响,“英雄”的核心特质没有发生根本改变,他不可能变成放荡不羁的詹姆斯·邦德(电影《007》系列男主角)或兵不由将的杰克·鲍尔(美剧《24》男主角),更不可能变成背叛国家的Nicholas Brody(美剧《国土安全》男主角)。
注释:
①胡克.一种反特片模式[J].电影艺术,1999(4)
②③罗伯特.麦基.故事——材质、结构、风格和银幕剧作的原理[M].中国电影出版社,2001
④⑤皮埃尔.让.法国影视教材——剧作技巧[M].中国电影出版社,2005
⑥汪流.电影编剧学[M].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9
⑦何新.艺术现象的符号——文化学阐释[M].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
参考文献:
1.黎鸣.谍战剧的黄金创意——电视连续剧《潜伏》谍战要素分析与编剧技巧[M].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2
2.尹鸿,马向阳.话语.身份.景观——从2009年谍剧热看类型电视剧的生产、消费和意义生成机制[J].电视研究,2010(1):48
(作者单位:宁波广播电视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