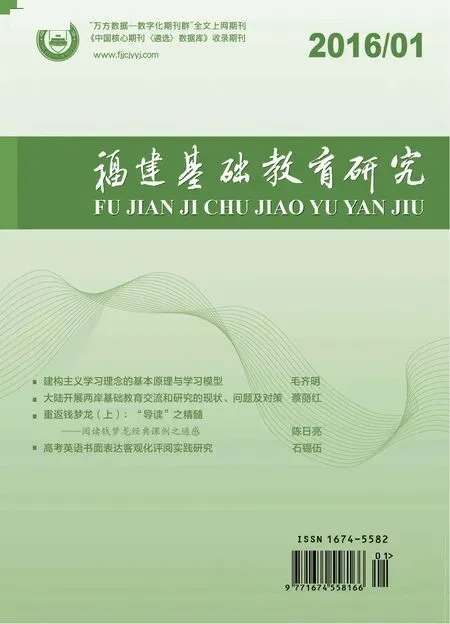重返钱梦龙(上):“导读”之精髓
——研读钱梦龙经典课例之通感
陈日亮(福州第一中学,福建福州350001)
重返钱梦龙(上):“导读”之精髓
——研读钱梦龙经典课例之通感
陈日亮
(福州第一中学,福建福州350001)
通过研读钱梦龙系列经典课例,结合钱梦龙“三主四式”教学阐述,对其导读法进行回顾、品析、梳理和探寻,试图揭示钱氏“导读”的价值内核,以及所独具的教学特色和教学效果。
钱梦龙教学法;导读;价值内核;教学特色
编者注:2015年12月18-19日,钱梦龙语文教学研讨会·新西湖笔会暨钱氏执教《愚公移山》35周年纪念活动在福州举行,本刊关注此语文教育盛会,特分两期刊登“闽派语文”代表人物、福州第一中学语文特级教师陈日亮的《重返钱梦龙——研读钱梦龙经典课例之通感》(本期刊登上篇,标题为编者所加),以飨一线广大语文教育工作者。
一、“导读”经验内核的追问
2015年寒假,我研读了华师大出版社新推出的《钱梦龙经典课例品读》[1]和多年前由教育部师范教育司组编的《钱梦龙与导读艺术》[2],以及多个名师同课异构的数十篇阅读教学案例,真有时空暌隔,滋味殊异之感。上个世纪的80年代,中学语文界风云际会,涌现出了包括钱梦龙在内的一批语文教学改革杰出的先行者,他们的名字和事迹几乎人人耳熟能详。到了30多年后的今天,向年青人问起他们的姓名,大多一脸茫然。我想,钱梦龙们曾是那个时代语文教学改革先行者和探索者,他们在我国当代语文教育史上留下的足迹,不能被一种群众运动式的改革进军所磨灭殆尽,成了一代人“失落的记忆”,于是油然而生抚今追昔、重返历史的念头。
曾在一个小范围内,听到孙绍振教授喊出“保卫钱梦龙”的口号。钱老师何时遭到围困?没有。那为什么要保卫?我知道孙教授的“保卫”实际说的是“捍卫”:捍卫钱梦龙的核心价值。有人认为钱梦龙“三主”和“导读”都属于传统教法的范畴,并不新鲜,甚至只具有应试的实用性,应该唾弃。然而,在语文界,钱老师的思想和经验确乎影响了整一代人,能产生如此辐射能量的教学观念和教学方法,不就已经体现其核心价值了吗?其实,我总感觉“三主”和“导读”,虽然是“核心”,但还不是最本质的内核。考察近现代百年语文教育史,教学须以学生为主体,许多人都主张过;教师要起主导作用,大多数人也都在实行,何以在上个世纪80年代,唯有钱梦龙能够独树一帜,先声夺人,创造出自成体系,又具有普适性开放性的教学经验模式,且提供那么多堪称经典的课例?这是否还需要我们继续追问——钱梦龙的经验内核,究竟是什么?
在《钱梦龙与导读艺术》一书里,钱老师回顾了自己在两位好老师的引导下,从一个“差生”转变成了好读书者,不断提高语文成绩的“成长之路”:开始学用小学字典到翻烂了《词源》;自吟熟背《唐诗三百首》,再到读《古文观止》《定盦文集》《随园诗话》,以至读林译小说;凭一本《诗韵合璧》迈进了学写旧体诗的门槛。从这一段自学经历,我们不能不注意到钱梦龙的“半生求索”中,就有他少年时代形成的“明显的自学倾向”。他说过:“我自身的经历使我深感自主意识和自学能力对一个人的成长发展有多么重要。”我们知道,一个人的成长之路,往往会深刻影响人的一生选择。尤其是作为一名教师,他所赖以塑造学生的,大半就是他自身的模型,不管自觉不自觉,教,总是要“顽强地表现自己”。正如王尚文先生所说:“教师所能教给学生的唯有自己。”就像我所体验和主张的“我即语文”,也是缘于自己半生的切身感悟,只是我少时苦无恩师指点,走了不少弯路,不是“求索”,而是磕磕碰碰的“摸索”罢了。
二、“导读”的独具特色
沿着钱梦龙的求索之路,再研读他的课例,我首先感觉,他的精彩而高效的导读教学,既体现那个年代一批语文名师教学经验的时代共性,又有着明显异于他人的鲜明特色。这个特色,并不是人们所乐道和欣赏的教学智慧和教学艺术,从根本上说更集中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导”自学生的“自读”
王荣生对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语文教学改革实验,曾有过这样的评价:“许多优秀教师创立‘教学模式’的路子……出发点也多是‘我喜欢’‘我觉得’。”若果真如此,那么钱老师则绝对是个例外。钱老师说过,“我十分重视教师‘教读’之前学生的‘自读’”“我更重视指导学生自己发现问题,提出问题,我的很多课都是建立在学生提问的基础上”。《钱梦龙与导读艺术》一书介绍他的三种基本课式,“自读式”就占了6页篇幅,而“教读”和“复读”则不到3页和2页,可见他对“自读”训练是格外重视的。16篇课例中,布置学生先在课前自读的就有11篇,有一节则是整节课都用来自读。1981年在浙江金华借班上鲁迅的《故乡》,让学生自读后用小纸片提问,少则五六题,多则十来题,全班竟提了六百多个问题。问题不在多与少,而在真与伪。钱老师说他尤其注意避免那些“诱使学生‘入我彀中’”的“教学圈套式”的“伪问题”。从课例中我们会不时听到这样的问话:
“请同学自己先说说看,看能不能自己提出疑问,自己解决疑问。”
“提出问题的时候,是不是想过答案?”
甚至可以这样“商量”:
“在决定这篇文章里哪些知识需要老师教之前,先请同学们讨论一下‘什么知识可以不教’。”
几乎在每一个课例中都能看到,学生自读之后的体会和问题,就成了他备课和教读的出发点,或引入,或设问,或启发,或点拨,或小结,师生以此为对话、互动的依据始终如一。哪怕有的学生暗自拿着教参回答,钱老师也不责备,反而赞扬这样做也是一种“主动”。像这样的“导”自学生自学的课,钱老师说他上得有些随便,“既没有环环相扣的严谨的结构,也不追求“鸦雀无声”的课堂纪律”。这当然不是说,他的课完全是自流的散漫的,钱老师非常重视对学生的预读作筛选、整理、提纯、归类。像教鲁迅的《故乡》,他把六百多个问题经筛滤归为七类,逐一讨论解决;教《论雷峰塔的倒掉》,就挑选学生的问题卡片并编了号,让拿到号的同学按序号提问,这些序号就代表了教学环节,在每个节点钱老师都适时作出简明扼要的小结。如此贴紧学生自学的全生态的教学流程,无论和当年教师大多习惯把思想教育目标列一条,语文知识内容列一条,语文能力要求再列一条,或者是今天刻板划一的把“三维目标”各自表述的教案模式,是大异其趋的。正由于对学生自学的高度重视,对学情的熟知与把握,钱老师的“导”才会做到适时而施,见机而动,师生之间达到了完美的契合,就像学生所总结的:“把难题解决了,课也读懂了……印象特别深。”这样始于自读,既导之以径,又示之以范,充分显示了钱氏导读法的独具特色。
2.“导”入文本的言语形式
钱老师说:“我上课时最关心的问题是,学生是通过怎样的途径进入文本的?是通过浮光掠影的阅读,一知半解的猜测,还是通过对文本中词语、句子的理解、咀嚼和品味?”这就关系到阅读教学应该“教”什么,是教文本的言语内容,还是怎样进入文本的言语智慧?叶圣陶主张国文教学须“侧重言语形式的讨究”。侧重言语形式,不是轻视言语内容,而是避免滑过形式而直奔内容,因而也是为了能够更好地进入内容。但进入内容还不是终点,进入之后再返回形式,才算是抵达语文课程的终端:学习语言文字的运用。所以文本的言语形式,就成了教师导读的唯一往返途径。
于是,我们又会不时读到钱老师常作这样的提示:
○你这个解释哪儿来的?
○回答问题时一定要根据书本上说的,这样解决问题才能有根有据,有说服力。
○能从这很普通的、往往被人忽略的词,看出它后面隐含的信息,书就该这么读。
这些提示当然也不见得有什么不寻常,但是能够时时提醒,处处指点,引领学生潜心于课文的字里行间,遵循着字不离词、词不离句、瞻前顾后、联系比较等等的规矩习惯,集中于语感的培养和词语语境意义的把握,切切实实培养学生感悟和运用语言文字的能力,绝不是偶一为之,更非一日之功。例如教《故乡》,引导学生对“故乡到底美不美”的探究;教《睡美人》,讨论如何理解“B角是个倔强和执着的人”;教《死海不死》,对什么是文章趣味性的启发;教《中国石拱桥》,就几个虚词作用的比较解读;特别是对梁启超《少年中国说》最后一段极其精彩的对诗化语言的想象与领悟。上个世纪80年代所总结倡导的“因文悟道,因道学文”,钱老师以其课例提供的教学示范堪称典型,也多为广大教师所熟悉仿效。
3.“导”向“领悟读书之法”
教师既知应该侧重言语形式的讨究,那么他的“主导”最终应该导向哪里,也许还没有真正明白,或者说,还没有形成理念自觉。钱老师说:“在我心目中,语文课就是教读课,‘教读’就是教学生读书使之达到‘不需要教’的最终目的。”因此他备课首先考虑的不是怎样“讲”文章,而是自己怎样“读”文章。所谓“教”,是着重介绍自己读文章的思路、方法和心得。因此阅读教学的目的不是“教懂文章”而是“教会阅读”,是“使学生的自读体会浅者深之,误者正之,疑者解之,进而领悟读书之法”。从16篇课例中,我们会不时读到钱老师这样提醒和指导:
○回答问题要遵守一条规则,这规则是什么?(学生:言必有据。)据在哪里?(学生:在课文里。)这就说明我们学习课文要——(学生接答:瞻前顾后。)
○这样理解很好。说明我们看文章能前前后后照应起来看。
○读文章要“思前想后”,这是一种很重要的阅读方法。
○回答问题、说明理由的时候别忘了讲“因为……”。
○请进一步作整体的观察:句和句之间在因果关系的构成上有什么特点?
在如此这般的寻常话语背后,有着钱老师所一贯重视的语言思维训练。例如,当学生总是习惯非此即彼地看问题,问到杨二嫂是正面人物还是反面人物时,钱老师随即指出:“我们还是换一种思想方法吧。是不是一定要讲好人还是坏人呢?”进而特别强调:“想问题要步步深入地追问,这里既有阅读方法,也有思维方法。”又比如,学生在品析句子时,常以为找到某种修辞知识拿来套一套,套对就是了。钱老师则适时告诉学生:“本来是十分生动的比喻,我们首先忙着去分析什么是本体,什么是喻体,还有什么味儿?难道除此以外就没有别的读法了吗?能不能换一种更有兴趣的读法。”他所谓的“有兴趣的读法”就是展开想象。“只要我们展开了想象,也就理解了比喻的内容,本体、喻体的问题自然就迎刃而解了。请展开想象,并且用尽可能生动的语言把你想象中的画面描绘出来。”这种读书方法也同样运用于教读文言文:“宁可要对文章有一种准确、生动的感觉,而不要为了翻译而忽略这种直接的感受。”在我看来,这种强调用自己的话说出自己感知理解的“以言传言”,是一项非常重要的阅读训练。此外,他还反复要求学生记住并练习“在初步理解的基础上背诵,在背诵的过程中加深理解”的“背读法”。由于钱老师对“读法”的高度重视,因此只要学生肯动“天君”,哪怕只动那么一点点,他都敏感地抓住不放,给予积极鼓励。有一次他发现学生回答问题时偷看书,却表扬道:“偷看的能力也是一种很重要的语文能力。因为偷看时要求眼光迅速从书上扫过,用最少的时间捕捉到自己迫切需要的文字信息,这种能力不是很有用吗?”当然他也及时指出:“不能用这种能力来对付考试。”
始于学生“自读”提出问题,再继以启发学生思考如何一步步往前走:“大家提了这么多问题,第一步走得很好。那么,第二步怎么走呢?”最终依然引导学生自己总结学习的收获:“经过两堂课,同学们在学习方法上有些什么体会?”如此始终以指导读法、用法为指归,钱氏导读法的精髓正是体现在他所说的“把主动权交给学生”的教学过程中,以养成学生“自奋其力,自致其知”的读书习惯。今天当我们在谈到“教什么”比“怎么教”更为重要时,一方面,把读书方法这个最重要的“什么”忽略了,另一方面,又把包含“过程与方法”的“怎么教”的作用贬低了,所剩下的只能是概念的传输与空洞的说教了。如果一节语文课学生在读法写法等等方面无所收获,读再多的范文又有什么用呢?
学生主体在受教之前,通常是自发的,而不是自觉的。为了使学生从“半自动阅读”向“全自动阅读”的转化,钱老师一直在关注和引导着学生的“自动”。他的认真细致的教学态度是令人钦佩的。无论学生的发言,还是教师对其进行点拨、引导、扭转、纠正,钱老师总是耐心听取,择善而从,见机而动,绝不做虚情假意的赞美,夸大其词的表扬。每有发现学生解读正确或说出新见,无不欣然赞许:“有道理,有说服力,我都被你说服了。”“对,对!你比老师高明!”他也从不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学生,不宣示什么标准答案——他也许根本就没有“备案”。有一次,讨论闰土为什么把“我”叫“老爷”时,一个学生说是封建等级观念的毒害,话刚出口,钱老师就追问他是怎么知道的,是自己想出来的还是书上看到的,却忽然警觉不对:“啊,我打断你的话了吗?对不起。”立马改口道:“这个问题你怎么回答得这样好呢?”甚至还能听到这样的话:“太好了!太好了!谢谢你的指正,我提这个问题是有些多余,现在我声明取消。”当然,他也从不随意接过学生的回答再来一番解说发挥,作出师必贤于弟子的姿态,倒是常常听到他也像学生中之一员似地说声:“我同意。”以兵教兵,以兵教官,都是他最乐于采用的方法。
“逐渐去扶掖,终酬放手愿。”叶圣陶先生多次提到“放手”。教师“主导”最难能的便是“时时不忘放手”。[3]从钱老师的课例里,我们发现三十多年前师生的“对话”与“互动”已到达怎样的高水平,那显然不是为对话而对话,为互动而互动,其高妙的集中体现,则是“不忘放手”。教师步步相伴随行,从牵手、扶手到松手、放手,逐渐引导学生从自发主体发展为自觉主体,这一个过程,正需要钱老师那样的细心与耐心,一旦缺乏细心、耐心和信心,主导变为主宰,主体沦为玩偶,那是很容易的事。
三、“导读”是“三实”的范本
研读钱老师的课例时,我对其课的主线分明,理路清晰,结构紧凑,绝不夭矫蟠曲,旁逸斜出,有很深刻的印象。这一点,也是和今天不少的观摩课例迥乎不同的。总的看来,那些课例都很注意体现新课改理念,从课的“饱和度”看,从教师对文本内涵的“发掘”看,从教学方式方法的“创意”看,乃至从教师的口语表达看,确有令人耳目一新之感。那么感觉不同的是什么呢?粗略想了想,大概上个世纪80年代,致力于语文教学改革的一批名师,无不特别注重45分钟的课堂效率。他们很讲究课的“瘦身”。记得浙江绍兴的一位教研员陈阿三,曾说过这样的话:“那时对文本的解读停留在‘一元’上,可为什么它比今天的多元解读更具有指向性和穿透力?这是值得思考的。”他认为“关键的一条,单纯。单纯的文本,单纯的思想,单纯的教法,单纯的课堂。”像钱老师这样,不着意于课的形式多样,而唯以切实有效是务,所追求的是教的内容“结实”而非“饱满”,是教的方法“有效”而不是“多样”,于是就形成了本色当行的常态性的课堂特征:单纯。从16篇课例,我们可以发现,由于特别注重读书方法习惯的教学价值,就不会着力在情感、态度、价值观上“注水”“加料”。经过点拨与纠正,学生只要明白怎么读就可以了,没有必要再在读的内容上去深挖,其课的流程才能做到“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绝不放纵奔流,泛滥无归。真正做到了叶圣陶先生所说的“在这些场合给学生指点一下,只要三言两语,不要啰里啰嗦,能使他们开窍就行”。
真实,扎实,朴实,这“三实”是我长期对语文教学实效高效的探索与追求,而钱梦龙老师的导读教学,我认为恰是最完整也最完美地为这“三实”提供了经验的范本:由于导自学生的自读,所以“真实”;由于导入文本的言语形式,所以“扎实”;由于导向“领悟读书之法”,所以“朴实”。这些都无需再加以解说,从所有钱氏的课例中,我们都会获得极其深刻的印象。
[1]钱梦龙著,彭尚炯编.钱梦龙经典课例品读[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2]教育部师范教育司组编.钱梦龙与导读艺术[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3]叶圣陶著,朱永新编.叶圣陶教育箴言[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3.
(责任编辑:刘火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