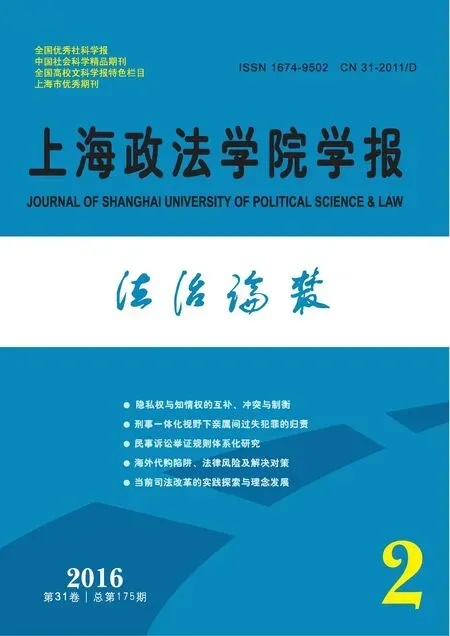以审判为中心场域下庭审记录方式的信息化改革——以刑事审判为例
李遵礼 杨远明
以审判为中心场域下庭审记录方式的信息化改革——以刑事审判为例
李遵礼1杨远明2
作者单位:1.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江西省吉安市人民检察院
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要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而要做到以审判为中心,强化庭审辩论功能,实现和充分反映诉讼的程序正义,除了完善和落实关于庭审的各项诉讼原则等外在性、原则性保障外,还要完善保证庭审程序公正性与正当性的内在具体制度,于是庭审记录就成为了一项十分重要的制度构建。②张卫平:《论庭审笔录的法定化》,《中外法学》2015年第4期,第917页。但是,对于庭审记录的重要性,无论在学理上(包括各种诉讼法教科书中)还是实践中均未引起必要的重视。实际上,庭审记录是实现审判中心主义十分重要的技术性工作之一。③龙宗智:《论建立以一审庭审为中心的事实认定机制》,《中国法学》2010年第2期,第155页。因此,在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中,我们应该重视对庭审记录这一技术性制度的改革。本文通过对庭审记录的实证调查,发现庭审记录中存在着种种问题,并分析了现行庭审记录对推进“以审判为中心”诉讼制度改革的掣肘作用。最后尝试提出利用信息化技术,采用庭审全程同步录音录像为主的记录方式逐步代替传统的笔录方式,以克服庭审笔录存在的弊端,以期成为司法公正的一个新的增长点。
一、对庭审笔录的相关调查
(一)相关的法律规范
我国对庭审记录的相关规定散见于法律和司法解释中(见表1),但都仅仅作了粗略的规定。对庭审笔录应该囊括哪些内容没有规定,实践中只好由书记员自行决定,如果记录的内容得不到当事人认同便会引起争执。另外,法律规范对庭审笔录的制作标准、制作要求、制作程序以及如何申请补正等具体问题也缺乏详细的规定,使庭审笔录在现实运行中陷入失范的困境。另一方面,理论界对庭审记录也缺乏关注,导致庭审记录在实践运行中无法获得理论上的指引。

表1 我国有关庭审记录的法律规范
(二)庭审笔录的实践运行现状
笔者以2015年C市Y中院刑事审判庭审结的前100件刑事案件的庭审笔录为分析样本,通过查阅电子笔录卷宗和同步录音录像,开展访谈等方式对庭审笔录的现状进行调查,发现呈现以下几方面的特点。
1.庭审笔录大量记载“略,参见侦查卷宗第×卷第×页”来代替记录公诉人宣读的侦查卷宗材料
笔者对该100份刑事案件庭审笔录的样本进行调查分析发现,庭审笔录往往对公诉人在庭审中所宣读的公诉书、庭前供述笔录、证人证言笔录、鉴定意见书等相关笔录的具体内容不予记录,取而代之的只是简单地把公诉人宣读材料所在侦查卷宗的第几卷第几页记录在庭审笔录里。比如在调研李某犯故意伤害罪一案中,公诉人宣读的两份证人证言笔录、一名同案被告人的庭前供述笔录以及鉴定部门的鉴定意见等内容在庭审笔录中没有任何记载,仅仅记录相关材料对应所在侦查卷宗的卷册和页码。相关详细调查情况详见图1。
2.庭审笔录在归纳陈述时存在加工、挑选、曲解陈述人意思的情况
笔者将该100份庭审笔录样本与庭审同步录音录像逐一对照分析,发现有些庭审笔录与当事人陈述存在信息失真,如以下案例:
【案例一】张某犯故意伤害罪一案。被告张某在庭审中供述:“我听说我老婆被徐某打了,我就走出单位去外转转,看能不能碰到徐某,如果碰到的话我就跟他说一下这件事情,想让他赔礼道歉,这件事情就这样解决了。”庭审笔录记载为:“我得知徐某打了我老婆后,我就从单位出发去找徐某解决,要他赔礼道歉。”

图1 庭审笔录样本对公诉人所宣读的公诉书和侦查笔录的记录情况
【案例二】陈某犯抢劫罪一案。审判长问被告人张某是否在十天之前收到起诉书副本?是否在三天之前收到法院传票?被告张某回答:“我收到了起诉书副本,也收到了传票。但是我记不清什么时候收到的,收到多少天了。”审判长:“在卷材料显示你于十天前收到起诉书副本,于三天前收到法院传票。”被告张某:“好的”。庭审笔录记载为:“审判长:‘张某,你是否在十天前收到起诉书副本,在三天之前收到法院传票?’张某:‘是的’。”
【案例三】韩某犯故意杀人罪一案。被告人韩某在庭审中供述:“当时我俩扭打在一起,慌乱中我拿起一把水果刀乱刺,刺到哪记不清了,隐约有一点印象,好像划到了他的手。”庭审笔录记载为:“当时情况比较慌乱,我拿起一把水果刀乱刺,结果刺伤了他的手。”
以上只是从调研样本中摘录的三个案例,事实上样本中存在很多类似的情况。案例一在归纳被告人意思时存在加工记录,有意无意增强了被告“主动出击”的主观故意。案例二在记录时挑选了被告人的意思表示,使存疑的程序合法瞬间毋庸置疑。案例三的庭审笔录曲解了被告人的意思,使不确定的案件事实经过笔尖一挥立刻变得清晰可见。
3.庭审笔录很少或无法记录人的表情、态度、肢体语言等非语言表达方式
人类的交流与表达方式除了语言之外,还有大量能够贴切传达人之所思、所想、所感的方式,如笑、哭、微表情、肢体语言等等,这些被称作“沉默的语言”。在调研中,很多庭审笔录都没有对诉讼参与人的这些非语言表达方式进行记录,有记录的也只能记录一些简单的非语言表达,如,哭、颤抖、点头、摇头等。对于恐惧、坚定、犹豫、疑惑等深层次的非语言表达在笔录样本中没有得到丝毫体现,但却在录音录像样本中真实发生。笔者对上述1 0 0份庭审笔录样本的调研过程中,统计了庭审笔录对当事人表情等非语言表达的记录情况(见图2)。
4.因庭审笔录内容的记载、补正、签字确认导致的矛盾多发
笔者通过电话和走访的方式,对C市Y中院及其下辖基层法院共50位法官就庭审笔录所引起的矛盾进行了访谈,其中包括3 0位刑事法官和2 0位民事法官。在访谈调研中发现(详细见图3),现实中很多当事人认为庭审笔录记载内容未能准确表达自己意思,或者要求更改补正庭审记录内容,但对方当事人又不同意法院更改补正,而我国法律对庭审笔录的记录和补正只是笼统地进行了规定。另外,还有很多当事人对庭审笔录因为种种原因拒绝签字,虽然相关法律规范对此规定了一些解决办法,但仍导致当事人对法院的不信任,甚至演变成申诉、上访。广受关注的云南澄江县法院“拷律师”案就是因律师认为庭审笔录遗漏了自己观点拒绝在庭审笔录上签字所引发的冲突。

图2 庭审笔录样本对非语言表达的记录情况

图3 法官在办案中遇见因庭审笔录的记载、补正、签字而产生矛盾的情况
5.庭审笔录无法全景式反映法庭全貌
庭审笔录只能反映诉讼参与人的意思表达,对法庭设置、法官及陪审员举止、旁听情况等法庭场景没有记录或无法记录。但在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下,在庭审中所有可能影响证据采信、事实认定和定罪量刑的场景都应被记录下来。另一方面,庭审笔录无法对法官、检察官、陪审员举止进行监督,对当事人或旁听人员扰乱法庭纪律等行为无法有效固定证据。
二、用笔录固定庭审对以审判为中心诉讼制度的掣肘作用
(一)容易导致案卷笔录中心主义,削弱了审判中心的地位
审判中心主义是近现代司法文明的重要体现,也是各国诉讼制度普遍认同的一项基本原则。它要求司法审判在侦查、公诉等整个诉讼活动居中心地位,保证庭审对证据采信、事实认定、法律适用中具有终局决定权。但现行庭审笔录无法反映庭审的原汁全貌,长达几个小时的开庭审理最后只浓缩成了十几页或几页纸的笔录,对公诉人宣读的笔录证据只记载其在侦查卷宗材料的哪一页,对其内容则没有记录,导致法官无法根据本应全景式反映证在法庭、辩在法庭的庭审记录进行事实认定以及案件裁判,使得法官在庭审结束后仍然转向查阅移送上来的侦查卷宗材料,导致法庭审理流于形式,屏蔽了庭审活动对侦查、起诉的有效性进行结论性评断的最终决定作用,弱化了庭审的事实查验、法理释明、冲突处理及其正当化功能。①龙宗智:《刑事庭审制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8页。另一方面,在上诉案件中,二审法院所要审查的应当是一审法院的裁判结论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方面是否存在“确有错误”,因此,一审法院的审理过程和裁判结论应当是二审法院进行上诉审查的重点,为此,二审法院无论以何种方式进行法庭审理活动,都离不开对一审法院审理记录的审查。②陈瑞华:《侦查案卷裁判主义——对中国刑事第二审程序的重新考察》,《政法论坛》2007年第5期,第104页。现行一审庭审笔录不能忠实、淋漓尽致地展现庭审活动,对于公诉方宣读的笔录证据内容也没有全面记录或没有任何记录,导致二审法官同样无法通过庭审笔录审查一审审理过程和裁判结论,于是不得不再次转向移送上来的侦查卷宗材料,导致了案卷笔录中心主义,进一步削弱了庭审本就孱弱的中心地位。
(二)“归纳式”记录当事人陈述存在信息失真,折损了庭审查明事实的作用
1.口语与书面语的天然差异使当事人口头表达无法准确跃然纸上
法国语言学家阿里斯(Harris)认为,口语作为一种听觉符号系统,是以时间展开的,具有线条型的特点;文字作为一种视觉符号系统,是以空间展开的,具有二维的特点。所以,写在纸上的文字是静态的东西,而口语是充满活力的辩证语言。③郑立华:《口语与书面语关系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第27页。因此,口语与书面语的历史起源不同,表达特征不同,承担的交流传播功能不同,再加上口语的随意性、模糊性、跳跃性,导致口语与书面语之间存在天然的鸿沟,作为书面语的庭审笔录也就不可能成为当事人口语的“肖像”,全面准确地表达当事人意思。 比如,当事人说话音调、语速、语气、停顿等等。同时,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很多地区都有着自己当地的方言,很多方言无法转换成现代汉语,或者即使转化后也并不能充分表达方言原意。
2.由于主客观原因导致书记员在归纳记录当事人陈述时存在信息丢失或扭曲
笔录是经过记录人主观认识过滤和重新表达后的产物。④朱立恒:《传闻证据规则与侦查笔录的运用》,《法学杂志》2006年第2期,第124页。在法庭审理中,一方面,由于客观上有的书记员归纳能力欠缺,书面语言组织能力不强,培训不够等原因导致庭审归纳记录存在丢失或曲解原意。另一方面,由于主观上书记员有意无意地挑选、提炼、再加工陈述人的意思,目的是为了确定并固定陈述人模糊的口头表达,方便法官按照犯罪构成要件进行裁判,以致在归纳润色中不知不觉地改动原意。同时由于被告人在法庭上处于相对弱势地位,对庭审笔录不敢计较太多,大都不会仔细核对,甚至根本不看就签字确认(见图4)。
(三)庭审笔录无法记录当事人的情态证据,忽视了司法认知规律
情态证据是指在庭审时,被告人或证人的面部、声音或身体等各部分及其整体上的表现出来的能够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材料。⑤蔡艺生:《让尾巴摇狗:美国情态证据实证研究》,《时代法学》2012年第5期,第83页。上世纪5 0年代,美国学者麦拉宾发现,一条信息所产生的影响力7%来自文字,38%来自声音,55%来自表情、动作和服饰等非语言行为。且表情传达的隐蔽信息更具真实性,无法通过意志加以控制。⑥谢小剑、颜翔:《论同步录音录像的口供功能》,《证据科学》2014年第2期,第193页。中国古代司法审判就非常重视人的神态表情,采用了“五听”的诉讼方式。情态证据虽然在我国从证据资格、证明力、证明标准等方面都在法律上被否定,但它在司法实践中仍然发挥着间接佐证作用(见图5)。情态与言词共同消除着意义上的不确定性,表达着事实,并为信息交流所不可或缺,如果忽视情态证据,必然代表着对合理认知规律、司法规律乃至是司法正当性和合理性的忽视和否定。①蔡艺生:《让尾巴摇狗:美国情态证据实证研究》,《时代法学》2012年第5期,第90页。所以,庭审记录理应把代表客观真实的当事人情态记录下来,否则与审判中心主义的诉讼理念存在背离。

图4 被告人及辩护人看阅庭审笔录并签字确认所用时间情况

图5 笔者在中国裁判文书网通过检索关键词查找相应文书的数量情况
(四)记录跟不上问答的速度,削弱了庭审的连贯性、效率性和对抗性
书记员的记录速度远远不及人们说话的正常速度,即使在“归纳式记录”的实践操作中,由于需要概括归纳当事人的陈述,需要组织语言把当事人的口头表达转述成书面语言,书记员的记录速度仍然跟不上说话的速度。在对庭审录像样本调研中,常常遇到庭审录像好像突然暂停,原来是法官要求当事人停顿下来等一下,以便让书记员进行整理记录。另外,法官常常在庭审中要求当事人把刚刚说过的话重复陈述一遍,或者要求当事人放慢语速,目的都是为了让书记员有足够的时间进行记录。但是这种做法就割裂了庭审的连贯性,也削弱了庭审的对抗性。此外,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要在庭审活动结束后由书记员宣读或者自己阅读庭审笔录,核对无误后签字确认,降低了庭审的效率。且按照现有法律规定,当事人单方就可以申请法院对自己的陈述进行补正,也损害了庭审笔录的权威性。
阿花见我没有诚意,脸色又阴了,抽了抽鼻子,一行泪又蜿蜒而下。我拿纸巾递给阿花,阿花甩开我的手。我再递,她再甩我的手。我干脆自己动手揩阿花脸上的泪。
三、对庭审笔录“归纳式记录”的正当性的质疑
(一)记录效率的现实桎梏不能否认“镜像式记录”的原本理论逻辑
法作为社会行为规范,与人类社会并存,具有悠久的历史。随着近现代司法的发展,逐渐形成了“剧场化”的现代司法构造,将情景演绎下的事实调查、法庭辩论记录下来,使诉讼过程有据可查,能在一定程度上情景再现。在信息化技术不发达的时代,庭审只能通过传统的人工记录方式,采取“归纳式记录”。但并不能因为庭审记录效率的现实桎梏而否认庭审记录本应“镜像式记录”的理论逻辑,归纳式记录只不过是对现实庭审记录方式的无奈妥协。在信息化技术高度成熟的今天,在审判中心主义理念背景下,我们对庭审“归纳式记录”应该重新审视。因为,正义的标准具有历史性,正义应随着历史的不断发展被赋予不同的标准。当现代信息化技术对庭审进行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完全可以达到“镜像式记录”条件下,应该对现行庭审记录方式进行改革。事实上,在德国、美国、新加坡等域外国家都已经采用数码录音对庭审进行记录。我国香港法院早在2 0年前开始,就逐渐废除了庭审书面记录,转变为全面采用数码录音来记录法庭审讯。①孟焕良:《庭审记录走上“信息高速公路”——浙江“试水”以录音录像代替书记员笔录改革》,《中国审判》2015年第11期,第20页。
(二)对当事人意思的“归纳裁剪”属于司法判断权范畴,应由法官而非书记员享有
一般来说,对当事人表述的记录越接近原话就越能忠实地反映了当事人意思,就更能达到庭审记录的功能。然而在司法实践中绝大多数书记员无法达到记录原话的要求,只能对当事人原话进行归纳记录。一个进行了半天或一整天的庭审,最后由书记员浓缩在几页或者十几页的笔录纸上,再由法官从这些笔录纸上抽丝剥茧出案件事实。这实际上是先由书记员对庭审活动进行第一遍删繁去冗后形成庭审笔录,成为法官裁判的依据,再由法官对庭审笔录进一步去繁存精,裁剪抽离出案件事实,从而适用法律进行裁判。在这里需要重点指出的是,书记员对当事人陈述进行概括归纳记录,是对案件事实的裁剪,涉及到当事人的权利义务的处分,应属于司法判断权范畴,只能由法官专属。因为不管是从理论上还是从司法实践中,书记员与法官有着不同的职责分工。书记员一般负责事务性工作,而法官履行司法判断权。所以,现行由书记员对当事人陈述进行归纳裁剪的记录方式应该进行改革。
四、庭审记录方式的信息化改革
正如前所述,审判中心主义对庭审记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近年来,我国法院信息化建设取得了快速发展,在此背景下,如果庭审记录仍然采用传统人工记录方式,这无异于用冷兵器思维考量现代战争。因此,应该对现行庭审记录方式进行信息化改革,采用庭审同步录音录像为主的方式代替现行庭审笔录。
(一)同步录音录像记录方式的价值功能
1.裁判依据。庭审同步录音录像将庭审活动以更完整、更立体的方式进行全景再现,祛除了笔录可能存在损害原意或者丢失原始信息的弊端,还可以将当事人的语气、情绪等情态证据忠实记录,可作为法官对案件进行裁判的依据。
2.程序性证明。程序性证明是指在司法诉讼过程中,控、辩一方或双方依法针对各自的程序性请求或程序性争议,在中立的裁判者面前展开的论述或说服活动。①孙记:《程序性证明——一个证据法学不可缺失的概念》,《北方法学》2007年第5期,第110页。传统的庭审笔录只是法庭上言语的堆砌,并不能清晰反映庭审程序性阶段,同步录音录像记录整个庭审的进程,可以作为证据对庭审程序是否合法进行证明。
4.监督庭审活动。传统庭审笔录重点记录庭上言语表达,对法官的行为举止无法记录。现实中,有些法官开庭着装不规范,接打电话,动不动叱喝当事人,野蛮打断当事人发言,这些情况得不到记录和监督,最终将折损司法的威信和法律的力量。通过同步录音录像,可以记录和监督庭审活动,成为法官考评的对象,促进法官行为的规范化。
5.法律人才培养的素材。将整个庭审活动通过同步录音录像记录下来,可以成为法学院校人才培养的教学素材,也可以成为法官培训的生动素材。
6.司法公开。现阶段我国司法公开发展进程还无法满足当事人和社会民众不断增长的权利主体意识和权利保障需求,也无法满足新形势下当事人和社会民众对司法活动所应具有的程序交涉功能的需求。②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课题组:《关于加强司法公开建设的调研报告》,《人民司法(应用)》,2009年第5期,第44页。进一步深化司法公开的内容和方式是人民法院工作的一个重点。通过同步录音录像向当事人和社会公众公开庭审活动,可以作为法院深化司法公开的一个有益探索。
(二)庭审同步录音录像的制度构建
利用同步录音录像进行庭审记录是一个新鲜事物,由于传统记录方式在法院内部的工作惯性,以及社会民众心理接受预期,所以,在推进同步录音录像进行庭审记录过程中应循序渐进,稳步推进。
1.确立录音录像作为庭审记录方式的法律地位。按照目前我国法律规定,录音录像不是法定的庭审记录方式。虽然2 0 1 0年最高法院发布了《关于庭审活动录音录像的若干规定》,但该规定把庭审录音录像定位为法院审判管理的措施,是提高法庭记录质量,核对当事人申请补正笔录的辅助性手段。《规定》发布以来经过近五年的摸索推广,法院已经对庭审录音录像进行了硬件技术储备,同时也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现在应该从制度层面上确立庭审录音录像的法律地位,把录音录像确立为庭审记录的法定方式。
2.适用范围。开庭审理的案件一般都可以运用录音录像进行庭审记录,还包括接访、执行或听证等活动。但按照法律规定不公开审理的案件,或者案件调解部分,经检察院建议或者当事人申请,可以不采用庭审录音录像而用传统的庭审笔录方式进行记录,因为录音录像具备与外界有较强交互性质的信息化技术和设备,可能会损害当事人利益或公共利益。另外,对于巡回法庭等不具备录音录像条件的也可以采用传统笔录进行庭审记录。
3.全程进行,同步录制。用录音录像记录庭审活动必须保证全程不间断进行,要与庭审进程保持同步。在庭审中因故休息、庭审结束等处理环节都要记录,不得暂停或删减录音录像。另外,法庭需要设置多个音频信道,分别记录法庭全貌、法官席、公诉人席、被告席、辩护席、证人席、书记员席、旁听席的活动,确保庭审记录全面、客观、真实。
4.书记员编辑时间节点标签供庭后快速检索查阅。为了方便庭后对庭审录音录像中所需要的某一片段进行快速检索查阅,录音录像软件应设计可供书记员在庭审录音录像过程中进行编辑标签的功能,书记员可在录像视频进度条上编辑注明庭审阶段、关键语句及时间节点。
5.程序告知。推行录音录像进行庭审记录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诉讼参与人应该有权利提前知道自己所参与的庭审的记录方式,所以,人民法院应该提前告知诉讼参与人。一方面应该在给当事人的《开庭传票》或者给证人、鉴定人的《出庭通知书》上告知将采取全程同步录音录像进行庭审记录,另一方面审判长在宣布开庭时也应进行庭前释明,说明庭审将采用录音录像进行记录。如果诉讼参与人不同意采用录音录像进行庭审记录,需要向合议庭说明理由,若理由正当充分,经合议庭同意,可以不采用录音录像进行庭审记录,而用传统笔录方式进行记录。
6.确立出庭检察员和陪审员对庭审录音录像的监督职责。我国相关法律法规没有规定庭审笔录需要由出庭检察员签字确认,实践中检察员对庭审笔录也往往缺乏监督。采用庭审录音录像进行庭审记录,就需要出庭检察员和陪审员对庭审录音录像过程进行监督。在诉讼参与人、公诉人、陪审员等人的席位面前安装电子显示屏,对庭审录音录像的画面进行同步显示,对录音录像过程中的疑问可以向法庭提出。
7.录音录像的保存。庭审录音录像作为庭审全部活动的记录,应一并存入电子卷宗内,保存在服务器上,做到三级联网。当事人、承办人或者上诉法院都可以在内网上查阅。同时,为了保证庭审录音录像的原始性和真实性,防止被篡改、伪造,庭审录音录像在录制结束后,书记员应当庭刻录光盘,并由当事人、出庭检察员和陪审员当场签字封存,作为庭审记录的母本,具有最高证据效力,结案时随案卷材料归档保存,非因特殊原因,非由签字方共同启封,不得使用。
8.当事人及社会公众查阅。庭审录音录像是对庭审活动的记录,具有卷宗材料的性质,存入卷宗正卷,当事人有权申请查阅。另外对于社会公众查阅的问题,随着司法公开逐渐深入,公众想要查阅庭审录音录像的,可向人民法院申请,由法院作出是否准许的决定。所有查阅庭审录音录像的,但未经法院许可,任何人不得复制、拍录、传播庭审录音录像。
五、结 语
“每一个经验丰富的公诉人和辩护律师在开始其刑事诉讼之时便认识到其可能败诉,……所以他们必须尽一切可能制作出能向复审法院表明下级法院未主持正义的审判记录。”①[美]乔恩·R·华尔兹:《刑事证据大全》,何家弘等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3页。美国学者华尔兹教授的这句话道出了庭审记录的重要价值,但庭审记录在我国理论与司法实践长期被忽视。我国目前庭审笔录的运行现状在一定程度上剥夺了审判中心主义的实现空间。法学研究不能只满足于立法上的逻辑周延,还应关注司法实践的样态。因为,
强诉辩双方有针对性辩驳的能力,不能答非所问。辩驳要围绕争点展开,避免纠缠枝节问题。同时,诉辩双方还应知道,“查明”不等于“证明”,“示证”不等于“说服”。“公诉人出庭支持公诉的目的不是为了将证据移交给法庭,而是在法庭上通过举证、质证,根据现有证据对辩方提出的质疑进行论证与反驳,并通过阐释证据之间的逻辑关系,将零散的证据整合成完整的体系,通过理性的论辩使他人信服。”①百晓锋:《新民诉法第247条与面临“十字路口”的司法拍卖改革》,《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3年第2期,第112-125页。辩护律师亦然。此外,诉辩双方还要增强有效说服的能力。需知,庭审作为一种主体之间的说服活动,不仅仅是一个“根据证据进行理性对话的问题”,其中还涉及到辩论的艺术、如何调动心理情感因素等心理学技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