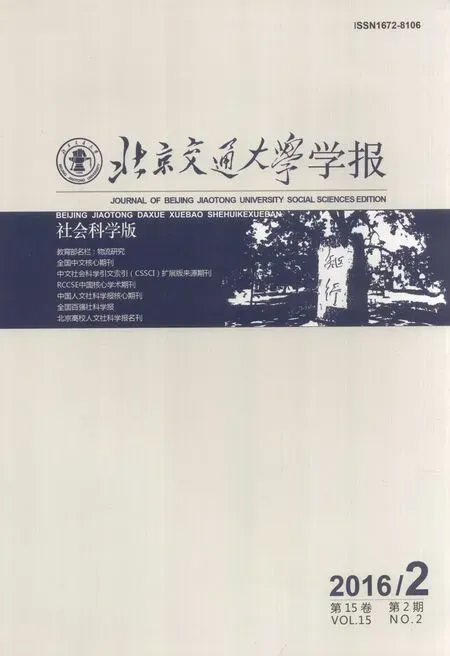“十三五”时期新一轮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研究
黄 群 慧
(中国社会科学院 工业经济研究所,北京 100836)
“十三五”时期新一轮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研究
黄群慧
(中国社会科学院 工业经济研究所,北京 100836)
摘要:“十三五”时期,为了适应经济增速趋缓、结构趋优、动力转换的经济新常态,必须推进新一轮国有经济布局的战略性调整。当前国有经济存在总量大,但功能定位模糊、过于集中于重化工业、地方国企扩张较快、创新方向和效率还不能满足创新型国家的要求,面临国际"竞争性中立"的严峻挑战、自然垄断性行业有效竞争不够和竞争性行业产业集中度不高等问题。“十三五”时期的新常态下国有经济布局结构战略性调整的目标,应该重"质"轻"量",不再纠结于国有经济占整个国民经济的具体比例高低的"数量目标",而应更加看重优化国有经济布局、促进国有经济更好地实现其功能定位和使命要求的"质量目标"。具体需要基于功能定位分类推进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基于国家战略性标准和公共服务性标准选择调整国有经济的产业布局、基于全面深化改革和优化市场结构双重目标来协同推进国有企业兼并重组。
关键词:“十三五”时期;经济新常态;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
一、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国有经济取得了巨大的发展,在保持我国经济高速增长、推进我国快速工业化进程、提高经济国际竞争力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1978年到2013年的国有企业改革大体可以划分为“放权让利”、“制度创新”和“国资管理”三个大的阶段(黄群慧、余菁,2013)[1],各个阶段中积极推进了众多重大改革措施,包括经济责任制、利税改革、承包经营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和构建以国资委为核心的国有资产管理新体制等等。其中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两方面重大改革,对于国有经济取得今天的发展成就,发挥了重要作用。考虑到迄今为止我国国有企业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方面还有待进一步探索和完善,可以说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发挥了更大作用。上世纪90年代末,以收缩国有经济战线为核心的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不仅改变了国有经济量大面广的局面,更为关键的是由于国有企业更多地集中到与工业化中期发展阶段相适应的重化工领域,从而整体上解决了国有企业如何脱困问题。
当前我国经济正在步入速度趋缓、结构趋优的“新常态”,这意味着经济发展阶段发生了重大变化,从工业化中期步入到后期(黄群慧,2014)[2],在这个新阶段我国经济呈现出一系列趋势性变化,同时也面临着相应的风险。接下来一个直接的问题是,经过战略性改组、适应工业化中期阶段的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应该进行怎样的再次战略性调整,才能够适应步入工业化后期的环境变化,从而适应和引领“新常态”。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健全国有资本合理流动机制,推进国有资本布局战略性调整,引导国有资本更多投向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坚定不移把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更好服务于国家战略目标。”[3]这意味着,继“九五”时期末期围绕国有企业脱困目标推进国有资本战略性调整后,“十三五”时期,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下,我国将围绕更好服务于国家战略目标实施新一轮的国有资本布局战略性调整。本研究试图对经济新常态
下国有经济战略调整指导原则、基本方向和整体筹划进行初步研究。
二、“十三五”时期国有经济发展面临的新挑战与新要求
“十三五”时期我国经济环境最大的变化是步入经济新常态。习近平主席在2014年11月10日指出,我国经济新常态基本表现为经济增速从高速转为中高速、经济结构优化、经济增长动力转化三大基本特征[4]。2014年12月9日党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归纳了经济新常态在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出口和国际收支、生产能力和产业组织方式、生产要素、市场竞争、资源环境约束、经济风险、资源配置模式和宏观调控方式等九个方面的基本特征[5]。这些特征表明经济新常态是我国一个新的经济发展阶段。从我国的工业化进程看,我们研究表明,这个新阶段意味着我国进入了工业化后期,也就是说工业化后期正是步入经济增长新常态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大的趋势性变化,包括经济增长速度方面的经济增速放缓趋势,经济结构方面的经济服务化趋势和产业内部的结构高级化趋势,而在经济增长动力方面,供给方面的要素集约化趋势和去产能化趋势,以及由于这个过程还与国际上“再工业化”和第三次工业革命重合,出现了工业化与信息化、制造业与服务业深度融合的趋势(黄群慧,2015)[6],也就是说以前所熟悉的经济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与此同时,我国国家层面也推出了“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中国制造2025”等大的国家发展新战略,需要国有企业承担新的使命。面对“十三五”时期经济新常态的这些趋势性变化和国家发展新战略,对于国有经济而言,一方面环境变化对国有企业提出了新挑战,国有企业要生存和发展必须迎接挑战、适应新的环境变化——“适应新常态”;另一方面,新的经济发展阶段国家将赋予国有企业新使命,进而也给国有企业提出了新要求——“引领新常态”。
(一)适应经济增速放缓的新常态,积极转变国有经济发展方式
2001年到2011年,中国经济增长率年均为10.4%,而2012年、2013年和2014年的经济全年增速为7.7%、7.7%和7.4%,2015年第1季度和第2季度的经济增速均为7%。中国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2014)预测2016~2020年增长率预期为6.4%~7.8%;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长期增长”课题组预测2015~2025年平均增速为6.5%(刘世锦,2014)[7];中国社会科学院宏观经济运行与政策模拟实验室预测2016—2020年我国潜在经济增长率为5.7%—6.6%,2021—2030年潜在经济增长率5.4%—6.3%(李扬、张晓晶,2015)[4]。这意味着2012年以来的经济增速放缓是一个趋势性的变化,而不是一个周期性的短期下降、将来会“V”型反弹。对于这个趋势性变化,理论界分别给出了人口红利消失(蔡昉,2013)[8]、结构性减速(中国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2013)[9]等理论解释。在我们看来,这个趋势性变化是因为我国从2011年以后已经从工业化中期步入工业化后期,各国历史经验表明,工业化后期与工业化中期相比,一个重要的经济发展特征变化是在工业化中期由于依靠高投资、重化工业主导发展而支撑的经济高速增长将难以为继,工业化后期由于主导产业的转换、潜在经济增长率下降,经济增速将会自然回落(黄群慧,2014)[2]。
与我国快速工业化进程、投资驱动高速增长、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相适应,一直以来我国国有经济发展方式以投资驱动的规模扩张为主导。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大环境下,企业面临着众多的发展机会,模仿型排浪式消费需求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投资需求使得“跨越式发展”成为多数企业追求而且可以实现的发展战略目标。与民营企业的企业家机会导向驱动的“跨越式”发展方式不同,由于主客观条件使得国有企业更多地倾向选择投资驱动的“跨越式”发展方式,一是国家赋予国有企业承担国家安全、经济赶超等方面的国家使命,需要在涉及国家安全行业、自然垄断行业、重要公共产品和服务行业、经济支柱和高新技术产业中的国有企业在规模上迅速扩张与大型国外跨国公司抗衡;二是地方政府出于税收和地方经济发展业绩的需要,对地方国有企业迅速扩张规模有很大的需求;三是由于政府官员的任期制和国有企业企业家的组织任命制,国有企业决策者有更强的依靠投资快速扩张的动机。长期实践下来,国有企业也就更习惯于这种投资驱动的“跨越式”发展方式;四是经过国有经济战略性重组,与我国快速工业化进程相适应,国有企业大多处于需要高投资的重化工业;五是在融资体制机制上,国有企业具有得到大规模投资的更多的便利性。
随着我国经济阶段逐步步入经济新常态,经济增速从高速转为中高速,模仿型排浪式消费阶段基本结束,低成本比较优势不可持续,市场竞争从低成本转向差异化,要素规模驱动力减弱,经济增长将更多依靠人力资本质量和技术进步[10],国有企业所熟悉的投资驱动的“跨越式”发展方式已经无法适应环境的新变化。在新的经济发展阶段,国有企业要在明确自己的国家使命和功能定位的前提下,通过不断创新,实现有盈利的而非“高利的”、可持续的而非跨越式的发展。为此,需要积极推进对国有经济基于使命进行企业分类和功能定位、基于定位进行国有经济战略性重组、基于企业分类构造有利于创新的现代企业制度和治理机制等一系列重大改革任务和措施,进而促进国有经济从“投资驱动的跨越式发展方式”向“创新驱动的可持续发展方式”转变。
(二)适应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的新要求,积极推进国有经济布局结构战略性调整
对于经济新常态而言,更为关键的特征是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从三次产业间结构看,到2013年,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例达到了46.1%,而工业增加值占比为43.9%,服务业占比首次超过了工业,成为最大占比产业。无论是从中国的工业化进程看,还是从产业结构高级化趋势看,2013年服务业产值比例首次超越工业产值比例,在一定程度上都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转折点。而2014年服务业占比达到48.2%,高出工业占比5.6个百分点。2015年上半年服务业占比进一步提升到49.5%[2],经济服务化趋势明显。从工业内部结构看,高加工度化和技术密集化趋势明显,技术密集型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迅速。在整体工业增速下滑的背景下,工业中的原材料行业、装备制造业和消费品行业中,装备制造业增长迅速,居三大行业之首。从具体行业看,高技术产业增速一直高于工业平均增速,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生物制药、新能源汽车等行业发展尤为迅速[2]。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高技术产业的增加值过去两年持续保持在10%~12%的高速增长,比规模以上工业平均增速高出将近5个百分点[10]。与此同时,钢铁、电解铝、水泥、平板玻璃、造船等产业的产能过剩问题突出,传统经济与新兴经济呈现“冰火两重天”的增长格局,这更是彰显了我国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的必要性。
进入21世纪,与我国工业化中期阶段的工业化进程相适应,我国国有资本大多分布在重化工业。到2012年,我国工业和建筑业的国有资产占全国国有资产比重为43.06%,而工业中煤炭、石油和石化、冶金、建材、电力、机械等重化工行业国有资产占全部国有资产比重为78.44%[11]。应该说,对于工业化中期的中国发展而言,这些行业总体上关系到国计民生,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但是也必须看到,这些行业中,诸如煤炭、冶金、建材,都属于产能过剩问题比较突出的行业。实际上,伴随着我国进入了工业化后期和新技术革命的推进,一方面这些行业中一些产业的国家战略意义已经减弱,另一方面这些产业年度需求峰值已经达到,未来需求逐步减少,这些行业的产能过剩已经是绝对过剩。如果国有资本继续主要分布在这些行业,一方面国有资本的国家使命和战略意义将越来越不突出,另一方面国有企业效益也将受到影响,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国有企业做大做强做优的目标也将越来越难以实现。因此,在工业化后期的经济发展新常态下,国有经济要适应经济结构优化转型升级的新要求,积极推进国有经济布局的战略性调整。
(三)适应经济增长动力转换的新要求,以全面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推进创新驱动战略
进入工业化后期,决定经济增长的供给要素条件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从劳动力要素看,到2010年以后,由人口年龄结构产生的“人口红利”逐步消失,2012年和2013年,中国15到59岁劳动年龄人口分别比上年减少了345万和244万,劳动参与率自然也在不断下降,已经从2005年的76%下降到2011年70.8%;从资本要素看,工业资本边际产出率不断下降,2002年中国工业边际资本产出率为0.61,2012年则下降至0.28(江飞涛等,2014)[12]。这意味着在工业化后期劳动力、资本等要素驱动乏力,更为根本的动力来自创新,这正是所谓“创新驱动战略”的本意。这种创新既包括一般意义的技术创新,还包括深化改革开放意义的制度创新[2]。从技术创新意义上看,需要通过技术创新适应工业化和信息化融合发展的新趋势,促进传统产业不断升级和新兴产业的培育和发展,深化工业化进程,实现产业结构高级化,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从制度创新意义看,一方面通过制度创新可以破除阻碍我国现有生产要素充分供给的体制机制障碍,推进要素市场化进程,促进供给要素数量和供给要素效率的提升,另一方面制度创新可以破除我国技术创新的体制机制约束,提升我国技术创新效率,从而又促进工业化进程的深化,发挥深化工业化进程的推动力。这意味着经济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发展的新的“源”动力更大程度上表现为制度创新。
全面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构成了经济新常态下制度创新的重要内涵,成为经济新常态下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一方面,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的要求,国有资本投资经营要服务于国家战略目标,具体包括提供公共服务、发展重要前瞻性战略性产业、保护生态环境、支持科技进步、保障国家安全,这要求国有企业必须相应地调整自己的经营战略方向,基于这些国家使命要求来确定未来的战略方向[13]。通过经营战略调整和实施来实现支持科技进步、发展前瞻性战略性产业等使命,这样国有企业作为一种重要动力推动新常态下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全面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不仅有利于增加国有企业自身的活力,推动国有企业技术创新和市场竞争力,从而更好地实现做大做强做优国有经济进而推动整体经济增长的发展,而且还有利于创造公平竞争环境、建立有效的竞争秩序,从而有利于非公经济和整体经济的发展。例如混合所有制改革不仅有利于国有企业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激发了市场活力,还有利于避免“竞争性中立”约束、促进“走出去”战略的有效实施,同时还拓展了民营企业的成长空间。又如,自然垄断性行业的国有企业改革要进行业务战略调整,将国有资本更多地集中于自然垄断性的业务环节,而非整个行业链条,从而有利于提高整个行业的竞争程度和效率;再如,在过度竞争或者产能过剩的行业,国有企业要积极推进兼并重组战略,有利于一些行业建立合理的产业组织结构,形成有效率的产业集中度,提升整个行业的效益。
总之,面对“十三五”时期经济发展新常态这样经济环境的重大变化,以及国家实施“一带一路”、“中国制造2025”等新的重大国家战略,国有经济发展战略必然要做出重大变革,这不仅要求企业内部业务发展战略与组织结构做出相应的变化,更为关键的是要在国有经济宏观层面进行战略性调整,这既包括整体布局结构的调整,也包括产业组织结构的调整。如果说,从1996年以来以收缩国有经济战线为核心的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是第一次,这次在新常态下国有经济的战略性调整则是第二次,或者是再调整。新常态下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与第一次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最为本质的区别是,国有经济结构调整是以更好地服务于新常态下国家经济发展战略为目标,而不是以收缩国有经济战线为目标。这意味着国有经济结构再调整,不仅仅是做好国有资本的“减法”,还要做好国有资本的“加法”,围绕新常态下国家使命和国家经济发展目标实现国有资本的有效流动。
三、现有国有经济的布局结构与存在的问题
虽然广义的国有经济是指以经济资源归国家所有为基础的一切经济活动和过程,可以理解为国家所有的全部行政事业性和经营性资产及在此基础上衍生出来的经济活动,但一般论述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的“国有经济”,是在狭义层面上使用,主要是指经营性国有企业资产及其活动。
(一)国有经济总量不断扩大,但国有经济功能定位不明确
经过2003年以后的“国资发展”阶段,从总体上看我国国有经济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如果按照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的估算数据,2011年我国的国有经营性资产,也就是非金融企业国有总资产(含负债)为70.3万亿元(李扬等,2013)[14];根据《中国企业发展报告2015》(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2015)引自财政部和国资委的数据,2011年、2012年和2013年我国国有企业的合并报表总资产分别为85.38万亿、100.23万亿和104.1万亿,其中国有资本总量(国有实收资本及其享有的权益额)分别为21.99万亿、25.18万亿、29.60万亿。同样根据财政部的数据,2003年全国经营性国有资本7.0万亿元,而到2014年全国经营性国有资本达到33.7万亿元,年均增长超过30%。同期国有企业数量从146 446家上升到160 515家,增加了14 069家[11]。如果以2013年国有企业合并报表资产104.1万亿计算,我国国有企业资产和GDP的比例约为1.8:1,而2007年OECD(经合组织)国家的该比值为0.25∶1,这意味着我国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远比OECD国家突出。国有经济的快速发展[15],与国资委成立以后,建立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激励约束机制相关,也和国有经济大多处于快速增长的行业布局相关。但是,国有资本的快速扩张,引起了“国进民退”、国有资本利用行政资源获取垄断地位、损害了市场公平和效率等一系列的非议。这反映出实际上,考核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率并不是适合所有国有企业的,关键是要明确国有资本的功能定位是什么,进而考核国有资本是否实现了其定位要求,对于一些定位于公益性或者政策性目标的国有企业,并不需要考核其盈利或者国有资本保值增值率。现实的情况的是,由于我国并未对国有企业实施分类治理,没有对每家国有企业具体赋予其使命,许多国有企业的经营范围既包括市场化的业务,又包括政策性的业务,横跨竞争性领域和自然垄断性领域,结果造成国有企业会面临“盈利性企业使命”与“公共性政策使命”诉求的冲突。一方面,国有企业作为企业要通过追求盈利性来保证自己的不断发展壮大,这需要考核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另一方面,国有企业要弥补市场缺陷,定位为公共政策工具,服务公共目标,这要求牺牲盈利。这两方面定位要求,使得当前国有企业陷入赚钱和不赚钱两难的尴尬境地——不赚钱无法完成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壮大国有经济的目标,赚了钱又被指责损害了市场公平和效率、牺牲了公共服务目标(黄群慧、余菁,2013)[1]。由于国有经济布局总体覆盖了竞争性、自然垄断性和公共政策性等各类领域,而不同领域国有企业的经营目标又没有明确区分,甚至一家国有企业的经营业务就覆盖了各类不同性质的领域,再加之国有企业领导人具有行政官员和职业企业家的双重角色,也就是说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国有企业领导人,都存在混合定位或者定位不清的问题,这使得国有企业不能够成为一个真正的企业。因此,未来需要基于功能定位和使命要求调整现有的国有经济布局,对国有企业进行分类治理。
(二)国有经济主要分布于第二产业,但已经呈现向第三产业调整的明显趋势
单从中央企业看,2013年中央企业分布在第一产业的资产总额占全部中央企业资产总额的0.2%,第二产业占64.5%,第三产业占35.3%(宋群,2014)[16]。如果从全国国有企业看,在农林牧渔、工业、建筑业、地质勘探、交通运输、邮电通讯、批发零售、房地产、信息技术服务、社会服务业、卫生体育服务业、教育文化、科研技术、机关社会及其他等14个大行业中,2014年全国国有工业企业数量占比最大,为26.6%,2014年全国国有工业企业资本数量也是最大,占比达到33.32%。如果简单将工业、建筑业和地质勘探对等为第二产业,2014年国有企业资本约40%分布于第二产业。应该说,我国国有经济的产业结构与整体国民经济产业结构基本吻合。而且,总体上与我国的经济服务化的结构性变化趋势相适应,我国国有工业企业资本在全部国有企业资本占比自2007年逐年下降,在2007年国有工业资本占全部国有资本的比例还高达50.67%,7年间该比例下降了17.35个百分点,而同期在社会服务业的国有资本从9.05上升到24.07%,上升了15.02个百分点。如图1所示,将上述14个行业简单划分为第一产业(农林牧渔)、第二产业(含工业、建筑)、第三产业(含地质勘探、交通运输、邮电通讯、批发零售、房地产、信息技术服务、社会服务、卫生体育服务业、教育文化、科研技术、机关社会及其他),可以看出,2005年到2014年10年间国有资本在产业间的占比变化,总体上呈现第一产业占比一直保持在1%左右,而第二产业占比下降、第三产业上升的趋势。
(三)工业国有资本主要集中在重化工行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分布不足
如果按照财政部的工业行业划分,将工业划分为石油和石化工业、电力工业、机械工业(含汽车工业)、冶金工业、煤炭工业、烟草工业、化学工业、军工工业、电子工业、建材工业、医药工业、纺织工业、食品工业、森林工业、市政公用工业、其他工业等16个大行业,那么2003年以来工业国有资本主要集中在石油石化、电力、机械、冶金、煤炭等行业,这5个行业国有资本之和占整个工业行业国有资本的比例在2003年、2008年、2013年、2014年分别为66.03%、76.54%、73.31%、71.55%,如图2所示。其中石油石化和电力一直是占比最大的两个行业,基本占比在45%到50%之间,已有半壁江山;冶金行业的国有资本占比一直居第三位,2014年让位于机械工业;煤炭工业国有资本占比在2008年曾居第四位,但在2014年已经居第六位,低于机械工业和市政公用工业。机械工业和市政工业国有资本占比近些年显著提高,已分别从2008年的7.08%和3.05%提高到2014年的9.98%和7.54%,体现了产业结构高级化趋势和国有经济服务民生的功能定位。但是,总体而言,由于资本大多分布在传统产业,不少处于价值链的中低端环节,产能过剩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布局不足并存。一方面,中央企业有2亿吨过剩粗钢、约20%的氧化铝和约25%左右的水泥产能过剩,另一方面,有关节能环保、新兴信息产业、生物产业、新能源、新能源汽车、高端装备制造业和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国有资本比重低,中央企业中这类企业仅占10.62%(宋群,2014)[16]。根据中国工程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发表的《2015年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报告》[17],截止到2014年上半年,位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上市公司中63.5%属于民营企业,13.6%为中央国有企业,13.2%为地方国有企业。这意味着从工业行业分布看,国有经济在体现国家经济发展战略方向方面还缺乏足够的引导作用。在过去的十多年中,由于中国正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重化工业处于大发展的时期,工业国有资本这种战略性布局是合理的,正是过去十余年的重化工业的景气周期以及主要靠重大投资项目拉动的经济增长模式,使得国有经济部门资产与收入的规模增长相当可观。但是,中国正步入经济新常态,过去十几年中形成的国有经济倚重重化工布局和规模扩张的发展方式,已经无法适应工业化后期的经济新常态的要求[2],产能过剩、经济效益差的问题日益突出,工业国有资本亟需从产能过剩领域退出转向战略性新兴产业,形成适合经济新常态下的工业国有资本行业布局结构。
(四)地方国有企业资产总量不断增大,但效益低于中央企业
从隶属关系和区域分布看,地方企业国有资本占比近年来不断上升,大于中央企业国有资本占比,其中东部地区国有资本总量超过地方国有资本一半,但中西部地区国有资本占比呈不断上升趋势。根据财政部数据,截止到2014年,我国地方国有企业106373户,远远高于中央企业户数,占全部国有企业总数的67.1%;地方国有企业的国有资本总量为198911.8亿元,也高于中央企业的国有资本总量,占全部国有企业的国有资本总量的54.8%。自2008年以来,地方国有企业的国有资本占比不断上升,从2008年的41.3%上升到2013年的57.7%,2014年有所下降。从具体各省情况看,各省国资国企规模差异巨大,各省国资国企规模和经济发展水平相关,2012年资产排在前面的分别是江苏、上海、广东、北京、重庆、浙江、天津、山东等,其国有资产总量都超过两万亿元(马淑萍、袁东明,2015)[18]。2014年东部地区的国有企业数量和国有资本的总量都占全部的56%,中部和西部的国有企业数量分别为20.1%和23.4%、国有资本比重分别为18.0%和25.7%。从趋势上看,近些年中部和西部国有资本的占比呈现上升趋势,在2005年中部和西部国有资本占比只有11.6%和11.4%,这意味着中部和西部国有资本占比近几年提高了一倍左右。总体上看,地方国资国企的功能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承担供水、供气、公共交通等公共服务功能,二是承担城市发展和基础设施的建设开发功能以及土地、资金等要素供给功能,如重庆市属国有企业30%的资产集中在公共基础设施领域,湖北省仅交通投资集团一家企业的资产就占省属经营性资产总量的50%以上。三是承担培育支柱产业、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功能。例如,上海市属经营性企业资产80%以上集中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等关键领域和地方优势产业,湖南省属企业资产的71%集中在机械制造和冶金产业,陕西、河南省属国有企业资产主要集中在能源化工、装备制造、有色金属等行业(黄群慧,2015)[19]。相对于中央企业,地方国资的另外一个特征是总体回报较低,根据财政部《2013年国有企业财务决算报告》统计数据,虽然地方国有资产总额比中央国有资产总额多出6.9万亿,但2013年中央国企创造的净利润为1.2万亿元,约为地方净利润的2倍。这说明地方国企的收益水平和盈利能力不如中央国企(项安波、石宁,2015)[20]。另外,各地国有企业在收益水平、盈利能力上存在明显差异。根据2014年中国统计年鉴,2013年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利润总额和总资产贡献率分别为15 194.1亿元和11.9%,而各地区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这两个指标差异最大,前三位利润总额分别为陕西1371.1亿元、上海1313.9亿元、山东1214.0亿元,后三位利润总额分别为西藏0.91亿元、海南16.2亿元、青海37.6亿元;前三位总资产贡献率为黑龙江20.4%、上海18.2%、广东17.3%,后三位总资产贡献率为西藏1.1%、北京6.2%、山西7.3%。从隶属分布体现出地方国有资本迅速扩张和盈利能力差并存的特征,从区域分布上看这个特征在中西部表现更为突出,正面的可能原因是近年来地方尤其是中西部地区城市基础设施发展和公共服务功能的改善,但也折射出近年来地方政府过度负债问题的风险在扩大,以及一些后发地区也开始在重化工行业布局,加剧了产能过剩问题。从中央和地方国有资本功能定位看,地方国有资本更加合理的定位是地区的公共服务功能,中央国有资本更加适合发挥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引导作用,要针对这个定位来对现有的国有资本隶属和区域布局进行战略性调整。
(五)中央企业海外资产不断扩张,但面临“竞争性中立”的挑战
从国际化布局看,国有企业中中央企业发挥了关键作用,但未来面临“一带一路”战略下的使命要求和国际“竞争性中立”的严峻挑战。根据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外汇管理局2014年9月份联合发布的《2013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2012年底和2013年底,在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中,国有企业分别占59.8%和55.2%。2013年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已达5434亿美元。2013年,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为927.4亿美元,其中国有企业占43.9%;有限责任公司占42.2%,股份有限公司占6.2%,股份合作企业占2.2%,私营企业占2%,外商投资企业占1.3%,其他占2.2%,从中可以出国有企业是我国企业走出去的主力军。在国有企业中,中央企业发挥了更为关键的作用。例如,2005到2010年中央企业海外并购金额在全部企业并购金额中占比分别为83%、86%、80%、91%、76%、74%(易纲,2012)[21]。截止到2014年底,共有107家中央企业在境外设立8515家分支机构,分布在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十二五”以来中央企业境外资产从2.7万亿元增加到4.9万亿元(如果按照2013年中央企业总资产48.6万亿,中央企业的境外资产占比约为10%左右),年均增长16.4%;营业收入从2.9万亿增加到4.6万亿元,年均增长12.2%;中央企业境外投资额约占我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70%,对外承包工程营业额约占我国对外承包工程营业额的60%。尽管中央企业通过海外并购已开始了国际化进程,并开始参与国际产业分工与经营,但整体尚属于“走出去“的初级阶段,还缺乏对国际分工的深度参与,尤其是积极利用国际产业转移、加快产业全球布局的格局还没有真正形成(张毅,2015)[22]。从未来国有资本海外布局的战略调整看,需要注意两方面的问题,一是要积极响应“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积极拓展区域布局。迄今为止,我国国有企业走出去战略的海外区域布局主要还是香港、美国、澳大利亚、新加坡、英国等(不包括开曼群岛、英属维尔京群岛),按照2014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计算,2013年对外直接投资存量香港占比57%、美国占比3.3%、澳大利亚占比2.6%、新加坡占比2.3%、英国占比1.8%。从贸易看,2013年“一带一路”国家的进出口贸易总量占我国进出口总量的25%,中国进出口总量占“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贸易总量的11.5%(程军,2015)[23]。作为贯彻执行“一带一路”战略的主力军,国有企业任重而道远;二是国有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越来越受到美国倡导的“竞争性中立”规制的约束。美国在推动以TPP为核心的新的贸易与投资新秩序过程中,试图将国有企业界定为“深受政府影响”、“20%及以上的股权”,并试图对这些企业以“竞争性中立”规制对其国际化行为进行制约,包括通过“边境内措施”来规范政府对国企行为影响、通过严格报告和强制执行制度保证信息的全面及时披露、通过审查质询及制裁制度强化竞争性中立规制执行力等等。虽然现在TPP还在艰难的谈判过程中,我国国有企业未来需要未雨绸缪,既要通过各种手段影响TPP谈判过程利于我国国有企业走出去,又要积极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避开走出去的障碍(冯雷、汤婧,2015)[24]。
(六)国有企业创新资源和成果不断增加,但还不能满足创新型国家战略要求
从创新资产分布看,国有企业、尤其是中央企业集中了大量的优质创新资源,也取得了大量高水平研发成果,但创新方向和效率还不能够完全满足创新型国家建设、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使命要求。从创新资源看,截至2011年底,中央企业拥有科技活动人员和研发人员125万人,其中两院院士226人;中央企业R&D经费支出总额快速增长,从2007年不足1000亿增长到2011年的2747.21亿,年均增长29.4%;《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确定的我国需要突破的11个重点领域,中央企业都有涉及;16个国家科技重大专项,中央企业参与了15个;863计划的参与率达到29.5%,科技支撑计划参与率达到23.3%,即使在基础研究领域973计划中,参与率也达到13.5%。从创新产出看,全国国有企业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专利21.4万项,其中中央企业13.7万项;2005到2011年,中央企业共获得国家科技奖励467项,占国家科技奖励总数的24.6%,其中获得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3项,占特等奖的100%,一等奖44项,占57.9%,国家技术发明一等奖3项,占 37.5%;在载人航天、绕月探测、特高压电网、支线客机、4G标准、时速350公里高速动车、3000米深水钻井平台、12000米钻机、实验快堆、高牌号取向硅钢、百万吨级煤直接液化等领域和重大工程项目中,中央企业已经取得了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李政,2012)[25]。但是,一项实证测度研究表明,到2009年中国工业行业中58.8%的行业已经达到或者接近OECD(经合组织)主要国家的水平,但有11.8%的工业行业还大幅度落后于OECD经合组织主要国家的水平,这些行业主要是两类,一类是世界领域创新活动频繁、以医药和光电设备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型工业,包括医药制造,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机械制造业;另一类是垄断性强的工业,包括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煤炭采选业,石油天然气开采业,烟草制品业,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燃气生产和供应业,水的生产和供应业。这意味着,一方面要考虑加大创新资产在科技及高新技术研发方面的布局,加强在重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方面的技术投入,加强在相关业务上科技力量的配套布局;另一方面要深化国有企业改革(陆铭、柳剑平、程时雄,2014)[26],尤其是垄断行业的国有企业改革,激发国有企业的创新活力,从而提高国有企业的创新效率,尽快缩小我国技术差距,为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贡献力量。
(七)国有企业规模不断扩大,但产业组织结构还有待进一步优化
从产业组织视角看,国有企业户均国有资本规模不断扩大,但存在自然垄断性行业有效竞争不够与竞争性行业产业集中度不高的问题。自国资委成立以来,国有企业的规模扩张迅速,基于财政部国有企业财务决算报告数据计算,2003年国有企业户均国有资本只有0.48亿元,到2014年,国有企业户均国有资本上升到2.1亿元。根据2014年中国统计年鉴计算,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户均总资产2003年为2.76亿元,到2013年上升到18.8亿元,而同期私营工业企业的户均总资产从0.22亿元上升到0.9亿元,无论是规模,还是规模的增速,国有企业都远远大于私营企业。2014年,国有大型企业、中型企业和小型企业的国有资本占比分别是44.5%、22.5%和33%,国有资本主要集中在大型企业中。虽然国有企业规模不断扩大,但是我国的竞争性行业,与国际上相比总体上行业集中度仍不高,影响了企业的效益水平。以钢铁行业为例,美国、日本、韩国钢铁产业代表了世界的最高水平,这三个国家钢铁产业的集中度都很高,2007年美国、日、韩前4家钢铁企业市场占有率分别为68.7%、73.9%、88.87%,而我国前4家钢铁企业市场占有率只有35%;再如煤炭行业,目前我国前4大企业市场集中度仅占20%,前8家市场集中度也仅为28%,比较合理的比例应分别达到40%和60%(李荣融,2013)[27]。又如,中国制造业市场结构与美国相比,2007年的数据显示还是呈现高度分散型特点,在中国480个制造业四位数行业中,寡占型产业(H≥1000)仅有60个,占全部行业数的12.50%,而在美国435个制造业行业中,寡占型产业有134个,占全部行业数的30.8%。与之相反,在中国制造业市场结构中,极端分散型产业(H<100)有116个,占全部行业数的24.17%,高度分散型产业(100≤H<200)有106个,占全部行业总数的22.08%,而美国这两种市场结构类型比重分别只占全部行业总数的7.58%和6.67%(郭树龙、李启航,2014)[28]。另外,从世界500强视角看,中国世界500强企业的市场集中度水平与美欧日的世界500强企业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按2010年各国世界500强企业营业收入占全球行业总产值的比重计算,美国和欧盟在炼油化工、制药、汽车等行业的全球垄断地位十分明显,其世界500强企业占全球行业总产值的比重高达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中国目前只有炼油化工一个行业在2010年超过了世界行业总产值比重的10%,与欧美国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胡鞍钢等,2013)[29]。经过多年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在电力、电信、民航、石油天然气、邮政、铁路、市政公共事业等具有自然垄断性的行业中,国有企业占据了绝大多数。应该说,这总体上符合国有经济的功能定位,但是,并不是这些行业的所有环节都具有自然垄断性,一般认为,电力产业的输配电网,铁路行业的路轨网络,石油产业的输油管线,天然气行业的输气管线,电信行业的电信、电话和宽带网络,属于自然垄断的网络环节,而电力行业的发电、售电业务,铁路的运输业务,石油和天然气的勘探、销售业务,电信行业的移动电话、互联网、电视网络和增值业务等属于可竞争的非自然垄断环节。现在由于国有企业的经营业务涵盖整个行业的网络环节和非网络环节,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有效竞争,影响了社会服务效率[30],社会上对这些行业的国企意见比较集中,而且也正是这些行业,腐败问题也往往比较集中。实际上,这些行业的国有企业改革已经成为我国国企国资改革的焦点行业。
四、“十三五”时期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的方向与措施
“十三五”时期新一轮国有经济的布局结构战略性调整的目标,应该重“质”轻“量”,不再纠结于国有经济占整个国民经济的具体比例高低的“数量目标”*例如,有文献在研究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时,曾具体规划国有经济活动占GDP的比例从2012年的小于等于40%逐步降低到2020年小于等于30%、2030年小于等于20%。详见陈东琪等: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的方向和改革举措研究,载于《宏观经济研究》2015年第1期。,而应更加看重优化国有经济布局、促进国有经济更好地实现其功能定位和使命要求的“质量目标”。通过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新常态下的国有经济功能定位可以更加明确,更好地服务于国家战略与服务于民生目标,在创新型国家建设,“一带一路”、“中国制造2025”等国家战略中发挥关键作用;行业布局更为合理,国有资本绝大部分集中于提供公共服务、发展重要前瞻性战略性产业、保护生态环境、支持科技进步、保障国家安全等真正关系到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关键领域以及公益性行业的优势企业中,进一步增强国有企业在这些领域的控制力和影响力;明确不同类型国有企业之间、中央和地方国企之间的功能定位,使企业之间的层级布局结构关系更为科学;国有企业的规模和数量分布更加合理,形成兼有规模经济和竞争效率的市场结构;国有经济股权布局趋于优化,混合所有制经济蓬勃发展,国有经济活力更为凸显,形成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优势互补、融合发展的局面[30]。
(一)基于国有企业功能定位分类积极推进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深化国有经济改革的四方面重大任务,包括推进国有经济功能定位与战略性重组、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建立以管资本为主的新国有资本管理体制以及完善现代企业制度,我们认为这些改革任务的前提是国有企业的分类改革(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课题组,2013)[30]。面对庞大的国有经济,需要明确其功能定位和使命要求,在此基础上将国有企业分为三种类型,即公共政策性、一般商业性和特定功能性,或者说是公益类、商业一类、商业二类*根据2015年9月出台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国有企业被分为公益类和商业类,其中商业类又被分为两类,一是主业处于充分竞争行业和领域的商业类国有企业,二是主业处于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主要承担重大专项任务的商业类国有企业,这实际上也是分为公共政策、一般商业和特定功能三类国有企业。。由于现有的国有企业大多是三类混合,或者说没有明确其具体定位,因此在界定其功能定位的基础上,短期需要通过推进战略性调整来实现其企业分类,长期则通过建立以“管资本”为主的管理体制,利用国有资本投资公司和国有资本运营公司这两类平台实现符合其相应功能定位要求的国有资本合理、有效的流动。具体这三类企业的划分和相应的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的方向可参见表1。

表1 基于功能定位和企业使命推进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
(二)基于国家战略性和公共服务性标准科学调整国有经济产业布局
基于国有经济的基本功能定位服务于国家战略和公共民生的共识,经济新常态下我国国有经济产业布局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方向是重点发展国家战略性强和公共民生服务性强的产业。新常态下我国推出“一带一路”、“中国制造2025”等国家战略,同时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我国公共民生服务水平有了更高的要求,这要求将以前分布于产能过剩的重化工领域的国有资本,调整到与“中国制造2025”相关的高端与新兴制造业、与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相关的产业、与完善中心城市服务功能相关的产业等领域中。这构成了未来我国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的重要内涵。如表2所示,按照国家战略意义和公共服务意义的两方面标准,具体分析了各个产业在新常态下的地位变化,相应给出了国有资本在这些领域的布局变化,表明了国有经济产业布局的战略性调整的方向。
这里还应该强调说明四点。第一,随着经济服务化的趋势,未来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逐步下降,国有资本总体的调整方向是占比将会减少,但是工业的国家战略意义并不会降低,主要体现在创新型国家建设方面。同样我们期望国有资本发挥前瞻性、战略性的引导作用也主要体现在创新方面。无论是战略性新兴产业,还是“中国制造2025”的十大领域,国有资本进入都是期望能够发挥创新带动作用。虽然国有企业的创新作用一直存在争议,但是从我国创新资源分布看,也只有国有企业、尤其是大型央企才能真正担负起国家创新体系中重大自主创新生态系统的核心企业的角色。问题的关键是要形成科学的国企创新战略。国有企业要将更多的创新资源集中于重大自主创新生态系统的构建,通过整合创新资源引导创新方向,形成创新辐射源,培育具有前瞻性的重大共性技术平台和寻求突破重大核心技术、前端技术以及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先导技术,从而有效发挥国有企业在调整经济结构,产业转型中的带头和引领作用。
表注:“↓”表示该行业的国家战略意义下降,或者民生服务意义下降,或者国有资本可逐步减少;“→”表示该行业国家战略意义未发生变化,或民生服务意义未发生变化,或国有资本大致不变;“↑”表示该行业的国家战略意义上升,或者民生服务意义上升,或者国有资本可逐步增加。
从国家创新战略角度看,国有企业应当在三类重大共性技术平台建设中发挥主导作用,一是战略共性技术,这类共性技术是处于竞争前阶段的、具有广泛应用领域和前景的技术,这类共性技术有可能在一个或多个行业中得以广泛应用,如信息、生物、新材料等领域的基础研究及应用基础研究所形成的技术。二是关键共性技术,这是指关系到某一行业技术发展和技术升级的关键技术。三是基础共性技术,这是能够为某一领域技术发展或竞争技术开发作支撑的,例如测量、测试和标准等技术(黄群慧,2013)[31]。第二,同样是国有资本布局,中央企业和地方企业的国有资本布局的重点是不同的,中央企业国有资本布局重点体现为实现国家战略意图和全国性公共服务网络,而地方企业的国有资本布局重点应该主要体现为地方城市公共服务、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由于地方国资总量要大于中央国资总量,因此未来地方国资的改革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尤其是地方国资平台公司的改革,对防范我国经济风险、促进我国经济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第三,在那些国家战略意义和公共民生服务意义不突出的产业领域,国有资本原则上应该沿着逐步收缩的方向进行调整。即使是国有资本有所增加的产业领域,国有资本也主要应该以混合所有制方式进入,例如公用事业工程也应该大力推进PPP方式,要尽量避免以国有独资方式进入。第四,与表2中所列国有资本布局领域不同,“一带一路”战略所要求的是国有企业海外业务区域布局的调整。因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众多,国有企业需要针对各国情况差异寻求技术合作、产能合作、资源合作等,这些合作就不限于表2中所列的国有资本增加的产业领域。在“一带一路”战略下,国有经济战略性布局的重大调整表现为海外区域布局战略调整,要求国有企业“走出去”战略的重点更多地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转移。
(三)基于全面深化改革和优化市场结构双重目标协同推进国有企业并购重组
并购重组,是实施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的重要手段。2014年底,依托“一带一路”的国家战略,两大铁路设备制造巨头中国南车集团公司与中国北方机车车辆工业集团公司正式合并为中国中车集团公司,2015年5月,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与国家核电技术公司正式合并为国家电力投资集团公司,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后新时期中央企业的大规模并购重组拉开帷幕。2015年12月,中国远洋集团与中国海运集团宣布重组。这些并购重组在资本市场引起极大的关注。自国资委2003年成立以来,央企这类并购重组并不鲜见,通过并购重组,已经将196家中央企业减少到现在的110家,而且从国资委成立以后,就有报道说国资委也曾提出将中央企业数量缩小到30至50家的改革目标,只是迄今为止并没有实现。我们认为,这个目标是符合未来新常态下中央企业高效运营监管的实际的,应该积极推进中央企业的并购重组。但是,我们认为,通过国有企业并购重组调整国有经济布局,需要考虑到全面深化改革的需要,也要考虑到建立有效的产市场结构的需要,基于这两方面需要协调推进国有企业并购重组。从新时期全面深化国有经济改革需要看,一方面要通过重组解决自然垄断性行业的垄断问题,旨在优化相关业务配置和遏制垄断,形成自然垄断性行业的主业突出、网络开放、竞争有效的经营格局;另一方面要有利于建立以“管资本“为主的国有经济管理体制,通过并购重组能够推进十八届三中全会要求的组建国有资本投资公司和新建国有资本运营公司。从优化市场结构需要看,国有企业在特定行业内的企业数量既不是越少越好也不是越多越好,否则不是造成垄断就是造成国有企业过度竞争[30],国有企业兼并重组要有利于形成兼有规模经济和竞争效率的市场结构,有利于化解产能过剩问题。基于这样的考虑,我们认为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推进国有企业并购重组。
首先,选择市场竞争程度相对高、产业集中度较低、产能过剩问题突出的行业,包括资源类行业、钢铁、汽车、装备制造、对外工程承包等领域,在这类领域通过并购重组,减少企业数量,扩大企业规模,突破地方或部门势力造成的市场割据局面,促进形成全国统一市场,有效提高产业集中度、优化产能配置和促进过剩产能消化。需要强调的是,由于这类领域产能过剩突出、经济效益比较差,所以推进这类产业的并购重组应该是当前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的的重点和当务之急。
其次,在具有自然垄断性的领域,区分自然垄断的网络环节和可竞争的非网络环节性质,根据行业特点整体规划、分步实施,通过企业重组、可竞争性业务的分拆和强化产业管制等“多管齐下”的政策手段,推动可竞争性市场结构构建和公平竞争制度建设,使垄断性行业国有经济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更具活力的组成部分,改革和发展成果更好地惠及国民经济其他产业和广大人民群众[30]。如果说,第一次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将国企业务集中到具有自然垄断性行业上,那么,新常态下的再调整则要将国企业务集中到自然垄断性环节上。具体而言,要研究将电信基础设施、长距离输油输气管网、电网从企业剥离出来,组建独立网络运营企业方式的可行性。在可行性通过的基础上,可以考虑:(1)石油行业一方面要通过兼并重组、注入资本金等政策将中海油、中化集团整合成一家新的国家石油公司[30],另一方面要深化中石油和中石化内部重组,按开采及管道输油、炼油、设备安装制造、销售等环节组建若干专业化公司,开采及管道输油环节由这三家公司独资或者控股,其它环节引入民营企业组建混合所有制公司;(2)电网行业要在分离网络环节和非网络环节业务的基础上,实现国家电网公司和南方电网公司网络环节的合并,输配分离后,国家电网公司和区域电网公司经营输电网,配电网划归省电网公司,售电及设备制造等业务放开,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3)运输业中的民航业重点培育几家区域性航空运输企业,解决航空支线垄断程度过高的问题,把航油、航材、航信三家企业改造成由各航空运输企业参股的股权多元化的股份有限公司[30]。同时,铁路也要按区域组建若干家铁路运营公司;(4)电信行业按照基础电信业务(基站、固化网)和增值服务业务分别组建专业化公司,基础电信业务由中国移动、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三大公司控股,增值服务业务放开,发展混合所有制企业。
再次,积极推进“管资本”为主的国有资本管理体制的建设,应通过行政性重组和依托资本市场的并购重组相结合的手段,改建或者新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将分散于众多行业、各个企业的国有资产的产权归为这些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持有。我们认为,无论是竞争性行业,还是垄断性行业,其国有企业并购重组都应该与建立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相结合。对于竞争行业的国有企业的重组,应该通过组建国有资本运营公司的方式推进,重组后的国有企业产权由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持有;对于垄断性行业的重组,应该通过改建国有资本投资公司方式推进,重组后的国有企业产权由国有资本投资公司持有。当前推进的中央企业重组,没有与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要求相结合,属于单方面推进,将来还会面临再次重组的可能性。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在地方层面组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要特别注意应同时切断原地方的融资型平台公司与政府的融资功能的联系,使平台公司向市场化和实体化转型。
最后,对国资委监管系统之外的中央企业的重组,也应该有所考虑。除国资委监管的百余家企业和财政部、汇金公司监管的20余家企业外,近百个中央部门仍拥有近万家国有企业,它们将来也应被纳入国资统一监管的范畴,成为参与改革重组的重要主体,从而建立起“三层三类全覆盖”国有资本管理新体制(黄群慧等,2015)[32]。
五、结语
“十三五”时期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下推进新一轮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是一项重大的改革系统工程,需要科学规划、稳妥推进、协同配套。本研究给出了有关“十三五”时期经济新常态下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的方向和措施的一些建议,但在具体推进过程中还要制定具体的战略调整规划以及相应的政策法规,提出具体配套措施。尤其是推进新一轮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可能会出现各种风险,包括国有资产流失、职工权益受损、社会冲突和群体事件等,需要提前防范和积极应对。
参考文献:
[1] 黄群慧,余菁.新时期新思路:国有企业分类改革与治理,中国工业经济[J].2013,( 11).
[2] 黄群慧. “新常态”、工业化后期与工业增长新动力[J]. 中国工业经济 , 2014,(10).
[3]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N].人民日报 ,2015-11-04.
[4] 李扬,张晓晶.新常态:经济发展的逻辑与前景[J].经济研究,2015,(5).
[5] 王姝.中央首次阐释“经济发展新常态”九大特征[N].新京报,2014-12-12.
[6] 黄群慧. 工业化后期中国经济面临的趋势性变化与风险[J].中国经济学人,2015,(2).
[7] 刘世锦. 在改革中形成增长新常态[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
[8] 蔡昉. 认识中国经济的短期和长期视角[J].经济学动态,2013,(5).
[9] 中国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 中国经济转型的结构性特征、风险与效率提升路径[J].经济研究,2013,(10).
[10] 朱剑红.一个不错的增长速度[N]. 人民日报, 2015-07-16.
[11]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中国企业发展报告2015[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15:57.
[12] 江飞涛,武鹏,李晓萍.中国工业经济增长动力机制转换[J].中国工业经济,2014,(5).
[13] 陈东琪,臧跃茹,刘立峰,等.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的方向和改革举措研究[J].宏观经济研究,2015,(1).
[14] 李扬,等.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2013[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29.
[15] 陈小洪.国有经济的功能和分类:理论、趋势和政策[J].产业经济评论,2015,(1).
[16] 宋群.深化中央企业布局和结构调整研究[J].全球化,2014,(7).
[17] 中国工程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2015年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报告[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5.
[18] 马淑萍,袁东明.地方国有资本管理的探索与启示[N].中国经济时报,2015-02-13.
[19] 黄群慧.地方国企国资改革的进展、问题与方向[J].中州学刊,2015,(5).
[20] 项安波,石宁.鼓励地方因地制宜地探索国资管理模式,中国经济时报,2015-03-29.
[21] 易纲.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机遇、风险与政策支持[J].中国市场,2012,(12).
[22] 张毅.加快一带一路建设,推动国际产能合作[J].国资报告,2015,(7).
[23] 程军.构建金融发展大动脉、助推“一带一路“经贸大发展[J].世界经济调研,2015,(14).
[24] 冯雷,汤婧.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应对“竞争中立”规制[J].全球化,2015,(4).
[25] 李政.中央企业自主创新报告2012[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3:10-12.
[26] 陆铭,柳剑平,程时雄.中国与OECD主要国家工业行业技术差距的动态测度[J].世界经济,2014,(9).
[27] 李荣融.问题不是垄断,是行业集中度太低[J].市场观察,2013,(6).
[28] 郭树龙,李启航.中国制造业市场集中度动态变化及其影响因素研究[J].经济学家,2014,(3).
[29] 胡鞍钢,魏星,高宇宁.中国国有企业竞争力评价(2003-2011):世界500强的视角[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1).
[30]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课题组.论新时期全面深化国有经济改革的重大任务[J].中国工业经济,2014,(9).
[31] 黄群慧.中央企业在国家自主创新体系中的功能定位研究[J].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13,(3).
[32] 黄群慧,余菁,贺俊.新时期国有经济管理新体制初探[J].天津社会科学,2015,(1).
(责任编辑:刘越)
Strategic Readjustment of State-owned Economy in the Thirteenth Five-year Plan
HUANG Qun-hui
(Institute of Industrial Econom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836, China)
Abstract:In the 13(th) Five-Year Plan, it is of necessity to push forward the strategic adjustment of the layout of state-owned economy in order to accommodate the new economic normalcy of slowing economic growth, structural optimization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driving force. The current state-owned economy is large in amount but dispersed in functional orientation and over-concentrated on heavy industry. Besides, the local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re expanding their business quickly and facing problems such as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 neutrality and insufficient effective competition in monopolistic industries, and low degree of industrial concentration in competitive industries; their direction of innovation and efficiency cannot meet the requirement of constructing innovative country. It is proposed in this paper that the state-owned economy in the new economic normalcy should be readjusted strategically. Specifically, priority should be given to the "quality" rather than "quantity" of the economy, shifting the emphasis from the share the state-owned economy takes in the national economy to the optimization of the layout of the state-owned economy, in order to realize the functional orientation and quality objective of the state-owned economy. Three measures must be taken to achieve this purpose, namely, strategically adjusting the state-owned economy according the functional orientation, adjusting the layout of the state-owned economy according to the requirements of national strategy and public service, furthering the merger and restructuring of the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ccording to the objectives of comprehensively deepening reform and optimizing the market structure.
Key words:the Thirteenth Five-year Plan; new economic normalcy; layout of state-owned economy; strategic adjustment
中图分类号:F276.1;F123.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06(2016)02-0001-14
作者简介:黄群慧,男,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工业经济》、《经济管理》主编,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产业经济、企业管理。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制造2025’的技术路径、产业选择与战略规划研究”(15ZDB149);河南大学“新型城镇化与中原经济区建设河南省协同创新中心”资助项目。
收稿日期:2015-12-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