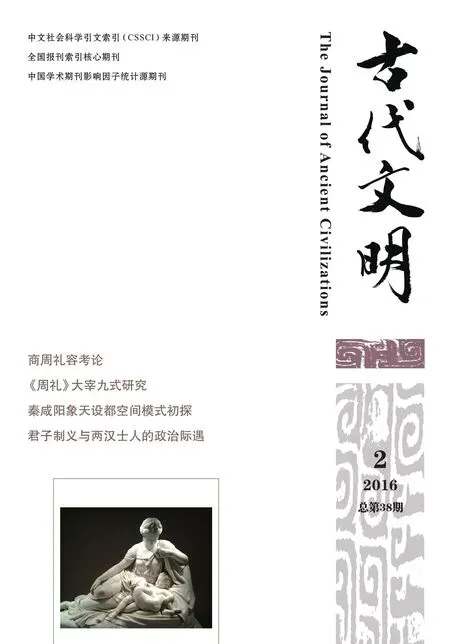秦咸阳象天设都空间模式初探
郭 璐
秦咸阳象天设都空间模式初探
郭 璐
提 要:象天设都是贯穿中国整个帝制时期的规划设计传统,秦咸阳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天下之都”,其象天设都的空间布局模式具有重要学术价值。本文试图绕开文献与考古实证不足的局限,从外围逼近核心,通过考察战国秦汉时期其他类型“象天制器”的模式得到基本猜想,进而对社会文化、科学知识及技术方法进行综合研究得到可能模式,再以此为纲,分析秦咸阳相关文献与考古资料,得到其象天设都的具体空间模式:天象垂直投影,中宫天极居中、东西南北四宫分别与地上四方相对,五宫星座与都城各片区人工建设一一呼应。这种关系的建立并非“机械投影”,而是在保持星座间的几何拓扑关系和文化象征意义的基础上,结合地面实际建设条件,进行适当协调、妥协,形成天地一体的空间模式。
关键词:秦都咸阳;象天;空间模式
* 本文受第57批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项目(项目批号:2015M570102)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项目批号:51378279)资助。
秦都咸阳1秦咸阳有144年(公元前351年—公元前207年)的建都史,其中前129年为诸侯国秦国的都城,后15年为秦帝国的都城,本文所讨论的主要是后者。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帝国的都城,其空间布局在继承先秦都城规划设计的基础上,开辟了一个全新的时代。象天设都是起源于先秦的规划设计思想,它贯穿于中国整个帝制时期的都城建设中,是论证政权合法性的重要手段,影响深远。秦都咸阳象天而设史有明载,对其空间布局模式进行研究对于中国古代都城史与城市规划史具有重要价值。现有研究已取得不少成果,但观点纷纭﹑莫衷一是,直接的历史文献与考古材料的不足是难以突破的瓶颈。本文试图运用新的研究方法,另辟蹊径,提出一家之言。
本文研究的基本思路是:从整体俯瞰局部,从外围逼近核心,从抽象走向具体。象天设都的空间模式不是孤立的,它与其他门类象天的“造型”模式是同一时代背景下的产物,有其社会文化﹑科学知识及技术方法上的必然性。可以首先考察战国秦汉时期可考的象天制器的模式,从中得到象天设都模式的猜想;在此基础上,对时人关于天﹑地结构及天地关系的文化观念与科学知识以及通用的城市规划设计的技术方法等加以研究,得到象天设都的可能模式;以此可能模式为纲,引领和组织对秦咸阳相关文献资料与考古材料的分析应用,得到其象天设都的具体空间模式。
一、秦都咸阳,象天而设
秦人本发源于陇东,秦孝公十二年(前350年),商鞅在渭北“作为咸阳,筑冀阙”,1司马迁:《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03页。次年秦迁都于此,惠文﹑武﹑昭襄﹑孝文﹑庄襄等数代君主在此基础之上不断有新的营建。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统一中国,开始在帝都咸阳进行大规模建设,兴建了六国宫殿﹑阿房宫﹑极庙等一系列宫室建筑,修复道﹑甬道以联系各宫室,治驰道﹑直道以通天下,并大量移民以充实咸阳。咸阳迅速地由“一国之都”成长为气势宏大的“天下之都”。(图1)
历史文献中明确记载秦都咸阳的规划布局中有象天设都的思想。《史记·秦始皇本纪》最为完整地记录了始皇扩建咸阳城的思想与过程,其中有两处明确提出其具有将天上星辰与地上宫殿相比附的思想:“作信宫渭南,已而更命信宫为极庙,象天极”,3司马迁:《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第241页。“为复道,自阿房,渡渭,属之咸阳,以象天极,阁道,绝汉抵营室也”。4中华书局1959年版将此断句为“为复道,自阿房渡渭,属之咸阳,以象天极,阁道,绝汉抵营室也”。(司马迁:《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第246页。)从考古发现来推理,阿房宫距离渭河较远,不可能直接从此渡渭,但是以其为起点再转而到其他位置渡渭是可能的,故而有本文的断句方式。“天极”﹑“阁道”﹑“营室”都是星宿的名称。《三辅黄图》成书于东汉或曹魏初,是保存至今的最早最完整的一部关于秦咸阳﹑汉长安的地记,其卷一有载:始皇“筑咸阳宫,因北陵营殿,端门四达,以则紫宫,象帝居”,5何清谷:《三辅黄图校释》卷1,《咸阳故城》,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22页。“紫宫”为天上星座,与渭北咸阳宫相应。张衡《西京赋》载:汉长安城“览秦制,跨周法……正紫宫于未央,表峣阙于阊阖”,6萧统编,李善注:《文选》卷2,《赋甲 京都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52页。说明汉长安仿效秦都,具有象天设都的思想。
将都城建设与天相联系是先秦时期即已产生的规划传统。在人类社会早期,即借助通天的巫术,显示权力与上天之间的密切联系,以保证统治的稳定性和权威性。伴随着社会发展,巫术色彩逐渐淡去,君主仍要借助一些手段向民众昭示其统治权来源于上天,以论证其政权的合法性。人力自然无法直接作用于天,“天人关系”往往是通过人对大地的经营,建立“天地关系”来实现的。《易·系辞》有云:“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7王弼﹑韩康伯注,孔颖达等正义:《周易正义》卷8,《系辞下》,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86页。“在天成象,在地成形”,8王弼﹑韩康伯注,孔颖达等正义:《周易正义》卷7,第76页。“王天下”是从仰观俯察﹑建立天地联系开始的。都城作为政治权力的中心,具有强烈的象征性和唯一性,在都城建设中模仿天象,就成为建立天人关系﹑树立政权合法性的一个重要手段。殷商人自诩都邑为“天邑”,自称王朝为“天邑商”,意即作邑建都追求上天的体认,按照上帝的意志安排都邑位置与筑邑时间。1《尚书·多士》:“予一人惟听用德,肆予敢求尔于天邑商”,孔颖达疏引郑玄注:“言天邑商者,亦本天之所建”。甲骨文中所记载的信息可为此提供证据:“王乍(作)邑,帝若(诺)。[王乍]邑﹑帝弗若。”(帝即上帝,详参刘桓:《殷墟卜辞“大宾”之祭及“乍邑”﹑“宅邑”问题》,《中国史研究》,2005年第1期。)据《吴越春秋》的记载,春秋时的吴国和越国在都城规划建设中都有象天的举措,伍子胥规划吴都时“象天法地,造筑大城。”2赵晔:《吴越春秋》卷4,《阖闾内传》,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2页,第25页。范蠡规划越都时“乃观天文,拟法于紫宫,筑作小城”。3赵晔:《吴越春秋》卷8,《勾践归国外传》,第107页。秦始皇统一天下后所推行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制度,都明显地是在先秦时期旧有制度的基础上整合﹑提炼﹑完善而成的,象天设都作为源远流长的城市规划设计传统对秦代的都城建设产生影响是十分自然的。
秦代具有象天设都的政治与文化土壤,“天人相应”是秦代主流的社会文化观念,是其政治制度制定的指导思想之一。权臣吕不韦主持编纂的《吕氏春秋·序意》篇中即明言:“爰有大圜在上,大矩在下,汝能法之”,4吕不韦著,陈奇遒校释:《吕氏春秋新校》卷12,《序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654页。《明理》篇中还对天象与人事的对应关系进行了系统分类和阐述,明确表达了天与人结构相同,人事与天事规律相近,可以互相感应。5吕不韦著,陈奇遒校释:《吕氏春秋新校》卷6,《明理》,第362-363页。秦始皇本人深信君权神授,追求天人沟通,多次出巡祭告上天以宣示政权的合法性,并冀图求仙海上,还重新制定了信仰和祭祀序列,6《史记·封禅书》载:“及秦并天下,令祠官所常奉名山大川鬼神可得而序也”。(司马迁:《史记》卷28,《封禅书》,第1371页。)追求政制与天道相呼应。营国制度作为政治制度中关键的一部分,追求与天相应﹑象天设都是很有可能的。
秦代也具有象天设都的知识与技术基础,这一时期天文学知识发达并日趋成熟﹑阴阳术数盛行。天文学在中国古代社会有特殊的重要地位,“三代以上,人人皆知天文”,7顾炎武著,陈垣校注:《日知录校注》卷30,《天文》,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695页。秦时已经有较为精确的天文观测,后世天文学主干之一的“二十八宿”这一名词首次出现是在《吕氏春秋·圆道》,《十二纪》和《有始》中还列出了部分或全部二十八宿星名,与后世星名和排序一致。《史记·天官书》虽成书于西汉中期,但汇总了有史以来,尤其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天文学成果,可以认为是秦汉时期皇家天文机构所掌握的天文知识的代表,8伊世同:《<史记·天官书>星象——天人合一的幻想基准(待续)》,《株洲工学院学报》,2000年第5期。其中全面系统地描述了全天星象与分野,星宿的位置功能﹑运行规律以及与占星相关的人间事务。与此同时,秦代的政治制度推崇阴阳数术,奉“五德终始”,行“四时之政”,阴阳家是一个精通天文知识并掌握堪舆﹑营建本领的群体,在这一群体的主导下,象天设都具有知识和技术上的可行性。
二、象天设都的可能空间模式
象天设都是先秦秦汉时期都城规划的一个重要传统,但是除了前文列举的少数文献之外,对其具体空间模式的记载非常稀少,零散的考古成果也难以呈现出象天设都的具体面貌。在具体条件无法摸清的情况下,可以转换思路,并非从一开始就针对咸阳进行研究,而是首先从外围进行概括性﹑整体性的探讨,将象天设都作为战国秦汉时期“象天制器”的一个门类,通过挖掘其他门类象天的形态模式的共同特点得到基本猜想,再根据战国秦汉时期的文化背景﹑知识基础探索可能模式,并通过对当时惯用的规划技术的研究来验证其可行性。
1,象天制器的共同特点:抽象表达而非具象模拟
在先秦秦汉时期,象天思想体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不仅是都城规划,在更小尺度的器物的制造中也多有体现,对此有比较明确的文献记载,可以看出象天制器的基本模式都是从自然天象中提取出某种相对抽象的形态模式,再根据所制之器的实际情况,找到相通之处,进行创造性地表达,而非刻板地具象模拟。如:车舆:“轸之方也,以象地也。盖之圜也,以象天也。轮辐三十,以象日月也;盖弓二十有八,以象星也”。1见郑玄注,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卷40,《考工记第六·辀人》,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914页。贾谊《新书·容经》中也有类似说法:“古之为路舆也,盖圆以象天,二十八橑以象列宿,轸方以象地,三十幅以象月。”(贾谊撰,阎振益﹑钟夏校注:《新书校注》卷6,《容经》,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230页。)古琴:“前广后狭,象尊卑也;上圆下方,法天地也;五弦官也,象五行也”。2蔡邕著,吉联抗辑:《琴操》,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90年,第1页。这是以形态象天。董仲舒有“服制象天”之说,其具体解释是:“剑之在左,青龙之象也;刀之在右,白虎之象也;钩之在前,赤鸟之象也;冠之在首,玄武之象也。四者人之盛饰也”,3董仲舒:《春秋繁露》卷6,《服制象天第十四》,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91页。这是以位置排布来象天;凡此种种,并无完全模拟星象﹑机械对应的例子。清崔述《考信录》在阐释《易经·系辞》中“观象制器”之说时提出:“不过言其理相通耳,非谓必规摹此卦然后能制器立法也。”4崔述:《补上古考信录》,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7页。这一思想也与象天制器的思想模式类同,核心在于“理相通”,而非刻意“规摹”,是抽象模式,而非具象模拟,在象天设都的过程中极有可能也是采取这样的方式。
当代对于秦都咸阳象天模式的研究中,不少学者认为宫室布局(或包括其他类型人工建设)是某一时段星象的具体投影,有谓冬至前后者,5徐卫民认为:冬至前后傍晚位于咸阳天顶的银河和仙后星座旁围的主要星宿与渭河横桥附近的主要宫苑的位置,被安排在一条垂直线上,使天象与地面互相对应。渭河象天汉,咸阳宫象紫宫,横桥象阁道,天极象阿房宫。(见徐卫民:《秦都咸阳的几个问题》,《咸阳师范学院学报》,1999年第5期)有谓十月黄昏者,6陈喜波认为:每年十月的黄昏时分,营室星正当南中天,北极星巍然不动,银河居中东西横跨,此时天空中的星象格局正好对应于地上渭水两岸的各个宫殿。咸阳宫象天极,阿房宫象营室。(见陈喜波:《“法天象地”原则与古城规划》,《文博》,2000年第4期。)王学理也有类似的观点,认为所据星象为9—11月,他还扩大范围,将秦咸阳的一系列宫殿都与当时之星象进行了比照。(王学理:《法天意识在秦都咸阳建设中的规划与实施》,见袁仲一编:《秦俑秦文化研究》,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421—425页。)这些研究肯定了咸阳象天设都思想的存在,指出了象天模式的可能性。但是,从规划设计实践的角度出发,城市规划是综合考虑功能需求﹑地理条件﹑文化观念等复杂因素的结果,这种直接对应的模式,缺少弹性,事实上较难应用于现实中。另有个别研究者提出咸阳象天并不拘泥于某时之星象,而是空间模式上的类同,贺业钜提出以咸阳城为“天极”,宫殿环绕如众星拱极的空间模式设想,7贺业钜:《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史》,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6年,第311页。刘九生则依据“内涵明确”﹑“方位确定”两条原则,将《史记·天官书》中的五宫星象与秦帝陵建设相联系。8刘九生:《秦始皇帝陵总体营造与中国古代文明——天人合一整体观》,《唐都学刊》,2013年第2期。这些研究虽然还比较概念化或局部,但是揭示出从抽象模式入手,研究秦都咸阳象天的可能性。
2,象天设都的可能空间模式:中心相对,四方相应
如何得出象天设都的抽象模式?首先,要明确秦代社会普遍接受的大地和天象的结构模式,可以发现“中心—四方”模式是时人认识世界的基本方法,天﹑地都被笼罩在这个结构模式中;其次,要明确其所认为的天地之间相互关系的模式,可以看出在“盖天说”的思想下,天地呈中心相对﹑外围相应的对应关系;两相结合,可以得到象天设都的可能“抽象模式”,即:中心相对﹑四方相应,当时通用的城市规划设计的技术方法也可证明这一模式的可行性。
自先秦至秦汉,人们认为“中心”与由其拓展而出的“四方”构成了他们所生存的物质世界的基本空间结构。早在殷商甲骨文的卜辞中,“四方”﹑“四土”等词已与“中商”等并举,频繁出现。9参卢央﹑邵望平:《考古遗存中所反映的史前天文知识》,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中国古代天文文物论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年,1—16页,冯时亦指出殷代四方风卜辞明确显示,四风与四方有着固定等对应关系(冯时:《殷卜辞四方风研究》,《考古学报》,1994年第2期。)四方﹑东土﹑西土等都习见于两周文献。《诗经·大雅·江汉》:“经营四方,告成于王。四方既平,王国庶定。”10此外,“四方”还见于《诗经》之《小雅·节南山》﹑《大雅》之《棫朴》﹑《皇矣》﹑《下武》﹑《民劳》﹑《周颂·执竟》;《尚书》之《牧誓》﹑《金滕》﹑《召诰》﹑《雒诰》等两周文献中。四方就是王所统治的天下,王位于天下之中,治理四方。这种“中心—四方”的结构模式一直延续到秦,从始皇二十八年东巡琅琊所刻石碑即可看出:“皇帝之明,临察四方……皇帝之德,存定四极……六合之内,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尽北户,东有东海,北过大夏。人迹所至,无不臣者。”1司马迁:《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第245页。成书于汉初的《礼记·王制》中也明确的体现出这种结构模式:“中国戎夷五方之民……东方曰夷……南方曰蛮……西方曰戎……北方曰狄。”2郑玄注,孔颖达等正义:《礼记正义》卷12,《王制》,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338页。这种“中心—四方”的空间模式贯穿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可以说是古人认识世界的一个基本工具,四方﹑四海﹑四夷﹑四至﹑四境乃至九州等等,都是这一空间模式下的产物。
时人对于天象结构的认识也无法脱离这一模式,斗极3北斗与极星的合称。《尔雅•释地》:“北戴斗极为空桐。”疏:“斗,北斗也;极者,中宫天极星,其一明者,泰一之常居也,以其居天之中,故谓之极。极中也,北斗拱极,故云斗极。”(郭璞注,邢昺疏:《尔雅注疏》卷7,《释地第九》,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616页。)居中,二十八宿分属四象,环列于周,同样形成一种“中心—四方”模式。对于北半球的人而言,天象的变化规律呈现出围绕北天极的“斗转星移”,北天极被认为是天空的中心,所谓“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4何晏等注,邢昺疏:《论语注疏》卷2,《为政第二》,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461页。北斗是近邻北天极最易于辨识的星宿,围绕天极旋转,具有指示方向的作用,“斗为帝车,运于中央,临制四乡”。5司马迁:《史记》卷27,《天官书》,第1291页。围绕着天中,古人将天球黄赤道附近的恒星划分为二十八组,即“二十八宿”,《周礼》中有“二十八星”之说,6《周礼·春官宗伯》:“冯相氏掌十有二岁﹑十有二月﹑十有二辰﹑十日﹑二十有八星之位”(郑玄注,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卷26,《春官宗伯第三·冯相氏》,第818页。)《周礼·秋官司寇》:“硩蔟氏……以方书……二十有八星之号”。(郑玄注,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卷37,《秋官司寇第五·硩蔟氏》,第889页。)《吕氏春秋》和《礼记·月令》完整地记述了二十八宿的名称和排列顺序。这二十八宿根据分布方位的不同,又分别归属于代表东南西北四个方向的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种神兽,亦即“四象”。《尚书·尧典》第一次将四星与四方对应,建立了将天空星象以正交方式分为四区的天空坐标体系,7明确记载了“四仲中星”的观测,鸟﹑火﹑虚﹑昴四星与四方相对应:“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旸谷。寅宾出日,平秩东作。日中,星鸟,以殷仲春。厥民析,鸟兽孳尾。申命羲叔,宅南交。平秩南为,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鸟兽希革。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饯纳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虚,以殷仲秋。厥民夷,鸟兽毛毨。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孔安国传,孔颖达等正义:《尚书正义》卷2,《虞书·尧典》,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19页。)《吕氏春秋》将二十八宿分为九野,事实上也就是四个正交方位的扩充细化;8《吕氏春秋·有始览》:“何谓九野?中央曰钧天,其星角﹑亢﹑氐;东方曰苍天,其星房﹑心﹑尾;东北曰变天,其星箕﹑斗﹑牵牛;北方曰玄天,其星婺女﹑虚﹑危﹑营室;西北曰幽天,其星东壁﹑奎﹑娄;西方曰颢天,其星胃,昴,毕;西南曰朱天,其星觜嶲﹑参﹑东井;南方曰炎天,其星舆鬼﹑柳﹑七星;东南曰阳天,其星张﹑翼﹑轸。”(吕不韦著,陈奇遒校释:《吕氏春秋新校》卷13,《有始》,第662页。)《淮南子·天文训》之五星﹑《史记·天官书》之五宫等都是将二十八宿按方位分为五组﹑并与四象一一联系。在出土文物当中也能够清晰地看到这种天象的结构模式: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的战国初期漆箱盖上绘有围绕一个“斗”字的青龙﹑白虎,四周漆书篆文二十八宿名称;9潘鼐:《中国恒星观测史》,上海:学林出版社,2009年,第10页。西安交通大学出土的西汉墓墓顶有环状的二十八宿带,图的东南西北四边有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定位,可以明确地看到二十八宿与四象﹑四方的对位关系。10呼林贵:《西安交大西汉墓二十八宿星图与<史记·天官书>》,《人文杂志》,1989年第2期。
战国末期至秦汉,天文学上普遍认可的宇宙模式是“盖天说”,11钱宝琮认为:“盖天说起源可能是在从战国末期到前汉初期的时期里。”成书年代约在公元前100年的《周髀算经》系统地运用定量的﹑几何模型的方式阐述了盖天说。(钱宝琮:《盖天说源流考》,见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编:《钱宝琮科学史论文选集》,北京: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377-403页。)在此思想之下,天地之间呈现出上下相覆,中心相对,外围相应的模式。盖天说认为“天象盖笠,地法覆盘,天离地八万里”,“极下者其地高人所居,六万里滂沱四隤而下,天之中亦高四旁六万里”。12《周髀算经》卷下,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年。在《吕氏春秋·有始览》﹑《淮南子·地形训》当中也有对天地中心相对的记述。2从“式”,这一先秦秦汉时期进行天文历算和方位测定的主要工具中可以更加清晰地看出这种结构模式。式盘分为两部分,上为圆形的天盘,下为方形的地盘,天盘中心绘有北斗,外围环以按星空方位排布的二十八宿,地盘则可明显看出是一个从中心发散,沿“二绳四维”3“二绳”互交,构成东西南北四方,“四维”互交并叠合于“二绳”之上,构成东北﹑西北﹑东南和西南。“二绳”与“四维”的交点被视为中方。向四面八方延伸的平面。4式盘模式多样,此为对其模式的概括归纳,详参李零:《“式”与中国古代的宇宙模式》,《中国文化》,1991年第1期。天盘中心有孔,可扣置于地盘的中轴上而旋转。(图2)由此可以看出先秦秦汉时人脑海中天地对应的空间模式是:天圆地方,天地呈垂直投影关系,上下相覆﹑中心相对,相应的环列的二十八宿便与地面上的“二绳四维”相呼应。
基于以上对战国秦汉时人所认可的大地模式﹑天象模式与天地关系的认识,可以得出象天设都的可能模式:中心相对﹑四方相应。上文所述是其在文化思想上的可能性,与此同时,也具有技术方法上的可行性。在先秦秦汉时期,通过立表测影辨别四方以确定中心与边界,是进行城市规划与设计的核心内容,《周礼》之《地官·司徒》与《考工记》中对此有详尽的记述,也就是运用圭表测影实现“辨方正位”的“土圭之法”,而圭表本身又是进行天象识别与测度的重要工具,5吴守贤编:《中国古代天体测量及天文仪器》,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8年,第364页。也就是说“辨方正位”的工作可以很便利地与观测星象的工作结合起来。那么,以“中心”与“四方”为线索来实现天之星象与地之空间规划布局的相互呼应也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班固《西都赋》在记述汉长安的营建时有云:“体象乎天地,经纬乎阴阳”,6萧统编,李善注:《文选》卷1,《赋甲 京都上》,第11页。可见体象天地﹑象天设都是与经纬阴阳﹑辨方正位紧密结合在一起的。
此外,历史文献中虽然没有明确记载象天设都的具体空间模式,但是从其上一个层次“天下”,与其下一个层次“建筑”的相关记载中可以明确的看到这种以方位为线索,中心相对﹑四方相应的空间模式。《史记·天官书》所载二十八宿与十二州的对应关系,明确地是以四方为依据的。7《史记·天官书》:“二十八舍主十二州,斗秉兼之,所从来久矣。秦之疆也,候在太白,占於狼﹑弧。吴﹑楚之疆,候在荧惑,占於鸟衡。燕﹑齐之疆,候在辰星,占於虚﹑危。宋﹑郑之疆,候在岁星,占於房﹑心。晋之疆,亦候在辰星,占於参罚。”《正义》:“太白﹑狼﹑弧,皆西方之星,故秦占候也。荧惑﹑鸟衡,皆南方之星,故吴﹑楚之占候也。辰星﹑虚﹑危,皆北方之星,故燕﹑齐占候也。岁星﹑房﹑心,皆东方之星,故宋﹑陈占候也。辰星﹑参罚,皆北方西方之星,故晋占候也。”(司马迁:《史记》卷27,《天官书》,第1346—1347页。)汉未央宫有:苍龙阙﹑朱鸟堂﹑白虎殿﹑玄武阙,亦与方向有关。1白虎殿:《汉书》中多次提及白虎殿,成帝建始四年,尽召“直言之士诣白虎殿对策”。(班固:《汉书》卷60,《杜钦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673页。)《汉书》卷九十八《元后传》:百姓歌云:“土山渐台西白虎”。成帝“微行出,过曲阳侯第,又见园中土山渐台似类白虎殿”。(班固:《汉书》卷98,《元后传》,第4024,4025页)王莽“大置酒未央宫白虎殿,劳赐将帅。”王莽见起义军进城,忙与群臣自前殿南下,“西出白虎门”,“就车,之渐台”。(班固:《汉书》卷99,《王莽传》,第4089﹑4191页)白虎门当为白虎殿之门,据此可知白虎殿在前殿西南渐台附近,渐台在沧池之中,沧池在未央宫西南。朱鸟堂,又名朱雀堂。《汉书·王莽传》:王莽令“孔秉等与州部众郡知晓地理图籍者,共校治于寿成朱鸟堂。”(班固:《汉书》卷99,《王莽传》,第4129页)莽改未央宫为寿成室,可见朱鸟堂在未央宫。又“王路朱鸟门鸣”,王莽以为吉祥,令四方之士“从朱鸟门入而对策”。(班固:《汉书》卷99,《王莽传》,第4144—4145页)王路即王路堂,王莽改未央宫前殿为王路堂。朱鸟门当是朱鸟堂之门,从朱鸟门入而对策之处当是前殿的主体建筑,据此可知朱鸟堂很可能就在未央宫前殿之南。苍龙阙﹑玄武阙:《史记·高祖本纪》:“萧丞相营作未央宫,立东阙﹑北阙﹑前殿﹑武库﹑太仓。”《集解》引《关中记》云:“东有苍龙阙,北有玄武阙,玄武所谓北阙。”(司马迁:《史记》卷8,《高祖本纪》,第385—386页)《三辅黄图》有云:“苍龙﹑白虎﹑朱雀﹑玄武,天子四灵,以正四方,王者制宫阙殿阁取法焉。”2何清谷:《三辅黄图校释》卷3,《未央宫》,第160页。也可以明确地看出这种以方向为依据的天地对应关系。
三、秦都咸阳象天模式与方法分析
基于以上的分析,本文将从“中心相对,四方相应”的抽象模式出发,挖掘和整合历史文献与考古成果中的线索,对秦都咸阳象天而设的具体规划布局手法进行推测与分析。研究中的具体天文知识以《史记·天官书》为主要来源,它是秦汉时期皇家天文机构所掌握的天文知识的集中的体现,3伊世同:《<史记·天官书>星象——天人合一的幻想基准(待续)》,《株洲工学院学报》,2000年第5期。并参考《吕氏春秋》﹑《淮南子》﹑《晋书·天文志》等相关文献。《史记·天官书》中将浑天星象划分五区,即所谓五宫:中宫是“紫微大帝”及其子属﹑正妃与藩臣所居,也就是斗极居中的位置,东宫苍龙,南宫朱鸟,西宫白虎,北宫玄武,分别包括了分布在四个方位的二十八星宿。
以“中心相对,四方相应”为基本线索,考察文献记载与考古成果,将秦都咸阳中心区域与东西南北四方的各项人居建设以空间位置关系为标准,分别与五宫星象进行比照,并以建筑功能与星象的象征意义相比照作为辅证。可以发现,秦都咸阳以极庙为中心,象征天极,区域中一系列宫室﹑苑囿﹑陵寝环列于周,象征东南西北四宫,形成了中心明确﹑秩序井然﹑气势宏大的区域性都城。
1,以极庙象征天极,确立地区中心
在天空的星象中,居中者为中宫天极,是整个天象结构的中心。在秦都咸阳的规划布局中,以始皇的生祠——极庙象征天极,确立了整个地区空间的中心。
始皇二十七年(前220年),于渭南修建极庙,这是始皇生前为自己修建的生祠,秦二世元年(前209年)奉其为“帝者祖庙”。4司马迁:《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第266页。极庙象征天极是《史记》明载的,“已更命信宫为极庙,以象天极”;5司马迁:《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第241页。关于天极的性质和地位,《史记·天官书》载:“中宫天极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6司马迁:《史记》卷27,《天官书》,第1289页。可见天极居于中心,为众星所环绕,在天空中的地位是至高无上的。这也与始皇所筑之极庙的地位是相应的,这是始皇的生祠,是帝都咸阳的中心。天极并非是指一颗星,而是代指中宫(又名紫宫),极庙周边在诸侯国时代已有章台﹑兴乐等宫,还有秦诸宗庙,这些都是渭南具有重要地位的建筑,它们将极庙环绕于中,共同组成象征中宫天极的宫殿群。其中极庙自当象征帝星,章台与兴乐二宫,环护极庙于左右,恰与匡衡十二星拱卫帝星的格局相似。
在中宫天极诸星中,北斗位于帝星之南,特别具有指明方向,联系四方的作用,《史记·天官书》有云:“斗为帝车,运于中央,临制四乡”,7司马迁:《史记》卷27,《天官书》,第1291页。角﹑南斗﹑参诸宿分别位处东﹑北﹑西宫,斗﹑极位于中央,与诸宫建立密切的联系。在修筑了极庙之后,始皇立刻着手修建以极庙附近为中心的道路系统,“自极庙道通郦山,作甘泉前殿,筑甬道,自咸阳属之……治驰道”。1司马迁:《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第241页。极庙一带正位于北通甘泉南抵子午的南北大道与东连郦山的东西大道的交汇点附近,似乎正象征了北斗“运于中央,临制四乡”的特点。(图1)
2,帝陵为东宫
始皇即位后即开始在位于当时的朝宫咸阳宫东南方向的郦山修治陵墓,但其在位的前十年,政权主要掌握在权臣手中,这一时期的陵墓营建应当也是由吕不韦等人主导的,可能就是东陵的扩展。十六年(前231年),始皇“初置丽邑”,充实人员,作为大规模开展陵墓建设的保障,而始皇陵真正大规模的营建是从始皇三十五年(前212年)开始的。2《史记·秦始皇本纪》载:“隐宫徒刑者七十余万人,乃分作阿房宫,或作丽山。发北山石椁,乃写蜀﹑荆地材皆至……因徙三万家丽邑,五万家云阳。皆复不事十岁。”(司马迁:《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第256页。)又载:“及并天下,天下徒送诣七十余万人,穿三泉,下铜而致椁,宫观百官奇器珍怪徙臧满之。令匠作机弩矢,有所穿近者辄射之。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机相灌输,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以人鱼膏为烛,度不灭者久之。”(司马迁:《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第265页。)《三辅黄图》载:“始皇穷极奢侈,筑咸阳宫,因北陵营殿,端门四达,以则紫宫,象帝居。”3何清谷:《三辅黄图校释》卷1,《咸阳故城》,第22页。其此处所述当为始皇统治早期,以咸阳宫为政治中心之所在,进行扩建,比象紫宫(即中宫)。这样来看,郦山位居咸阳宫东南,恰好位于东宫的位置上。天下统一后,都城中心南移,帝陵也仍在东方,可认为仍处于东宫的位置。
从《史记·天官书》的记载来看,东宫是一个帝廷﹑路寝﹑明堂﹑军队﹑市邑﹑臣属﹑庙宇等齐全的另一个天庭。如果将咸阳宫城所在视为中宫,是最重要的帝王之廷,那么陵墓选址在东宫位置,是另一个天庭之所在,也可认为在某种意义上印证了《吕氏春秋》中“世之为丘垅也……其设阙庭﹑为宫室﹑造宾阼也若都邑”的说法。4吕不韦著,陈奇遒校释:《吕氏春秋新校》卷10,《安死》,第542页。
进而,我们可以从空间位置和象征意义出发,将东宫各星与秦始皇陵的各项建设进行比照,从中可以发现一些可能的对应关系。(1)封土与氐。氐星代表“路寝”,5《史记正义》引《星经》云:“氐四星为路寝,听朝所居”。(司马迁:《史记》卷27,《天官书》,第1297页。)《西京赋》:“正殿路寝,用朝群辟。”李善注曰:“周曰路寝,汉曰正殿。群辟,谓王侯公卿大夫士也。”(萧统编,李善注:《文选》卷2,《赋甲·京都上》,第54页。)是处理国家大事的办公地点,也就是秦汉时期所谓的前殿,在建筑群中具有最为重要的地位,这与封土在陵墓建筑群中的地位相应。《三辅黄图》记载汉高祖刘邦的长陵在陵上作有建筑“以象平生正殿路寝也”。6何清谷:《三辅黄图校释》卷5,《宗庙》,第305页。(2)便殿与亢。便殿位于封土的西北方向,具有辅助性质。在氐星偏西北的方向上有亢星,代表外朝,7《史记·天官书》:“亢为疏庙”,《索隐》:“《文耀钩》:‘为疏庙’,宋均以为疏,外也;庙,或为朝也。”(司马迁:《史记》卷27,《天官书》,第1297页。)是听政之所在,与便殿的性质相近。(3)丽邑与天市垣。丽邑遗址位于今临潼区新丰街道办事处刘寨村附近,8《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始皇十六年(前231年)“置丽邑。”(正义》引《括地志》云:“雍州新丰县,本周时骊戎邑。”(司马迁:《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第232页。)又《史记·高祖本纪》汉高祖十年(前197年)“更名丽邑曰新丰”。(司马迁:《史记》卷8,《高祖本纪》,第387页。)由此可知汉新丰是在秦丽邑的基础上改筑而成。在帝陵陵园的北部。始皇曾经迁徙关东六国及秦内部的豪族大贾于此,以强本弱末﹑统御六国,同时“丽亭”﹑“丽市”等陶文91994年,在刘寨村东南杜村基建工地内发现大量砖﹑罐﹑盆﹑筒瓦﹑板瓦以及灰土﹑木炭等秦汉遗物,很多器物有陶文。陶文内容总计有3类49种。第一类为中央官署制陶作坊类,有“大匠”﹑“大毂”﹑“北司”﹑“宫丙”﹑“宫各”﹑“宫烦”﹑“宫易”﹑“宫之”﹑“宫□”﹑“居室”﹑“都船掩”﹑“右歇”;第二类为官营徭役性制陶作坊类,有“泥阳”﹑“西道”﹑“西处”﹑“安邑皇”﹑“安邑禄”﹑“安奴”﹑“宜阳工武”﹑“宜阳工昌”……第三类为市亭类,有“丽亭”﹑“丽市”。(王望生:《西安临潼新丰南杜秦遗址陶文》,《考古与文物》,2000年第1期。)的出土也都证明丽邑有市亭,有手工业与商业机构。在氐星的东北有由一组左右环绕的二十二颗星,即后世所谓的天市垣,分别以宋﹑齐﹑韩﹑楚等诸侯国的名称命名,其中又有四星曰天市,六星曰市楼。这与“隆上都而观万国”10萧统编,李善注:《文选》卷1,《赋甲·京都上》,第8页。且具有手工业与商业功能的丽邑是相呼应的。(4面积分别为:面积为1.426万平米﹑6000平米﹑520平米(4号坑未建成)(据: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编著:《秦始皇帝陵园考古报告1999》,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21—23页。))马厩坑与房。在帝陵陵园外城东南的上焦村一带有一个规模庞大的马厩坑遗址,埋藏有大量马骨和陶俑,代表中央厩苑。秦人向来以善于养马著称于世,2《战国策·韩策》:“秦马之良,戎兵之众,探前趹后,蹄间三寻者,不可称数也。”(《战国策》卷26,《韩策一·张仪为秦连横说韩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934页。)此遗址亦为至今为止在始皇陵周边发现的规模最大的陪葬坑。氐星东南为房星,“房为府,曰天驷”,3司马迁:《史记》卷27,《天官书》,第1295页。以马厩象房星自然在情理之中。且房星为东宫的重要星宿,与心宿同为东宫的主星,其地位也与马厩坑遗址的地位相应。(5)兵马俑陪葬坑与衿﹑舝。兵马俑陪葬坑位于帝陵以东,上焦村马厩坑东北,由4个大小不一的兵马俑坑组成,4面积分别为:面积为1.426万平米﹑6000平米﹑520平米(4号坑未建成)(据: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编著:《秦始皇帝陵园考古报告1999》,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21—23页。)一般研究认为其代表威震东方﹑护卫帝王的军队。在房星东北有钩衿二星,其北又有一星曰舝(辖),即键闭。钩衿二星为“天子之御”,5班固:《汉书》卷26,《天文志》,第1308页。“为主钩距,以备非常也。”6司马迁:《史记》卷27,《天官书》,第1296页。键闭亦为“掌管钥”之星。7司马迁:《史记》卷27,《天官书》,第1296页。可见,这一组小星均含有锁钥﹑防卫的含义,与兵马俑坑的功能性质一致,且其成组成团分布的特点也与兵马俑坑的布局特点有接近之处。
始皇帝陵直至秦末尚未完全建成,可以设想规划中可能还有其他的重要建设是与心﹑天角等东宫中的其他重要星座相对应,形成一个更加完整的天人相应的空间图景。(图3﹑4)
3,渭北宫室为北宫
在诸侯国时期,咸阳作为都城,其重心主要在渭北,建设了以咸阳宫为主的若干宫室。始皇统一天下前后,又开展了营建六国宫室﹑扩建咸阳宫等建设行为。在咸阳地区的象天格局中,渭北诸宫室正位于北宫位置。
将北宫各星与渭北宫室进行比照,可以发现彼此之间存在一定的相互呼应的关系。(1)咸阳宫与营室,渭桥与阁道。孝公自栎阳移都咸阳时即建有咸阳宫,后世又不断经营建设,长期以来都是咸阳最为重要的宫室,在始皇统一天下于渭南确立极庙为新的中心之后,位于渭北的咸阳宫在整个都城地区中的地位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史记·天官书》载:紫宫(即中宫)“后六星绝汉抵营室,曰阁道。”1司马迁:《史记》卷7,《天官书》,第1230页。天极为中宫,营室属北宫,阁道为中宫北端跨越天河的一组星,联系了天极和营室。《史记·秦始皇本纪》:“为复道,自阿房,渡渭属之咸阳,以象天极,阁道,绝汉抵营室也。”2司马迁:《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第246页。此意甚明,极庙是为天极,咸阳宫是为营室,阁道则为横跨渭河的渭桥。从其他文献记载来看,营室星代表天子重要的离宫别馆﹑布政之宫,3《史记·天官书·正义》:“营室七星,天子之宫,亦为玄宫,亦为清庙,主上公,亦天子离宫别馆也。”营室是重要的天子之宫。(司马迁:《史记》卷27,《天官书》,第1291页。)杨炯《少室山少姨庙碑》:“太微营室,明堂布政之宫。”(杨炯:《杨炯集》,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67页。)《史记·天官书》:“荧惑为勃乱,残贼﹑疾﹑丧﹑饥﹑兵……其入守犯太微﹑轩辕﹑营室,主命恶之。”(司马迁:《史记》卷27,《天官书》,第1317﹑1319页。)太微﹑轩辕都是天子理政的处所,将扰乱太微﹑轩辕﹑营室的星象共同视为战乱的象征,也可见营室与这二者有相近的性质。这一点是与咸阳宫的功能性质相同的;同时,营室又名定,是营建宫室的参照物,4《尔雅·释天》:“营室谓之定”,郭璞注:“定,正也,作宫室以营室中为正。”(郭璞注,邢昺疏:《尔雅注疏》卷6,《释天第八》,第2609页。)《诗·鄘风·定之方中》:“定之方中,作于楚宫”,即是此意。(毛公传,郑玄笺,孔颖达等正义:《毛诗正义》卷第3—1,《国风·鄘风》,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315页。)《史记·天官书·索隐》引《元命包》云:“营室十星,埏陶精类,始立纪纲,包物为室”。(司马迁:《史记》卷27,《天官书》,第1309页。)咸阳宫是定都咸阳时最早建设起来的最为重要的宫室,自然成为后世营建宫室时的参照。(2)六国宫室与虚宿。六国宫室是始皇仿效战败的诸侯国宫室所建,“秦每破诸侯,写放其宫室,作之咸阳北阪上,南临渭,自雍门以东至泾﹑渭,殿屋复道周阁相属。”5司马迁:《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第239页。这应当是一个较长的过程,从始皇十七年(前230年)灭韩开始,在统一天下后应达极盛,其具体位置今天尚无完全可靠的考古证据。6刘庆柱认为其在咸阳宫东西两侧,即牛羊村附近(刘庆柱:《秦都咸阳几个问题的初探》,《文物》,1976年第11期;刘庆柱:《<谈秦兰池宫地理位置等问题>几点质疑》,《人文杂志》,1981年第2期)王学理认为在今咸阳东的渭城湾到杨家湾之间的北原(王学理:《秦都咸阳》,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74页。)徐卫民认为在已经发掘过的秦都咸阳一﹑二﹑三号建筑遗址北的怡魏村一带,与王学理认为的位置相近(徐卫民:《秦都城研究琐议》,《浙江学刊》,1999年第6期。)史籍所载的六国宫室位于“咸阳北阪”且“南临渭”。根据今天的地形来看,渭河以北的地区从西南向东北抬升,故六朝宫室比较可能是位于咸阳宫的东北方向。北宫营室之东北有虚宿,《史记·天官书·正义》:“虚主死丧哭泣事……亦天之頉宰,主平理天下,覆藏万物。”7司马迁:《史记》卷27,《天官书》,第1309页。六国战败,是为“哭泣之事”,而秦则“平理”之,“覆藏”之,收六国之精华于此一隅。六国宫室应与北宫虚宿相呼应。(3)望夷宫与北落师门。望夷宫是秦代的重要宫殿。建于泾水之滨,有望北夷,护都城之意义。此处必定屯有重兵,守卫咸阳,抗击北夷。秦都咸阳“自雍门以东至泾渭,殿屋复道相连,周阁相属”,8司马迁:《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第239页。位于泾河边缘的望夷宫应当是都城宫殿区的北端边缘。在北宫星宿中,营室星正北9此处考虑的空间模式是将全天星象正投影,则天极位于正中,北宫位于其北,越远离天极则越北,这与传统天文研究中以天极为北的方位观不同。有羽林天军﹑垒﹑北落(又名北落师门)诸星。据《史记·天官书·正义》:羽林天军为“天宿卫之兵革出”,垒星为“天军之垣垒”,10司马迁:《史记》卷27,《天官书》,第1309页。都具有明确的军事防卫的功能。北落是营室之北的较为瞩目的大星,象征天军之门,北落师门的位置与性质与望夷宫一致,羽林天军﹑垒等星则象征望夷宫周边所屯守的重兵。(图5﹑6)
4 ,西部皇家苑囿为西宫
在诸侯国时期,咸阳周边便建有宫廷苑囿,昭王时秦有五苑,据《韩非子·外储说右下》记载诸侯国时期应侯请求将秦“五苑”中的“蔬菜橡果枣栗”发放给遭遇饥荒的民众。秦始皇时期对渭南苑囿多有扩建,《史记·滑稽列传》载始皇“欲大苑囿,东至函谷关,西至雍﹑陈仓”,11司马迁:《史记》卷126,《滑稽列传》,第3202页。后虽因优旃之谏而放弃,但是对于苑囿的小规模扩建却是可能的。
秦代苑囿的具体位置今已难考,《三辅黄图》有言:“汉上林苑,即秦之旧苑也。”12何清谷:《三辅黄图校释》卷4,《苑囿》,第230页。西汉在秦苑的废墟上建设了汉之苑囿,只能根据汉苑之记载来初步推测秦苑的范围。班固《西都赋》云:“西郊则有上囿禁苑,林麓薮泽,陂池乎连乎蜀汉。缭以周墙,四百余里。离宫别馆,三十六所。”2萧统编,李善注:《文选》卷1,《赋甲·京都上》,第10页。《三辅黄图》载有汉西郊苑,与此相类,3何清谷:《三辅黄图校释》卷4,《苑囿》,第244页。可见西郊应当是秦汉时期禁苑的核心区域。《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始皇三十五年(前212年),“乃营作朝宫渭南上林苑中”,4司马迁:《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第256页。证明秦时渭南有上林苑,其范围史无详载。亿里根据《史记·秦始皇本纪》﹑《长安志》﹑《秦封宗邑瓦书》等的记载及秦代行政建置的情况,认为上林苑范围基本是“西界沣水,东至今西安市劳动公园,北起渭水,南临镐京”。5亿里:《秦苑囿杂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6年第2期。这一范围恰是在极庙﹑章台﹑兴乐等宫殿群的西南方向。此外,秦咸阳西南方有一组供帝王游猎的宫苑,包括长杨宫﹑萯阳宫﹑五柞宫等。6《汉书·地理志》,盩厔县注云:“有长杨宫,有射熊馆,秦昭王起。”(班固:《汉书》卷26,《地理志》,第1547页。)《三辅黄图》:“萯阳宫,秦文王所起,在今鄠县西南二十三里。”“长杨宫,在今盩厔县东南三十里,本秦旧宫……门曰射熊观,秦﹑汉游猎之所”;(何清谷:《三辅黄图校释》卷1,《秦宫》,第27﹑37页。)《元和郡县志》卷二:“秦五柞宫在(鄠)县东南三十八里。”(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2,《关内道二》,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31页。)这一组宫苑位于终南山北麓,毗邻涝水,山林秀美,风景宜人,研究者普遍认为此间为秦一大禁苑。考古与文献记载也证实,秦咸阳在渭南的主要池沼也都在极庙西南方向,包括牛首池﹑镐池﹑滮池等。(见表1﹑图7)
秦汉时的皇家禁苑与后世主要用于观赏游乐的皇家园林不同,它物产丰富,并饲养羊﹑鹿等牲畜以供给郊祀或宴客,同时也是天子射猎的场所。扬雄《羽猎赋》记述其可提供“蔬菜橡果枣栗”,“财用足以奉郊庙,御宾客,充庖厨”,7萧统编,李善注:《文选》卷8,《赋丁·畋猎中》,第387页。《汉旧仪》中记载上林苑中饲养有百兽,可供祭祀﹑宴飨﹑射猎等。8《汉旧仪》:“上林苑中昆明池﹑镐池﹑牛首诸池,取鱼鳖,给祠祀。用鱼鳖千枚以上,余给太官。”“上林苑中,广长三百里,置令丞左右尉,百五十亭苑,苑中养百兽,禽鹿尝祭祠祀,宾客用鹿千枚,兔无数,佽飞具缯缴,以射凫雁,应给祭祀置酒,每射收得万头以上,给太官。上林苑中,天子遇秋冬射猎,取禽兽无数实其中,离官观七十所。皆容千乘万骑。武帝时,使上林苑中官奴婢,及天下贫民赀不满五千,徙至苑中养鹿。因收抚鹿矢,人日五钱,到元帝时七十亿万,以给军击西域。”(卫宏撰,孙星衍校:《汉旧仪》卷下,王云五主编:《汉礼器制度及其他五种》,上海:商务印书馆,1939年,第16—17页。)《史记·平准书》也记载上林苑中养有羊。9初,式不愿为郎。上曰:“吾有羊上林中,欲令子牧之。”式乃拜为郎,布衣屩而牧羊。岁余,羊肥息。(司马迁:《史记》卷30,《平准书》,第1432页。)
据《史记•天官书》的记载,西宫诸星可提供祭祀牺牲(娄)﹑五谷(胃)﹑粮草(刍),可用于游猎(毕)﹑饲养禽兽(天苑)。这些功能与秦皇家苑囿的功能是一致的,其位居西方的位置也与处于极庙宫殿群西方的诸苑囿相当。西宫有咸池星,代表天池,也是太阳洗浴的地方,2《楚辞·九歌·少司命》:“与女沐兮咸池”,王逸注:“咸池,星名,盖天池也。”(王逸《楚辞章句》卷2,《九歌·少司命》,四库全书,1953年,第11页)《淮南子·天文》:“日出于旸谷,浴于咸池。”(刘安:《淮南子》卷3,《天文训》,第32页。)这与位于极庙以西的诸池沼的位置和含义是相应的。
5 ,营阿房以象南宫太微
始皇三十五年,欲于渭南营建新的朝宫,首先营建规模宏大的前殿,这是新朝宫最为重要的宫室,因建于“阿房”,故名为“阿房宫”。3关于阿房宫﹑阿房前殿﹑前殿阿房等名词的概念范围多有讨论,如:王丕忠:《阿房宫与<阿房宫赋>》,《西北大学学报》,1980年第3期;王学理:《“阿房宫”﹑“阿房前殿”与“前殿阿房”的考古学解读》,《文博》,2007年第1期;辛玉璞:《“阿房宫”含义别说》,《秦文化论丛》第2辑,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7年。本文根据《史记·秦始皇本纪》的记载,认为阿房为地名,或者对该地的描述,所谓“先作前殿阿房”,“作宫阿房”,相当于是“先作前殿于阿房”,“作宫于阿房”,因而阿房宫是建于“阿房”的前殿的临时名称。作为一期工程的前殿直至秦末尚未完工,则新朝宫未被命名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本文就直接以新朝宫称之。前殿工程的规划设计非常宏大,但直至秦末也未完工。今天考古发现的前殿遗址位于古皂河以西,渭河以南,今赵家堡﹑古城村一带。4李毓芳﹑孙福喜﹑王自力等:《阿房宫前殿遗址的考古勘探与发掘》,《考古学报》,2005年第2期。这一位置处在极庙﹑章台﹑兴乐这一建筑群的西南方向。
据《史记·天官书》的记载,南宫有衡宿,即后世所谓的太微垣的主要构成部分,这是天帝的南宫,乃三光(日﹑月﹑五星)入朝的宫廷,其前后左右有大臣﹑大将﹑执法的官员﹑诸侯﹑蕃臣等坐。其旁有权宿,又名轩辕,象征后宫。1司马迁:《史记》卷27,《天官书》,第1299页。《淮南子·天文训》中论述了太微与紫宫的关系:“太微者,太一之庭也。紫宫者,太一之居也。”2刘安:《淮南子》卷3,《天文训》,第29页。也就是说太微是天帝处理政务之宫庭,紫宫为天帝居处之寝宫。太微的性质及其位置是与阿房宫的功能及其与极庙的相对位置相呼应的。可以推断阿房宫可能是象南宫太微而建。此外,史载阿房宫“表南山之巅以为阙”,3司马迁:《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第256页。南宫有天阙星,即阙丘二星,象征“天子之双阙”,4司马迁:《史记》卷27,《天官书》,第1302页。此二星在太微以南,似与阿房宫所表之阙有呼应关系。
6,对都城地区宫室的整体充实
始皇规划的渭南新朝宫事实上只兴建了前殿阿房宫,且尚未最终完成,但是从历史记载来看,这一时期,始皇有一个规模宏大,对都城地区的宫殿进行整体充实的宏伟规划。《史记》载:始皇三十五年(前212年),“乃令咸阳之旁二百里内,宫观二百七十,复道甬道相连。”5司马迁:《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第257页。《三辅黄图》载始皇广扩宫室:“规恢三百余里,离宫别馆,弥山跨谷,辇道相属,阁道通骊山八十余里。”6
如前文所述,秦始皇将渭河两岸,南至终南山,北至泾水,西至长杨﹑五柞宫,东至丽山园,包括宫室﹑陵墓﹑苑囿﹑自然山脉与河流等的广阔区域,以一个统一的思想规划为一个整体,以极庙为中宫天极,其他四宫各有所象。西起长杨,东至丽山,大约为80余公里,汉一里约为417.5米,7陈梦家:《亩制与里制》,《考古》,1966年第1期。这一范围正是所谓“咸阳之旁二百里”的范围。始皇在统治的最后几年中有一个对这一范围进行全面的充实和建设的宏大规划,可以想见,如若这一规划完全实现,以极庙为中宫天极,宫观苑囿与天空中之星象相比附,环绕于四周,将是一幅天地交辉﹑群星灿烂的壮阔图景。(图8)
四、小结
通过对秦都咸阳的研究可以发现,在咸阳及其周边地区的规划设计中确实存在着象天设都的思想。其主要模式是以天极为中心,四方相对,天地垂直投影,根据位置关系,建立天上之星座与地上之人工建设之间的关系。值得注意的是,一定时期内,人们对于天象的认识是一定的,但是规划设计对象的自然地形﹑既有建设条件则各有不同,不可能将一定的天象完全机械地“投影”到地面上,而是要通过人的巧思,在保持天空中星象的几何拓扑关系及象征意义的基础上,根据地面上的实际条件,进行协调﹑妥协,从而将在天之象与在地之都完美地融合为一个整体。《史记·太史公自序》引司马谈《论六家要旨》:“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不先定其神,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8司马迁:《史记》卷130,《太史公自序》,第3292页。象天设都的模式也体现出这样的特点,以神(即精神内涵与基本规律)为本,不完全拘泥于具体的形态。
秦始皇对秦都的大部分建设是在前人基础上改建﹑扩建而成的,并不是完全的新创。始皇正式掌握政权之前,帝陵已经开始营建,渭南咸阳宫沿用日久,已有章台﹑兴乐﹑上林等,阿房据载亦已在惠文公时有所营造。秦始皇在此基础上,基于象天设都的思想,对原有宫室进行了有选择性的扩建,并适当地增添新的建设,对原有的建设秩序进行了重新的建构,并不断有所调整,脱胎换骨般地形成了一个气魄宏大﹑意味深远﹑前所未有的全新的天下之都。《淮南子·诠言训》有言:“神贵于形也。故神制则形从,形胜则神穷。”9刘安:《淮南子》卷14,《诠言训》,第159页。这个过程中规划设计所具有的“神”,起到了“点石成金”的作用,使得原本普通的物质空间之“形”,具有了特殊的精神内涵,所谓“全新”,不是物质建设的全新,而是精神气象的全新。
象天设都,它的表现是天地关系的建立,它的目标是天人关系的融合,而它的产生是人地关系的作用,其对象是地面上的物质建设,其主体是人。正如《吕氏春秋·序意》所谓:“上揆之天,下验之地,中审之人。”2吕不韦著,陈奇遒校释:《吕氏春秋新校》卷12,《序意》,第654页。《易·系辞》有云:“神而明之,存乎其人”。3王弼﹑韩康伯注,孔颖达疏:《周易注疏》,第262页。空间布局的“神”是与人的社会文化信仰与精神追求息息相关。一方面是主事者,秦始皇有并吞六合的千古一帝之宏大气魄,始有秦都咸阳之高远境界。事实上,帝都咸阳的规划设计过程是伴随着始皇对政权的掌握和思想的变化而逐步推进的,从萌发,到确立,再到盛大,即便在其身后,按照其思想制定的既有之规划仍然起着绝对的主导作用,象天设都是其大一统制度建设的一部分。另一方面是受众,象天设都有明确的宣示政权正统性的作用,因而必然需要得到民众的理解和接受,这有赖于人文观念中对天人相应的笃信以及继承战国又不断拓展的天文知识基础。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咸阳象天虽史有明载,但是由于历史文献与考古成果阙如,秦都咸阳的具体城市格局在学界尚无明确共识,渭南新朝宫等始皇心目中的宏伟规划蓝图亦未完全实现,故而本文所提出的象天设都的格局只是对一种可能性进行探讨,希望藉此探究其基本模式和思想方法,而非刻意考证具体细节,敬请方家指正。
[作者郭璐(1986年—),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博士后,北京,100084;英国李约瑟研究所访问学者,Cambridge CB3 9AF UK]
(责任编辑:王彦辉)
【帝制中国】
[收稿日期:2015年11月3日]
DOI:10.16758/j.cnki.1004-9371.2016.0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