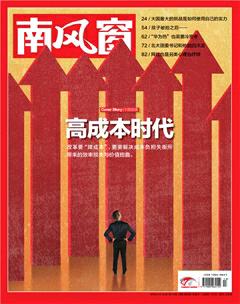两种创业,一种重压
张墨宁
在一个社会成本普遍升高的时代,创业公司不可能永远享受低成本,也很难在经济转型时期独善其身,近两年的轻资产创业浪潮既是资本对低投入、高回报的追逐,而另一方面,这也反映出高成本下的恐慌。
在互联网创业圈,经常能听到这样的传奇故事,投资人追在创业者身后,以近乎央求的语气允许他能投钱进来,哪怕少一点也行。而创业者冷眼相对:“不好意思,我们有更适合的合作伙伴了。”
这当然不是创业与资本市场的普遍关系,大多数人还是要不断找钱,直到有人看好自己的项目。不过,这也能说明,与制造业相比,互联网创新的确更容易拿到融资。
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创业其实分两种,一种是重资产的创业,一种轻资产的创业。前者受地租、人工等高成本因素的影响程度较重,而后者相对较轻。
比如,不少人会认为,互联网创业会因为其“轻资产”和低边际成本,可以避免部分制度交易成本,而一定程度化解高成本的重压。但实际上,在中国经济进入普遍的“高成本时代”之时,这样的创业是否真的会成为一个例外,或许还是个未知数。
资金虽过剩,成本却不低
2014年,全国新登记注册市场主体1292.5万户,注册资本20.66万亿元。新登记注册企业365.1万户,同比增长了45.88%。创业主体的持续、快速增长,标志着新一轮的创业浪潮正在来临。
2015年,平均每天有1.2万家市场主体诞生。资本正在抛弃实体经济转向虚拟或者其他服务领域,催生了创业的相对低成本运作。尽管失败率非常高,但风险更多来自于商业模式成功与否,而不像制造业那样,受到生产要素成本、全球市场变化以及政策风险各方面的挤压。
看起来,“低成本、高回报”的行业在近两年形成了一个“泡沫”,也吸引了很多精英“回流”中国。出生于1990年的北京人阴明就是其中之一。
“一个行业的爆发肯定要有泡沫,有了泡沫,这个行业才能发展,比如说唐诗时代,就是诗歌的泡沫,但会让一代人里面的佼佼者全都投身于这个事业,从而产生伟大的人,如果没有创业热潮的话,斯坦福毕业的人根本不会回北京的。”阴明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此后申请至剑桥大学学习计算机科学。
读研究生期间,他和几个朋友做了一个留学数据库,可以检索某个学生申请了哪所学校,成绩如何,最后有没有申请成功。他当时并不知道国内的创业已经炙手可热,只是出于兴趣看是否能吸引更多的学生,聚集足够的用户之后,才图商业价值。
那时候,他还没有成熟的构想,但已经有投资人看中。于是,阴明回到了国内。2014 年 10 月底开始了第二个项目,以硅谷流行的 Product Hunt 模式来推荐优秀的互联网人才。一个月后,项目便获得了天使投资。今年年初,已经有千万级的A轮投资。现在的“稀土掘金”形成了一个技术人群的社区,主要靠广告和人才对接盈利,虽然已经有营收,但还不足以覆盖成本。
这个年轻人此前唯一的“管理经验”就是高中时期当过宣传委员。这样的履历在中关村并不独特。但低成本、高回报又有很多技术含量的互联网创业无疑改变了工业化时代的游戏规则,这给了他足够的机会。
“互联网创新企业的负担确实比较轻,因为我们是在尝试,尝试本身就是成本,但让你尝试的那个人在内心已经做好了出错的准备,这个风险是有人跟你共同承担。”阴明说,所谓的投资,就是你在钱上不用多想了,可以把心力更多永远产品上。
不过,梁佟有不同的看法。她是一家在线教育互联网公司的创始人,2012年前后开始创业,那时资本市场还处在一个升温的阶段。不到一年的时间,资本对在线教育的追捧程度就已经非常火爆了。
“我觉得拿钱容易和资金成本低是两回事,比如说股权融资,成本其实是非常高的。因为创业的成功率很低,意味着成功的企业就要背负投资人其他失败案例的成本,他们对资金回报是有要求的,如果十个里面有九个企业倒掉了,投资人就会把所有的期望都放在成功的企业身上。所以,对股权以及未来的业绩回报都有比较高的要求。”梁佟说。
2013年,她就拿到了天使投资,在现在的股权比例里超过20%,当时的投资是300万元,现在已经接近3000万元了。“相当于两三年内获得了十倍的增值回报,这个一定是比银行收益高吧。”她说,2015年,公司又拿到了1500万A轮投资,附带需要有业绩回报的对赌条件,核算之后,成本其实是非常高的。梁佟说:“尽管我们不是制造企业,但也一直在为资本付出很高的代价。”
资本对创业公司回报率的高要求会是创业者的成本压力,但不可否认的是,在一个大浪淘沙的市场环境中,创业者的准入成本确实在降低。今天,所有的投资者都在热切寻找有爆发潜质的互联网相关领域,从前两年的O2O、众筹,延伸到现在的网红、段子手,资本非常热衷于制造和追逐下一个爆款产品。从这个角度来说,轻资产的互联网创业是中国经济的另一面,与哀愁的重资产民营制造企业形成了巨大反差。但是,它们都不可能脱离整个社会成本高企的基本环境。
人力、房租是“两座大山”
梁佟现在更愿意以寻找政府项目支持的方式降低成本,在中关村,高新企业只要主动寻找,获得一些对应的扶持基金或贴息贷款还是很容易的。“虽然数额不大,一年也就是二三十万,但如果仔细研究政策的话,未来能拿到百十来万应该没什么问题。”她说。
阴明就没有耐心省这些钱,他们的团队更热衷于技术开发,除非有人拿着一张表告诉他填完了就可以拿钱,否则他是不会把时间花在研究优惠政策的。创业之前,他对财务、税务也完全没有概念。“看报表的时候,很多款项都超出了我的预期,给员工发工资要交很多税,公司的任何一个经营行为几乎都涉及到交税。”他说,此前完全不知道税费、款项这么多。
人力成本非常高,这是梁佟和阴明共同的感受。“创业热潮无形中推动了很多成本上升,比如程序员本来没那么贵,由于创业太火,大家都缺程序员,一个程序员的人工价格就提升了不止50%。”阴明说,他的团队现在有18个人,人力成本占到了公司支出的八九成。“一般的大学毕业生要求也不低,到不了七八千的话基本上没有人会来。”他说。
梁佟的公司里,工资最高的技术人员年薪在五十万以上,这还不是非常资深的程序员,她觉得已经贵到离谱了,为此她尽量多招一些兼职人员和实习生来节约成本。
在北京,高房租当然是每家民营企业的重负。梁佟的创业起步于一间教堂咖啡馆,那时候标志性的草根创业聚集地车库咖啡还没有很大名气。每天早上,她和两个小助手就到咖啡馆集合,点一杯咖啡坐一整天,讨论、分析国外的教育产品,到了饭点就在旁边的拉面馆简单对付一下。“人家也不会轰我们走,当时他们店里正在装修,反正也没什么客人。”梁佟说道,为了省咖啡钱,三个人也不是每天都见面,只有周一、三、五去,二、四就在家办公。
在咖啡馆过度了几个月之后,梁佟就搬到了中关村的创业孵化器厚德创新谷,那里每个工位只要1500元,刚开始的时候还能打折到1200元,这样就能大大节约开销,还能有见投资人和客户的便利。创业之前,梁佟已经在高校工作多年,辞职后拿着几十万积蓄作为启动资金,人员越来越多的时候,她就搬到了中关村另一座写字楼,四百多平的空间,房租每年七八十万。
人力成本和高房价成本,这是企业面临的两项涨幅最大的运行压力。去年3月,雅虎宣布关闭北京研发中心,其内部成员曾经说道,原因很简单,雅虎在中国本来就没有业务。中国一线城市研发的人力成本涨得太快,北京的人力成本大约为印度的四到六倍。
2015年,四大一线城市甲级写字楼租金全面上涨,租金本来已高企的上海,全年有近一成的涨幅;2014年租金还下跌的广州,2015年也上涨了2.6%。2015年,北京甲级写字楼月租金高达332元/平方米,蝉联中国甲级写字楼物业租金最贵之地。在金融、IT以及专业服务等行业的内资企业的驱动下,促成了大量新租、搬迁及续租交易。由于旺盛的市场需求,空置率的上升也并未对租金产生影响,2016年第一季度仍然呈上涨趋势。
对于互联网创业公司来说,这是无法规避的一部分成本。一些不堪重负的小公司也开始“逃离”北京,转而去二三线城市发展。
实现理想中的生活有多难?
对于创业者来说,个人生活的高成本负担当然是极大的压力。很多的联合创始人都不不会辞去原来的工作,许诺的股权分红很有诱惑力,但什么时候兑现充满了不确定性,而眼前的衣食无忧更为重要。
阴明在这方面没有太大的压力,他不需要像外地人那样要考虑生活负担,父母在这个城市有稳定而体面的工作,能够支持他从香港读到伦敦。“但我自己现在也要考虑生活成本,父母的观念比较西方,他们有不止一套房子,但不会主动提供给我住,我自己也不愿意。”阴明说,真正独立生活之后,他才惊讶于北京很多方面的生活成本比香港贵。
目前,他在公司拿的是固定工资,除了实习生,属于第二低的级别,每个月要负担高额房租,只能靠原来的积蓄维持还算过得去的生活水准。读书的时候,他有奖学金、有父母的支持,还能靠技术赚外快,而现在必须完全投身于公司。“以前我是一个不怎么考虑开支的人,虽然从来不买奢侈品,但是花钱不过脑子,也不会自我限制,但现在,想喝一杯咖啡的时候就会考虑一下,下午还要见个人,不如到时候再喝吧,以前是完全不会想的。”
阴明自我解嘲:“我现在也是买优衣库的人了。”这个家庭优渥的年轻人说他在真正独立之后,才发现挣一块钱比登天还难。
半年前,他跟父母表达了自己的想法,如果25岁到30岁之间不把自己提升到某一个阶层,再去突破就很难了,这五年基本上是定调的阶段。另外还跟父母算了一笔账,30岁的时候要在东二三环有一个80多平米的公寓,有辆车,每年有一两次国际旅行。算了一下,每一年的收入涨幅至少要有50%~60%才可能实现。“当然,这只是一个目标,生活总是会打脸。”他说。
教育背景、创业经历,以及公司未来的股权分红,这些都会令他比一般在北京的同龄人更容易实现梦想。但阴明对前景也不会盲目乐观,他对这个新兴市场有冷静的判断,并且随时做好了倒掉的准备。
去年,阴明身边还有三十几位朋友可以一起聊创业,现在只剩下一个人了,其他的已经全部“死掉”,“创始成员互撕,公司没有盈利能力,做不出产品,或者商业模式是错的。”阴明说,以他的观察,去年是比较混乱的一年,“我一直都这么形容,你卖煎饼我也卖煎饼,都是5块钱,你的好吃我的烂,如果市场有足够的需求,你应该开两个煎饼摊,我应该被淘汰,但是在蜂拥而至的创业浪潮中,给我十万让我好好做下去,那我就可以只卖3块钱,你反而活不下去了,市场很奇怪地淘汰了做煎饼好吃的人。”他说,今年的创业市场就冷静多了。
在一个社会成本普遍升高的时代,创业公司不可能永远享受低成本,也很难在经济转型时期独善其身,近两年的轻资产创业浪潮既是资本对低投入、高回报的追逐,而另一方面,这也反映出高成本下的恐慌。当理性回归,泡沫褪去,没有什么是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