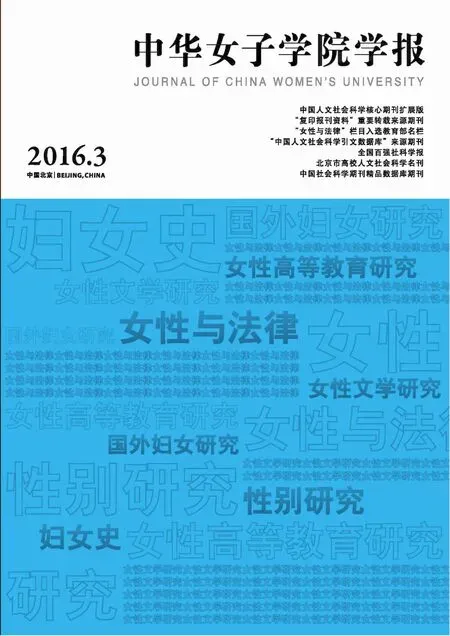妇女社会组织的项目制治理
——以北京市为例
王颖
妇女社会组织的项目制治理
——以北京市为例
王颖
摘要:妇女社会组织作为治理主体参与社会治理,是我国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在项目制治理下,国家对不同的妇女社会组织采用差异化的治理模式:对妇联的让渡式统合和对民间妇女社会组织的福利式吸纳。国家通过项目制实现对妇女社会组织的治理和赋权,并进而实现对妇女的治理和赋权。
关键词:妇女社会组织;项目制;治理;赋权
妇女社会组织,也称为女性社会组织、妇女非政府组织、妇女NGO等。妇女社会组织作为治理主体参与社会治理,是我国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我国社会治理的关键机制和模式已经从单位制转化为项目制。[1]妇女社会组织如何适应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需求,实现组织转型,并在社会治理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和角色,值得深入研究。
本研究以北京市为例,采用访谈法和问卷法,于2014年12月至2015年12月对北京市妇联和三个民间妇女社会组织进行了调查。本文将妇联受访者编码为FL,三位妇女社会组织受访者分别编码为MJ1、MJ2、MJ3。问卷调查对象主要针对北京市H区妇联工作人员。
一、妇女社会组织
广义上讲,由妇女基于联谊、维权等需要组成的社会组织或以妇女儿童为受益群体、以促进性别平等、代表和维护妇女权益为职能的社会组织,均属于妇女社会组织。学术界对妇女社会组织的研究存在两种视角,即组织社会学的视角和国家—社会关系视角。组织社会学的研究视角侧重于研究组织的分类、特点、功能、组织内部治理、组织的影响因素等。国家—社会关系视角则将妇女社会组织作为对象,置于国家与社会的二元主体中进行分析。
学者从组织社会学视角对妇女社会组织进行了不同的分类。如Howell以组织起源、领导委员会的组成、议程和活动以及自我规制为主要指标,提出我国妇女社会组织的谱系,从最小自主性的妇联,到妇联衍生组织、其他党政组织的衍生组织、妇女行业和专业协会、民间妇女组织,到享有最多自主性的未注册的妇女组织。[2]按照与政府的关系,妇女社会组织可以划分为妇联和民间妇女社会组织。近年来,妇联在国家政治体系中的合法性逐渐加强,并从行政性功能转向群众性功能。[3]妇联的作用包括:在公共政策决策层面推动社会性别意识的决策主流化;在公共参与层面推动妇女参与基层民主自治和民主管理;在服务层面打造个性化的公共服务产品。[4]但是,妇联存在倒金字塔的组织结构失衡、系统内层级式控制机制的弱化、组织内部资源获致的非均衡性、“层层发动、典型开路”的动员方式和“全面出击、遍地开花”工作方法的单一和滞后等问题。[5][6][7]而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在于重新界定妇联与党和政府的关系。自下而上建立的民间妇女社会组织,使妇女多样性的利益诉求有了更多渠道和组织依托,具有灵活的组织运作方式、先进的工作理念和社会化的筹资手段。[8]但是,受到父权制、计划体制的路径依赖、政治法律体制中双重管理规定的影响,存在发展相对缓慢、对妇联依附等问题。[9]
除组织社会学视角外,部分学者将妇女社会组织作为对象,纳入国家与社会关系框架中进行分析。如Keech-Marx对妇女NGO运用“将私域丑事置于台前”的策略来推动反家暴进行了分析。[10]175-199妇女组织通过与国家话语共鸣的方式建构性别话题,使其行为合法化并推动社会变革。
这些研究或关注个体组织层次的分析,或关注宏观层次的制度分析和结构分析,并未将变迁的国家社会治理的制度性机制纳入分析中,揭示国家和社会从隔离到嵌入融合的交互过程中妇女社会组织所独有的特质及角色。
二、妇女社会组织的项目制治理
项目制是近十年来社会治理体制机制运行中极为独特的现象。项目制首先作为资源分配模式,随后成为治理机制,体现着国家权力意图与治理效果。当前的研究集中于解析项目制的治理形态、对国家权力和科层结构的影响及中央和地方关系、项目执行过程中不同主体的行为和策略,关注于财政领域、公共服务和文化工程。除王向民[11][12]的研究外,对于项目制社会组织治理的研究较为缺乏,项目制实际运作过程和效果的经验证据及影响条件和因素的分析更付诸阙如。
在妇女社会组织领域,项目制治理逐渐形成一种新的治理结构,具有政府行为主动性、创新性和策略性的特点,以提供妇女服务和实现性别平等为目标,在过程中体现服务化、专业化和技术化。在国家回归的基础上,项目制突破了传统的条块,在新的利益调整格局中,妇女社会组织作为主体参与社会治理,实现国家和社会组织的赋权增能、协调发展。在强调共建共享的精细化治理理念下,国家对不同的妇女社会组织采用差异化的治理模式,即对妇联的让渡式统合和对民间妇女社会组织的福利式吸纳。
妇联对同类别、同性质、同领域社会组织的发展、服务、管理工作中,在政治上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在业务上处于龙头地位,在管理上经政府授权承担业务主管职能,在代表地位、资源、程序等方面拥有其他妇女社会组织无法竞争的实力。为政府提供管理渠道的同时,进行妇女利益的聚集、表达和输送功能,将纵向的政府目标与横向的民间利益和目标有机协调起来。
国家通过让渡式统合,实现对妇联作为妇女利益代表资格的确认,达到组织与国家体制的制度化统合和联结。在社会组织双重管理体制弊端不断暴露、合法性不断式微的背景下,妇联逐渐承担起政府让渡的管理和监督的职能,作为政府、社会、市场和国际的资源中心和转换中介,通过构建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沟通渠道或制度程序,实现社会个体、群体、组织以及政府系统之间的互动。
民间妇女社会组织通过直接提供服务解决社会问题和通过服务赋权妇女来增强其参与社会治理能力的角色,同时扮演着反映诉求和问题、进行社会性别意识和性别主流化倡导的角色。重要的是民间妇女组织强调妇女的“实用性社会性别利益”和“战略性社会性别利益”。[13]实用性社会性别利益即妇女即时的需要和改善女性当前的境遇,为特定妇女群体提供救助、服务、维权、教育培训、情感联谊和互助;战略性社会性别利益则为长远的妇女解放所需达到标准,通过理念和政策倡导、社群动员等,有目的地改变现有的关乎妇女群体权益的公共政策或实务作法,间接促成环境改变以更符合妇女的相关需求,包括获取公认、使其修正与促进提升的过程。实用性社会性别利益和战略性社会性别利益的并存,使民间妇女社会组织兼具服务和倡导的功能。
国家通过购买服务等福利式吸纳实现对民间妇女社会组织的治理。福利式吸纳作为国家和组织化的社会之间的政治和经济安排,部分民间组织被国家选择性地邀请来协助政策的执行。[14]民间妇女社会组织的认同、议题、价值诉求的特殊性,能让组织拥有主体性与实力,通过社会动员和资源汲取,弥补妇联组织基层人员缺乏、组织资源匮乏和资源获取能力不足的缺陷,形成群众化、社会化的妇女服务和倡导格局。由于民间妇女社会组织存在长期受制于国外援助者的限定方向、来源不稳定、缺乏能力建设等问题,项目制则成为其提高能力建设和完善内部治理的一个重要渠道。

图1 妇女社会组织的项目制治理
以北京市为例,妇联在2009年被认定为“枢纽型组织”后,进一步深化了作为政府、社会、市场、国际资源的吸纳和整合的中介体,承担着资源转介和提供,孵化、培育和监管社会组织的角色。北京市妇联强调“盘活存量资源,整合现有资源,做大增量资源,吸纳外部资源,优化人力资源”。至2011年5月底,北京市妇联购买社会组织服务项目的参与人数累计达21282人次,举办活动1273场次,投入配套资金141.1万元,共150家社会组织参与,累计提供社会服务6182小时。至2013年底,北京市妇联通过市、区、街乡、社区四级妇联组织联系妇女社会组织2000余家,包括文化、服务、社会经济、联谊等类别,其中973家已纳入北京市妇联社会组织管理系统。[15]
以H区为例,妇联系统内2014年共有23个“妇女之家”项目,其中,家庭建设类项目3个、志愿服务类项目8个、文体活动类项目3个、家庭教育类项目9个,涉及家风传承、家庭教育、助老孝亲、民生公益、心理关怀、精神文化等多个领域。H区共投入资金19.63万元(其中,H区妇联投入资金13.68万元,街道投入资金5.95万元),开展各类活动460次,直接受益居民人数5582人。同时通过项目实施,新培育了志愿者470人。①参见:《城市妇联组织和工作方式改革创新研究》项目调查资料(内部资料),2015年11月。2015年,项目数量为20个,其中9个项目采取联合型运作形式,分别归为家庭环保类、能力提升类、技能培训类等3大类型,与3家专业社会组织合作开展,H区妇联、各街道共投入资金18万余元,通过项目实施发动社区工作者和志愿者791人,年内开展活动1229次,直接受益居民人数6189人,新培育志愿者331人。[16]
通过项目制,在纵向条线分布系统中弱势控制关系的妇联组织,可以对传统的架构和科层逻辑进行修正,打破条块限制,拓展管理职能,进一步获得自主权、合法性和权威性。首先,面对长期以来妇联可调用经费的缺乏,项目制模式使妇联统合了系统内外的资源。
“妇女一人一元钱,作为我们的经费,我们把这个拿出来,作为项目经费,各社区申请。”(FL-H-1)与此同时,作为枢纽型组织,妇联申请和承接了来自市级社会建设专项资金购买社会组织服务项目,带来了系统外的新的资源。此外,基层妇联还汲取了街道、社区的资源。“妇联里的资源有限,但是遇到好的项目,我们可以从街道找钱,都是街道大盘子里的。”(FL-H-3)而这种资源的获取,部分原因是妇联工作人员兼职街道其他职务所带来的多元性、便利性和可操作性。长期以来,妇联专职工作人员较为缺乏,兼职现象非常严重。如北京市H区的妇联工作人员中仅有46.5%的为专职,其中有1项兼职人员占到了28.0%,2项兼职人员占到了26.3%。①参见:《城市妇联组织和工作方式改革创新研究》项目调查资料(内部资料),2015年11月。兼职带来了妇女工作的繁重和妇联工作专属性的弱化,却使妇女服务资源的筹集和动员的多元化成为可能。随着资源的增加,妇联在购买服务的同时,也尝试购买社工岗位以充实基层专业人力资源,从而解决妇联工作人力不足的问题。
项目制的运行强化了妇联组织的专业性。一方面,妇联组织各种专业培训用以提升工作人员的专业能力;另一方面,妇联鼓励基层工作人员考取专业社工师资格。北京市H区妇联有34.6%的工作人员拥有社会工作师的专业技术证。妇联通过专业和技术治理,加强职能专属性,从而增强在政策中的话语能力,增加妇联的动员能力,提高妇联对社会资源的吸纳和聚合能力,整合来自政府、市场、国际组织的资源,使性别意识得到倡导和宣扬,促进性别平等主流化。同时,通过孵化、培育和整合,建立妇女社会组织共同体,进一步创新社会组织治理模式。
而项目制的方式,也使妇联组织与民间社会组织的合作有了更为灵活和多元的方式。“我们之前和一个社会组织合作,购买他们的服务——儿童课后托管。但是做得非常不好,就是孩子放学有个地方,也没有服务和活动,后来去的孩子越来越少。刚开始就一股脑把钱打给他们,即使发现他们做得不好,也没办法管理。后来,再过一年,我们就不会和这个组织合作了。购买服务,可以让我筛选组织,而且我们也学会怎么和社会组织合作,各自做自己擅长的事情。”(FL-H-3)
与此同时,通过项目制,妇联也孵化了民间妇女社会组织。如H区妇联的“BBT”,作为妇联项目培训萌发的组织,于2013年成立,为期10个月的项目着重于成员专业能力的培训,而培训则由J民间妇女社会组织来进行。
“我们的成员年龄都比较偏大,最开始培训的时候都说这些有什么用,让我们直接帮助,直接下去做。但是后来发现,通过培训,我们建立了专业的制度、章程,也学会了专业的服务知识,对自己、家人和帮助对象都有用。通过专业的培训,这个组织就建立起来了,10个月的项目培训结束,组织也还在自己运行。我们的活动现在每周都开展。做社区工作,开始的时候每次活动都得要我们带着,现在不用了,她们自己运作、自己开展活动。”(FL-H-4)妇联孵化和培育的民间妇女社会组织,不仅在项目结束后继续运作,同时调动了来自社区个人和企业的志愿者资源和其他物质资源。
与此同时,民间妇女社会组织在项目制下也进行了组织调整。“我们就进入了养老领域。现在养老护理还要分出来,它还是会细化的,那我们就在这种细化中让农村妇女更职业化。我们现在更多的可能就是解决社会服务问题,找到自己的一个定位,让自己这个机构能做得更专业化。”(MJ1-1)
国家通过项目制,实现了治理的体制扩容,使不同类型的社会组织,主动或被动纳入体制的直接管理或链接中,成为治理主体,并与国家建立了新的关系。国家通过差异化的模式实现了对妇联和民间妇女社会组织的治理。与此同时,国家通过妇女社会组织实现了对妇女的增权。项目制的治理机制模式必然对妇女社会组织自身、妇女社会组织间的关系和格局、妇女社会组织与国家的关系产生影响。
不同类型的妇女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扮演着差异化的角色,从而实现国家层面的治理能力现代化。在项目制下,妇联和民间妇女社会组织可以形成网络化共同体。妇女社会组织领域内部的治理模式由层级动员转向多线动员。妇女社会组织网络共同体的建立,在承担政府让渡空间和资源的同时,还可以进行主动的空间拓展和资源拓展。而社会性别意识和理念有利于网络组织、群体、成员的认同,使这一共同体的建立成为可能。同时,“性别平等主流化”使妇女社会组织网络化发展可以纳入其他不同政府部门和民众。随着社会组织层面的共同体建立、自我增能与自治及治理的主体性参与,妇女个体层面的增权和社会参与也会获得提升。
三、妇女社会组织项目制治理下的问题
妇女社会组织领域内的项目制在实际运行中,由于组织和体制等方面的原因,仍存在着一些问题。
首先,妇女社会组织领域相较于其他领域项目,资源总量和种类都较少,承接主体较为单一。如2014年,北京市H区各级妇联承接过妇联项目的比例为33.3%,其中,环境保护类、家庭建设类、文体活动类项目居多。承接妇联项目资金有57.8%是在100至5000元之间;24.4%在5001至10000元之间;10001至20000元之间的有12.2%,20001至50000元之间的有2.2%;50001元及以上的仅为3.3%。①参见:《城市妇联组织和工作方式改革创新研究》项目调查资料(内部资料),2015年11月。妇女专项项目多依赖民政、社工委等部门,妇联作为发包单位,项目承接者为内部化组织的较多,体制外的对象较少。妇联系统和民间妇女组织之间的合作需进一步联结。在开展政府购买服务项目时,妇联工作人员是项目的主要执行者,H区妇联承接过妇联系统以外的政府购买服务项目的仅为27.9%。开展政府部门购买服务项目的具体执行者为妇联干部的占75.5%;选择社区志愿者的为60.8%;而专业志愿者的比例只有33.3%。项目的开展培育了一大批社区志愿者,成为除妇联干部之外的一支重要力量,同时专业志愿者的协同参与也使项目的专业化得到了保证。但是,社区妇联工作人员也表达了项目制下,因专业能力不足而带来的困难:“我们现在怕申请项目,我们不专业,如写申请书都得让实习的学生帮忙,更别说具体开展项目。之前的社工培训我们非常受益,如何策划、服务和组织建设,我们都学习了。但是我们也还有其他的工作,还有兼职的,去做多个项目精力非常有限。我们希望的是第三方来做项目,具体开展项目,我们可以协助。”(FL-H-5)
其次,项目制模式可能导致民间妇女社会组织强调服务提供而排挤批判倡议的职责与功能。“中国今后改变经济发展模式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加强社会服务,而在社会服务领域,女性的就业机会和岗位真得很多。……而像我们这样的NGO组织又都在疲于奔命地做项目,热衷如何把自己做得更好从而让政府买单这些领域,在推进性别平等观念上弱化了,而缺少一些归纳性的东西。”(MJ1-1)可以看出,项目制模式实现了权力从国家到社会的转移,也同时实现了政府对社会的再渗透。但是,项目制对民间妇女社会组织的福利化吸纳,在强调服务提供的同时却使得倡导的组织功能弱化。妇女社会组织面对的不仅是国家,还包括社会中的男权意识。妇女社会组织实现治理主体,不仅要理清与国家的关系,还包括社会性别理念的倡导和实现。妇女社会组织以女性主义关怀为出发点,将女性作为运动主体的组织过程,在对妇女个体进行服务提供和增权的同时,不能也无法抛弃对于性别平等理念的倡导和关怀。
再次,项目分类可能造成社会组织碎片化、缺乏长期规划等问题,不利于实现组织自治。从社会组织的培育与自治角度而言,具体而琐碎的项目分类可能造成社会组织的碎片化,社会组织无法实现对该领域完整而长期的规划,因而无法实现社会组织的自治与规模化生长。妇女社会组织需要避免对政府资源的依赖和惰性,将妇女赋权的公共价值情怀和公共服务精神放置于前位,更好地遵循服务逻辑而非行政的逻辑。与此同时,国家在执行规定和项目规划的同时,也要注意给予妇女组织制度和政策空间,使其可以自主性地进行调整和改变。
最后,在项目制制度下,部分妇女社会组织可能出现国家治理缺失等问题。在国家从社会生活中逐步退出时,国家制度本身的复杂性以及不同制度与不同层级政府之间的磨合和冲突可能削弱国家的控制力,从而为妇女社会组织在没有国家干预情况下的自我组织创造条件。如何通过项目制实现对妇女社会组织的整合性治理,是治理实践中无法回避的现实议题。
四、结论
妇女社会组织的项目制治理,作为一种耦合性的制度设计,逐渐成为能动性和策略性的国家治理机制。国家对不同类型妇女社会组织采取了让渡式统合和福利式吸纳的差异化的治理模式,并可能引致妇女社会组织的差序格局。本文将社会性别视角纳入社会治理分析,不仅关注国家和妇女社会组织之间在项目制治理中的关系的结构模式,还关注二者的互动过程和变动趋势。尤为重要的是,探讨国家主动地运用项目制实现对社会组织的治理,及各类妇女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方式。妇女社会组织的项目制治理,作为国家治理模式的创新,不但可以实现国家层面的治理能力现代化,社会组织层面的共同体建立、自我增能与自治以及治理的主体性参与,还可以实现对于妇女个体层面的增权和社会参与。
实现对妇女增权是妇女社会组织建立和维系的基础和本质。项目制中的妇女社会组织,应更多地关注不同类型妇女的主体性问题。通过对不同类型妇女的参与式增权,引导妇女群众参与社会治理,提升妇女自我管理、民主参与和监督的意识和能力,进一步为妇女建立社会网络,构建社会资本。
【参考文献】
[1]渠敬东,周飞舟,应星.从总体支配到技术治理——基于中国30年改革经验的社会学分析[J].中国社会科学,2009,(6).
[2] Howell, J.. Women’s Organizations and Civil Society in China[J]. International Feminist Journal of Politics, 2003,(2).
[3]马焱.妇联组织职能定位及其功能的演变轨迹——基于对全国妇联一届至十届章程的分析[J].妇女研究论丛, 2009,(5).
[4]刘莉.妇联组织参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新思考[J].妇女研究论丛,2008,(11).
[5]金一虹.妇联组织:挑战与未来[J].妇女研究论丛,2000,(2).
[6]丁娟,马焱.妇联承担政府职能的优势与阻力研究[J].妇女研究论丛,2006,(S2).
[7]仪缨.不同的声音:一次别开生面的“中国妇女组织研讨会”[J].妇女研究论丛,1999,(3).
[8]肖扬.对妇联组织变革动因及其途径的探讨[J].妇女研究论丛,2004,(4).
[9]黄粹.民间妇女组织发展的制度环境析论[J].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4).
[10] Keech-Marx, S.. Airing Dirty Laundry in Public: Anti-domestic Violence Activism in Beijing [A]. Unger J.. Associations and the Chinese State: Contested Spaces[M]. New York: An East Gate Book, 2008.
[11]王向民.中国社会组织的项目制治理[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4,(5).
[12]王向民.分类治理与体制扩容:当前中国的社会组织治理[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5).
[13] Molyneux , M.. Mobilisation without Emancipation ? Women’s Interests, States and Revolution in Nicaragua [J]. Feminist Studies, 1985,(2).
[14] Howell, J.. Shall We Dance? Welfarist Incorpora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State-Labour NGO Relations in China[J]. The China Quarterly, 2015, 223.
[15]北京市妇联社会工作部.北京市妇联2010年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总结[EB/OL]. http://www.bjwomen.gov.cn/web/static/articles/acatalog_270/article_10007/10007.html.
[16]北京市东城区妇联.在分享中提升项目化管理实效[EB/OL]. http://ldj.bjdch.gov.cn/n5687274/n5724111/n5724204/ 15382275. html.
责任编辑:张艳玲
Project Grant Governance of Women’s Organizations——A Case Study of Beijing
WANG Ying
Abstract:Women’s organizations participating in social governance are of fundamental significance to the modern state governance system. Under the governance of project grants, the government has adopted differential models for different organizations, transferred power to the Women’s Federation, and welfare capacity to related NGOs. Through the projects the state can govern and empower women’s organizations so as to empower women.
Key words:women’s organization; project grants; governance; empowerment
DOI:10.13277 /j.cnki.jcwu.2016.03.007
收稿日期:2015-11-18
中图分类号:D442.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3698(2016)03-0047-06
作者简介:王颖,女,中华女子学院社会工作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性别研究、教育社会学、社会福利与社会政策。100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