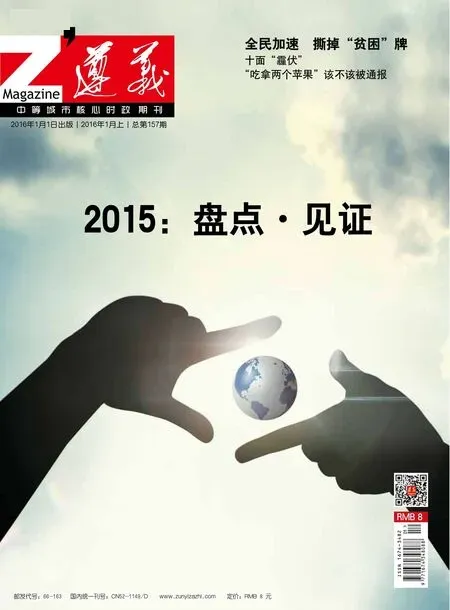《巴黎协定》越过终点 走向新征
文丨吴朗
《巴黎协定》越过终点 走向新征
文丨吴朗

一份长达32页的文件,让2015年12月12日19时26分成为了一个不寻常的时刻。随着法国外长、巴黎气候大会主席法比尤斯手里那把绿色树叶造型的小槌子在梆子上敲出“笃”的一声,名为《巴黎协定》的文件正式获得全球195个缔约国与欧盟的一致通过。上千人聚集的现场爆发出长达1分半钟的热烈欢呼,不少代表甚至热泪盈眶。
这份被称为“应对气候变化的历史性一步”的文件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不具法律约束力的决定,第二部分是具备法律约束力的《巴黎协议》,将致力于通过一揽子措施,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减缓气候变化对人类发展与生存以及生物物种存亡所带来的不可逆的影响。其中针对后2020年全球气候变化应对行动的《巴黎协议》,是人类通过的第一份要求所有国家共同做出温室气体减排努力的国际条约,具有国际法层面上的法律约束力。
来之不易的1.5摄氏度
长达两周的谈判中,最一波三折的情节莫过于1.5摄氏度控温目标的逆袭。2009年缔约方在哥本哈根大会达成初步共识:要将本世纪末的地球平均温度增幅相比前工业化时代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这一目标后来正式写入2010年的坎昆决议中。
据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第五次评估报告分析,2摄氏度目标下,全球需在本世纪中叶于2010年基础上减少40%至70%的温室气体排放,到本世纪末实现零排放。
从第一天谈判开始,小岛国们就拿出了一份受认可的最新科学研究。它们指出,控制地球升温在2摄氏度还是太过危险,不少小岛国已经面临家园被海水淹没不得不举国移民的处境。在第一周的交涉中,小岛国坚持要将这份科学研究递交至大会方的要求,遭到以沙特阿拉伯为首的石油生产国的阻扰。此外,已经升温近1摄氏度的事实也让人们对于1.5度控温的可行性大打问号。于是,1.5摄氏度一直被保留在方括号内,在被删除与被保留之间盘桓。
事情在12月8日出现了转折。一个以欧盟和79个非洲国家与加勒比海、太平洋岛国组成的联盟走到台前,打着“高雄心”的旗帜,为1.5摄氏度站台。美国在第二天也意外地高调宣布加入该联盟,随后巴西也宣布加入。
“高雄心联盟”一时吸引了无数在场媒体的镁光灯,但不管“高雄心联盟”是否确实起到作用,12月10日公布的文本中,首次确立了“全球升温目标要控制在远低于2摄氏度,并努力控制在1.5摄氏度极限值”的说法,这让对协议力度抱有较高期望的人们一时颇受鼓舞。
但数位欧美科学家很快就为这股情绪浇了一盆凉水,指出看上去雄心勃勃的控温目标,却和文本中实际作出的减排操作性规定上有很大的脱节,在减缓长期目标一节,文本既没有提到实现碳排放峰值的时间,也没有提到停止使用化石能源,甚至用“温室气体排放中和”这样缺乏定义的词取代了更有力度的“去碳化”的表述。
这个意见显然很快得到了重视。在12日下午公布的终极版草案文本中,“温室气体排放中和”被更具科学性的表述所取代——“在本世纪下半叶实现温室气体源的人为排放与碳汇吸收之间的平衡”。新的表述比之前的文本在科学性上更为明确了,排放达峰和全球减排的趋势都与1.5摄氏度至2摄氏度控温目标情境一致,但“将升温控制在1.5摄氏度,就意味着我们必须在随后的十年提高减排雄心”。
“世界变了”语境下的区分原则
相比美国等发达国家,中国和印度早就退下了法律约束力的火线,并早早表示愿意接受一份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中国气候谈判代表团团长解振华在行前发布会上大方表示,中国盼望一份有法律约束力但坚持共同但有区分原则的新协议。对于它们来说,区分无疑是最重要的底线。
1992年制定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强调,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减排要承担“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这在《京都议定书》中有更为具体的体现。《京都议定书》规定,《公约》附加一所列的43个缔约方有具体明确的强制减排任务,但对非附件一的发展中国家则没有任何强制规定。《公约》对附件一缔约方的规定,是历史和当下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来源国。
但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发展和温室气体排放在近几年呈现急速上升势头,尤其是中国已成为碳排放第一大国,人均碳排放量也渐赶上欧盟。同时,当年附件一中的一些国家大部分都遭受了2007年经济危机的冲击,经济增速放缓甚至出现衰退,温室气体排放下降显著。
发达国家认为,世界变了,23年前《公约》中的分类早已过时,应该更强调“共同”的责任而不再是“区分”。这也意味着,当年并不具有强制减排责任的新兴经济体也必须纳入进来,承担碳排放责任,做出减排努力。
“世界变了”语境下,另一个在会场不断发酵的想法是,气候资金“捐赠者阵营”应该拓展到“有能力国家”或“愿意承担”的发展中国家队伍中去。欧盟和美国甚至一度以此作为它们答应2020年后气候资金注资以每年1000亿美元为下限的条件。
但中国、印度等国家仍强调发达国家排放的历史责任。一位印度谈判代表就指出,截至目前全球所排放的二氧化碳体量上,印度的排放仅占了3%,“印度还有3亿人口家中没有用上任何能源,就这样开始要求印度和发达国家处在同一水平上减排,这难道公平吗?”
在最后的成文中,发展中国家基本守住了区分原则。严肃寡言的印度环境部长普拉卡什•贾瓦德卡尔最后终于满意地发言表示:“巴黎协议意识到了并且承认了印度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对发展的迫切需要。”
低碳之路
作为一份国际协议,《巴黎协定》为团结全人类与气候变化作战吹响了号角,但具体的作战方不仅仅是国家,更是地方政府、民间组织、企业和个人。
英国智库新气候经济高级顾问雅克布对《巴黎协定》仍毫不吝啬地给出了好评。他的理由之一,是《巴黎协定》向政府、企业和个体投资者发出了一条明确的信号——绿色低碳的经济发展之路是惟一的正途,依靠化石能源而获得发展的经济体已经走到了尽头,现在再投资煤矿或者油田风险显然都变大了。
那些具有前瞻性的投资者,已经纷纷转向清洁能源投资领域。巴黎气候大会第一天,世界首富、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就发起了一项规模达数十亿美元的清洁能源研发倡议,Facebook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阿里巴巴执行主席马云等多位亿万富翁加入了这一“能源突破联盟”,致力于可将清洁能源商业化推广的研发项目投资。这一项目将配合另一个由20个主要碳排放国和化石能源生产国于同天发起的“创新任务”倡议,加入该倡议的国家承诺会将各自对清洁能源基础研发领域的投资翻倍。
可以说,早在巴黎大会之前,化石能源的颓势就已注定,《巴黎协定》则进一步放大了这一信号,或让它们的“死期”来得更快。《巴黎协定》的达成,也标志着对气候变化影响的政治共识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而这份政治共识在大多数国家皆是由一种由下至上的途径而反映出来的。
中国在环境与气候议题上也形成了由下至上的一次次推动。中国的能源结构以煤为主,不仅深受气候变化灾害的影响,因燃煤而造成的大城市空气污染问题更是严峻。而一些专家指出,气候变化影响甚至会增加雾霾发生的频率。在巴黎气候大会举办期间,北京遭遇了一次史上最严重的雾霾侵袭,并拉响了史上第一次空气污染红色警报。
中国谈判代表邹骥认为,严重的环境污染实际上是中国想要力促巴黎协议达成目标的内在动力。“中国不仅不会阻碍谈判进程,反而是最积极最着急想要促成这件事的。中国才是真正的更有雄心,而这些雄心都是落在实际的表现上,不是喊口号转移话题上。”
“政府已经开始行动了,但他们做得还不够,并且还易受到丰厚的碳利润的诱惑。但是《巴黎协定》让他们认识到了这个问题也创造了将持续向他们施压来提高自主减排目标的体系。”雅克布指出,协定会驱动投资、市场和技术走向低碳领域,并降低相关产业成本,从而使得制定更高的减排目标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来说都变得更轻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