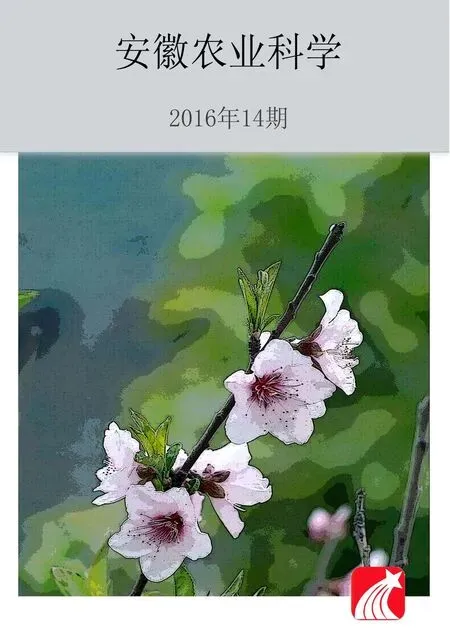农村政治权力参与社会财富分配的范式研究
石 婷,朱婷婷
(南京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江苏南京 210095)
农村政治权力参与社会财富分配的范式研究
石 婷,朱婷婷*
(南京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江苏南京 210095)
摘要财富分配不均一直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重要问题。影响财富分配的因素有很多,鉴于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对权力规范化的强调以及防止权力滥用导致腐败等要求的提出,笔者着眼于政治权力对社会财富分配的影响进行研究。在文献回顾的基础上,首先试图论证政府权力对二次财富公平分配、有序调节的突出成就。其次,着眼于我国农村地区,通过简单的统计发现掌握不同政治权力的村干部和普通村民家庭的人均收入情况确有较大差距。针对这一验证结果,从社会资源分配不公、不同群体的不均等赋权、公共权力的隐性收入3个方面,剖析权力扭曲阻碍财富公平分配的现象产生的原因,最后从经济、政策、制度3个方向探求解决路径。
关键词政治权力;收入差距;财富分配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经济飞速发展。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看到了计划经济的弊端,对所有制进行了改革与调整,确立了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这一制度给我国经济带来活力,将生产要素纳入分配方式中,在坚持效率优先的同时兼顾公平性。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逐步实现共同富裕,这种发展模式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被采用过,然而遗憾的是,大部分实践过后的结果是,期望出现的“涓滴效应”变成了“回流效应”,引发了严重的后果:财富差距不断扩大,形成“中心-边缘”二元社会结构。这种日益扩大的财富差距问题更是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我国社会发展的失衡与失序。
从我国整体经济水平来看,不管是城市还是农村,区域间还是区域内部,收入差距问题广泛存在。相关统计数据也表明,我国的财富差距显著。从区域内部差异的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收入角度来看,改革开放后农村家庭人均纯收入为133.6元,到2006年人均纯收入已经上升至3 587.0元,年均增长12.47%。就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而言,1978年的恩格尔系数为0.68,2000年下降为0.49,2006年进一步下降为0.43(数据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200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对农村居民3年的收入做了跟踪调查,调查对象达到6 000多户。研究结果表明,其中20%的收入最高的农村居民家庭的收入值是最低的20%农户收入的10倍之多。此外,根据第6次人口普查结果看出,农村居民人口为6.74亿人,占总人口的50.32%。我国农村人口非常庞大,这是不能回避的问题,农村是我国发展之根。因此,我国的收入差距问题很大一部分原因来自于农村收入差距问题。研究好农村收入差距问题对我国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此外,收入分配的不均阻碍着我国经济的协调可持续发展,更会打击低收入人群的积极性,产生社会不稳定因素。
政府是最重要的权力主体,其政治权力更是社会资源公平分配的重要因素,并在分配社会资源和调节、监督社会财富公平分配中具有巨大作用。党的十七大强调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要更加注重公平性。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也着重指出,我国的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要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深化分配制度改革,加大再分配调节力度,着力解决收入分配差距较大问题,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促进共同富裕和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这充分表明了政府深化财富分配改革的重大决心。因此,笔者试图以乡村为例,通过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来具体阐明政治权力在社会资源分配中的参与力度和功能,旨在为消除我国财富差距以及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提供有力的实践支持。
1政治权力对财富分配影响机理的理论支撑
无论是通过理论文本的解读,抑或是社会现象的分析,都能得出一个感性的基本假设,政治权力确实对财富分配产生重要影响。然而,其中的影响机理还需进一步深入探究。只有通过对其内在机理的分析,才能有效进行恰当的路径建构,并最终消解财富差距问题。
一方面,肯定政府作为最重要的权力主体在二次分配中起到的一定积极作用。政府利用手中的政治权力,通过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行政手段来调节财富分配,平衡东西方地区发展水平,缩短城乡两极差距。另一方面,不能回避政府在二次分配中利用手中的政治权力以权谋私的问题。“经济人”角色使得某些官员动用职权,利用各种手段来寻租,以达到个人获利的目的。一些调查显示:农村土地流转过程中,一些政府盲目追求流转比例和流转规模,土地没有真正流转给想要种地的农户,而是在土地流转政策的掩盖下搞起圈地运动,违背了农民的意愿,损害了农民的利益。这些现象表明分配中权力的权威性、便捷性不仅导致权力的腐败,而且使得分配中的弱势群体没有真正受益,违背了二次分配更加注重公平的宗旨。二次分配中权力的扭曲和界限的不清是财富公平分配的极大障碍。
1.1公共选择理论中政治家的经济人假说公共选择理论认为政治范畴的政策选择都是出于理性的原则,并且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做出的。也就是说,政治家的经济人理性特征也同样被反映出来,政府的公共行为本身是一个关于利益的目标函数,换言之,政府及其公务人员都是具有自身利益目标的。公务人员追求自己的个人利益,而公共政府追求自身的公共利益,除此之外,还有一些部门、地方组织、大集团、小集体都有自己的利益偏向。总结来说,政府基本上是代表了公共利益,但是这些公共利益仍然带有一些偏向,代表着一定的利益范畴。早期观点认为,政府公职人员是大公无私的,不能代表任何一方利益,必须做到无观点,更没有自己的利益诉求。公共选择理论却打破这一设定,把经济人假定引入到政治领域,认为行政人员也是经济人,有自己的观点和立场,在公共选择时不由地会向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做出选择,其目的不是公共利益,也不是官僚机构的效率,而是个人利益的最大化。那么这样就出现了“政府失灵”论。政府失灵论认为当市场中的交易人变成了政治领域的权力行使者、决策制定者,政治家们在公共领域依然会像在经济市场上一样表现出个人的本性,即效益最大化。对于个体选民来说,他们一般会将选票投给那些能给自身带来更多利益的政治家或者政策方案,个人视角的局限性让他们不会将整个社会的公共利益纳入到自己考虑的范畴,而对于官员自身或者那些政治家而言,他们在政治场面上角逐的时候更多的是寻求政治权力的效用最大化,地位最大化,待遇最优化等,而公共利益可能只处于次要位置。公共选择理论的另一重要贡献在于,它解释了很多政治领域权力滥用以及腐败问题。可以这样说,公共选择理论是一个关于个人主义的理论,是把个人需求放在首位的理论,将官僚集团的选择转换为官僚个人的选择,将政府行为转换为公职人员个人行为来研究。这些理论对实际的应用在于以此揭露政府低效率现象,分析权力滥用和腐败产生的原因。我国公务员对增加待遇和收入的期望会导致其过分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这就是导致公务员系统中往往出现形形色色隐性腐败现象的原因之一[1]。
1.2政治学领域寻租理论寻租理论有着现代经济学深深的烙印,现代寻租理论最先是由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提出的,他是从对外贸易分析而来,他认为当政府通过进口限制等方式对贸易进行限制的时候,便会使人们为获取更多利润而加剧竞争[2];此外,巴格瓦蒂在克鲁格和塔洛克寻租思想的基础上提出相关概念,即直接非生产性寻利概念,这是指产生货币收益但没有产生货物和劳务的活动[3];此外,布坎南(J·Buchanan)、布雷彻(R·Breeher)、斯里尼瓦桑(T·N·Srinivasan)、托利森(R·Tolliso)等人也对其有过深入研究与探索[4]。寻租理论的关键起点是如何界定寻租。总的来说,寻租理论的出现区分了生产性寻租活动和非生产性寻租活动,增强了经济学对现实生活的解释能力。
寻租是指由于政府干预国家政策及行政控制,例如物价管制等,从而人为控制某些商品及劳务供给量来提高其市场价格,从而产生非生产性利润相同性质的租金,而这些租金会导致人们采取各种手段去竞相寻租。布坎南认为寻租简单而言就是人们试图通过各种手段将预期收入的当前价值极大化,这在一定程度上较强地体现了新制度经济学理念。塔洛克认为寻租活动是内生于政府垄断的权威和强制之中的,纯粹的私人垄断是不可能的[5];此外,垄断需要大量资源,但是在寻租的过程中会导致资源利用的扭曲;再者,寻租理论发源于对外贸易的进口垄断分心,但无论哪一种干预手段都会产生同样的结果,在垄断产生的寻租和避租中,都会产生资源的极大浪费,最终导致腐败[3]。权力寻租是政治权力带来隐性收入的最主要途径。权力寻租主要表现为两种形式,一个是权钱交易,另一个是权权交易。权钱交易是将金钱作为寻租的最终目的,利用权力收取租金,为个人谋取私利,满足个人欲望,这也是权力寻租中尤为典型的一种。用权力谋取私利或者金钱就是权力寻租。当今不少腐败的官员用手中的职权来帮助一些人获得私人的非法目的,而他获得租金。权力寻租的另一种是权权交易,权力寻租者也喜欢使用权权交易,权权交易的形式就是用自己手上的权力换取别人手中的权力,这种权力之间的换取是一种更加隐蔽的腐败形式,更加不易被发觉,他通过一定的中介完成,很难被法律识别[6]。
2权力差异带来收入显著性差距的实证分析
该研究所用的数据是农业部农村固定观察点2009年的调查数据(The National Rural Fixed Observation Point Survey Data)。根据研究所需,选择2009年调查的横截面数据,通过村表和户表的合并并剔除存在的缺失值的样本之后,总共剩余19 887个家庭样本,包括干部户个数856户,覆盖31个省市,28个村庄,其中东部地区有7 452个户,占总样本约37%;中部地区有7 653个户,占总样本约38%;西部地区有4 782户,占总样本约24%。由于笔者的研究重点是家庭的收入情况,因此提取家庭收入以及人口数量,得到家庭人均收入情况,再进行实证检验。
为了研究权力对财富分配产生的影响,特以是否拥有公共权力为标准,将农户人为地分割成村干部家庭和普通村民家庭。村干部家庭以户主拥有一定的公权为特征,然后比较拥有政治权力的农户家庭是否在家庭人均收入上较普通村民家庭的人均收入有显著的差异。通过大样本进行显著性检验,如果存在显著差异,那么就可以初步断定,政治权力确实在财富分配上起到一定的影响,即政治权力参与了财富的分配。
通过独立样本t检验来验证干部户收入和村民家庭收入是否存在显著差异,为分析收入差异和对假说提供依据,从而提出相关政策建议。表1是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主要报告干部户和村民家庭各自的家庭收入状况。

表1 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
通过t检验可以看出,拒绝原假设,即干部户全年平均收入-村民家庭全年平均收入=0,接受备择假设:村干部户和村民户之间的收入差距不等于0,并且结果显示村干部户家庭收入显著高于普通村民户收入。这就基本印证了前文的假说,通过大数据检验,发现掌握公权的家庭在人均收入上确实显著高于那些普通村民的家庭。这意味着村干部户收入显著超过村民户收入的现象确实存在,并普遍存在于全国的各个省份。
3权力参与财富分配的原因分析
3.1社会资源的分配不公从收入差距看,社会资源分配不公是一个由表及里的过程。何伟指出:“收入差距、分配不均等状况只是社会问题的一种表现,资源分配上存在不公才是这个表象背后真正的原因。”马克思说:“消费资料的分配是社会分配的本质表现,而任何消费资料的分配又都体现着生产条件和生产关系的本质属性。”[7]也就是说,这些资源包括经济、政治,他们通过这些资源创造经济收入,而拥有较高经济收入的人又通过自己的经济优势获取更多的资源以满足他们的需求。因此离开社会分配问题谈收入差距是无法解决收入差距问题的。社会资源的分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天然性差异,主要表现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首先,城乡之间由于城市离政治文化中心较近的优势更容易获得优秀的人才、信息资源和先进的科技,可以充分发挥资源的价值,获得高额收入。而农村地区缺乏人才和科技,本来就缺乏的资源又不能充分发挥价值,这使得城乡之间的差距拉大。其次,从东中西区域资源分配来看,东部资源优厚而西部资源稀缺,这个资源布局也吸引着大量人才涌入带来技术,推动发展,这使得东中西部地区的资源差距进一步拉大。资源分配不公的另一方面表现在社会强者和弱者对社会资源占有率的分布,这是利益主体之间的博弈,强者借助自己的优势地位获得更多的资源,同时强者会集中强者之间的力量,力图支配资源的分配方向,使资源源源不断地流向强者,因此,强者不断从弱者那里掠夺走有限的资源,资源渐渐流向强者的群体,这样导致资源分布结构愈加畸形,比重失衡。小比重人口拥有大部分资源,而大比重人口拥有小比重的资源。金钱可以诱导权力的偏向,这些拥有大量财力资源的集团在政治领域更易于获得较多的政治资源和教育资源,循环往复,这些资源又让他们有能力谋取更多的经济资源,相辅相成,恶性循环,从而富者更富,贫者更贫。由此可见,资源分配不均是导致收入差距扩大的首要原因。
3.2不同群体的不均等赋权这里的权利不仅包括资源获得权,还包括政治权、经济权、教育权等。社会性公共产品的供给实质是社会权利资源的配置问题[8]。首先,就当代民主社会而言,人民应该拥有一定的政治权利,公民的政治平等应该体现在公民能够享有这些权利,包括选举权、被选举权、表达意见权利、监督检举行政官员权利、参与制定基本政策和规则的权利[9]。政治权利是其他一切权利的基础和前提,公民一切权利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政治所决定的。不难发现,在政治权利不平等的制度当中,公民也很难获得平等的生存权利、经济权利、受教育权利、发展权利等。那些拥有更多政治权利的人会在获得其他权利方面占尽先机,而政治地位相对弱势的群体会遭到排挤,无法获得平等的生存和发展的权利。另外,很多其他权利都是依附政治权利而产生的,诸如教育制度、财富分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都是通过行政等政治手段确定的,受到法律保护,行政部门强制执行,而政治上的强势群体会充分利用自己的政治权利制定出更有利于他们的方案和规则来保障自己的既得利益。政治上的弱势群体表现为没有政治权利或者不知道如何使用自己的政治权利,甚至在权利被侵犯的时候不知道用法律捍卫自己应有的权利。在政治生活中,常常表现为剥夺选举权利,被阻止不能通过有效渠道表达自己的意愿,基层民主选举存在贿选、政府官员贪污腐败现象暗示着公民政治权利意识单薄,官僚体制运行存在弊端[10]。因此,政治生活领域,弱势群体的各种利益不能得到表达和满足,于是在其他各个领域都无法与那些政治强者群体共享利益果实,这就存在巨大的不平等性[9]。3.3公共权力的隐性收入一直以来,“隐性收入”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在很多情况下表现为不同的形式,存在多种变形,形式多样化,内容复杂化。“隐性”是与“公开”相反的[11],而隐性收入与隐性腐败紧密相连,隐性腐败是指极个别的国家公职人员因各种各样的原因,没有做到廉政,利用自己的公共权力,打着行政的幌子为自己谋取一些利益,他们用的手段通常非常间接、隐蔽,危害了公共资源和公共利益。他们利用法律的漏洞故意不作为或者乱作为,给他人设障以获得他人对他的人情交往。
另外,基层乱收费现象也是隐性收入的重要来源,大部分在县、乡镇及村级单位,许多都属于典型的农村“三乱”,即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12]。同时,还有一些乡村基础设施建设上向村民乱摊派的现象,加重了村民的经济负担,例如乡村道路的修缮、公益事业的建设等。很多乡镇政府鼓励这种收费,实际是为了增加自己的部门收入,建立自己的小金库。
4结论及政策启示
为了防止“权力之手”变成“掠夺之手”,必须改进政治权力在社会财富分配中的效用。政治权力在社会财富分配过程中,可以通过立法权力、行政权力和司法权力间的关系表现出来。目前,我国经济环境复杂,要保证收入分配的有序性,必须通过政治权力来协调,从而监督社会财富公平分配。首先,政府要合理运用经济手段规范分配秩序,在保护合法收入的同时取缔不合理收入。再者,充分运用法律手段,使社会财富的公平分配有法可依,违法必究。再次,通过行政手段和监督手段保证财富的公平分配。行政手段具有强制性,有助于保障利益一致性并纠正分配中的混乱现象。此外,监督手段通过从多角度、多层次对社会财富分配进行有效监督,确保收入分配从起点到结果都遵循公平公正的原则。总而言之,从解决路径来看,从经济干预、政策偏向及制度保证3方面来进一步解决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
4.1经济干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加大再分配调节力度,着力解决收入分配差距较大问题。在发展平衡性、协调性、可持续性明显增强的基础上,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公众称之为“倍增计划”。首先,我国收入分配改革应该注重减少极富极贫的人数,增加中等收入人群。具体而言,就是通过有效的税收体制,提高农村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防止生活成本过快增长对农村居民消费产生的挤出效应而不利于中等收入群体的崛起,最终要通过体制与制度的保障来促进农村居民财富合理地向中等收入群体流动。其次,市场是只“看不见的手”,政府是只“看得见的手”。在我国的政治经济环境下,“看不见的手”需结合“看得见的手”,从而控制各种消费品的价格,提高农民收入。具体而言,其一,通过提高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降低农业生产资料的价格,以达到农民增收的目的。其二,减免农业税收,通过税收调节高收入,改善低收入,取缔非法收入。
4.2政策偏向政府应充分发挥宏观调控作用,通过政策引导、财政支持及技术支持,充分挖掘西部优势资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发展战略是非均衡分配的,政府在科教文卫体、公共服务及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支出多年来都偏向城市或东部经济较发达地区,而使得农村地区及西部地区的发展动力不足。十七大提出“再次分配更加注重公平”,笔者从时间序列数据上观察到政府对农村科教文卫事业、公共服务、社会保障支出的比重逐年提升,从农业中提取的工业发展资金逐年下降,极大地缩减了农村贫富差距。新农村建设提出之后,政府采取有效措施,例如增加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加大农资综合直补力度等。国家发改委主任马凯在2007年谈国家宏观政策时则表示,中央政府建设投资用于直接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的投入,用于支持基础教育和公共卫生等社会事业发展的投入,较2006年均有所提升。国土资源局将中央和地方土地收益直接用于支持农业发展的资金数量将超过1 000亿元。
4.3制度保证积极完善权力机制的改革,建立适度的分权制度,将具体化的政治权力转化为职权,并明确职权范围。与此同时,建立并完善农村的选举制度,使村干部政治权力具有公开性与程序性。具体而言,明确公开性就是尽可能暴露那些村干部以权谋私的行为,尤其是村干部处于最基层的权力,容易拥有较大的分权,政策下达不到位的现象可能导致惠民政策不能真正落实,这就需要明确资金流向,实施乡镇账务公开制度,避免滋生腐败,并以乡镇政府为表率建立信用系统。此外,政府在增收个税的同时,也必须进一步建立和完善乡镇官员个人财产申报和公开制度,接受公众的监督,这样便是通过程序性使政治权力主体谋取私利的可能性得到最大程度的遏制,以制度保证社会财富分配的公平与公正。
参考文献
[1] 文舒婷. 我国公务员隐性腐败的现状、成因及防治对策研究[D].长沙:湖南师范大学,2014.
[2] 克鲁格.寻租社会政治经济学[J].美国经济评论,1974(6):8-16.
[3] 伊特韦尔,米尔盖特,纽曼.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1卷[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914-925.
[4] 托林森.寻租的福利分析与实证分析[J].经济学动态,1990(5):66-71.
[5] 戈登·塔洛克.寻租[M].李政军,译.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
[6] 陈健. 我国地方政府的权力寻租:现状、原因及治理[D].上海:上海交通大学,2008.
[7]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3.
[8] 王春福.社会权利与社会性公共产品的均等供给[J].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0(1):90-94.
[9] 王一多. 政治权利平等是公民社会权利平等的前提条件[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11):87-89.
[10] 孙小双.权利公平的社会哲学思考[D].济南:山东师范大学,2014.
[11] 居丽.公务员隐性收入问题研究[D].南京:南京师范大学,2007.
[12] 于小鹏.关于权力腐败之成因及其应对措施的分析[D].北京:中国政法大学,2010.
作者简介石婷(1990- ),女,江苏南京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行政管理(人力资源管理)。*通讯作者,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行政管理。
收稿日期2016-04-13
中图分类号S-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17-6611(2016)14-279-04
Paradigm Research on the Application of Rural Political Rights in Social Welfare Distribution
SHI Ting, ZHU Ting-ting*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0095)
AbstractWealth inequality has been a important problem in China′s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re are many factors affecting the distribution of wealth. The third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8th Central Committee emphasized the power normalization and prevention of corruption. In this research, we researched the effects of political rights on the distribution of social welfare. On the basis of literature review, we firstly tried to demonstrate the achievements on distribution of wealth and the adjustment on wealth by government. Then, statistics of rural area in China found out that there were great differences in per capita income between village cadres and ordinary rural family. Causation of this power distortion hindering the fair distribution of wealth were analyzed from three aspects of the unfair distribution of social resources, the uneven empowerment of different populations, and the invisible income of public power. Finally, solutions were put forward from economy, policy and system.
Key wordsPolitical power; Income gap; Distribution of wealt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