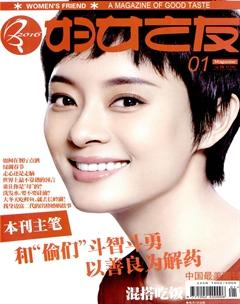李敏回忆录
背景:李敏,抗联老战士。少年李敏母亲去世,父亲和哥哥进山参加抗联,家里只剩她孤身一人,在党组织的帮助下先参加抗日宣传队,后参加抗联。本文选取《李敏回忆录》,文中讲述和战友。
返回祖国
当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这一喜讯传来时,整个八十八旅沸腾了。十四年的艰苦奋战,终于打败了日本侵略者,光复了祖国,三千万东北人民终于结束了亡国奴的生活。
苏联出兵以后,经与苏联远东方面军协商,双方根据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可能出现的情况,共同商定抗联部队的任务如下:
随同苏军返回东北后,迅速抢占战略要点,接收东北;抗联干部在各战略要点的负责人分别担任该地苏联红军卫戍司令部副司令,协助苏军占领和管理新解放的城市,肃清敌伪残余分子和其他反革命分子,维持秩序;利用既是抗联人员,又是苏军人员这一有利地位,建立各地党组织,发动群众,建立人民武装。
1945年8月10日抗联教导旅在驻地召开了反攻东北、配合苏军消灭日本关东军动员大会。周保中总指挥在会上作了动员报告,号召全体指战员为消灭日本侵略者,争取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而英勇战斗。

抗联教导旅经过了几年的政治学习和军事训练,已经成为一支懂政治、讲战术,能征善战的部队,许多教导旅抗联干部、士兵直接参加了苏联红军出兵东北的战斗。其中一百六十多人编入到苏联第一方面军,八十多人编入到苏联第二方面军,还有一百多人编入到后贝加尔方面军作为先遣部队,执行特殊任务。另外,7月末,有一部分人(伞兵部队)空降到东北,潜入敌后进行战前侦察。这些由抗联指战员组成的先遣部队,有长期对日作战的经验,地理环境熟悉,出色地完成了各种特殊任务,东北抗联空降特遣部队为苏联红军在短期内迅速消灭东北的侵华日军,发挥了特殊的作用。空降的先遣小分队做出了很大的牺牲。
东北十四年抗日武装斗争,消灭敌人大批有生力量,日军伤亡人数无准确统计,据抗联第二路军总指挥周保中推算:1931-1937年抗联歼敌十万三千五百人,1937-1945年歼敌八万二千七百人,共计十八万六千二百人。日军在东北兵力:1937年二十万,1940年四十万,1941年为七十六万。其中被抗联牵制者约有十万。
没有哪一场战争,像东北战场这样酷烈,东北抗日联军孤悬于敌后,与数十万日本侵略者进行了长达十四年的殊死搏斗。“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没有经历的人是写不出这样的诗句的。在这场残酷的斗争中,抗联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人大多战死,这是有史以来,世界上任何一支军队所少有的,无论是总司令、军长还是士兵,在残酷的十四年斗争中,每时每刻都面临着饿死、冻死和战死的威胁。仅军级干部就牺牲了三十多位,师级干部一百多位。当残忍的敌人剖开杨靖宇将军的胃时,他们所能看到的只是树皮、草根和棉絮,没有一粒粮食,就连凶恶的敌人也不能不被中国人的顽强与坚毅所折服。
对于东北抗日联军参加远东战役的历史功绩,斯大林和苏联政府给予很高的评价和认定。
1945年8月下旬,斯大林代表苏联政府授予周保中(八十八旅旅长)、张寿篯(八十八旅政治副旅长)、王效明(八十八旅二营营长)、王明贵(八十八旅三营营长)等四人“红旗勋章”,以表彰他们在“远东战役”中的功绩。
为了应付国内复杂的斗争环境,回国时,要求东北抗日联军指战员都要更名换姓,如周保中改为黄绍元,张寿篯改名为李兆麟,崔石泉改为崔庸健,冯仲云改为张大川等。我改名为李敏,这个名字我一直用到现在。
八十八旅规定,回国时,嫁给朝鲜族的汉族女战士都要随丈夫去朝鲜,相反朝鲜族的女战士嫁给了汉族就要随丈夫去中国。

当时,在北野营结婚的汉族女战士王玉环嫁给了朝鲜族崔庸健;汉族女战士李淑贞嫁给了朝鲜族金京石;鄂伦春族女战士李桂香嫁给了朝鲜族金勇贤(金大宏)。她们三位都要随丈夫去朝鲜。我们这些朝夕相处,生死与共的战友眼看就要天各一方,大家的心情都十分的难过,个个泪流满面,不知何年何月能再相见……
同志们已经陆续走了两批了,我们待命的人员个个心急如焚,都想一下子就回到祖国的怀抱。
这一天终于来到了。1945年9月11日,我们乘车从北野营去伯力。当要走的那一刻来临时,大家什么都不要了,生病的战士把自己泡的珍贵的药酒都扔了,同志们只有一个心愿:回国!回国!快点回到祖国!
当汽车开到伯力时,天色已晚,我们在这里住了一夜,第二天中午登上了一架小型军用飞机向着祖国飞去。
飞机上坐有二十来人,除了抗联回国人员外,还有五名苏联军官一同前往。飞机上引擎轰鸣,虽然我们听不到彼此的说话声,但是巨大的喜悦都闪现在脸上。
飞机飞过黑龙江了,我们趴在机舱的窗户上向下观望,黑龙江好似一条银色的玉带,在秋日的阳光下闪闪发光,过了黑龙江,那就是我们的祖国啊,我们回来了!
忘不了第一次过黑龙江时,我们被敌人追击,在白福厚团长、杜指导员的带领下江中准备就义的情景;忘不了第三次过江,我们趴在窄小的木排上,险些被黑龙江的滔天巨浪掀入大江的时候……第一次过江的战友好多都已经牺牲了,他们永远地长眠在了黑土地上,长眠在深山老林里,他们没能看到祖国光复的这一天。
那天我们出了机场,陪同我们的苏联军官联系了一辆大卡车。卡车载着我们奔向了北安正街的一个日式楼房。据说,这座房子是伪满的“兴农合作社”。
当时的北安,街上乱哄哄的,人们都在捡拾日本人扔下的各种用品。百姓们大包、小包用麻袋、用包袱皮包着日本人丢弃的和服和被褥之类的东西。看到我们这些穿着苏联军装的中国人,都很好奇。
在这里将就住了一宿,第二天早上我们登上了一列南去的火车,由于敌人撤退时沿线铁路破坏严重,列车走走停停,傍中午时分才来到了海伦。
那一天海伦火车站人山人海,大批的日本战俘聚集在这里,他们也都等着上火车,站台内不少商贩在卖煮熟的玉米。一个日本战俘也许是饿急眼了,抢了一个老乡的苞米就吃了起来,老乡跟他要钱,他直摆手,陈明看到了,拽住那个战俘就要打他。
这个时候,站台里的百姓们发现,我们虽然身穿苏联军装,但都是黑眼睛黑头发的中国人,大家都好奇地围了上来,张光迪同志站在人群中间,大声地说:“老乡们,我们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我们打败了日本关东军,我们回来了,我们胜利了,我们即将要建设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国家。”百姓们对他的讲话报以热烈的掌声。
讲完话张光迪他们在苏联红军的陪同下,消失在了茫茫的人海。
看到他们走了,热情的老百姓,把热乎乎的苞米从车窗里直往我们的手里塞,老百姓对我们东北抗日联军的这种热情令我们十分感动。
下午5点左右,列车终于到了绥化。走出了绥化车站,我们惊喜地看到,好多学校的老师和学生在列队欢迎我们,当地百姓和社会各界人士也来到了车站。他们手里拿着五颜六色的小旗,脸上都挂满了笑容。车站前有一个土台子,陈雷同志跳上土台子,发表了演讲。
陈雷讲道:“我们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联军,我们和苏联红军一起打回来了,我们在毛主席、朱总司令的领导下,坚持了十四年的抗战,打败了日本关东军,今后,我们再也不是‘亡国奴’了。共产党历来主张民主,反对独裁、反对卖国;主张和平,反对内战。我们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人民的新政权,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富强的新中国,我们要让老百姓都过上好日子。”
陈雷同志的讲话,博得了阵阵热烈的掌声。讲完话,我们上了一辆吉普车,从东门向西开去。绥化正街上的原伪警察署现在是苏联红军的驻地,苏联军官卡萨拉耶夫(少校)是驻绥化的卫戍司令,陈雷同志到了这里担任副司令之职。
这是一栋二层小楼,我们被安排在二楼的一个房间。房间不太大,是日本式的布置,里面有个套间,有一张铁床,我和陈雷同志就住在了里间。外间没有床,铺的是榻榻米,门是拉门,其余的同志住在了外间。我们和苏联红军在同一个叫作“大菜馆”的食堂吃饭,食堂定时、定点,过了时间饭馆就关了,每天吃的还是黑面包、苏伯汤。
这里的生活用品基本还全,有洗脸的地方。在这里,我还拣到一个写着“勤劳奉仕”的木头箱子和日军用的一只大皮包、一只小皮箱和一面黑框大镜子,以后我们就用这几样东西装电台、文件和子弹。这几样战利品已经陪伴我六十七年,几次搬家我都一直带在身边,可以说已经成为文物。
还记得当时陈雷同志看到这个大皮箱,高兴地说:“哈哈,这个牛皮真厚啊,要是煮了吃,一定能炖一大锅……”
当时在场的李海清乐着接话:“你还没吃够那皮带,靰鞡鞋啊……”
1948年的夏天,为了巩固东北大后方,为了迎接新中国的建立,我们急需有知识、有文化的干部充实到各个领域。我申请去学习,经王鹤寿书记批准,省委组织部部长赵德尊同志给开了介绍信,我被派往哈尔滨外国语学院去学习俄语。
只身一人,拎着简单行李的我来到了哈尔滨。当时的外语学院在中山路南,一栋大房子是课堂,旁边几栋俄式小楼是我们的寝室。学员来自东北各地,有的学员是八路军、新四军的后代,这些学员大都二十多岁,都是通过政审进来的。我们的校长是刘亚楼和从延安来的,王玉(女),教务长是延安来的赵洵(女)和赵相两位老师,主教老师是一位四十岁左右的俄罗斯妇女叫娜塔莎,助教是一位年青的俄罗斯姑娘名字叫娜佳。
安顿下以后,紧张的学习就开始了。我们每天天一放亮就爬起来背单词,每天一小考,周末大考。我在苏联呆过几年,多少还有些基础,没有基础的学员,学起来就十分吃力了。那时候,我们在经济技术等方面还是挺依赖苏联的,把他们称为苏联老大哥,所以学好俄语也至关重要。
周末休息的时候,我去老首长冯仲云家里去看望他。冯仲云当时是松江省主席。他的夫人薛雯同志正在筹建东北烈士纪念馆,她是第一任馆长,我把自己精心保存了八年的歌曲集献给了东北烈士纪念馆。
冯主席的家里客人不断,大部分都是东北抗联人员。他家当时有两间屋子,冯仲云夫妻睡一张小铁床,我们去了都睡地板,吃饭自己做,大家说说笑笑,其乐融融,仍旧保持着当年抗战时的习惯。
看到老首长我感到十分亲切,我向他汇报了这几年的工作,他鼓励我一定要好好学习,他说没有知识,没有文化将来是不行的。这个时候,薛雯同志和我说:
“小李子,你知道吗,李升老人也在这里。”
“李升?是那位带我上山的李爷爷吗?”我急切地问。
“是啊,他1938年被捕,被关押在依兰县监狱,‘八一五’光复才出来,出来后,他找到了冯主席,冯主席把他安排在伪满警察署(现东北烈士纪念馆)的房子里住下了,现在有专人照顾他。”
原来,1938年初,北满抗联部队与活动在南满的抗联第一路军失掉联系,几次派人都联络不上,最后只得把这个艰巨的任务交给这位已年过七十的老人。他二话没说,一个人冒着零下四十多度的严寒,踏着没膝深的大雪,进入人迹罕见的长白山原始森林。每天只能啃几口冻得像石头似的苞米面饼子,吃几口雪。脚冻肿了,手冻裂了,他全然不顾,仍顽强地寻找着,好几次昏倒在雪地里,就这样走了一个多月,终于在一片森林里找到了抗联一路军的队伍,完成了通信联络任务。
李升跑交通被捕过几次,每次他都机智地把文件吞进肚里,无论敌人怎样毒刑拷打,他也不吐露半点机密。由于找不到证据,不得不把他释放。同年夏,他寻找第一路军回来,走到依兰时由于叛徒告密而被捕,日军把他当作重要政治犯关押起来,对他施以种种酷刑,灌煤油、烙铁烙、站铁刺笼子,他浑身被刺成数不清的血窟窿,疼痛钻心,死去活来,但他始终坚贞不屈,最后被判处十年徒刑。1945年8月日本侵略者投降后,李升才走出监狱,辗转寻找党的组织。1946年8月,年已八十岁的李升老人回到哈尔滨,打听到当时已任松江省主席的冯仲云,回到了党的怀抱。由于他年岁大,在狱中受刑过重,身体不好,党组织安排他长期休养,并派专人照料其生活。
听说李升爷爷就在哈尔滨,我迫不及待地想立刻见到他,薛雯同志说:“走,我带你去看他。”我们来到了原来伪满警察署的那栋房子,李升爷爷住在一个套间里,抗联老同志刘奎武夫妇负责照顾他。
我和薛雯同志进了屋,屋子挺亮堂。这是李升爷爷吗?我好像是在梦里。李升爷爷老了,头发胡子全白了,他双手拄着一根拐杖坐在炕沿上。我拼命抑制住奔涌而出的泪水,走到他的面前。这时,薛雯同志问他:“李老,你看看这是谁?”
李爷爷抬起头看了看我,多么熟悉的目光啊,就像当年在板场子时看我的眼神一模一样。看完后他说:“不认识,我不认识她。”
我着急了,我说:“李爷爷,是我,小李子,小凤啊!”
“小凤?”李爷爷好像在他的记忆里搜寻,忽然他说:
“小凤,你是小凤?你还活着啊?”
我再也忍不住了,跪在地上,趴在李爷爷的膝盖上哭了起来。
李爷爷摸着我的头也哭了:“小凤啊,你活着,我差点没死啊,死了就见不到你了……”
“是啊,李爷爷,我们都活着,多好啊,可吴玉光和裴大姐他们都牺牲了”
李爷爷真是老了,哭得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嘴角还流出了口水,我赶忙站起来给他擦了去。李爷爷说:“小凤啊,你长大了,我老了,我差点死在监狱里啊……”
1951年国庆节,李升爷爷被选为东北抗日联军代表,去北京参加国庆观礼,受到毛泽东主席接见,不久他被邀为黑龙江省政协常委。(完)
本栏编辑/桃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