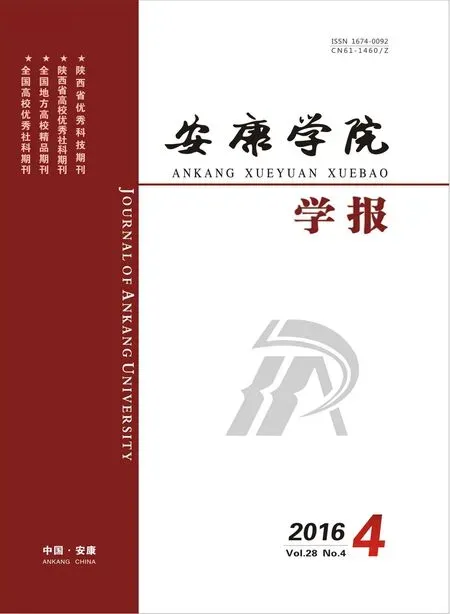论刘宋时期的调谑之风与文化精神变迁
李 鹏
(临沂大学 文学院,山东 临沂 276005)
论刘宋时期的调谑之风与文化精神变迁
李鹏
(临沂大学文学院,山东 临沂 276005)
一个时代的文化精神,不仅仅表现在重大的政治历史事件或者鸿篇巨著上,还体现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甚至细枝末节上。这些细枝末节的东西,往往因为参与主体的广泛性,反而更能成为一个时代的缩影。刘宋时期的调谑之风即是如此。透过它,我们不仅可以了解当时思想的混乱与复杂,而且对了解南朝的社会风俗、文化发展以及文学演进等也多了一个观测点,同时我们还可以由此看到人文精神变化背后为人与为文之间相互影响与促进的关系。
刘宋时期;调谑之风;文化精神;人生百态
调谑,即调侃戏谑之意,刘宋时期此风颇兴。伴随着调谑风气的发展,幽默与讽刺文学的创作也较为繁荣。林语堂先生曾言,幽默是一种人生观,是一种对人生的批评,同时也反映了作家、作品的风格。这一时期士人嬉笑怒骂的背后体现出的文化心理,以及对当时的文学创作所产生的影响等,正是本文着重探讨的内容。
一、调谑中的世相与士风
刘宋代晋不仅仅是简单的朝代更替,也是中国历史、社会发展的一大转折。出身低微的刘裕开始了皇权独断,“寒人”在政权中的作用开始突显,门阀政治虽渐趋衰落却惯性依在,皇室内部猜忌、杀戮频仍。然而,整个社会的不稳定状态,却似乎为调谑之风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折射出了当时社会的百态人生。
首先,刘宋时期的调谑之风,反映出名士风流的余绪。刘宋时期的士族名士,仍有东晋时的“任诞”与“排调”,表现出传统文化心理的强大惯性。魏晋时期世风放诞,士人以嘲谑为戏。葛洪称“世故继有,礼教渐颓,敬让莫崇,傲慢成俗。俦类饮会,或蹲或踞,暑夏之月,露首袒体……不闻清谈讲道之言,专以丑辞嘲弄为先。以如此者为高远,以不尔者为騃野。”[1]而至刘宋,此风仍炙:
(何尚之)与太常颜延之少相好狎,二人并短小,尚之常谓延之为倂,延之目尚之为猴。同游太子西池,延之问路人云:“吾二人谁似猴?”路人指尚之为似。延之喜笑,路人曰:“彼似猴耳,君乃真猴。”[2]785
承天年已老,而诸佐郎并名家年少,颍川荀伯子嘲之,常呼为奶母。承天曰:“卿当云凤凰将九子,奶母何言邪!”[3]1704
无论是嘲谑他人还是自嘲,表现出了魏晋名士的那种放达心态。然而士人相谑,也并非仅以轻薄目之。张畅与北魏李孝伯对答,笑骂“白贼”,史评“吐属如流,音韵详雅,风仪华润,孝伯及左右人并相视叹息。”[3]1605至于当时士人纷纷以文义相标榜,乃至彼此相轻而嘲谑:
孝武尝问颜延之曰:“谢希逸月赋何如?”答曰:“美则美矣;但庄始知‘隔千里兮共明月’。”帝召庄以延之答语语之,庄应声曰:“延之作秋胡诗,始知‘生为久离别,没为长不归’。”帝抚掌竟日。[2]1554
故意无视语境而摘录貌似平实的语句以供嘲哂,有文人相轻意,却也表现出士人的高雅与素养。而范晔诸人临刑,即使内心实有贪生之念,却仍表现出士人面对生死时无忧无惧的雅量:
(范晔)在狱为诗曰:“……虽无嵇生琴,庶同夏侯色。寄言生存子,此路行复即。”……将出市,晔最在前,于狱门顾谓综曰:“今日次第,当以位邪?”综曰:“贼帅为先。”……妹及妓妾来别,晔悲涕流涟,综曰:“舅殊不同夏侯色。”晔收泪而止。[3]1882
晋朝名士嵇康临刑前泰然抚琴为人所熟知。而夏侯玄在被考掠时不发一言,临刑前脸色不变,也是名士做派。范晔的诗用他们的典故,表现自己对生死的态度。在临刑前调笑位次、不惧生死,倒也差强人意。只是与亲人作别前哭哭啼啼,虽是人之常情却惹得外甥谢综不满,故而出语调侃范晔言行不一。相比较之下,谢综更具名士之风也。
其次,刘宋调谑之风背后是士人面对皇权的无奈与挣扎。范晔被处死,也反映出了此时高门的境地已经大不如前,主强臣弱之格局已成必然之势。加之刘宋诸帝统治严酷,士人朝不保夕。所以士人往往以调谑免祸。在宋文帝统治时期,士人尚可保持高贵狂傲之态,故袁淑在宋文帝前嘲笑顾荣,顾恺之尚能正色斥之①《宋书·顾恺之传》记载顾恺之和袁淑曾经在文帝前议论江左人物,谈及顾荣,袁淑对觊之说:“卿南人怯懦,岂办作贼。”觊之正色曰:“卿乃复以忠义笑人!”。。然宋孝武帝调谑群臣则肆无忌惮。如《宋书·王玄谟传》载:
孝武狎侮群臣,随其状貌,各有比类,多须者谓之羊。颜师伯缺齿,号之曰鳓。刘秀之俭吝,呼为老悭。黄门侍郎宗灵秀体肥,拜起不便,每至集会,多所赐与,欲其瞻谢倾踣,以为欢笑。又刻木作灵休父光禄勋叔献像,送其家厅事。柳元景、垣护之并北人,而玄谟独受“老伧”之目。凡所称谓,四方书疏亦如之。[3]1975
周一良先生在论及刘义庆“不复跨马”时指出,“跨马”在当时会成为表达政治野心的一种方式,所以在猜忌之心颇重的宋文帝面前,还是低调些的好。在世路更为艰险的宋孝武帝统治时期,“嘲谑”同样具有符号化意义。士人若想避祸乃至延续恩宠,和光同尘似乎是一种必然的选择。若仍持东晋时代的高贵与狂傲,则恐有性命之忧。如《南史》卷34《沈怀文传》载宋孝武帝每次宴会,在座的都要大醉。而沈怀文平常不饮酒,又不好戏谑,孝武帝称其为“异己”。谢庄曾劝沈怀文说:“您每每与他人不一样,恐怕很难长久。”后来沈怀文果然被孝武帝借故处死。又据《南史》,孝武帝曾让江智渊唆使王僧朗嘲弄他的儿子王彧。江智渊很严正地拒绝了。孝武帝非常生气,直呼江智渊父亲的名字说道:“江僧安就是一个白痴,白痴才会互相爱惜!”江智深不堪羞辱,伏席痛哭不已。由此也渐渐不被孝武帝所喜,直至后来忧惧而死。
刘宋诸王也以调谑文士为常,如袁淑为人喜欢夸诞,始兴王刘浚便用三万钱来戏弄他,让他做了次过路财神。一些士人为求仕进,必然变高傲为谄媚,让人感到了高门士族的无奈与悲哀:
(刘)德愿性粗率,为世祖所狎侮。上宠姬殷贵妃薨,葬毕,数与群臣至殷墓。谓德愿曰:“卿哭贵妃若悲,当加厚赏。”德愿应声便号恸,抚膺擗踊,涕泗交流。上甚悦,以为豫州刺史。[3]1376
刘义庆《世说新语》曾有曹丕在凭吊王粲时让宾客学驴叫以寄托哀思的记载,读之令人有悲有喜更有莫名的感动,我们从中不难体会魏晋人的真性情。但在这里,我们看到的只是一个没有下限的高级哭客而已。至于出身低微之士,为求仕进,常以恩幸作为进身之阶,所以他们更不以高门士族之矜持为意了:
(孝武帝)令医术人羊志哭殷氏,志亦呜咽。他日有问志:“卿那得此副急泪?”志时新丧爱姬,答曰:“我尔日自哭亡妾耳。”志滑稽,善为谐谑,上亦爱狎之。[3]1376
最后,皇室调谑之风,反映出他们的粗鄙。刘裕起于行伍,其文化修养实不敢令人恭维。然恐为世家大族所轻,所以颇慕风雅。又自其开始,便注重对宗室的教育,以期拉近与士族在文化上差距。诸宗室也颇重文艺,故其中不通文墨者,往往成为被调谑的对象:
(刘)义宾弟义綦,元嘉六年,封营道县侯。凡鄙无识知,每为始兴王浚兄弟所戏弄。浚尝谓义綦曰:“陆士衡诗云:‘营道无烈心。’其何意苦阿父如此?”义綦曰:“下官初不识,何忽见苦。”[3]1470
由于出身阶层的不同,他们对世族既防且羡。刘宋皇室对世族打击不遗余力,对士人风流的模仿也颇多用心。然而他们大多为粗鄙之辈,言行举止往往不一,又大多画虎类犬。虽都自诩文采风流,但最得心应手的却是里巷之歌谣。故陆机诗文即使在刘宋朝流行一时,但刘义綦却也不知自己与陆机所处时代相差甚远,所以才被刘浚等戏弄。当然,刘浚也不过五十步笑百步而已。至于刘宋王室之教养,也着实让人诟病。赵毅称:“宋武起自乡豪,以诈力得天下,其于家庭之教,固未暇及。”[4]宋室闺门多无复道德伦理,而皇室言行亦多薄劣。虽然嘲谑本身不是高雅之行,但毕竟有雅俗与恶俗之分。但我们看孝武帝调谑之行,实为狎辱群臣。至于明帝内宴,以观裸体妇人为欢笑,已是桀纣之行!此等调谑,实和高门名士的任诞相去甚远;嘲谑之行亦是徒具任情放荡之形,而无雍容华贵之姿。正如钱穆先生所言,“只稍微熏陶到一些名士派放情肆志的风尚,而没有浸沉到名士们的家教与门风,又没有领略得名士们所研讨的玄言与远致。在他们前面的路子,只有放情胡闹。”[5]从上面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刘宋时期调谑成风以及其中反映出的士风变化。他们或以任诞为高,或以嬉笑谄媚,或以放浪为乐,或以调谑取容。其间既有雅士的高标、士人间的揶揄,又有君臣间的狎戏、宗室的放荡。世间万相,尽在这调谑之中。
二、调谑中的创作与文风
作为表现士人才情的文学创作,也沾染了调谑之风。在这里,调谑风气其实也折射出一种审美标准。这种审美标准不仅表现在对士人气度、文化品格的评判上,也表现在文学创作中。伴随着刘宋时期调谑之风的盛行,幽默文学的创作也进入长足发展的时期。
在诗歌方面,有即兴的戏作。《宋书》载刘邕令王歆之作劝酒歌,王歆之即席而作曰:“昔为汝作臣,今与汝比肩。既不劝汝酒,亦不愿汝年。”此歌化用孙皓《尔汝歌》:“昔与汝为邻,今与汝为臣,上汝一杯酒,令汝寿万春!”[6]以表达对刘邕嘲弄与不屑。而何长瑜则以韵语嘲义庆州府僚佐:“陆展染鬓发,欲以媚侧室。青青不解久,星星行复出。”(《全宋诗》)此诗写陆展染发以取悦小妾,但不想没过多久,满头又是星星白发。读来令人展颜而笑。而民歌中尤多调谑幽默之辞,如《读曲歌·其三十》:“白门前,乌帽白帽来。白帽郎是侬,良不知乌帽郎是谁?”明知故问,表现了情人间的调笑戏弄,饶有风味。我们已知在刘宋时期民歌为皇室所激赏,文人也多有拟作。所以,如果说民歌的此等声情也影响到了文人创作,也并非无的放矢。
文章中的嬉笑怒骂,皆令人会心。羊希与周朗书相戏,周朗报羊希书亦辞意倜傥。其骂羊欣“观诸纸上,方审卿复逢知己。动以何术,而能每降恩明,岂不为足下欣邪,然更忧不知卿死所处耳。”[7]476让人拍手称快。乔道元《与天公笺》,直接向天公哭穷:
道元居在城南,接水近塘。草木幽郁,蚊虻所藏。茅茨陋宇,才容数床。无有高门大户,来风致凉。积污累熏,体貌萎黄,未免夏暑,逆愁冬霜。冬则两幅之薄被,上有牵绵与敝絮,撤以三股之丝綎,袷以四升之粗布,狭领不掩其巨形,促缘不覆其长度。伸脚则足出,挛卷则脊露。[7]571-572
此文极尽描写穷苦之能事,似乎希望上天垂怜。语言平直如家常话,幽默风趣。钱钟书云此文:“刻划己身穷乏之状,而出以诙谐。”[8]又宋世诸公主,莫不严妒。宋明帝随令虞通之为江敩作《让尚公主婚表》,极写丈夫惧内之态,公主对丈夫之防嫌之严:
至如王敦慑气,桓温敛威,真长佯愚以求免,子敬灸足以违诏,王偃无仲都之质,而倮露于北阶,何瑀阙龙工之姿,而投躯于深井,谢庄殆自同于矇叟,殷冲几不免于强鉏。
出入之宜,繁省难衷,或进不获前,或入不听出。不入则嫌于欲疏,求出则疑有别意,召必以三晡为期,遣必以日出为限,夕不见晚魄,朝不识曙星。至于夜步月而弄琴,昼拱袂而披卷,一生之内,与此长乖。又声影裁闻,则少婢奔迸;裾袂向席,则老丑丛来。[7]545-546
宋室闺门之风实在让人不敢恭维。《宋书·赵伦之传》便载始兴王刘浚与海盐公主私通,二人为嫡兄妹关系;孝武帝女山阴公主更是令人发指,曾直接要面首三十余人。褚渊是她的姑父,她竟毫无避讳的想公然逼为淫乱!此篇仅仅提及公主的妒忌之行,可谓给皇室留足了颜面。士人往往对诸公主敬而远之。难怪此文云若辞婚不成,宁愿“刊肤剪发,投山窜海”,逃之夭夭了。此文以调谑之语为之,读之令人捧腹不已,作者亦可避祸。
谐隐之作,是文学创作受调谑之风影响的突出表现,其中以袁淑成就最高。观袁淑所作《鸡九锡文》 《劝进笺》 《驴山公九锡文》 《大兰王九锡文》 《常山王九命文》等作,皆仿照公文的形式。如果说虞通之的《让尚公主婚表》体现了调谑之作的宣诫作用①《宋书·后妃传》载,宋明帝“以此表遍示诸主。于是临川长公主上表曰:‘妾遭随奇薄,绝于王氏,私庭嚣戾,致此分异。’”看来对她们还是有所触动的。,那么袁淑的这些作品则表现出了谐隐之作的刺世功能。如《鸡九锡文》:
维神雀元年,岁在辛酉八月己酉十三日丁酉,帝颛顼遣征西大将军下雉公王凤,西中郎将白门侯扁鹊,咨尔浚鸡山了:维君天姿英茂,乘机晨鸣,虽风雨之如晦,抗不己之奇声。今以君为使持节金西蛮校尉,西河太守,以扬州之会稽封君为会稽公。以前浚鸡山为汤沐邑,君其祗承予命,使西海之水如带,浚鸡之山如砺,国以永存,爱及苗裔。[7]442
这些作品的有趣之处在于强烈的反差效果。“九锡文”乃是典丽庄重之公文,作为册封功勋卓著之功臣之用。此文却用在鸡的身上,有不伦不类之感。而且其文字越是凝重典雅,越让读者觉得滑稽可笑。这种手法,正类似于法国罗伯尔·埃斯卡尔皮特所说的“高尚的文体用来处理一个下流的主题或一个粗俗的文体用来处理一个高尚的主题。……这一讽刺和由此引出的幽默在某些文学作品中则冠以一个诙谐的名称,但这仅仅是一个名称而已。”[9]其他如《驴山公九锡文》 《大兰王九锡文》等亦是如此,从而达到对讥刺世事的目的。谭家健先生认为“袁淑的基本手法是处处双关,句句影射,尽量模仿历代九锡的体例和套语,在种种冠冕堂皇的漂亮外衣之下,让读者隐约感到,朝廷九锡盛典不过是‘沐猴而冠’罢了。”[10]正是着眼于这些作品的刺世目的。
而文学上调谑之风的发展,莫过于专门文集的出现。刘义庆集合门下文人编撰《世说新语》,其中专列“排调”等节,排调即诙谐滑稽之意。专门记载士人的诙谐调谑言行。至如《隋书·经籍志》则有:“《诽谐文》十卷,袁淑撰”[11]的记载,不能不说也受到了当时调谑之风的影响。这对丰富文学的表现方式,无疑有着积极的作用。然而,大部分的游戏之作,如果仅仅着眼于其娱乐功能,必然对后世文学创作产生消极的影响。如刘师培在评论谐隐文时指出,“谐隐之文,起源古昔。宋代袁淑,所作益繁。惟宋齐以降,作者益为轻薄,其风盖昌于刘宋之初。”[12]
三、嘲谑与时代文化精神的变迁
由上可知,刘宋时期的嘲谑之风不仅广泛存在于朝堂,同时也蔓延到文化生活的诸多方面。所以它犹如一扇窗户,透过它我们可以看到刘宋时期的政治与文化生活的诸多表象。
首先,嘲谑之风盛行反映了士人文化精神的变化。刘宋政权的建立,虽然整肃了朝政,却也混乱了士人的言行和思想。由于自身的门第与文化优越感,士族文人往往自视甚高。如在王僧达等人看来,皇亲国戚的鄙陋其实不值一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不同于皇室的鄙俗,士人间的调笑行为更有阳春白雪之意。如颜延之与何尚之之间的调侃,依稀可见名士的放浪形骸;谢庄与颜延之相互的嘲讽,更像是智者间的言语交锋;谢综临刑前轻松调笑,是世族一贯秉持的风流与尊严。但是士人也明白,崛起的刘宋政权毕竟不同于传统的世族政治。在皇权的威迫之下,为了家族的存续,他们又不得不虚与委蛇。于是,士人风骨慢慢变得百不存一。对此,王夫之评述道:“宋自孝武迄于明帝,怀猜忌以待下,四十余载矣,又有二暴君之狠毒以间之,人皆惴惴焉旦夕之不保,而茸靡图全之习已成。”[13]就嘲谑而言,高门大族如谢庄者劝人和光同尘。朝廷中不善此道者,也会成为异端的存在。刘德愿之流,则干脆变士人的高傲为下位者的谄媚。同时,面对嘲谑的态度,也可略窥士人的思想。如江智渊虽然面对孝武帝的嘲谑只能伏地而泣,但他的哭泣却是因为其父亲的名讳被人提及,这还是世族重孝轻忠观念的体现。袁淑曾被顾恺之驳斥“以忠义笑人”, 《诽谐文》十卷也自他的手笔,然而就是他在刘邵叛乱时宁死也不附逆,恰是士人忠君思想的表现,最终他的谥号为“忠宪公”。总之,高傲与谄媚、坚守与通变在刘宋士人的生活中可以是一种矛盾的共生。
其次,这种矛盾共生的状态,也是刘宋人的一种存在方式或生存智慧,并通过嘲谑折射出来。刘宋一朝,父子相残、叔侄攻伐、兄弟交征,所谓的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只是一个笑话,刘宋宗室只剩还没有来得及发出“只恨生在帝王家”的悲号。自以为得计的始兴王刘浚叛乱身死,宋明帝生存的秘诀则是“每以笑调佞谀”免祸。经常受戏弄的刘义綦也安然活了下来,想必能诚恳的接受别人的嘲谑,并做到恰如其分地配合的人,应该不是真正的庸劣粗疏之辈。刘义綦死后的谥号为“僖侯”。据《逸周书·谥法解》的解释:“小心畏忌曰僖”。宗室如此,士人也自有其生存的智慧。把忧愤化为嘲哂,用幽默消解苦闷,是一种自我调解与超脱的方式。把生活用嬉笑进行调侃,用佯狂来面对世人,玩世不恭的背后是一种生存方式。受益于庄子的魏晋士人的谐趣,在此时成了很好的取容工具。颜延之和谢庄的相互嘲讽,看似是文人相轻,但只要想想宋文帝本人“好为文章”,而“自谓物莫能及”的性格,就知道颜谢二人的问答实在是充满了智慧。要知道恃才傲物的谢灵运就死在宋文帝手里,元嘉三大家之一的鲍照也被迫“为文多鄙言累句”[3]1480。在宋孝武帝时,谢庄便曾警告沈怀文“每与人异,亦何可久”。不好嘲谑嬉戏的沈怀文果然被谢庄一语成谶。
最后,嘲谑也体现了时代审美精神“尚俗”的一面。就现存的嘲谑作品来看,其创作目的大体可以分为娱乐和刺世这两个方面。刘宋之前,此风既笃。汉代王褒《僮约》,描写主人的苛薄,僮仆的的固执刁滑,诙谐可笑,实属游戏之文。汉乐府《战城南》:“且为客嚎,野死谅不葬,腐肉安能去子逃”之语,“以极诙谐的笔调写极沉痛的情绪”[14],贬刺战争的无道。至于竹林七贤的佯狂傲世,陶渊明的失意调侃,都亦谐亦刺,刺多于谐。而至刘宋,玄风消退,文学中重情思潮重新抬头。故通观此时调谑之作,大多纯为娱乐之文。如乔道元《与天公笺》所咏贫穷,流于插科打诨,与陶渊明咏贫诸作自有天壤之别。至于袁淑的一些作品,似有一定的社会指向,但游戏笔墨的意味更浓。甚至于鲍照也概莫能外。其《拟行路难》第九首:“结带与我言,死生好恶不相置。今日见我颜色衰,意中索寞与先异。还君金钗瑇瑁簪,不忍见之益愁思。”“还君金钗瑇瑁簪”一语化用了汉乐府《有所思》的句意。而“今日见我颜色衰,意中索寞与先异”的嗔怨与南朝民歌极为神似。然而正是这直白如话的语言,造成了诗歌诙谐生动的效果。所以,清人叶矫然引鲍诗中平直幽默之语云:“至其质而诙,直而转趣,则如‘今朝临水拔已尽,明日对镜复已盈’,‘君不见亡灵蒙享祀,何时倾杯竭壶罂’,‘结带与我言,死生好恶不相置。今日见我颜色衰,意中索寞与先异’,读之令人失笑,觉‘俊逸’二字,复不足以尽之。”[15]正指出了鲍照诗歌通俗直白、谐趣有味的一面,而这恰与刘宋文学中“俗”的倾向性以及重视文学作品的娱乐功能有关。
总之,一个时代的文化精神,不仅仅表现在重大的政治历史事件或者鸿篇巨著上,还体现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甚至细枝末节上。这些细枝末节的东西,往往因为参与主体的广泛性,反而更能成为一个时代的缩影。刘宋时期的嘲谑之风即是如此。透过它,我们不仅可以了解当时思想的混乱与复杂,而且对南朝的社会风俗、文化发展以及文学演进等也多了一个观测点。比如就文学的娱乐性来讲,在刘宋以后的南朝,继续影响到各种文学体裁,并在诗歌创作中发挥到了极致。与之相伴的,则是南朝士人纵情声色的生活态度。这说明,为人与为文存在相互影响与促进的关系,而其背后的动因则是人文精神的变化。
[1]杨明照.抱朴子外篇校笺(上)[M].北京:中华书局,1991:601.
[2]李延寿.南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5.
[3]沈约.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4]赵翼.廿二史劄记校证[M].王树民,校证.北京:中华书局,1984:238.
[5]钱穆.国史大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271.
[6]刘义庆.世说新语校笺[M].修订本.杨勇,校笺.北京:中华书局,2006:701.
[7]严可均.全宋文[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8]钱钟书.管锥编[M].北京:中华书局,1979:1331.
[9]罗伯尔·埃斯卡尔皮特.幽默[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115.
[10]谭家健.六朝诙谐文述略[J].中国文学研究,2001(3):18.
[11]魏征,等.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1089.
[12]刘师培.刘师培中古文学史论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92.
[13]王夫之.读通鉴论[M].北京:中华书局,1975:526.
[14]萧涤非.乐府的诙谐性[M]//萧涤非.萧涤非说乐府.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208.
[15]叶矫然.龙性堂诗话[M]//郭绍虞.清诗话续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964.
【责任编校杨明贵】

I206.2
A
1674-0092(2016)04-0019-05
10.16858/j.issn.1674-0092.2016.04.005
2016-03-01
李鹏,男,山东临沂人,临沂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魏晋南北朝文学和中国传统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