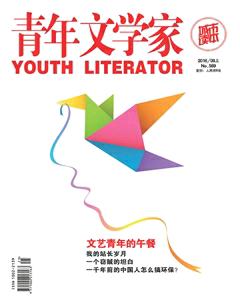敦煌,一个黄金时代的塑像
于坚


敦煌起天末,一色掩万颗。雪平沙不动,窟高释有课。
香火无消息,丹青细琢磨。游客不来了,仙人房间阔。
——《雪后蔼莫高窟》
前年秋天我来的时候,旅游团狂沙般地席卷敦煌,那些壁画几乎看不见。现在没几个人,守卫的士兵趁着阳光大好,坐在为游客准备的长椅上打瞌睡。尘嚣散去了,敦煌安静地露出来,洞窟前面的大河结了冰,沙漠被雪洗过,显得更为圣洁。敦煌只有两块:莫高窟以及包围着它的一切。包围者纯净神圣,没有杂质,大地的作品。被包围者幽暗深邃,五色绚烂,人的作品。
托朋友邵晓平的福,再进45窟,其间塑像温柔中正。比较之下,北魏的作品战战兢兢,太硬,宋的东西大约又自觉望尘莫及,偏于呆板。如果独立看的话,却都是第一流。佛的面容移步换景般地微妙变化,有时候看着是佛,有时候看着是俗人,有时候看着是母亲,有时候看着是父亲,有时候看着是爱人……不确定,前一步后一步、左右、蹲着站着感觉都不一样。庄严中正又不失温柔慈悲。身怀喜悦,身在欢喜,仿佛某种持久而纯净的做爱过程,只有持续宁静的快感,而没有丝毫邪念。不再是肉体的快感,而是精神的快感,但身体的魅力并没有消失,来自身体的直观就在眼前,令人着迷,恋恋不舍。敦煌色胆包天,无法无天的色,色就是空。色本是赞美诸神的,但色的极致超越了这个赞美,诸神成了色的载体,空明,超越了宗教的局限,共享成为无边际的。空无的在场导致阐释的激情,导致“六经注我”的“有”的万象。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也可以说成,道生敦煌(佛教),敦煌生造像(缘起),造像开眼(众生),众生如千手千眼观音,有万只眼。道是一,也是万千微妙。每个人都看见敦煌,但每个人看见的都难以言说、确认、定于一尊。只有置身于这个场中,才能心领神会,身心俱焚。敦煌是无法被复制的,那些画册永远只有介绍信的功能。
在275窟,朋友李坚蹲着看了很久,拿个电筒,一寸一寸地琢磨。邵晓平没了眼镜,凑得最近。北凉时代塑的菩萨。交腿而坐,穿着裙子。两边是狮子。令我感动至深,光芒微明、慈悲,确是伟大的作品。伟大得如此的健康、质朴、强壮、美妙、近人,如某种美女和力士合为一体的状态在阴阳之间微明,交替于人体最有魅力的部分,丰满圆润。一种被唤醒的最深刻的性欲,吸引着人最纯洁地去爱、去皈依。望着它,我无法自拔。这样的神态竟然被如此亲近地出现人面前,世界上的一切宗教奇迹都不足道了。它们太远,总是太远,总是在上面、总是有隔岸观火的距离。而这位菩萨即刻就进入到你的生命中,仿佛是你的梦坐在那里,你的喜悦、你的尺度、你的爱情,也坐在那里。凝神。他凝聚了神。神被凝聚在那泥巴中。这个窟有一种隐隐的源自西域的阿波罗精神,崇尚青春感、力量、精神高迈。
早期的作品还有青春气息。青春其实是拘束的,期待着解放,解放也难免乖戾、极端。而唐是伟大的成熟,是秋天中丰腴的大地。夏日已逝,但死亡还很遥远,还是生命最强大的时刻,最盛大的时刻。悲剧的黄金时代有自觉的内敛,丰满飘逸是内敛的结果,无论早期还晚唐,唐敦煌都不歌颂乖张夸饰的青春气象,绝不旁枝溢出,它是伟大的创造,但是到神态为止,诸神从来不是青春狷狂之辈。就是涅盘图上的神,也是中年。这不是年龄,而是精神的饱满,完美。
220窟。第一次进来,是贞观时代的场,壁画上明确地写着:贞观十六年(公元642年)环壁是一场欢乐颂。神在上面、中间,世界在下面、周围。匠人们创作中间的时候庄重,严谨,但在下面、周围的时候却很放松,做鬼脸,不似上面中间的诸神都有模式,样子,下面周围的世界画得更狂放、生动、野性,但随心所欲而不逾距。在同一场中,同时建构与解构着。建构与解构阴阳互补,彼此交替。这里的王不是佛陀,而是工匠自己的笔墨,世界与神明的距离,全掌握在他手心,他画得越登峰造极,世界与神的距离就越接近。欢乐颂,白天夜晚,鼓乐齐鸣,歌舞升平,神人同乐。但不是西方交响乐里面那种围绕着指挥棒的被组织起来的强力欢乐,而是天地神人各有其位,各得其乐的欢乐颂,不仅因为神的在场而乐,更因为欢乐在场而乐。帝王被画在一个角落里望着这一幕,惊呆啦!似乎在考虑是否退位。
天地神人的欢乐颂,是线条和色彩的狂欢。有个舞女,完全是王羲之的草书,云烟醉舞。隶书、篆书、草书、楷书、甚至涂鸦分布其间,但尊卑有序,这组线条是颜体般的丰厚庄重,那组线条泛着隶意,篆书的装饰味道,赵孟頫式的端庄清秀;这群线条有永和九年的曼妙,那群线条有怀素的迷狂。“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图中全是美人啊,佛陀、菩萨、侍女、僧众、供养人、无不是美人!女性化的线条,就是男性也是云般地的飘着,柔美丰满肥厚。
再进158窟。超越环抱着它的大漠,那个诞生它的春天早已过去,无数时代也被时间消灭,但它还在这里,慈悲的美,永恒的美。默视良久,无言。后来朱晓阳在昏暗中说,涅盘图也是《最后的晚餐》。然!达芬奇《最后的晚餐》是虚构的实景,气氛诡秘,黑暗的面容、写实的刀子、钱袋。不信任,怀疑,出卖、秘密的氛围,像某场悲剧的一幕。涅盘图是另一番景象,表现性的,突出的是一种精神力量,佛陀的巨大身躯和超凡脱俗的面容都是纯粹的虚构,但并不离奇,它只是超凡脱俗,但没有丧失与人间世的亲和力,那样巨大的身躯我们以为是自然而然的,那真是佛的身躯。神之离去也像安息的父母一样,闭目睡去,僧众像子女一样围着痛嚎。这是一个相当世俗的场面,如果不说是涅盘图,还以为是谁家慈母睡去。那睡去的神态是大漠的神态,灰色的神态。不是死亡,而是在喜悦中安祥地睡着了。死亡并不存在,佛睡在永恒的喜悦中。坐着,它是偶像,躺下来,是大地之身。
佛睡了,大漠醒着,这就是出色。
道法自然,就是向过去学习生活,向敦煌学习生活,向大漠学习生活,向兰州城里的一碗拉面学习生活、向沙漠上的一只秃鹰学习生活。生活不是创造,新生活并不存在,美好的生活世界总是对存在的再次领悟。它们存在着,我们才知道何谓生活。在往昔的时代,向历史学习生活的冠冕堂皇,谁也不会嘲笑玄奘,他的西天取经就是向过去学习生活呵!佛陀难道不是过去的神么,难道不是一种生活方式么?敦煌早期洞窟里的造像显示,这个大智者是赤脚的、浑身充满力量的壮硕男子,他的身体被赋予一种大地的质朴力量,他确实是赤着脚走在大地上传他的教的。只有过去中才存在着未来佛。普鲁斯特的写作可以视为向过去的学习,取经,是过去敞开了他的语言。语言存在于时间的黑暗里,光明中没有语言。尼采在某处说过,在自己的身上克服时代。他说得多好啊,克服自己身上的时代,就是要向过去学习生活,向酒神狄奥尼索斯学习生活。日神的光芒已经遮蔽了生活世界。
过去不仅仅是书本上的历史,而是一种生活方式,生活的细节。克服时代,就是要克服那种时代性的生活习性,克服它安装在自己身上的种种细节。这是一个连婚姻和妊娠也被革命过的时代。1957年,我的摇篮床被交出去炼了钢铁。1966年,我外祖母藏着的名贵字画被她自己亲手烧掉。我母亲的手指一生都没有戴过戒指,先是这种玩意被国家意识形态判为邪物,到1966年,中国婚姻中已经没有戒指,之后是这种玩意本身完全失踪了。我记得我父亲有一次为他单位的同事老罗主持过一场同志式的婚礼,唱革命歌曲,戴着大红花,其实这才是史无前例。在1966年以后,越境并不像“流亡”一词所意味得那么诗意而严重,也就是回到一只戒指而已。
这个时代泯灭细节的行径可谓浩瀚如沙,这种对日常生活世界的革命扫荡是在制造时代沙漠。许多知识分子在批判历史的时候总是喜欢那些耸人听闻的事件、数据,而在我看来,革命最深刻之处,乃是戒指、阳台、炮仗、汽锅鸡、毛笔、脂粉盒、烟斗、炮仗、拉面祭器配料……。敦煌其实就是过去时代的一只碗。那些不朽的画面其实是在告诉我们何谓生活。敦煌在它自己的时代不是梦,而是现实。敦煌在时间中成为梦想,这个梦想使我们知道何谓黄金时代,何谓的真正的生活。这是关于生活的伟大教科书。
出了洞窟,马云、陈恒还惦念着前年秋天在敦煌的集市上吃过的某碗油泼麺。我们就去找,那个大排档还在。当时,这个被锅烟子熏得黑乎乎的大棚里,人声鼎沸,到处火光闪闪,一张张汗水淋淋的光脊背在流着热光,啤酒瓶倒下一大片,走路不小心就人仰马翻。现在荒凉了,许多摊子回家过节还没有开业。他们立即认出了那位老板娘,老板娘受宠若惊,外地食客再找上门来恐怕不多。我则感觉不妙,过节都不打烊,大约不会好吃到哪里去。麺抬上来,味道一般。马云和陈恒很失望,这是两个不同的场合,前年,水涨船高,大棚里热火朝天,人满为患,恐怕是个摊子都是好吃的,现在么,水落石出。那本是一碗无心之面,只是为了赚个小钱。